HTML
-
1914年6月,在随汉斯·杜里舒、马克斯·韦伯和威廉·文德尔班等人学习过一段时间之后,赫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 Plessner, 1892-1985) 从海德堡来到哥廷根随胡塞尔学习,直至1916年2月。胡塞尔此时接受了弗莱堡大学的聘任,并于4月离开哥廷根。普莱斯纳无意效法英加尔登、施泰因、考夫曼等学生,继续随胡塞尔转到弗莱堡大学,而是与更多其他同学一起,中断了在胡塞尔身边的学业。他最后在埃尔兰根大学(1916年)和科隆大学(1920年)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考试和任教资格论文考试,并于1926年在科隆获得副教授的职位。由于带有犹太血统,普莱斯纳在纳粹执政期间不得不放弃教职并离开德国,先后滞留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以及执教于荷兰格罗宁根,并且在二战期间藏匿于荷兰乌得勒支和阿姆斯特丹。二战后他回到德国大学任教,最后任职于哥廷根大学,并曾担任一段时间的哥廷根大学校长。
在第一次去哥廷根随胡塞尔学习之前,普莱斯纳已经有了相当复杂的科学与哲学的学术背景。他于1910年开始在弗莱堡大学学习生理学,两个学期后到海德堡随库尔特·海尔普斯特(Kurt Herbst)和汉斯·杜里舒①等学习医学和动物学,同时也随文德尔班、韦伯等人学习哲学、社会学等。
① 杜里舒(Hans Driesch, 1867-1941) 是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机能论哲学的倡导者。他于1920年应梁启超等人组织成立的“讲学社”的邀请来中国讲学。他的中国之行的起因以及他与胡塞尔的交集可以参见笔者《胡塞尔的未竟中国行——以及他与奥伊肯父子及杜里舒的关系》,载于《现代哲学》2015年第1期。
普莱斯纳对他与胡塞尔当时见面的情况以及后面的背景回忆说:
以有所保留的方式并且带着适当减弱的夸赞,我有幸作为西南德意志阵营的又一先锋而受到了欢迎,这个状况对于一位大学生来说毕竟还是不同寻常的,而其中的原因在于,他不是空手而来,而是带着一本真正的、1913年在海德堡的C.温特[出版社]出版的书,尽管我并未将它作为文德尔班愿意接受的那种博士论文来撰写和提交。显然,《科学的观念》产生于杜里舒的观念圈,而非海德堡学派的观念圈,但这一点无论对于文德尔班还是胡塞尔都是无关紧要的。
文德尔班在我递交该书时向我提出的建议让我十分吃惊,这个建议促使我中断了已经相当成熟的在动物学博士论文方面的工作——完全违背了我的老师C.赫普斯特的忠告——并且使我全身心地陷入到对博士考试的准备之中。半年的时间就足以让我放弃计划并使我明白自己在专业上是多么缺乏训练。当我心情沉重地向文德尔班报告,我决定到哥廷根去在胡塞尔指导下进行训练时,他有些吃惊并且对我如此这般的幼稚报以微笑,但他还是不无宽容地允准我离去,并祝愿我在“现象学家”那里一切顺利。他并未因为此事而对我耿耿于怀。当时海德堡的人对胡塞尔并不看好。胡塞尔只是让拉斯克感①到不安,因为拉斯克在其哲学逻辑学的研究中开始对新康德主义处理先天问题的方式抱以怀疑。[1]29
① 埃米尔·拉斯克(Emil Lask, 1875-1915) 是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的学生,新康德主义西南德意志学派的重要代表,先后在海德堡大学任私人讲师和副教授。1915年在一次大战中阵亡。
要想清楚地了解普莱斯纳在这里所做的对自己学习生涯的有所省略的叙述,还需要对它做一个大致的梳理并加入一些补充说明:还在海德堡大学读书期间,普莱斯纳便已在海德堡大学的C.温特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一本论著《科学的观念:关于它的形式的一个设想》(Die wissenschaftliche Idee, ein Entwurfüber ihre Form)。这本书按普莱斯纳自己在这里的说法“产生于杜里舒的观念圈,而非海德堡学派的观念圈”。他本来已经准备在其动物学方面的博士导师海尔普斯特(Kurt Herbst)指导下撰写动物学博士论文,而且论文“已经相当成熟”,但在他给文德尔班看了其已出版论著《科学的观念》之后,文德尔班主动向他建议以这部论著的一个部分来做博士论文。于是普莱斯纳中断了他的动物学博士论文,全力准备在文德尔班这里完成哲学博士论文。但正如这里所引述的那样,“半年的时间就足以让我放弃计划并使我明白自己在专业上是多么缺乏训练”。他最后决定放弃在海德堡的文德尔班那里的博士考试计划,去哥廷根随胡塞尔学习。
这里还可以参考普莱斯纳在其“自传”中给出的类似叙述:
[文德尔班的]这个慷慨提议让我伤透了脑筋,因为我不想将我的动物学研究弃之不顾,而且我对哲学史一无所知。我请求给我考虑的时间,但随后便抱着对文德尔班之善意的信任而端出了我的建议:我还是去哥廷根胡塞尔那里,因为我的研究本质上依据于他。场景如下:“如果您认为可以从那个现象学家那里学到什么的话。”我的父亲仔细地关注着我的这种无礼。[2]16
然而,一位认真的读者在这里肯定会提出疑问:即使普莱斯纳如其所说在半年之后了解到自己缺乏哲学史训练,那么他为何不继续做他的生物学博士论文,而是中断了海德堡的学业,去了哥廷根胡塞尔那里呢?如今看来,普莱斯纳所做的这些叙述和回忆显然是有所隐瞒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杜里舒于1914年7月3日致胡塞尔的信中了解到。它对在普莱斯纳后来的自传与回忆中未给明的背景原因做了如下的客观交代。普莱斯纳曾在1913年出版了他的处女作之后寄赠给了胡塞尔一本。在去哥廷根拜访过胡塞尔之前或之后,他也请杜里舒写信给胡塞尔,探询后者的基本态度,即是否有可能用他在文德尔班那里提交的文稿到哥廷根大学胡塞尔这里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接下来便可以理解杜里舒在给胡塞尔的信中所述:
请您允许我在下面为了我的一个年轻朋友和学生的事情而给您写几句话。这个事情关系到来自威斯巴登的赫尔穆特·普莱斯纳先生,他曾在大约一年前给您寄过一本题为《科学的观念》的论著。
普莱斯纳在1913/14年冬季与文德尔班讨论过这部论著,后者表示愿意将它的一个部分即中间的三分之一作为博士论文接受下来,只需再写一个简短的引论加上去。但现在看起来,文德尔班当时根本没有较为仔细地读过这部论著,因为当普莱斯纳今年夏初将博士论文稿本私下交给他后,他将它搁置了两个月,而后才如此顾虑重重地对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以至于普莱斯纳无法再考虑在这里正式地递交这个文稿。
普莱斯纳首先是受了您的影响;他1911年来这里时已经读过您的《逻辑研究》之大部;其次他受到我的《秩序学说》和《逻辑学作为任务》的影响[3-4]。文德尔班现在根本不喜欢现象学,也不喜欢所有新的东西(包括李凯尔特的学说);因此才有他的拒绝的态度。
今天普莱斯纳请我在您这里询问一下,您原则上是否会倾向于对他论文进行考试。如果您倾向于此,那么他很快会带着他的论文来向您做自我介绍。此外,是文德尔班自己建议他来找您的。
我还要说明一点:普莱斯纳完全独立地撰写了他的《科学的观念》。在它完成之前,我既未看过文稿,也未看过清样。[5]57-58
从杜里舒这里的陈述可以看出,他这里的说法在许多方面有别于普莱斯纳的说法。例如,究竟是如普莱斯纳所说,他拒绝了文德尔班的慷慨提议并告知自己已放弃在他那里的计划而准备去哥廷根随胡塞尔学习现象学;还是如杜里舒所说,文德尔班开始建议,但最终又拒绝了普莱斯纳的申请,并亲自建议普莱斯纳去胡塞尔那里。再如,究竟是普莱斯纳在1914年6月拜访过胡塞尔之后才请杜里舒写信询问,还是在杜里舒在同年7月3日写信给了胡塞尔之后才去哥廷根拜访胡塞尔,诸如此类。
无论如何,在普莱斯纳简略而平淡的陈述后面很可能隐藏了一定的无奈与辛酸:由于文德尔班当时是海德堡大学的哲学讲席教授,因而他的不认可也就差不多意味着普莱斯纳无法在哲学系完成其博士考试,包括在受文德尔班之聘任职于海德堡大学的副教授杜里舒那里。然而普莱斯纳为何在中断半年之后没有再转回动物学,继续他那“已经相当成熟的”博士论文研究,对此普莱斯纳在其自传与回忆中均未作出说明。可以确定的仅仅是,他开始寻求在其他学校进行哲学博士答辩的可能。这便是他1914年6月到哥廷根探访胡塞尔的缘由。
但胡塞尔在同年7月9日给杜里舒的回信中给明了一种拒绝的态度:“可惜普莱斯纳的论著不符合我们院系的要求,因为它的基本核心(50个印张)是从一部已经发表的著述中,即从《科学的观念》中提取的。这是普莱斯纳先生自己告诉我的。因而我必须将这部论著再寄还给他。”[6]59
这也就意味着,普莱斯纳无法立即在哥廷根胡塞尔这里用已有的博士论文计划申请博士答辩,而是需要重新准备一份博士论文。很可能是按照胡塞尔对一般学生的要求,普莱斯纳需要在他身边听几年的课,然后再开始撰写现象学方面的论文①。因而普莱斯纳于1914年冬季学期到哥廷根开始随胡塞尔学习现象学。关于新的博士论文的论题,普莱斯纳回忆说:“刚好他[胡塞尔]的《观念》于1913年出版,它使我产生勇气对它的自我概念与费希特的自我概念进行比较。胡塞尔同意了。”[2]17但这个选题仍然是普莱斯纳为了方便博士考试而选择的应景之作,后来它也成为他没有继续跟随胡塞尔去弗莱堡的理由:“我不想跟他去弗莱堡,因为我的康德研究既让我远离现象学,也让我远离费希特。”[2]19
① 参见施泰因基于亲身经历的说法:“他[胡塞尔]已经习惯于人们在敢于进行独立研究之前先在他那里听几年课。”[7]218
-
的确,普莱斯纳来哥廷根在胡塞尔名下的学习从一开始就有些勉为其难,而且他后来在哥廷根随胡塞尔学习的时间实际上也不长。如果他的确是于1914年6月来到哥廷根面见胡塞尔,那么这月底便发生了斐迪南大公夫妇遭到枪杀的萨拉热窝事件。7月德奥宣战,随后各个学校的课程都停止。普莱斯纳实际上是到冬季学期恢复开课之后才在胡塞尔的课上出现。在胡塞尔1916年4月离开哥廷根之前,他随胡塞尔学习的时间实际上不到三个学期。后来胡塞尔应聘去了弗莱堡,他并未随胡塞尔同行,而是随即也离开哥廷根转致埃尔兰根,在文德尔班的学生保尔·亨瑟尔(Paul Hensel)那里递交了他的哲学博士论文《开端上的超越论真理的危机》(Krisis der transzendentalen Wahrheit im Anfang),并于1916年12月在亨瑟尔的名下完成博士考试。该论文于1918年出版。
这也就意味着,在1911年到1916年的五年时间里,普莱斯纳曾有过四位博士导师,并计划撰写过四篇博士论文,但实际上他最终的博士论文没有经过任何一位博士导师的真正指导。所有这些情况,既可以视作使普莱斯纳成为如其自称的“并不忠于胡塞尔的学生①”的原因,也可以视作其结果。
① 除了这篇1959年的文字外,普莱斯纳此前还在1938年发表过悼念胡塞尔的文章《现象学:埃德蒙德·胡塞尔(1859-1938) 的事业》,此后还在1975年的《哲学自述》中写过他在哥廷根时期的简短回忆。对此可以参见:Helmuth Plessner, “Phänomenologie: Das Werk Edmund Husserls(1859-1938)”, in Helmuth Plessner, Zwischen Philosophie und Gesellschaft. Ausgewählte Abhandlungen und Vorträg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9, S. 43-66, 以及“Selbstdarstellung”, in Ludwig J. Pongratz (Hrsg.), Philosophie in Selbstdarstellungen I,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75, S. 274-276.
虽然普莱斯纳频繁更换导师和学校,但他仍然成功地做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获得他的哲学博士学位。因此,可以理解埃迪·施泰因在普莱斯纳于冬季学期1914年6月②到达哥廷根后对他的第一印象:他“是以哲学为专业的,而且目标明确地驶向学院的职业生涯”[7]253。这个印象的确是敏锐而准确的。当然,我们后面将会发现,这里的“哲学专业”不能做狭义的理解。
② 参见普莱斯纳的回忆文字《于哥廷根时期在胡塞尔身边》:“1914年6月,我身着礼服、头戴礼帽去造访这位尊者,当时这也是一个大学生应做的事情。”[1]30
普莱斯纳的这个策略虽然帮助他获得了短期的利益,但后来他也不得不为此付出长期的代价:他为随后的任教资格论文花费了更多的时间,而且为等待正式教职花费的时间也相对较长,尽管他在获得正式教职之前发表的成果甚丰。在此问题上,施普伦戴尔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与评论,即便他对普莱斯纳与文德尔班和胡塞尔之间曾有的关系并不了解:“可以猜测,在声名远扬的哲学家文德尔班和胡塞尔那里进行博士考试显然会更有可能促进他的学院前程。普莱斯纳为何没有‘将这些机会转变为发生事件’,原因还不得而知。而有一点是确定的:保尔·亨瑟尔被行内人看作是一位亲切可爱的、有教养的、追求其个人兴趣的哲学行外人,而他个人则被视作‘柏林犹太贵族的高贵与才智的体现’。在他这里做博士考试或许是愉快的,但它导向的首先是学院的无人区。”[8]87
其实只要了解前面提到的背景,那么这里的“不得而知的原因”是很容易推断出来的:无论在文德尔班还是在胡塞尔那里,普莱斯纳都需要为博士考试付出多年的努力,这是他不愿意踏上的一条相对漫长的道路,而他最终宁可选择了方便的捷径。他在其自传中曾提到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作为职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对他的影响[2]17。韦伯在这里所说的“Beruf”(职业)首先要做“Berufung”解,即精神方面的“召唤”“天职”,或“志业”。但在普莱斯纳这里,表现得更为明显的是学术之为“Beruf”的另一个更为通常的含义,即物质方面的“职业”。因此,从上述背景交代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普莱斯纳之所以到哥廷根随胡塞尔学习,原因实际上并非如他在关于胡塞尔的回忆文字中所说:他不想再坚持德国的新康德主义传统,并从现象学那里看到了突破传统哲学的可能性。
普莱斯纳在这篇“更多是谈论自己”[1]29的回忆文字中就自己对当时哲学形势的看法以及对现象学的理解曾做过如下的回忆:
哲学的处境对于一个初学者而言当然要显得简单一些。他觉得观念论的传统在本质上已经完结,并且已经被认识论纲领向它突显出来的那些具体科学所超出。对于在自然与历史中不断递增的经验财富而言,哲学向意识的客体化作用的回溯已经丧失了驱动力。生物学的或历史学的思考者会随这种理论而遭遇最大的困难,因为人连同其意识首先是一个发展的产物,而后借助于其摆脱了优先于经验领域的意识,重又成为这个发展的缔造者。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已经对此有所思考,但他们当时在学院哲学中并未受到重视,而这些都于事无济,尤其是思辨体系看起来早已遭到了经验研究者的反驳。
反抗精神在为自己寻找根据,但并未在这些根据上燃放自己。我们当时想要从被传授的那些堆积如山的知识老套中突破出来,并且抛弃那些妨碍我们看到开放可能性的颓废无力之累赘。如其所是地看世界,简单而直接,不带成见和理论,以自然科学家的方式,他们只在自己与事物之间放置一个问题,而不会在文献的群山下窒息。这曾是实证主义者们的纲领,但他们失之于感觉主义的成见。迈农的对象理论作为认识论的对应项又让人觉得过于狭隘。莱姆克看起来在其基础科学中虽有种种努力却仍然过于束缚在传统上。在所有反叛传统的哲学家中似乎只有一个人成功完成了突破:胡塞尔。
撇开所有理论而“面向实事”的口号当时对于专业内的年轻人所起的作用必定与十九世纪中期外光绘画对于学院派所起的作用相似。它在方法上已经一并包含了对素朴的、前科学的世界观的平反,并且因此而像实证科学那样与日常生活的态度相衔接。可以“自由地”哲思,并因此而可以“首先”撇开一切至此为止就论题已说过的东西,这就相当于发现。因为,当我们忙于某事时,被我们始终视而不见、置之脑后的恰恰是我们日常活动的自明性地带。除了处在类似从熟睡中醒来时那样的临界情况,没有人会对此感到吃惊,即:有“事物”围绕在他周围,他可以前进、侧行和回退,有他和这整个多彩的世界存在[1]30。
这里表达的对现象学的看法不太像是普莱斯纳当时就有的理解,而更像是在学习多年后得出的体会。除了“撇开所有理论而‘面向实事’的口号”——这可能就是杜里舒所说的胡塞尔对普莱斯纳“首要影响”的内涵所在——之外,普莱斯纳的这个现象学理解更多是与舍勒的而非胡塞尔的现象学立场相一致。对于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普莱斯纳一开始便有一个消极的印象:“一门束缚在意识视域中的哲学看起来无法胜任这个动荡不已的时代。它的深思熟虑连同其作为阿基米德关系点的自我太像是已经过气的十九世纪的各种观念论。”[1]35而对于普莱斯纳在哥廷根初期的学习,他的师姐施泰因也曾留下一段有趣的回忆:“我时而也在大学之外与他[普莱斯纳]在一起……当普莱斯纳先生从城中心的老市民住宅中出来陪我回席勒街时,他会向我阐述他的‘体系’,并且向我解释,他在哪几点上无法与胡塞尔同行;但他并未恰当地将自己的意思说清楚。”[7]253
从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普莱斯纳在他学习的一开始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同时对胡塞尔的现象学持有怀疑与批判的态度。如果胡塞尔还记得这个学生,他在回忆或评价时一定会像他就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也就普莱斯纳感叹说:“可惜决定了他的哲学教育的并不是我。”[9]234不过胡塞尔很可能并没有记住普莱斯纳。在胡塞尔的十卷本《书信集》中,普莱斯纳的名字仅出现在上述这两封信中。而在《胡塞尔年谱》中,与普莱斯纳相关的信息仅有他在哥廷根参加胡塞尔1914/15年冬季学期、1915年夏季学期和1915/16年冬季学期的三次听课记载,且都来自普莱斯纳自己的回忆录。
-
与英加尔登一样,普莱斯纳也曾写下了关于胡塞尔的授课和私人交谈情况的回忆文字:
关于胡塞尔的授课情况:
胡塞尔过多地是一个自言自语者,因而按照通行的看法并不是一个好讲师。他不具备任何历史感。他的关于哲学史的大讲座所遵循的是宇伯维克-海因泽①,并且将整个哲学史叙述为一个尝试走向现象学的序列,而且是一个由于急躁和体系的欲望而一再失败之尝试的序列。即使在以费希特的《人的使命》、休谟为基础的和以“自然与精神”为系统标题的讨论课上,受到讨论的也只是具体的实事问题,而非整体的关联,甚至也不讨论作者与文本的历史。今天人们会将此称作范式课程(paradigmatischer Unterricht),但从根本上说则不是范式课程,而只是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学显微镜检测的案例。这里没有什么被诠释,人们横穿过文本,并且拿某个东西用作导向独立思义(Besinnung)的纯粹契机。在手中旋转的铅笔之费解性的引导下,人们突然陷入到映射(Abschattung)以及背面的现象中,或者,舒尔特-悌格斯小姐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光荣的任务:描述在她坐着时所体验到的处身情态(Befindlichkeit)。我无法想象这一小群未来的教师候选人究竟会从中获益多少,但只要知道胡塞尔是什么并且想要什么,就不可能不注意到他的严肃工作态度。[1]34
① 这里指的是由宇伯维克(Friedrich Überweg, 1835-1909) 所撰、海因泽(Max Heinze, 1835-1909) 所编的多卷本哲学史著作《哲学史纲要》(Überweg-Heinze, 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关于胡塞尔与他人交流的情况:
胡塞尔显然很难置身于他人的思路之中。虽然他觉得我试图将《观念》之自我概念与费希特之自我概念进行比较的博士论文计划很好,但他对此无法提供建议。缺少了已被证实为善解人意的中介者莱纳赫。1914年9月,在我的哥廷根学习生涯之初,我在同学圈里还遇到英加尔登,只有一天,他给了我几个上路的暗示。我应当只在老师面前陈述我的东西。我有规律地进行此事,每隔一段不长的时间于早晨9点去胡塞尔那里,并在旧式的黑沙发上就座。在书桌上方可以看到面向城市的大窗户的光亮。淡淡的烟雾向来访者透露出房屋主人清晨的工作强度,他坐在我对面的左边,并且极为友善地请我报告。不到五分钟胡塞尔便会打断。某个语词在他那里引发了一系列的想法,他开始演讲,常常依据他从存放在书桌里的大堆手稿中取出的札记。我并不容易跟随那些细致入微的描述,常常会失去线索,被他带有奥地利-摩拉维亚腔调的,斟酌且从容的声音迷惑住了。通向费希特诸精神丰碑的桥梁没有展示出来。直至十二点半,我被仁慈地允准离去:“您就这样继续做吧。”[1]33
在这份关于胡塞尔的回忆文字中所描述的胡塞尔负面形象要多于其正面形象。但从一个如他自己自称的“并不忠于胡塞尔的学生”的角度来观察胡塞尔也有其特别之处。它与笔者在关于胡塞尔与英加尔登关系的论述中引述的英加尔登的相应回忆正好形成对照。笔者在其中也引述了英加尔登“关于胡塞尔的讲座的情况”“关于胡塞尔主持的讨论课”和“关于胡塞尔与他人的谈话时的情况以及他独自工作时的情况”三个方面的回忆和描述②。普莱斯纳与英加尔登的回忆和描述都是真实的事实,但视角不同,解释和评价也不一。
② 参见笔者的待刊论文《胡塞尔与英加尔登——兼论现象学本质论、现象学美学的形成与发展》。
看起来普莱斯纳从胡塞尔那里学到的东西并不多,而且在许多方面,普莱斯纳自然科学的生物学教育背景使得他从一开始就对胡塞尔的现象学持有保留和批评的态度,而后在他逐步形成的基本哲学立场上,他的哲学人类学与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越来越处在“正相对立”的位置上。普莱斯纳从未认同过胡塞尔对科学做最终论证和奠基的想法,如布瑞耶尔所说:“胡塞尔试图将整个哲学并随之而将所有科学都建立在一个新的、方法上可靠的基础上,普莱斯纳接受了所有科学的认识并将它们加工成为一个新的、一体化的起点,它避开了超越论分析与经验分析的两分。”[10]4如果说普莱斯纳对胡塞尔的观念论现象学有所接受和继承的话,那么这至少是在意识的意向性和先天本质方面。当然这两个方面也是舍勒所赞同的。而在舍勒与胡塞尔的分歧中,普莱斯纳基本上会站在舍勒一边,“他参与舍勒对胡塞尔观念论倾向的批评,即从一种原奠基的意识领域出发来说明所有现象的构造、也包括人类意识现象的构造”[10]2。看起来他是在反对笛卡尔以来的主体性哲学以及胡塞尔对它的复活尝试。但笛卡尔的动机仅仅是在胡塞尔哲学中得到彰显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在普莱斯纳曾于哥廷根听过的胡塞尔“自然与精神”关于胡塞尔在“自然与精神”①的讲座中,还包含着另外一个规定着胡塞尔后期思想的方面。
① 标题下所做的相关思考,可以参见笔者的文章《纵横意向——关于胡塞尔一生从自然、逻辑之维到精神、历史之维的思想道路的再反思》,载于《现代哲学》2013年第4期,第52-58页。
普莱斯纳自己曾提到在人类精神史上为希腊哲学所特有的,而后被西方哲学并不完全成功地继承下来的双重方向:“人类精神向着哲学的独立做了三次腾飞:在中国、在印度和在希腊。但唯有希腊人才因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特殊宗教和政治境域而成功地赋予关于总体世界的思想以一个双重的方向:其一是朝向对象之物的方向,其二是朝向起源之物的方向。”[11]176前者也被他称作“对象性的世界观察”的方向,后者则被他称为“起源性的生活观察”的方向。在这里,普莱斯纳已经看到了上述从希腊哲学开始直至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当代西方哲学传统遗产,并以此方式对其加以维续和传递。这是在普莱斯纳那里尚存的一些哲学的东西。他在这个说法中表达出的哲学理解十分精辟,实际上相当于至此为止对人类在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方面双重努力的概括。古希腊哲学中“对象性的世界观察”与“起源性的生活观察”之双重方向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是通过巴门尼德斯和赫拉克利特的双重哲学立场而得到宣示,在近代西方哲学中则是通过笛卡尔―康德―胡塞尔与黑格尔―狄尔泰―海德格尔的双重动机而得到体现②。
② 但普莱斯纳认为哲学的独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印度的另外两次腾飞中都没有“成功地赋予关于总体世界的思想以一个双重的方向”。这个论断下得过于仓促,应当是出于他对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思想的无知或不解。在古代中国的《易经》《老子》与《论语》《孟子》中已经可以找到这两个方向上的丰富思考。而在古代印度,仅在佛教思想中,缘起论和实相论的相关思想就已经可以代表这两个方向上的成熟思考。。
-
尽管普莱斯纳看到,纳托尔普的(首先也是狄尔泰的)意义上的精神科学只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短命的配对”[1]29,但他仍然在这个方向上再次尝试对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进行综合,而他的出发点与他的教育背景一样,更多在于自然科学:人类学首先以自然科学、关于有机物的科学为出发点:“没有人的哲学也就没有精神科学中的人的生活经验的理论。没有自然哲学也就没有人的哲学。”[12]26在这个奠基顺序上,普莱斯纳的哲学思想比舍勒的少了超验的部分,多了经验的部分。
的确,如果普莱斯纳还被视作带有现象学烙印的社会学家或哲学人类学家,那么这大多是因为舍勒的影响。从各方面看,普莱斯纳都更多是舍勒的学生而非胡塞尔的学生③。如果说他曾受到“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的影响,那么很大部分也是在此意义上言之。当然更多的舍勒影响是来自其哲学人类学的思想方面。这是因为普莱斯纳后来到了科隆,于1920年在这里以《哲学判断力批判研究》(Untersuchungen zu einer Kritik der philosophischen Urteilskraft)为题完成了任教资格考试,而后于1926年在科隆获得副教授的职位。在此期间,舍勒也于1921/1922冬季学期获得科隆大学的教授职位,并于1925年在这里首次开设了关于“哲学人类学纲要”的讲座。普莱斯纳在科隆期间所受的舍勒影响一方面与情感现象学的分析与研究有关,另一方面与哲学人类学的构想和展开有关[13]13。他的《诸感官的统一:一门精神麻醉学的纲要》(Die Einheit der Sinne: Grundlinien einer Ästhesiologie des Geistes)以及代表作《有机体的诸阶段与人:哲学人类学引论》(Die Stufen des Organischen und der Menschen.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都是在这个时期他所身处的舍勒作用圈中完成的。
③ 对此还可以参见普莱斯纳为舍勒撰写的悼念文字:H. Plessner, “Erinnerung an Max Scheler”, in Paul Good (Hrsg.), Max Scheler im Gegenwartsgeschehen der Philosophie, Bern und München: Francke Verlag, 1975, S.17-27.
舍勒之于普莱斯纳,类似胡塞尔之于英加尔登、施泰因、芬克,以及海德格尔之于伽达默尔。可以说,在普莱斯纳学习生涯中,他所受到的影响按时间顺序依次来自杜里舒、韦伯、文德尔班、胡塞尔、舍勒。
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舍勒、普莱斯纳和盖伦共同完成了哲学人类学的学科创立:“舍勒的最后工作是写了一篇纲要式的论文,题目是《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这篇文章实际上提出了人类学的纲要。他开拓了一个新大陆,这片新大陆刚一发现,就有一位叫赫尔穆特·普勒斯纳的研究者跟进,后来又有阿诺德·盖伦迈出了自己的步伐。”[14]76
普莱斯纳后来成为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哲学人类学家和社会哲学家。尽管他在哲学界的影响并不很大,但眼下世界哲学的发展路线的确与他多年前就采纳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哲学越来越多地从形而上学走向哲学人类学。这个走向在接下来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是否会干脆丢掉“哲学的”定语累赘,成为纯粹的人类学,目前还不得而知。实际上,当“哲学”不再是名词,而已成为一个修饰词时,它就已经是可有可无的了。
由于哲学人类学是从现象学运动内部发展出来的一个思潮,而且如今成为一个可以说是后现象学的学科,因而还在30年代初(1931年)便首先受到胡塞尔的批评,并且在后来的近30年时间里(1938-1964年)也一再受到海德格尔的批评。
胡塞尔在世时便曾在“现象学与人类学”的标题下抨击过在哲学人类学中表露出的人类主义和相对主义思想取向,主要是针对舍勒的哲学人类学,但也将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海德格尔生存哲学的思想归入这个潮流:“近十年来,在德国较年轻的哲学一代人中可以看到一种急速增长的哲学人类学倾向……所谓的现象学运动也受到这个新趋向的侵袭。据说哲学的真正基础仅仅是在人之中,而且是在其具体-世俗的此在的本质论中”,胡塞尔呼吁“在人类主义和超越论主义之间做出原则性决断”,即做出“凌驾于哲学和人类学或心理学的所有历史形态之上的原则性决断”[15]164①
① 而在此前于1929年7、8月期间阅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过程中,胡塞尔也在书中写下这样的评论:“海德格尔将构造-现象学对存在者与普全者的所有区域、总体的世界区域的澄清加以变调或变韵(transponiert oder transversiert),使它们成为人类学的东西;整个问题域都是改写(Übertragung),与本我相应的是此在,如此等等。在这里,一切都变得深邃式的含糊,而它在哲学上失去了价值。”[16]13。
在海德格尔方面,他对哲学人类学的发展趋向也早有关注,他于1938年所做的以下论断几乎就是专门针对舍勒和普莱斯纳的:“在业已终结的形而上学之时代中的哲学就是人类学。是否要特意地说‘哲学的’人类学,这是大同小异的。在此期间哲学已经成为了人类学,并以这种方式成为形而上学之衍生物的战利品,形而上学在这里是最宽泛意义上的物理学,它包括了生活的和人的物理学、生物学与心理学。一旦成为人类学,哲学本身便在形而上学方面走向毁灭。”[17]85当然,哲学的“毁灭”、哲学被逐入“人类学”,抑或形而上学的“被克服”[18]34,39,70,诸如此类的说法在海德格尔那里并非是完全的贬义词,它同时也意味着新的开端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在此期间一再谈论的“第一开端”和“另一开端”以及在此之后谈论的“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都意味着在不同名义下的“哲学”之重生的可能性。
从现象学到哲学人类学的发展是1900年《逻辑研究》发表以来的胡塞尔现象学和随之形成的现象学运动的一个主要展开方向。这个方向是带有舍勒、普莱斯纳思想踪迹的。另一个方向则带有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思想踪迹:从现象学到解释学的发展方向。这两个方向应当可以视作纯粹现象学的哲学理论最终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中的具体实践成就,它们后来还在法国现象学哲学的发展中得到进一步的接受与充实。
就人类学的发展方向而言,普莱斯纳在其《有机体的诸阶段与人》第二版前言中就已经发现,在萨特和梅洛-庞蒂那里可以发现有与自己的表述完全一致的东西[12]34。而前面曾引述的布瑞耶尔的《普莱斯纳与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的论文,就是在“交互主体性人类学”标题下实施的一个研究计划,而且在这里还提到了“现象学的人类学”的设想,在与“身体现象学”的关联中,它还可以继续伸展到“神经哲学”“有机体的现象学”等方面[10]16。
除此之外,还可以特别关注近年来新出版的现象学家的文献,老一辈的例如E.图根特哈特的《以人类学取代形而上学》[19];新一代的例如A.施奈儿的《出去:关于一门现象学的形而上学和人类学的种种构想》[20]。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现象学的人类学的发展势头甚至要强于现象学的解释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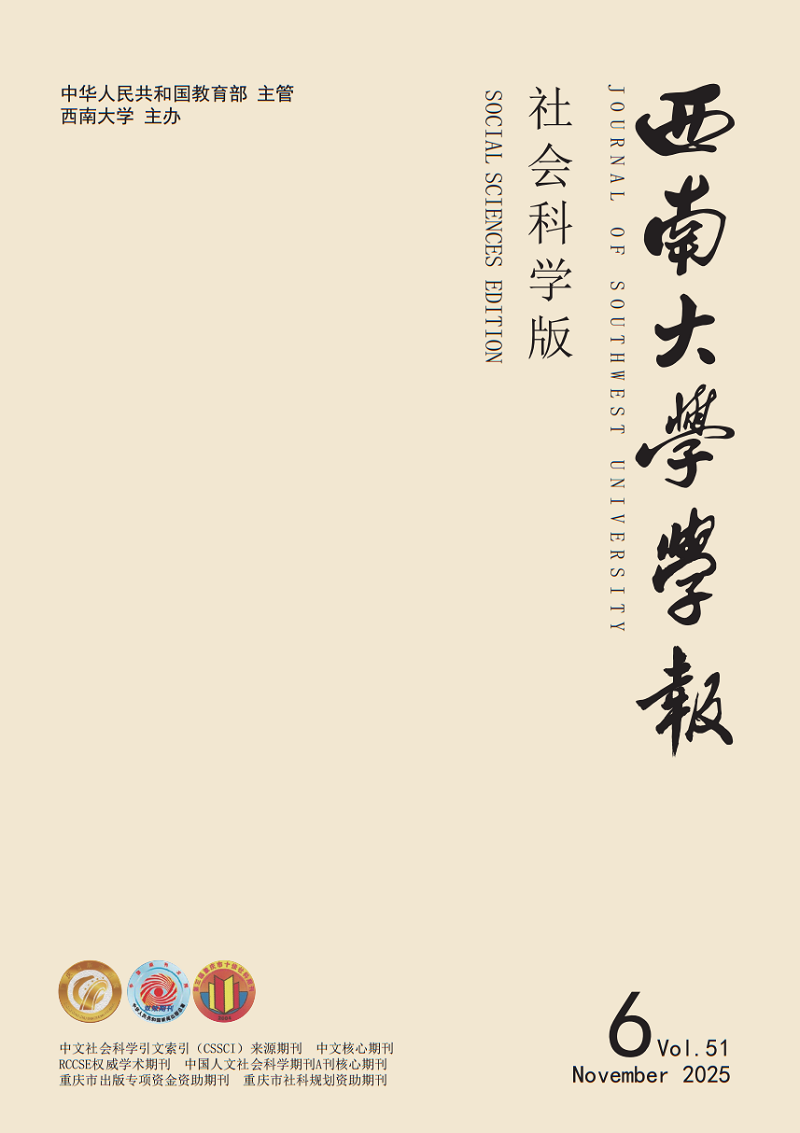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