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古代职官制度研究中,对于职官职掌的研究是学界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通常是根据相关典章记载,结合史料对某一职官的职能条分缕析地研究。从常理判断,若官员单独任职某职事官,其职能即以此为主,而是否有兼任官及其兼任何官何职则是官员本身职权的关联性问题。本文拟从某一职官同时兼任其他职官的视角来做剖析,这样可以从新的视角来完善对其职能的分析①。
①古代朝官除了本部门职能范畴内的权责外,还有相关的一些工作,比如参加朝参决策、百官大会决策等。参见: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第七章《唐代外交决策制度》(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309页)。对于职官的职能进行专题细化研究为职官史的通常思路,这方面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中对于鸿胪寺、尚书主客司等机构的外交职能的探究尤为具体周详。近年来对于唐代职官制度的研究无论是各类重要朝官还是地方职官,都取得了颇多成果,其中仍以探讨其职掌为基本目标,本文也是在探究吏部侍郎职能中逐渐认识到应该从相关联的问题中寻求突破,兼任官视角的探究亦即为了加强对其本官职能的认识。
吏部侍郎在唐代吏部职官体系中具有仅次于吏部尚书的职权与地位,自始至终发挥着重要职能。笔者此前曾对吏部尚书、侍郎的职权做过探讨,基本观点认为唐代尚书省后期虽然渐呈式微之势,但从法理而言,其职权与前期并无二致②。就吏部侍郎而言,单任其职者自当以尽吏部职责,那么若同时有兼任官,则需要考量其任职情况如何,从这个角度梳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唐代吏部侍郎的职权发挥情况。在古代职官任命中,对于高品位的职官而言,又每每兼任其他职官,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于某类职官的研究势必需要考量其兼任官与本官的关系或两者之间的影响。作为唐代重要的职事官而言,在对吏部侍郎的职能的考察中,因其本官关涉其他职官选任、进迁等人事问题,则尤为需要注意其兼任官情况,以全面了解在有兼任官的情形下,其原有的职能如何体现。
②参见拙文《唐后期吏部尚书职掌探析——以行政法为视角》(《吏治与中国传统法文化:中国法律史学会2010年会论文集》,法律出版社2011年)、《唐前期吏部侍郎职掌考论——以武德贞观朝为例》(《历史教学》2012年第5期)。笔者此前从迁入官角度对吏部侍郎的选任做了探析,也涉及到其职能情况,参见拙文《唐代吏部侍郎选任考察——以迁入官为视角》(《郑州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与本文从兼任官角度入手相比,从迁入、迁出官视角来研究,是另外一种视角。另外,王孙盈政对唐代后期的尚书省进行了系统研究,参见其博士论文《唐代后期的尚书省研究》(浙江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
为了了解兼任官情况,先了解一下唐代职官的一些基本问题,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职官制度演变后,唐代的职官制度比较规整,此前看似随意的加官等情形,在唐代制度化为散官与勋官,当然随着职官的演变,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官制现象,如检校官制。这样在唐代,职事官、散官、勋官、检校官及爵封等构成了一个官员仕途过程中丰富多彩的官位特征,其中官员的散官、勋官、爵位等一般按其特定品秩而变迁,并无一人有两种散官、勋官或爵位的情况。检校官情况略有复杂,唐前期检校官实际上是授官任职的一种情况,具有实际职任,这个层面亦属于本文拟关注的兼任官职范围,而唐后期检校官则与散官性质相近,成为一种体现品秩特征的职官序列①。
①关于检校官研究,较为系统的研究可见赖瑞和《论唐代的检校官制》,《汉学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年6月)。其他研究还有:张东光《唐代的检校官》(《晋阳学刊》2006年第2期)、夏丽梅《隋唐检校官制度初探》(《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对于两种或两种以上职事官相兼领,我们会考虑两个职事官职务是否会彼此影响。唐人对职事官兼任在不同情形下有不同认识,比如,贞观时期,“新立晋王为皇太子,名士多兼领宫官,太宗欲令(岑)文本兼摄”。岑文本辞以“臣以庸才,久踰涯分,守此一职,犹惧满盈,岂宜更忝春坊,以速时谤。臣请一心以事陛下,不愿更希东宫恩泽”[1]卷70,p2538。最终没有兼任东宫官,说明这种兼任无论如何是要牵扯本职工作的。同样在贞观时期,“监察御史陈师合上书云:‘人之思虑有限,一人不可兼总数职’”。这个说法虽然最终被李世民否定,但也说明时人有相应的认识,即一个职位的发挥需要足够的“思虑”[1]卷18上,p608。对于唐代的职官兼领,从具体职官来分析进行探讨,是行之有效的一个视角,本文即拟以吏部侍郎为例进行,分析其兼领其他职务情况为何?是否会影响自身职能发挥?有何互相影响之处?等等。
本文关注视角为吏部侍郎这一具体官职,拟从其担任者兼任其他职官角度来探析相关问题。唐代中后期广泛存在使职差遣的情况,这导致了本官与本职的脱离,成为唐之后如北宋时期寄禄官等官制的滥觞,而在唐前期虽然差遣不是主流,但也开始出现非正式选任的情形,这从吏部侍郎的选任方式或兼任官中有明显体现,比如以“检校”形式兼任吏部侍郎或吏部侍郎为本官而“检校”其他官职:温彦博、唐临、李敬玄即以他官兼检校吏部侍郎,崔日用则以吏部侍郎检校雍州长史[2]544、546、548、564,这类情况实际上属于任命其担任吏部侍郎官职或兼职吏部侍郎。还有一种情况属于以他官临时性兼任吏部侍郎事,比如韦万石,“上元中,自吏部郎中迁太常少卿。……寻又兼知吏部选事,卒官”[1]卷77,p2672。这类情况实际是其他职官代管吏部侍郎事务,也是一种兼职情况,且在唐代所占比例不小②。
②这涉及到古代职官制度中的“真吏”问题,相关研究参见:黎虎《说“真吏”——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史学月刊》2009年第5期)。周文俊《南朝兼官制度新探》(《学术研究》2015年第9期)对南朝兼官做了整体探讨。
本文结合吏部侍郎兼任官情况,拟分三个层次进行探讨。
HTML
-
唐代吏部侍郎计有14任是以宰相兼任,可视为宰相层面的兼任官。现细考其任职情况如次③。
③本文涉及到吏部侍郎的统计主要依据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年版),该书为“研究唐史必备之高水平参考书、工具书”(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其中收录的尚书省职官情况迄今仍是最为权威的,成书后虽不断有墓志等新史料出现,但就尚书省职官而言,从数量增补上并无太大变化,比如近年新出相关研究中对于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已有论者在严耕望基础上有所增补,但数量极少,前者补充2人(详见:王建峰《唐代刑部尚书研究》,第3页,山东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张金龙教授指导),后者补充5人(详见:卫丽《唐代工部尚书研究》,第102页脚注1,山东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张金龙教授指导)。在借助新发现碑刻等进行补充中有一些新的发现,如吴浩《唐仆尚丞郎表补》(《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一文补充了王续、张孙祥、骞味道、孟履忠、崔慎由、孙简等六位吏部侍郎担任者。李卫硕士论文《〈唐仆尚丞郎表订〉补》(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是从文献考证角度系统研究《唐仆尚丞郎表》一书的新作,其中对于严耕望的一些具体考证提出了新见,不过并未增订新的吏部侍郎。
太宗朝高季辅,其担任吏部侍郎时表现优异,“凡所铨叙,时称允当”。甚至得到太宗的亲自褒奖,“太宗尝赐金背镜一面,以表其清鉴焉”①。这在唐代吏部职官中可谓是少见的殊荣,其任职时间也较长,担任吏部侍郎兼任宰相时间为贞观十九年(645)二月,时吏部尚书为杨师道。同年三月,杨师道兼任宰相后便从征高丽,实际上不主管吏部之事,而由刘洎负责吏部尚书事,此后,马周以宰相接任,再后卢承庆曾执掌吏部五品选事,后高季辅接任吏部尚书[2]491-492。尽管高季辅在吏部侍郎任上称职有加,而吏部尚书这时职掌与侍郎不尽相同,两者分工明确且都较为忙碌。卢承庆临时兼任过吏部五品事(实则为吏部尚书权责)即表明吏部尚书与高季辅的吏部侍郎职权仍有不同。另外,高季辅兼任官职为太子右庶子,贞观十七年李治被立为太子直至即位为唐高宗,高季辅自此为太子宫官员,同时为重要朝官,至“二十三年五月己巳,太宗崩,庚午,以礼部尚书、兼太子少师、黎阳县公于志宁为侍中,太子少詹事、兼尚书左丞张行成为兼侍中、检校刑部尚书,太子右庶子、兼吏部侍郎、摄户部尚书高季辅为兼中书令、检校吏部尚书,太子左庶子、高阳县男许敬宗兼礼部尚书”[1]卷4,p66。其太子右庶子为本官,吏部侍郎、户部侍郎为兼官,任官形式分别为“兼”“摄”。可知高季辅一直为太子李治的东宫官,后又兼任吏部侍郎,大概在不早于贞观二十一年时接替李纬“摄户部尚书”[2]628。则高季辅在贞观永徽之际迁为吏部尚书前,以宰相兼任太子左庶子、吏部侍郎、户部尚书。按《唐会要》卷七四《掌选善恶》所载时间,高季辅在贞观十七、十八年即以吏部侍郎发挥铨选职能,则是时兼任太子右庶子并未影响其职能发挥。而“(贞观)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亲统六军发洛阳。乙卯,诏皇太子留定州监国;开府仪同三司、申国公高士廉摄太子太傅,与侍中刘洎、中书令马周、太子少詹事张行成、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五人同掌机务”[1]卷3,p57,则因为太子已“监国”,更可以宰相兼吏部侍郎发挥职权,实际上是时的太子右庶子的职权反而不甚明显②。综合而言,高季辅在宰相位时,从太宗朝到高宗朝,其宰相官职于李治即位后,由“同掌机务”转为“兼中书令”,兼任官则由吏部侍郎升为吏部尚书,足以说明高季辅在两朝皆曾以宰相执掌吏部事务,可见地位非同一般。
①《旧唐书》卷七八《高季辅传》,第2703页。“金背镜”这一赐品具有特殊性,从李世民角度而言应该说是有其渊源所在,贞观十六年,李世民针对刚去世的魏徵进行评议时,曾用“镜”比喻:李世民“尝临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第2561页)
②太子右庶子作为重要东宫官属,在此之前,高士廉“升春宫,拜太子右庶子。”(《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第2442页)。房玄龄“入春宫,擢拜太子右庶子”(《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第2461页),二人后皆为太宗贞观朝宰相。实际上,若无太子监国这样实际上太子掌管国家政治运转的情形,东宫官的安排在国家行政系统中的作用并不突出,因为太子东宫系列的官属不可能取代以皇帝为核心的国家制度的运转,但东宫官属的安排于政权的延续有其特定的价值所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令太子熟悉政务、独立运行一个特殊机构的需要,因此有论者认为:“廷臣兼职宫僚,沟通了未来皇帝与廷臣的联系,新天子登基,必然起用兼宫僚的廷臣,这有利于新旧政权交接且保证了政局的稳定和新皇的统治。”(赵英华《唐前期东宫官研究(公元618年-713年)》,北京师范大学2008年历史学博士论文,施建中教授指导,第156页)
高宗朝的赵仁本和李敬玄。赵仁本以宰相兼任吏部侍郎及正谏大夫,“时许敬宗为右相,颇任权势,(赵)仁本拒其请托,遂为敬宗所构”[1]卷81,p2759,是时许敬宗亦为宰相,“元狩三年,……进中书令,仍守侍中。……改右相,辞疾,拜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年老,不任趋步,特诏与司空李勣朝朔日,听乘小马至内省。……咸亨初,以特进致仕,仍朝朔望,续其俸禄。卒,年八十一”[3]卷223上,p6338。即便许敬宗在高宗朝受荣宠如是,但同为宰相的赵仁本因有兼任官吏部侍郎,具体负责吏部之具体职能,在拒绝许敬宗“请托”时,后者亦无可奈何,只能采取排挤赵仁本不再担任吏部侍郎的办法,正所谓:“敬宗嫉其掌选守正,故去其司列选权以为右中护,知政事如故。”[2]548若赵仁本“司列选权”不去除,许敬宗即便“嫉其掌选守正”,也较难从容应对。可见宰相多此兼任官,仍是宰相具体职权的扩充。赵仁本同时还兼任正谏大夫,该职“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4]卷2,p247。正谏大夫即谏议大夫,为重要谏官,也是供奉官系列[4]卷2,p33,关于其性质,通过史籍记载可知其亦为重要侍臣之一,如贞观时期,“太宗寻又愍其受刑之苦,谓侍臣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忽断人右趾,意甚不忍。’谏议大夫王珪对曰”云云[1]卷50,p2135。“自是,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得闻政事,有所开说,太宗必虚己以纳之。”[5]卷55,p1114谏议大夫为唐代谏议制度中的最重要职官之一。又如中宗朝李景伯“景龙中为谏议大夫。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各命为《回波词》,或以谄言媚上,或要丐谬宠,至景伯,独为箴规语以讽帝,帝不悦。中书令萧至忠曰:‘真谏官也’”[3]卷116,p4244。可知,单为谏议大夫即可参与皇帝决策,亦可参与宰相的“平章国计”。赵仁本身为宰相已参与最高决策,而皇帝与侍臣之间的日常互动也是最高层面决策范畴,加上职掌吏部事务,赵仁本的权位较重,深得皇帝信赖。李敬玄,“时员外郎张仁祎有时务才,敬玄以曹事委之。仁祎始造姓历,改修状样、铨历等程式,处事勤劳,遂以心疾而卒。敬玄因仁祎之法,典选累年,铨综有序”[1]卷81,p2754。是时李敬玄以宰相兼任吏部侍郎期间做了很多有效的改革,安排吏部员外郎张仁祎具体负责,最终效果良好,李敬玄任职期间做到了“铨纵有序”,李敬玄以宰相兼任吏部侍郎一职,除了宰相必要的工作“参政事”外,史籍充分介绍了其任职吏部侍郎的工作情况,可见其兼任官对其本职工作并无干扰,甚至因为其担任宰相,有助于切实推动吏部职能的改进。李敬玄任职吏部侍郎期间,吏部尚书史载阙员,后概因其表现优异而进迁为吏部尚书。
武后称制及称帝时期的魏玄同。魏玄同以宰相两次兼任吏部侍郎,即在宰相层面本官发生迁转:吏部侍郎·宰相衔→黄门侍郎·宰相衔→左丞·宰相衔→黄门侍郎·宰相衔·兼吏部侍郎→户部尚书·宰相衔。新旧《唐书》及《唐会要》都记载了魏玄同关于选举制度方面的一次上疏①,就魏玄同上疏论选事内容而言,实际上是对于吏部职权的改革,其主张更偏重于弱化。这可能与其以宰相兼任吏部侍郎时,与韦待价同样以宰相兼任吏部尚书在相关职权发挥上很不得力,“(韦)待价素无藻鉴之才,自武职而起,居选部,既铨综无叙,甚为当时所嗤”[1]卷77,p2672。这里所言“甚为当时所嗤”,应该包括其吏部同僚,魏玄同自然也名列其中。一方面,魏玄同对于吏部铨选相关制度的拟调整与改革,另一方面,时为吏部长官的韦待价的“铨综无序”,可以说魏玄同的上疏并非空穴来风,亦属于由来有自。只不过,吏部制度的形成与完备,并非以恢复汉魏旧制的改革主张所能逆转。因此,即使以宰相身份提出,也未能为朝廷认同,结果“疏奏不纳”[1]卷87,p2853。
①记载上在时间方面略有出入:《旧唐书·魏玄同传》定在“弘道初,转文昌左丞,兼地官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第2853页)这个时间之前。《新唐书》卷一一七《魏玄同传》载于“再迁吏部侍郎。永淳元年,诏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第4252页)之后。《唐会要》卷七四《选部上·论选事》:“垂拱元年七月。”(第1582页)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第551页)以此为确。
武周时期的吉顼、顾琮。吉顼以宰相兼吏部侍郎,陆象先,“本名景初。……秩满调选,时吉顼为吏部侍郎,擢授洛阳尉,元方时亦为吏部,固辞不敢当。顼曰:‘为官择人,至公之道。陆景初才望高雅,非常流所及,实不以吏部之子妄推荐也。’竟奏授之”[1]卷88,p2876。吉顼虽为宰相而实际上在正常履职吏部侍郎职权,对于选授官职直言乃“至公之道”,即属于吏部侍郎权责范畴内行为。洛阳尉为“从八品下”[4]卷30,p750,属于吏部侍郎铨选范围,即便如此,陆元方也表现出“固辞不敢当”,虽说有亲属回避之嫌疑,但也表明吏部铨选还是相当严格的。顾琮,“久视元年七月,……顾琮除吏部侍郎,时多权幸,好行嘱托。琮性公方,不堪其弊”[5]卷74,p1494。顾琮担任吏部侍郎期间的情况可谓艰难,“不堪其弊”,后升迁宰相兼吏部侍郎,在某种意义上也归入“权幸”范围,则毫无疑问有助于其良好发挥吏部侍郎职能。
魏玄同、郭待举、吉顼、顾琮四人都是在武则天秉政时以宰相兼吏部侍郎。同时期还有郭待举,史载其任职时职权发挥情况不详。
睿宗朝的崔湜、郑愔,崔湜“与郑愔同知选事,铨综失序,为御史李尚隐所劾,愔坐配流岭表,湜左转为江州司马”[1]卷74,p2622-2623。即便身为宰相,因为职权发挥出现问题,亦存在被“劾”的可能。后崔湜又因“上官昭容密与安乐公主曲为申理”及“韦庶人临朝”等又曾任宰相兼吏部侍郎等职官[1]卷74,p2623。显示了当时职官管理方面与政局之间的关联,整体前者受制于后者。
据《唐仆尚丞郎表》可知,在高宗朝特别是显庆之后吏部尚书总计员阙时间约24年。有吏部尚书年数约为16年,而在武周朝总计员阙时间约10年,则在从显庆元年(656)到长安四年(704),大概48年时间内,有近34年时间没有吏部尚书。结合以上分析,唐高祖、唐睿宗、唐玄宗时期基本没有吏部侍郎人物担任宰相,唐太宗朝仅1任,其他吏部侍郎担任宰相的时间与武则天掌权有一定关系,可以认为在武则天掌权时期,吏部侍郎的权力有所膨胀,就尚书吏部内部来看,吏部侍郎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吏部尚书的位置,在朝廷中也时有吏部侍郎上升到宰相的位置,和吏部尚书平分秋色。这一时期吏部侍郎即便以宰相兼任,其主要政治作为除了宰相职权外,仍可看出发挥了吏部侍郎的相应职权,可谓是吏部侍郎权力和地位膨胀的时期,其结果应该就是造成了吏部侍郎与吏部尚书铨选方面职权的趋同,主要体现就是铨选范围的一致,正如《唐会要》所载:“吏部尚书”条载:“(吏部尚书)掌铨六品七品选。侍郎掌铨八品九品选。至景云元年,宋璟为吏部尚书,始相通与侍郎分知,因为故事者也。”[5]卷58,p1178
唐肃宗朝崔涣以宰相充江淮宣谕选补使,“时未复京师,举选路绝,诏涣充江淮宣谕选补使,以收遗逸”[1]卷108,p3280。据此可知因为安史之乱的影响,当时年度铨选受到影响,“举选路绝”,具有常选资格的选人或前资官则无法到都城参加“常调”,朝廷不得不采取措施,以保障职官系统的运转,“诏宰相崔涣巡抚江南,补授官吏”[1]卷10,p244。可能因为整个职官系统受到安史之乱的影响,崔涣此次履职并不顺利,“惑于听受,为下吏所鬻,滥进者非一,以不称职闻。乃罢知政事,除左散骑常侍,兼余杭太守、江东采访防御使”[1]卷108,p3280。除了职务上出现问题外,也有可能其宰相身份是出于玄宗任命,而在肃宗朝被刻意排挤,史载:“房琯以败军左降,崔圆、崔涣等皆罢知政事,上皇所命宰臣,无知政事者。”[1]卷108,p3278因为当时职官管理系统整体而言已很紊乱,已非无战事之前的情形可比,安史之乱对吏部铨选工作的影响很深,“初,肃宗在凤翔,丧乱之后,纲纪未立,兵吏三铨,簿籍煨烬,南曹选人,文符悉多伪滥。上以凶丑未灭,且示招怀,据到注拟,一无检括”[1]卷108,p3278。整个吏部工作没有了章法,在这种情形下,崔涣的工作势必难以开展顺利,若如此,给予其“选补使”的差事,其中也就不免掺杂着有意找到把柄以免去其宰相职任的意味。
从唐玄宗到穆宗朝,除肃宗时有崔涣这一接近吏部侍郎职掌的事例外,并无宰相兼任吏部侍郎之情形。“先天已前,诸司官知政事,午后归本司决事,兵部尚书、侍郎亦分铨注拟。开元已后,宰臣数少,始崇其任,不归本司。”[1]卷106,p3244唐玄宗朝以前,本官加宰相衔后从兼任官视角而言,一方面要有宰相职任需发挥,另一方面其本职职务仍是其中重任,这从前文考述宰相兼吏部侍郎情况可见一斑。另外,从三省长官情形亦可看出,如尚书省长官便经过了为当然宰相到须加衔“同中书门下三品”等职衔后方才为宰相任,加衔的三省长官本身亦有其本职工作,如李勣,“高宗即位,其月,召拜洛州刺史,寻加开府仪同三司,令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是岁,册拜尚书左仆射。永徽元年,抗表求解仆射,仍令以开府仪同三司依旧知政事。”李勣从尚书左仆射到开府仪同三司的本官转换,意味着不再兼任尚书省事务,而仍为宰相职务。既然如此,以宰相兼任吏部侍郎职务,则需要同时处理宰相事务和吏部侍郎事务,即日常的“诸司官知政事,午后归本司决事”,两种职官事务皆很繁重,宰相职务自不待言,吏部侍郎职务中单铨选一项即很繁重:“故事,吏部三铨,三注三唱,自春及夏,才终其事”[1]卷106,p3244。由此看来,吏部侍郎作为“贰尚书”而参与铨选的过程,其工作量颇为不轻,故而虽整体上宰相兼领吏部侍郎比例占宰相总数或吏部侍郎总数并不为高,但已有的事例中仍可以看到宰相兼吏部侍郎后职权的增加与任务量的增加①,具体到吏部侍郎的铨选工作,也是如此。
①有学者的研究也体现出,本官加衔而为宰相后,其本官职掌亦未因此而完全消弭,即便唐后期也是如此,参见:王孙盈政《论唐后期的尚书省宰相》,《历史教学》2014年第10期。
唐后期穆宗朝李程担任吏部侍郎后,到敬宗即位后升迁以宰相兼任吏部侍郎。《全唐文》卷六十八敬宗《授李程平章事制》谓:“周旋台阁,阅历中外,秀造称其得俊,衡镜表于无私,……秉彝伦以澄躁竞,核名实以镇浮虚。协睦乃僚,无替朕命,爰因铨品之鉴,载伫烹饪之功。可尚书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散官勋赐如故。”诏书既肯定了其担任吏部侍郎时的贡献,又期待其在宰相任上继续发挥好吏部侍郎之职权,正所谓“爰因铨品之鉴,载伫烹饪之功”。文宗朝的李宗闵,在任命其为宰相的诏书里提及“奉丝纶于掖垣,平铨综于省闼。……宜升枢轴之尊,俾叶钧衡之政”[6]授李宗闵同平章事制,卷69,p728,显示了对李宗闵在吏部侍郎职位上的重用。唐末再次担任吏部侍郎的杨涉曾短暂兼任宰相,具体情形不得而知。综合后期三任吏部侍郎曾兼任宰相,也不排除对其吏部侍郎工作的加强,因为从前揭李程、李宗闵的任命诏书中可见一斑,而杨涉曾两次任职吏部侍郎,多少显示其在这一职位上有一定的可行性。
-
京畿职官一方面是地方官,另一方面因为在京畿地区为官,多参与朝廷事务也具有中央官的性质,比如京兆尹即可以参与日常朝参,“朕日出而御便殿,召宰相以下计事,而大京兆得在其中”①。太宗朝温彦博(雍州治中)、玄宗朝崔日用(检校雍州长史)、代宗朝严武(京兆尹),都是以京畿职官兼任吏部侍郎。温彦博,“授雍州治中,寻检校吏部侍郎。彦博意有沙汰,多所损抑,而退者不伏,嚣讼盈庭。彦博惟骋辞辩,与之相诘,终日喧扰,颇为识者所嗤”[1]卷61,p2361。虽为雍州治中检校吏部侍郎,史籍主要体现了其后者任职的表现。崔日用,“及讨萧至忠、窦怀贞之际,又令权检校雍州长史”[1]卷99,p3088。显见,彼时之雍州长史乃唐玄宗有意安排其亲信之人为京畿职官,以为稳妥。此前崔日用亦在类似情形下担任过该职,“讨平韦氏,其夜,令权知雍州长史事”[1]卷99,p3088。严武,“李芃字茂初,赵郡人也。解褐上邽主簿,三迁试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山南东道观察支使。严武为京兆尹,举为长安尉”[1]卷132,p3654。按严武为京兆尹有一定权限去举荐李芃为其属官,一般而言,长安尉为吏部铨选范围内职官,则严武兼任吏部侍郎的身份使得这一举措更顺理成章且便利。对于举荐职官而言,因为宰相的职责之一就是选拔有才能之人,唐中后期,贞元“八年四月,窦参罢黜,憬与陆贽并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憬深于理道,常言:‘为政之本,在于选贤能,务节俭,薄赋敛,宽刑罚。’”[1]卷138,p3776若为宰相层面职官进行举荐,属于可以理解范畴,如“宰相杨收奏授(孔纬)长安尉,直弘文馆”[1]卷179,p4649。一般情况下则需要参与吏部常选或科目选,前者如路泌,“建中末,以长安尉从调,与李益、韦绶等书判同居高第,泌授城门郎”[1]卷159,p4190。“从调”即参加吏部铨选而得以授官,长安尉作为前资官而参加吏部铨选后,可以再授更高级别的新官职。王珣,“天授初,珣及进士第,应制科,迁蓝田尉。以拔萃擢长安尉,因进见,武后召问刑政,嘉之”[3]卷111,p4136。此例当非科目选,科目选确定于唐后期,此或为制举系列。无论为何,其选任亦经考选程序则无疑。科目选又如德宗朝辛祕“贞元年中,累登《五经》、《开元礼》科,选授华原尉,判入高等,调补长安尉”[1]卷157,p4150。就严武例来看,以京兆尹与吏部侍郎兼任,相当于增加前者的职权,拓展了其人事选任权力,而其任职在京畿,具备中央官与地方官的双重特征,不影响吏部侍郎职权的发挥,并有助于其选任合适人选担任其属官。
①〔唐〕元稹,《卢士枚权知京兆尹制》,《元稹集校注》(周相录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3页。关于唐代京兆尹的研究参见:张荣芳《唐代京兆尹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版。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京兆府……武德元年,改为雍州。……天授元年。改雍州为京兆郡,其年复旧。……大足元年罢,以鸿、宜、鼎、稷四州依旧为县,以始平等十七县还隶雍州。……开元元年,改雍州为京兆府,复隋旧名。”则雍州治中、长史与京兆尹性质相近,“皇朝置雍州别驾,永徽中,改为长史,正四品下。开元初,改长史为尹,从三品。然亲王为牧,皆不知事,职务总归于尹”[4]卷30,p741,雍州长史实际上为雍州即后改为京兆府的地方长官,如苏良嗣,“永淳中,为雍州长史,时关中大饥,人相食,盗贼纵横。良嗣为政严明,盗发三日内无不擒擿”[1]卷75,p2630。“久视元年,(薛)季昶自定州刺史入为雍州长史,威名甚著,前后京尹,无及之者。”[1]卷185,p4804“皇朝复曰治中,后避高宗讳,改曰司马。”雍州治中仅次于长史。综合而言,地方官兼任皆为京城长安为核心的地方官,实际上因其特殊性,还具有朝官的特征。
-
黄门侍郎:高宗朝的唐临、刘祥道;谏议大夫:中宗朝宋璟。尚书左丞:玄宗朝张倚。
唐临为高宗朝第一任吏部侍郎,实际是接任由吏部侍郎迁为吏部尚书的高季辅的职位。刘祥道是时隔不久高宗朝又一例以黄门侍郎兼吏部侍郎事的官员。按照铨选程序,黄门侍郎(门下侍郎)是吏部铨选后经过门下“过关”的负责官员之一,也是相关官文书形成的必要步骤,因此黄门侍郎对吏部有相应的责任,必然对其有一定的了解,这也是三省制制度的特征。实际上,作为黄门侍郎兼吏部侍郎事的刘祥道对吏部制度是有深刻认识的,这体现在其提出的建议上,“(刘)祥道以铨综之术犹有所阙,乃上疏陈其得失”[1]卷81,p2750。这次“上疏”虽然最终没有起到根本性作用,但这也是唐代吏部制度一直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可见,刘祥道作为相关责任者对其职位职权的深刻认识,也是职官职能的体现。
中宗朝宋璟曾兼任谏议大夫,“神龙元年,迁吏部侍郎。中宗嘉璟正直,仍令兼谏议大夫、内供奉,仗下后言朝廷得失”[1]卷96,p3031。通过兼任官使得宋璟与单任吏部侍郎多了一些特殊职权,除执掌吏部具体行政事务外,还可以对朝廷事务发表自己的认识,属于进一步密切了与皇帝等权力核心层的关系。
玄宗朝张倚以尚书左丞兼吏部侍郎。《旧唐书》卷一〇六《杨国忠传》在吏部铨选事例中曾涉及张倚:“(杨)国忠既以宰臣典选”,作为吏部侍郎的张倚主要协助其进行相应工作,“故事,注官讫,过门下侍中、给事中。国忠注官时,呼左相陈希烈于座隅,给事中在列,曰:‘既对注拟,过门下了矣。’吏部侍郎韦见素、张倚皆衣紫,是日与本曹郎官同咨事,趋走于屏树之间。既退,国忠谓诸妹曰:‘两员紫袍主事何如人?’相对大噱。其所昵京兆尹鲜于仲通、中书舍人窦华、侍御史郑昂讽选人于省门立碑,以颂国忠铨综之能。”这里言及的张倚主要体现了其吏部侍郎之职权特征。尚书左丞与右丞,“掌管辖省事,纠举宪章,以辨六官之仪制,而正官僚之文法,分而视焉”[4]卷1,p7。据此可知尚书左丞兼吏部侍郎则当更严肃于后者职权的发挥,然而在权臣杨国忠兼领吏部尚书的情况下,与铨选有关联的门下省官员的职权都被侵夺,何况作为下级官员的吏部侍郎,只不过是忙于“趋走”的办事人员而已。
-
司卫卿(卫尉卿):武周朝陆元方;御史中丞:中宗朝萧至忠。太常少卿:郑愔(检校吏部侍郎事);太子宾客:文宗朝郑肃。
陆元方,以司卫卿即卫尉卿兼吏部侍郎,虽兼两职,相对而言,吏部侍郎职务似更繁忙:“陆元方常任天官侍郎,临终曰:‘吾年当寿,但以领选之日伤苦心神。’言讫而殁。”[7]卷3,p21可见吏部侍郎之工作繁忙,陆元方即便曾任宰相,追忆仕宦经历,仍因“领选之日伤苦心神”。吏部侍郎工作性质使然,自然繁忙,加上其尽职尽责,“或言其荐引皆亲党,后怒,免官,令白衣领职。元方荐人如初,后召让之,对曰:‘举臣所知,不暇问雠党’”[3]卷116,p4235-4236。可谓“九流铨总,代天理物,公执其衡镜,而野无遗贤”[6]文昌左丞陆公墓志,卷231,p2342。自不待言,而陆元方本人也谨小慎微,其子陆象先“秩满调选,时吉顼为吏部侍郎,擢授洛阳尉,元方时亦为吏部,固辞不敢当。顼曰:‘为官择人,至公之道。陆景初才望高雅,非常流所及,实不以吏部之子妄推荐也。’竟奏授之”[1]卷88,p2876。对其子的安排,即便符合程序,陆元方也谨慎推辞,可见其处世之格外小心,如此能不“伤苦心神”?
萧至忠,“神龙初,武三思擅权,至忠附之,自吏部员外擢拜御史中丞。迁吏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恃武三思势,掌选无所忌惮,请谒杜绝,威风大行”[1]卷92,p2968。按萧至忠依附武三思而行使吏部侍郎职掌时“无所忌惮”,这里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其兼御史中丞,而“御史大夫之职,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中丞为之贰。……侍御史,……凡事非大夫、中丞所劾而合弹奏者,则具其事为状,大夫、中丞押奏”[4]卷13,p378、380。有了这个兼职,在发挥吏部职掌时,更容易做到“请谒杜绝,威风大行。”否则吏部侍郎在执行权力时,稍不合法即可为御史台限制,如裴漼,“累迁监察御史。时吏部侍郎崔湜、郑愔坐赃为御史李尚隐所劾,漼同鞫其狱。安乐公主及上官昭容阿党湜等,漼竟执正奏其罪,甚为当时所称”[1]卷100,p3128。崔湜、郑愔担任吏部侍郎时即被御史台官员御史李尚隐与监察御史裴漼共同弹劾。也有御史中丞直接弹劾吏部侍郎的事例,“龙朔二年,司列少常伯杨思玄恃外戚之贵,待选流多不以礼,而排斥之,为选者夏侯彪所讼,而御史中丞郎余庆弹奏免官”[5]卷74,p1592-1593。即便安史乱后,御史台也一直发挥对相关机构的监察职能,比如,大历八年(773年)“二月甲子,御史大夫李栖筠弹吏部侍郎徐浩”[1]卷11,p301。
郑愔兼任太常少卿,史籍主要展示了其作为吏部侍郎的情形,“神龙中,左台中丞侯令德为关内黜陟使,尚隐佐之,以最擢左台监察御史。于是,崔湜、郑愔典吏部选,附势幸,铨拟不平,至逆用三年员阙,材廉者轧不进,俄而相踵知政事,尚隐与御史李怀让显劾其罪,湜等皆斥去”[3]卷130,p4498。这里不提郑愔兼太常少卿事,而后又升迁为宰相,即便如此,也不能避免被“显劾其罪”。
文宗朝郑肃,“(开成)二年九月,召拜吏部侍郎。帝以肃尝侍太子,言论典正,复令兼太子宾客,为东宫授经。既而太子失宠,上不悦,有废斥意。肃因召见,深陈邦国大本、君臣父子之义。上改容嘉之。而太子竟以杨妃故得罪。乃以肃检校礼部尚书,兼河中尹、河中节度、晋绛观察等使。会昌初,武宗思太子永之无罪,尽诛陷永之党。朝议称肃忠正,有大臣之节。召拜太常卿,累迁户部、兵部尚书”[1]卷176,p4574。是时郑肃兼任太子宾客,主要“为东宫授经”。
以上兼任官,主要考虑其是否影响吏部侍郎工作发挥,结合史料而言,并无这方面的情形出现。
-
①相关研究参见:杜海斌《唐代集贤院新探》,文载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2016年第2期(总第23辑),三秦出版社2016年版。
李季卿、王延昌、杨绾、徐浩、蔡邕。此五位皆为代宗朝吏部侍郎。李季卿、王延昌二人是在这样背景下兼任集贤院待诏的:“上以勋臣罢节制者,京师无职事,乃合于禁门书院,间以文儒公卿,宠之也。”[1]卷11,p278实际上此五位吏部侍郎先后任职,皆兼任集贤院职,也堪称“文儒”之士,且并非“无职事”者,集贤院虽“掌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但也有与吏部有关联的职掌,“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1]卷43,p1852。这里对于贤才的征求多少与吏部的职能类同。代宗朝永泰年开启的吏部侍郎待诏集贤院,有五任吏部侍郎持续如此任职且在其本职上仍发挥着主要作用:李季卿,“振拔幽滞,号振职”[3]卷202,p5748。是吏部选官优越性的良好表现。王延昌在吏部任上提出一些改革措施,大历元年(766)二月敕:“许吏部选人自相举,如任官有犯,坐举主。”这个敕文是朝廷回应王延昌上奏后发出的,“从吏部侍郎王延昌奏”[5]卷75,p1614。杨绾,“再迁吏部侍郎,历典举选,精核人物,以公平称”[1]卷119,p3434。徐浩,“又为吏部侍郎、集贤殿学士。坐以妾弟冒选,托侍郎薛邕注授京尉,为御史大夫李栖筠所弹,坐贬明州别驾”[1]卷137,p3760。“甲子,御史大夫李栖筠弹吏部侍郎徐浩。……徐浩、薛邕违格,并停知选事。壬申,永平军节度使、检校右仆射、滑州刺史、霍国公令狐彰卒,遗表荐刘晏、李勉代己”[1]卷11,p301。侧面可知徐浩、薛邕吏部职任上发挥作用。
一. 类型一:以京畿职官检校
二. 类型二:中书、门下二省职官兼任
三. 类型三:三省外其他朝官
四. 类型四:集贤院待诏①
-
以他官兼任吏部侍郎事,这属于职官体系中类似使职差遣性质的职官安排,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以吏部职能为主,进行一次临时或非正式的任职安排,使其执掌吏部职能。相对于其兼任而言,其本官职官情况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唐代有50任为他官兼任,占可考吏部侍郎294任数的六分之一强,比例可谓不小。其中开元十三年有一次为10位职官分十铨进行,为兼任中的特殊情况。综合而言,除德宗朝卢翰其本官情况不可考外,其他49人,其本官有左丞(4)、右丞(3)、中书舍人(10)、吏部郎中(2)、兵部侍郎(3)、散骑常侍(3)、刑部侍郎(2)、户部侍郎(2)、工部侍郎(2)、其他皆1任者为:太常少卿、太仆少卿、大理少卿、黄门侍郎、黄门监、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御史中丞、给事中、蒲州刺史、魏州刺史、荆州长史、郑州刺史、怀州刺史、宰相,另有2任为:代宗朝李岘以荆南节度使知江淮选补使;宪宗朝赵宗儒以东都留守权知吏部,掌东都选事。以上三省官合计36任,其中以中书舍人又最多,这个情况与唐代吏部侍郎迁入官情况又近似。
以他官兼任吏部侍郎事,针对性明确,主要是以铨选为主。比如中书舍人卢藏用。“中宗景龙末,崔湜、郑愔同执铨管,数外倍留人。及注拟不尽,即用三考二百日阙。通夏不了,又用两考二百日阙。其或未能处置,即且给公验,谓之‘比冬’。选人得官,有二年不能上者。有一人索远得留,乃注校书郎。选司纲维紊坏,皆以有崔、郑为口实。愔坐赃贬江州员外司马。卢藏用承郑氏之后,尚有七百余人未授官,一切奏至冬处分。大遭怨讟。”[7]卷3,p21-22卢藏用,“神龙中,累转起居舍人,兼知制诰,俄迁中书舍人……景龙中,为吏部侍郎。藏用性无挺特,多为权要所逼,颇隳公道。又迁黄门侍郎,兼昭文馆学士,转工部侍郎、尚书右丞”[1]卷94,p3001-3004。卢藏用先以中书舍人兼吏部侍郎事,主要是对此前崔湜、郑愔“选司纲维紊坏”的局面进行纠正,所谓“累擢中书舍人,数纠驳伪官”[3]卷123,p4374,后专任吏部侍郎,“自四年掌诰,九品作程,峻而不杂,重轻咸当,简而能要。浮竞斯远。刀尺之委,铨衡已归,特选周才,更符佥望。可检校吏部侍郎,仍佩鱼如故”[6]授卢藏用检校吏部侍郎制,卷251,p2534。
地方官除李岘与赵宗儒外,其他5任都是开元十三年(713)事。此次分十铨,参与地方官有蒲州刺史、魏州刺史、荆州长史、郑州刺史、怀州刺史。封禅,《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载:开元十三年,“冬十月癸丑,新造铜仪成,置于景运门内,以示百官。辛酉,东封泰山,发自东都。十一月丙戌,至兗州岱宗顿。……十二月己巳,至东都。……是冬,分吏部为十铨。”原因为“会帝封太山还,融以选限薄冬,请分吏部为十铨”[3]卷134,p4558。地方官当是随唐玄宗封禅回到东都后,因宇文融奏请,与其他朝官一起参与铨选。是时吏部侍郎仅蒋钦绪疑似在任,亦可能吏部侍郎员阙。严耕望考证:蒋钦绪,“开元十四年,或上年秋冬,由御史中丞迁吏部侍郎”[2]574。时吏部尚书为裴漼,“漼早与张说特相友善,时说在相位,数称荐之”[1]卷100,p3129。而张说与宇文融关系不洽,“中书令张说素恶融,融每建白,说辄引大体廷争”[3]卷134,p4558。此次分十铨,实际上规避了吏部尚书裴漼的职权,其中难免有张说与宇文融政争的关系,而吏部侍郎的员阙,加上时间紧张,故而宇文融的建议得到唐玄宗肯定。前所未有的分十铨也符合时间紧迫的前提。地方官的参与中,崔琳、王丘此前曾历职吏部侍郎,贾曾,“开元六年,玄宗念旧,特恩甄叙,继历庆、郑等州刺吏,入拜光禄少卿,迁礼部侍郎”[1]卷190中,p5029。韦虚心,“荆扬潞长史兼采访使,所在官吏振肃,威令甚举,中外以为标准”[1]卷101,p3147。崔琳本为张说所推荐,后却有特立独行表现,反而与张说关系出现问题,“自是每有制敕及曹事,沔多所异同,张说颇不悦焉。寻出为魏州刺史,奏课第一,征还朝廷,分掌吏部十铨事。以清直,历秘书监、太子宾客”[1]卷188,p4928。其作为地方官能取得“奏课第一”的业绩,从而直接分管吏部事,二者间不无关系。从这五位参与吏部职能的人员或官职而言,朝官与地方官各占一半,地方官参与铨选,应该说于铨选对象有关联,唐玄宗即位后一直重视地方官员选拔,此前在“开元二年,(李朝隐)迁吏部侍郎,铨叙平允,甚为当时所称,降玺书褒美,授一子太子通事舍人。四年春,以授县令非其人,出为滑州刺史”[1]卷100,p3126。对于地方官而言,刺史等长官无疑最熟悉其任职情况。综合分析可知,地方官中除官员本身情况或曾任职吏部侍郎、或于地方表现优异等因素外,蒲州(“京师东北三百二十四里,去东都五百五十里。”《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魏州(“在京师东北一千五百九十里,去东都七百五十里。”《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荆州(“在京师东南一千一百八十二里,至东都八百五十三里”《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郑州(“至京师一千一百五里,至东都二百七十里”《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怀州(“在京师东九百六十九里,至东都一百四十里。”《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基本都与东都相距很近或不甚远。“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诣行在。”[3]卷124,p4383与都城距离的远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地方官与皇帝关系亲密的程度,所以综合来看,参与铨选的这批地方官应该与皇帝关系相对亲近。
-
唐高祖朝殷开山(元帅府司马)、高宗朝裴行俭(洮河道左二军总管)、睿宗朝赵彦昭(关内道巡边使)、玄宗朝刘彤(江东江西宣慰使)、代宗朝李季卿(充使宣慰河南江淮)、武宗朝高铢。
担任其他职任去发挥作用,在吏部侍郎这个层面而言,所见事例为以上几例。其中殷开山为唐初朝官,军事活动仍是当时朝廷重要乃至主要任务之一,殷开山此前便有军功,“参预谋略,授心腹之寄”,深得朝廷信任,成为唐初第一位吏部侍郎,后“从击薛举,为元帅府司马”[1]卷58,p2312。高宗朝裴行俭,担任吏部侍郎时间较长,且任职表现优异,“与李敬玄为贰,同时典选十余年,甚有能名,时人称为裴、李。行俭始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等法,又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以为故事”[1]卷84,p2802。其中对吏部行政制度的建设也贡献良多。担任吏部侍郎期间,先后两次担任军事长官,“吐蕃背叛,诏行俭为洮州道左二军总管。寻又为泰州镇抚右军总管,并受元帅周王节度”[1]卷84,p2802。能够担任参与军事征伐活动,是因为裴行俭早先曾得到唐初名将苏定方的传授,“时苏定方为大将军,甚奇之,尽以用兵奇术授行俭”[1]卷84,p2801。睿宗朝赵彦昭,“入为吏部侍郎,持节按边”[3]卷123,p4377。即“关内道持节巡边使”[1]卷92,p2967。《资治通鉴》卷二一〇《唐纪二十六》·睿宗景云二年(711):“时遣使按察十道”[8]卷210,p6666。胡三省注曰:“太宗贞观十八年,遣十七道巡察;武后垂拱初,亦尝遣九道巡察,天授二年又遣十道存抚使。至是分为十道按察使,以廉按州郡,二周年一替。”又《资治通鉴》下文曰:“议者以山南所部阔远,乃分为东西道;又分陇右为河西道。六月,壬午,又分天下置汴、齐、兖、魏、冀、并、蒲、鄜、泾、秦、益、绵、遂、荆、岐、通、梁、襄、扬、安、闽、越、洪、潭二十四都督,各纠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恶,惟洛及近畿州不隶都督府。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卢俌等上言:‘都督专杀生之柄,权任太重,或用非其人,为害不细。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时巡察,奸宄自禁。’其后竟罢都督。”严耕望认为,赵彦昭即为“按察十道”之一[2]567。果如此,则赵彦昭之“持节巡边”之职权虽不属于吏部侍郎规定范畴内之工作,但亦与吏部侍郎执掌官员人事有一定联系,另外,外出巡视期间,其本职工作自然不能担任,后很快又迁为左御史台大夫。当时处于政局交替阶段,吏部工作似乎并不紧要,如同时担任吏部侍郎的马怀素即因“属朝廷以刑政所急,改授大理少卿”[1]故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兼昭文馆学士侍读上柱国常山县开国公赠润州刺史马公(怀素)墓志铭,卷995,p10305。代宗朝李季卿,“拜吏部侍郎。俄兼御史大夫,奉使河南、江淮宣慰,振拔幽滞,进用忠廉,时人称之”[1]卷99,p3102。此前,李季卿已兼任集贤院待制,“上以勋臣罢节制者,京师无职事,乃合于禁门书院,间以文儒公卿,宠之也”[1]卷11,p278。实际上这个兼任并不妨碍其吏部侍郎本职工作,主要是为与无职事之勋臣配合而已。此后的兼职却与其吏部侍郎的职权有一定关联,如“诏征(权皋)为起居舍人,又以疾辞……李季卿为江淮黜陟使,奏(权)皋节行,改著作郎”[1]卷148,p4001-4002。“补剡县尉。改会稽尉。宣州观察使殷日用奏为判官,宣慰使李季卿又以表荐,连授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1]卷153,p4084李季卿以吏部侍郎担任宣慰使,多考察官员行能,这与其本官职能有必然联系①。高铢,在武宗会昌平泽路后,“吏部侍郎高铢、给事中卢弘正专往宣慰”[1]武宗平潞州德音,卷77,p810。
①其他事例还有,《旧唐书》卷一九三《列女·卢甫妻李氏传》:“澜女卢甫妻,又泣请代父死。并为贼所害,宣慰使、吏部侍郎李季卿以节义闻。”(第5148页)《旧唐书》卷一五四《孔巢父传》:“永王璘起兵江淮,闻其贤,以从事辟之。巢父知其必败,侧身潜遁,由是知名。广德中,李季卿为江淮宣抚使,荐巢父,授左卫兵曹参军。”(第4095页)笔者按,严耕望认为,永泰元年“即次年或前后一年,充使宣慰河南江淮”。笔者据《旧唐书》卷一五四《孔巢父传》所载时间,则当在永泰前一年,即“广德中”宣慰河南江淮。果如此,则其在吏部侍郎任上便于地方巡视,同时兼任之待制集贤院偏重为形式上官职,并无实际特定职任。
就出外巡视、宣慰等来看,甚至相关职任的推荐或选拔也与吏部有关,或者说是吏部尚书的职掌之一,此从唐临担任吏部尚书时情形可以管窥,显庆三年(658),“雍州司士许祎与来济善,侍御史张伦与李义府有怨,吏部尚书唐临奏以祎为江南道巡察使,伦为剑南道巡察使。是时义府虽在外,皇后常保护之,以临为挟私选授”[8]卷200,p6311。这里明言唐临以吏部尚书身份“选授”了江南道与剑南道的巡察使。当时吏部尚书职权地位隆重,官员人事问题由其掌管,而巡察地方者自然以地方官是否做到尽职尽责为主。结合吏部尚书这一职能特点,联系此处以吏部侍郎赵彦昭等外出巡察地方,则更说明这属于吏部职能的范畴内的题中之义。
以上几例恰好又分为两组情况,一种为与吏部侍郎无关之兼任官,一种或多或少牵涉吏部职能之兼任。合并而言,两种兼任官发挥职能时都使得本官职能无暇顾及。另外,郝处俊亦曾在吏部侍郎任职期间,“属高丽反叛,诏司空李勣为浿江道大总管,以处俊为副”[1]卷84,p2797。
一. 类型一:他官临时兼任吏部选事
二. 兼任官类型之一:临时担任其他职务
-
唐代吏部侍郎作为重要的职事官,其担任者兼任其他职事官或职任的情况从唐初一直到唐末都有出现。其中亦有其担任者以其他官兼任吏部侍郎或吏部选事者,本文皆视为吏部侍郎兼任官来研究。唐代计有可考吏部侍郎294任,85任有兼任官,这其中又有50任为其他官兼任吏部侍郎事的情况。总体而言,吏部侍郎担任者有兼任官情况并不占很大比例,但接近30%的比例仍值得关注。
本文拟探讨的问题,从有兼任官的角度看,需要具体分析其兼任官是不是会影响彼此原有职能发挥,两种职事官兼任会不会影响正常工作的开展,以上根据兼任官情况进行分门别类的分析。得出的基本认识是,吏部侍郎具有兼任官的情况,大体分为几类,以宰相兼任吏部侍郎者,比较分散,数量在兼任官中所占比例虽相对不少,但并不限制到吏部侍郎职权的发挥,且因为兼任该职,对于宰相职权也是加强。其他以京畿长官,中书、门下二省职官,以及司卫卿、太常少卿、太子宾客及集贤院学士等兼任吏部侍郎的事例分析来看,都以吏部侍郎职掌为其重要或主要工作。
吏部侍郎与吏部尚书构成了唐代吏部机构的长官层次,从唐初继承隋制后,吏部即开始执掌官员人事问题,其中吏部司协助长官进行官员铨选,包括这一职能在内的职官人事管理职能则在有唐一代都毫无例外地保留着。不过,从70%以上的吏部侍郎未曾兼任其他官职的情况推测,该职事官应当说职务相对紧要,有诸多具体事务要做,与更高层面的吏部尚书不同,后者多兼任宰相,加上有吏部司与吏部侍郎协助,很多具体事务不必事必躬亲。另外,从以他官临时兼任吏部选事来看,在特定情况下,吏部侍郎法理内的工作在必要时还需要其他职事官专门临时承担。这些都体现了作为唐代职官制度中的选官制度的关键环节,吏部侍郎的职能在制度上给予了充分保障,以维持其特定职能的运行与发挥。除此之外,吏部侍郎担任者因为其特有的才能,会被委派去承担其他特定工作,如担负军事方面任务,这时候吏部侍郎的本职工作则不得任其发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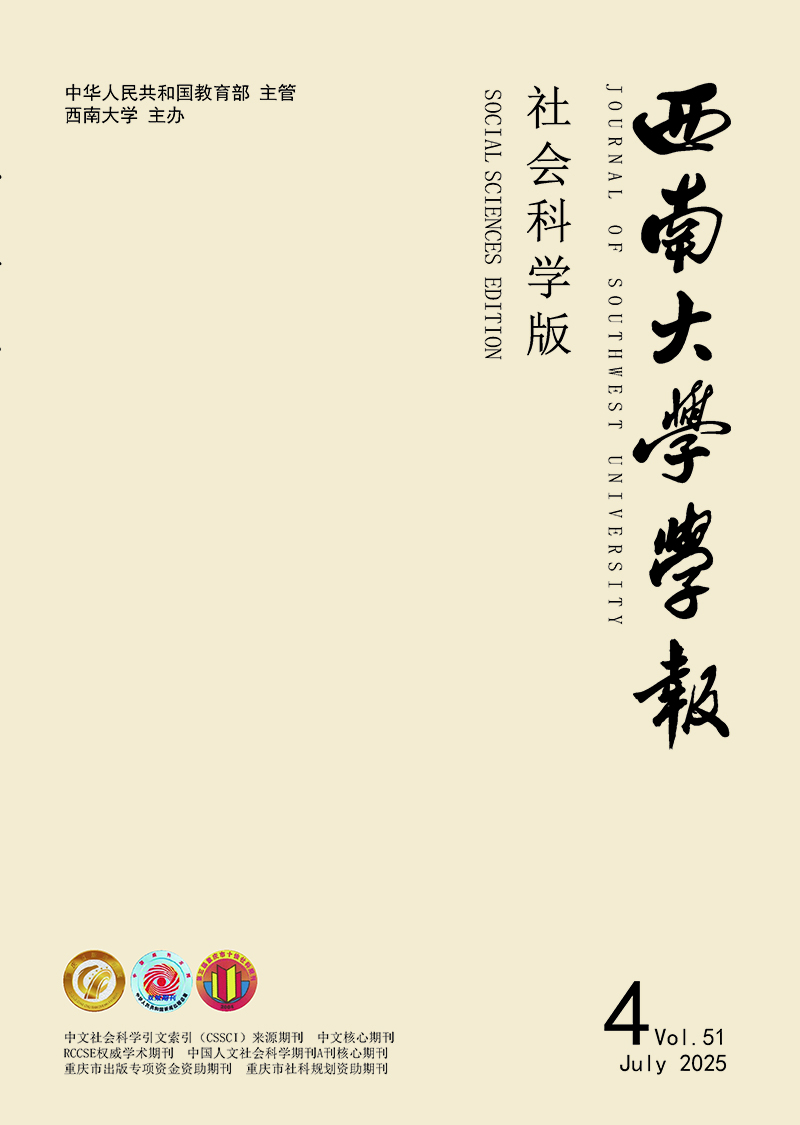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