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唐传奇武侠小说出现到21世纪“大陆新武侠”,每一时代的武侠小说家在为“侠”设置活动背景时,几乎都会选择一个与当下现实无涉的时空,无论这一时空是“明确历史朝代”“虚拟历史朝代”还是“淡化历史朝代”,都会基本指向中国古代社会之“历史”,以示所述是过去发生的。正是在这一时空前提下,小说家通过重现或“改变”历史生活图景,在塑造“侠”形象的同时,表现出对历史的深刻思考,揭示历史与文明进程的规律和意义。历史时空、历史想象、历史生活、历史规律等在武侠小说中的综合呈现及普遍存在,可以概括为武侠小说文体类型的历史性。
从现有研究文献看,历史与武侠小说的关系问题在1980年代以来的武侠小说研究中有一定涉及,主要可分四类:一是对具体作家作品历史运用的技巧、效果和价值进行研究,如张根柱对金庸小说“历史写作策略”的探讨[1],韩云波对黄易“探索发展”阶段回归历史的价值分析[2]。此类成果最多。二是对武侠小说史上某一时期历史与武侠融合情况及效果价值进行的整体判断,如汤哲声对历史与武侠融合带来的民国武侠小说繁荣的分析判断[3],肖显惠对大陆新武侠新历史主义观的分析揭示[4]。三是对武侠小说历史运用的某一具体类型进行研究和价值判断,如韩云波对“文明架空历史”类型的探讨[5]。上述三类成果相对于其研究对象而言,不乏深刻精辟之见,但都不是立足于武侠小说类型整体而将“历史性”作为武侠小说重要类型特征加以审视的。四是个别研究成果立足于武侠小说整体来研究“历史”,如蔡爱国论述了作为武侠小说叙事元素的历史,但他又认为“历史对武侠小说来讲并不是必要性的存在”[6]。此外,即使有当代小说家及研究者明确提出武侠小说的背景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观点,也多是在探讨其他问题时只字片语式的散论,并非专门研究历史与武侠小说的关系问题,并不能充分揭示武侠小说的历史性类型特征。
鉴于“历史”在武侠小说中的普遍存在以及目前研究的不足,应将“历史性”作为武侠小说的一个重要类型特征进行专门研究。从类型特征研究武侠小说的历史性,不仅能够弥补当前该领域研究的不足,而且可以厘清历史与武侠小说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确立历史性之于武侠小说的重要性和美学意义,从而有助于武侠小说文体本身的理论建设。本文拟在考察梳理武侠小说历史性表现基础上,分析武侠小说历史性特征的生成原因,并探讨武侠小说历史性特征的美学意义。
HTML
-
历史性从武侠小说出现就已表现出来,并在后世发展中不断强化。在此过程中,历史与武侠的结合不断深化,变化也越来越丰富。
-
自唐传奇开始的古代武侠小说,都将叙事时空设定在“历史”之中。唐传奇中数十篇与侠有关的作品,大都明确交代了朝代或年号,或是朝代年号兼而有之。如裴铏《聂隐娘》从“贞元中”写到“开成年”,《昆仑奴》时间设定在“唐大历中”,袁郊《红线》写“至德之后”,段成式《僧侠》叙“唐建中初”,许尧佐《柳氏传》从“天宝中”写到“天宝末”,薛调《无双传》写“建中”年间,蒋防《霍小玉传》写“大历中”,杜光庭《虬髯客传》从隋末写到“贞观中”。这些作品的作者虽然都是唐代人,但作者所在年代与作品所写年代都有相当时间间距,或几十年如《聂隐娘》《僧侠》《无双传》《霍小玉传》,或上百年如《昆仑奴》《红线》《柳氏传》,或二三百年如《虬髯客传》。到武侠小说发展较为成熟的明清,无论长短篇,多将时代背景选择在前朝。明代短篇小说《杨谦之客舫遇侠僧》的故事发生在宋高宗建炎二年,《李汧公穷邸遇侠客》的背景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从文末“只待包龙图相公做了府尹”可见是在宋代。明代长篇小说《水浒传》故事背景在北宋徽宗年间,《禅真逸史》以南北朝南梁与北魏对立为背景。明末清初,承《水浒传》余绪而成的《水浒后传》将背景放在北宋,《后水浒传》背景在南宋;成书于道光年间的《荡寇志》《绿牡丹全传》的背景,前者在北宋,后者在唐代武则天时期;道光、咸丰年间石玉昆《三侠五义》背景在北宋;晚清唐芸洲《七剑十三侠》背景在明正德年间。明清武侠小说也有写本朝的,但作者存世年代与作品所写年代相距数十年或百年以上。明代短篇小说《神偷寄兴一枝梅》所写嘉靖年间与作者凌濛初主要生活的万历、崇祯年间相距数十年。清代《儿女英雄传》所写康熙末雍正初、《彭公案》所写康熙年间,与作者文康所在道光年间、贪梦道人所在光绪年间,相距都有一二百年。
20世纪以来的武侠小说,普遍将叙事时空设定在“历史”之中。民国时期,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背景在清末,赵焕亭《奇侠精忠传》背景在清乾嘉年间,姚民哀《四海群龙记》背景在晚清,文公直《碧血丹心》三部曲背景在明代,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以康熙即位第二年为叙述开端,王度庐“鹤-铁”五部曲以清代为背景,郑证因《鹰爪王》故事发生在同治年间,朱贞木《七杀碑》以明末张献忠入蜀为背景。在新派武侠小说中,梁羽生主要以唐、宋、明、清四个朝代为背景;金庸主要涉及春秋、南北宋、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清代等,即如《笑傲江湖》《连城诀》《侠客行》等表面无明确朝代背景的作品,书中描写表明只能在中国古代;古龙小说看似完全抛开历史背景,但字里行间透露出叙事时空是在古代,如《多情剑客无情剑》中主人公李寻欢的“探花”身份及“一门七进士,父子三探花”的家庭背景,只能是在古代。在后金庸时代,温瑞安主要以南北宋为背景写“四大名捕”系列、“神州奇侠”系列、“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黄易以明代为背景写《覆雨翻云》,以战国为背景写《寻秦记》,以隋末唐初为背景写《大唐双龙传》,以两晋南北朝为背景写《边荒传说》等。在大陆新武侠小说中,凤歌《昆仑》《沧海》的历史背景分别在宋末元初和明代嘉靖年间;步非烟“武林客栈”“华音流韶”系列背景在明代,“天舞”系列背景在唐代,“昆仑传说”系列背景在隋代;小椴以南宋为背景写《杯雪》,以唐代为背景写《长安古意》《洛阳女儿行》《开唐》;碎石、拉拉的“周天”系列背景在西周,《逝鸿传》背景在五胡十六国;时未寒“明将军”系列虽无明确朝代背景,但朝野各方势力较量与争斗的故事同样是在古代;沧月“镜”系列与燕垒生“天行健”系列,虚构的朝代背景也是以古代社会为基本架构。
从唐传奇到大陆新武侠,作家作品众多不能尽述,但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到:其一,无论是历时性的千余年间的发展继承,还是共时性的每一武侠小说发展重要阶段的多样呈现,小说家虽然对“侠”的理解不同、创作追求不同、表现风格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将叙事时空设定在“历史”而非当下现实之中,表现出武侠小说历史时空设定的普遍性。其二,在时间设定上,作品中的“历史”距离小说家所在时代究竟有多远,古今小说家的选择有相同也有不同,同一时代不同作家的选择有相同也有不同,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选择也有相同和不同。从作品实际看,古代小说家一般选择本朝之前的某一朝代,或者选择本朝某一历史时期,但这一历史时期与小说家所在时期一般至少相距数十年以上,且不是同一位皇帝;现当代小说家一般都选择在民国之前的中国古代或近代社会,其中,选择近代社会如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江湖奇侠传》之类的较少,而以选择古代社会为普遍。其三,“历史”作为时空背景,主要有三种表现方式:一是“明确历史朝代”,有些比较简略甚至只有朝代名,有些比较复杂而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多有涉及,这一方式从唐传奇到大陆新武侠运用最多;二是“虚拟历史朝代”,表面虽无明确朝代背景,但江湖人物、朝廷势力、不同国家民族乃至人神交织等所构成的世界,展现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图景;三是“淡化历史朝代”,既无明确年代与真实历史人物,也不涉及朝廷官府,表面上似乎只是纯粹的江湖故事,但作品中的肖像、环境描写以及地名、人物身世家庭、江湖势力等,表明所述故事只能发生在古代。后两种方式在现当代特别是当代武侠小说中运用较多。
历史时空设定直观地表明作品中所述不在现实世界之中,而是在过去,从而与现实拉开距离。它是武侠小说历史性首要且重要的表现,武侠世界由此得以展开。
-
武侠小说的历史性可以只表现在历史时空的设定上,许多只出现朝代名或虚拟、淡化朝代的作品正是这样,如唐传奇《僧侠》《京西店老人》和古龙中后期小说。但武侠小说的历史性又不仅只表现于历史时空设定,历史时空设定既是时间距离但又不只是时间距离问题,在设定的历史时空中如何运用“历史”,既关联着小说家的侠义观念和创作追求,也关联着小说家的历史观及其对历史的思考与探索,甚至是对历史本质、规律、意义的可能性揭示。历史时空设定如上述所说主要有明确历史朝代、虚拟历史朝代和淡化历史朝代三种方式。这三种方式在具体运用上又大体可分为借用历史和架空历史两种方式。
其一,借用历史。小说家借“历史”表现“侠”之活动和精神,抒发现实感受,寄寓审美理想。最典型的体现是设置明确历史朝代,且多涉及真实历史人物和事件。具体可分两种:一是取材于真实历史人物和事件,在正史、野史、传说等材料基础上想象加工,虽不能说是“演义”但具有演义性质。如据宋史和传说而成的《水浒传》,平江不肖生根据晚清历史人物大刀王五、霍元甲等而写的《近代侠义英雄传》,文公直以《明史·于谦传》为依据再参阅野史笔记传说而完成的《碧血丹心》三部曲等。二是将虚构的武侠故事植入真实历史背景并与真人真事发生密切关系。与前一种方式相较,前者是在历史真实基础上的虚构,后者是将虚构依附于历史真实;前者是虚构服从于历史真实,是小说家立足于历史真实的想象,后者则是历史真实服从于虚构,是小说家根据虚构人物、故事而选择和想象历史真实;前者的主要人物一般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后者的主要人物则是虚构的“侠”,这种方式较之前者运用更为普遍,如唐传奇《聂隐娘》《虬髯客传》、金庸《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梁羽生《萍踪侠影录》《七剑下天山》、温瑞安“四大名捕”系列、黄易《边荒传说》《大唐双龙传》、凤歌《昆仑》《沧海》、小椴《杯雪》《开唐》等。在这一方式中,一方面是借用历史元素较多,包括设定明确的朝代或更具体的时间,出现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描绘设定时代的权力争夺及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杀伐,反映设定时代的真实政治文化生活、社会思想状况以及民风民俗等,因而对历史生活图景有非常丰富的重现和描绘。另一方面,当小说家在此过程中对“历史”有自觉的思考与探索时,常常能够揭示和反映出一定的历史规律和意义,如金庸小说之于民族对抗与融合、温瑞安“四大名捕”之于权力制衡之局、凤歌《昆仑》之于科学和人类能力延伸的探讨等。有的作品由于将“侠”的表现与真实历史生活图景、历史规律探寻等结合起来,甚至类似于历史小说,如金庸《鹿鼎记》就是如此。只出现朝代名及虚拟朝代、淡化朝代的作品,或许只是借“历史”作叙事时空以表现“侠”,并不涉及真实历史生活图景的复现与描绘,但亦可在小说家的历史思考中表现历史规律,如金庸《笑傲江湖》试图反映中国三千年的政治生活本质等。
其二,架空历史。这是21世纪以来首先在网络小说中出现的“历史”运用方式,并因此创造了一种新的历史小说类型。何谓“架空历史”?在目前尚不太多的研究中,下述说法较为准确:“指叙事主体面对既定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发展结果有所不满,从而对历史撰述加以虚拟改变的一种小说叙事。”[7]“从情节模式上看,它往往设定一个具有现代意识或现代身份的人,或是在一个虚构的历史时空,或是通过时空穿越的方式,回到正史记载的历史情境,通过一己的力量‘创造’了历史或‘改变’了历史进程。”[8]黄易《寻秦记》是公认的架空历史小说与武侠小说“穿越”开创之作,他的其他作品也有不少采用架空历史方式。大陆新武侠有众多作者以架空历史方式进行创作,主要可分为历史性架空(有明确朝代并涉及众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和虚拟性架空(虚拟朝代)两种,不过由于武侠小说更具幻想性,架空历史在武侠小说中的表现与在历史小说中的表现存在一定差异,有更多的奇幻或玄幻色彩。不同作者的具体架空方式也有不同,韩云波在“大幻想”小说前提下按架空程度的不同将“架空历史”分为三类:“一是人性真实历史,是在真实的历史朝代背景下表现以现实性为主体而又同时揉合了神性因素的人性冲突和文明反思”;“二是文明架空历史,是在虚构的历史朝代背景下表现具有文明进程意义的‘看不见的手’对人性与神性的束缚与叛逆”;“三是神性架空历史,在纯虚构的朝代背景和空间背景之下,以显性层面的神性隐喻文明进程中的人性与非人性的冲突”;方白羽“游戏时代”系列以及碎石、拉拉的“周天”系列,燕垒生“天行健”系列,“云荒三女神”沧月、丽端、沈璎璎的“云荒”系列,就分别是三类“架空历史”的代表作品[5]。这一概括或许不能涵盖大陆新武侠所有作家作品的架空历史运用情况,但作为整体勾勒还是比较清晰而准确的。
在“历史”的运用上,如果说借用历史的小说家主要持守传统历史观,表现为对已有历史撰述的认同,在此前提下展开叙事;那么架空历史的小说家则拥有更多后现代语境下“新历史主义”的特征,试图在叙事中“改变”历史撰述。架空历史虽然叙事主体色彩更浓,也常对“历史”进行“改变”“压缩”“变形”,以致有违真实历史生活图景,时空上可能“穿越”古今,但同样具有比较充分的历史性:一是其时空设定主要是真实历史朝代或虚拟历史朝代,即便由“今”穿越至“古”,也是以“古”为主;二是架空“历史”并非小说家任意而为,而是建立在对相关历史撰述的充分储备和分析判断之上,同时在有真实历史朝代背景的架空中还会有较充分细致的描述;三是小说家在架空历史中常常对历史和文明进程进行反思,揭示历史规律和意义,如黄易《寻秦记》《大唐双龙传》等“借武道以窥天道”对历史乃至人类命运的反思,燕垒生“天行健”系列对文明必然战胜蛮荒的历史规律的揭示。
借用和架空在“历史”运用方式上尽管有别,但二者之间并非不能融通,在借用中架空,或在架空中借用,二者都完全可能,如步非烟“华音流韶”系列的“半架空”就是如此。究竟是借用还是架空,或者是借用和架空的何种具体方式,又抑或是借用和架空兼而有之,不同小说家有不同选择,同一小说家的不同作品有不同表现,同时,因为小说家的学识与才力存在差异,具体运用上亦有笨拙与巧妙、表象与深层之分并因此决定作品的质量。无论是借用还是架空,小说家都主要将叙事时空设定在“历史”之中,或就此演绎较纯粹的江湖故事,或在此前提下进入历史,在复现或改变真实历史图景的同时揭示历史规律和意义。总之,自古及今的武侠小说普遍采取“明确历史朝代”“虚拟历史朝代”“淡化历史朝代”三种方式,将叙事时空主要设定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之中,并在这一时空前提下主要以“借用”和“架空”两种方式,或完全描绘较纯粹的江湖世界和“侠”的活动,或将江湖世界、“侠”之活动与真实历史生活图景描绘紧密结合起来,或让“侠”参与到“改变”了的历史图景之中,既塑造“侠”的形象又展示历史生活、探寻历史规律、揭示历史意义。历史时空、历史生活、历史想象、历史规律、历史意义等的综合呈现,显示出武侠小说具有充分的历史性。
一. 历史时空设定
二. “历史”运用方式
-
历史时空是武侠小说历史性的首要表现,其他历史性表现因之而产生。武侠小说叙事时空主要是历史时空,与小说家所在当下现实形成疏离,与中国古代小说讲史传统、小说家的历史知识储备和个人兴趣等不无关系,原因则在于“侠”之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武侠小说的文体需要。
-
“侠”作为现实实体究竟出现于何时,学界虽有争论,但较普遍的说法是春秋或春秋以前,如徐斯年认为:“‘侠’作为一种具有特别气质的人,起源甚早,见诸典籍,至少在春秋时期即已不乏典型。”[9]4《韩非子》对“侠”的描述和攻讦,《史记》《汉书》记载的诸多个体和群体,确证了“侠”在春秋战国秦汉时代的真实存在。汉代以后正史撰述虽不再为“游侠”专门立传,但并不表明“侠”不存在。首先,“侠”能否入正史,既取决于“侠”的实际存在及影响,也取决于史家的价值判断。正史不为“侠”立传并不说明现实无“侠”,因为芸芸众生中具有轻财轻生气质和重交情守承诺者大有人在。其次,正史述“侠”并不只在“游侠”之传中,无“游侠”之传并不意味着其他人物传中不述“侠”,如《晋书·祖逖传》之“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旧唐书·郭元振传》之“任侠使气”等。再次,“侠”虽不入正史,但在各种野史笔记及传说中并不难寻踪迹,如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宋代吴淑《江淮异人录》、清代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中记载的诸多侠客及事迹,“杂俎笔记所录,固然是采诸委巷杂谈,其事未必可信。但多少仍可反映侠的一般状况”[10]68。“侠”在东汉以后仍然十分活跃,隋唐豪侠、宋明绿林、明清帮会即是其典型而生动的存在形式。
“侠”在中国古代长期积淀而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武侠小说正是在这一文化传统中于魏晋萌芽、唐代成形、明清成熟起来的反映中国社会、表现中国人价值观念的本土小说类型。它与“侠”文化传统的关系是互动的:一方面,历代小说家尽管面对的“侠”文化传统在丰富和深厚程度上有别,但“侠”的历史存在及文化传统无疑是武侠小说展开想象的重要依据。没有“侠”文化传统,就没有武侠小说的诞生和发展,小说之“侠”走进“历史”自然是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历代走进“历史”的小说之“侠”,既反映历史又表现当下的文化现实,成为“侠”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激发小说家的创作激情。对武侠小说家而言,自春秋至清末绵延不绝的“侠”的存在和文化传统,就是他们创作的想象之源与历史文化前提。
-
“侠”是什么?最早言“侠”的韩非视“侠”为“肆意陈欲”的“暴憿之民”,司马迁在“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的前提下高扬“侠”之“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等品质。韩云波考察“侠”之古代历史的真实存在后认为:“侠有求生存、反秩序、讲义气、尚武功的一面;又有享乐、捣乱、小我、强暴的一面,侠就只能是在英雄与流氓之间蹒跚前行。”[11]龚鹏程强调古代之“侠”可能“只是一些喜欢飞鹰走狗的恶少年,只是一些手头阔绰、排场惊人的土豪恶霸,只是一些剽劫杀掠的盗匪,只是一些沉溺于性与力,而欺凌善良百姓的市井无赖”[10]2。“英雄”与“流氓”或者“侠”与“盗”,究竟哪一面才是“侠”的本来面目?“侠”与“盗”多有相似之处,如轻生死、重义气、喜结拜、犯法令等,区别只在于行为的价值准则不同,当其济危扶困、义薄云天时为“侠”,当其横行乡里、欺凌弱小时则为“盗”。“侠”“盗”可分离亦可一体两面,既能彼此接纳也能相互转化,情况非常复杂。如果说,自先秦而始的古代之“侠”是“侠”“盗”杂处而渐次由“侠”及“盗”;那么,现代黑帮则主要是“盗”,如源自清代又活跃于民国的洪帮(天地会)、清帮已“由反清复明的团体蜕变为反共卖国的黑帮”“由社会秘密结社蜕变为流氓地痞聚集的黑窝”“由民间下层互助组织蜕变为社会的黑瘤”[12]。由“侠”而“盗”,离“侠”的价值标准虽已渐行渐远,但从文化本源来说,视之为“侠”亦可,如鲁迅言及“流氓的变迁”时所言:“‘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13]现当代小说家既然都面对着所在当下“侠”的现实存在,按说以现实之“侠”为对象进行创作或虚构“侠”在当下现实中的活动并无不可,并不是非要将“侠”放在“历史”之中,然而,现实之“侠”的性质让小说家不便做出这样的选择。
其一,现实之“侠”与小说之“侠”有距离。小说之“侠”是小说家的审美创造,塑造的“侠”之形象虽然古今有别,但整体上主要是作为公平正义、独立自由的符号出现的,具有理想性和幻想性,因而小说家不仅更关注和强调“侠”的“英雄”一面,如反专制、抗压迫、尚独立、求自由、助弱小等,而且会把“英雄”一面尽可能放大。现实之“侠”的“盗”或“流氓”一面并不符合小说家的审美要求,承载不了小说家对于“侠”的精神赋予。
其二,现实之“侠”无论是“英雄”气盛还是“流氓”气浓,对既定社会秩序都必然产生威胁、对抗和破坏,因此常遭打击。小说之“侠”虽然不是现实之“侠”,但其更加理想化的“英雄”一面可能比现实之“侠”的破坏性还要大。若是让“侠”在现实时空中放纵施为,凌驾于法律之上自掌正义,而且还要以欣赏的态度讴歌之,作为现实个体而存在的小说家不能不说会有很多禁忌而很难自由书写,“侠”也因此很难得到充分描述,或者即使书写出来,恐怕也难以传播出版。所以,小说家在创作武侠小说时,一方面会基于自己对“侠”的理解,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对“侠”尽可能进行符合当下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改造;另一方面需要采取将叙事时空与当下现实社会隔离的叙事策略,让“侠”进入“历史”,这样,既符合历史传统,又能避免与现实贴得太近而可能产生的种种限制与束缚,从而更加从容地叙事,让“侠”可以更加自由地纵横驰骋。古代、现代小说家需要采取这样的叙事策略,当代小说家更需要采取这样的叙事策略,因为日趋完善的民主与法制秩序不容藐视和践踏,故其最佳叙事时空是中国古代的专制社会,正如金庸所说,武侠环境是“中国古代的、没有法制的、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不合理社会”[14]。
-
春秋以来现实之“侠”或有“武”或未必有“武”,有“武”之侠可以“以武犯禁”,无“武”之“侠”则凭义气立身扬名。从唐传奇开始,“侠”与“武”渐渐融合起来。“武”与“侠”的融合奠定了武侠小说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文体规范,二者缺一不可,因为有“侠”无“武”则“侠”不能有效行侠,有“武”无“侠”则失去武侠小说的类型根本。所以“武”之描写既是判断武侠小说是否为武侠小说的根本依据之一,也是衡量小说家水平及作品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因此,小说家不仅不能不写“侠”之“武”,而且还要将“侠”之“武”写好。于是就可以看到,唐传奇以来,“武”之描写日益从单一到丰富,从简单到复杂,从笔墨较简到极力渲染,尤其民国武侠小说以来,一方面是源自唐传奇的充满道术、法术之气的“武”更加具有仙魔、奇幻色彩,另一方面是源自实有传统武术而较为朴实的“武”之描写开始走向“纸上功夫”,成为小说家施展才学、驰骋想象力的重要所在,几乎所有杰出小说家都在为如何创造出自己的“武学”而煞费苦心。对读者来说,“武”之描写也成为吸引读者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人们喜欢看武侠小说,其根本的原因之一,便是人们对武功及其打斗的激烈、紧张、精妙甚至恐惧的场面与细节的爱好”[15]。
问题是,侠客叱咤江湖所必须凭借的“武”,无论是技击还是道术,无论是刀剑还是拳掌,也无论是实际存在的中华传统“武术”还是小说家极尽想象力而创造的与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科学等相结合的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匪夷所思的“武功”,都只有存在于以冷兵器为主的古代历史时空中才能激发出读者的阅读想象,并在想象中认同,从而显得可信。反之,倘若将“侠”放在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单凭人力根本无法抗衡的热兵器肆虐的现代社会,虽然不能说“武”毫无用处,但是极尽“武”之夸张描写,让“侠”完全依靠拳掌、刀剑或者某种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内涵的神奇“武功”抑或法术、道术在枪弹纷飞中行侠仗义,而且完胜敌人,未免显得荒唐可笑;而如果弱化“武”之描写,既不充分也不神奇,或者干脆让侠客弃“武”而拿枪弄炮,武侠小说的趣味又将大打折扣,甚至是否还能称之为武侠小说,恐怕都是一个问题。因此,要尽显“武”之神妙、魅力,对民国以来的武侠小说家而言,都需要将叙事时空放在古代。
-
“传奇”作为唐代文人表现文采以获取名声、增加科举考试成功性的“行卷”,可谓穷尽想象力之极致。其中的武侠作品更是鲜活表现出“传奇”二字的意蕴,如“侠”之身份的卑微性与遇事之际侠客本色显现的突然性,行侠过程中道术、法术、剑术之“武”的超凡性,行侠之后飘然不知所踪的神秘性等,武侠小说的“传奇”特征由此初步奠定。后世武侠小说的传奇性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小说流派、不同作家笔下虽然不尽相同,但总体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或仙魔斗法、或半人半仙、或现实人生的想象世界,各种门派、帮会、势力构成的复杂险恶、波诡云谲的“江湖”,“侠”在成长、行侠过程中经历或遭遇的各种奇人、奇事、奇境、奇物、奇情,道术、法术、神力之“武”或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和内涵的“武”之描写的玄妙,报恩复仇、夺宝伏魔、正邪相争、王霸雄图、权力制衡、战争与和平构成的激烈矛盾冲突,悬念、巧合、意外、误会、计谋等手段充分运用而产生的情节跌宕起伏等,都具有强烈的传奇性,这在文化积淀中迅速成为江湖世界的叙事法则,成为武侠小说的重要类型特征。
传奇性意味着非常性、超常性,意味着与现实中人的正常认知和日常经验的不相符合。现实世界当然也存在各种“奇”,但武侠小说所“传”之“奇”构成的浪漫而波诡云谲的江湖世界,与现实世界存在较大距离,自不便与现实发生联系。只有与现实拉开距离,才能让读者在想象中觉得“可能”而接受,正如徐斯年所说:“传奇性很强的武侠小说体裁,宜乎处理产生于相对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不为常人所知的素材,以及与现实距离较远的素材。”[9]163-164要与现实拉开距离,“历史”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中国几千年浩瀚深邃的历史传统,正史、野史、笔记、传说等历史记录的不相吻合以及无论怎样记录都会遮蔽掉的丰富、可能的历史内容,国家分裂与统一、民族杀伐与融合中的历史转折,权力倾轧、势力角逐的激烈冲突,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偶然与变数,“侠”的流动、变化、建功与挣扎困斗等,都可以为小说家书写传奇提供巨大而无尽的想象空间。当然,与现实拉开距离书写传奇不一定选择“历史”,还可以选择“未来”,但问题是,一方面,历史是已发生的因而遥远且蕴含丰富,未来是未发生的因而可以预言幻想但虚无缥缈;另一方面,特别是对现当代小说家而言,“侠”作为实体丰富地存在于中国古代历史之中,而于现实基本无存,遑论未来?武侠小说渲染之“武”主要在冷兵器时代,在高科技主宰的未来时代缺乏描绘空间。武侠小说的根基和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历史为背景就可以充分吸纳和展示传统,而若将背景放在未来则难以保证武侠小说的中国特色。所以,“未来”的不可知性和虚构性或许可以让小说家书写传奇,但更具必然性的选择应该是“历史”。
中国古代社会“侠”的存在及因此形成的侠文化传统,是武侠小说历史性生成的历史前提和文化前提;作为英雄之“侠”的形象塑造、玄妙神奇之“武”的渲染、传奇江湖的描绘等要求,是武侠小说历史性生成的文体前提。二者交互作用,使历史时空成为武侠小说得以具有本土性、文化性、想象性、合理性、可信性存在的必要时空。在这一意义上,武侠小说虽然不是历史小说,但历史性无疑是武侠小说这一中国传统小说类型的根本属性。
一. “侠”的历史存在与文化传统
二. 作为英雄之“侠”的形象塑造
三. 玄妙神奇之“武”的渲染
四. 传奇“江湖”的描绘
-
历史与武侠的融合方式和程度因作家自觉意识、历史素养、创作追求等因素的不同而有差异,所能产生的美学效果自然也不同。从整体看,历史性之于武侠小说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
-
理查德·泰勒认为:“艺术世界的真实性可能近似于生活的真实,近似于一个日常现实生活的环境。但是,作者也同样有可能表现一个观念、一种理想,或一个与我们所了解的世俗存在的细节和行动几乎没有什么明显联系的存在状态。”[16]武侠小说家创造的江湖世界、塑造的“侠”的形象属于后者,因为,“武侠小说之所以被人视为‘成人的童话’,便在于其通过对所谓‘大侠’形象的重塑与改造,对现实世界的生活实况做出了一种成功的艺术超越和诗性逃避。关键在于,没有这种以浪漫主义文学原则为依据的‘诗性逃避’,也就没有成功的艺术超越;没有这种艺术超越,也就没有优秀的武侠叙事所独有的艺术价值”[17],这种诗性逃避和艺术超越的重要前提正在于进入历史。
进入历史从而实现对现实的艺术超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从小说家看,无论基于何种现实感受,抒发何种哲理情思,表达何种观念理想,将江湖世界放在历史之中而与所在现实世界隔离,无论是借用历史还是架空历史,都意味着小说家对现实可能产生的一切束缚在精神上实现超越,从而真正进入审美状态,任由想象力肆意放纵,天马行空地进行审美创造。如主要通过虚拟架空历史方式创作奇幻武侠小说的沧月所说:“感谢奇幻这种体裁的存在,给我提供了最广大的舞台,让我有一种天高海阔的自由,可以摆脱一切束缚,淋漓尽致地描绘着心中所有梦想——这是其他体裁所不能给予的。”[18]其二,从小说家创造的江湖世界看,因为进入历史,所呈现的是一个寄寓着小说家审美理想而不同于现实“世俗存在”的幻想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侠”可以经历各种奇幻惊险的人生,身怀各种可以睥睨宵小、傲视群雄的武功奇技,身陷各种激烈的矛盾冲突,遭受各种艰难困苦,甚至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但最终从弱小到强大、从平凡到超凡,完成或报恩复仇、或锄强扶弱、或破案擒凶、或保家卫国、或追求自由、或挑战自我、或向往和平、或改变历史的使命,成就正义与理想的神话。这个正义与理想的神话超越于现实之上,形象而深刻地浸润着世人之于公平公正、自由平等、和谐和平等人类价值的渴望。其三,从读者看,在进入武侠小说的历史时空而暂时与真实生活隔绝的阅读时空中,因生活困顿而产生的烦恼与苦闷可以在无奇不有的江湖世界中忘却,因现实的卑微与无力而产生的无奈与痛苦可以在领略“侠”的无所不能时得到释放,因社会不公而产生的不满和渴望可以在“代入”“侠”的恣意与狂放中得到宣泄,从而也在精神上实现自我超越。
-
“奇”与“真”是相互矛盾的统一体。只“奇”不“真”,奇则奇矣,也能产生超越现实的美感,但难免流于虚假甚至荒诞不经而不可信;只有既“奇”又“真”,“奇”而致“真”,才是最高境界。金庸认为:“因为武侠小说情节离奇,许多事情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有了历史背景,可以增加它的可信度。”[19]这是武侠小说解决“奇”“真”矛盾关系的重要方式。小说家在无限扩张其想象力从而描绘超越现实的江湖世界时,借用历史背景的多少和强弱程度,直接决定着读者对作品接受的真实感。一般来说,历史背景中真实元素少而弱则传奇色彩更浓,历史背景中真实元素多而强则既“奇”又“真”。历史背景在武侠小说中最充分而典型的运用,莫过于在小说中设定明确的朝代,出现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反映所设定时代的真实政治文化生活,描绘所设定时代的真实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杀伐,让“侠”与历史人物发生联系抑或“侠”就是由历史人物演义而成,让“侠”参与进入历史事件以及国家民族间的斗争与政治生活之中。江湖传奇之“假”与历史背景之“真”相间,“虚构”之“侠”与“真实”历史人物和事件交织,其结果是“真”因“假”而演义得丰富生动,“假”因“真”而变得可能可信,以致“真”“假”莫辨,似乎历史原本就是这样发生的,似乎小说描写之“侠”真的这样存在过。汤哲声认为:“武侠小说在江湖世界里,增强了小说的传奇色彩,但是故事有一种缥缈之感,以历史事件为背景,不管武侠故事如何传奇,它都有了‘根’,给人以真实之感和厚重之感”,因此,“历史学科的介入给予武侠小说美学构成的最大贡献是‘真实性’”[3],这一断语是准确而合理的。
-
侠客适意任性的场所主要在“江湖”——似乎独立于既定社会秩序之外的时空存在,多涉山林、民间社会,与“江山”——朝廷官府、国家社稷、民族存续相对立。如果说“江湖”主要在锄强扶弱、济危扶困、正邪相抗中表现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人性善恶,那么“江山”则主要在权力争夺与制衡、朝代延续与更迭、民族冲突与融合中表现政治本质、历史兴衰、文明进程。将真实历史背景与武侠传奇相结合,就是将“江山”与“江湖”相结合,将国家社稷与民间社会相结合,将政治本质、历史兴衰、文明进程与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人性善恶相结合。将“江湖”与“江山”相结合,让“侠”身在“江湖”而心系“江山”,游走于“江湖”和“江山”之间,甚至更多地涉足“江山”,不仅可以增强武侠传奇的真实性,而且可以因朝代变化而产生变化性,更可以在此视野之下充分展开和容纳广博深邃的社会生活内容以及小说家基于现实感受和认知对人性价值、文化精神、历史发展、社会理想、文明进程的深刻思考,从而呈现出叙事内容的深广性。
虚拟朝代和淡化朝代的武侠作品同样可以具有内容的深广性。虚构朝代但仍以“江湖/江山”为基本架构表现“侠”的作品,尽管其“江山”因虚拟而与真实“江山”无涉,但其外在呈现的势力角逐、国家征战、民族杀伐、朝代变换以及内在暗含的小说家对历史、文明进程的整体深刻洞察,无疑具有内容的深广性,如燕垒生“天行健”系列就是如此。淡化朝代或有朝代名却极少涉及具体真实历史内容的作品,虽然更像是纯粹的江湖传奇,其深广性可能相对较弱,但如能在不同于现实庸常的激烈矛盾和斗争中深刻揭示人性如古龙小说等,或者借助这一江湖传奇深刻揭示人性同时表达对中国历史与政治本质的深刻思考与认识如金庸《笑傲江湖》等,也能显示出内容的深广性。
可以说,历史的博大精深既深蕴过去又昭示现实与未来,历史视野下的武侠世界必然产生内容的深广性,只不过深广度会因历史与武侠传奇融合的方式、程度以及小说家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
武侠小说家自己无论是否身在“乱世”,他们给小说选择历史背景或虚构朝代时,常将“侠”的具体活动时空设定在“乱世”。何以如此?一般而言,“乱世”之中,统治者因政权不稳、江山失固而无心也无力对“侠”予以约束和打击,甚至需要借助“侠”的力量;社会因纲常废弛、王法难顾而秩序混乱、人祸不断;百姓因烧杀抢掠、压迫摧残而流离失所、无辜牺牲。“乱世”对统治者、社会以及百姓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却正是“侠”可以仗剑行侠的广阔空间,正如陈平原所说:“游侠精神本质上与法律、秩序抵牾,故其最佳活动时空为‘乱世’。”[20]
“乱世”背景设定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小说家将历史背景设定为“乱世”,固然是为了让“侠”能够更自由地任性使气,路见不平而拔刀相助,但更是为了让“侠”在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能怀着强烈的家国意识,以天下苍生为念,担负起拯国家民族于既倒、救黎民百姓于水火的历史使命。这在民国以来的武侠小说特别是新派武侠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越是民族冲突异常激烈、国家存亡系于一线、百姓生灵涂炭的“乱世”背景,越能充分表现“侠”之为国为民、谋求和平而勇于奉献牺牲的英雄壮举。自然,在现实之中,国家兴亡、民族独立、百姓安康并不能主要凭借“侠”的壮举,“侠”也无力担负起这样的责任;而在纯粹的江湖传奇中,也并非不能塑造出独立自由、悲天悯人、冲破重重艰难险阻而伸张正义,让读者为之心摇神驰、寄托无限遐想的“侠”的形象。当小说家在审美创造中,让“侠”既身在江湖又心系天下,既有江湖人物的恩怨情仇又有历史英雄的壮怀激烈,既追求独立自由又关心百姓疾苦,既在一般江湖世界里重义轻生又在历史兴衰、国家存亡时挺身而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作为这样一种审美形象而存在的“侠”,其形象无疑更加丰满生动,也更具有悲壮感、崇高感,其精神感召力也会更加强大。
一. 现实的超越性
二. 感受的真实性
三. 内容的深广性
四. “侠”的形象塑造的丰满性
-
叙事时空为历史时空而非当下现实时空,在此时空下展开叙事,塑造“侠”的形象,是武侠小说自古及今的普遍表现。不过,并非所有作家作品都以历史时空为叙事时空,特别是从当代武侠小说来看,并非所有作家作品都以中国古代社会为背景。表现大致有四:其一,以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为叙事时空,如慕容无言的“唐门”系列、“大天津”系列。其二,以当代现实社会为叙事时空,如古龙《绝不低头》,温瑞安“今之侠者”系列、“六人帮传奇”系列,九把刀《功夫》及“杀手”系列中的多部作品。其三,以近代以来百年社会发展为叙事时空,如张大春《城邦暴力团》,既涉清末又写民国以及抗日战争,直到台湾当代现实,而且落笔即从当代现实写起。其四,以未来社会为叙事时空,如黄易《星际浪子》,尽管学界对于《星际浪子》是否是武侠小说存有争议,但从武侠小说角度看则可以认为是“科幻与武侠深度融会”[2]。
这些作品的存在是否可以成为否定当代武侠小说的叙事时空主要是中国古代社会,进而成为否定武侠小说历史性的依据呢?显然是不能否定的。其一,以民国以及抗战时期为叙事时空,虽然不是中国古代社会,却相对于当代社会本就是历史,与武侠小说的历史性特征并不矛盾。其二,这些作品有的是小说家在创作大量以中国古代社会为背景的作品后的一种求变和尝试,如古龙、温瑞安,有的是小说家为探求武侠小说创作新的可能性,如黄易、张大春、九把刀等。其三,这些作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目前都远逊于以中国古代社会为背景的作品。
当代武侠小说主要指向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性,这是武侠小说历史性的重要表现,但它不应成为创新的桎梏。从“后金庸”武侠看,为不同于甚至超越于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既往武侠小说,小说家们大多有立足当下的创新意识,并自觉致力于各种探索及文体实验,如“盛世”武侠的描绘,科幻、玄幻、动漫、游戏元素与武侠的融合等,叙事时空的上述改变只是文体实验中的一种表现。这种改变值得肯定和赞赏,至少它丰富了武侠小说的叙事时空,至于是否可以因此开辟武侠小说创作的新天地,目前尚难以判断,因为这样做有很多关系难以处理,例如“侠”之“武”与包含枪炮在内的高科技“武力”、“侠”之“奇”与人们的正常思维逻辑和认知、“侠”之“行”与民主和法治的社会现实、“侠”之“精神”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等各种关系之间的分寸,并不容易拿捏,但着眼于武侠小说的发展,不妨一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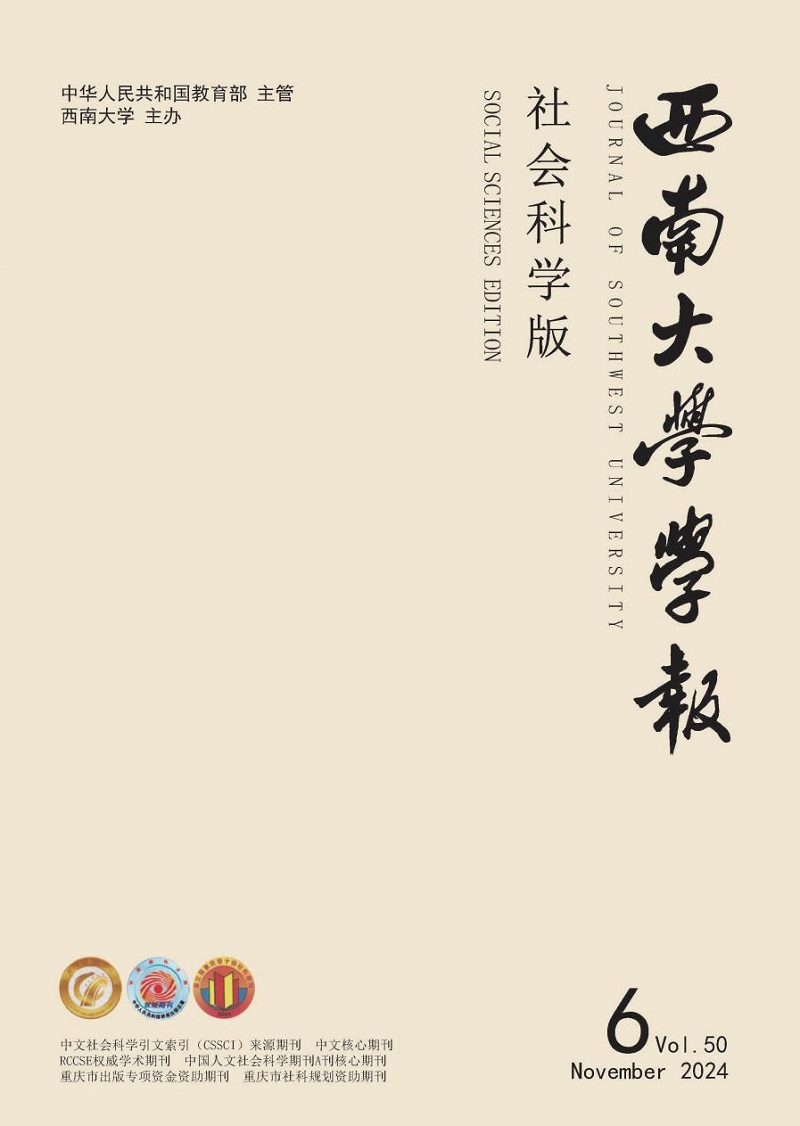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