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以来随着商业的大发展,商品经济有了显著提升,各地商人不断走出去,形成了如“晋商”“徽商”“陕商”“粤商”等十大商帮。这些商人到全国各重要市镇,在那里交易商品、构建网络、打造人脉,在那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传说。为更好地打开市场,快速了解所在地的商业信息,同时又保证本地商业队伍的有效凝聚,各地开始出现大量商业会馆。它不隶属官方,也非私产,而是当时商人队伍壮大、商业能力提升后的社会组织。
会馆,滥觞于宋代,明清时开始活跃,各地商帮将其设于各主要金融中心、商贸集散地及重要城镇、码头,是彰显本地商人、商业实力和当地商业状况的重要指标。会馆在京城设置较早,可溯至永乐十八年(1420)[1]14-17,即从应天府迁都北京后。此后会馆职能不断增加,成为非定期讲学处和科举试馆。随着明代社会风气的转变,“士商合流”趋势加强,会馆渐具工商性质。早在汉代就有“郡邸”,属公产性质,且有政治和商业共存的现象,这与明清会馆有类似特点[2]94-95。其中工商会馆,分为手工业会馆和商人会馆[3]。明代地方会馆以赣、闽、浙、徽为多。万历时,山、陕商人才在京师设立会馆,但明显北少于南[1]15-16。明清会馆完全因商而生,以粤商最早[2]。会馆出现的首因即市场扩大、商人增多[4]。
会馆研究学界成果丰富。大多只谈及会馆本身,从其功能调整[5]、戏曲发展[6]等内容。还有海外学者论证会馆与公所[7]337。国内从历史沿革角度论证,如张正明[8]、朱英[9]等。但缺乏构建原因的内在解读。对传统会馆碑刻的功能扩展与内容解读尚显不足[10]。目前多视为史料补充,以补充地区商业资料,整合相关数据,分析一地经济发展,体现行业商人的地位。以经济数值判断地方商业和金融资本、经济水平的增衰,如刘建生[11]、许檀[12]、郝平[13]等。
笔者通过对商业碑刻的细读,分析晋商会馆的构建原因,展现时代局限下晋商的突破和变通,它的建立促进商业行为的有效完成,而非仅为府、县接待处,商业组织才是它的基本特征。本文拟在前辈学者广泛研究的基础上,以会馆碑刻内容深入探讨明清山西商业会馆的发展历程,探索明清易代过程中商人的积极变化,体现历史变幻下会馆构建的历史动因。
HTML
-
碑刻是古代中国常见的一种记述政治、社会、文化内容的载体,形式多样且含有丰富的社会发展信息,是古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心雕龙·诔碑》:“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14]它多以镌刻有文字的历代碑、碣、造像碑、经幢、石幢、摩崖题记、墓志铭、画像石等主要形式。碑的最初用途并非刻字,而是充满实用价值。如观日影、测方向、记时刻等。在汉代是下葬时起固定作用的装置[15]总序。古代碑刻应用广泛,除以上作用外,渐有记述的传统。始皇横扫六合,开始巡行天下,就展现碑刻记述的多样:“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禅梁父,刻所立石。”[16]242以上共有三次用碑刻书写的过程,其中就有碑刻书写的功能:颂德,祭祀,歌功。此外还有其他功能[17]①。
① 此外还有哀诔、歌咏、颂扬、示范、铭记、图文、应用等用途。
明清以后,碑刻的书写与记述作用依然保持,只是根据行业需要有所调整,且应用于当时经济社会的诸多方面。它在明清晋商与会馆构建中的作用更为明显,多得益于它具有易保存的特点,利于证史、补史[15]。达到“至于馆之所以立兴,夫馆之所由名,则前碑具在,余无赘焉”[18]436的效果。明清各地山西会馆在构建、维修后都会以碑刻对其行为进行记述或说明,碑刻流行至明清除外观庄重外,彰显厚重、不易毁损亦是一因。从会馆语言优美、用词考究的碑文可见其碑刻树立有三大用途。
-
会馆不是官方或民间筹建起来的,而是一群初来乍到且无依无靠的商人所建,它急迫且必需。“自示之后,□遇西商多友无家可归,身后别无亲丁,□埋义地,□用扛夫者,永远□本孙的定抬价□给不侍。”[18]531正所谓“感同身受”,因为是曾经无助的亲历者或见证人,因而希望后人或会馆成员能以同理心将其传递。还有对出资身份和资金来源的介绍:“一则出之于吾乡之铺户也,开设有地,而子母常权;一则出之于吾乡之行商也,来往不时,而懋迁有术。”[18]437这就说明商人与会馆的关系,既是会馆的建设者,同时也带动商人的成功。
建设过程很是不易,所购土地、房屋的位置、基础条件造成会馆基建的难易不一。“第阁虽告竣,而院落未成,阁旁之广狭不一,阁下之坡坎须平,势处卑下,而水之所聚,雨辄为忧境……且无以壮观瞻,无以便应酬,无以骋眺望,而备梓材,尔时未议及之想,亦绌于力限于势,不能不有待于后也。嘉庆八年,杜瑞隆、潘交泰等接理会事,昼夜经营于二十年,乃于其中之卑者高之,则土不惮运而陂坎胥平也,隘者扩之,则地不惮购而广狭维称也。”[18]436商人只是群体的代称,但由于记述不足、遗失无考等原因,使很多人的名字湮没,若能有幸记录就很值得后人尊敬。“建祠于兹者……迄于今百数十年矣,续修者不一而足。道光癸未,王恒吉等嗣首其事……谨据事之始末。”[18]458-459
-
国有国法,行有行规。既然是一专门的商业组织,其繁杂的事务、混杂的人员必然要以严格的行为守则应对各种复杂的往来。“都会之成规,安商即所以惠民,至于久而相安,人人称便之事,更不容平地生波,以滋扰累也。”[19]104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稍有不慎损失的就不仅是金钱,更可能卷入诉讼纷争。“一从实业重商权,集股纷纷嚷破天,引出许多绷子手,招摇诡诈尽磨研。”[20]95
1.房屋契约妥存,无论古今中外、于公于私,土地购置都是一项重大事务,购买前手续应交割清楚,之后妥存契约印信,以免造成纠纷。但会馆初期由于管理经验不足、责任心缺失,时常出现契约毁失、权责不明的现象。因此通过碑文书写展示利权,宣示对所在会馆房屋、土地的所有权,以避免日后的麻烦。如“将红契存于秋会匣内,年深日久,恐有遗失,因此立石”[18]342。“内有东房四间,因暂放动产,讨限十五日腾交,具结在案。”[19]842且很注意内部秩序的建设,尤其严格管理与约束内部经营与人员往来。“优人不戒于火,延烧戏台山门暨钟鼓二亭,嗟乎!数载经营一朝毁之,物之难成易败也如此哉。”[18]476否则极易遭受无端损失,“蔡盛名适求出相识之人说合,情愿代书雇约,保其看馆……甫两越月,即私行典当馆中器具,(蔡)素知馆契纸久遭回禄,遂妄据火神庙与会馆仙翁庙毗连,陡起贪夺之心,致与涉讼坊城”[19]109。
2.行规制定,营商是商人主业,既不应弄虚作假,也不可随意受损。此类碑文是以文字的书写表明本行业的固有态度,如“本镇之有杂货行由来已久,似无烦于再议矣,第以人心不古,规矩渐没,或翼重资弄巧成拙,或□□□头循私而害公,因是赔累莫支,以致倒塌之患者有矣”[18]379。“颜料行桐油一项,售卖者惟吾乡人甚伙,自生理以来,绝无开行店□,亦绝无经济评价,必本客赴通自置搬运来京,报司上税,始行出卖……有网利傅天德者,既不开行,又不评价,平空索取牙用,捏词叠控,幸蒙都宪大人执法如山,爱民如子,牌批云‘凡一切不藉经纪之力者,俱听民之便,毋得任其违例需索,扰累铺户,致于未便。’龙图再世,其在安居乐业者,固应歌功而颂德。”[19]104每当在此情形下,“行客闻之胆战,每每发货他处,铺家见之心寒”。杂货行通过公议规程,去除原有弊病,达到“主客两便,利人利己,不必衰多而益寡”的成效。“前有行规,人多侵犯,今郭局同立官秤一杆,准斤十六两,凡五路烟包进京,皆按斤数交纳税银……各循规格,不可额外多加斤两,苟不确遵,即系犯法,官罚银不等。”[19]129这就赋予行规更多的法律意味。
3.处境调整。商人初到异域,人生地不熟,乡土社会中原本“熟悉”的规则逐渐失灵。这就使商人需要勾连地方官员、豪强,取得地方的庇护,帮助自己解决各种难题,进而表现出了商人在当地的“不一般”。如“敬演之时,竟有一种在宜人后声言拿戏需索讹诈,实属不法,合并出示晓谕”。“向来每逢敬神演戏,文武大小衙门并无阻扰,后因乡地兵役舞弊诈索,阖镇赴城。官蒙府宪陈太老爷出示晓谕,阖镇遵□,勒石以垂不朽云。”[18]380此碑文除感谢陈府宪的帮助外,还借机与官员熟络。且可避免下次“麻烦”的来临。晋陕豫三省“各商来苏办货者,向从浦口行运,由来旧矣,各走各路,听其自便,而按时销贩,从无愆期……同治八年冬……督抚宪出示,令三省之商,概由淮关行走,即淮关报税……众商于是惊讶……几欲停止不运……不日荷蒙恩准,仍由浦口行走……此诫大宪体恤商情之至意,第恐日久又有异议,将禀批示论勒石……分寄各省马头存储”[19]168。但解决不法行为的利器却是官方晓谕,而非国家律令。一旦官商“反目”,受苦的还是商贾。
-
开门营商,信字为先,为避免竞争恶化(和为贵),同时也防止本行的“规则紊乱”,各行会各自要求,如商家统一秤斤“其间即有改换戥秤,大小不一,独网其利,内弊难除,是以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公议秤足十六两,戥依天平为则,庶乎较准均匀,公平无私,俱各遵依……后不得暗私戥秤之更换”[18]340。之后还提出若违犯约定,则“举秤禀官究治”。
商与官打交道,难免受后者欺蒙,设立碑刻就以文字昭示官方已有前言,告知商家免受蒙混。如“蒙府宪齐大老爷查讯,具祥谕令,照以奏册完税,蒙署藩琦大人批如详饬遵……署府宪熊大老爷饬提覆讯……屡蒙上宪彻底根查……永远遵行,砌石记之”[18]422。特别是涉及商贾切身利益的事例,更是详细记述,使成定制。“我等过载行先辈,原有议定章程,奈世远人湮,前定者百无一二,即支官席片,屡经加增,日复一日,以一倍十,总倾业办公,毫无已时。”进而导致“差务繁紊,赔苦不堪”[18]475。确定最终定额:“每年,府、县署凉棚茶席二千三二百条,宛博林三驿每一百条,府考八百条,院考六百条,县考三百条,教场、院府考五四百条,至有贡差换仓,以及摭抚宪阅兵,另酌办理,恐历久加增,后不复前,故立琐珉,以为千古流传去尔。”[18]475
还是减少官方需索的凭证。“凡晋省商人,在京开设纸张、颜料、干果、烟行各号等……自今以往,倘牙行再生事端,或崇文门税务另行讹诈,除私事不理外,凡涉同行公事,一行出首,众行俱宜帮助资力,不可藉端推诿,致失和气。”[19]155
以上是会馆中石碑的三种主要应用形式,在要求会众的同时,还提醒会众“不得节外生枝”[18]450,定要遵守规约,以免再生嫌隙。
一. 记录、缅怀商人功德
二. 确立会馆的行事依据、重申要求
三. 总结经验教训、警醒后人
-
明代是古代中国商业发展后的全面革新阶段,原本的个人经营在清初受到挫折,个体商人在地方的力量壮大进程被阻断。进入清代,个体商人逐步有了改善和自我扩充的意识和能力。清承明制,承接的亦是教训及认识,清代晋商不愿重蹈覆辙,希望以群体的力量化解社会对商业的阻挠。群体由个人组成,且不会妨碍个人的成长,会馆构建就是应有之义。
-
山西商人从乡土中走出,来到陌生之地,求得温饱是其基本诉求,却也不能得。“里区谒舍之间,虽同乡共梓,往往有相顾无相识者,一旦投辖有地,殿寝而外。”[18]343这就很是悲凉。且若要在此长久发展,找到一个容身之地更是急迫,“我乡之往来于斯者,或数年,或数十年,甚者成家室,长子孙,往往而有,此会馆之建所宜亟也”[21]331。会馆是最为基础的要求,因为商贾外出的直接目的并非只为“联桑梓、通款洽、结乡里之好”,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是发展与团结的需要。因此条件一旦成熟后,“通都大邑,商贾云集之处,莫不各建会馆,以时宴会,聚集于其中”[18]358。“京师……第南城以内,东西辽旷,赁房而散处者,恒苦于聚晤之不易,则所以汇乡井于一堂……端有赖于会馆之设焉。”[19]152“来者踵相接,侨寓旅舍几不能客,有老成解事者,议立公所,谋之于众。”[18]525随着规模扩大与人众增加,会馆建设逐渐提上议事日程,但实现非常不易。“天下事创始难,创始于客寓市厘之地为尤难,盖以东西南北之人聚会于此,静躁不同,言语亦异,非若一邑一乡之生,同井而居同里也。”[18]524
“事非创其所未有,则其有之也难而易,情非出于所乐为,则其为之也易而难。”[19]116会馆构建表面上是“联乡情、笃友谊也。”那为何不在各自乡土,又何必跋涉至此?实际表达了在乡土以外发展的强烈欲望,因此,会馆构建就是一种“从欲望到需要达成的过程”[22]。只是这种欲望在面对痛苦时才利于实现[23]。因此,“都市相较于乡村,有的是自由空气,这些独立的手工业者们为着反抗领主的压迫,增加了互相团结的意识,同时,为着要巩固加强他们自身微弱的经济单位,更不能不一起排出那些妨害他们的阻碍物,会馆也就应运而生”[2]14。
-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遑论以此为业的众商。天下“虽名利分途,而作客则一”[19]181。众所周知,山西会馆建筑主体很多原由庙宇改建,或在地方修建大量戏台。它们很早就为地方民众熟知,晋商通过少量投入将其改头换面,有了“平地起高楼”的效果。而会馆奠基仪式的规模不可谓不宏大,其邀请者上自地方高官,下至地方士绅,都是当地头面人物,又为其起造势之效。还有以另类的方式宣扬本会馆,“因醵金会馆……除公用外,独赢三千余金,庙之壮丽不可有加,又不可折空人私,因铸铁旗杆二株重五万余斤,竖于大门之左右”[18]423。似乎有一种认识,即商业会馆的豪华装饰代表了商家的经济实力,表明本行业的信誉好、产品优,便于商人的商品推广。体现会馆中商人有很强的经济实力,“万户千门百尺楼,搜罗货物萃神州,唯将劝业为宗旨,男女随心任意游”[20]91,因而,清末各地都形成由会馆组成的重要商业街区。
会馆主要是一商业性的社会组织,营利是其主业,但也发现其过多地承担了与其本业无关的诸如宣教、布道、讲礼的副业。“民必克敬于神,神则应之,必克敬于明幽则通之……无心求福,神必佑之。”[18]517它是会馆的一种日常宣发与积极表达,以配合官方的社会教化需要。在积极地完成目标后,以期达到勾连官方媒介、赢得官方肯定的目的。这是一种道德的宣扬,而道德与获利的结合并不抵牾。因为“只有满足了这种私欲,真正自律的道德才可能出现”[24]。
从经验上说,会馆内为一群专业的营商从业者,他们在这里分享经验和教训,共同就某个问题探讨可行的对策。“维夫诸货之有行也,所以为收发客装,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论评市价。”[19]109可见会馆成员依然深耕于此,维持其获利的能力。晋商海内闻名,但也并非都为豪商巨贾,“惜蒲属本小利微,力薄费繁,不能望人向背,谨遵前议,与本行同约:铺中每进钱一千,抽取二文,银数亦然”[18]421。如此一来,既获取会馆构建之资,又避免苛敛商贾。但在这华丽幕布的背后又是一副怎样的现实景象?曾有外国人就中国葬式发出感慨,认为“其中不能说没有虚荣和矫饰的成分”[25]26-27,但至少不全是,它是一种传统的社会扶助性活动,在会馆构建背后亦可被同理看待。
-
明清时期,国家政权高度集中,政府的高压政策使得社会非常压抑,商人除要提升营商水平外,还需不断在政治上出彩,否则很难发展。而会馆就非常需要依靠官方的支持,否则不利于会馆及商号的统一。在国家末期,私有产权的保障机制成为判断一个社会稳定性的重要标志,商人在营商的同时,还不断对政治形势的变化“翘首以盼”,这就是私有产权的危急时刻[26]17。这是一种传统“技能”的沿袭。陶朱公曾喟然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之后“浮于江湖、治产积居,而不责于人”[16]3257,1752。陶朱公就从政客变为成功的商人,其中政治因素的促进应该占比不小。“自余之初通籍也……我西商合阖建山陕会馆于城之偏,工既迄功,徐子云天寓书里中,将乞余一言以镌诸石。”[18]343可见需要常与官员沟通,会馆碑文的撰写就是一个绝佳机会,如清代著名的孙嘉淦、栗毓美、阎敬铭、董文焕、祁寯藻等,近代政、学两界的贾景德、郭象升等人,他们都身居高位,由他们代笔书写,绝对是最好的拉拢手段。既满足官员的虚荣心,又能拉近官商间的距离。可被视为一种官方规范的铺陈,如果“规范”体现多数人的利益,那它就是理性的,否则就是基于力量的变化。以便保障特殊利益领域里的权力平衡[27]148。
会馆是以相同籍贯、行业为基础构成的经济组织,其人员的年龄、学识、背景等因素都很复杂,特别是构建之初,很难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还不熟悉彼此的特长,除抱团取暖、互相安慰外,更为关键的是如何有效调动会众的积极性,使其充分发挥各自所长。“他山之助,遍及行商,众议难谐,几似挨门而乞。”[18]381可见,会馆最初的某项简单动议都难以推行,遑论其他更大的号召,这也成为会馆初期的窘态。会馆中的每一个成员大都长久地在江湖历练,其人脉、关系、个人技能都值得应用,特别是会馆的建成就得益于会众非凡能力的展现。“未逮者,以事巨用广,工大费奢……且楼建所需,非大木无以胜任,而厥木惟乔,实产南邦,越道里之遥而购之,恐非易事,抑更有难者,欲造虹梁云栋之奇,非具月斧云斤之手,无以施其巧”,在这种困难局面下,“毅然以为己任,各输其诚,各展所长,或识优而审其向背,或奖善而劝其募化,或效奔走取材于楚,泛江河而来宛郡,或周知四方,遍访匠师,集工□垂之技于庙建”[18]370。但其过程是艰难、复杂的,“于是构良材、求大木,得楩楠于涧底,遇松柏于山峰,运以输巧,雕以游龙”[18]464。山西闻喜县人乔海明,“字朗斋,设金店于山东,业大盛,倡修山西会馆于济南,赀为西商捐集,而金店董其成,工竣有余赀,又于千佛山建房屋多间,备游览者之憩息,乔朗斋之名遂大著于济南”[28]。
即使钱少事简,会馆依然没有松弛管理。特别是涉及钱粮,总能事事明了,“历年工务繁杂,未及列清勒石,李乔龄等以此钱为数不多,历时已久,如不□彰,恐今之慷慨捐施者意淡心弛”[18]421。为防会众“意淡心驰”,勒石记述就成为必需。虽无具体钱数,却表达了对捐施者的认可和会馆透明管理的渴望。通过调动众人,实现商业的再发展。“自此立为新社,会议轮流经理。一以彰神恩之浩荡,一以序客心之和谐。”[18]524这就避免了“薅羊毛”式的人员激励。“虽凭借之无多,实成功之至巨。”[18]463由个人到众人,除数量变化,更促进商人力量的增加,打破过去费钱费力、单打独斗的狼狈局面。
一. 寻安身之所、营商之地
二. 求利求名
三. 统一商号、调动成员积极性
-
明代的商业类碑刻以个人记述为主,山西商人在明中后期力量积聚和快速崛起,表现为以个体商人为主的发展形式,或因家庭需要、或是被迫从事,总之明代是以个体商人的活跃为历史特征,明代有些山西商人并不以成为富商巨贾为目标,而是以一种“事了拂衣去”的姿态示人。“吾经营垂四十年,而今吾事足矣,不归何时!于是,赉囊橐,携妻子,脱然以归。”[18]118也许是明代晋商缺乏进取意识,抑或是给予不同时代商人的各自选择。
明代晋商只将营商视为一种工作,却不能因此认为明代晋商没有深入或努力不足。他们除涉险远走外,甚至还根据个人经验书写商业类书籍[18]120-122,不可谓不钻研。但在当时商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始终是“所试者小,所济者寡”[18]122。这就为清代晋商的大展拳脚埋下伏笔。可谓是“以群萃州处,察四时权百货之为便哉”[18]343。“余因情切桑梓,困难所在,最为深悉,爰据事实而为之记。”[19]912因此,该记录就流露了明清商人的真实心意。
-
会馆内部建设中常涉及关帝、文昌(功名)、财神、金龙四大王(水神)、太上老君、药王、仙翁、火神、酒仙、马王爷等神仙大王庙宇殿堂的修建。“此善作所以善成,善始所以善终,良非易也。”[18]447“第岁月既久,戏台不无飘摇之虞,大厦将覆……未免有泄而不蓄之憾,并议欲增饰之。”[18]359若不加修理则趋于崩坏,且有违前人功德,“一非妥侑圣神之道,并失前辈向善之诚”[18]421。这是一脉相承的民间信仰,时人希望被神庇佑,并表达敬意。
从会馆内部的营建规模就可见一斑,“其规模之阔大,制度之精详,祷祀常殷,歌舞不辍,而且龛前之供奉,殿内之铺陈,即寻常物具而华美巨丽,不极诸势之所可致兴,夫力之所能为而不已,盛矣乎”[18]436。甚至将生理兴旺的结果归纳为神的庇佑,“非诚赖官明断之才,邀神默佑之力欤”[19]109。“夫人之精神新则振奋,陈则萎靡,今神之楼既已无时不新矣,则镇之生理必新而又新可知也,亦必久而益新可知也。不止于是,凡履是地者,亦必皆振发其精神无不鼓舞振作新可知也。”[18]474而构建则归结为“因思夫庙建神之灵”。还将会馆振兴亦归于神灵,“自光绪二十年后,不惟会事不振,而且积弊难返,言之痛心,书之裂眦,幸神莫佑,重兴得人”[7]557。同业商店集合在一处,结果自然就有了共同行动的机会,共同祭祀神佛就成为先发生的事,更进一步,也为营业上的方便和利益相互出力[7]。这就表明会馆是受“礼”的促成,商人也乐于遵从。可见“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29]。至此,实现“工商业者从精神信仰共同体向世俗利益共同体的趋势转变”[30]。
明清易代后,晋商以更好的发展面貌示人,而它势必引起统治者的忧虑,担心引发潜在的管控风险,为消除官方疑虑,商人会馆中开始积极引入那些传统的民间神灵,既满足晋商原本的乡土信仰,又将那些神灵崇拜推至前台,视为商人行为的“引领者”,借会馆创建、修补的契机,隐藏在该理念中。如“善”是统治者与地方教化的需要,齐人心、便商旅更是当务之急。为响应这一号召,会馆成员也在积极践行,“为善最乐,积众善以要其成,则其善靡尽,大美难继,萃众美以踵其事,鼐其美无穷”[18]458。从而将真正的“人”的意图加以隐藏,以免商人群体不被容于当时。可见,会馆中的“神”除了日常的信仰外,从理论上已代替了“人”的作用,“人”更多是一个执行者。
从实用角度出发,传统神灵也有警醒世人的作用。商贾日日以利为先,恐其心不知所向,行为无有约束,因此,“以风示商贾,使熙熙攘攘竞刀锥子母者,日夕只承于帝君之旁,庶其触目惊心,不至见利忘义,角诪张而相徂诈也”[18]488。明清社会出现“士商合流”的趋势,儒家规范由商人体现已很普遍,而商人本就充满纪律性,二者的结合就产生一种“以礼入法”[31]的传统演进。商人的规范、约束是礼的延续,辅以权力的加持,二者内容在碑刻中很明显。
-
传统职业讲求“父子相继”“子承父业”。随着明清时代的来临,营商已非唯一选择。却有很多人依然遵循父辈或沿袭家族的意愿,具体原因有二:首先,是家庭条件的困厄。“幼读书颖异,累于食指,不克卒业,后协办盐务,家计日丰。”[32]247“后嗣因家寒,读书不能上进,欲改经营,手乏资本,又属外行……一时难以高发,只得奔走他乡。”[33]其次,是家庭发展的需要。“缘时逢不辰,家计伶仃,不得已,仰遵父命,徙业营商,然而非其志也,以孤子之身,崛然起家,累赀数千金;因遭家不造,未遑肄业诗书,年弱冠支持家务,兼之贸易为生,有少年老成之誉,自后家道颇昌,捐授登仕佐郎之职。”[32]143,251
我们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到自身以外寻找解释自身命运的理由,成功和失败不可避免地会调整我们对周遭世界的看法,正如此,成功的人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好的世界,并乐于看其照原样保持下去,但失意者则希望看到急遽改变的世界,哪怕我们自身的处境是由能力、个性、外贸或健康等个人因素形成的,我们还是会坚持向外寻找理由[34],即使非常艰难。“夫事创始者难,继其志者亦复不易。”[19]103会馆并不设在会众的乡土内,人员的流动使得晋商开始考虑培养成员,或吸收新的商业力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会馆将长久地屹立在城镇、码头,而商人却会不断更换、代代延续。这是会馆中每一个商人的阵地,会馆是他们一生的心血,代表了他们对自我行为的认同,否定会馆意味着否定每一位创建者、修缮者的努力。通过会馆的构建,切实达到“踵美前人,兴起后进”[19]123、“忆前徽之未远,幸继起之在兹”[18]464等功效。而会馆发展的根本还仰赖“人”的经营与传承,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一旦人才培养出现断档,行业自然难以为继。进入民国,会馆传承不足开始衰退,其他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只因码头中衰,继起无人,一切手续竟尔历年空悬。”[18]550“历年既久,经理乏人,渐有欹缺,来往过斯者,徒兴茂草之嗟,念创立之难,而废败之易也。”[19]152可见行业人才培养的必要,只有将团结会众,才利于会馆的构建和传承,实现“既得坐贾之影从,还仰行商之乐输”[18]464的长久。最终“托业兹土者,可以久安,可以长盛”[18]408。
-
在碑刻中总能发现“山陕”字样的标题,且为数不少。它是对山西、陕西两省商人的合称,既然合称自然有其原因。将山陕通称,正是两省的历史联系和地理距离决定的,同时经济上的趋同也为他们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一旦相遇于旅邸,向因方语,一时蔼然而入于耳,嗜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异乡骨肉,所极不忘耳。”[21]332他们成为古代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的同盟军。“俾相识相敬相和睦,联秦晋为一家,结恩谊于异域。”[18]529但最初山陕商贾合力营商,其状态并非后世宣扬的和谐,“回忆初建之时迄于今……山陕诸友,辐辏而聚此地,其势至涣也”[19]301。之后,通过磨合使两省商人在会馆构建中得以一馆容纳、命名,可见山陕两省商人关系之密切。他们齐心协力、共创商业奇迹,在会馆构建中做到无分你我、同气连枝,“创建乃山陕商人慷慨捐财,虔诚募化者也”[18]341。“虽曰多寡不侔要皆翕然而罔怪”,真正起到了“鼓人心作善之机”[18]341的作用。遇到问题彼此互相扶助、共同解决,“嘉庆中,雨风剥蚀,颇有倾颓两省之人惧其湮废,重葺而新之……予秦人也与晋素联梓谊,因从其请”[18]449。“况疆里攸分,征求必慎,或取资于山右,盛借助于关中,秦晋本如一家,同声同气,管鲍尽为知己。”[18]526
在此,也不应回避山陕两省商帮本身具有的激烈竞争现状和各自的商业习惯、特性,毕竟分属两省,因为“权利是对方给的,不是自己主张的,义务是自己认识的,不是对方课给的”[35]147。发展的需要促成两省商帮的紧密结合。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何况两个省域,但也不应将其视为一个绝对同质的商业群体,而应从历史的发展脉络着眼[26]绪论11。并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凡与斯役者,或缔好如管鲍,则群且爱之慕之;或隙末若萧朱,则群且避之戒之,勿惜小利而□干糇,勿耀厚□而忘节俭,肃宾而厚旅,亲人而事神。”[18]343山陕会馆的出现表明区域间的合作渐已打破行政区划的坚冰与桎梏,展现会馆对商业的促进,真正做到了商人间的“盟誓婚姻,往还无间”[18]343。
-
众所周知,山西会馆多选建在交通便捷、人流充足的城镇都会,如北京、汉口、洛阳等通衢。“赊旗店,四方客商集货兴贩之墟……年来人烟稠多。”[18]340北舞渡,“舞阳县之巨镇也”[18]341。“侧闻齐地,当水陆之冲,阛阓喧阗,衽帏汗雨。”[18]343“斯镇居荆襄上游,为中原咽喉,洵称胜地。”[18]370这里鱼龙混杂、是非繁多,一旦遇事就不是某个商人过去在本乡本土之中所能解决或处理的,因而商人就需要依凭一个有强大力量的社会组织代个人出面。
“历来服官者、贸易者、往来奔走者不知凡几,而会馆之设,顾独缺焉,岂真无能为之人,能为之时,能为之力欤?抑亦莫为倡之,谁为和之也。”[19]116以期真正做到“竭诚经理,勿致复为废弛,以期绵绵延延”[19]157。最后应从现实出发,就眼前考量。“倘诸君子仅创于前,而众善人莫为于后,则需费浩繁,日久殆尽,何以永远辉煌?”[18]496会馆构建者希望其实业能够长久,否则非良法、失美意[18]423。在商贾经理下,真正实现“董事者奉公洁己,众出纳之必严,费不至于虚靡,功期归于实用”[18]526。在会馆碑记的最后会将当次捐施者个人或商号的名字进行罗列,既是对捐施者的行为赞赏,又是会馆透明财务管理制度的要求。它主要以捐款多寡的顺序进行排列,行业不同、商号规模各异,有千两,有数文,且不论他们的捐款金额,这正体现了会馆“众人”的强大合力,表达了明清晋商发展中隐藏的“分力”“借力”理念。正是那些普通个体商人的存在,创造、书写了会馆的辉煌历史。
怎奈时代的发展超越了个人乃至群体的意愿。进入民国后,传统商业会馆力不从心,逐渐从传统社团向新式商会迈进。“力加整顿,联合秦晋,各举代表……详注同乡录,取消鼎元社,改为山陕同乡会。”[18]557在介休有十五行“就斯地设立商会……迄今二十余年矣,商行已发展至二十余业,其内部组织亦由总理制而递更为委员制”[19]865。可见,会馆原有规范机构的共识基础在历史大变动中遭到破坏,因为不仅是会馆本身,更是社会制度的瓦解。即最后的破败[36]。徐永昌曾在日记中描述过一件类似的事[37]76-77①,该名晋商守业不屈不移,堪与古时老堤头、守坟人相媲美。山西会馆的构建,更是历史发展下以惠民、尊神、利国三驾马车并行下的时代产物,它们三者在会馆中或单一,或结合,不断衍生出各异的会馆映像。晋商等通过对三者的有效利用,既避免个人或商号的迅速发展而招摇,又可在“法不责众”的情形下出头、扬名,进而实现基础稳定、事业上升、商业壮大的既定目标。
① 民国二十年,“河北大名城东二十余里临运河一个码头,现在亦不算冷落,所谓龙王庙就是地以庙名,该庙原系山西商人一个会馆,内供龙王神像,因而会馆以神名为庙,其时该庙已做商会,而码头仅有一个山西人,乃与地方争此产权,直讼到北京乃得平,其父为山西高平人,在此地娶妻生子。”
一. 神占主,人居次
二. 商业传承的需要
三. 打通区域间的彼此认同
四. 互相成就,彼此扶持
-
《广志绎》中提及:“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中平阳、泽、潞三地就是明清时代的重要商业市镇,它们的形成并非易事,是晋商最初依靠手提肩扛、牵马推车实现的不易结果。应认识到,“旅居到相对开放的贸易社会的想法从来不是危险的,所以似乎已为大多数政府所接受,以侨居行为为基础的商业移民格局为日益安全的各种形式的交通所强化,并进一步为对国际贸易至关重要的通讯技术促进和加强”[38]。自明代始,山西苦于地狭人稠、自然环境恶劣,人们为谋生计就多外出经商,或在本土,或走到外面。他们最初的想法不一定是为成大事业,能糊口即可。因此在生计维持的推动与营商获利的吸引下,就此开始弃农从商,或兼作小本生意,以期增加收入。明末山西商人的“原始路径”已趋于难行,明清承绪的商业开始朝经济上的高度集权与职业分立破坏的趋势奔涌,使“原来的循分自进路途亦绝”[35]66-69,而自我创新之路尚浅,这就制约了明清山西商人和商业会馆的发展。所以经商虽然非原先的职业生涯规划,但所处的不堪社会现状仍需被扭转。事实上,山西人自明初完成“开中法”的国家需要后,就认识到商业对他们的意义,也逐渐找到实现发展的正确方向。
明清时期的国家机构高度发展,它的“文明水准”很高,还有政治机构职能分工明确、行政组织复杂、劳动分工专门化、机会均等、社会流动频繁、成就标准重于关系标准等特征[27]138。会馆就在此社会状态中突出重围,它背负着个人和乡土的无限期许,通过各种或隐蔽或公开的手段,实现其在各地开花的结果,最终带动个人和乡土的地位构建和经济成长,这就是山西商人通过会馆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进而不断增强、展现自我变革的能力。正所谓“万古不朽之事业,皆千古好事者之精神”[19]157。明代晋商以乡土为根基,并在其中长久的立足下去。虽然明代士商互动的历史情景很复杂,且碑文内容不乏溢美之词,但其写作必定是以事实为基础,在字里行间不乏明代晋商的真实努力和信念留存,一代代的晋商锻造了自我磨砺、推陈出新的能力,看似不经意间,晋商那一缕“幽光”跨越时代的阻隔,为清代会馆的持续构建打下坚实的理论根基,彰显了明清时代的商业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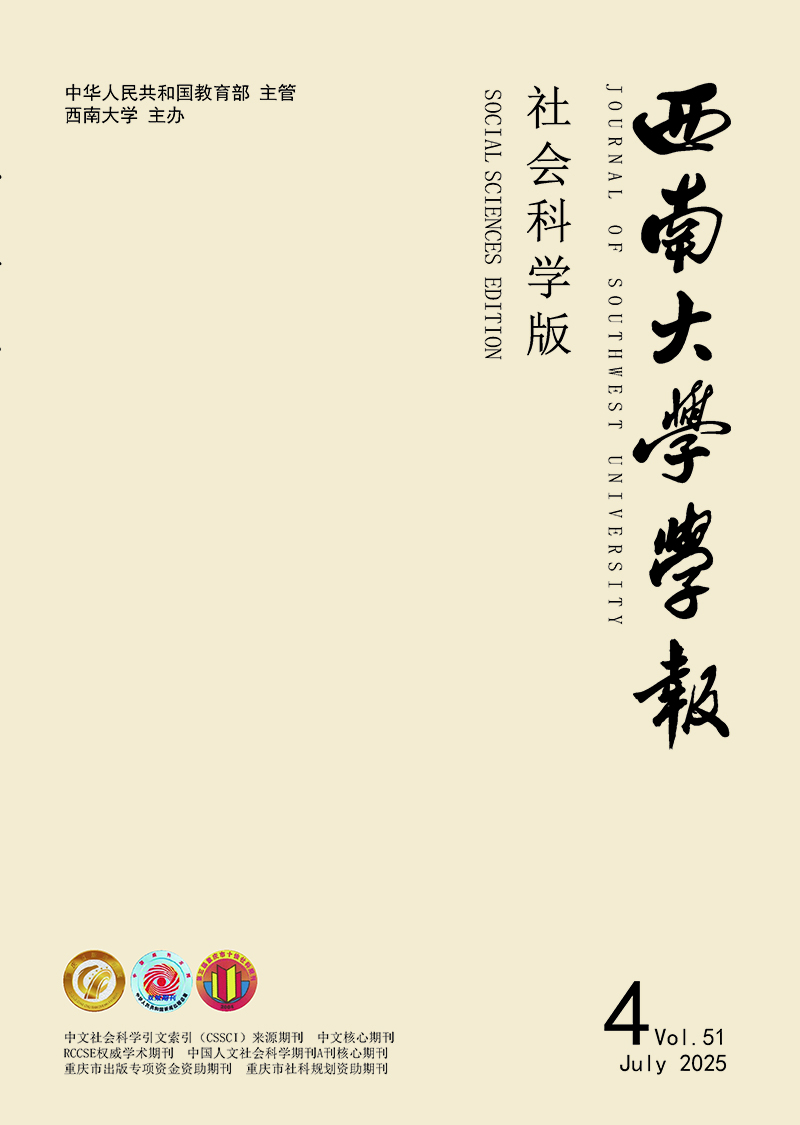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