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9月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1]。该论述在会后被总结为“四个共同”,“精练概括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各民族的命运共同体”[2]。尽管“四个共同”的提出距今已近四年,但学界对该论述的研究热度不减,有文章分析了“四个共同”的理论渊源、理论价值、实践方式和内在逻辑等方面[3-8],也有文章研究如何结合具体历史事件将“四个共同”融入教学之中[9]。综观以往研究,尚无文章结合“四个共同”研究各族对清代中国疆域统一的贡献,进而展现“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因此有研究主张,将“四个共同”与相关史实进行融合,“深入挖掘中国分合治乱历史过程中各民族‘四个共同’的发展主线”[7]。
本文之所以结合“四个共同”涉及“疆域”的论述和清代中国疆域统一的历史进行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缘于篇幅所限,清代历史中涉及“四个共同”的事件和人物众多,全时段、总括式研究并非单篇论文可以实现,本文聚焦“四个共同”中的“疆域”,源于疆域的重要性,即如相关研究所言,“疆域为首要条件,疆域是历史、文化和精神产生和发展的必要前提”[5]。二是源于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相比明朝,清朝的大一统更为深入;相比元朝,清朝的统一时段更为长久,即如学者所言,清朝“奠定了近代中国疆域的基础”[10],也因此,清代有大量涉及中国疆域统一的历史素材。通过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四个共同”的内涵,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清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提供具体素材。具体来说,本文通过研究清代涉及疆域统一的历史事件,从局部统一与清代大一统的关系、各族对清代中国疆域统一的贡献两个方面来论证“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观点,并从中总结清代中国大一统的经验和启示。
HTML
-
“今天,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富饶辽阔,这是各族先民留给我们的神圣故土,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美丽家园”[1],而清朝为近现代中国疆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本文所研究的“清代中国疆域统一”史是指截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完全统一新疆之时清朝疆域形成的历史,主要聚焦清代北部和西部疆域统一的进程,因为顺治朝时清朝即基本统一了南方,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统一台湾,实现了对整个南方的统一,而清朝统一北部和西部疆域的时段贯穿了顺、康、雍、乾四个朝代,涉及“四个共同”的历史事件类型更多、时段更长。
实际上,清朝在其前身后金政权创立之后,即已开启统一中国北部疆域的历程,最终从一个地方性的政治力量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中国疆域统一的历史,不只是中央政权统一边疆的历史,也涵盖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少数民族政权的出现和发展,为大一统的到来积累了条件,“为下一个历史时期更大规模的统一在进行着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发展的质与量的积累”[8]。
-
在明朝国力强大的洪武和永乐时期,虽然疆域相比两宋时期更为广袤,但未能实现对整个北部疆域的完全统一,例如从元大都北逃至蒙古高原的北元政权曾长期与明朝并存,故而乾隆帝认为明末后金政权“破察哈尔林丹汗,而元始灭”[11],有学者认为明代时“元顺帝与明朝的关系颇与宋帝和辽金元的对峙情况近似”[12]。明中后期明朝国力不如明初,逐渐丧失了对河套及嘉峪关以西地区的稳固统治。
《三国演义》曾言“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13],然而综观明末这个时段,王朝更替与疆域分合的定律是否能够继续如此演进,其结果并不确定。明朝末年的中国,在疆域统一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彼时,经历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西方国家国力渐强,开始谋求在中国南部的殖民利益。明天启朝时,荷兰殖民者侵占澎湖,“乘汛出没,虏掠商艘,焚毁民庐,杀人如麻”[14]。后来明军虽然击败了荷兰,但荷兰对东南沿海的威胁依然,即如明人所言,“战夷舟坚铳大,能毒人于十里之外,我舟当之无不糜碎,即有水犀十万,技无所施”[14]。此外,明末时沙俄领土已扩张至西伯利亚,并积极刺探明朝情报,了解明朝虚实,万历朝时,沙俄使者曾混入蒙古部落进入北京[15]。到十七世纪中叶明清鼎革之时,沙俄已征服西伯利亚的勒拿河流域以及贝加尔湖附近区域,兵锋开始触及中国的东北、蒙古诸部,为此后清朝同沙俄的雅克萨之战埋下了伏笔,即如相关研究所言,“l7世纪中国明清易代之时,沙俄基本完成了对西伯利亚的侵略占领,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1636年(明崇祯九年),俄国人第一次知道了黑龙江”[16]。在中国南部和北部面临西方侵略的明朝末年,中原地区起义云起,大顺军和大西军在各省攻城拔地,明朝疲于应付;在广大边疆民族地区,明朝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力经营。例如东北地区兴起的后金政权,在松锦决战中击败了明军,明朝已无力统一东北。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来整合疆域,这一历史重任后来转移到“后金-清朝”肩上。
从顺治朝到康熙前期,沙俄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威胁是持续的,因此无论是顺治朝还是康熙朝,清朝都曾防备沙俄。顺治十年(1653),清廷得报,“罗禅兵从吴喇河下,于我等住处经过……欲将尔撒哈连吴喇以东与我们纳贡,以西弄泥吴赖索陇人与皇上纳贡,因此前往去说分地一事等语”[17],“罗禅”及“罗刹”为清人称呼俄国人的别称,可知彼时沙俄有侵占我国东北之意,清朝也提防沙俄的侵略野心。
-
① 为便于论述,本文采取《圣武记》中以地理位置为依据来划分蒙古诸部的标准,将清代蒙古分为漠南蒙古(内扎萨克蒙古)、漠北蒙古(喀尔喀蒙古)、漠西蒙古(亦称准噶尔蒙古)、青海蒙古等部分。
明朝曾在东北地区先后设立奴儿干都司、建州卫等管理机构,但万历末年至崇祯朝时,明朝逐步丧失了对东北地区的统治能力。万历后期,努尔哈赤逐步统一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大部、东海女真,并通过联姻、武力征服等方式,臣服了漠南蒙古众多部落,此后又通过萨尔浒之战击败了明朝,明军大败亏输,明朝辽东镇的沈阳、辽阳等地被后金占据。在后金崛起于东北之际,漠南蒙古大汗林丹汗也开始了其统一蒙古诸部的进程,然而林丹汗“有宋康、武乙之暴”[18]94,其才德不足以支撑其雄心,造成漠南蒙古诸部的离心,后来漠南蒙古诸部多归附了后金。崇祯七年,被后金击败的林丹汗病死于甘肃大草滩。崇祯八年,林丹汗之子额哲投降后金,后金从其手中得到传国玉玺。传国玉玺是中国古代王朝正统性的重要象征,南宋灭亡时,“宋主遣其(宗室)保康军承宣使尹甫、和州防御使吉甫等,赍传国玉玺及降表诣军前”[19],传国玉玺落入元朝宗室之手。元朝灭亡后,被元顺帝携至关外,明朝一直搜而未得。彼时,皇太极认为所获传国玉玺即宋代传国玉玺②,象征其具有称帝的资格,因此于崇祯九年改元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反映了其对中原政治文化的自觉接纳。到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之前,清朝基本统一了包括山海关以东地区的绝大部分东北地区和漠南蒙古地区,为清朝入关后将中原内地、东北、漠南蒙古连为一体奠定了基础。
② 无论此玉玺是否为宋代玉玺,都无法否认皇太极得玉玺而称帝的历史。
-
顺治元年四月,入仕清廷的大学士范文程提出清军入关后的策略,“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20]卷4,顺治元年四月辛酉。范文程建议此次入关应以占据中原为目标,而非短暂停留。之后多尔衮认可该议,亲率满、蒙、汉精锐力量进攻山海关。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后很快占领了原明朝九边地区。顺治二年,北方直省地区基本被清朝统一。到顺治末年,清朝基本消灭了南明势力,自此中原直省地区、东北地区、漠南蒙古地区连为一体,统一台湾也逐渐进入清朝视野。
崇祯朝时,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被明朝招安,郑芝龙招徕了不少汉族前往台湾开垦谋生,初步奠定了台湾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和融合的局面。顺治末年,郑成功北伐失败,在反清志向不变但复明又力所不及的时候,郑成功决定收复台湾。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挥师东进,击败了盘踞台湾的荷兰侵略者,使得台湾地区回到了中国人的统治之下。对郑成功而言,收复台湾也是其恢复先祖基业的尝试,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曾作诗:“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21]郑成功收复台湾,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清朝统一台湾地区奠定了基础。
康熙元年,壮志未酬的郑成功去世,其子郑经成为台湾地区的管理者,郑经及其之后的郑氏势力性质开始蜕化,逐渐走向了历史的反面。如三藩之乱爆发时,郑氏势力配合三藩反清,却在福建同靖南王耿精忠争抢地盘,“海逆郑锦乘耿精忠叛,窃据漳、泉诸郡”[22]卷79,康熙十八年二月甲戌。台湾为“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23]120,清朝若不统一台湾,东南沿海将无宁日。康熙亲政后采取了一些措施发展生产、缓和矛盾,清朝统治中华的正统性不断增强。康熙八年康熙智擒鳌拜,实现了完全亲政;次月正式废止实行多年的圈地之法。康熙帝还积极主动地接纳中原政治文化,清朝统治者自身在政治文化上同中原士人价值观逐渐趋同,清朝越来越具有正面的、新兴的中央政权形象。康熙二十年清朝平定了“三藩之乱”,康乾盛世渐有发端。在康熙帝决定统一台湾之际,面对清朝的统一要求,郑氏势力“请照琉球、高丽等外国例,称臣进贡”[22]卷109,康熙二十二年五月甲子,可见郑氏势力已退化为割据政权。后来康熙帝拒绝台湾成为朝贡国而主张完全统一台湾,原因之一便是台湾居民多为中国福建人,与琉球或朝鲜不同。康熙二十二年,清朝出兵台湾,在澎湖击败了郑军,当年七月十五日,郑氏政权正式向清朝投降,自此台湾地区与中原内地等地连为一体。
-
明朝建文、永乐时,宗喀巴进行宗教改革,创立了黄教(格鲁派喇嘛教),该教派在青海和西藏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宗喀巴去世后,他的弟子们继承了衣钵,“所遗二弟子,一曰达赖,一曰班禅”[24]。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时,黄教在漠南蒙古雄主俺答汗的支持下,在蒙古各部日益传播和流行。明朝末年明朝丧失了对边疆的统治能力,青海和西藏地区也陷入内部动荡,急需一股政治势力进行内部统一。此时,居住于我国新疆北部的和硕特蒙古首领顾实汗,在五世达赖的邀请下,出兵青海和西藏,于崇祯末年统一了青海和西藏地区。此后顾实汗联合五世达赖,形成了蒙藏联合政权。顺治九年,在清朝的邀请和顾实汗的支持下,五世达赖亲赴北京觐见顺治帝,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25],标志着清朝同西藏地方除了朝贡关系,又多了一层册封关系。自此往后,达赖活佛转世得到中央政府册封后方才名正言顺。册封权则是清朝治理西藏的重要一步,为此后清朝完全统一西藏提供了法理依据。顺治十年,顾实汗亦得到了清廷的册封。
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第三次亲征漠西蒙古①噶尔丹抵达宁夏,青海蒙古诸部在康熙帝的影响下决定主动归附清朝。康熙三十六年十一月,康熙帝于紫禁城保和殿接见前来朝拜的青海扎什巴图尔台吉等人。次年一月,康熙帝封扎什巴图尔为亲王,封土谢图戴青纳木扎尔额尔德尼为贝勒,封彭楚克为贝子,标志着清朝基本确立了对青海地区的统治。康熙五十六年,漠西蒙古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派兵绕道新疆南部占领了西藏。从明末至清前期,西藏黄教格鲁派先后在蒙古诸部传播,成为蒙古诸部的主流宗教,因此,占据西藏的漠西蒙古试图“挟黄教以令蒙藏”,威胁到清朝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面对这一危局,年老的康熙帝并未暮气沉沉,决定“驱准保藏”,最终于康熙五十九年“遣兵进藏,立即讨平之”[26]666,击败了漠西蒙古军队,进一步统一了西藏,实现了西藏与中原内地的整合。
① 在清代史料中,亦称卫拉特蒙古、厄鲁特蒙古、准噶尔蒙古、准噶尔部,驻牧于清代新疆北部。
-
② 亦称外蒙古或喀尔喀蒙古。
在清朝忙于平定三藩时,新疆北部的漠西蒙古在噶尔丹的带领下快速崛起,最终统一了新疆。康熙中叶,噶尔丹将视线转向东方的漠北蒙古等地。彼时漠北蒙古内争,噶尔丹乘机干涉,于康熙二十七年攻入漠北蒙古,漠北蒙古“三部落数十万众瓦解,先后东奔”[18]101,逃入漠南,噶尔丹也尾随侵入漠南蒙古,康熙帝不得不亲征反击,最终于康熙二十九年在漠南蒙古乌兰布统地区击败了噶尔丹军,噶尔丹败逃。康熙三十年,清朝组织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在多伦诺尔会盟,决定在漠北蒙古实行盟旗制度,确立了对漠北蒙古的统治。此后,清朝在应对漠西蒙古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对新疆地区的统一。
清初顺治朝时,新疆哈密地区和吐鲁番地区同清朝建立了通贡关系。康熙前期,哈密既同清朝通贡,也向漠西蒙古纳赋,但总体而言,康熙前期哈密更受漠西蒙古的控制。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覆亡,哈密首领额贝都拉遣子郭帕伯克,将噶尔丹子色布腾巴勒珠尔献给清朝,哈密“其地始内属,授为扎萨克一等达尔汉”[26]301,标志着清朝确立了对哈密的统治,新疆东部地区开始纳入清朝疆域,为此后进一步统一新疆打下了基础。康熙五十四年和康熙五十六年,漠西蒙古军队先后侵袭新疆哈密地区和西藏地区,康熙帝决定正式统一吐鲁番,作为应对漠西蒙古的前沿。清朝在决策统一吐鲁番时,并非是一味采取武力,首选是“招抚之即与哈密相类,既入国家版图,自不得不善为保护”[27]695,这一策略取得了预期效果。康熙五十九年,在清军的招抚下,吐鲁番地方首领阿克苏尔坦、沙克扎拍尔、额敏和卓等人归附了清朝,清朝得以和平统一吐鲁番。乾隆十八年,漠西蒙古杜尔伯特部三车凌(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蒙克)率部众一万余人投附清朝,清朝统一新疆的条件日益成熟。乾隆十九年,漠西蒙古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亦归附清朝,“与纳默库、班珠尔二台吉共率所部兵二千、口二万东奔,叩关内附”[18]146。乾隆帝为一劳永逸、彻底击败常年威胁清朝北部疆域的漠西蒙古,决定发兵进一步统一新疆。乾隆二十年二月,漠西蒙古首领达瓦齐为清军所击败,逃入南疆,被乌什城阿奇木伯克霍吉斯执献给了清军。乾隆二十四年,清朝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实现了对新疆的完全统一。此后,清朝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和各参赞大臣,并驻军、移民、设治,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大为加强,也为清末新疆建省积累了条件。
从以上论述可知,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力量在实现局部统一后,有的是主观上促进了清朝疆域的统一,有的则是客观上带来了清朝的大一统,佐证了“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的观点。
一. 明末时中国疆域统一面临新挑战
二. 清朝入关前实现了对东北和漠南蒙古①的局部统一
三. 郑成功收复台湾为清朝统一台湾创造了条件
四. 青藏地区局部统一与清朝统一青海、西藏
五. 漠西蒙古崛起与清朝统一漠北蒙古②和新疆
-
从区域统一的角度看,各区域的局部统一为清朝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从参与统一的具体力量来看,清代各族都参与到了清朝疆域统一的具体行动当中[28],“历朝历代的各族人民都对今日中国疆域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29]。
-
在清朝统一台湾的战事中,除了广大汉族士兵,还有畲族将领蓝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叔祖福建提督义山公家传》和《国朝先正事略》等史料对蓝理在清朝统一台湾战事中的浴血奋战作了浓墨重彩地描述,特别是蓝理腹部受伤的部分。《国朝先正事略》记载:“公鏖战自辰至午,手杀八十余人,身被十余创,正酣斗间,忽贼炮斜飞过公腹……。”[30]此段论述提到蓝理腹部受伤,具有可信性,蓝理在清代被称为“破肚将军”。蓝理在清朝统一台湾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作为先锋进军澎湖,有冲锋陷阵之功。施琅在上疏汇报第一次澎湖之战时提到:“署右营游击蓝理等,以鸟船首先攻敌。”[22]卷110,康熙二十二年闰六月己巳彼时施琅选派了诸多将领参战,在疏中首提蓝理,可见蓝理的重要作用;二是蓝理是澎湖决战一举击败郑军的功臣,蓝理在最后的决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三是蓝理在澎湖海战中救过深陷重围、危在旦夕的施琅。此外,在清朝统一台湾之际,台湾地区“各乡社百姓以及土番,壸浆迎师,接踵而至”[23]110,包括台湾高山族群众在内的各族人民为清朝顺利接管台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以上论述可知,各族都在清朝统一台湾、实现对东南疆域的统一上做出了贡献。
-
在康熙末年清朝统一西藏的过程中,满汉等各族兵民皆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清朝最早驻防在西部的八旗,西安八旗参与了清朝经略西藏的诸多战事。康熙五十五年,清廷调部分西安八旗前往青海地区,以防止漠西蒙古侵入青海和西藏。康熙末年,漠西蒙古入侵西藏后,驻扎在西宁前线以备进军西藏的清军中,即有西安满族兵。康熙五十七年清军第一次驱准保藏,亦是由西安将军作为军队统率,彼时“西安将军额伦特率兵五千援藏,全军覆于喀喇河”[31],为清朝的大一统做出了牺牲。康熙五十九年清朝的“驱准保藏”、统一西藏之役,定西将军噶尔弼从四川进军,“云南一路满汉官兵,奉调赴巴尔喀木地方,与将军噶尔弼会兵进藏”[22]卷287,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己丑,此外,云南丽江纳西族土知府木兴等亦主动请缨效力,派遣土兵五百人随同清军进军西藏。同时,各族还加入清朝统一西藏战事的后勤保障之中,如康熙末年清军入藏时,陕西泾阳县知县焦应旗等即随军入藏,其职责是“押送牛羊随大兵后,以济军糈”[32],组织各族百姓随军运粮。四川地方亦是如此,清军统一西藏之初,“自打箭炉至拉里,曾将四川绿旗、土司番兵,共留三千五百余名,挽运粮饷……”[22]卷299,康熙六十一年九月戊子,汉、藏等各族保障了清朝统一西藏之初地方的稳定。除了以上民族,还有清代东北索伦士兵(主要由达斡尔、鄂温克两族构成)参与了康熙末年清朝统一西藏的战事,并做出了贡献[33]。
-
康熙二十九年,由于噶尔丹率军南下进入漠南蒙古,清朝为预备漠西蒙古的威胁,稳定西北疆域,在山西右卫地区派驻了八旗。在清朝统一西北疆域的过程中,如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西路军中除了京城八旗、西安八旗、察哈尔八旗外,还有山西右卫八旗。雍正八年(1730),清朝兵分两路,试图统一漠西蒙古,当年十二月,雍正帝命凉州驻防八旗兵一千名前往肃州,凉州八旗是西路军的兵源之一。乾隆二十年正月,清朝再次出兵统一新疆,清朝从凉州、庄浪、宁夏调拨数以千计的满族八旗兵先行赴新疆哈密驻扎[34],宁夏、凉州、庄浪八旗由于地处西北,成为清廷出兵统一新疆的先锋。从以上论述可知,以满族为主的西北八旗是清朝统一西北疆域的重要依托。除此之外,清代索伦兵亦加入了乾隆二十年至乾隆二十四年清朝统一新疆的战事中。彼时清军北路军和西路军皆有索伦兵加入。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乾隆帝在《御制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文》中提到“然我满洲索伦众兵士,无不念国家之恩,效疆场之力,故能以少胜众”[35]卷600,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辛亥,可知索伦兵在清朝统一新疆中功劳甚大。
-
在清朝统一西北疆域的过程中,陕甘绿营参与了诸多战事,在某些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也是清朝绿营精锐所在,即如康熙十八年康熙帝所言,“各省绿旗兵,向推秦兵精锐”[22]卷84,康熙十八年九月庚子。康熙三十四年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清军的西路军中,振武将军孙思克统率的陕甘绿旗兵就占相当比例。康熙三十五年,清军西路军在昭莫多猝遇西逃的噶尔丹军,此战清军大获全胜,陕甘绿营战绩甚多。此次战役获胜意义重大,为清朝次年顺势统一新疆哈密和青海地区创造了条件。陕甘绿营中除了汉族,还有相当比例的回族士兵,如乾隆十二年时,“固原镇兵,回教十居七八”[35]卷290,乾隆十二年五月壬寅,可知陕甘绿营回族士兵比例之高。陕甘绿营在清朝统一疆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乾隆十九年五月,清廷统一新疆前夕,北路军和西路军中有甘肃各营、安西绿营兵一万人,其中即有相当比例的回族士兵。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固原提督齐大勇派一千名精干绿营兵加入西路军。关于清代回族加入绿营、参与清朝统一疆域战事的历史,清末时陕甘总督左宗棠十分熟稔,他认为清代很多回族士兵因为在西北边疆的军功被提拔为地方大员。由上可知,主要由汉族和回族组成西北绿营为清朝统一西北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
乾隆十八年时,漠西蒙古内部动荡不安,杜尔伯特部首领三车凌归附清朝。乾隆十九年五月,三车凌亲赴热河避暑山庄朝觐乾隆帝,分别被封为亲王,郡王、贝勒。乾隆二十年,三人因军功分别被晋封为汗、亲王、郡王,乾隆帝曾作杂言诗《弹汗行》评价对三车凌的封爵,其中有言:“亦存其汗号,都尔伯特至今世禄其孙曾。”[36]三车凌及其所属杜尔伯特蒙古族为清朝统一新疆等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乾隆十九年底清朝出兵征讨漠西蒙古首领达瓦齐前夕,杜尔伯特部派兵一千名加入了清朝的西路军。正是在杜尔伯特部三车凌的有力配合下,达瓦齐在南逃南疆乌什后被擒获。除了三车凌,部分杜尔伯特蒙古族亦在统一新疆的战事中立功,如加入八旗系统的杜尔伯特蒙古族巴图济尔噶勒,原先为杜尔伯特部的宰桑,在清军击败达瓦齐时立下大功,当时,达瓦齐拥众万人,踞格登山崖,巴图济尔噶勒等人率军突击,以少胜多,大获全胜。后来,巴图济尔噶勒等人还协助清朝统一南疆地区。乾隆二十三年底至乾隆二十四年初,定边将军兆惠所率清军在叶尔羌附近为大小和卓军队所围困,巴图济尔噶勒参与了解围,并立下战功,乾隆帝曾作诗夸奖该人:“先是围解黑水困,元戎遣救抡二臣……其勇诚超群。”[37]又如普尔普,曾为都尔伯特部宰桑,后在清朝统一和阗的过程中立下功绩。
-
康熙三十六年清朝统一哈密,康熙五十九年清朝统一吐鲁番,两地的维吾尔族首领皆在此后清朝统一新疆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哈密首领玉素布、吐鲁番首领额敏和卓等人不仅参与了清朝统一新疆的战事,还为统一之初新疆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其一,直接率军协助清朝统一新疆。乾隆十九年九月,清朝筹备出兵统一新疆,哈密维吾尔族首领玉素布亲率维吾尔族士兵从征。吐鲁番首领额敏和卓更是直接参与了统一南疆的攻城之战。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在进军库车城时,身在前线的额敏和卓面部为敌炮所伤,乾隆帝得知后十分爱惜,下谕要求额敏和卓今后“不可冒险攻战,致有疏虞”[27]704。乾隆二十三年底至次年初,兆惠率领的数千清军在叶尔羌附近为数万敌军所围困,“额敏和卓等固拒之”[27]704,额敏和卓彼时在军中协助兆惠抵抗住了敌军的多次围攻,最终坚守到了援军的到来,此防御战亦被称为“黑水营之围”或“黑水营之战”。此战清军突围而出,意义巨大,主力尚存,而随着援军的相继到来,清朝统一南疆指日可待。
其二,利用民族身份配合清朝统一新疆。清朝统一北疆时,额敏和卓利用自身民族身份开展招降工作,使得吐鲁番另一首领莽噶里克归附了清朝。在清朝计划统一南疆之初,乾隆帝意识到额敏和卓可能在统一南疆上发挥独特作用,提到“尔受朕厚恩,且系回部望族,为众所信,若能设计诱擒……”[35]卷542,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己亥,试图让额敏和卓利用民族和宗教身份来消弭叛乱。清军进军乌什时,额敏和卓探知乌什伯克霍集斯仍居城内,建议争取该人,原因是“霍集斯势埒两和卓,若遣使往间,或成功速”[27]704,此议得到了乾隆帝的肯定。此后霍集斯归顺了清军,清军得以顺利统一乌什,霍集斯后来也成为清朝经略南疆的助手。此外,哈密维吾尔族首领玉素布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清朝安抚新附部族的助手,例如“阿克苏降,定边将军兆惠檄玉素卜驻阿克苏,寻乌什降,复檄驻乌什”[27]690,可知玉素布在南疆诸城的善后工作中地位重要。
其三,为清朝统一新疆提供情报和决策咨询。清朝统一南疆之始,乾隆帝曾让额敏和卓参与决策,即清廷应当派多少兵力、于何时出征,并命额敏和卓参赞军务,在前队行走。乾隆二十三年,清廷授额敏和卓为参赞大臣,随同靖逆将军雅尔哈善征大小和卓。额敏和卓为乾隆帝的决策和清军行动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如乾隆二十三年,额敏和卓“侦沙拉斯等贼由库车遁叶尔羌”[27]704。额敏和卓还积极派遣属人为清军进军南疆提供向导,乾隆帝认为额敏和卓所派之人俱可信任。乾隆二十四年初,清军破围回到阿克苏。当年夏,清军整军进攻喀什噶尔,额敏和卓“谍布拉呢敦、霍集占弃城遁”[27]704,故而清军乘势统一了喀什噶尔。
此外,漠南蒙古地区的察哈尔蒙古、土默特蒙古、阿拉善蒙古等部皆在清朝统一新疆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如乾隆二十一年清朝出兵统一新疆期间,清廷“派察哈尔兵一千名……阿拉善兵五百名,合之兆惠带出兵二千余名,约共兵六千余名,以为进剿之用”[35]卷528,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丁丑。从以上论述可知,各族都是清朝统一疆域的依托,印证了“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亦如相关研究所言,“各民族都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空间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5]。
一. 畲族将领蓝理与清朝统一台湾
二. 满、蒙、汉、藏等族在清朝统一西藏中的贡献
三. 满族八旗是清朝统一西北疆域的依托
四. 汉族和回族组成的绿营兵与清朝统一西北疆域
五. 杜尔伯特蒙古族与清朝统一新疆和乌梁海地区
六. 哈密、吐鲁番维吾尔族与清朝统一新疆
-
在明末清初中华大地动荡不安、外部侵略压力空前的背景下,发端于中国东北的后金-清政权,及时统一了中原和边疆,中国再次进入大一统时代,使得抵御沙俄等外敌侵略成为可能(例如中俄雅克萨之战),反映了“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1]。同时,结合“四个共同”和清代各族对中国疆域统一贡献的历史,可得出以下几点历史经验和启示。
-
后金在建立之初,进行了满族内部的统一,此后又统一了漠南蒙古诸部,形成了“满蒙联姻、联合”的特殊关系。在早期统一东北的战事中,努哈尔赤主要聚焦于内部统一,也不具备入主中原的实力,仅同明朝争夺东北地区的统治权。皇太极继位后,接纳了更多的汉族将领,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原政治文化,并愈加重用汉族势力。待皇太极获得所谓的传国玉玺之后,便改元称帝,使得后金-清的政治制度进一步中原化,并具有了入主中原、统一中华的意识。崇祯十年,皇太极提到自己梦到万历帝,还得到了金朝史书,诸臣认为这是“吉兆”,“盖将代明兴起,故以历数授我皇上也”[38]卷36,崇德二年六月甲寅,反映了彼时皇太极欲取明朝而代之的内心想法。皇太极驾崩后,在李自成出兵攻陷明朝都城北京之前,清朝统治者顺治帝在多尔衮等人的辅政下已做好了入关的准备,无论李自成是否攻陷北京城,都不影响清朝破山海关而入中原的决心。后来,康熙、雍正、乾隆等帝,以中华自居,认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39]卷86,雍正七年九月癸未,接力统一中华疆域,最终实现了大一统。
-
以清朝对西藏的统一为例,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和五世达赖在明末时整合了青海和西藏,他们对清朝兴起、明朝衰亡的趋势有着清晰的认识,曾遣使绕道漠南蒙古前往沈阳同皇太极建立联系。崇祯十六年,顾实汗致书皇太极提到:“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佑。”[20]卷2,崇德八年九月戊申得到了皇太极的允许,但未及该议成行,皇太极便驾崩,达赖亲往沈阳祈福并同清朝建立紧密联系的计划暂时搁浅。清朝入关统一中原之后,特别是统一甘肃、四川等直省地区之后,西藏地方与清朝的沟通更为顺畅,最终有了顺治九年五世达赖亲自赴京朝觐并接受册封的历史性事件。从这个角度看,地方政治力量的疆域“小统一”为后来中央王朝疆域大统一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即如相关研究所言,“地区性统一政权对地方经济的开发,与中原地区联系的加强,以及在主观和客观上对各民族各地区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推动作用等,是不容忽视的”[6]。
-
以漠西蒙古为例,虽然该部一定程度上威胁过清朝的边疆,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了中华疆域。一方面,该部与清朝的冲突具有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族群在疆域和政治上争高下的意涵,康熙帝认为漠西蒙古首领噶尔丹“势盛志大,必舍命觊觎中原地方”[40],有入主中原的企图,清朝必须全力应对。漠西蒙古在侵袭漠北蒙古、西藏等地时,虽然短时间内造成了清朝对地方统治的动荡,但客观上又为清朝进一步加强在边疆地区的统治、完善边疆治理体系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漠西蒙古的崛起客观上也阻止了沙俄向新疆地区的扩张。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时,沙俄觊觎新疆,彼时的漠西蒙古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曾派兵阻击沙俄军队,“经过三天激战,迫使侵略者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计划”[41],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沙俄的侵略野心,具有反抗外国侵略、保卫中华疆域的历史意义,为后来清朝统一该政权时接管这些疆域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清代满文史料也曾提及康熙朝后期漠西蒙古与沙俄关系并不友好,曾扣留沙俄入境人员[42]。倘若清初时新疆地区没能崛起一个相对强大的地方政权,那么在清朝后来统一新疆之前,新疆地区可能面临更多的来自沙俄的侵略压力。也因此,有研究认为策妄阿拉布坦反抗沙俄侵略的举动,“有力地维护了准噶尔乃至中华民族的主权和统一”[43]。
-
综观清代历史,一是各族上层统治者是清朝疆域统一的促进者,如清前期的诸位皇帝,励精图治、锐意进取,推动了中国的大一统;同时,新疆哈密首领额贝都拉、吐鲁番首领额敏和卓等人,顺势而为、主动归附,所辖地成为清朝管理下的扎萨克旗,直接充实了清朝的疆域;又如杜尔伯特首领三车凌归附清朝,增强了清朝推进统一的信心,促进了清朝正式统一新疆。二是在上层统治者之下,各族的兵民亦是清代中国疆域统一的促进者,即如前文所述,康熙五十七年八旗兵第一次入藏驱逐漠西蒙古势力,五千八旗劲旅在青藏高原全军覆没、折戟沉沙,为清朝的疆域统一做出了巨大牺牲,而此后的康熙五十九年,清朝更是调拨了满、蒙、汉、回、藏、纳西等族兵民,参与清朝驱逐漠西蒙古军队的战事,最终恢复了西藏的稳定,实现了清朝对西藏的完全统一。各族兵民为清代中国疆域的统一作出了重大牺牲,他们都是维护中华疆域的英雄,值得铭记与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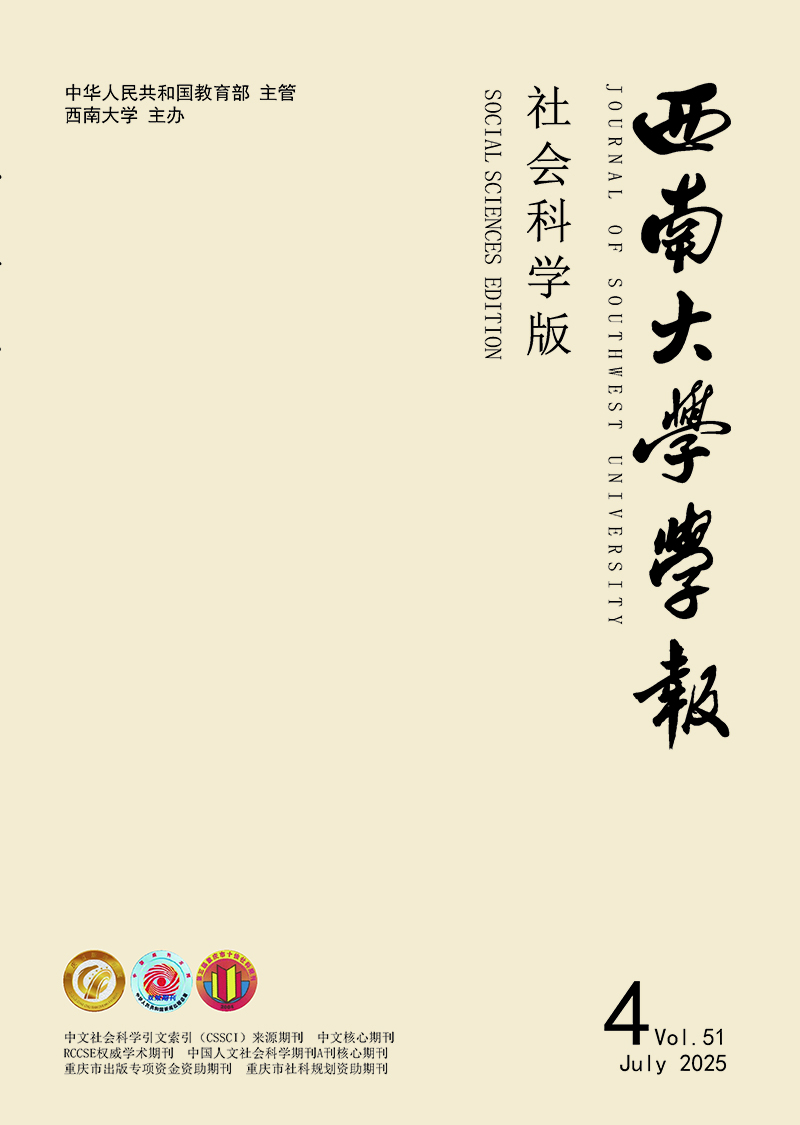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