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ML
-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文学研究界对文学地理抱持极大研究热忱,文学地理学渐成显学,产出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就目前而言主要有两条研究路径。一是聚焦人—地关系,以地理环境决定论为主体的传统研究路径。刘勰《文心雕龙》的“江山之助”说及东、西方典籍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1],为这种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江山之助”说包含文学风格地域论[2]、人文与自然互动论[3]等理论命题。地理环境决定论对文学地理学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建构作用,虽当下仍有学者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进行辩护[4],但因其不重视人的主体性作用而饱受诟病,有学者因此提出了“地理环境制约论”作为替代方案[5]。二是受西方当代文化和空间研究影响,聚焦权力生产的地理空间研究路径。陈舒劼等以性别、阶级、种族为具体讨论对象,探讨了空间理论重构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可能性[6]。用空间权力网络去重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路径,也受到了部分学者质疑,他们要么担心“因此衍生了文学地理泛化的弊端”[7],要么主张文学地理空间批评与表征权力和知识的后现代空间批评之间“性质不同,不可混为一谈”[8],提倡文学地理学批评要特别注重研究“文学文本空间形态中的地理要素及其来源、构成和价值”[9]。沿着上述两条路径出现了一些理论命题,例如“地图说”“本位说”“边缘说”“关系说”“空间说”五大方法理论[10]等。
无论是两条研究路径抑或五大方法理论,皆说明中国学界还未就文学地理学在概念、学科归属和性质、研究方法等方面达成重大理论共识,文学地理学“在我国还是一门相当年轻的科学,其学科概念的完善、学科归属的确定和研究方法与基础理论的建构都还处于探索阶段”[10]。检视已有研究成果,可发现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如果不是唯一的话)原因是学界对“文学地理”这个关键概念有不同理解。例如,杨义的文学地图或文学地理是指包括区域文化、作家的空间流动、家族迁移、文化中心的空间转移等地理空间,采用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方法,观照生成文学作品和文化精神状态的外部地理空间,较少探究文本内的地理空间形态[11-12]。曾大兴用涵纳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文学地域性来概括文学地理,突破了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单向度影响说,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互动的辩证关系[13]。梅新林洞察到文学与地理学的结合纽带是空间,主张地理的外层空间和文学的内层空间应贯通一体,倡导地理学的科学实证法和文学的美学阐释法相结合[14]。邹建军主张自然山水构成了文学地理的主体内容,包括作家经历的自然山水、媒介渠道获取的地理和宇宙新知、作品呈现的审美自然山水等[15]。学界对“文学地理”还有不少论述,这里无法逐一概述。相关讨论虽然内容广博,但贯穿其中的两条主线明晰可辨,即外部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和文本的审美地理环境,表现为实证多、资料多、系统理论少的“二多一少”研究局面,还未能构建起一个学科所应有的研究范式和科学理论。
文学是人学,“文学地理”顾名思义,其根本点和出发点就是人与地之间的交往互动关系。空间和时间是构成文学的两个根本维度,文学自诞生之时起便有文学地理。构筑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概念、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一方面要结合当代批评理论,坚持跨学科的研究道路,另一方面要对中西历史积淀的文学地理思想资源进行消化和吸收。地理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是文学地理思想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却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和讨论。中西创世神话显示,古人习惯从身体角度认知周围世界,反之亦然。据俆整《五运历年纪》,盘古死后,身体化成了宇宙万物,风云、雷霆、日月、田地、星辰、四极五岳等皆系盘古身体幻化而来[16]。希腊神话将地母盖娅视为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之母,说明人类的身体来自大地。这种人、地类比甚至同构的修辞文化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而是成为人类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鉴于“地理是国家得以存在的物质载体”[17],国家出现后便与身体产生修辞关系。中国包含天人合一、王朝地理的天下观就是将国家、地理、身体融为一体的宇宙论思想[18]。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不仅隐含鲜明的身体政治论,而且用身体隐喻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喻论的本质和核心”[19]。西方亦然,从希腊古典时期经由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欧洲政治思想有“一个将国家进行人格化类比的历史”,抽象的国家或宇宙被简化为具体可见的“物理现实和单个的人体”[20]。欧洲中世纪晚期至现代早期,盛行国王二体论思想,目前对政治身体的讨论大多关注国王政治身体的权力(如王权)运行机制[21-22],未能意识到地理在建构国家人格化的政治身体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地理景观、地图、地理空间是国家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作品为研究案例,探讨地理景观、地图、地理空间如何借助人格化修辞手段去表征国家政治,以期对中国文学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论命题有所借鉴和启示。
-
地理景观包括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地理景观,前者如高山、河流、森林、荒野等,后者如欧洲的城堡、中国的长城以及花园和城市景观等。人、景同框的地理叙事在中国山水画和西方风景画中皆有体现,早期现代英国文学凭借西方传统宇宙论的几何学理论,打通了人体与地理景观之间的隔阂,以表现作家的政治理想。地理景观与身体之间的类比与中国“天圆地方”说可以形成共振,且有助于辨析后者蕴含的政治地理内涵。
-
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不乏景观身体化、身体景观化的叙述场景。斯宾塞的传奇史诗《仙后》第2卷第9章第22节描写了一座名叫“阿尔玛”的城堡(Alma Castle):最上端是圆形,最下端是三角形,中间部分是正方形;正方形“按七和九的比例,分配均匀”;“九是设置在天空上面的圆,/一切汇成了一个音域,美妙而婉转”[23]。这座城堡的结构常被解读为人体结构,圆形代表人的头颅,三角形指伸开的两条腿与地面形成的构图,正方形暗示人体的中间区域。该卷主要人物该恩和亚瑟进入城堡参观,行经路线按照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的身体内部空间顺序进行,先是从口进入身体,经过食道,抵达腹部的消化系统,然后从腹部上升,经过心脏,步入大脑部分,结束这场身体之旅[24]239-246。这场类似解剖术的身体之旅涉及古典体液医学理论、灵魂论、身体—国体类比论等复杂概念。本文主要聚焦身体—国体类比论,进而探索背后的地理信息。斯宾塞不惜笔墨重点叙述三个身体场景:腹部、心脏、大脑。腹部以拟人手法描写食物进入胃部后如何被消化,然后如何被肠道吸收,以及产生的废物(尿液和粪便)如何排出体外。这一系列工作是由相应的体力劳动者完成的。心脏则是各种情感的生发地,更是阿尔玛本人的居住场所。这里的九种拟人化情感都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但她们表达了对阿尔玛的绝对服从。大脑部分叙述了涉及历史记忆、当下现实、未来远景的三位智者,他们为阿尔玛的统治提供咨询和指导。
英文单词Alma字面意义就是人的灵魂,更准确地说是人的理性灵魂,这个理性灵魂“统治肉身,接受身体的一切服务”[24]476,使得节制的身体成为“理性的堡垒”[24]261。有人从希腊哲学的灵魂说解读该恩和亚瑟的身体—城堡之旅,认为阿尔玛城堡代表了植物、感觉、智性三重等级有别的灵魂[25]。但是,单纯的灵魂说忽视了古希腊的灵魂—国家类比说。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用国家类比灵魂,辩称两者有相似的结构,其观点可简述为:“与城邦中手艺人、护卫者、统治者三分类似,灵魂也分为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即欲望、激情、理智。手艺人对应着灵魂中的欲望,负责生产;护卫者对应着灵魂中的激情,负责守卫;统治者对应灵魂中的理智,负责治理。当欲望、激情和理智各安其分、各司其职时,灵魂达到了正义。”[26]将柏拉图的城邦灵魂与阿尔玛城堡的三处身体叙事相对照,不难发现它们高度相似。那些在腹部消化排泄系统进行劳作的人,对应苏格拉底的欲望和手艺人,心脏部位九种情感与激情相关,其职责是接受阿尔玛的统治并保护她,阿尔玛接受大脑三位智者的建议,代表理智对整个城堡进行正义统治。就历史演化而言,城堡含有不言自明的政治内涵。“城堡”castle源自拉丁语castellum,后者常用来表达《圣经·新约》中的村庄、城镇、灵魂,这些用法影响了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城堡概念,既指贵族、王室、军队使用的具有防御或者进攻功能的建筑物,也引申为能抵御邪恶力量攻击的灵魂,出现了人的灵魂城堡或者精神城堡之说,使得世俗的城堡与神圣的教堂之间具备了某种相通性[27]。欧洲中世纪晚期兴起国家身体理论,认为国王是头,臣民是肢体,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合众体”,即政治身体[28]。这一切说明,阿尔玛城堡不仅呈现了人的自然身体形态,更以隐晦的方式暗示它是一个政治身体,阿尔玛如同国王,通过头颅的理性功能对国家“合众体”的自然身体进行管理而成就政治身体的正义美德。
人体与地理空间甚或宇宙空间的对应关系,产生了一个含义丰富的空间概念隐喻,即“地球是放大的人体”[29]。如果说阿尔玛城堡是以灵魂的拟人化修辞策略来类比国家,那么,它的垂直结构和几何构架就构成了这个国度的地理空间。“几何”概念来自古埃及,意即“测量大地”,圆形、正方形、三角形是几何的原型形式[30]。这就是说,几何的本意是边界,这些边界通过圆形、正方形、三角形这三个基本的几何形式得到解释。按此原理,阿尔玛城堡的几何构架就是对身体政治的地理绘制,暗藏着浓厚的政治伦理意义。地理景观可以用高山、森林、平原、花园、洞穴、河流等词汇表达。与周围较为平坦的荒野比较起来,阿尔玛城堡如同高山,最能表征作为高山特征的是位于阿尔玛城堡最高处的圆,诗人说它是“天空上面的圆”,明确了其高度。与这个圆形处所相配的数字是9。文艺复兴时期,数字9指天使和恒星天,表达灵魂和精神[31]。灵魂和精神是主持智慧、理性之头颅的属性。就空间而言,山峦、山峰处于高处,与人的头颅形成呼应,也就是说,山峦或者山峰是地理意义上的头颅。
《仙后》继承了古希腊神话和圣经的高山地理叙事传统,整合诗人的家国情怀和新教立场,形成了带有明显意识形态性的高山地理叙事。随着以哥伦布发现美洲为标志的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航海图、指南针成为当时海外探险家的标配,以之辨明方向。但《仙后》的冒险骑士既无地图或航海图,也没有指南针,他们通过亲身的空间经历获取第一手地理知识,高山知识便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仙后》采用讽喻手法,骑士们经历的高山既指地理景观,更蕴含宗教和政治伦理意义。因高山如同主智慧和理性的头颅,该恩和亚瑟进入高山式的城堡顶部后,他们阅读历史的过程就是他们的头颅接受智慧和理性的过程,由此获得新知,为下一步的冒险旅程锚定方向。高山如同航海图,给迷路的远航人指明方向。这种“高山—头颅—新知”的空间经历模式,在其他几卷中都有或明或暗的体现,这里再举第1卷红十字骑士的空间经历为例。
红十字骑士被“仁慈”女士带到一座高耸挺拔、建有教堂的山上,那里隐居着一位虔诚的老修士,叙述者将此山比喻为摩西领受十诫的西奈山,或者耶稣给门徒传教的橄榄山以及希腊缪斯们吟唱圣曲情歌的帕纳索斯山。正是在这座神圣的山上,骑士从老修士那里知晓了自己的身世和未来的奋斗目标。根据老修士的讲述,骑士曾被农夫收养,与尘世的田垄和耕作相关,故名为乔治[24]133-134,136,其所蕴含的劳作美德吻合了斯宾塞的新教伦理立场。乔治作为骑士,按照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化当属贵族,更何况本是王子,但现在要付出相应的劳作。有学者认为,红十字骑士的身世叙述暗示了诗人企图通过“道德警示”来改造“贵族们习以为常的安逸生活”,但“更多的还是试图通过对劳动的重视,尤其是对农事劳动的强调或赞许来重塑贵族价值观”[32]。当然,圣乔治作为英格兰的守护神,意味着民族的安全和强大都需要劳作来守护,这决定了红十字骑士的命运和前提是为国效力。可以说,居住在高山上的修士如同人的头颅一样,给红十字骑士指明了未来人生的奋进路线,为他最后成功屠龙提供了精神向导。
-
刘成纪认为,圆形有和谐、完整性、统一性等美好意义,世界许多民族具有“尚圆”的空间文化传统,中国“天圆地方”概念涵纳以圆盖方、方趋向圆的地理审美思想[33]。阿尔玛城堡与人体结构合二为一,“天圆地方”概念能有效揭示该城堡蕴含的空间伦理思想。那些居于四方形、三角形等方形部分的人物服从阿尔玛的统治,表明方趋向圆,整个阿尔玛城堡趋向圆,体现了圆的潜势或特征。阿尔玛城堡虽地处荒野,每天遭受象征非理性的敌人的攻击,却屹立不倒、毫发无损,除了圆形的壕沟和围墙构筑起的物理保护层外,更是理性构筑起了最强大的“圆”保护层。由于自然、人体、几何具有认知概念上的通约性,几何空间便有了相应的对应地景空间。圆形表征了具有理性和信仰护卫功能的头颅,居中心位置,对应的地景是高山、城堡等;正方形的人体腹部是四种基本元素和体液的处所,暗示内心的矛盾和冲突,对应的地景是平原、水池等;人体的三角形部位最不稳定,驻扎有低级的欲望,对应的地景常是森林、峡谷、洞穴等布满危险的阴暗之地。但是,这些地理空间所代表的概念世界并不是绝对的,圆形空间可能因保护功能的丧失而演化为正方形甚至三角形空间,正方形、三角形空间因有保护元素的介入而具备圆形空间的潜势或者归入圆形空间的范畴。此时就会出现国家地理空间原有景观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则与政治身体状况相对应。
花园、王宫、海岛因分别有篱笆、围墙、水域等防护成为城堡或者高山的变异地理表现,并与人体产生或显或隐的关联。这里以花园为例进行讨论。与无序的荒野相反,花园体现了一种和谐理想:“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喜欢排列整齐的树木、按几何图形设计的花坛,以及封闭性的长方形地面。艺术家们认为可以严格地测量空间,并将其设计成一片可以测量的图案。数、量和比例的关系成为和谐的特点。园艺家们按照比例在园中种植花草,并把各种成分协调为一个单元。”[34]这里所说的几何图形、数、量、比例、单元等是理性的符号表达,这意味着和谐因理性而生。正因如此,物理的花园便可用来表达人的身体状况,健康或者病态。自14世纪后半叶起,英国诗歌出现了“灵魂的花园隐喻”,有的作品中“作为灵魂隐喻和尘世文明景观的美好花园是同一个东西”[35]。花园是运用几何构图对旷野进行改造的结果,所以任何花园都存在缺席的旷野,即旷野是不在场的在场者。这同样可以解释灵魂花园的存在状态。灵魂花园由其本身所具有的理智与情感、善良与邪恶等二元对立属性所规定,充满不稳定性和变化性。这就出现了茂盛或者萧条、有序或者破败等状况的花园景观变化。
莎剧《亨利五世》启幕不久,坎特伯雷大主教这样评价刚登上王位的亨利五世:“凭他年轻时的那份荒唐,谁又能想到啊。他的父王才断了气,他那份野性仿佛也就遭了难,跟着死去;对,就在这时候,‘智慧’,真像天使降临,举起鞭子,把犯罪的亚当驱逐出了他的心房;从此,那一座‘乐园’净是纯洁的精灵在里面栖息。”[36]110坎特伯雷大主教将灵魂比喻为花园,显示亨利王子的灵魂花园经历了巨大变化。用几何构图来解释的话,亨利的灵魂经历了从充满欲望的三角形荒芜花园到理性统治的圆形伊甸园的转变,即实现了从方到圆的转变。亨利五世已经成长为一位好园丁,意味着他会将国家打理为一座好花园。“智慧”的原文是consideration,暗示亨利王子成为国王之后处理政事深思熟虑。这种国王无疑会让其臣民受益良多,国泰民安,伊里主教情不自禁地庆幸“我们是有福了”[36]110。伊里主教用“我们”这个集体称谓暗示国家是一个共同体,作为手足的臣民和作为头脑的国王成为不可分割的、花园式的政治身体,国王是园丁,臣民则是花园里面井然有序的植物。
然而,当理性的防护功能丧失时,意味着圆形的消解,美好的花园或者屹立高耸的城堡让渡给贫瘠的荒原、充满变化和危险的森林和水域、黑暗的洞穴等地理景观,与城堡身体的三角形形成对应。《理查二世》的约翰在赞美了不列颠岛如同受到护卫的花园之后,接着哀叹道,英格兰“现在却像一幢房屋、一块田地一般出租了”[37]351。“出租”说明花园不复存在,甚至连代表文明的房屋、田地都没有了。导致花园消失的原因是英王理查二世的专横、昏庸、暴戾。该剧第三幕第四场有园丁和仆人之间关于花园的对话,直指理查二世治下英格兰的荒野现实。园丁要求仆人去“斩下那些长得太快的小枝的头”,因为它们在“共和国里太显得高傲”(即获得了特权),园丁自己则“要去割下那些有害的莠草,它们本身没有一点儿用处,却会吸收土壤中的肥料,阻碍鲜花的生长”;仆人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他认为整个国家都出了问题,感慨地反问园丁:“你看我们那座以大海为围墙的花园,我们整个的国土,不是莠草蔓生,她的最美的鲜花全都窒息而死,她的果树无人修剪,她的篱笆东倒西歪,她的花池凌乱无序,她的佳卉异草,被虫儿蛀的枝叶凋残吗?”[37]385花园被巧妙地用来暗指政治身体,表明英格兰这座身体花园失去了理性的统治头颅,被野性力量占领和控制,变成了破败的荒原。
一. 城堡、高山与理性政治身体
二. 地理景观变化的政治身体
-
随着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16、17世纪欧洲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地图制作业随之兴旺起来,地图作为一种文学意象逐步进入文学作品。莎士比亚笔下,表示地图和图绘含义的map多次出现在其作品中[38]。绘制或者拥有地图不仅意味着空间知识,更以视觉符号的修辞方式传递着地理空间触发的权力较量、情感纠葛等公共和私人话题。
-
莎士比亚的长篇叙事诗《鲁克丽丝受辱记》记叙了发生在罗马王政时代的一个悲剧。罗马王政时代最后一位国王路修斯·塔昆纽斯的儿子塞克斯图斯·塔昆纽斯(本文以下简称“塔昆”)强暴了鲁克丽丝,导致其自杀身亡。当施暴者塔昆逃离后,气愤、悲伤、痛苦的鲁克丽丝凝视着自己房间里挂着的一幅画,画面“精妙逼真地画着普里阿摩斯的特洛亚”[39]130。虽然这幅画的主题是特洛亚战事,但以城市为空间布局的画本质上就是一幅地图。就地图的图绘语言而言,画面有城市景观,如“高耸入云的伊利昂”“崇楼尖塔”“被围的城头”“烈焰烛天的特洛亚”[39]131,134,136等。此外,画面也不乏河流景观[39]134。从城景和河景看,这确实是一幅传统地图,由此决定了人物也是地图符号的一部分,即具身化地图。刘成纪称这种地图为审美地图,中国传统地图大多充当了“美学和人文观念的视觉标志物”,有时具有“立体实景地图的性质”,而且“地图的山水化几乎全面主宰了隋唐以降中国地图制作的方向”[40]。西方地图文化亦为同理。欧洲中世纪乃至早期现代时期的许多地图带有装饰性质,人物、赞主、景观等写实图像成为装饰性地图的有机组成部分[41]。地图中的实物、人物、动物、自然和人文景观与用经纬线表达的地理符号融为一体,演化为相互表达的互构关系,置身其中的身体成为地图的一部分,与地图形成互构关系。拉丁词汇Typus(地图)表示墙上的一幅画,暗示地图可以作为装饰图画挂在墙上,反之亦然。据此,鲁克丽丝房间墙上的图画是一幅审美地图。
值得注意的是,鲁克丽丝将自己等同于画中的人物,意味着她将自己的身体置于画中、置于地图之中。诗歌文本以工笔画式的细腻手法描写鲁克丽丝从画中寻找自己的代言人,她找到了特洛亚王后赫卡柏,把自己认同为这位“伤心绝望的老妇人”[39]134,与这位悲痛欲绝的老妇人进行思想交流,认为她们有着共同的敌人[39]135-137。此外,鲁克丽丝还“两眼扫视着,在画上到处寻觅,发现谁困苦无依,她就为谁哭泣”[39]137。鲁克丽丝逐渐将自己的遭遇和痛苦与特洛亚的遭遇和苦难进行认同,她认为依靠诡诈获得特洛亚王的信任而成功实施木马计划的西农,已经变成眼下依靠谎言而进入她房间的塔昆,从而“使我的特洛亚覆亡”[39]140。鲁克丽丝将自己的身体完全等同于特洛亚,特洛亚得到了充分的具身表达,并通过地图场景,形象地展示了这个女性身体遭遇的创伤景况。
鉴于鲁克丽丝自杀前将自己等同于地图画中的特洛亚,那么,鲁克丽丝是否影射了罗马地图或国土呢?当塔昆深夜进入鲁克丽丝卧室后,他凝视着床榻上熟睡的鲁克丽丝,诗人用战争意象来修饰塔昆即将对鲁克丽丝造成的伤害[39]87。这些战争意象与前文叙述鲁克丽丝凝视的特洛亚地图场景如出一辙,诗人接下来叙述道,塔昆那双得意忘形的手“停留在袒露的胸脯——她全部领土的中心”[39]87。“全部领土”表明鲁克丽丝的身体已呈土地状、地图化了。所以,当塔昆的两只手触摸鲁克丽丝的身体时,诗人运用了军队攻城的修辞方式,鲁克丽丝的身体被喻为“象牙墙”“市民”“迷人的城郭”[39]89。加之“她全部领土”,鲁克丽丝俨然是一座有城墙护卫的城池了,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市民。
就审美意义而言,鲁克丽丝身体的地图修辞已经与诗歌后半部分特洛亚的地图修辞具有等价的政治审美效应了。塔昆攻城略地,强行进入鲁克丽丝的身体,实为一个毒化和玷污行为。鲁克丽丝后来将自己比喻为特洛亚,是一座被外来力量破坏的城池,但读者很清楚,作为一个罗马市民,鲁克丽丝应该是罗马城,她被塔昆强暴和玷污实为罗马被集权政治强暴和玷污。鲁克丽丝用尖刀放出自己身体中被污染的黑血,指向罗马政体即将清除塔昆家族这股政治污血。当鲁克丽丝的夫君及其部下抬着鲁克丽丝的尸体在罗马城游行时,实则是抬着一幅被塔昆家族王权统治毁坏了的罗马地图。这里,共和思想视每个平民的身体为政体地图的有机组成部分,甚或本身就是一幅微型的政体地图,对平民身体的破坏,就意味着对国家地图的践踏和蹂躏。这幅破败不堪的罗马政治地图唤醒了罗马人的良知,他们起来推翻了塔昆家族的统治,罗马走向了共和制。
-
绘制地图通常需要圆规、罗盘、刻度尺等制图工具。马洛的戏剧《帖木儿大帝》描写帖木儿围攻大马士革时,帖木儿告诉该城总督的女儿奇诺科拉特,即使是神的领地,他也要用手中的剑夺取,谴责“那些瞎了眼的地理学家……把世界弄成了三块”,声称自己要用手中的剑重新绘制世界地图,将自以为豪的征服之城大马士革作为“中轴线的开始”[42]236-237。欧洲中世纪地图绘制师根据宗教信仰和有限的地理知识绘制T-O地形图,帖木儿则要用军事征服和战争武器修改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地图,剑成为了他绘图的圆规和刻度尺。整个戏剧反复提及帖木儿的剑,多处描写帖木儿及其军队,以及追随者征服、占领的地理路线。整部《帖木儿大帝》就是用利剑、长矛等征服工具绘制的一幅帝国侵略征服地图,为这幅地图定位的罗盘是戏剧人物所言的命运女神。帖木儿穷毕生功力,构筑了一个疆域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政治身体,依靠命运女神和利剑绘制的地图成为这个政治身体的绝佳视觉修辞表达。
国王二体论把与政治运行机制相关的行为纳入政治身体范畴,以此为视点,则不难发现帖木儿的身体变化与地图扩张之间的微妙关系。当奇诺科拉特被劫持到帖木儿面前时,她直呼后者为牧羊人,帖木儿则辩解道,牧羊人只不过是出生时的身份而已,而他“注定将征服亚洲,/震惊这个世界,/扩展他帝国的疆土/向东向西,沿着福玻斯的行进路线”[42]148-150。帖木儿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他要靠征服成为一个拥有广阔领土的帝国君王,并以太阳神自诩。接着,帖木儿脱下了身上的牧羊人服装,穿上了铠甲,拿起了战斧[42]150。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帖木儿首先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了改造,使牧羊人的自然之体被赋予帝王的政治之体,并通过征服广阔地理疆土而得到强化。剧本通过帖木儿本人和其他戏剧人物之口,将帖木儿的身体神圣化、地球化、宇宙化,从而隐晦而又巧妙地将帖木儿建立的帝国处理为一个神圣和宇宙化的身体。例如,本是率骑兵前来与帖木儿作战的波斯贵族特瑞达马斯见到帖木儿后,被后者的仪表所震撼,惊叹帖木儿虽是牧羊人出身,其相貌、气概、眼神等身体表征可以藐视众神,上可挑战天神,下可战胜地狱恶魔[42]156-157。另一位波斯贵族对帖木儿卓尔不群、伟岸挺拔的身体赞不绝口,以阿特拉斯(Atlas)来作譬喻,惊叹帖木儿“四肢健硕,关节强壮,双肩宽阔,可比背负天穹的巨神阿特拉斯”[42]163。阿特拉斯因支持泰坦族反叛宙斯失败而受到惩罚,流放到宇宙最西边以双肩擎托天穹,16世纪荷兰地图学家墨卡托制作的第一幅世界全景地图集的扉页,便是阿特拉斯肩负天球(一说地球)的图画,后来地图绘制人便用Atlas指代地图集。波斯军中贵族米恩德尔认为帖木儿同时集中了神圣和邪恶力量,“根本不是出自人类种族”,可以蔑视和抛弃任何法规,“明目张胆誓要实现野心”[42]184。帖木儿可能熟悉《旧约》,称自己“注定要成为上帝之鞭,/让全世界感到害怕与恐惧”[42]203,彰显了他将身体神圣化的自我命名。
总之,帖木儿拥有政治身体之后就不断将自然身体神圣化、地球化、宇宙化,使得他的政治身体无限膨胀。在帖木儿看来,不断征服世界就是表达神圣化和宇宙化政治身体的有效方式。如果说地球是上帝绘制的原始地图,那么帖木儿就要以新神祗的身份挑战那幅神圣的原始地图,绘制一幅展现自己政治身体的地图。但帖木儿的自然身体规定了他不是永恒的神,其生命伴随征服走到了尽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不忘那幅表达政治身体的地图,他让随从给他一张地图,要“瞧瞧世界还剩多少地方供我征服”,鼓励他的两个儿子去征服他未能征服的地方,嘴中不断念叨“我将死去,还有这里没有征服”,然后将地图递给他的儿子[43]。虽然他临终前给儿子和追随者展示了一幅他想用利剑、长矛、马蹄等征服武器绘制的世界地图,但随着身体的消解,他最后意识到自己不是神,只有神才可绘制出真正的世界地图,他模仿神绘制的帝国地图终将归还给神。帖木儿最后拿起的那幅世界地图是其世界帝国政治身体的可视化表达,然而,一个病入膏肓的自然身体无法完成世界帝国政治身体的绘制,当他的身体呼出最后一口气而倒下时,那幅置放在他尸体旁边的世界地图也会悄然发生变化,帖木儿的政治身体终将消解。将一具尸体和一幅世界帝国地图并置,这样的舞台场景极具戏剧张力,暗含了剧作家对极端个人主义的辛辣讽刺和对帝国政治野心的警示,也是对当时主张人可以比肩天神的西方传统宇宙论的反思。
-
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启幕不久便是李尔王拿着地图、将国土分给三个女儿的场景[44]。学界大多认为李尔“是一个老迈昏聩的国王”[45]。当然,也有学者主张李尔划分国土和爱之考验的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安排或政治骗局,目的是防止他死后可能出现的国家动荡,只是因为小女儿出于对超越政治的美德和真实的执著而不配合李尔的政治骗局,由此产生了政治权利和自然权利冲突的悲剧[46]。本文认为,李尔的悲剧不仅源自政治权利和自然权利之冲突,更主要的是源自他那剥离具身性的二元认识论。李尔视王权符号为抽象化、绝对化和神圣化的象征性体系,并将自身视为一个不受自然空间和自然物质约束的万能符号,即他认知的只有抽象的政治身体,无视自然身体,殊不知国王二体论强调政治身体和自然身体合二为一,任何疏忽政治身体和自然身体之内在联系的行为都将导致政治动荡甚至政治悲剧。李尔将小女儿强征为政治身体的一部分,并以爱的游戏骗局打破政治身体的王位继承规则,但小女儿拒绝被强征为政治身体,而是坚守自己作为普遍意义上的女儿对父亲的自然身体应尽之义务,这种认知冲突导致李尔的愤怒爆发,进而危及不列颠国土。
因为李尔视政治身体为符号,最具符号表征的政治身体是那幅地图。符号化的过程就是剥离血肉、消解生命的过程。李尔想以绘制地图的方式来叙述君王的绝对权威或君权神授思想,但遗憾的是他最终失败了。李尔未能意识到地图不是一个空洞的能指符号,而是一个涵纳山川湖泊、森林草原的具身性存在。那幅被他随意处置的地图不是一个符号,而是政治身体的重要部分。就此而言,李尔对地图的认知远不及前面讨论的鲁克丽丝和帖木儿大帝。对于李尔的地图,著名莎学家霍克斯评论道:“正是地图构成了地面环境,而非简单地描绘或者呈现地面。”[47]意即地图不是抽象的几何数理表达,而是一个鲜活的身体,是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的承载体。地图的物质性、具身性规定了地图的生命属性,李尔对地图进行分割,意味着李尔视地图为一种无生命的符号,并以此来表征他那至高王权而已。李尔犯了一个关于政治身体的认知错误。早期现代时期,欧洲政治思想有“土地身体—政治身体类比说”,主张“身体、家庭、国土、统治者、政治身体本质上相互交织且相互说明”[48]。不止一位学者注意到,李尔对地图/王国的分割“采用了解剖学家的分割手法”,他对“那幅地图的专横切分实则是对王国进行了解剖式的割分”,剧本包含了“用地图表达的解剖行为”[48]。美国学者索戴的研究显示,欧洲“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末见证了有关人类身体的‘新科学’的诞生”,这个“新科学”就是对人体进行解剖,产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文化”[49]。展示解剖文化的最主要的地点是解剖剧场。所谓解剖剧场,就是外科医生解剖尸体的地方,医学学生或者普通观众可以来这个场所观看外科医生解剖尸体。当时的解剖对象是被执行了死刑的犯人和医院里面病逝的病人,自然是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地图是国土的表达,是一个具有鲜活生命的政治身体。但是,李尔却动用国王的权力,以极其粗暴的手段——君权这把解剖刀——将这个用地图表达的生命体给肢解了,使得国家遭遇动荡,个体丧失生命。由于国土、家庭、统治者、政治身体等之间形成的相互表达和类比,有学者指出,“正是那一个(手指地图的)分割手势,李尔豆剖了他的王国、家庭和理性”[48]。地图被肢解,意味着李尔的政治身体被切分为两个部分,转移到两个女儿身上。一体二身这种政治怪胎不会长久存在,两个女儿为了获得完整的政治身体,她们不仅要把李尔驱逐出去,而且她们两人之间展开了内斗。戏剧最后以伤痕累累的尸体剧场落下帷幕,与李尔肢解代表政治身体的地图形成了绝佳的呼应,充分彰显了破坏政治身体完整性所导致的悲剧。
一. 莎士比亚的特洛亚地图与罗马政治身体
二. 帖木儿的征服地图与帝国政治身体
三. 切分地图的李尔王与被肢解的政治身体
-
地理空间的性征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具身化空间表征,一是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引发的性征联想,例如高山和方尖碑引发的男性力量想象;二是男性或者女性力量主导形成的性征化空间。中西文化不乏性征化的地理空间。据《易经》,“乾”卦代表天,象征着男性、阳刚和创造力;“坤”卦代表地,象征着女性、阴柔和承载。中国皇宫的布局往往遵循“乾上坤下”的原则,是国家地理空间男性化叙事的代表。比如《西游记》中“女儿国”的地理空间神秘而充满诱惑,与女性国度形成呼应。国家地理的性征化叙事千姿万态,本节举隅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以期窥视国家政治形态如何通过性征化地理叙事得到表达。
-
男性身体与男性气概互为表达,男性气概的地理空间通常是体现理性、刚阳、勇敢、力量的地理空间。莫尔《乌托邦》第2卷叙述了一个公有制海岛国家的生活状况,但评论界未曾关注到海岛地理空间性征化改造及其隐含的国家政治,以及与第1卷英格兰国家地理空间形成的鲜明对比。乌托邦岛被征服之前名叫阿布拉克萨(Abraxa),极可能是希腊字母组合,表示365,该数字与古希腊诺斯替派的神秘宇宙学说相关,但无人知晓这个岛名的确切含义[50]。空间的神秘与女性相关。同时,因涉及征服,大航海时代欧洲殖民者常将新世界类比为一位等待被征服的女性。这样,乌托普国王将被征服的海岛重新命名,实则就是一个祛神秘性、祛女性化的行为。
祛女性化标志着构筑男性地理空间的开始。乌托普国王下令将海岛连接大陆的一面掘开15海里,“让海水流入,将岛围住”。此工程浩大,此前讥笑会白费力气的邻国人看见工程完工后“无不惊讶失色”[51]50。从邻国人的反应看,乌托邦人对海岛空间进行改造展现了力量、自信、勇敢等美德,空间改造的目的是保障国家安全,显示了理智的防务原则。空间改造之后,乌托普国王便进行了地貌的文明化建设,主要体现在城市、花园、房屋、田野诸方面。乌托邦有54座城市,每座城市的市貌相同,讲述者只叙述了首都的空间布局。这座城市呈四方形,依山而建,直达山脚一条较大的河流,同时还有一条发源于城基所在山峰的小河穿城而过。从这个城市的空间布局可以看出,乌托邦人将城、山、水融为一体,空间层次分明。城市依山而建,远观则是将原来的山变成了城,雄伟的气势颇显阳刚之气;水顺山而流,尽显阴柔和滋养。山、城为显,水藏于城中和山脚属于隐,这种地理空间隐含男性力量主导国家统治的文化地理,颇似乾上坤下的中国文化建筑地理。
乌托邦的男性地理空间在房屋和花园空间上也得到充分展示。乌托邦的房屋都是沿街而建,“每家前门通街,后门通花园”;因乌托邦无私产,每个房屋安装的都是折叠门,“便于用手推开,然后自动关上,任何人可随意进入”,且“每隔十年用抽签方式调换房屋”[51]53。乌托邦人花时间经营花园,里面有各种花草和水果,任何人都可以来花园品尝水果、欣赏花草,而且按照房屋交换规则,花园每隔十年要易主。空间私密性是女性空间的标配,例如中国文化或者古典小说中的闺房私密性,外人不得随便进入。乌托邦的空间私密性被彻底消解,突出了男性空间的透明性、开放性、自然性。
学界发现,“无论是地形地貌、面积大小、城市数量、物产丰富方面,乌托邦与英格兰之间都有着极为惊人的相似性”[52]。这种地理相似性的诗学旨趣是什么呢?根据第1卷的叙述,英格兰推行私有制,没有乌托邦人崇尚的自然理性,掠夺、占有成为普遍现象,圈地运动使得田地荒芜,贵族阶层懒惰懈怠,军人无精打采,无业者靠盗窃为生。圈地运动使得英格兰乡村土地荒芜,城市街道狭窄脏乱,与乌托邦国长满嘉禾的田野、宽阔和整洁的城市空间形成鲜明对比。《乌托邦》的讲述者将这种国家地理空间的反差,归因于与所有制相关的体现男性气概的自然理性的在位或阙如,以达成批判英国政治制度的目的。
当然,表现男性气概的地理空间远不止《乌托邦》体现的自然理性的国家空间,山野、大海更适合展现刚阳、勇敢、力量等男性气概。这里举两例。马洛戏剧《迦太基女王狄多》中的埃涅阿斯肩负到意大利重建特洛亚的使命,大海成为注定要经历的地理空间。面对充满狂野、风暴、危险的大海,埃涅阿斯展示了男性力量。虽然受到狄多女王的诱惑,他最终战胜了自我,扬帆启航去意大利建立新国度。展现男性气概的大海空间也昭示了未来罗马帝国的国家地理,正是依靠地中海,埃涅阿斯的后人建立了跨越三大洲的罗马帝国。莎剧《辛白林》的威尔士山野荒凉、人迹罕至,只有因受命运差遣而来这里风餐露宿的一位大臣和两位王子,成为一个只有男性在场的地理空间,但是艰苦的环境练就了勇敢、奉献、刚强的男性气概,他们每天祭拜太阳实则是一种男性崇拜仪式。后来,当不列颠遭到罗马军队入侵时,正是这三位勇敢男性的及时援助才使不列颠军队转危为安,守护了国家地理空间的安全。
-
女性地理空间以其细腻、优雅、阴柔、神秘为特征,景观常诉诸感官。《红楼梦》的大观园充满女性气息,其中“怡红院”“潇湘馆”等名称与女性相关,建筑、景观和人物举止充满了女性的细腻和优雅。女性地理空间也常被用来表征国家政治,早期现代英国书写女性空间时,大多表现出一种政治空间焦虑,这极有可能是西方性别二元对立哲学的空间表达。
斯宾塞《仙后》第2卷第12章第42~80节描写了一座名为“福乐谷”的花园,主人是一位女妖式的人物阿克拉霞及其侍女,外出探险的骑士进入这座花园便会被感官享受和情欲迷住,放弃远征探险而沉溺于肉体享乐。福乐园结构层次分明,诗人说它是一座关锁的花园,意味着它被篱笆或者墙垣围了起来,门廊是其唯一出入口,然后依次是三个核心区域:凉亭、喷泉、中心部位的福乐谷。布鲁克认为,这三个核心区域象征了人体的“肝、心、脑”[53]140。也就是说,这个花园结构是一个平躺着的人体结构,是一个具身化的地理空间。
这个花园身体的性别是什么呢?答案隐藏在花园的文化地理中。该花园既有人工艺术品,更多的则是与女性相关的香花、植物、水果、泉池、溪流、绿荫、小鸟等景色,是视觉、嗅觉、听觉、触觉等感官获得享受的场所。该恩骑士和代表理智的帕尔默一进入花园,就被迷人的景象所吸引和震撼,展现在他们面前是“一片广袤的平原,周围尽是/赏心悦目的景观,漂亮的草地/绿草茵茵,花神弗洛拉自豪地/用全力将她装扮得流光溢彩,/她的艺术母亲用这方式,/似乎要把吝啬的自然加以蔑视,/如同将她打扮成炫耀的新娘,/清晨身着盛装步出闺房”[24]278。诗人将这座花园称为“她”,明确了花园空间的性别属性。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的爱神花园“是女子的象征,诸如花木、果实、溪泉等各种自然之美都被用来比喻女子的面庞或形体之美”,甚至“形同睡美人”[53]140。斯宾塞通过富含女性身体文化意义的自然意象、器具和身体行为,例如葡萄藤(54节)、酒杯(56节)、溪流(58、62节)、常青藤蔓(61节)、裸女戏水(63-68节)等,给读者呈现了一个极具感官诱惑的具有性暗示的“爱神花园”。
学界常从古典节制伦理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有关自然与艺术之争两大角度,阐释福乐谷的伦理、心理和文化内涵,自20世纪70年代后殖民批评兴盛之后,有学者关注到该花园可能指涉美洲[54]或英国当时的殖民地爱尔兰[55]。但这些研究较少关注女性地理空间与英国殖民扩张之间的张力。
在花园入口处的象牙大门上雕刻着伊阿宋去黑海岸边获取金羊毛的故事[24]277。在英国早期现代,希腊神话英雄伊阿宋乘船冒险的故事常被用来指称海外探险获取财富。斯宾塞笔下那些外出冒险的骑士就是伊阿宋。当伊阿宋以获取金羊毛为最高追求时,他虽历经险象环生的生死冒险却展示了理性和果敢的英雄壮举;当伊阿宋被爱情和物质享受诱惑时,他则遭遇悲剧。美狄亚总是与毒药相关,伊阿宋获取金羊毛后娶回美狄亚,注定了伊阿宋的悲剧,伊阿宋的命运是船和海洋,而不是甜美的爱情和物质的享乐。以此为参照点,则不难理解斯宾塞笔下那些进入福乐谷这个女性地理空间的骑士的命运。阿克拉霞也常与毒药相联系,她的一个酒杯毒死了一位骑士[24]168,那位与他行乐的骑士昏睡不醒,情景如同中毒[24]284。16世纪后期,英国谋求海外扩张,斯宾塞的《仙后》用骑士的冒险故事为英国的海外事业摇旗呐喊,那些沉醉于安稳享乐的人如同步入福乐谷的骑士,他们沉迷于女性地理空间的感官享受和肉体愉悦,如中毒一般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同时这也隐射了诗人对伊丽莎白一世守土思想的焦虑。
虽然伊丽莎白女王声称自己拥有男性君王的“胸怀和气度”[56],但她只想守护王朝边界而不是像西班牙王国那样主动谋求海外扩张。1593年女王发表议会演讲,其中陈述了她的守土政策:“自从朕成为君王以来,虽然朕拥有拓疆扩土的机遇和实力,却未曾去谋求增广吾国版图。……朕之所愿乃是恪尽公正君主之职守,治理好吾邦疆域。”[57]此时距离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已近5年,但女王仍无海外扩张计划。女王的话还表明,她的守土意识招致了部分朝臣的不满、指责甚至反对。福乐谷里面那些骑士受到女妖蛊惑,解除了武装,沉湎感官享乐而无法自拔[24]284,不仅意味着精神中毒,更标志着海外扩张需要的男性气质被阉割。作为一位帝国诗人,斯宾塞用福乐谷的女性空间来隐晦地指责女王的守土意识,利用诗歌达成对政治的介入。当然,如果诚如前述学者所言,福乐谷影射了美洲或爱尔兰,那么,福乐谷的女性空间则是对殖民骑士的警示,警告踏上那片本该被征服的女性空间时,他们有被征服的危险,避开被征服的办法则需要理性(帕尔默)做向导。诗歌在谴责守土意识和警示踏上殖民土地可能遭遇的女性空间威胁之间,形成了一种政治审美张力。
基于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女性空间对国家地理构成的潜在威胁成为英国男性作家感兴趣的话题。再如《迦太基女王狄多》,陆地和大海构成了鲜明的地理反差。对埃涅阿斯来说,陆地不仅安全,更有温馨、舒适的宫殿物质享受,以及狄多的销魂爱情。狄多对埃涅阿斯表白道:“把我的怀抱作为你的意大利,它的王冠与疆土都由你支配。”[58]89她力图用女性身体置换埃涅阿斯的国家地理计划,配合这场戏的地理环境是雷雨、森林和山洞,表明迦太基遮蔽了埃涅阿斯的男性太阳。狄多力阻埃涅阿斯起航出海,说她要“让他的船搁浅在我的胸上”[58]106。埃涅阿斯最终摆脱了女性提供的舒适陆地生活,扬帆踏入展现男性气质的海洋空间。莎剧《麦克白》的三个女巫占据了一片荒原,这片伴有雷电和蒙蒙细雨、夜里总是出现女巫的神秘空间,与麦克白夫人的欲望心理形成呼应,女性所在的两个空间改变了麦克白将军的人生轨迹,成为苏格兰宫廷谋杀和夺权的导火线。
一. 国家地理的男性气概表达
二. 女性地理空间与国家政治焦虑
-
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到早期现代,欧洲对宇宙、自然乃至国家的认知带有鲜明的具身性,即万物与人的身体形成对应关系,万物可以用人的身体进行解释,反之,人的身体是宇宙、自然、国家的缩影或注脚。国家的存在必须以地理空间为依托,没有地理空间就没有实体性的国家存在。国王二体论的早期现代政治哲学虽视国家为身体,却忽视了地理表达政治身体的叙事功能。地理景观、地图、地理空间是国家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具身化的审美方式呈现国家政治形态。本文的讨论显示,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以具身化的认知修辞方式书写地理,有效地将地理与政体进行整合,地理由此被赋予政治生命意义。地理景观和人的身体在几何构图中获得了共同的政治话语,用圆形表达理想的政治身体状态,彰显了人文主义者的理性治国理念;早期现代地图不是抽象的政治符号,而是被赋予了身体属性,从身体角度解读国家地图有助于明察政治身体的现存状态;二元对立的性别观念形塑了地理空间的性别表达,揭示了当时的男性政治偏见和性别政治焦虑。早期现代英国作家以人的身体为视点,赋予国土以血肉和生命气息,重现地理空间的身体属性这一古老文化传统,将整个国家视为一个地理政治生命体,孕育了重要的现代政治哲学思想。
本文所论地理与身体的互指和类比修辞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属于人文地理学范畴,与中国古代地理思想有契合之处。中国古代地理思想将宇宙—地理、国家、人类与神话整合为一体,凸显了鲜明的人文地理属性。例如,中国夏禹时期制作、现已散佚的实物铸鼎地图《山海图》融景物、神话、国家地理为一体,后人根据不同文字记载绘制的《山海图》传递了“人—地—国”一体的王朝地理主题[59]。不能以现代自然地理的科学系统框架去解释中国古代地理,“中国古代的地理学是发达的社会人文地理学”,自然物只是媒介,“形而上的哲理”才是论证的最终对象,不仅道家、儒家眼中的自然界相异甚远,而且“天下”“华夏”“中国”“九州”“四海”是包纳个人、国家、地理等信息的地理概念,与王朝历史、王朝理念、王朝价值、王朝疆域构建、王朝政治地理秩序、文化观、道德观发生着关联[60]。这样看来,包含国家政治思想的人地类比修辞在中西文明史上皆有较为坚实的地理思想史背景,可以成为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命题,也意味着系统、丰富的人地关系理应成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突破的关键点。如何建立以新的人地关系为本体,景观、地图、空间、陆地水文、物候等多元组合为地之极,政治、经济、伦理、文明交流互鉴等多元组合为人之极的“一体二极多元”文学地理学,可能成为中国文学地理学理论建设的未来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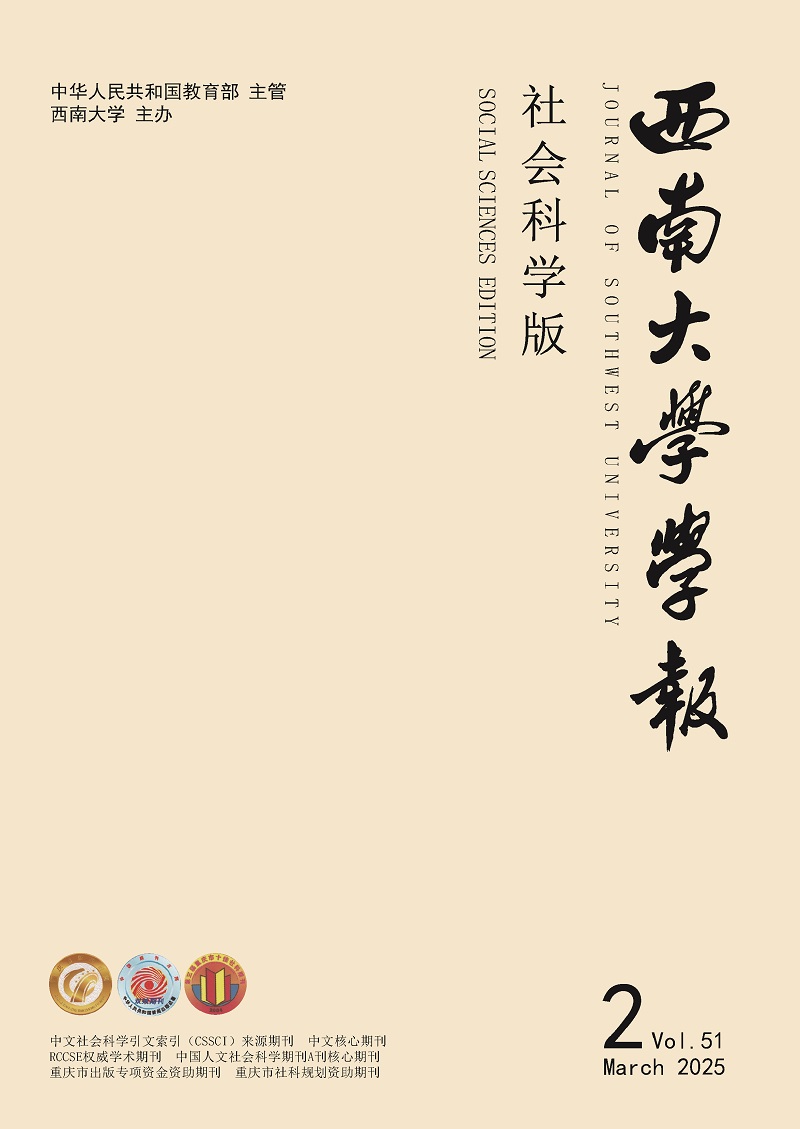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