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决策者而言,环境经济政策主要有以下几大目标:控制污染有用,具有经济效率,在政治上可接受,与现有法律框架保持一致,为经济主体创新提供激励.由于这些环境经济政策目标较多且很分散,现有经济学文献尚未对不同环境经济政策做出较为一致的优先排序,特别是在面源污染领域,理论界尚未建立一种普遍认同的政策规制机制[1].实际上,环境经济政策的选择,除了要考虑政策本身的特征之外,还要考虑环境问题的特征[2].比如,在气候和地貌方面的不同特征使得同一流域内的某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受到面源污染的侵害,这就要求环境经济政策机制的设计应当基于场地的特异性[3].这一要求给面源污染的规制增加了难度,因为面源污染排放量难以进行有效观测或不能以合理的成本观测.因此,不可能将污染排放追溯到排放者个人,并运用诸如庇古税之类的最优(first-best)政策工具对面源污染进行规制.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专注于设计直接控制污染的政策工具,如经济奖励或环境标准等.然而,这需要被规制的要素投入或管理实践可以被简化为一个易于观测且与污染排放高度相关的决策选择子集[4].这一系列的限制使得这些规制工具在经济学意义上只是次优的(second-best).同时,实施这些规制政策可以为减少排放提供强有力的工具,但可能同时也会诱导非法排放污染物等问题,比如非法倾倒或焚烧,或者以一种低成本、高污染的方式不正确地使用污染性要素投入等[5].
在面源污染管控这一特殊领域,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策工具,欧盟等发达国家对面源污染的规制主要采用相关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则等管控政策.但是,学术界缺乏能够使用现有数据分析管理手段、位点特异性、水体质量之间关系的工具,而且这些政策工具没有提供经济激励,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会自愿地减少面源污染排放.因此,引入新的清洁型生产技术,实施良好的环境规则,往往无法有效解决农业面源污染问题[6]. Palmer等[7]、Walls等[8]及Fullerton等[9]学者提出了基于激励的规制工具(incentive-based instruments),在具备最优庇古税(first-best Pigouvian tax)多数特征的同时,对政策执行的监管需求可以实现最小化.这就是两部门规制工具(two-part instruments),也称为两部门规制政策,它实际上是一个政策组合,包含对污染性产品、要素征收环境税和对在产品生命周期结束时进行回收的行为或者采用清洁型技术的行为进行补贴这两个部分. Fullerton等[9]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中给出了一个最优的、封闭形式的解决方案,Walls等[8]则在一个局部均衡模型中给出了同样形式的解决方案.
两部门规制政策,可以视为对玻璃瓶或电池等可回收产品“存款—退款”形式的生产运营模式.但是,与这种所谓的“存款—退款”体系相比,两部门规制政策并不意味着税收和补贴相等,它们并不一定针对同一产品或同一主体,即这种政策工具并不定向地针对某一产品或某一个体,税收与补贴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两部门规制政策旨在避免可执行性问题,并通过对污染性产品征税的同时,对诸如购买清洁型产品或采用清洁型技术的市场交易进行补贴来实现污染管控.正如Fullerton等[5]所指出的,两部门规制政策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情境中使用.面源污染的规制就是一种典型的适用情境,但现有文献对这种方法的研究严重不足.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设计不同的两部门规制政策工具,引导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水平达到社会最优水平.同时,我们将比较这些不同的两部门规制工具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从这方面来讲,设计两部门政策工具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可以看作经济学文献中的新工具.
但是,设计农业面源污染的规制政策,必须解决几个关键的问题,克服几大困难,而这些问题和困难都是现有文献尚未很好地解决的.为了在一个更为现实的经济框架下分析两部门政策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相关问题,必须将农业生产的过程和步骤尽量细化分解,越精确越细化越好,特别是要将不同的产出和多种要素投入以及产出和投入之间的关系纳入模型之中.只有这样,才可能明确界定税收或补贴的计算基础,从而使面源污染排放者无法逃避税收或以欺诈的方式获得补贴.与Fullerton等[5]建立的模型相比,在面源污染情境下要素投入或生产技术不能简单地被划分为清洁型和污染型,而只能说要素投入的使用方式导致了更低或更高的面源污染排放.因此,技术进步没有反映在资本或要素投入中,但体现在了管理实践上.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即要素投入本身的应用不能构成两部门规制政策的一部分,尽管购买要素投入的行为形成了可观察的市场交易.为了克服管理实践中无法观测的问题,我们引入一个认证公司(accredited firm)的认证来证明要素投入是否按照良好的环境实践来使用.换言之,我们建立一个最佳管理实践(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市场,而且这些市场交易可以用于设计两部门规制政策工具.
由于采用有利于环境的要素使用方法往往都是出于自愿,我们的建议也涉及自愿协议(voluntary agreements)的相关文献.例如,Segerson等[10]将自愿政策和强制政策结合起来,诱导成本最小化的面源污染减排行为.他们的研究表明,如果税收政策在实践中可以向前追溯,税收和补贴两种政策的组合比各自单独实施更加有效.然而,正如他们所指出的,在实践中往往不会满足这一条件. Millock等[11-12]的研究也建立了一种两部门政策机制,这种机制包含一种自愿性政策(使用监控技术或者安装监控设备)和一种强制性政策(对污染排放征收排污税). Lankoski等[13]提出了一种类似的方法,但他们不主张对生产技术进行监管,而是建议由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自行申报.从这一方面讲,我们提出的方法与Millock等[11-12]和Lankoski等[13]等人的方法类似.但是,他们的方法是以监管生产技术或自行申报为前提,而我们的方法是依赖于一个认证公司保证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遵从.此外,他们的政策设计侧重于面源污染排放或要素投入使用,而我们提出的方法不仅为规制者提供了污染排放[11-12]或者主要污染要素投入[13]的规制工具选择,而且还涉及各种非污染性要素投入和产出的规制工具.本文的建议与以往文献中的方法主要区别在于,我们考虑了多种要素投入和多种产出的情况.如果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生产不止1种产品,并且使用的要素投入之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或者不同产品的产出之间存在关联,那么这一区别就显得非常重要.后一种情况可能以不同产出之间的垂直链条形式出现,或者以副产品(无论是好是坏)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提出的方法提供了额外的政策工具,包括税收、补贴、对所有投入产出返还等,并且考虑到了生产过程的扭曲问题,而如果决策者仅仅依赖于要素投入导向的模型或者忽略要素投入之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时,这些问题就不会考虑到.
本文的分析提出了一个设计经济激励机制的建议,通过使用一系列纯监管方法以实现有利于环境的生产过程.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面源污染规制机制,我们假设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同时养殖生猪、种植谷物,生猪养殖产生粪便,粪便又用作谷物种植的肥料,但粪肥的使用方式有高污染、低成本和低污染、高成本两种类型,我们称前一种为“不好的做法”(bad practice)、后一种为“好的做法”(good practice).但本文设计的这种面源污染规制机制,不仅仅适用于农业面源污染的管控,还适用于规制者无法监控有利于环境质量的生产方式或者监控成本很高的其他面源污染规制.
HTML
-
鉴于面源污染问题的区域性,以及面源污染行为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有限,我们考虑建立一个局部均衡模型.模型假设有2个:①假设存在一个社会计划管理者(环境规制者),其政策目标就是实现社会净剩余(W)最大化.社会净剩余定义为产出收入减去私人生产成本之和,再减去农业面源污染(在本文的研究中就是地表水和地下水由于农业生产使用矿物化肥和粪肥或有机肥导致的硝酸盐污染)造成的以货币衡量的福利损失. ②假设存在n个同质的完全竞争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同时种植谷物、圈养生猪.生猪圈养产生的粪便是一种副产品,可以作为肥料用于耕地增肥.为了种植谷物,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主要投入两种要素——水和氮肥.氮肥的投入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从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购买矿物化肥;另一种方式是利用生猪养殖的粪便.但生猪粪便的使用又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相对比较污染但比较便宜的形式(不好的做法);另一种是污染较少但成本较高的形式(好的做法).
-
在本文的经济分析中,我们的目标是从社会最优的角度确定最佳的技术选择.鉴于从个体最优角度和社会最优角度的结果往往不一致,我们设计了一种两部门规制政策,并比较分析了这种政策与排污税的适用性和效率差别.同时,由于两部门规制政策基于税收和补贴工具,一些相关变量属于私人信息,我们分析了面源污染个体在多大程度上遵从个体理性约束,那就是即便在税收和补贴政策的情况下,采用“好的做法”利用粪肥是否也是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最优选择.
社会净剩余(W)的数学表达式为
上式中,pc(qc)和ps(qs)分别代表谷物种植、生猪养殖需求函数的反函数.等式中的变量含义分别如下:xb为生猪粪便用于“不好的做法”时的氮质量浓度,xg为生猪粪便用于“好的做法”时的氮质量浓度,xm为矿物化肥的氮质量浓度,单位都为千克氮每公顷;xw为水的灌溉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公顷;xh为每个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开垦种植的平均耕地面积,单位为公顷.各参数的含义分别为pw,pm,ph,分别代表xw,xm,xh的市场价格;θm(xm)代表使用矿物化肥造成的每公顷氮排放量,θb(xb)代表生猪粪便用于“不好的做法”产生的每公顷氮排放量,θg(xg)代表生猪粪便用于“好的做法”产生的每公顷氮排放量.我们假设3个氮排放函数都是严格凸的,一阶、二阶导数分别满足θ′>0,θ″>0.由于θl(xl)(其中l=b,g,m)代表因xl这种形式的氮肥使用造成的剩余氮排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对所有的xl而言,都有xl>θl(xl),对不等式两边求导数可得θl′(xl)<1.由于农业生产总氮排放E造成的以货币衡量的损害函数可以表示为D≡D(E),其中D′>0.总氮排放E≡nxhe,e为每公顷耕地上矿物化肥和生猪粪便的使用造成的氮排放总量,即
由于生猪粪便与生猪产出之间具有比较固定的比例关系,所有的产出成本可以用生猪粪便而非生猪产出数量来衡量.对生猪粪便采用成本较低但污染较大的办法(不好的做法)进行处理,成本为pb(单位为元/kg);采用成本较高但污染较小的办法(好的做法)进行处理,成本为pg(单位为元/kg).这样,平均每公顷耕地年产出生猪数量
${\dot q_s} $ (头/公顷),可以与粪便产出数量关联起来,从$ {{\dot q}_s} = \frac{{{x_b} + {x_g}}}{\gamma }$ ,其中γ为1头生猪产生的粪便数量.因此,整个地区的生猪生产函数为${q_s} = n{x_h}{{\dot q}_s} $ .整个谷物生产投入使用的氮肥总量为xm+xb+xg,但投入的氮肥总量并未完全被作物利用,有一部分多余的氮肥以氮排放(面源污染)的形式向环境排出,数量为θm+θb+θg.因此,被作物实际吸收利用的氮肥数量为xf=(xm-θm)+(xb-θb)+(xg-θg).实际上,谷物生产函数
$ {{\dot q}_c}$ (吨/公顷)依赖于两个要素投入—投入使用的灌溉用水量xw和作物吸收利用的所有氮肥xf=(xm-θm)+(xb-θb)+(xg-θg). xl-θl(xl)(其中l=b,g,m)表示投入的氮肥总量减去氮排放,即代表对作物生产有效的氮肥数量.因此,每公顷耕地的谷物生产函数可以写成${{\dot q}_c} = f({x_f}, {x_w}) $ ,整个地区的谷物供给函数为${q_c} = n{x_h}{{\dot q}_c} = n{x_h}f({x_f}, {x_w}) $ .我们假设谷物生产函数对xf,xw都是严格凸的.特别说明,函数的下标表示该函数对下标表示的变量的偏导数. -
我们对表达式(1)分别求解xb,xg,xm,xw,xh的导数,可以得到社会净剩余W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2) 式和(3)式意味着[D′(·)+pcfxf](θb′-θg′)=pg-pb,(4)式-(6)式的推导使用了这一等式.一阶必要条件(2)式-(5)式表明,对一个内点解(interior solution)而言,xb,xg,xm,xw必须投入到边际社会利润(marginal social margin)等于边际社会成本(marginal social cost)的那个点上.边际社会利润对一个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而言,就是额外1单位投入要素产生的额外产出;边际社会成本就是在完全竞争市场中要素投入的价格,加上1单位额外的要素投入对环境的边际损害,要素投入的价格包括生猪粪便处理应用的成本(好的做法和不好的做法,其成本分别由(2)式和(3)式给出).清洁型要素投入xw(水的使用)对环境几乎不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等式(5)要求使用水的边际净利润与水的边际成本相等.最后,等式(6)表明耕地投入使用量(xh)的社会边际利润与其社会边际成本相等.
在第二部分,我们将在可能存在两部门规制政策的情境下,求解个体决策的最优化问题.所有的政策工具都可能诱导实现社会最优.
-
假设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选择要素投入和产出水平以实现个体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决策过程中并不考虑生产过程的外部性,即忽略谷物种植和生猪养殖对环境造成的面源污染损害,可以据此计算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正确激励的环境税水平,让他们选择要素投入和产出水平,以使个体最优的决策与社会最优的决策保持一致.假设本模型中的环境税有3种类型:①对产出征收的环境税,在本质上是一种流转税(增值税或消费税);②对要素投入征收的环境税,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流转税;③对面源污染排放行为征收的环境税,实际上是一种排污税.我们以下标表示对某种要素投入(或产出,或污染排放)征收的环境税:tqc是对谷物产出征收的环境税,tqs是对生猪养殖征收的环境税,tb是对采用“不好的做法”利用生猪粪便行为征收的环境税,tg是对采用“好的做法”利用生猪粪便行为征收的环境税,tm是对使用的矿物化肥征收的环境税,tw是对农业生产用水征收的环境税(资源税),th是对耕地使用行为征收的环境税,te是对氮排放(面源污染)征收的环境税.这些环境税既可以是正的(税收),也可以是负的(补贴),从而构成一种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两部门政策工具.
接下来本文将分别讨论5种情境下,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可行性和效率问题.第1种情形为基准情形,环境规制者可以观测污染排放情况;在第2种情形中,环境规制者对所有的要素投入行为具有完全的信息,从而可以获得社会最优的结果;第3种情形与第2种情形相似,但环境规制者只对要素投入的使用方式具有不完全的信息;在第4种情形中,污染排放行为无法观测,但可以对谷物产出和一些生产要素投入进行监控;在第5种情形中,谷物种植和生猪养殖以及一些生产要素投入行为,可以被环境规制者有效地监管.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个人的利润函数为
求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个人利润π最大化问题,分别求π对xb,xg,xm,xw,xh的偏导数,可以得到个体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一阶条件(8)式-(12)式表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通过选择投入和产出水平实现最大化利润,每一种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出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包括环境税在内).
1.1. 模型假设
1.2. 模型设定
1.3. 社会最优问题
1.4. 私人利润最大化问题
-
在这一部分,本文将分5种具体情境比较分析最优的农业面源污染规制政策机制:第1种情境为最优庇古税情形,规制者可以观测每一个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氮排放水平;第2种情境为完全信息情形,规制者可以观测要素投入及其使用方式;第3种情境为有限信息情形,规制者可以观测要素投入的数量,但无法观测投入的方式;第4种情境为规制者可以观测谷物产出和部分投入;第5种情境为规制者能够观测谷物和生猪2种产出及部分投入.其中第1种情境是基准分析框架,用于与其他4种情境下的最优规制政策做比较.
-
我们仍然假设,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选择xb,xg,xm,xw,xh等要素投入以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但是环境规制者可以对面源污染排放进行观测.在这种情境下如果我们假设tb=tg=tm=0,并对其余的环境税做出(13)式-(17)式的限制,一阶条件(8)式-(12)式会导致(2)式-(6)式定义的社会最优结果.
从(13)式和(14)式可以得到
这与等式(15)一起可以推出te=D′(·).因此,剩下的几种环境税tqc,tqs,tw,th可以分别表示为
(18) 式-(22)式表明,在最优状态下te=D′(·),也就是对面源污染排放征收的庇古税te与边际环境损害相等.如果这一条件成立,(13)式-(21)式表明,没有必要对产出、投入或者生猪粪便的利用行为(好的做法和不好的做法)征税,以达到社会最优状态.也就是说,在规制者可以监测每一个生产经营主体面源污染排放水平的庇古税情境下,排污税是有效的环境税形式,投入税、产出税形式的环境税,其最优税率为零,即
即便面源污染的特征使得环境规制者很难对污染排放行为进行监管,本文仍然对规制者可以监管污染排放行为的情形进行了分析,并将其作为基准与其他情形做比较,特别是规制者必须寻找其他的税收/补贴机制的组合政策,从而实现最优的(first-best)结果.
-
在这种情境下,规制者不必具有观测污染排放和产出选择的能力,即tqc=tqs=te=0.但是,规制者必须能够监测所有投入(xb,xg,xm,xw,xh)的数量及其类型(污染型或清洁型).这样,可以将所有要素投入之间的替代过程纳入模型分析.因此,使用两部门规制政策会产生最优(first best)结果而非次优(second best)结果.在这种情形下,以下的税收/补贴政策组合可以实现社会最优.
将以上这些规制工具放在(8)式-(12)式中,发现这些等式可以推导出等式(2)-等式(6)表示的社会最优状态.因此,由等式(22)-等式(26)定义的两部门规制政策可以实现社会最优.等式(22)-等式(25)表明,3种环境税是严格为正的,一种为零.相反,(26)式中对耕地使用征收的环境税,其符号不能直接判定.由于函数θl,l=b,g,m在区间[0,xl*]上是严格凸的,并且θl(0)=0,我们可以得到θl′xl*>θl′(xl*).由于D′(·)>0,对耕地使用征收的环境税为负,即
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对耕地使用征收的环境税是一种环境税式支出,即一种补贴.如果污染排放函数是线性的,并且严格凹的,我们可以得到θl′xl*≤θl(xl*),l=b,g,m.因此,在污染排放函数为线性的严格凹函数情况下,对耕地使用行为征收的环境税可以为零,也可以为正.换言之,在这种情形下对耕地使用征收环境税,而不是对其进行补贴.耕地使用环境税为负(实际上是一种补贴),其隐含的逻辑在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每公顷的税收负担为D′(·)θl′xl*,l=b,g,m.但是就耕地使用而言,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税收负担应该为环境损害与污染排放Dθl′(l=b,g,m)相乘.由于污染排放函数是严格凸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单位耕地实际税收支出与正确的税收支出之间的差为正,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付出了太多.因此,耕地使用的环境税实际上成为一种税式支出或补贴,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付出的太多代价给予补偿.
-
在有限的信息条件下,规制者可以观测所有要素投入的数量却不能观测要素投入的使用方式,因为要素投入如何使用属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私人信息,这会导致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与规制者之间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现有的很多文献考虑了逆向选择问题并建立规制面源水体污染的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有关农业生产类型(或产出)的信息是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私人信息.这些模型假设要素投入或者产出[14]是可以观测的,而面源污染排放水平则是无法观测到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类型和产出(或投入)变量的函数.情境3分析的情形与以往的文献明显不同,因为我们假设面源污染排放不仅仅取决于要素投入的数量,还取决于要素投入使用的方式.此外,Innes等[15]建立了一个关于面源污染规制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面源污染者可以通过报告高排放水平以换取更低的环境税.但是,这种机制比较苛刻,要求规制者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调查等方式确定面源污染排放水平.然而,一旦粪便被使用,规制者无法推定其使用的方式,因而这一方法在情境3中不具有可行性.
由于对用不好的做法使用粪便行为征收的环境税,明显高于对用好的做法使用粪便征收的环境税,即tb>tg,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有激励向规制者报告用好的做法处理粪便,即便这根本就不是事实.同样,由于规制者无法有效观测粪便利用处理的方式,就无法根据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农艺措施而征收不同的环境税.为了克服这种逆向选择问题,规制者可能按照较高的环境税标准tb对所有的粪便利用处理行为征收环境税,而不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是采用“好的”还是“不好的”农艺措施.为了获得关于使用粪便方式相关的信息,规制者可以创建一个认证主体(figure of an accredited verifier),证明粪便是按照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措施使用处理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自主决定是否与这个认证主体签约合作.这类认证主体,既可以是代表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进行粪便化肥利用处理的公司,也可以是业务仅限于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认证其粪便化肥利用处理属于低污染、高成本方式(好的做法)的服务主体.在后一种情形下,认证者实际上是监控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采用好的做法利用处理粪便化肥,有利于维护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自身的利益,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形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才可能得到政府的补贴或返还.为了简化说明,假设认证者在2种情形下的成本都以pv来表示,这一成本反映了认证者委托服务的成本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自行使用处理粪便肥料成本之间的差异.只要使用了粪便肥料,认证者就向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放一个证明,证明按照正确的方法(好的做法)使用处理的粪便肥料数量.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向规制者(政府)出示这一证明,并按照每单位数量(千克)tb-tg的标准,获得正确使用处理生猪粪便的补贴.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获得的补贴(返还)等于采取正确的方法(好的做法)利用处理生猪粪便而导致的边际环境损害的降低tb-tg=D′(·)(θb′-θg′)>0.
当不存在不对称信息时,等式(22)-等式(26)以及tqc=tqs=te=0所定义的税收/补贴机制实现了社会最优配置.因此,诱导私人信息的额外成本由pv给出,这些成本不是由规制者承担,而是由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担.如果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获得的补贴tb-tg能够覆盖掉这部分额外成本pv,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就可能采用认证者提供的认证服务.同时,由等式(22)-等式(26)定义的其他两部门规制政策工具,可以确保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产生社会最优的粪便,从而实现生猪养殖水平的最优化.因此,在两部门规制政策下,采用好的做法利用处理粪便肥料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其净利润水平高于采用不好的做法利用处理粪便肥料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这种限制正如有关不对称信息的文献所界定的那样,可以被认为是个人理性的约束.存在这种个人理性的约束,是两部门规制机制显著区别于税收、补贴或可交易排污许可等传统经济激励机制的标志.个人理性约束的出现是因为采用好的做法利用处理生猪粪便完全是自愿的行为,而因为边际环境损害减少获得的补贴或返还,需要覆盖支付给认证者的认证成本.
如果采用好的做法处理生猪粪便带来的社会净剩余(W)增加,无法覆盖认证者的认证成本,实施两部门规制政策或引入认证者的机制,从社会的角度而言就不是最优选择.当边际环境损害减少幅度较小,或者认证者的认证成本较高,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时,就会出现上述情形.
但是,也可以放松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同质性的假设,考虑异质性的问题.我们将n个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分为k组(k为自然数,且1≤k≤n),属于同一组j=1,…,k的
$ {n_j} = \frac{n}{k}$ 个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具有同质性,即他们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fj(·),相同的面源污染排放函数θlj(·),l=b,g,m,相同的产出水平和相同的生猪粪便使用处理成本pbi,pgj.第j组的每个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可选择的变量分别为xbj,xgj,xmj,xwj,xhj.从而,社会最优决策问题为我们仍然沿用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利润函数的概念,采用与前述推导相同的方法,可以求得社会最优和个人最优的一阶条件.比较这些一阶条件,可以求得针对每一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环境税tjqc,tjqs,tbj,tgj,tmj,twj,thj以使这些主体的行为和决策符合社会最优的要求.这些环境税将对情境2作出反馈.然而,求解最优环境税要求环境规制者知道每一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面临的生产函数、面源污染(氮)排放函数和生猪养殖产出函数以及生猪粪便使用处理方式等信息.假设环境规制者知道每一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污染排放函数,但不知道其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在这种情形下环境规制者如果知道每一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生产函数和成本分布,那么可以实施一个排污许可交易机制,允许生猪粪便采用低污染、高成本方式(好的做法)产生的氮排放许可证在专业市场上进行交易转让.更具体地讲,规制者知道生产函数fj(·),pbj,pgj,nj的值和每组生产经营主体占比等信息,同时规制者已经为生猪粪便的低污染、高成本使用处理建立了一套认证制度体系.在这种框架下,规制者可以计算整个群体所有要素投入的最佳配置方式,但无法计算单个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要素配置的最佳方式.因此,规制者能够决定整个群体采用好的做法和不好的做法使用处理粪便肥料造成的面源污染排放的最优水平,两种粪便使用方式下的最优排放分别为Eb*,Eg*. Eb*的大小可以通过向所有组使用粪便肥料的行为征收与平均边际环境损害相等的环境税tb*来实现;Eg*的大小可以通过为采用不好的做法使用粪便肥料的行为建立一个排污许可交易制度而得到.排污许可交易必须通过对每一组污染排放函数的差异进行加权平均,即如果第1组的生产经营主体采用好的做法使用1千克粪便肥料导致的氮排放是第2组的2倍,那么给定相同的粪便化肥,第1组的每个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得到的污染排放许可量应当是第2组的2倍.排污许可的交易价格由交易市场决定,并且参与交易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获得了单位数量为tb*的补贴.情境3的分析,一开始就给出了个体异质性条件下这种规制机制的各种条件.
-
考虑规制者可以观测谷物生产和部分而非所有要素投入的情形,即tqs=tm=te=0.对矿物化肥不征收环境税,其背后的激励机制在于,尽管我们的模型假设存在n个同质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但在本区域以外的其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可能具有不同的生产函数,这就意味着应当对矿物化肥的购买行为征收不同税率的环境税.但是,由于不同地区的税收不同给矿物化肥的黑市交易提供了激励,这会破坏农业面源污染规制政策,因此分割矿物肥料市场是不可取的.同样,由于化肥的运输成本相对较高,出现化肥黑市的可能性不大,可以对采用好的(不好的)做法使用粪便肥料的主体,进行补贴(或实施征税),并且这种两部门规制政策会比较有效.因此,监管机构可以对玉米产出、水、耕地的使用以及生猪粪便不好的使用处理行为征收环境税.将(8)式-(12)式与(2)式-(6)式以及tqs=tm=te=0联立方程组,可以求得同时实现社会最优和个体最优的一阶条件为
结果表明,对水的最优环境税tw为负,而对谷物生产的最优环境税tqc为正.对于生猪粪便使用行为的环境税与情境3相同,对采用好的做法使用粪便的行为实施补贴,补贴数量为单位粪便tb-tg.如果谷物生产不使用矿物化肥而只依赖于粪便要素投入(θm=0,θm′=0),对于耕地使用征收的环境税就是严格为负的,即对耕地使用行为实行补贴政策.考虑面源污染排放函数为凹(convex)函数,由等式(33)可得
这一系列的计算过程表明对谷物产出征税,而对低污染要素投入或使用方式进行补贴.但是,如果没有特定的假设,等式(33)的符号无法确定,因此需要用实证分析来弥补理论推导的不足.
-
我们分析规制者不仅能够观测生猪养殖和谷物种植,而且能够观测水和生猪粪便投入(包括好的做法和不好的做法)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下tm=th=te=0.把对生猪养殖和谷物种植以及水和生猪粪便投入的环境税带入等式(8)-等式(12),会发现对生猪养殖征收的环境税tqs在等式中消失.为了将等式(8)和等式(9)中的tb和tg分开,我们将等式(12)中的相关变量替换掉,这样tqs会在一阶条件的表达式中消失,这是由于生猪生产函数和排污税在数学上具有线性特征.因此,我们无法通过一阶条件来决定对生猪产出的环境税.对于tqs的不确定性,无论是试图求解tqs和tqc,还是单独求解tqs都无关紧要.但是,我们可以实证分析对生猪产出的环境税,因为对最优化问题的数学求解并不是基于一阶条件的.
除了以上5种情境,还可以根据信息情况设置更多的情境,并进行比较分析.但是,为了简明起见,我们没有分析更多的情境,上述5种情境代表了主要的实际经济运行状况.通常而言,两部门规制政策具体选用什么规制工具,或者通过将其值设定为零而不选用某种工具,主要取决于监测相关数据的条件和能力.但是,由于规制者决定了5个变量的最优值,从而给出了5个一阶条件,不可能将8种可供选择的规制工具(实际上就是对8个变量的税收或补贴)都纳入分析,而最多可以将5种规制工具纳入模型分析.换言之,必须有3种规制工具被设置为零,以保证社会最优解唯一.在规制者无法有效观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是否采用好的做法利用处理生猪粪便的情形下,规制者可以通过创建一个认证者来解决不对称信息问题.
2.1. 情境1:规制者可以观测每一个生产经营主体的氮排放水平(最优庇古税)
2.2. 情境2:规制者可以观测要素投入及其使用方式(完全信息)
2.3. 情境3:规制者可以观测要素投入的数量但无法观测投入的方式(有限的信息)
2.4. 情境4:规制者可以观测谷物产出和部门投入
2.5. 情境5:规制者能够观测谷物和生猪2种产出及部分投入
-
由于面源污染无法追溯至特定的污染排放者,向农业生产中的氮排放征收一个最优的(first-best)环境税,对环境政策制定者而言不具有可行性.另一方面,可以设计一种由纯环境规制工具组合而成的两部门政策,把对可观测要素投入和产出水平征收环境税或进行补贴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调整自身的决策和行为,并最终实现社会最优的面源污染排放水平.这些自愿但基于经济激励的政策工具,在实现对行为监管和政策执行需求最小化的同时,具备最优的(first-best)庇古税的绝大多数特征.我们的研究旨在丰富有关面源污染领域两部门环境规制机制设计和实施的理论文献,特别是探讨两部门规制政策在解决农业面源污染管控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潜在可能.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氮排放等不仅受污染性要素投入数量的影响,还受这些要素投入使用方式的影响.由于监管机构无法区分要素投入的使用属于好的做法还是不好的做法,我们引入了一个认证者,以克服相关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就要求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就生猪养殖产生的所有粪便,按照污染高、成本低(不好的做法)的使用方式缴纳较高的环境税tb.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只有在获得认证者的证明,说明其产生的粪便数量和使用粪便的方式属于好的做法时,才能根据用于好的做法的粪便数量获得政府补贴.
本文的研究发现,实现社会最优的方法很多,至少包括2种两部门规制政策:①对污染性要素投入征税,对耕地使用补贴的政策组合;②对产出和采用不好的做法使用粪便肥料的行为征税,而对非污染性要素投入和采用好的做法使用粪便肥料的行为补贴的政策组合.同时,本文的研究也说明了可以如何利用经济激励设计面源污染规制政策,以提高对面源污染问题最佳管理实践(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的接受度.
本文的研究至少具有3个方面的政策启示:①在点源污染规制领域普遍采用的环境税工具,可以在农业面源污染规制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这有赖于环境税政策机制的科学设计,更具体地讲,需要将环境税与补贴等其他政策工具配合使用. ②基于环境税的两部门机制在农业面源污染的规制方面,需要充分考虑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行为征税的政治可接受性,对传统的家庭式农户征税可能有悖于社会公平正义,但对规模化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征税则具有可行性.因此,征税对象有2种方式:一是对所有农业面源污染排放者普遍征收,但对污染损害较小的单个农户实行减免税政策;二是对单个农户不征税,而只对规模化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征税. ③基于环境税的两部门规制政策工具在农业面源污染领域的应用,需要“三农”领域的持续深化改革加以配合,比如,在新型农业生产服务主体的培育方面,需要考虑支持农业技术认证主体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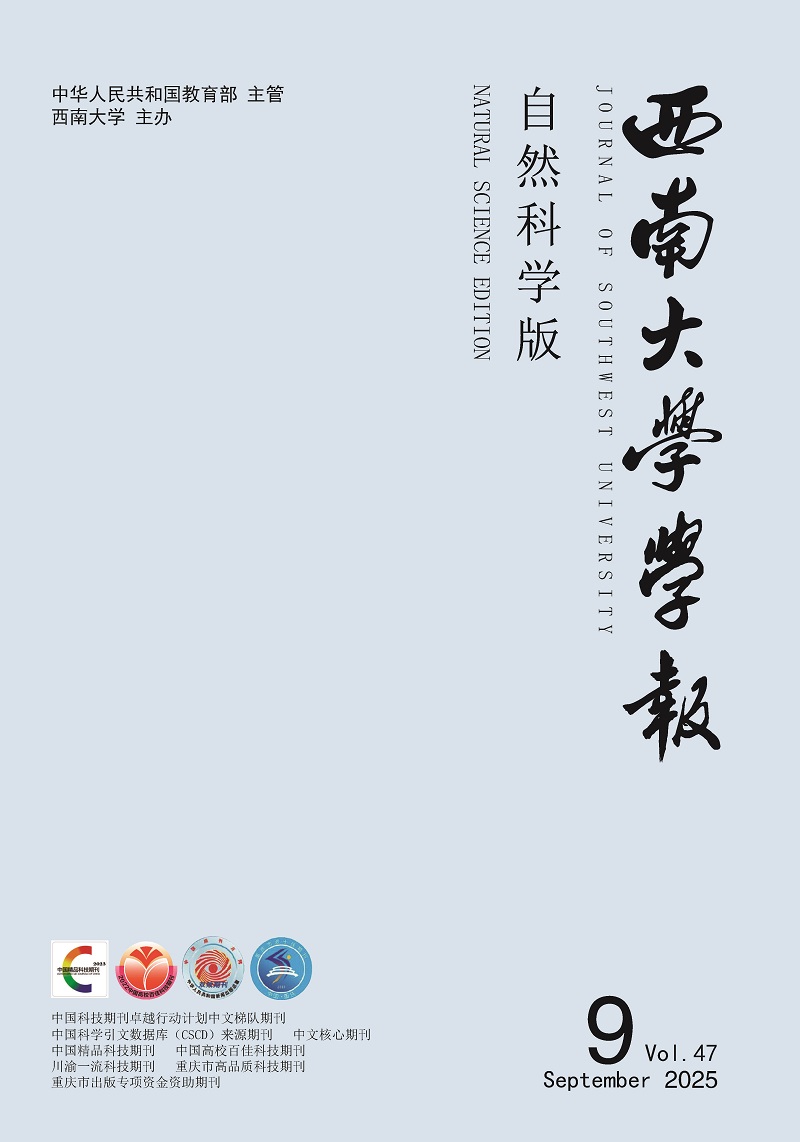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