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广义上的蜀道是中国古代秦、陇、鄂、藏等地通往四川盆地交通道路的总称,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通道,积淀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传统意义上的蜀道则以秦蜀古道为主,指由关中平原翻越秦岭、经过汉中盆地再穿越大巴山通往成都平原的道路,其中北有穿越秦岭的褒斜、故道(陈仓)、傥骆、子午四道,南有大巴山中的米仓道、金牛剑阁道及荔枝道三道(即所谓“北四南三”)。另有由陇南文县翻越摩天岭入蜀的陇蜀阴平道,因三国末邓艾奇袭蜀汉得势而在历史上名噪一时,历史上虽使用相对稀少,但也属于蜀道的重要支线①。此外,鄂蜀峡江古道、川滇与川黔盐运古道、川藏茶马古道等也属于广义蜀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蜀道(秦蜀古道)在中国古代长期承担着沟通国家政治中心长安与西南大都会城市成都的交通干道功能,同时也是以成都为辐射中心的西部交通网络。蜀道在中国古代是沟通中原与西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不仅在中国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我国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线性文化遗产(lineal serial cultural heritage)之一,在今天更被看作是连接陆上丝绸之路与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同时蜀道沿线穿越秦岭、大巴山两大山系,生态景观资源与文化观赏资源丰富,也是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富集地带。文献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同样也是蜀道研究的前提。但多年来的蜀道研究中,虽然学者常常引用相关蜀道文献,但对蜀道文献本体的研究却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
① 古代阴平道起于阴平,即今甘肃文县的鸪衣坝,经文县县城翻越四川青川县境的摩天岭,经唐家河、阴平山、马转关、靖军山,到达四川平武县的江油关(今南坝乡),全长265公里。
HTML
-
虽然“蜀道文献”是近年才提出的概念,但学术界对蜀道文献的研究早已有之。蜀道文献早在商周之际已经出现,据王国维研究,周初金文青铜器《散氏盘》中提及的“周道”即后来蜀道重要干线之一“故道”的前身。此后《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正史文献已对秦蜀交通多有记载,汉魏两晋时期,在扬雄《蜀王本纪》、谯周《三巴记》、皇甫谧《帝王世纪》、左思《蜀都赋》、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及南朝乐府诗中的蜀道记载渐趋丰富。唐宋诗歌中有大量诗人旅蜀往还留下的蜀道诗、蜀道赋与散文在这一时期也有一定数量,如柳宗元《兴州江运记》、欧阳詹《栈道铭》、孙樵《书褒城驿壁》《兴元新路记》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蜀道文献。元代以降,蜀道旅游兴盛,文人学士留下更加完整的蜀道游记,如明代张瀚《松窗梦语·西游记》、清代王士祯《蜀道驿程记》《秦蜀驿程后记》、张邦伸《云栈纪程》、陶澍履栈行纪《蜀輶日记》等,都是著名的蜀道游记。至于秦汉以来古人在蜀道上镌刻的诸如陕西汉中褒斜道石门石刻、兴州(略阳)灵岩寺石刻、四川巴中南龛石刻、甘肃成县《西狭颂》石刻、徽县北宋“新修白水路”石刻等,都是蜀道石刻文献的代表。随着蜀道研究的渐趋繁荣,作为蜀道研究基础的蜀道文献近年来也受到一定的重视,研究的热点是唐宋明清蜀道纪行游记文献,如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清代王士祯《蜀道驿程记》《秦蜀驿程后记》《陇蜀余闻》、张邦伸《云栈纪程》、张素含《蜀程纪略》、陶澍《蜀輶日记》、陈奕禧《益州于役志》等。一些高校地方文化研究机构也开始重视蜀道游文献,如西华大学四川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中心立项有“明清蜀道游记研究”资助项目。在蜀道文献整理方面,李勇先、高志刚等主编的《巴蜀珍稀旅游文献汇刊》[1]、《日本藏巴蜀珍稀文献汇刊》[2]是两部大型的蜀地文献汇编丛书,以影印形式收录了多部古代到近代四川游记,其中就涉及不少蜀道行旅的文献。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蓝勇等主持汇编的重庆市重大社科项目《稀见重庆地方文献资料汇点》(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稀见重庆地方文献汇点》(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历史文献中的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也对多部重庆地方珍稀单行本文献作了收录、点校,其中有不少涉及蜀道南段文献。刘庆柱、王子今主编的《中国蜀道》[3]为大型集成式蜀道综合研究丛书,其中第六卷《艺文撷英》集中选录了自汉代至民国多部篇(部)蜀道诗赋、行记、石刻,包括部分珍贵的古代蜀道绘画、地图。《中国蜀道》大型丛书旨在总结历代有关蜀道的开通和使用,并从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考察角度,多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对蜀道及其研究进行了梳理与分类,是一部集大成式的蜀道研究大型丛书,从交通线路、历史沿革、人文地理、文化遗存、建筑艺术、艺文撷英、科学认知等方面分别对蜀道的历史载体和文化影响进行考察和说明,以求准确、全面地认识蜀道,也多处涉及对蜀道主要文献的简要评介。
蜀道石刻文献方面,目前整理出版质量较好的是汉中博物馆前馆长郭荣章主编的由三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石门石刻大全》。此书编者多年来研究汉中地方史及褒斜道摩崖石刻,为编著该书不顾年老体迈,多次深入秦岭深山峡谷攀援拓印录文,对现存褒斜道东汉至晚清的石刻文字作了尽可能齐全的收录和校注,为保存蜀道褒斜道段石刻文献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关于该书的学术价值,冯岁平发表有书评,认为《石门石刻大全》“既有对石门石刻的综括论述,如石门石刻的总数、分布、成因、评价等,又有对包括‘石门汉魏十三品’在内的每种石刻位置、形制、文字、作者、内容、价值和保护现状等的探索;既有对石门石刻真伪、损害与保护的探讨,又有对石门摩崖石刻、碑碣的系统研究”,而且是书实地考察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对前人有关褒谷石刻之遗漏多有补充纠误,“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严肃的学术著作。对石门石刻的整理与研究,此书亦利在当代,功在后世”[4]。冯岁平也是对蜀道石刻文献投入研究较早的学者,早在1998年即发表《关于〈郙阁颂〉文献的研究》[5],对东汉名刻《郙阁颂》的音韵学、文献学价值、研究学术史及其研究得失作了述评;其《〈石门颂〉鉴定三题》[6]对东汉褒斜道石门另一重要石刻《石门颂》则从镌刻技术手法、书法文字风格、历代拓印及其拓本评价方面作了论述。
随着蜀道研究的深入,也有一些学者致力于蜀道文献研究现状的关注,冯岁平《连云栈行纪文献展现蜀道变迁》[7]通过访谈形式概括了清代行纪类文献现存数量和种类,其特征是该书主要以诗文合璧的形式记述蜀道的发展与演变,认为清人蜀道纪行内容丰富,是研究蜀道的重要依据,也指出目前对蜀道资料研究尚较薄弱。《蜀道驿程记》系清代康熙时王士祯典试四川时,由京入蜀,记其沿途所见之作。在陕西、四川段记程中,真实记录了清初蜀道沿线的山川地貌、风俗民情、城镇乡村,史料价值甚高,向来受到历史地理学者看重。但有关《蜀道驿程记》的专门研究文章不多,仅有刘艳伟《〈蜀道驿程记〉的史料价值》、高宇《王士祯入蜀游记交通地理研究》[8-9]等寥寥数篇,对《蜀道驿程记》及其《秦蜀驿程后记》的交通史及历史地理学价值进行了简要探析,理论探讨层次较浅,发表的刊物也大多是地方高校学报,影响较小。对张素含《蜀程纪略》,近年也有学者给予关注,称之为“中国纪游文学史的典范之作”,见孙天胜《中国纪游文学史上的杰作—张素含〈蜀程纪略〉》[10],但也仅限于此篇。历代蜀道图画也是蜀道文献的一种特殊形式,唐宋以来出现一些以蜀道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如唐李昭道(一说李思训)《明皇幸蜀图》近年来引起了学者的重视,但多从绘画理论予以探讨。北京大学李孝聪近年着力于域外中国历史地图的研究,2004年他对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清代无名氏绘《陕境蜀道图》作了初步研究,与毕琼合作发表《〈陕境蜀道图〉研究》[11]。后来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中考证,该图应绘于乾隆十六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751-1820)前后,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冯岁平接连发表《美国国会图书馆藏〈陕境蜀道图〉再探》[12]《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汉江以北四省边舆图〉述考》[13],对《陕境蜀道图》进行了更加细化的研究。总体而言,目前对蜀道文献的整理仅仅集中在少数行纪名著方面,对蜀道文献的全面整理与研究尚未全面展开。
-
蜀道文献作为一种特定的线性文化地域历史文献,大致可划分为史志典章类文献、行旅游记类文献、诗歌题咏类文献和石刻碑碣类文献四大类别。目前对蜀道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又基本上可概括为文献整理出版与文献学术研究两个方面。蜀道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已经有一定进展,如前所述,时下蜀道文献的整理基本以影印出版古籍为主,兼及少量蜀道重要人物的文集点校出版。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一门专门学问,涉及诸多学科理论、知识及其规范,也有其本身的特殊性,如文献作者生平背景与著作编年,版本流传中的珍本和善本的刊刻、流传与讹误,文献作者的考证及其文献所涉史事、人物的考证,辑佚、校勘、证伪、避讳等,还包括整理者自身古代汉语及其文献学、版本目录学等知识素养等,都是文献整理不容忽视的问题。目前的蜀道文献整理与研究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组织协作,呈现各自为政的状态。虽然一些地方高校和地方政府成立了蜀道研究机构,如陕西理工大学成立有“秦岭蜀道文化研究所”,西华师范大学设立有“蜀道研究院”,四川省四川西部经济文化发展研究院设有“蜀道文化研究所”,西南大学新近成立有“蜀道文献研究中心”,但真正从事蜀道研究的专职人员仍然很少,蜀道文献研究基本上属于自发性与各自为政,而且重量级成果很少,像郭荣章这样数十年沉潜其中的蜀道文献学者寥若晨星。对蜀道文献的整理一般是地方学者根据本地资源整理相关乡土人物著述,如对蜀道重要人物王士祯(渔洋)及其著作的整理与研究基本上是山东学者在研究,对另一蜀道重要人物张问陶(船山)诗文的整理也主要是四川遂宁本土学者在不懈努力,而且他们整理的出发点并不以蜀道为重点。对历史上的陕籍蜀道人物及其文献,主要是汉中、宝鸡及其个别外地学者研究。这种划地为域的做法虽然可以结合本土资源出一些地方化的研究成果,但也难免造成视野狭窄、零敲碎打和重复式的整理出版。
二是蜀道文献整理基本上皆参照四川大学《儒藏》《蜀藏》丛书形式,以捆绑式影印结集出版为主。如《巴蜀珍稀旅游文献汇刊》[1]、《日本藏巴蜀珍稀文献汇刊》[2]、《蜀道行纪类编》[14]都是影印出版。这样做固然可使一些珍贵文献版本借用现代影印出版技术得以“接力式”保存而避免失传,有较省时省力,出版成本相对较小,出版周期短暂的优点,使一批学者不易寓目的珍贵蜀道文献得以“原始面貌”出版发行。但因对文献本身并没有校勘、标点,古籍中的一些错误与缺漏往往得不到纠正和弥补,社会影响不大,也不利于读者阅读,一定程度上降低蜀道文献的利用价值,而且在文献内容方面存在重复编印、出版,容易造成读者购买、选择上的误导与困惑。
三是目前出版的一些蜀道文献由于整理者的学历知识背景及其个人能力的差异,也显得整理成果良莠不齐,特别是有关诗文集校注存在问题不少,对蜀道诗文有关地名、掌故、人物、事件的考证方面存在一定讹误,因缺少正常的学术批评而长期得不到纠正。如清代乾隆年间著名诗人张问陶(船山)诗集中有大量的蜀道(栈道)诗歌,但现代学人对其栈道诗的注释却不尽人意,甚至多有错误。以近年点校、注释出版的《船山诗草全注》[15]对清代张问陶褒斜道段行旅诗注为例,粗一翻阅,即可发现其中有不少注释错误百出,如船山《望栈道作》诗有“返照明汧渭,苍苍见益门”,注曰:“益门,古镇名,在陕南。”[15]166我们知道这里的“益门”当指明清时期宝鸡的益门镇,在今陕西宝鸡西南8公里,地当由秦入蜀之咽喉,清代诗人王渔洋、张问陶、张素含、林则徐皆曾路过此地,并留有诗篇,并非在秦岭以南的陕南。这显然是一个常识性错误。更有甚者,作者还杜撰出一个“益门城县”。如对船山《益门镇石上小憩》,则解释为“益门镇,即今宝鸡益门乡,古为益门城县。县有益门山,山有益门关,关为进四川必经之地”[15]167。自古以来各种舆地志书上从未有过“益门城县”的记载,且明清时期的宝鸡也只是一个县级建置,怎么会冒出来一个“益门城县”?显然,这与作者不了解宝鸡地区政区沿革与缺乏严谨检索文献的态度有关,因而无中生有地杜撰出来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益门城县”。实际上船山诗所提及的“益门镇”在清雍正《陕西通志》中有明确记载,该书卷三引《益门镇志》说:“陕西既入关,平衍千余里,西南抵宝鸡,复岸然山合,唯一隘口始入,是为益门镇。秦山嵯峨,清江滉漾,路唯鸟道。出镇南云栈百折,达荆梁,通滇益。名镇以益,义取诸此。”《船山诗草全注》对《宝鸡》一诗中“山入回中乱,天临剑外低”中“剑外”的注释也有问题,注者将“剑外”注释成“剑门关外,又称剑南,指四川成都”,恰好使“剑外”地理空间南辕北辙。按“剑外”当典出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句,实指四川以外,怎么可能是“指四川成都”?此外,该书《武关驿》诗注武关驿“在陕西商南县西北”[15]182,而实际上武关驿在今陕西汉中市留坝县南;将“七盘岭”注为“阳平关南,四川广元北”[15]184,实际上张问陶诗中的“七盘岭”位于今汉中市汉台区河东店镇连城山,系古褒斜道南出秦岭的褒谷口,唐代诗人沈佺期《夜宿七盘岭》诗有“浮客空留听,褒城闻曙鸡”之句即为一证,类似错误不一而足。实际上这些褒斜道上常见的地名错误只要查阅相关的地名辞典类工具书即可避免,若再辅之以一定的地理考察就会注释得更加准确、具体,也有助于加深对原诗文的理解。张问陶是清代中后期与袁枚齐名的著名诗人,享有“蜀中第一诗家”的美誉,但今人《船山诗草全注》却出现数量惊人的常识性错误,让人颇为遗憾,也发人深思。
四是目前蜀道文献的研究过多集中在已经为学界所熟悉的《蜀道驿程记》《蜀程纪略》、张邦伸《云栈纪程》和《栈云峡雨日记》等少数几部蜀道行旅文献层面,重复性研究较多,开拓性探讨稀少;文献出版也多以影印复制为主,点校本文献整理较少,不利于读者阅读和社会使用。仅就蜀道行旅文献而言,除了上述几部学人耳熟能详的名著外,尚有陶澍《蜀輶日记》、张香海《宦蜀纪程》、文祥《蜀轺纪程》、陈涛《入蜀日记》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的大量蜀道文献有待整理。清代入藏大臣途经陕南、四川的日记也有不少涉及蜀道记载,如清果亲王爱新觉罗·允礼《西藏日记》(又名《西藏往返日记》)就有不少途经秦巴山地驿道间的纪事与诗作,学人知之者少。鸦片战争以后,大批西方外交官、商人、学者等来华,有不少深入中国西部蜀道沿线的外国旅行者,也留下了一批西方人蜀道游记。除了前揭日人竹添井井《栈云峡雨日记》,还有不少包括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人所写蜀道日记,这批蜀道游记系以异域人“他者”(other)角度撰写,广泛记载晚清蜀道沿线陕西、四川的社会、民俗、乡村、城镇、经济等情况,对晚清民国蜀道沿线种植和吸食鸦片、青楼妓女、聚众赌博等基层社会负面文化现象时有揭露与批判,有重要的历史社会认识价值。目前域外人士的蜀道行纪文献,除了对日人竹添井井《栈云峡雨日记》、中野孤山《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山川早水《巴蜀》有翻译、出版外,大部分西方人的蜀道游记尚未翻译引进,如日本学者、书法家牛丸好一《汉中石门摩崖石刻研究》至今尚无中译本。这在今后需要加以特别关注,应该有计划地对海外蜀道文献进行翻译、校勘、出版。
-
走向自觉与兴盛的蜀道研究已有三十年了。从零星自发到渐趋繁盛,从鲜有问津到备受关注,蜀道研究出现诸多令人欣喜的态势,所出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汉中、重庆、成都的学者在这方面贡献尤多。但也毋庸讳言,有关蜀道文献本身的研究却始终是一个弱项,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蜀道研究的纵深发展。文献整理与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与前提,从这一角度而言,蜀道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可谓任重道远,可做的事情还很多。以笔者之管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整理与研究。
-
蜀道文献的整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就文献整理的种类而言,绝非几部履栈纪行游记所能涵盖,搜集、整理视野不能过于狭窄。虽然“蜀道文献”是近年来才提出的学术概念,但文献本身的起源与发展却源远流长,虽相当零散却又十分丰富,只是历史上从未有过专门的分类整理。从广义上讲,蜀道文献整理与研究应该包括对史志典章中的蜀道资料、历代诗歌中的蜀道资料、各类碑刻地志中的蜀道资料、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及近代以来西方人经行蜀道的行旅资料,包括宗教(道教、佛教)经典中的蜀道资料等的全面搜集、整理。通过团队协作,对蜀道这条我国重要的线性文化遗产提供丰富的历史论证和科学研究可信度较高的文献资料,并通过对蜀道文献的搜集、分类、点校、整理和出版,将珍贵的蜀道文献长期保存。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将蜀道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也充分说明该项工作已经得到国家最高社会科学管理层面的重视。这个项目的完成,将是我国现存19条线性文化遗产中第一个大型线性文献资料汇编与研究重大成果。待纸质文献的整理告一段落,条件成熟时,还可组织相关科技力量,利用现代数字信息技术制作蜀道线性文献资料全息数据库,使得蜀道文献得以永久性保存,同时也是对目前川、陕、甘三省全力推进的争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蜀道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蜀道申遗”工程最有力的学术支撑。
-
蜀道文献丛书以行纪文献为主,但也不排除对各种类书中蜀道纪事、诗文的辑佚、汇集。其中与蜀道关系最为重大的历史人物别集可以考虑重新全部校点、注释和出版。蜀道行纪文献的出版应不同于以往影印复制、捆绑式出版模式,而是以选择善本为基础,加以校勘、标点、注释,以更加方便于读者,服务于社会。目前比较成熟可行的方案是采取集体攻关、协调合作、联合作战的方式,推进“历代蜀道史志文献汇辑”“历代蜀道诗赋文献汇编”“历代蜀道石刻文献汇释”“中外蜀道行纪文献汇编”的整理出版。
-
蜀道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交通要道,无论是雄奇的自然风光,还是丰富的名胜古迹,以及蜀道沿线神秘的山地社会,都对旅游者有强烈的吸引力,也早已引起国际旅行家与学人的关注。早在元朝初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即有蜀道之旅,其《马可·波罗游记》中就有其途经秦岭、大巴山褒斜道的生动回忆[16]第111章至113章。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日本僧人雪村友梅曾来中国求法,有入蜀行纪诗,遗著有《岷峨集》存世。明末清初,西方基督教开始传入中国西南地区,一些著名的传教士行旅蜀道,也有不少考察著述。如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方德望(Etiene Le Fevre,1598-1659)在陕南城固、洋县、汉中府一带长期布教,其口述资料中就有秦岭、巴山古栈道交通状况,见1696年巴黎出版的法国传教士李明所著《中国近况新回忆录》[17]。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大开,西学之潮强劲东渐,西方来华人士剧增,域外人士的蜀道行旅也达到高潮,其中不乏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西人蜀道考察、游记文献。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来华考察,于1871年至1872年完成从西安至成都的中国西南之旅,其学生蒂芬(E.Tiessen)编著的《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就对秦蜀栈道沿线的交通、民生、贸易、地质构造、生态环境有真实详细的记录[18]。清末民初,则有大量日本人到巴蜀地区旅游考察,撰写有不少蜀道游记,如竹添井井《栈云峡雨日记》、安东不二雄《中国漫游实记》、山川早水《巴蜀》、中野孤山《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上冢司《以扬子江为中心》、高山庆一《长江漫游日记》、神田正雄《从上海到巴蜀》及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撰写的《入蜀纪行》《滇云蜀水》《蜀汉之旅》《跋涉秦山蜀水》《思黔蜀之地》等[19]。虽然清末西方人来四川行旅考察目的各异,但其游记专业性强、史料价值大。目前除了《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竹添井井《栈云峡雨日记》、山川早水《巴蜀》、中野孤山《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等少数蜀道游记或包含蜀道考察的著作被翻译引进外,大部分西人蜀道游记尚沉睡在国外藏书机构,需要组织力量翻译、研究。
-
蜀道文献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也具有多学科研究的学术价值。从历史地理学研究角度看,历代蜀道文献是进行包括秦蜀古道在内的西南历史交通地理最重要的纪实文献载体,史志中的蜀道记载可以从国家与地方层面系统、全面地反映自古以来蜀道交通的发展趋势、交通盛衰、历代蜀道通塞与整修、蜀道与历代西南重大政治军事事件等,同时由于蜀道文献的多元性与丰富性特征,特别是历代蜀道诗歌文献与行纪文献对千里蜀道沿线的气候、植被、野生动物、河流水文、地质地貌等生态环境有生动真实的记录,是研究中国西南历史自然地理的重要文献载体。蜀道文献还对蜀道地带的农业、商业、人口、风俗、宗教信仰、民居建筑等有大量的记录,同样是进行西南历史经济地理与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史料依据。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蜀道文学是一道特别的风景线,魏晋南朝乐府诗中即有描写入蜀艰危的“蜀道难”这一诗题,与“陌上桑”“出塞行”“巫山高”等乐府诗题多次并行出现,内容多写蜀道的艰险难行与旅游者的悲伤感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有南朝阴铿《蜀道难》。唐宋时期蜀道文学兴盛,绝大部分著名诗人皆有蜀道之旅并留下诗赋作品,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陇蜀羁旅诗,白居易、元稹的巴地诗,薛能、胡曾、孙樵、韦庄等人的蜀中诗,宋代石介、张泳、宋祁、三苏父子、范祖禹、黄庭坚、陆游、范成大、吴泳、魏了翁、汪元量等诗人也作有数量不等的蜀道诗。宋元以降,虽然中国古代诗歌高峰已经过去,闻名全国的诗人不多,但仍然有不少文人墨客行旅蜀道,留有不少蜀道文学佳作,如明代诗人薛瑄、大名士杨慎、“前七子”中的康海与何景明,清代诗人王士祯、宋琬、张问陶、张邦伸等皆曾履践蜀道并有诗作或游记。可以说,蜀道文学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源远流长的支流,值得深入研究。
蜀道石刻文献与中国书法史关系重大,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汉代石刻书法流传至今已经十分稀少,而蜀道线上著名的“汉三颂”则较为完整地保存至今。“汉三颂”即甘肃成县天井山麓的《西狭颂》、陕西略阳灵崖寺的《郙阁颂》、陕西汉中褒谷口的《石门颂》。在汉中褒斜道南端褒谷口还有北魏书法经典代表作之一的珍品“石门铭”及两宋明清大量文人留下的石刻题记。这些石刻题记是中国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书法史石质标本,清楚地反映了从汉隶到魏碑再到宋代隶、楷、行书的演变过程和轨迹,其中不少题记还折射了平民书法的流变痕迹。因其珍贵的历史价值与书法价值,褒斜道石门书法受到清代至民国书法大家翁方刚、康有为、于右任等人的珍爱,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赞《杨淮表纪》“润泽如玉,出于《石门颂》”注,于右任甚至有“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觉泪湿枕”的由衷感叹。蜀道石刻绝大部分都是对古代蜀道开凿、维修主事者歌功颂德的刻石记录,可以说没有蜀道的开辟与交通发展,就不可能产生如此数量可观又无比珍贵的书法作品遗存。本次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蜀道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组“蜀道研究丛书”中有《蜀道石刻与中国书法史》撰写计划,即是出于蜀道石刻文献与中国书法史重大关系的考虑。
蜀道历史文献内涵丰富,历史跨度长,涉及层面广,涉及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中国古典文学、中国交通史、中国古代书法流变史、中国古代军事史、西南山地社会史、交通与国家、地方的关系等多个层面。以上所举,只是其中较为重要者,其余研究课题尚多。从跨学科与多维视角研究,正任重而道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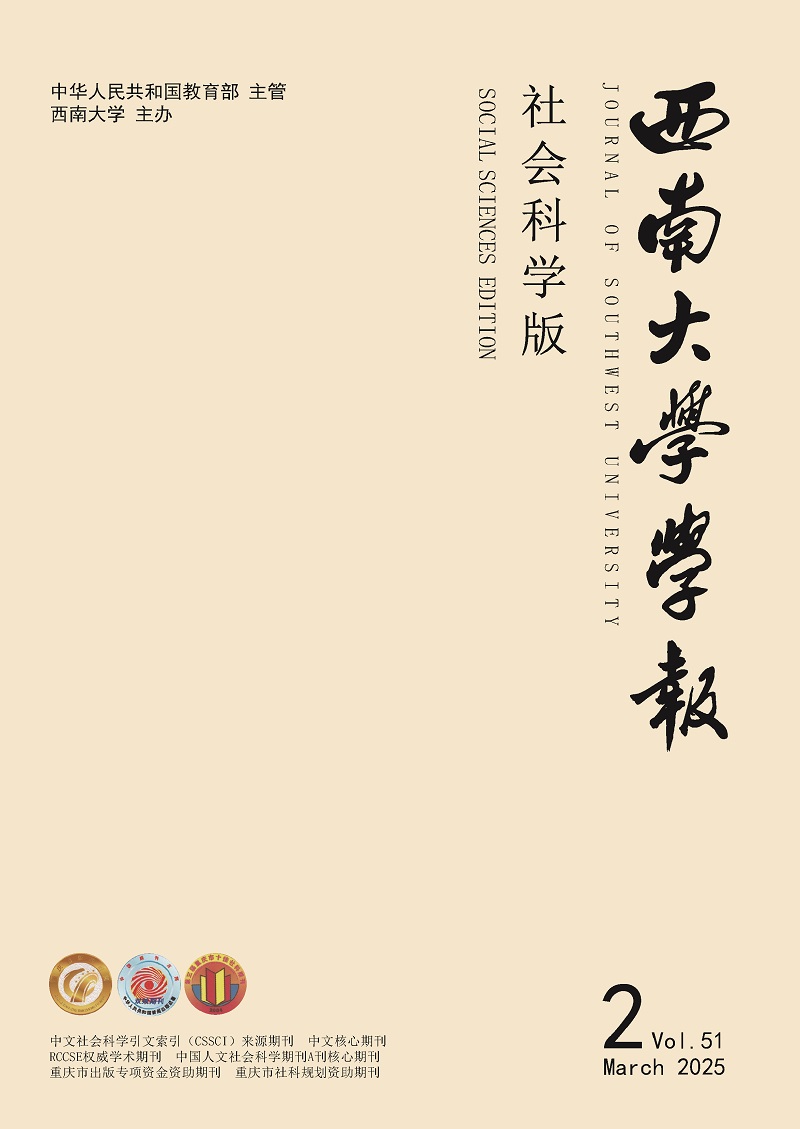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