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和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与科技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科技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新兴技术、新的教育学和变革知识的思想逐渐走向融合。这样,一个容纳了科技、教育学和变革知识的极度空间应运而生。在这个极度空间中,教育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发生变革,一个全新的教育生态系统正在形成。而且在这个教育生态系统中,人们可以享受到新兴科技带来的令人振奋而新颖的学习体验。
HTML
-
什么是极度空间呢?加拿大著名学者迈克尔·富兰(Michael Fullan)在其著作Stratosphere:Integrating Technology, Pedagogy, and Change Knowledge中进行了界定。他认为,在过去40多年里,三股伟大的思想力量——科技(technology),尤其是第一台个人电脑问世以后的科技;教育学(pedagogy),尤其是普及化高中教育以来的教育学;变革知识(change knowledge),尤其是变革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方式成为人们首要考虑的因素——相互依赖而存在。而且,当前这三股思想力量的大力协同增效作用凸显,在提升学习效果方面将发挥极大的推进作用。因此,他把科技、教育学和变革知识这三者的组合称为“极度空间”(Stratosphere)[1]2。他提出极度空间的目的在于让每一个学生的可持续学习成为可能。具体而言就是在教育领域积极融入科技的力量,从而拓展学习空间,形成更加简便高效的学习体验,为所有人建立一个全新且自主的学习体系。
从极度空间的界定来看,极度空间的核心构成要素有三:科技、教育学和变革知识,而且三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其中,科技为极度空间的形成提供技术支持与服务,通过不断扩展信息库(expanding warehouses of information)为整个教育系统的变革提供资源条件,促使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方式的变革,进而影响教育系统的整体变革。这种变革主要体现为教与学的双重变革:一方面是教师教学方式的变革;另一方面是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这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一是为学生提供多元的学习机会;二是帮助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在此基础上,教育与科技不断融合,从最开始的相离逐渐走向相交,最后实现深度融合发展——技术向教育回归。当然,在二者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新的教育形态的特征会逐渐凸显,这种变革会促使教育寻求更为新颖适切的新兴技术来为新的教学形态和学习形态的转型、定型与发展提供服务与支持。由此就形成了由科技、变革知识和教育学构成的具有闭合循环系统的极度空间,而且三者均扮演着多重角色: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既是整个循环系统的起点,又是整个循环系统的终点(如图 1所示)。
-
科技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科技的未来归根结底还是要关乎人类的发展和需求。当科技渗入到教育领域后,我们需要关注、思考的就是科技能为教育转型和变革做些什么,能提供哪些服务和支持。最为理想的状态就是科技想要达成的正是教育变革想要实现的,即“更高的效率、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新兴产业、更多的选择性、更好的专业化、更高的普适性、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互利共生、更多的美、更强的感知性、更强的结构以及更好的进化性”[2]270。在过去几十年中,科技遥遥领先于教育,主要原因不是科技变革的速度加快,而是教育发展缓慢[3]303。因此,我们目前要思考的就是,如何通过新兴技术为整个教育系统的变革服务,并推动其向理想的状态前进。也就是说,在科技一直领先的现实情境下,如何将科技的积极力量转化为教育变革的内在动力、促使教育与科技同步协调发展,是目前学界乃至全社会均需要关注的问题。因此,迈克尔·富兰指出:“学习活动(游戏)是一种与科技的赛跑,而且如果我们找到了正确的教育模式并融入相应的科技,学习会变得更加简单、深入并引人入胜。”[1]27-36
-
在21世纪,你知道什么,相比你能利用你知道的做什么,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创新知识或解决新问题的兴趣与能力,才是当今所有学生需要掌握的重要技能[4]142。在极度空间里,教育学关注的不再是教育所要实现的一个个长“清单”,它的重点在于关注真实的问题、兴趣与能力、深入现实的问题解决方法、合作学习(同伴学习)和内在动力。因此,教育变革本质上并不难实现,极度空间以学生的主观体验为训练目标,通过隐秘介入(stealthy intervention)、寻找意义和改变思维,促使师生加大学习投入,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激发学生学习与创造的激情,从而达到有效学习与干预,实现深度学习[5]。
极度空间通过借助新兴科技的力量,尤其是大数据、信息化和数字化的优势,将教育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难题和管理问题更加精准地描述或呈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在先进技术的引领下以更快、更便捷的方式学习和接受科学知识。实际上,这种教育变革的重焕光彩得益于科技的力量,是科技促使教育系统的整体变革,包括教育资源形态的变革、教学形态的变革、学校形态的变革乃至社会形态的变革[6]。未来教育资源形态的变革主要表现为知识的变革。首先体现为知识存储方式的变化。在极度空间里,知识的存储类似于云空间,但又不同于云空间,因为它比云空间大,蕴藏着巨大无比的互联网资源,但实际上又不能确定其准确位置[1]2。其次体现为知识传播方式的变革。在极度空间里,知识一改以往纸质书刊一对一的单向度传播模式,逐渐向一对多、多对多的多向度传播模式转变,这种知识的传播速度不仅呈现指数级递增的趋势,而且传播内容会经过各种科技力量进行系统性编排,使知识传播之间的每个环节都有机关联,实现知识传播的可预见和可调控[7]。最后体现为知识提取方式的碎片化和移动化。在巨大无比的互联网资源空间内,极度空间促使知识提取方式的变革。课堂教学不再是知识的提取或获得的主要途径,随之而来的是便捷式的移动获取,碎片化习得。这种变革知识的产生,使优质的教育资源回归大众,并形成新的教育生态,在教育系统内部构建起平等的教学关系[8]。
知识形态的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学形态,教学形态的变革则又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未来学校形态的变化,进而推动整个教育系统的整体变革,乃至社会形态的变革。这里则主要探讨在极度空间的影响下学习形态和教学形态的变革取向。可以认为,极度空间正在促使学生和教师的生命重焕光彩[1]30,带来学生学习的双重变革——提供多元学习机会(opportunities to learn differently)和学会如何学习(learning how to learn)。“人人享有优质教育”成为新时代教育的使命和挑战。随着科技尤其是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移动学习成为普及教育的新的可拓展空间,代表着学习的未来发展方向[9],也是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普及的重要途径[10]。从这个视角来看,科技的发展为人们的学习提供了更为均等的机会,人人都可以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接受优质教育的洗礼和熏陶。同时,科技的发展也促使学习资源的适应性增强,即通过技术(如大数据)对知识的传递进行个性化处理,使之更好地适应特定的学习环境、偏好和学生能力,做到“一个尺寸适合一个人”[11],实现个性化、定制化学习。此外,极度空间还促使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因为在极度空间里,每一个学生都被认定为可以在适当的学习情境中变得富有创造力。而极度空间环境中的学习法则就是直接着眼于一个问题,同时还要提前设定好离开的时间,以便用于反思或者沉浸于其他事情[1]45-46,即十分强调发挥独处时间(如冥想、休息、做些别的事情等)和兴趣对于学习效果的积极作用,赋予学生走出课堂的权利,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一些前所未闻的问题上,并运用一些他们从未用到的东西[4]32,更加全面、精细地审视世界的复杂性以及我们身处其中的位置。学习形态的转变,必然促使教学形态的变革。教学形态随着科技的融入而“焕发容光”,相应地,教师的角色也随之发生转变。教师在极度空间里扮演着4种不同的角色:重新组织者、鼓励者、促进者和拓展者。届时,合作学习或同伴学习将成为未来学习的主要形态,而教师将充分借助科技的力量,充当联结科技与教育的中介角色,将巨大无比的互联网资源变成所有人都能获取的免费学习资源,促使教学活动的变革。
-
变革知识意味着要将融合了科技与教育学的极度空间付诸实践,即将新事物付诸于实施。在极度空间里,变革知识并不是局部的小变革,也不是教育技术学领域的单一变革,而是教育生态系统的颠覆性变革与重构。变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大规模的有效实施,因为片面的、非系统的、表层化的实施容易导致变革的失败,那么将科技与教育学整合在一个新的事物中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上,促使教育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各种技术,在其产生之初一般都是为人类所忽视的。这种对待新技术的态度是正常的,因为人类害怕变革。但变革的推进和实施需要人类的支持,需要有人勇于探索,尝试新事物。因此,变革是推进教育改革、实现教育公平的必要途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随着“互联网+”“大数据”“设计+”“云计算”“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变革知识决定教育改革能否取得成功,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变革知识最终决定了科技能否为我所用。就变革知识而言,其要旨主要包括专注(focus)、创新(innovation)、同理心(empathy)、能力建设(skill building)、广泛传播(wide spread)、透明化(transparent)、剔除没有必要的事物(remove unnecessary things)和领导力(leadership)8个方面。然而,要想推动知识变革的完成,图 2所示的8个方面就必须同时实施并联系起来[1]119-120,即要求变革知识的各个构成要素必须搭配和谐、协同推进。
一. 科技(technology)
二. 教育学(pedagogy)
三. 变革知识(change knowledge)
-
从上文可知,极度空间得以运行的前提是科技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而变革知识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这只是极度空间理念层面的,要想使其付诸实施,还需要遵循一定的设计原则。具体来说,一方面要遵守成功产品的设计原则——专注、同理心、“简复化”(simplexity)、最小化可行产品(Minimum Viable Product, 简称MVP);另一方面又要遵循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能仅就技术谈教育,只有教育与技术达到深度融合才能使极度空间发挥实际效用。在数字化、信息化发展的浪潮中,成功的产品并不常见。乔布斯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他遵循了成功产品设计的3个原则——同理心(empathy)、专注(focus)和灌输(impute)。极度空间要想成为一种新颖且令人振奋的全新学习体系,就必须借鉴成功产品的设计原则。借鉴并不是直接拿来,而是在融合教育的基础上有所改变。由于灌输可能在某些程度上并不适用于极度空间,在此基础上,可将之转变为“简复化”。正如乔布斯所言:“我喜欢真正伟大的产品,它使得产品成本不高且简单易用。”[12]78
-
同理心,就是站在别人的立场和视角去理解与认同别人,它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一种感受和一种体验,也是一种技巧、一种修养和一种能力。在极度空间里,就是要有对所有生活形式的同理心[13],站在师生的立场和角度去感受、体验融合了先进科技力量的教育变革。那么,我们就要观照以下3个方面:(1)在教育领域融入科技的力量,必须考虑科技本身的适切性问题,即要以教育学或学习为基本点,因为科技本身不会使你变得聪明,虽然它让你看起来很聪明。如果没有教育学的积极引导,再强大的科技也不能称之为有效。(2)积极预测融入科技后的教育变革结果,如结果的好坏、变革的程度和深度等。理想的状态是形成一个实用且强大的核心理念——实用是指为变革的实施提供行动的指引;强大是指变革能够产生远超出我们预期的效果,即使不能引起大范围的变革,促使好事情在更大范围内发生也是好的。(3)融合了教育与科技的极度空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使学习环境的改善、激发师生的广泛参与,师生能否通过极度空间实现知识的再生产,并使之应用到对现实复杂问题的深入探究上。总之,就是要以教育学为核心,积极地将科技融入进来,营造全新的令人振奋的学习生态环境。
-
专注是极度空间得以成功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极度空间里,专注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专注意味着全神贯注,或者说进入一种心往神驰的状态。这里主要强调教师和学生在极度空间里的共同投入,尤其是学生学习的投入度。学生学习的投入度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1)融合了科技的教育学能否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即极度空间创设的学习环境必须新颖、引人入胜;(2)人的精力和时间在一定时空内是有限的,为了更好地做好我们想做的事,我们必须放弃那些不重要的机会。最好的状态就是前文所提到的“科技想要达到的就是教育变革所期望的”。以美国苹果公司为例,乔布斯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集中精力重点打造少数关键产品,注重产品的细节处理和个体触觉体验。
-
将科技融入到教育领域,不是为了将教育复杂化(complexity),而是借助科技的力量促使学习更为便捷、容易——“简复化”。就极度空间而言,就像设计智能手机的各种应用APP一样,新的学习环境的营造必须引人入胜,容易沉浸其中,而且在操作上既引人注目又“平易近人”。乔布斯在设计iPhone和iPad时,遵循的就是“至繁归于至简”的原则,即当你打开一个iPhone或iPad盒子的时候,“我们希望你的触觉体验已经为你如何看该产品定下了基调”[12]78。但简单不仅仅是一个视觉风格,也不仅仅是极简主义或者没有复杂情况出现,它需要挖掘复杂性。“想要真正的简单,就需要进入得很深。”[12]343因此,要想使极度空间“简复化”,就必须深入理解教育和科技,并找到教育与科技深度融合的切入点,既追求科技又注重教育,删减掉那些不必要的部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极度空间除了要遵循成功产品的设计原则外,还要特别注重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里主要体现为教育与技术二者之间的关系上。一般来说,要想实现教育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就要经历两个阶段:初期教育技术化和后期技术向教育回归[14]。就当下而言,教育与科技的融合仍然处于初期阶段,仅仅是将先进的科技简单地移植到教育领域,而并未充分考虑教育系统的复杂性,也未能真正地深入到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过程中。当前的情形是太多的应用程序“只是用于简单的操练或专注于传递可供消费的内容,而不是创造或重新使用”[15]。事实上,教育与科技融合的关键不在于应用了多少种新兴科技到教育领域,而是如何看待科技在教育变革中发挥的作用。极度空间要想被社会大众接受,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技术成熟和技术适用的问题,然后才是教育与技术的深入融合。而且在融合的过程中,应始终坚持教育中心[16]。因为在极度空间里,教育不是作为目的而存在,仅是促进个体全面发展的手段,而科技只作为环境条件出现,从外部持续推进教育整体的变革和现实问题的解决。
一. 同理心(empathy):不同立场的体验
二. 专注(focus):师生的共同投入
三. “简复化”(simplexity):事半功倍的效率
四. 教育技术化与技术向教育回归:深入到现实生活的问题解决
-
极度空间的有效运行,关键在于如何让科技奏效,即要创造环境让科技在教育教学改革中发挥实际效用。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科技都适用于教育教学。科技的力量目前已经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不得不承认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之大,而且影响深刻,但我们也不得不直面这么一个事实——教育发展迟缓,并没有像其他领域那样受科技的驱动而迅速发生变革。当下正是让科技进入学校、融入教育系统、推进教育变革的大好时机。因此,要整合教育学、科技和变革知识这三股力量。可行的方案如图 3所示。
-
在极度空间里,着力打造不可抗拒的学习体验是核心,而不是将经费、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并不那么重要的评价上。也即是说,要让教育学或学习成为极度空间的基本驱动力,而不能过分强调科技和变革知识的协同性,因为在很大程度上,科技的力量和变革知识的协同是为教育学或学习服务的。那么,如何才能让所有的事情都与学习相关呢?答案在于要让学生认知中的高阶技能占据极度空间的主导地位,并将变革知识的8个协同方面“发扬光大”。因此,需要构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让教师和学生分别承担与以往不同的关键角色:教师成为学生成长方式变革的推动者或导师,学生则越来越多地沉浸于对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之中。
-
从近些年科技与教育的融合来看,数字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它不仅促使知识存储方式的转变,而且还带来了知识传播、教学形态的变化。事实上,数字化的强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17]。时至今日,如果我们的学校和教师还在限制学生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设备),那么我们就是在墨守成规,抵制科技为教育带来的便利。就社会的发展趋势而言,放宽对科技的使用,尤其是要放宽科技在学校的使用,无论是对学校系统,还是对教师和学生,都是大有裨益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深层次与简单易行的方式,积极推进教育学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为学生进行创新性学习、个性化学习(定制化学习)提供宽松的外部环境[18]。
那么,问题在于如何最有效地发挥科技的作用?应该努力推动教育与科技同行,让科技渗透于教育的各个环节,通过科技推动所有的事情与学习相关。实践证明,与大自然作对,我们不会成功;同样,抵制科技,完全摒弃机器的深度学习、在线学习、移动学习等具有优势的新型学习方式,也是不明智和不可取的[19]。教育变革要随着创新的发展而不断深入,这可以从特种科技、社会创新和未来科技创新带来的未知红利(也有可能是危险的)3个方面加以论证。
首先,积极运用特种科技来推动教育变革。教育要有敢于融入特种科技(如语音识别、虚拟现实、物联网等)的勇气,允许新兴科技向教育领域渗透,同时直面特种科技可能对教育变革产生的各种影响,理解这种不可阻挡且不可逆的趋势。因为一种新的技术的使用,很快就会变成无处不在的现象,典型的代表就是智能手机在学生群体尤其是大学生群体中的普遍使用。很难想象当下大学生甚至中小学生还没有一个智能手机或移动终端(设备)的情形,这应当是很少见的。
其次,教育变革要与社会创新同步。教育要与社会发展相融合,适应社会需求而变革。例如,如何让老年人和青年人“为了培养集体智慧和社会健康”而聚在一起?事实上,老年人和青年人之间的学习现象具有极度空间的所有特点。这种现象充满真实生活的所有问题解决过程,并以相同方式教会青年人和老年人如何培养社会责任和环境意识。而且“当青年人教授老年人时,科技在代际关联(intergenerativity)过程中就成了一个自然的社会团结剂”[20],使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受益。
再次,预测未来科技可能带来的影响。就科技的发展而言,毋庸置疑,科技的发展速度将会加速,而且谁也不知道下一代科技将会为人类带来哪些红利或灾难。但从极度空间的设计原则和教育的发展规律来看,个性化学习(personalization learning)、同伴学习(peer learning)、代际间的相互学习(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将成为极度空间的主要学习形式。而且这种新型学习方式将在更大范围内精确地为所有人量身定制学习的内容、方法和目标。
-
有了无处不在的科技后,极度空间的运行还需要积极运用政府政策和各种策略来调动整个系统。这要求在变革整个教育系统时,要遵循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和自下而上的自主参与相结合的原则,将国家、地方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等利益相关者充分调动起来,构筑推动系统变革的利益共同体,使其从隶属关系转向伙伴关系,确保在整个过程中充分利用各种因素,推动科技、教育学和变革知识的整合。
为了调动整个系统参与变革,“必须将特定的高效的创新和策略与可以广泛传播的局部实施结合起来”[1]140。即要充分发挥变革知识的8个协同方面,使每一个协同方面均发挥最大效用,进而推动整个系统的变革。当然,在此过程中,科技的力量应始终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尤其是在推动内容的广泛传播方面。如果事情朝着预期的目标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惊人的、快速的和低成本的进步,为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及教育公平的实现奠定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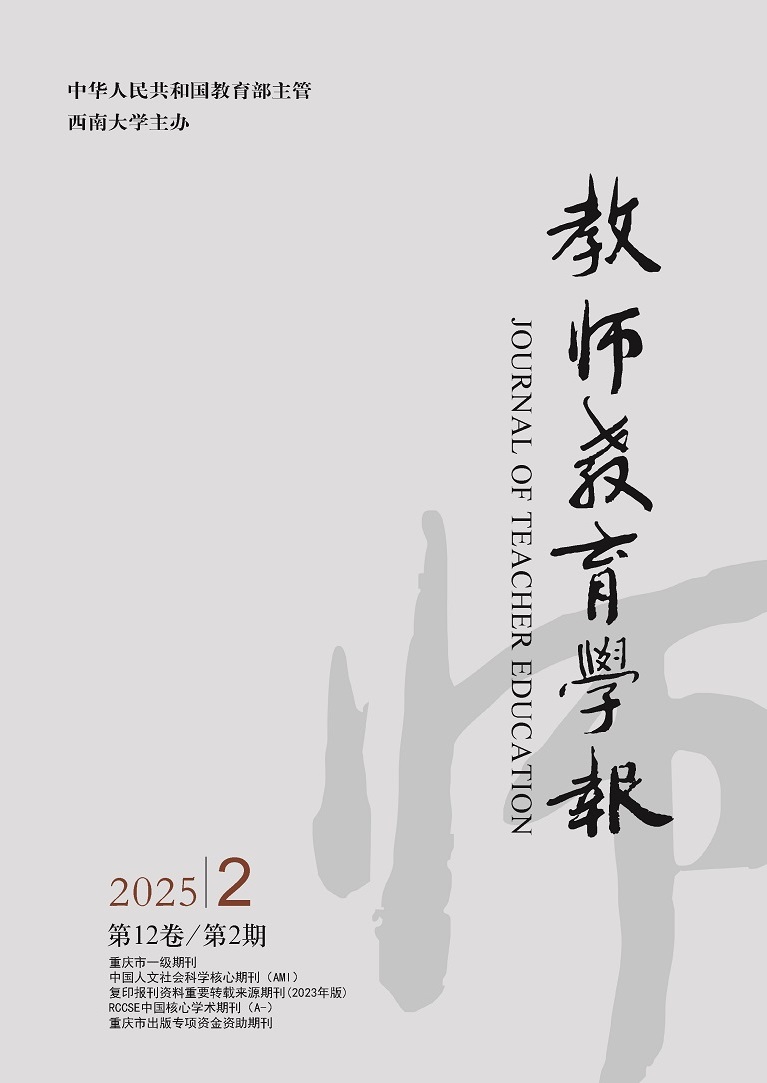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