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陶行知意识到挽救民族危亡要从人口数量占全国总人口85%的乡村着手,通过开展乡村教育的方法改造乡村生活,以实现救亡图存的教育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陶行知提出,乡村教育承担着乡村改造的任务,乡村教师担负着改造乡村社会的使命,因此,师范教师要下乡开展乡村教育。陶行知创办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培养了一批忠实追随其思想的弟子,他们将一生奉献给了国家乡村教育事业。从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研究的趋势来看,近五年,有学者从教育为民众、社会和国家承担伦理责任与价值追求的方面解读了陶行知的乡村教育伦理使命[1];也有学者从陶行知乡村师范教育观的本体内涵和乡村师资培养的辅助保障体系等方面分析了陶行知乡村师范教育思想[2];还有学者从乡村振兴视阈下对陶行知乡村教育进行再审视[3]。分析陶行知乡村教育情怀的内涵与实践可以进一步丰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学术研究成果。陶行知乡村教育情怀是指以陶行知及其弟子为代表的乡村教师群体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特质,其中包含实现“穷国教育”的政治抱负、改变“一百万乡村”的教育信仰,以及“向农民烧心香”的平民情感等内涵。
HTML
-
情怀本质上就是情感[4]。教育情怀是教师的一种职业情感和高级体验,这种情感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培养出来的,是教师对教育事业执着的最高境界,是摆脱了世俗利益的桎梏向内追求的精神力量。
-
国穷和国危是陶行知进行乡村改造所面临的国情。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外患侵略早已让它千疮百孔,而内乱又加重了灾难,导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政治腐败和军阀混战是当时民族危机的重要原因,帝国主义成为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大山。中国农民作为社会的底层被剥削被压迫,毫无民主可言,没有一点政治话语权。
首先,乡村教育情怀是一种政治关心。在中国传统乡村中,村民政治文化模式突出,农民不关心国家政治体制,也极少谈论政治事务,更没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激情或者可能性。中国知识分子属于臣民政治文化状态,他们与政治体系有着密切关联,一直以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陶行知想要改变当时农民的政治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于是提出通过培养有改造社会精神的乡村教师来改变整个乡村面貌等主张。这要求乡村教师抱有高度的政治关心和参与热情,帮助农民实现“锄头底下有自由”的愿望,谋取“在立脚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的政治生活[5],努力去改变中国政治结构,将村民政治文化向公民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转变。这是一场寄希望由教育革命而引起政治革命的运动。这场革命的阵地是中国乡村,这场战斗的主角是乡村教师。这场教育革命能否取得成功与乡村教师政治关心程度的强弱有着极大关联。政治关心既是乡村教师作为变革者的教育情怀,也是农民作为被变革者发生转变的核心。
其次,乡村教育情怀是一种救国抱负。陶行知说:“生民之涂炭,产业之凋敝,干戈之连结,经济之衰颓,外患之频临,不特无术防御,抑且视昔加甚。” [6]181辛亥革命,肇建共和,但并未能挽救晚清以来国家濒临民族危亡的境地,共和政体并不能挽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反而使国家和民族陷入更大危机之中。面对国家如此危难,陶行知确立了自己的救国理想,其主要阐述了两个问题:“什么是理想国家”和“怎样来建立理想国家”。对此,陶行知给出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建立“富而强的共和国”[7]18,并实现“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 [7]40,拥有“自由、平等、民胞”三大主义[6]182。陶行知给出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坚定地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并且要“制定出一套真正适合中国国情并为中国服务的教育制度来”[7]12。中国以农立国,有三万万四千万的人口在乡村,由此,陶行知提出了用乡村教育来改造乡村面貌从而实现救国理想的途径。从根本来说,乡村教师担负着救国使命,乡村教师要“一心一德的来为中国一百万个乡村创造一个新生命。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6]86。因此,乡村教育情怀就是一种救国抱负。
-
贫穷和苦难是陶行知乡村改造面临的考验。常年的政治动荡和农村旧生产方式的破产,以及兵乱匪祸、政府苛征暴敛,造成农村经济衰败凋落,农民生活境况难以想象的悲惨[8]81。而要办事就需要钱,更何况是在贫瘠的乡村建设学校。在办学过程中,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经济混乱是陶行知和他的弟子们常常遇到的问题。“今年我们从一月份590,000元预算开始,历经周期性物价飞涨,我们不得不在四月份采用1,678,000元的最低预算。这就意味着第一季度增加283%。”[9]就是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陶行知和他的弟子依然坚持着理想和信念,这无不体现出他们的使命担当和奉献精神。
首先,乡村教育情怀是一种时代使命。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的勇于社会担当和敢于直面社会问题的政治品格,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历史进程中,人们都会面临时代所赋予的使命。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其勇于担当的优秀品质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逐渐融合,凝聚成以救亡图存为主旨的民族担当”[10]。陶行知把改变国家厄运当成自己的时代使命:“我们生在此时,有一定的使命。这使命就是运用我们全副精神,来挽回国家厄运,并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交与后代,这是我们对千万年来祖宗先烈的责任,也是我们对于亿万年后子子孙孙的责任。”[11]陶行知提出,师范教育承担着兴邦的任务,乡村教师担负着“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6]74。“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成为乡村教师的责任[6]86。陶行知和陶门弟子将一生致力于乡村教育,并将其视为自己的时代使命。
其次,乡村教育情怀是一种奉献精神。奉献精神就是一种把主动付出、不求回报的行为视为快乐和幸福的精神[12]。奉献精神让乡村教师能够直面乡村条件极为艰苦的现状。陶行知让自己的学生做好心理准备:农村生活非常艰苦,在污泥里赤脚奔走,雪白的脸晒得漆黑,绵软的手上起硬茧,在风霜雨雪里做工、挑粪等。这些都是做乡村教师要经历的苦。奉献精神还支撑乡村教师能够直面办学时物质和经费匮乏的困难。1927年,陶行知不仅不领薪水,还说,“我预备翻书过活,日里为乡村教育努力,晚上翻书,这就是我的预定的计划”[13]132。甚至很多乡村教师常常两三个月领不到薪水。乡村改造需要乡村教师具备奉献精神。这种精神是一种锲而不舍、坚持付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乡村教师能够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撑。“我们深信最高尚的精神是人生无价之宝,非金钱所能买得来,就不必靠金钱而后振作,尤不可因钱少而推诿。”[6]75
-
传统和排外是陶行知乡村改造的无形阻力。陶行知及其弟子在进行乡村改造、办乡村教育时,常常遭遇来自中国农村内部的强大阻力。这股强大阻力就是中国农村的传统和秩序。中国传统农村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建而成的等级序差社会。“传统乡村社会中信任、规范的意涵与礼俗社会的内在秩序契合,村民对其产生共同性的情感认同,并保持一定的延续性,这是长期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稳定的内在原因。”[14]这种传统和属性是乡村对外的保护屏障,也使村民对外乡人有着天然仇视,同时也成为抵抗新思想新生活传入的无形力量。
首先,乡村教育情怀是一种情感归属。乡村教师要认同自身的农民生活和农民身份,有与农民同甘共苦的意愿,有将乡村改造事业进行到底的决心。这种身份认同还表现在乡村教师具备在农村生活的技能。陶行知要求所有乡村教师要拥有“农民的身手”,即既要掌握服务自己生活的劳动技能,又要掌握服务农民生产的教育技能。乡村教师有了农民身份认同,才会有“农民甘苦化”的情感共鸣[6]74,才会有念及农民的痛苦而为农民争取权利和幸福的行动。陶行知倡导所有乡村教师“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才配担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6]74。“向农民烧心香”的情感归属,是乡村教师融入乡村生活的“敲门砖”,是进行乡村改造的“劈山斧”,是乡村变乐园的“点金术”。
其次,乡村教育情怀是一种整体发展格局。乡村教师任务是以乡村教育为手段进行乡村改造的复杂的整体任务,不是简单的文字普及,也不是以儿童教育为目标的教学,更不是单单服务于乡村学校的工作。乡村教师要以整个乡村、整个社会为教育之地,以乡村的儿童、青年、妇女和老人等为教育对象,以农民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卫生生活、道德生活等为中心,对农民进行生产训练、卫生训练、科学训练等。而且,乡村教师战斗的舞台不仅仅局限在国内乡村。陶行知对乡村改造的决心是以世界格局来规划的:“第一步要谋中国三万万四千万农民之解放,第二步要助东亚各国农民之解放,第三步要助全世界农民之解放。”[13]127这也是其创办南京晓庄学校的意义。
一. 实现“穷国教育”的政治抱负
二. “改变一百万乡村”的教育信仰
三. “向农民烧心香”的平民情感
-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陶行知等人将全部的生命和热情都投入到乡村教育的实践和改造中。陶行知乡村教育情怀就是在这样一种“知—情—行”的实践循环中孕育而生的。知,即以乡村改造为己任的具身认知;情,即回馈乡土的情感共鸣;行,即全域拓展乡村教育实践。在行与知的关系上,陶行知认为二者互为始终,这也恰恰是其乡村教育情怀生成与乡村教育实践之间的关系。乡村教育情怀既是陶行知等人进行乡村教育改造的动力与内驱力,亦是他们在改造乡村的教育实践中蕴育而出的一种强烈的教育情感。改造乡村的教育实践既是陶行知等人将强烈的教育情感付诸行动的体现,又是他们将这种情怀不断升华的途径。
-
对社会负有变革的责任,对国家负有报国的理想,对乡村负有改造的使命,这是陶行知对时代青年、师范生提出的殷切希望,也是乡村教师情怀孕育的认知起点。费孝通提出:“人类行为是被团体文化所决定的。在同一文化中育成的个人,在行为上有着一致性。”[15]95民国肇建,社会变迁,文化变更,思想继替,社会正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陶行知等一批教育名流所倡导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理念逐渐形成了平民教育思潮,由此聚拢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志在以改造社会为己任,意在以乡村改造为救国之道。
首先,明确青年学生的社会责任。陶行知认为青年学生应负有求真的科学精神,要改造社会必具有委婉的精神,应对环境必具有坚强人格和百折不回的精神 [16]221。青年学生作为最有力量和希望的群体,陶行知希望其成为社会最具有改造精神的团体,而这也是时代给予青年学生的使命。
其次,养成经世济民的价值追求。陶行知深信教育亦能救国,认为师范生“干的是乡村教育的革命”[16]369,因而要有一种“我来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积极倡导更多有报效国家的大无畏精神的热血青年来做乡村教师。程本海是坚定的乡村教育支持者,最早加入乡村教育战线,他深信乡村教育是救亡大计,并提出一个“要完成国民革命,须厉行乡村教育”的计划,主张扩大乡村教育革命战线[16]455。程本海积极响应陶行知号召,呼吁有志青年学生随时加入乡村教育战线。“所以希望全国学生界忠实同志们,依据才能兴趣正式或随时加入乡村教育革命战线,齐心奋斗,以竟全功。”[16]369可以说,程本海是所有追随陶行知乡村教育改造践行者群体的缩影,他们认可乡村教育运动的意义,并以乡村改造作为人生奋斗目标,有着浓厚的乡村教育情怀。
-
20世纪初,陶行知批判以往的中国乡村教育教人将生存之根从乡村社会拔除,让人逃离乡土,认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6]85,提出乡村教育要回归乡土,推进乡村改造。当时中国农村社会正经历着传统生存方式破产、传统文化教育和生活伦理秩序瓦解,而新的合理的价值秩序、道德生活和生产方式又远没有建立的混乱时期,农村生活存在着生存危机与文化教育危机的双重困境。
首先,激发乐于回馈桑梓的爱乡情感。所谓“乡土”,是一个相对于城市而言的行政划分,它不单单是行政单位,还是一种个体成长的体验世界和精神世界,更是个体的文化发展社会。陶行知出生在安徽黄山歙县的一个小山村,曾经到美国留学,对国家的情感让他成为“很中国”的留学生。他关心安徽教育发展,“我对于安徽负有特别责任,不能不勇猛进行。”[13]11陶行知抽拨南京歙县试馆的月收入,作为歙县开展平民教育的费用,并亲身到安庆推进平民教育运动,还带领更有影响力的朱其慧一起到安庆开展活动。他曾经担任南京安徽公学校长,为旅宁安徽人提供教育上的帮助。1934年,为解决天灾带来的灾难,陶行知等人成立“歙县旅沪同乡普及歙县教育助成会”,决定在歙县王充创办歙县第一工学团,由方怀毅为总指导员,开展了纺织、农林等工学团以及合作社。陶行知曾与歙县知事汪镜人互通信件,表达了他个人对歙县平民教育发展的建议,提出鼓励造林,劝告禁烟禁赌,尤其提出了开展平民教育的步骤和计划。陶行知还在卢绍刘就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之时,提出推进安徽平民教育的十条建议。陶行知对家乡安徽的牵挂所传递的乡土情怀,正是乡村教育情怀的核心,也是孕育乡村教育情怀的温床。
其次,激活回归乡土的理性情感。费孝通在《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中提到,“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15]6。20世纪初,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将乡土社会边缘化。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呈现出整体性的乡土逃离,使得乡村社会现代文明空心化,现代文化传播在乡村社会里完全缺席。在这种背景下,回归乡土具有了两重意义。一是要求知识分子回归乡土,回馈桑梓。如果乡土社会要在以城市文明为中心的现代化社会结构中成为不可替代的存在,那么回归乡土是不二选择。乡村学校成为了改造乡村社会的文化绿洲,乡村教师成为引路人,所以,倡导生于斯长于斯的知识分子要回归乡土。二是寻找乡村教育的价值位序。陶行知推行的是回归乡土的乡村改造,而不是肤浅地追随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步伐。为此,陶行知提出了“乡村教师—乡村教育—乡村生活”的改造逻辑:“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我们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乡村教师。活的乡村教师要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6]85。
-
在实践中,意识和思想会不断得到完善和检验,而且还会得到验证思想的有效路径。“教学做合一”是培育乡村教育情怀的重要方法,即以做为中心、以事为中心、以农村实际生活为中心。乡村实际生活是乡村教育的中心,乡村改造是乡村教师做的中心。有行的勇气,才会有知的收获。知—情—行是培养乡村教育情怀的重要实践逻辑。
首先,强调根植乡村的实践价值。陶行知强调乡村教师要在情感上与农民甘苦与共,做行动上的巨人,践行乡村改造理念,强化情感体验。乡村教师通过融入农民生活、学会做农活和家务等方式,将教育与农业相结合,提升科学农业在乡村改造中的作用。乡村教师只有农民化,才能真切体会农民的苦与难,才会积极为农民争取权利。同时,乡村教师要在实践中教化农民,并且做到将学校与社会打通、教育与生活相融合,到田间地头劳作,“同农民交朋友,开办农民夜校,和农民合作开木工厂、合作社”[17],改善农民生活,教育才能有成效。
其次,开设有乡土气息的学校课程。在农村建设乡村师范学校,要使师生能够适应乡村生活,从而培养他们的乡村认同感。课程内容决定学生未来的方向,通过开设有乡土性的课程来培养学生的乡村情怀。例如,晓庄学校的课程就与传统学校里的课程不同,前者课程内容以生活教育为主,“一切课程都是生活,一切生活都是课程”[16]297。陶行知倡导的学校课程包括校舍建设、煮饭烧水、学习书本知识、运用所学征服自然等,一切生活日常之事都由学生自己动手完成,这便是生活教育。学生要扫地、擦桌、洗碗,平时还要种菜、学烧菜,一切自己的事情都要自己干。生活在乡村,学习在乡村,奉献在乡村,由此孕育出乡村教育情怀。
最后,开展“知行合一”的乡村教育实践。在实践中坚定理念,在理念的指导下行动。陶行知并不是培养坐而论道的乡村教师,而是强调通过“做事”方式来培养乡村教师的乡村教育情怀。方与严作为陶行知的战友和弟子,受陶行知的感召,将浙江湘湖师范建设成了另一个晓庄学校。在湘湖师范,以生活为教育中心,以农民为朋友,师范生不仅学习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还要学会干家务和农活。“象晓庄师范一样,每个学生通过学习与劳动,要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乡村教师。”[17]湘湖师范在方与严等人的努力下,声名大振,被冠以“浙江晓庄”之名而闻名全国,培养出很多坚定拥护乡村教育运动的乡村教师。南京晓庄学校的师生贯彻陶行知的“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的主张[6]85,在南京北固乡四十里内创办了晓庄、和平门、太平门、万寿庵、三元庵、吉祥庵、黑墨营等七所中心小学,一所劳山中学和燕子矶等四所中心幼儿园[17]。
一. 以乡村改造为己任的具身认知
二. 回馈乡土的情感共鸣
三. 全域拓展乡村教育实践
-
进入21世纪,我国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流动,乡村教育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农民对高质量学校教育的追求与农村学校教育质量薄弱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凸显,大量的农村子弟涌入城市学校,造成乡村学校萎缩。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农村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迫在眉睫。乡村振兴计划的重心在于发展乡村教育,这是阻断贫穷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印发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中就提出:“发展乡村教育,教师是关键,必须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8]2023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也提出,要继续实施“优师计划”“特岗计划”“国培计划”等专项计划[19]。新时代乡村教师要在乡村振兴的大环境下,完成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使命。
-
乡村振兴是陶行知乡村教育情怀历史传承的时代召唤。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随着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农民对子女的教育重视程度逐渐提高,对教育品质的要求和教育成功的期望也越来越高。教育质量薄弱的乡村学校显而易见不能满足这种需求。大量的农村子弟到城镇学校求学,一方面造成乡村学校萎缩和凋零,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家庭教育成本和学生时间成本。从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20]到二十大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1]可以看出,乡村振兴是关系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大计,是一项艰巨的时代任务,而“乡村教师是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乡村教育的基础支撑,是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22]。
政治关心是培养乡村教育情怀的时代要求。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社会发展国家富强的战略任务。当代大学生要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事业。政治关心是乡村教育情怀的时代传承。从古至今,教育对治国安邦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民国初期,陶行知等知识分子把乡村教育视为救国良方,号召一百万人加入乡村教师队伍并承担起乡村改造重任。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政治背景下,国家更需要“一支热爱乡村、数量充足、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乡村教师队伍”[22]。因此,厚植乡村教育情怀成了激发教师奉献乡村教育的内生动力。乡村教育情怀不仅体现了师德师风建设的内涵,还彰显了教师政治关心的底色,即敢于担当大任承担大责的政治抱负。这种政治关心和政治抱负是乡村教育情怀的底色和基调,是一种精神价值。厚植乡村教育情怀,就要从乡村振兴战略出发来培养师范生,使师范生理解兴农即为兴国的本质。“使他们产生对乡土的深厚情感认同、对家乡的热爱与责任感、对乡村振兴事业的历史使命感,以及作为家乡振兴生力军的自豪感。而这些情感素养,会使留在乡村、扎根乡土、积极献身乡村振兴事业成为更多乡村新一代的自觉选择,而不是不得已或退而求其次的谋生之道。对于乡村振兴的正确态度、情感认同,会激发出乡村新一代巨大的创造能量和乡村发展不竭的内生动力。”[23]
-
奥古斯丁提出“汝若不信则不明” [24]。认知是对不同概念的判断和选择,是人们行动的内在指引。根据社会认知学,人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都会受到当时社会认知的影响。一个群体内的社会认知是该群体成员之间沟通交流所形成的共识,为这一群体内成员所共享。尤其是对宏观社会性事务的认知,会影响人们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如理想、道德、信仰等。近代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特殊群体,他们以乡村建设情感为纽带,汇聚和培育志同道合者,由教育革命掀起政治革命。
乡土情怀是乡村教师扎根乡村、立志乡村建设的基石,是乡村教师奉献乡村教育的前提,是乡村教师在乡村安居乐业的精神动力,是乡村教育情怀的核心和根本。教师乡土情怀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乡土身份的认同。乡村教师认同乡土身份,就是认同本土文化和习俗、认同农业生产方式、认同农民生活方式和认同乡村教育的本土性等。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才会自发和自然地产生浓厚的乡土情结,并有着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意识,也才能孕育出乡土教育情怀,从而愿意扎根乡村。新生代教师具有比较先进的教育理念、信息技术能力等,是促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人力因素。二是新乡贤身份的认同。乡村教师具有知识精英身份和乡土身份的双重属性。知识精英的身份让其有了脱离乡村的资本、摆脱乡土的机会,同时也具备了促进乡村振兴的能力和本领。乡村教师不仅承担着乡村教育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还承担着农民生产技术的普及和培训任务,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引导者和组织者,还是农村扶贫工作的重要参与者[25]。这是时代所赋予的乡村教师的新乡贤身份。教师人才回流农村能形成一个磁场,影响和吸引其他人才回归故土,从而加快实施乡村人才支持计划,推动乡村振兴进程。正是具备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身份,乡村教师才有了与其他场域的知识精英不同的乡土情感,以及对乡村割不断的记忆和联系。
-
在儒家哲学中,知与行是儒家道德实践理论中讨论道德知识与道德践履关系时涉及的一对重要范畴。新时代背景下,“知行合一”被赋予了时代内涵。“一方面体现在统一认知与实践,运用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自觉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对于知行合一这个中国哲学重要观念的灵活运用上。”[26]培育乡村教育情感,既要重视知识的输入,又要重视实践体验,还要促成有意义的个体经验,从而有助于形成积极的乡土情怀。
开设有乡土特色的课程,是促成有意义的个体经验和丰富个体知识的有效途径。高等师范院校师范教育不仅要“注重其胜任一般性教书育人所需的普适性知识的传授”[27],更要重视乡土课程建设与开发。乡土课程开发要遵循本土性和乡土性两个基本原则,在内容选择上,可以通过物质性资源、精神性资源、生活资源等分类别进行建设。例如:物质性资源包括建筑风格、地理风貌等;精神性资源包括公序良俗、名人历史等;生活资源包括日常饮食起居等。统整课程,厚植师范生的乡村文化情怀,开展具有乡村教育情怀实践体验活动等,这些都是有利于帮助师范生扎根乡村的教育。高等师范院校可以在见习、实习的教育活动中选择乡村学校作为实习单位,甚至可以利用网络信息平台,构建高等师范院校与乡村学校之间的教师共同体。“师范生的实习、见习或者顶岗等活动都可以到这些乡村中小学校去,在‘教、学、做’中更多地去体验乡土情感,树立生在乡村、学在乡村、做在乡村、教在乡村的理想。”[28]这些实践活动都有助于培育积极的乡村教育情怀。合肥师范学院开展“行知学堂”,积极推进“小先生制”,鼓励师范生到乡村开展“行知学堂”,服务乡村教育和儿童,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展实践体验的范例。
一. 乡村教育情怀培养要以政治关心为底色
二. 乡村教育情怀培养要以乡土情感为支撑
三. 乡村教育情怀培养要以“知行合一”为途径
-
陶行知乡村教育情怀是以陶行知为核心的乡村教师群体普遍拥有的教育情感,有着教育救国的政治关心,也有着心系农民的乡土情感。新时代乡村教师亦背负着乡村振兴的历史重任。“培育具有乡村教育情怀的乡村教师是新时代师范院校的重要使命,更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乡村人才振兴与文化振兴的重要途径。”[29]以史为鉴,重新思考和审视陶行知乡村教育情怀的本质内涵,发现其与“提升思想政治素质” [22]“厚植乡村教育情怀” [22]的新时代乡村教师的国家需求不谋而合。新时代乡村教师要成为新技术新知识的传播者、新农村新农业的推广者、新生活新风俗的倡导者、新文化新思想的推动者,都可以从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情怀中汲取力量和智慧,不负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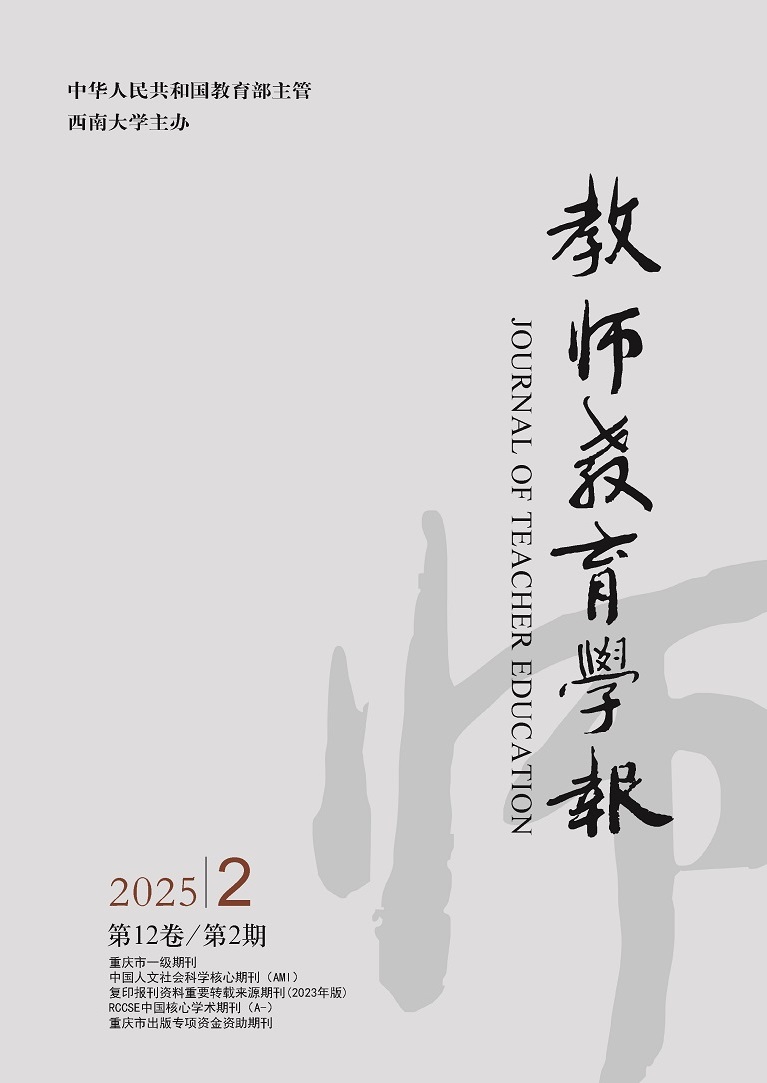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