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记》为什么要为刺客、游侠立传,历来众说纷纭。自班固“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的评论出世,“史公三失”就成为贯穿《史记》研究史的一个命题,其中游侠传的作旨自然成为绕不开的话题。仔细考究班固所论,他针对的是司马迁关于儒道的言论,以《游侠列传》《货殖列传》为例,以此证明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后人在讨论这个议题时多分而论之,未把这些传记和观点看成共同表达同一主旨的整体。如果对相关传记进行整体考察,就会得出与班固相反的结论。近代以来,更多学者从思想史渊源角度考察游侠,章太炎、梁启超、冯友兰、钱穆等提出“以儒兼侠”“侠出于墨”及儒侠(墨)对立、游侠私剑对立等观点[1],多以《史记》相关记载为论据,虽未着意于其相互关系,仍有助于从学理上认清侠的发展历史。当代学者从多方面展开了对游侠的探讨,宋超[2]、韩云波[3]从《史记》《汉书》比较或正史序列角度对比不同时代史家笔下的游侠,汪涌豪[4]、田蔚[5]探讨游侠的性格特征,韩云波[6]、王大建[7]对游侠发展阶段性进行考察,皆有可观之处。近年来在游侠群体及侠文化研究方面,更趋向于综合性和理论化,章培恒[8]、陈向春[9]的宏观研究成果有助于从文化发展角度理解《史记·游侠列传》。也有文章探讨了司马迁的义利观[10]、礼治思想[11]、平民意识[12]等,对深入理解《刺客列传》《游侠列传》《货殖列传》等相关传记之间的联系是有益的。更加重要的是,如果把这些传记看成一个表现司马迁礼义思想的典型序列来审视,就可从中看到司马迁考察历史的多角度立体思维方法,即从历史人物形象入手,结合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全面考察社会发展趋势的史学方法。陈其泰认为从《史记》五体配合的总体结构可以看出史家的观察力已由单一视角发展为多维视角[13],这与本文的写作构想有一致之处,并具有启发意义。从《史记》的《伯夷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货殖列传》等相关传记看,司马迁这种多维视角的历史观察力得到了充分展现,使刺客、游侠等传的仁义主题得到突出显现并统一起来。弄清楚这个问题,对探讨民族精神中仁义思想的发展演变、史家的思想认识及考史方法等,都将有所帮助。本文主要从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出发,从整体上重新审视这些作品,在分析其创作主旨的同时,考察其思维方式与考史方法的独特意义。因此,本文先分析两篇传记的宗旨,再综合起来看二者如何共同表达了司马迁的历史观,进而窥见其历史思维特点。
HTML
-
从《刺客列传》的写作宗旨看,司马迁突出刻画了刺客们一个很显著的性格特征,即“士为知己者死”,这已成为学界共识,本文不展开论述。要注意的是,《史记》中这些刺客或“不欺其志”,或“以死明忠信”,他们与“知己”之间有为“信义”而死的关联,如司马迁所说:“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义不为二心。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14]4022“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15]3079显然,这里强调的是刺客们对知己者的信义和忠诚。
-
《刺客列传》重点描写的荆轲形象颇具独特性。首先,荆轲与“知己”的关系及其所守之“义”与其他刺客不同。与荆轲构成“知己”关系的,是田光和高渐离,而不是燕太子丹。在整个谋划过程中,太子丹对荆轲的性格为人并不十分了解,他甚至怀疑荆轲的诚意,因此可以说荆轲并不是为了太子丹而去刺秦的。那么,荆轲刺秦的最根本动因是什么呢?结合荆轲传和《太史公自序》,荆轲传一开头就讲了荆轲游历的经历:
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其后秦伐魏,置东郡,徙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15]3066
司马迁很重视战国遗闻,他所记的荆卿轶事颇有意趣。庆,春秋时齐姓,齐有庆封。在卫而人称之庆卿,在燕而人称之荆卿,可见他始终没有归属,客居他乡,四处颠沛,心怀抱负,是一位游士类人物。鲁、卫在《论语》中是有特殊含义的,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16],“鲁、卫之政,兄弟也”[17]2507。鲁、卫、燕分别是周公、康叔、召公的后代,荆轲游历始于卫之衰亡,卫国在卫元君时已很弱小,沦为魏国附庸,秦灭魏后将卫元君迁到野王县。《太史公自序》:“周德卑微,战国既强,卫以小弱,角独后亡。嘉彼《康诰》,作《卫世家》第七。”[14]4015鲁、卫之衰代表着周德衰微,荆轲之游于卫、燕等国就别有意味,不仅仅是一个独行刺客。袁枚曾说:“以大义论之,凡为周之臣民者,复仇而义为六国之臣民者,复仇而义,彼荆轲者,独非周之遗民乎!……盖天下之苦秦久矣,其怜六国而思周也,更久矣。”[18]司马迁把荆轲作为“周之遗民”来写,意在“嘉其宗周之义”。这在写战国时也有反复陈说,《太史公自序》表明战国“世家”作旨说:“嘉勾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作《韩世家》第十五”,“嘉威、宣能拔浊世而独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14]4016-4017,等等。从《史记》体例编排看,《刺客列传》之后紧接着是《李斯列传》,李斯是秦代人物传的开始,所以荆轲就可看成宗周时代的结束。在卫之后,荆轲又游历了赵、燕等国,耳闻目睹了这些国家先后为秦所困的过程。由此,荆轲可说是战国末期六国反抗强秦的一个代表,其他如田光、高渐离、范於期、鲁仲连、张良等都是此时涌现出来的,是荆轲的陪衬。在这个意义上,荆轲之义超出了一般刺客“为知己者死”的道德范畴,具有更广泛的道义内涵,荆轲刺秦是出于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的救难行为。
其次,司马迁在写荆轲时赋予了比其他几个刺客更加丰富的性格内涵,兼有儒、侠、刺客的特征。为了突出其性格特征,司马迁接连增写了三则故事①,除“以术说卫元君”之外,还有“与盖聂论剑”“与鲁勾践争博”两件事,刻画了荆轲深沉自尊、酷爱自由、受辱不争、矢志不移的性格特征。紧接着又写了一段故事:
① 《史记》中“荆轲传”的史料来源,一说是《战国策》,一说是《燕丹子》。可参看张海明《〈史记·荆轲传〉与〈燕丹子〉比较论——兼谈〈燕丹子〉的小说文体属性及意义》,《文学评论》2013年3期,152-163页。
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15]3067
荆轲“好读书击剑”“为人深沉好书”“以术说卫元君”,行迹有似战国儒士。这里还写出了荆轲纵情任性、深沉不凡的性格:其深沉是由于不得知己,屡遭失败,虽坚毅自守,仍不免失意忧郁,得遇知己时喜极而泣,慷慨悲歌,旁若无人,正是豪侠游士任情、深情的表现。这些故事在《战国策》中没有记载,经过司马迁的增益,是对荆轲儒侠兼具性格的着意刻画。这一性格与他后来应田光之求而刺秦王的情节紧密相连。与他结交的“燕之处士”田光以“节侠”自许,并为消除燕太子丹的疑虑而杀身求仁。荆轲本人是认同这种身份和举动的:
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曰:“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15]3073
当刺秦之意受到太子丹质疑时,荆轲的反应与田光类似,可见他心目中亦有对“节侠”的默许和赞同。此前,太子丹以“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定位荆轲,荆轲思之良久乃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荆轲对于像曹沫那般刺客身份的接受是颇费踌躇的。《货殖列传》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记载:“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19]3962这很容易联想到荆轲。是否可以说,荆轲是“儒侠合一”的早期形态,而刺客身份乃时势所定。即荆轲本来是游侠,深受卫风任侠的濡染,只是他的最后一击奠定了其刺客身份。
司马迁在写荆轲刺秦王后,又增加了两则故事以彰显刺客特征。一是高渐离继承荆轲遗志,以筑击秦王不成;一是鲁勾践听说荆轲事迹后感叹:“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15]3078此处以所谓“非人”来对应“知人”,即“荆轲以为我不是他的知己”。鲁勾践是赞赏荆轲刺秦之举的,以不能被荆轲视为知己而深感遗憾,也可说是荆轲的事后知己了。正因为田光、高渐离这些“知己”的出现,使得荆轲的“刺客”形象越来越鲜明,刺秦王不成而死义,已到故事高潮。但直到高渐离刺秦和鲁勾践感叹,荆轲“士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形象才完整浮现出来,他们是荆轲精神的发扬者,并最终完成了他在历史上刺客身份的确认。
-
荆轲形象与其他刺客还有一点不同,即司马迁没有明确强调其“死名之义”。豫让刺杀失败后曾说“忠臣有死名之义”,为名节而死是刺客秉承的宗旨。《韩非子·五蠹》:“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韩非认为带剑者的刺杀行为都是为了个人名节。这种“显其名”的解危释难行为,与荆轲出于社会责任感的救难行为相比,是有明显差别的!相比于刺客“士为知己者死”的“义”,荆轲刺秦之举更有同情弱小、不畏强暴、已诺必诚的游侠意味。那么,在荆轲混而为一的形象中,到底蕴含了什么样的意旨呢?司马迁在荆轲形象的描写中,把刺客之义与游侠之义联系起来,共同塑造了侠客的道义精神,从而使二者在本质精神上统一起来。
司马迁为刺客立传的出发点不同于韩非子。韩非子从“游侠私剑之属”的行为特征和是否便于统治的立场出发,儒侠并举,“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20]。司马迁从社会情状和社会心理维度观察人们对刺客的认识,商君在秦变法,“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21],法家对“私斗”的整治由来已久。此外,战国“以市道交”的社会风气也普遍存在,如:
(冯煖)曰:“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趣市朝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愿君遇客如故。”[22]
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23]2967
上述普遍情况是韩非所称“游侠私剑之属”的社会基础,代表了战国时代“游侠”的基本道德状况,由于与儒家义利观不合而影响了人们的基本评价。汉初这种观念依然存在,贾谊说:“阖闾富故,然使专诸刺吴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荆轲杀秦王政。今陛下将尊不亿之人,予之众,积之财,此非有白公、子胥之报于广都之中者,即疑有专诸、荆轲起两柱之间,其策安便哉!”[24]贾谊把专诸、荆轲等刺客看作势利之徒并持打压态度。司马迁通过考察长时段历史中的刺客活动,发现他们既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义,也有“义不为二主”的忠信,还有荆轲身上儒侠兼具的义,这就使得他不仅要从社会风气变化角度,而且还要从道义观念变迁角度去重新审视刺客之义,视野角度的拓宽让他看到了刺客与侠、儒之间的联系纽带。
一. 兼具儒、侠、刺客特征的荆轲形象
二. 刺客之义与势利之交
-
对于游侠,司马迁欣赏的是游侠身上所体现的大“仁义”,即《太史公自序》所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14]4025从这些评价来看,侠与儒具有某种道德联系。
-
作为儒家的子路,却常被视为侠的始祖。从《论语》看,子路行事作风确实有游侠的特征。先看《论语》中这样几则记录: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25]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26]
上述“子路无宿诺”“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等,正是司马迁所赞赏的游侠“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的品质,即为承诺信义而不顾安危的至诚,以及排忧解难、轻利好义的热忱。又如: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17]2507-2508
儒家赞赏士的“言必信,行必果”,与司马迁概括的游侠“言必信,行必果”的信义,无疑是一致的。再如: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27]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16]
“无伐善,无施劳”就是不表彰自己的长处、不夸耀自己的功劳,这和“博施济众”的儒家理想及司马迁赞赏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游侠仁义如出一辙。《史记》中的朱家就是这种精神的积极实施者:“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28]3868朱家是司马迁心中最理想的游侠形象,把这些行为品质综合起来,就形成了司马迁对游侠精神的概括: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28]3865
此处儒侠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司马迁更在意游侠“功见言信”的特征,功见是重行动和效果,言信是重承诺和信用,以此强调游侠行动与信念的一致性。这在儒家宗师看来,也是士君子十分重要的品德: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豪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29]
孔子对曰:“所谓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明通而辞不争,故犹然如将可及者,君子也。”[30]
(澹台灭明)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31]
从以上看,儒家弟子中不乏以“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豪厘”“设取予去就”“言忠信而心不德,仁义在身而色不伐”为行事准则的人物,并且受到孔子、荀子等人的肯定。
司马迁似乎要有意突出儒侠之间的联系。儒者本有任侠一派,且不论司马迁对游侠的认识是否从这一派中抽绎而来,先看《仲尼弟子列传》的立传宗旨:“孔氏述文,弟子兴业,咸为师傅,崇仁厉义。作仲尼弟子列传第七。”[14]4020儒与侠的立传确实反映了同一个目的,即崇仁厉义。司马迁借用儒家核心概念“仁义”为游侠正名,将游侠精神看成是接续传统儒家仁义观念的可贵支脉,将其纳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系统之内。司马迁引用“鄙人之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他说:“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礄暴戾,其徒颂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28]3866这里对所谓“仁义”提出了质疑,认为游侠的仁义才是真正值得赞赏的。这是站在民间立场的“仁义”,其根本精神与先秦儒家仁义思想相吻合,把民间侠客之义纳入到了正统文化之中。司马迁凭借史家的力量为游侠立传,让曾经被“儒、墨皆排摈不载”的古代游侠进入史册,进入历史的文化殿堂里来[9],并有意在叙事之先借此明确自己记录游侠事迹、弘扬游侠精神的叙事原则,从而使游侠成为具有精神文化内涵的符号性形象。
-
司马迁的历史认知,与他观察刺客时所用的儒侠一体考察方式或历史视角有着很大关系。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首先辨别了侠与儒的命运变化及仁义变迁,确认侠作为一个随着历史演变而不断变化的群体,勾勒了侠的演变史。古之游侠即古之布衣之侠已湮灭不闻,战国任侠之风在四公子养士之风中得到培育和发展,至秦汉之际则有朱家、剧孟等游侠的出现,孝文帝时“季心以勇,布以诺,著闻关中”,汉景帝时侠者受诛,汉武帝时郭解被害。这部游侠简史,表现了司马迁作为史家的当行本色,也说明他写游侠并不纯粹发愤抒情。综观《史记》其他“任侠”人物传记,可以清楚了解到司马迁对西汉游侠发展史的系统总结[6]。司马迁从中寻求的是变中不变的仁义精神,并不是侠的身份标识。
司马迁在考察游侠发展史的基础上,对游侠仁义内涵进行了明确概括。这是通过层层比较来实现的:他对游侠之人和“儒者”季次、原宪加以比较,发现他们所坚持的“义”,“久孤于世”,“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比较而言,游侠之义最可贵之处是“效功于当世”和“功见言信”。在实践层面上,闾巷之侠对仁义的践行力度超过了布衣之儒,对社会影响更大,这是司马迁比较布衣之儒和游侠的初衷。他又比较了游侠之人与“富贵之侠”:“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此类侠者借其权势地位和财富招致“天下贤者”,和他们相比,“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完全靠自己的德行修养博得人们的赞誉。他把游侠之士与“豪暴之徒”区别开来,游侠之士“虽时扞当世之文网,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28]3867-3868。以上三项区分,表明司马迁对游侠之义的了解建立在深入的历史考察基础上,从而认为游侠是“贤豪间者”,可与圣贤、豪杰并立。这种比较,目的是为了突显布衣之侠的特点,而不是要区分游侠与比较者的优劣。但紧接着,司马迁通过郭解传具体展现了朝廷之儒与布衣之侠的激烈斗争,揭露了朝廷之儒迫害布衣之侠的残酷事实,从而让人看到现实社会中儒与侠的境遇。侯门仁义与游侠仁义的冲突在这里得到充分表现: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翁伯。[28]3872-3873
通过“上曰”“生曰”“公孙弘曰”,表明朝廷之儒对游侠坚决打压的鲜明态度,让人看到儒者片言杀人的手段。布衣之侠所持仁义与侯门仁义形成尖锐对立,而与布衣之儒的仁义合流,独立于侯门仁义之外,布衣之侠在与权势的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仁义精神。再对比《汉书》的评价或许可有更深入的认识,《汉书·游侠传》说“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其行为结果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32]。“窃杀生之权”揭示了游侠不为统治者所容的原因,即公孙弘所说的“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守职奉上之义”则是班固希望游侠遵守的道德。司马迁对汉武帝朝的“守职奉上”者如公孙弘、万石君、张汤、桑弘羊等,无不怀有讥讽厌恶之情,认为恰恰是他们丧失了儒家仁义之旨,是“缘饰以儒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兴利之徒。他在《叔孙通列传》中称叔孙通为“汉家儒宗”,显然是别有意味的。司马迁对游侠的认识不是孤立的,有对儒家历史发展的统观为基础。无论是对刺客还是对侠的内涵、发展史和结局的考察,都始终贯穿着这种儒侠一体的方式。
以这样一种古今联系、多方对比的思想方法考察不同历史人物,司马迁对游侠、刺客们布衣之义的抒写,突破了身份与地位、官方与民间的界限,表达了他对理想人格和仁义精神的追求。这种理想的表达既是对中华民族追求仁义道德文化历程的总结,也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可以继续追求的精神高标。
一. 对游侠仁义内涵的提炼
二. 儒侠一体的考察方式
-
司马迁一面清晰如实地记录着刺客、游侠与儒者的历史,另一面又试图将他们在仁义精神上统一为一个整体。这种矛盾情绪,使人联想到七十列传的首篇《伯夷列传》。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提出的天道与人道、是非与善恶的疑问,在《游侠列传》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答。
-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33]2585
这是司马迁在七十列传首篇中提出的质疑,也是从自古及今社会现象的对比中提出的。他首先提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是邪非邪”?由此将天道是非的命题过渡到善人与恶人的评价,与孔子所说“求仁得仁,又何怨乎”相呼应。要解答天道是非的问题,就要先判断仁善怨恶,对天道是非的疑惑就是他对仁义判断的怀疑,天道与人道就联系起来了。司马迁接着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他要从自己所观察到的历史现象中确立他对人的道德衡量和价值判断,并且特别提出重点关注的是“岩穴之士”及“闾巷之人”:“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33]2588到《游侠列传》,司马迁明确展示了此前对天道是非、仁义善恶疑问的看法。他看到持有布衣之义的闾巷之侠对“人道”之仁义的发扬,看到他们对“常与善人”之“天道”的践行,尤其赞赏他们用行动和生命载道的品质,如游侠的“功见言信”“千里诵义”,刺客的“立义较然,不欺其志”,从而突显“布衣之义”在儒家仁义失守时的历史贡献。从《伯夷列传》到《游侠列传》,表现了司马迁在现实中寻求理想的心路历程,他把天道是非命题和仁义判断命题统一起来,也就是把天道与人道统一起来,树立了对天人关系的新理解,即天道需要人道来执行和发扬。
-
那么,他是如何将这个天人关系的历史认识在《史记》中逐步统一起来的呢?也就是说,除了刺客、游侠这样的人物,《史记》其他篇章中是否也有一以贯之的认识呢?
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34]
太史公曰: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邹阳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亦可谓抗直不挠矣,吾是以附之列传焉。[35]
燕之初入齐,闻画邑人王蠋贤,令军中曰“环画邑三十里无入”,以王蠋之故。……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遂经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脰而死。齐亡大夫闻之,曰:“王蠋,布衣也,义不北面于燕,况在位食禄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诸子,立为襄王。[36]
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乎哉!”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田横……太史公曰: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37]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14]4026
这些人物,有儒生、高士、隐者、勇将、货殖等,司马迁统称他们为“布衣”,给予他们“至圣”“至贤”“智者”的赞扬,表现了对下层平民精神的人格观照和重视,他们匡危救世、排难解纷、守节不屈、坚守道义、反抗强暴、独立自主,他们可以动王侯,可以奋人心,使人慕义无穷。这些品质不是与游侠的侠义精神相通吗?鲁仲连的义不帝秦、邹阳的抗直不挠、田横的以死抗汉,都是对布衣之义的生动演绎。鲁仲连功成不受赏、排难解纷而无所取,不就与游侠的“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一致吗?如果说鲁仲连是儒者之义的体现[38],那么,游侠之义与儒者之义在这个层面是统一的。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迁描写刺客、游侠、儒士等所持的布衣之义,就在实质上消除了他们身份阶层的界限,而追求其内在精神的一致性。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了司马迁在大一统时代试图总结共同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努力。也就是说,司马迁通过为布衣立传及对布衣之义的阐扬,把游侠、刺客、儒者从精神品格上统一起来,试图从中发掘一种民族共同追求的理想人格。这个意图与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申明的宗旨是一致的,即为“闾巷之人”“岩穴之士”立传,也与《太史公自序》所说“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的“扶义”之旨相符。
正是在这样的仁义主旨指引下,刺客、游侠、儒士等布衣成为仁义精神的典型代表。就“布衣”一词和这个群体看,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为人关注了。唐且对秦王解说“布衣之怒”时,所举即“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39]。这些都只是把刺客看作春秋战国布衣精神的体现。直到司马迁作《刺客列传》《游侠列传》集中表彰他们的侠义精神,使之成为布衣群体的代表,这才强调仁义是布衣人格的重要构成元素。当然,司马迁的“布衣”不再是一种身份地位,而是普遍追求的人格精神。这种思想倾向从司马迁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也可以得到证实。《刺客列传》《游侠列传》都是以完整故事形式集中表现某一独特的代表人物。按常理来说,荆轲并不是典型的刺客,郭解也不是司马迁最欣赏的游侠,为何司马迁要为二人大费笔墨?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司马迁不是从刺客或游侠的身份地位、行为特征角度来写,而是从儒侠并行的思想文化发展角度去写。从荆轲这个儒、侠、刺客混同的形象推断,至少在战国末期,儒侠融合已经出现。到汉武帝时,司马迁更强调了郭解形象从好勇斗狠向谦退君子发展的性格特征,说明这种融合趋势已经很明显了。当然,司马迁之所以详写二人,也由于他们是时代风气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代表性人物。荆轲的代表性在于他把“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与战国时代的悲剧命运演绎到了极致,郭解则代表了秦汉布衣游侠的发展及其在汉武帝时代的结局。历史发展中时代因素的注入使得二人的性格呈现出复杂性,也因为他们既有丰富立体的性格,又能实在地反映社会现实,从而成为能够代表某个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的典型历史形象。这些成功的文学性书写为后来侠文学作品中亦儒亦侠形象的塑造奠定了基础。
从历史人物活动的角度考察历史,只是司马迁观察历史的一个维度,当他从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各个方面思考他们之间的联系时,刺客、游侠、儒士恰是相承的整体。司马迁在历史认识的层面上对游侠、刺客这一历史群体进行价值判断:刺客、游侠们的布衣之义联系了儒、侠,使得他们在精神品格上达到平等的沟通,因此游侠即使不为体制所容,也能在精神上延续。即使侠的身份指向及其所表现的社会价值观不断变动,司马迁所肯定和寻求的,始终都是他们在塑造民族精神方面对历史发展进程所起的积极作用[40],这就使得司马迁的史识和他总结的布衣之义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一. 天道是非与仁义判断的统一
二. 布衣之义的整合与民族精神的树立
-
由以上分析可知,司马迁对社会、历史、道德等的认识是有机联系的,贯穿于他对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描绘中,虽然有时显得有些隐约难辨,“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我们固然不敢自诩“好学深思”者,然心向往之,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挖掘司马迁考察历史人物的思维方式和考察方法的思想根源。
从传记类型来看,游侠、刺客传是类传,其立传旨意主要是反映某一时期的社会风俗,不是专为某人立传。因此,学者多认为《史记》类传具有“社会史”性质。对司马迁来讲,所谓“社会史”,不仅是对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的横断面加以考察,更在于从纵向时间维度以会通古今天人的观照方式进行哲理思考。首先,从“通古今之变”来看,战国至秦,社会上流行“剑刺”之风,不光是个人仇怨之间多行剑刺,国与国之间也以此解决问题。《史记·李斯列传》:“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41]燕太子丹之刺秦就是这种风气的必然产物。《刺客列传》除了彰显刺客之义的微旨外,还有揭示社会时代风气的用意。同样,《游侠列传》的出现也是汉初崇尚侠义的社会风气使然,“汉祖杖剑,武夫勃兴……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任侠之方,成其俗矣”[42],汉初很多朝官都是以侠义著称的,如窦婴、汲黯、季布、栾布、袁盎等[43]。可见《史记》类传更注重从当前社会历史现实出发去刻画社会文化心理的发展线索,这就使得司马迁不仅要针对不同的社会风气立传,还要从时间维度上对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的互相联系进行思考。其次,就“究天人之际”来看,司马迁常常把个人道德操守与时代风俗联系起来。具体地说,他在探讨刺客、游侠的历史时也试图寻找儒、侠之仁义在义利变迁中的发展轨迹,即经济发展与思想道德和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这表现了他整体综合地考察历史发展的思维方式。如《游侠传》记朱家、剧孟时特别讲到:“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周人以商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28]3868-3869从中就可以窥见司马迁在儒、侠与商贾之间寻求联系的努力。在《货殖列传》中可以找到相应的记录,如他说邹、鲁之风与周之风俗:
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19]3963
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19]3978
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19]3979
像曹邴氏、师史这些个体人物,对周、鲁“好贾趋利”风俗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不禁使司马迁感慨:“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19]3969司马迁还看到商贾之利对人们道德观念形成的影响:“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19]3952他进一步以自己所观察的历史事实来佐证:“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19]3955这里的“势”就是儒家道德的风衰俗变、由礼而利,由此揭示了侯门仁义形成的社会根源。《孟子荀卿列传》开篇说:
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44]
他从孔、孟罕言利的原因来进行解说,强调好利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在渐趋好利的社会风尚中能保持个人仁义节行的人,如朱家、剧孟之类游侠就引起了司马迁的关注。在《货殖列传》中有很多关于任侠的描写,并且都与其他列传暗合。如写三河之风:“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19]3960,“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19]3960,与平原君等传记暗合;齐风“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19]3963,暗指孟尝君列传及曹沫劫齐桓公等事;越楚之俗“剽轻,易发怒”,“清刻,矜己诺”[19]3964,与伍子胥传暗合;宛人“任侠,交通颍川”[19]3967,与灌夫等人传记暗合。这些相互勾连的考察与经济发展、时俗演进交杂在一起,从中约略可以领会太史公全面考察历史的微旨。所谓“见盛观衰”“观往知来”,司马迁歌颂布衣之义正是与他批判汉代官场兴利与争利的道德风气相表里的。钱钟书在解说《货殖列传》作旨时说:“《游侠列传》引‘鄙谚’:‘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汉书·贡禹传》上书引‘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司马迁传货殖,乃为此‘鄙’、‘俗’写真尔。”[45]不仅如此,司马迁还在《史记·平准书》中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发展的维度做了总结性的描述:
太史公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以至于秦,卒并海内……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饟,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46]
司马迁从虞夏以来的历史考察中看义与利的盛衰变化,认为殷周“先本绌末”之时尚可“以礼义防于利”。而“事变多故”之时则相反,“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直至于秦汉。这与《货殖列传》开篇所讲的观点一致:“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19]3949在司马迁看来,汉武帝时期仁义陵迟衰微,再加上“事变多故”,“争利”已是势所必然。由此可知,司马迁是从“观风俗以知政教”“以礼义防于利”的角度观察历史,关注的是争利社会中人们对仁义的追求和坚持,也就是不趋世风、勇于信诺、敢于实践、功见言信的勇猛精进的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迁对仁义变迁、势利之交的感慨,不仅是基于个人身份遭遇的愤慨,更是一个史学家对时事发展和风衰俗变的担忧:
主父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47]
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48]
太史公曰:张耳、陈余,世传所称贤者;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国无不取卿相者。然张耳、陈余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由殆与太伯、延陵季子异矣。[49]3137
《张耳陈余列传》所写势利之交是形势变则交情变,“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与《史记》中其他地方相通。为了突出这一主题,司马迁在张耳陈余传记末尾写了贯高的事迹,称其为“立名义不侵为然诺者”,显然是以势利之交与游侠之义对比而书之意。太伯和延陵季子也是作为张耳、陈余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吴太伯世家》“太史公曰”说得明白:“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50]就是以太伯与季札让国之仁义与势利之交进行对比。司马迁进一步指出势利之交的根本原因就是人们的争利、不知让。张耳、陈余的交恶即由此引发:
(陈余)乃脱解印绶,推予张耳。张耳亦愕不受。陈余起如厕。客有说张耳曰:“臣闻‘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今陈将军与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张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陈余还,亦望张耳不让,遂趋出。张耳遂收其兵。陈余独与麾下所善数百人之河上泽中渔猎。由此陈余、张耳遂有郤。[49]3130
这就是“太史公曰”所说的“所由殆与太伯、延陵季子异矣”,因而他才在《史记》中一再提倡让道,本纪之首的《五帝本纪》、世家首篇《吴太伯世家》、列传首篇《伯夷列传》均有嘉奖礼让之义。《史记·乐书》也提出:“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见利而让,义也。”他赞赏刺客之忠义、游侠之“廉洁退让”,都是源于这个认识。他还认为在利益面前知退让才是真正的智者、勇者,才能明了人生的真正价值: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23]2971
这里“退而让颇,名重太山”一句,实际上是讲人的生命价值与“奔义”“让利”紧密相关,司马迁并不欣赏那些轻易抛弃生命的行为。这些认识使他笔下的游侠与后世出现的那些不拘礼法、为人疏狂、重气轻生的侠客不同。
综上所述,司马迁对刺客、游侠等布衣之义的塑造根源于他“以礼义防于利”的主张。这使我们更加确信,从列传之首的《伯夷列传》,经《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至列传之末的《货殖列传》,始终贯穿了司马迁对义利变迁的考察。因此,司马迁对刺客、游侠等布衣之义的赞赏与对势利之交的愤慨,不在于某种个人的得失,而在于社会人生的某些普遍方面。
-
本文所梳理的司马迁在刺客、游侠传中表现出的仁义主旨及其多维视角,以及儒、侠一体的考查方式,只是他众多写史方法中的一种。全面总结司马迁这些写史、考史的方法就会发现,儒、侠一体的考察方式具有新的史学方法论意义。它包含了对韩非子等历代学者之历史认识考察的视角、对儒侠发展阶段的历时性考察视角和对社会未来发展趋势预写的视角,是立体的、开放的思维方式的体现,能更好地发挥史学总结文化演进的功能。有学者称之为“借儒形侠”的叙述方式[5]。实际上,司马迁是儒、侠并重的,他在儒、侠对举中,把儒的独善其身和侠“为死不顾世”的社会担当进行对比,此中已蕴含了对个人精神追求与社会责任感进行考量这一隐含命题。游侠“廉洁退让”“羞伐其德”的独立不羁的人格精神与他们对上层社会的反抗精神,也是后世儒士定位布衣身份时面临的选择。这种考察方式不是把儒与侠简单对立起来,而是在矛盾中寻求统一。当然,这种考察方式是以对社会经济、政治现实的考察为基础的。汉武帝之后,儒、侠的界限逐渐模糊,甚至儒、侠合一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有任侠之风的直臣构成“儒侠”统一的形态。精神品格上的一致性,使得游侠之义渐渐与儒家仁义相融合,这是儒侠合一的内在精神基础。此后,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唐代,游侠精神被儒家所吸收整合,成为唐人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出现了像李白这样的儒、侠精神合一的典型代表[51]。至此,游侠精神完成了对士人精神品格的建构,构成布衣精神的一个要素,并凸显了布衣的道义内涵和精神独立的价值取向[52]。司马迁最早总结和预写了儒、侠互补的历史发展趋势。此后,班固《游侠传》中那些具有儒家思想行为特征的游侠,以及他把陈遵和张竦一侠一儒对比而书的方法,恰好印证了这种历史发展趋势。这也说明司马迁在叙写游侠、刺客时采用儒侠一体的考察方式,本就是如实再现历史趋势的一种自觉选择。
司马迁在整部《史记》中所传达的思想及其思维方式是全面而丰富的,表现了史家思维能力的极大飞跃,向我们展示了在哲理思考指导下如何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根本要领和途径。通过《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及相关传记的分析略窥一斑,恰如欣赏一幅五彩错杂的织锦,其中贯穿着的一些经纬是读《史记》“心知其意”的门径,它为贯通地考察和论述历史发展、社会心理、文化精神、政治经济策略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楷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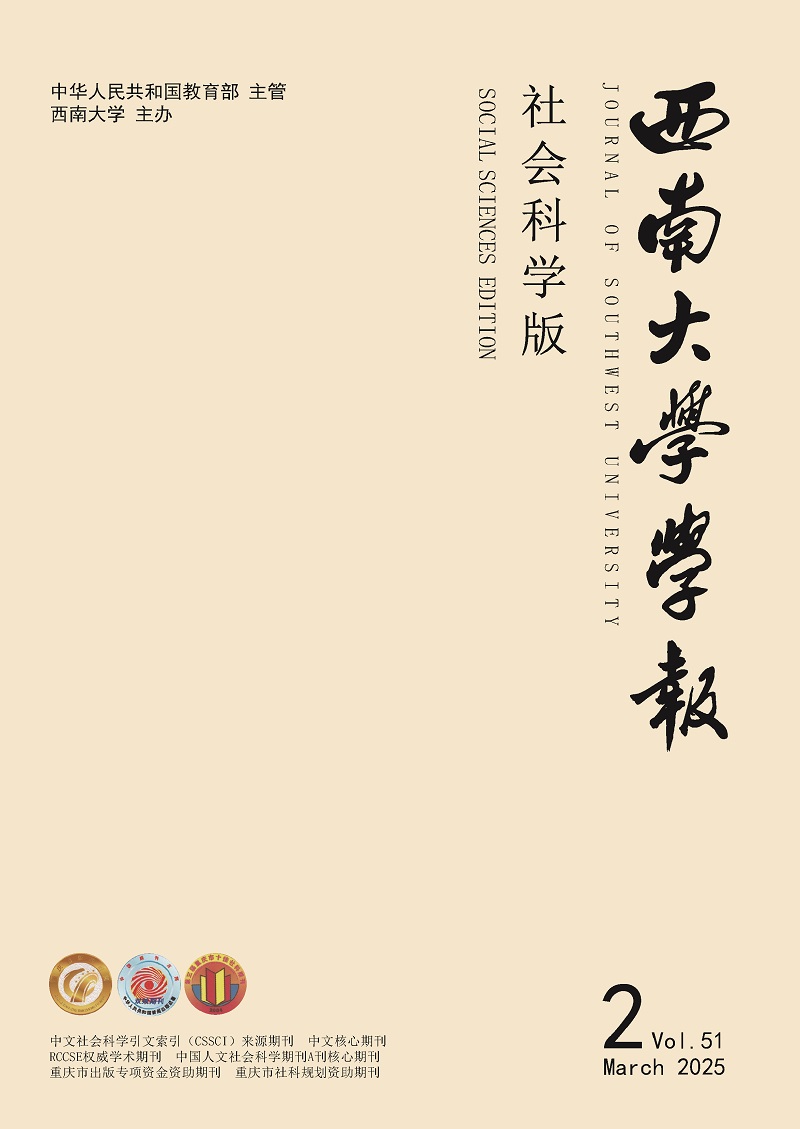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