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构具有民族品格和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需要认真清理、合理吸纳古典诗学遗产,有必要逐一追踪诗学话语的生成来源与轨迹。先秦时期的“兴、观、群、怨”“诗言志”等理论表述,奠定了中国诗学的根基和主流方向。然而,与《诗》关系密切的“采诗”与“采诗制”,却主要被视为一项政治制度,其诗学价值未引起足够重视。正式出现于班固《汉书》中的“采诗”叙述,强调诗与政治的关系,突出了诗的“观风”功能,继中唐元、白将“采诗”“采诗官”等吸纳进新乐府理论后,其诗学意义得以突显。唐以后新乐府或非乐府体诗中不断发出的“以俟采诗者”的呼声,反映出诗人对诗歌现实功能的追求。其中,元代文人自发组织的“采诗”活动还寄托着“斯文不坠”的信念和对统治者文化政策的不满。在日本古典文学中,也发现了“采诗”话语的踪迹[1]。显然,历代“采诗”叙述形成了充满发展性和涵容性的话语系列,《汉书》“采诗”叙述的发端意义由此可见。
学界对先秦“采诗制”的存在已基本无异议,近年来从《诗经》文本出发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采诗”证据[2-3]。有关《汉书》“采诗”叙述的分析,学界主要是与汉乐府采诗的功能和性质联系在一起的。有论者以“观风俗,知薄厚”作为乐府采诗政治意图和功能的证据[4]。也有论者认为班固并没有讲过乐府有采诗以观风俗的职能,所谓“亦可以观风俗”云云只是说明乐府所采歌诗具有“伴随而来的好处”[5]。直接针对《汉书》“采诗”话语形成的研究成果较少,就笔者所见,王红娟认为《汉书》“行人振铎徇于路以采诗”是对《左传》记载师旷引《夏书》佚文的改造[6],但没有进行论证,此说对本文的观点有所启发。总体来看,目前从文本话语角度对《汉书》“采诗”叙述生成的历史依据和文献来源尚无深入探究,对《汉书》在不同语境使用的“采诗”一词视为同义而没有揭示其所指的差异和话语背后的意义。本文对“采诗”关键性话语的生成来源和核心词语所属语境进行探索,意在以话语溯源的方式显示其被“生产”的轨迹,认识其汇聚型特征和现实指向意义,以此推进《汉书》“采诗”叙述的深度研究。
HTML
-
“采诗”话语最早最集中出现于《汉书》。《汉书》中《食货志》《艺文志》《礼乐志》的“采诗”叙述,既有对先秦政治制度的追记,也有对汉武帝时代乐府职责的陈述。对于作为政治制度的“采诗”,《汉书》的追记有其古史依据和汉代文献背景,关于这一叙述最主要的来源,本文认为一是《左传》所载师旷引《夏书》中“遒人徇路”之说,二是《尚书大传》《礼记·王制》所载天子巡守“大师陈诗观风”之说。
《汉书·食货志》云:“男女有不得其所者,乃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7]这里描述的是井田制下的社会状况,“行人”是周代职官,“行人采诗”指周代采诗。“太师”即周代“大师”之职,属“春官宗伯”之属,与小师、瞽曚等俱为乐官,掌乐事。据此,《食货志》描述的无疑是周代采诗之事。“采诗”之后需有音乐配置,以乐歌形式达于上听,实现“听诗”观政之目的。“采诗”“听诗”的意义,自王者而言可观风察俗、裨补王政,就百姓而言可各言其伤、疏通情志,由此形成上下通畅的良好政治生态。
“振铎采诗”可能出自《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载师旷的一段言论。晋侯质疑卫人驱逐其君之事,师旷就此指出,天子、诸侯治政皆有进谏制度:
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8]卷32,p4250
师旷引《夏书》这一内容,不见于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杜预认为出自逸《书》。孙星衍《尚书今古文疏证》未见此内容。如果师旷所引有据,那么,此《夏书》当是后来发现的孔壁尚书的一部分,时在汉武帝时,汉人谓之“逸十六篇”。东晋时出现的伪孔传《古文尚书》中有《胤征》篇,夏仲康执政时胤国之君胤侯奉王命征讨荒淫失职的羲氏、和氏,此即胤侯出征前对所部之众发表的誓师之辞,胤侯之辞中“遒人以木铎徇路”一段与师旷所引基本相同。《胤征》出自伪《古文尚书》,师旷所引当然不会出自于此。那么,班固“振铎徇路”说是否有可能出自汉人所谓“逸十六篇”呢?这涉及班固和《尚书》的关系。班固所撰《汉书》各传引《尚书》多用今文经,班固整理的《白虎通》也用《尚书》今文说,再考虑到今文经在两汉时均立于学官,因此,班固和今文《尚书》的关系更深。既然今文《尚书》不见“遒人振铎徇路”的记载,那么,《食货志》“振铎徇路”之说更有可能来自《左传》载师旷所引《夏书》。比较《食货志》“振铎徇路”与师旷所引《夏书》“振铎徇路”,相同或相近之处为:一是“木铎徇路”的行为;二是“孟春”的时间点。但二者所论一为夏代之事,一为周代之事,且“徇路”者由“遒人”变为“行人”。
首先讨论“振铎徇路”何意。从师旷引《夏书》前后文意来看,“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是对“遒人以木铎徇于路”的补充说明,因为“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更可能是常规化的进谏,不会只在“正月孟春”这一特定时间才进行,合理的解释是只有“振铎徇路”在“正月孟春”特定时期开展。伪《古文尚书·胤征》对这一内容语序的变动正合乎这种解释。《尚书正义·夏书·胤征》胤侯之辞曰:“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9]卷7,p332时间之后紧接“徇路”。《胤征》篇虽为伪作,且其材料可能取自师旷所引《夏书》,但“每岁孟春”这一句语序的变动,正反映了汉代以来学者的理解,“振铎徇路”发生的特定时间对于认识“徇路”何为至关重要。“遒人以木铎徇于路”一句的语意并不完整,按《周礼·小宰》“徇以木铎”郑玄注,振铎有警众之意,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10]卷3,p1409。据此,“遒人”一句从字面解释,即遒人于道路中振动木铎召集、警示众人,目的在于“谏失常”,即“谏”王和诸侯以改变错误的政令。显然,行为和目的之间存在叙述空缺,召集、警示众人如何达到“谏失常”的目的呢?杜预注《左传》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注此句为:“逸《书》。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8]卷32,p4250这个注释非常接近《食货志》“行人以木铎徇于路以采诗”,杜预此注很可能依据的就是《食货志》,“木铎徇路”信息改变的源头还在班固这里。《食货志》补充了师旷引《夏书》叙述的缺失信息,“徇于路以采诗”,是说“行人”于道路中振动木铎召集众人并宣示“采诗”政令以便收集歌谣,如此叙述就顺畅了。
《食货志》将夏代的“遒人徇路”改为周代的“行人徇路”,首次提出“行人采诗”说,《周礼》并无“遒人”一职,“采诗”之“诗”指周诗中的各地土风。“诗”在先秦和汉代文献中,很多时候指的就是“诗三百”。逸《书》中遒人徇路所采集的,按杜预注是“歌谣之言”。从夏代遒人“求歌谣之言”到周代行人“采诗”,这是《食货志》中发生的叙述置换。这一置换的依据,一是文献中有关周代“乐谏”的记载,二是先秦和汉代的《诗》学论述。
较之夏、商历史,先秦文献《左传》《国语》对西周政治制度记述更为清晰详细。师旷对晋侯所言“史为书,瞽为诗”的进谏形式,从属于天子听政制度。《国语·周语》“邵公谏厉王”篇也有相似记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11]卷1,p7由不同身份者细致分工所构成的完备进谏制度,只可能出现在“郁郁乎文哉”的西周时代。其中如瞽、史、师等职官,在《周礼》中都有记载。两种文献中记载的“瞽为诗”“瞽献曲”,指盲乐人以唱诗的形式讽谏天子,这是一种“乐谏”。宫廷中盲乐人的“唱诗”必然有一个前提工作,那就是“诗”的收集和汇聚,盲乐人的“乐谏”实际上是隐含着“采诗”内容的。将这个隐含式的前叙述揭示出来,建立起“采诗”“唱诗”“听诗观政”的“乐谏”程序,这是《食货志》“采诗”叙述的逻辑理路。从“采诗”到“唱诗”的中间环节,就是“献之太师,比其音律”。无论“瞽”还是“太师(大师)”,均为宫廷中的盲乐官,只是职责不同。“大师”属于高级乐官,从事为诗配音律和整理之事;“瞽为诗”“瞽献曲”中的“瞽”可能是唱诗的乐人,如郑玄所言:“凡乐之歌,必使瞽矇为焉。命其贤知者以为大师、小师。”[10]卷17,p1625
先秦和汉代的《诗》学论述是《食货志》“徇路采诗”说的又一依据。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西汉传《诗》的经学家,不论是当时已立学官的“齐、鲁、韩”三家,还是民间传述的《毛诗》,在论及《国风》时都不认为是采集而来的[12]。如对《关雎》的解说,《鲁诗》说:“周衰而《诗》作,盖康王时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韩诗》说:“今人君内倾于色,大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也。”《毛诗》说:“后妃之德也。”三家对《关雎》的作者和作意都指向上层,与民间无涉。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13]据此,西汉的《诗》学并不支持“采诗”说。但先秦诗学特别是出土的《孔子诗论》已经几乎明确指出“采诗”的存在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经学者鉴定确属先秦文献,时间可以上推到春秋时代,《孔子诗论》第三简论《邦风》,有“溥观人俗”和“大敛材”之说[14]。整理者认为,“敛材”是指收集邦风佳作,其实就是“采诗”[15];“溥观人俗”即根据《诗》观察民风民俗。《孔子诗论》可以说是明确支持“采诗”说的。那么,《食货志》“采诗”说确实受到“敛材”说影响了吗?《汉书·艺文志》“诗”类所收典籍未见此书,因此也不能论定班固受到了《孔子诗论》的影响。只能说先秦《诗》学中已有实质为“采诗”的论述了。
如果孔子关于《邦风》“大敛材”说对《食货志》“采诗”是否有影响难以论定,那么,考虑到《汉书》与《史记》的关系,《史记·乐书》的音乐观对“采诗”话语的影响更有可能。《史记·乐书》云:“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16]这里讨论的是音乐与政教之间的关系,其中提及雅颂之音、郑卫之曲,可知是以《诗》论乐的。因为各地民情风俗不同,通过广泛采集风俗之诗并以声律节制,付诸听诗审音,可了解民性民情民意以制定合理措施,在上裨益天子治理,在下教化民性。《食货志》“行人振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与《乐书》“博采风俗,协比声律”实质相同,仅表述不同。事实上,《乐书》论“诗”比《食货志》《艺文志》的“采诗”说包含着更丰富的诗学观念。《汉书》中的“采诗”说基本指向是天子治政,是对先秦“瞽为诗”“瞽献曲”所谓“乐谏”方式的延续书写;而《乐书》“以饰厥性”的说法兼顾了“博采风俗”的民性教化意义,这是《汉书》“采诗”说不曾触及的。
以上讨论了《食货志》将师旷引《夏书》“遒人振铎徇路”置换为“行人振铎徇于路以采诗”的历史依据和诗学背景。需要补充的是,《食货志》提出的“行人采诗”,据学者研究,周代的行人职官系统确实具备“采诗”的素质、条件和机会[17]。但《周礼》中并无明确的行人采诗记载,同时,“采诗”者身份在文献中记载不一,因此,《艺文志》笼统称为“采诗之官”而不再提“行人采诗”。设若班固完全肯定“行人采诗”,必然就不会有笼统的说法。班固虽第一次提出“行人采诗”说,但“采诗官”的说法更为后世所沿用,在元、白的新乐府理论中,反复呼唤朝廷重置“采诗官”,唐以后新乐府体或非乐府体诗歌中的“以俟采诗者”,就成为一个被不断表述的诗歌理想。
-
“行人振铎采诗”是“采诗”行为的描述,“采诗”说的核心在于彰明其功能和意义。《食货志》表述为王者不出户而“知天下”,这里应出自《老子》“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艺文志》对“采诗”功能定位更为明确、精要。《汉书·艺文志》云:“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18]“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指向王者治理天下,属于逐层递进的关系。只有在“观风俗”的基础上才可能“知天下”“知得失”,并进而制定和调整政治措施,实现“自考正”。据此,“采诗”的诗学核心可概括为“以诗观风”。《孔子诗论》“溥观人俗”,《史记·乐书》“博采风俗”已揭示了《诗》的观风价值,但这些可能并非《汉书》“采诗观风”说的全部依据和来源。
作为史学家和经学家的班固,曾参与白虎观经学会议,并奉命编写《白虎通》。经班固整理的《白虎通》“巡狩”篇引述了《尚书》和《尚书大传》的内容:
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尚书》曰:“遂觐东后,叶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尚书大传》曰:“见诸侯,问百年,太师陈诗,以观民命风俗;命市纳贾,以观民好恶。”[19]
《大传》的“观民风俗”与《艺文志》“观风俗”在文字表述上几无差别,“太师陈诗”则与《食货志》中“献之太师,比其音律”在“太师”这一关键人物的记述上完全一致。《尚书大传》本为今文经学的承传,考虑到班固与今文《尚书》的关系,可推测《艺文志》“观风俗”一说可能受到《大传》“陈诗观风”的影响。从“陈诗观风”到“采诗观风俗”,其间的逻辑关联在于“陈诗”的前提是“采诗”。“采诗”“陈诗”其实是一件事的不同阶段。但《食货志》《艺文志》的“采诗”联系着先秦的乐谏制度,属于天子听政制度,《大传》的“陈诗”事关天子巡守制,叙述语境不同。班固借用了巡守制记载中的“陈诗观风”话语,将其纳入到“采诗”功能意义的表述中。
“陈诗观风”说与天子巡守制文献记载的关系颇为复杂。天子巡守制最早见于《尚书》,但不见“陈诗”之说。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尧典第一·唐书》:“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20]此段文字孔颖达《尚书正义》列于“舜典”,所言帝舜巡守之事,同样未见“陈诗”。《史记·封禅书》引《尚书》,《汉书·郊祀志》引《虞书》,述天子巡守制与之基本相同。
天子巡守制的叙述中出现“陈诗”,是在《尚书大传》和《礼记·王制》中。《尚书大传》是今文尚书传承者伏生的弟子所述。《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列传》都记载了汉文帝时伏生教授《尚书》以及朝廷派晁错向伏生学习《尚书》之事。郑玄《尚书大传》“叙”曰:“生终后,数子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缺,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因经属指,名之曰传。刘子政校书,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21]1《汉书·艺文志》于“书”类著录《传》四十一篇,此即为《尚书大传》,这正是刘向校书时向朝廷所献伏生弟子所记述的《传》。《尚书大传》所述天子巡守才开始出现“陈诗”,《尚书大传·唐传·尧典》巡守事有数条,摘录部分如下:
五载一巡守,群后德让,贡正声而九族具成……乐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圣王巡十有二州,观其风俗,习其性情,因论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声八音七始。[21]6-7
古者诸侯于天子,五年一朝。见其身,述其职。述其职者,述其所职也。见诸侯,问百年,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俗,命市纳贾以观民好恶。[21]8
《大传》所述巡守事,既有舜帝巡守,也有泛论“古之天子”“圣王”巡守。郑玄于“因论十有二俗”句下注“今诗国风是也”,显然,他认为此处所论是周天子巡守事。加之其下又有“大师陈诗”之语,“大师”既为周代职官,所陈之“诗”也正是“诗三百”,所以《大传》论天子巡守事除舜帝外,当有更多周代之事。
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尧典》记载舜帝巡守并无“陈诗观风”,何以伏生传授、弟子张生和欧阳生记述的《大传》却有天子巡守“陈诗观风”之说?合理的解释是,《大传》在记载舜帝巡守事后根据先秦文献如《左传》《国语》等的记载,添加、补充了周天子巡守事,特别是提出了天子巡守的新的内容和意义,即“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俗”。这是今文《尚书》与《尚书大传》记述天子巡守事的不同之处。《尚书·尧典》这一文献,至少在战国前已有流布较广的定本[22],虽经后世整理增益,但保存的上古史料仍然很多,所记帝舜巡守之事应更接近历史。后出的《大传》有传述者加入的新内容,如王闿运《补注尚书大传叙》所称:“伏生所述,并孔为经。兼赅六艺,非唯书故。”[21]2既然“并孔为经”,就有可能将孔子所尊崇的周代制度纳入其中,《大传》出现周天子巡守“大师陈诗”之事应该是在传述过程中增加的。伏生于汉文帝时尚在世,伏生弟子张生亦为汉博士,追踪古制,为汉世制度建设提供历史依据,也是《大传》传述内容增加的现实原因吧。
《大传》“见诸侯,问百年”一段,很可能是《礼记·王制》“天子巡守”叙述的来源。《史记·封禅书》记汉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23],《汉书·郊祀志》有同样记载,说明班固认同此说。王闿运说:“大传之文,多入礼记。”[21]1产生于汉文帝时代的《王制》与《尚书大传》关系密切,学界多举《王制》篇中“大师陈诗观风”作为汉代“采诗”说之一,较少提及《尚书大传》,故特说明二者关系。
-
《汉书》“采诗”说有其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除了对周代采诗的追记外,《礼乐志》《艺文志》在汉武帝立乐府的叙述中再次出现“采诗”。《汉书·礼乐志》:“武帝定郊祀之礼,祀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24]《汉书·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25]这两条文献说明,武帝“立乐府”是为了服务郊祀之礼和朝廷新音乐的建设,采诗、采歌谣是这一时期乐府的新职能。作为一个音乐机关,乐府开展的两项工作,一是采集地方俗乐,用于“夜诵”,这是乐府援俗入雅之开端,后世此类做法颇多;二是为司马相如等所作新乐章《十九章》配曲。“夜诵”是郊祀活动的一种形式,“夜诵”有其依托的祭祀传统[26]。乐府中有专门的“夜诵员”,哀帝罢乐府时,这类人员属于雅乐乐人,因此得以保留。乐府采集“赵代秦楚之讴”用于祭祀,其他文献可以佐证。一是《史记·封禅书》记元鼎六年(前111) 李延年建议恢复郊祀之乐,公卿议论“民间祀尚有鼓舞乐”[27],既然朝廷音乐匮乏,新郊祀乐的建设就有可能吸收民间俗乐用以补充。二是《汉书·礼乐志》:“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28]班固批评武帝新乐从乐章到曲调皆不合古制。乐府既然参与了雅乐建设,“以郑声施于朝廷”就恐怕不仅仅是指乐府中的娱乐俗乐,而对于以俗入雅的做法,班固向来持反对意见。
有学者指出,这两条文献所言汉之“采诗”“采歌谣”,其实就是采集音乐和歌曲[5]。本文同意这一观点,进而认为乐府采诗与作为乐谏制度的古之采诗是不同的。“采诗”在历史与当代语境中的同时运用,虽然不能说是班固有意而为之的语言策略,但其结果便是很容易将汉之采诗与古之采诗视为同一性质的行为,汉乐府采诗遂上升至古之采诗的高度。《汉书》论行人采诗和古之采诗官,其意义指向采诗观风的政治目的,是对先秦文献中有关民间舆情收集记载的最终汇总。记述汉之采诗,则是在武帝定郊祀之礼、立乐府、制作新乐歌的礼乐文化建设背景中出现的。由古之采诗的制度形态到汉之采诗的音乐行为,这是不同性质和目的的两种“采诗”。学界多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作为西汉采诗观风之证据,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对地方风谣特征的说明,“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从文意和语气来看,“亦”字可解释为“同时也可以”,这是对乐府所采地方歌诗的补充性说明而非主导性评价。班固对汉乐府采诗主导性评价的缺失,是对新歌诗不满的反映。正因如此,班固才为新歌诗补充了传统意义,即古已有之的采诗观风,这是试图对古之采诗的意义回归。
如果说班固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汇聚出“采诗”这一话语,并将其调整、确定为一个有历史依据的制度形态,树立其权威性和典范意义,那么,这一话语的提取也许是有现实指向性的,即对武帝时代采集音乐和歌谣政治意义失落的潜在批评,是对采诗以补充郊祀之乐做法的不认可。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出自汉代文献的采诗说是汉人依据武帝乐府采诗行为联想而来的。情况可能正好相反。班固是以古之采诗作为依据,将表面相似而性质不同的两种音乐采集都名为“采诗”,从而以名实不符委婉批评汉之采诗。将“采诗”用于现实语境下的宫廷音乐,实际上具有否定性的话语暗示意义,当然,这种批评的力度是有意削弱的,即以“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作为功能性补救。
汉代乐府所采歌诗主要收录在《乐府诗集》相和歌曲中。这些歌曲中有一些反映家庭悲剧的歌诗,认为汉乐府采诗观风者以此作为证据。但汉相和歌中尚有夸耀富贵、描写游仙、抒发人生感慨、意在劝诫的歌诗,内容丰富,具有娱乐性和抒写情志的特点,就这些歌诗而言,若认为采集的目的在观察风俗、裨补时政,就太牵强了。以表现家庭悲剧的最合于观察风俗的歌诗来看,艺术形式已远远突破舆情需要。这类作品呈现的“戏剧化”场景,借助人物、情节、对话,在有限的艺术空间汇聚矛盾,意在强化艺术吸引力。显然,作为艺术歌曲的相和曲,其音乐意义压倒了舆情意义,音乐性是这些歌曲的本质属性,它们所提供的视听欣赏效果和情感撼动效果远远大于民情信息的获取。即便是那些反映鳏寡孤独群体生活现状及民生艰难的歌谣,一旦进入乐府提升为艺术歌曲,即会体现出一种宽泛的娱乐化特点,比如:听一个悲剧故事,引起情感触动;听一个富贵之家的故事,引起内心歆羡;听一个健妇持家的故事,引起赞赏愉悦;听一段游仙故事,飘飘然有凌云之想;听一段抒发人生短促的歌曲,引起伤感共鸣。汉乐府艺术歌曲的主要目的在于触动观者内心,或唏嘘感叹,或沉迷畅快,提供音乐娱乐和情志抒写。
乐府采诗即如东汉时代的乐府,因朝廷“观纳风谣”执政理念的影响,留意采集民生之作,但在进入乐府经过艺术加工后,其音乐娱乐功效成为首要考虑因素。自然,作为音乐机关的乐府采诗本是有历史依据的,周代“瞽为诗”“瞽献曲”“大师陈诗”等正说明采诗之事和乐官的关系。问题在于,瞽、大师的献曲陈诗行为主要出于政治目的,说明先秦时代诗、音乐与政教的密切关系。当这种关系在秦以后发生疏离之时,乐府职能就集中在音乐制作方面了,采集歌谣的政教意义实际上失落了。武帝时用于“夜诵”的赵代秦楚之讴是对民间俗乐资源的借用,这些歌诗有些在内容上可“观风俗,知薄厚”,但作为乐府歌曲的礼乐意义、音乐意义压倒政治意义。东汉朝廷重视采风,但乐府的采诗经过音乐形式的丰富和乐章歌辞的改造后,作为艺术歌曲的音乐意义也是首要的。据此,汉乐府的采诗行为已基本脱离了古之采诗的原初意义,放弃了古之采诗的政教目的。
除乐府采诗外,汉代还存在另一路径的采诗,这就是朝廷遣使巡行天下的采诗,学界以此作为汉代存在采诗观风的证据。对此需加分析。对比《汉书》《后汉书》可发现,《汉书》所记西汉遣使巡行之事很少,且未见采集风谣之举。《史记·平准书》记载武帝时期因吏民私铸金钱,“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国,举兼并之徒守相为利者”[29],这是为解决私铸金钱之事遣使巡行。《汉书·武帝纪》:“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鳏、独或匮于衣食,甚怜愍焉。其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30]这是遣使慰问弱势群体,并无广泛了解民情之意,也未提及采诗。《汉书·韩延寿传》记韩延寿治理颍川,曾“人人问以谣俗”[31],虽然重视据诗观风,但并非“采诗”。《汉书·王莽传》:“风俗使者八人还,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32]《汉书》所载“风俗使者”仅此一例。风俗使者“造歌谣”之事,当是王莽篡位政治计划中的一步,即制造民意。王莽爱好古制,遣风俗使者有其政治意图,也反映其依循古制的政治理念,此次“采诗”,不惟造假,且无关制度。
《后汉书》中巡行记载颇多,且明确有观纳风谣之举措。东汉光武帝起于民间,“广求民瘼,观纳风谣”[33],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33]。和帝时代“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34]。羊续拜为南阳太守,微服采问风谣[35]。可见,东汉以来,从朝廷到地方,观采风谣之事颇多,政治目的明确,与古之采诗接近。出于观风察俗目的的采诗,多涉及具体人、事,指向性明确,出现在相关史事记载中,是历史书写系统中的美刺歌谣。汉代朝廷采诗主要依托使者巡行天下的形式进行,是对古之采诗观风的继承,但这类服务于国家治理的采诗并未形成固定制度,因此也没有产生专门的歌谣集。朝廷和地方“观纳风谣”所采之诗,信息价值是第一位的,如果可满足观风察俗之政治需要,就没有更多理由一定要进入乐府配乐演唱。这类歌谣有其独立留存系统,并无证据表明朝廷的采诗与乐府机关的采诗之间存在沟通。
后人根据《汉书》有关乐府“采诗夜诵”的记述,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乐府采诗与古之采诗性质不同。《宋书·乐志》:“古者天子听政,使公卿大夫献诗,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秦、汉阙采诗之官,哥咏多因前代,与时事既不相应,且无以垂示后昆。汉武帝虽颇造新哥,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36]认为秦汉皆无“采诗之官”,朝廷歌曲与时事并不相关,因此也就丧失了古之采诗以观风的政治功能。中唐元稹、白居易也认为汉代不存在采诗官、采诗行为。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骠国乐》有云:“古时陶尧作天子,逊遁亲听康衢歌。又遣遒人持木铎,遍采讴谣天下过。万人有意皆洞达,四岳不敢施烦苛。尽令区中击壤块,燕及海外覃恩波。秦霸周衰古官废,下堙上塞王道颇。”[37]卷419,p4618白居易《新乐府·采诗官》有云:“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37]卷427,p4711从南朝到中唐,一致认为汉无采诗官,个中原因在于诸家是以观风察俗、有益王政的意义规定“采诗”的,并不认可乐府机关主要在音乐建设上的采集曲调和歌谣的行为。
-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如下三条结论:
第一,《汉书》“采诗”叙述属于汇聚型话语。这一话语的建构存在古史依据,即先秦文献中记载的天子听政制度、乐谏制度(献曲、献诗)以及天子巡守制度,也吸纳了先秦和汉代文献中的关键表述,包括《左传》载师旷所引《夏书》《史记·乐书》《尚书大传》中的提法。《汉书》中提出“行人采诗”“采诗之官”,突出了周代采诗活动,“采诗”的基本功能被表述为“观风俗”,其说为后世所沿用。
第二,《汉书》“采诗”叙述有其历史与现实语境。后者对武帝乐府采集音乐、歌谣行为的记述,实际上是一种话语借用,委婉批评作为音乐行为的乐府采诗对古之采诗的意义背离。东汉朝廷“观纳风谣”之举,属于另一途径的采诗。《汉书》对此不论,说明与乐府采诗并无沟通。
第三,《汉书》“采诗”叙述不仅是对先秦和汉代采诗活动的描述,且具有诗学意义。中唐元、白将“采诗”问题纳入到新乐府理论中,要求朝廷重置“采诗官”。宋元以来,新乐府体以及一些非乐府体的诗歌中频繁出现“以俟采诗者”的呼声,说明“采诗”已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诗歌理想,“采诗”问题作为古典现实主义诗学的价值得以彰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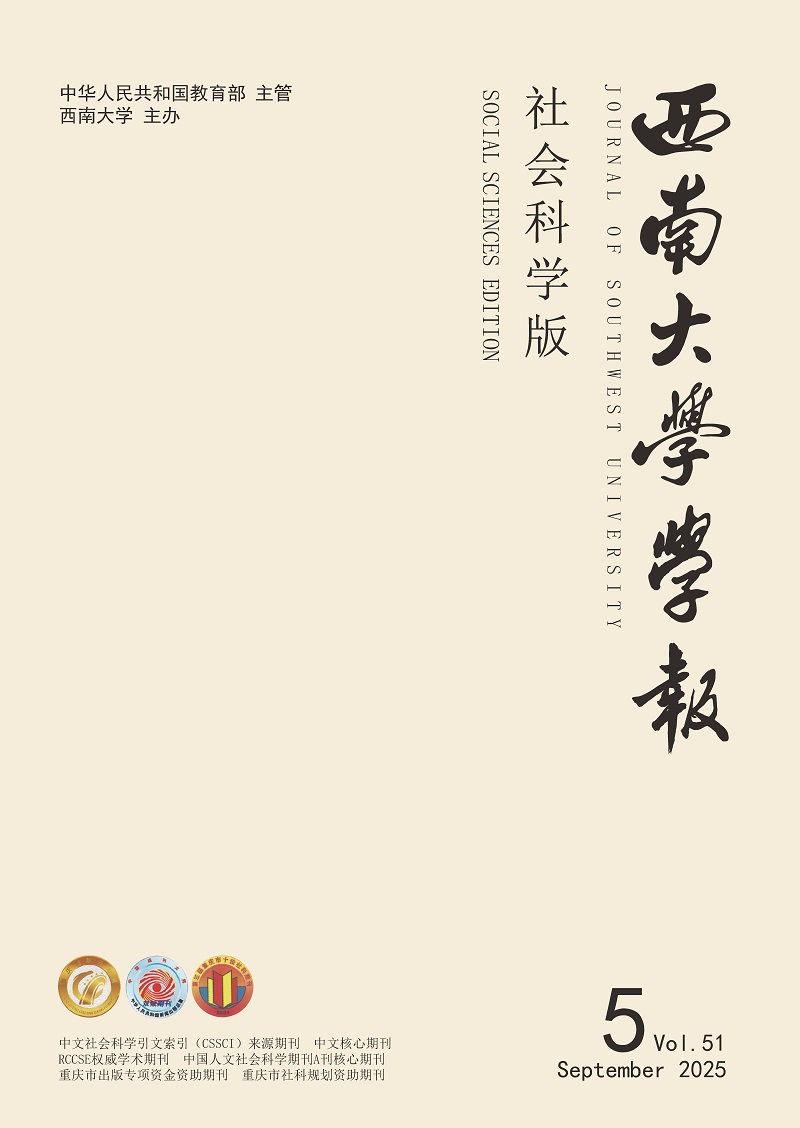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