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的既定关系是预先设定好的,所谓“兄弟怡怡”便是人们理想中的兄弟关系。然而,随着现代社会主体性的确立,传统社会的这种既有关系开始出现裂变,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周氏兄弟便是其中的代表。鲁迅、周作人兄弟(以下简称“周氏兄弟”)的失和时间是1923年7月19日。当日,周作人给鲁迅送来一封断交信,信中说:“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1]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对此表示不予辩解。鲁迅则仅在日记中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2]其他具体情形,作为当事人的周氏兄弟都没有更多的文字记载。许广平回忆鲁迅曾在信中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3],周海婴也认为鲁迅是被羽太信子赶出八道湾的[4]。有不少文章探讨了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但鲜有从现代社会主体性确立与传统社会关系裂变这一维度加以阐释的,尤其是没有据此拓展周氏兄弟失和对其文学世界建构的影响。
HTML
-
学界对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大体上形成了四种观点,即“家庭矛盾说”“伦理冲突说”“失敬说”“隐私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家庭矛盾说”。周氏兄弟的母亲鲁瑞说:“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贷,是不好的。”[5]101-102许广平描述鲁迅在八道湾生活的心情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之妇,日本人,名叫信子),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6]1126鲁迅三弟周建人回忆说: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300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着钱不够用[7]。鲁迅后来也针对经济问题感喟说:“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来了,生活才能够有点预算,比较不那么发愁了。”[6]1128这说明,鲁迅住在八道湾期间,其所挣的钱全部用在家庭开支上,还经常为生计犯愁,寅吃卯粮,自然谈不上所谓预算。这可作为周氏兄弟失和原因是经济因素的重要根据。
另一说法认为兄弟失和是两人性格乃至文化认同上冲突的结果[8]。杜圣修认为羽太信子的“癔病”是导致周氏兄弟产生误会的原因,进一步发掘导致“误会”的深层原因,得出了“周氏兄弟的失和与决裂……其更重要更深层的原因乃在于中国传统家庭制度”[9]的结论。此后,有学者把周氏兄弟失和置于“权威”的陷落与“自我”的确立这一视角,认为“周作人在‘五四’之后与鲁迅的决裂乃至日后对其持续不断的攻击,显然不仅仅由于兄弟二人在家庭矛盾或伦理冲突等方面的原因,而且也可能包含着周作人在‘自我’确立的过程中,释放其心理反抗的能量所汇聚的结果……而他的‘自我’也得以在此过程中逐渐确立”[10]。这样的解读深化了周氏兄弟失和这一本体研究的文化意蕴,使之超越了失和本体研究,深入到文化层面,对既有的本体研究具有推进作用。
持“隐私说”的学者认为周氏兄弟失和纯粹是当事人的隐私,不应过分深究:“周作人甚至撕掉了相关的那几页日记,说明这对当事人来说,纯属隐私,不应深究。”[8]或猜测兄弟失和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有关,或猜测两兄弟巨大的性格差异使然,都只是猜测而已,“隐私说”指向的正是人们猜测的“失敬说”“非礼说”。有学者针对这样的说辞认为:“从同时代的知情人,到数十年来的研究者,几乎都一致认为:此事是决不可能有的。‘失敬’云云,不过是信子的有意造谣、诬赖、诽谤。”[9]
无论“家庭矛盾说”“伦理冲突说”还是“失敬说”“隐私说”,兄弟失和至今依然是学界未解之谜。周氏兄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人物,兄弟失和不是一个或几个具体诱因导致的,应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不能寄望于用一两个因素来概括。除了兄弟之间因长期居住在一起引发的生活琐事矛盾之外,还有其深刻的文化因素。就其根本而言,周氏兄弟失和恰是周氏兄弟本身所张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延伸的自然结果,其本身具有历史的某种必然性和悖论性。周氏兄弟失和恰是两人从传统文化中走出之后确立了以五四新文化为圭臬的主体精神的必然结果,这种主体精神既体现在周作人身上,也体现在鲁迅身上。正是周氏兄弟作为矛盾的两方都坚持自我的主体性,毫无妥协余地,才导致兄弟失和无法转圜。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历史过程中,周氏兄弟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无法调节的矛盾,也发生在诸多其他具有血缘关系的兄弟身上。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兄弟失和对他们两人的情感和思想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其文学世界乃至人格世界的建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世界的建构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值得欣慰的是,当今学界已从周氏兄弟失和的具体考证中走出来,更多着眼于这一事件本身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荣挺进在搜集整理《晨报副刊》关于周氏兄弟失和的几则史料之后,提出兄弟失和事件是周作人思想转变的真正转折点以及成就其小品散文大师的“强力催生针”[11]。王宗凡等通过兄弟失和审视鲁迅的小说《孤独者》,与鲁迅因“兄弟失和”造成的心理创伤联系起来,尤其是通过对主人公魏连殳肖像、语言、细节等描写的分析,阐释了兄弟失和给鲁迅带来的巨大创痛[12]。张永辉通过对鲁迅作品《伤逝》《风筝》《颓败线的颤动》《弟兄》《采薇》等的分析,探讨兄弟失和后鲁迅思想的变化与精神境界的升华[13]。将作品分析与鲁迅人格结合起来,探讨鲁迅兄弟失和之后的思想境界和人格魅力,确实是较新颖的角度,但难免投射了太多作者个人主观性的认识,忽略了鲁迅自身一直存在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气质。还有学者通过分析鲁迅作品《风筝》《野草》《孤独者》《伤逝》等,深度阐释兄弟失和如何映射在不同作品中并对鲁迅心理和思想造成的巨大影响。周作人在写给曹聚仁的信中说,《伤逝》“猜想是在伤悼弟兄的丧失”,后来在回忆录中更明确地说他指的“不是早逝的幼弟,而是他自己”[14]。张钊贻认为,“两人思想本有的不同开始扩大,恐怕已使这位一直受大哥庇荫的周作人的内心深处,孕育着摆脱兄长‘控制’而走上独立自主道路的欲望。羽太信子对鲁迅的诬蔑正好符合周作人内心深处的需要……摆脱大哥,走自己的路”,因而面对羽太信子的诬陷,周作人“则毫不怀疑接受谎言,并于捏造未圆之处,加以救正”,最终得出“小说与鲁迅跟许广平的爱情发展有直接关系”[15]的结论,直接否定了周作人“伤悼弟兄的丧失”一说。不管《伤逝》是否像周作人所说“伤悼弟兄的丧失”,都不妨碍人们通过兄弟失和这一事件来阐释鲁迅作品。客观地说,这一事件必然对鲁迅产生某些影响,也自然会影响到鲁迅的文学创作。有学者在解读《祝福》时,侧重从“旧历年”“团圆”“仪式”等要素入手,通过结合鲁迅日记等方式,还原该小说的创作与鲁迅兄弟失和之间的关系,认为这部小说是借祥林嫂的死揭露社会秩序与人间关系在生活中的体现,认为《祝福》或许是兄弟失和后鲁迅自身处境的投射与象征[16]。这一分析注重把鲁迅作品置于鲁迅的真实生活语境之中,通过大量史料推测鲁迅的内心世界,对周氏兄弟失和的创作心理及思想性格转变进行系统梳理,为理解鲁迅及其作品提供了另一视角。
-
在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伦理法则中,“长兄如父”是父权关系的延展,父亲死后长兄替代父亲继续行使“父权”。传统社会尊崇“子孙繁衍”“多子多福”的观念又将亲情关系置于多种维度,使得家庭亲情伦理关系极其复杂,兄弟姐妹较多的家庭往往矛盾重重。如果说传统社会中“父权”尚能维系这种微妙的关系,那么五四以后“反抗父权”便将这种关系置于瓦解边缘。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谓“父慈子孝”“兄弟怡怡”是建立在“人”作为自我的主体性没有得到确认、个性意识没有觉醒的基础之上的,否则便很难做到“慈孝”“怡怡”。文学史上不乏诸多在“父权缺失”背景下构建起自身与新文学关系的例子,陈独秀、胡适、郭沫若、郁达夫等人都是如此。那么,作为“父权”延续的“长兄如父”又是怎样的情形?中国传统社会是怎样调节兄弟关系的?这种兄弟关系经历五四新思想后又是如何重构新的家庭伦理关系的?
不妨以最有代表性的儒家为例作一溯源。儒家文化针对社会各关系建立调节机制,将孝悌视为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前提,孝针对父子关系,悌针对兄弟关系,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悌。中国传统社会调适兄弟关系的机制,以长幼有序的伦理法则强调“兄为主,弟为辅”,兄拥有超越弟的权利,弟则在兄的规范、制约和庇护之下,兄弟表面上处于“怡怡”状态,矛盾冲突被表面的“和谐”所取代,“兄弟怡怡”确保了社会循着儒家规范的层级关系有序发展。五四新思想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局面,无论是反抗封建礼教陋习,还是挑战“父权权威”,都使原来的社会家庭伦理关系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在新观念的冲击下,体现家庭伦理关系的兄弟关系自然也受到威胁,作为建构主体意识的个体情感的发展,恰恰成为影响兄弟或家庭走向相同或截然相反的关键因素。
五四新思想的介入,使主体意识的建构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而接受文化的选择与方式又严重制约着独立个体思想的建构。从晚清到五四,中国传统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按照既有的规范和秩序发展的前提条件不复存在。五四以前,作为长兄的鲁迅在生活上给予周作人“父兄”般的照顾,还指导周作人求学、求业。从社会维度看,周氏兄弟在早期乡村生活中,兄弟关系奠基于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法则之上。父亲去世之后,鲁迅在家庭中承担起重要的角色。作为兄长,他不仅拥有更多的家庭责任,而且还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这表现在鲁迅既要为家庭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还要为家庭承担起融入家族、村庄乃至社会的使命,如鲁迅要到本家进行交涉等,这些工作都是周作人难以体察的。在此历史场域中,周氏兄弟的关系自然是兄长为主、弟弟为辅。如果将传统社会中习以为常的家庭伦理关系置于五四时期“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关系中,就会显示出其极不平衡的一面。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介入,兄弟都没有走出他们祖辈赖以生存的空间,则兄弟之间的关系将会循着既定法则继续维持下去。然而,周氏兄弟秉承的那种传统兄弟关系的前提条件已不复存在,基于传统的“兄弟怡怡”不仅有可能走向失和,而且还可能走向“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周氏兄弟作为从中国传统社会走出来的第二代学生,他们在接受了新式教育之后,已经确立起自我的主体意识,支撑起他们之间关系的基本法则不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既有兄弟法则。而是一种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平等法则,这就必然会颠覆既有关系,使传统兄弟关系出现严重失衡。虽然五四新思想对家庭伦理关系造成一定冲击,但并不是所有“兄弟怡怡”都会“反目成仇”。就中国现代文学史来看,“兄弟怡怡”者大有人在,如沈雁冰与沈泽民兄弟,潘梓年、潘菽、潘汉年三兄弟等。遵守父训坚持“实业救国”理想的沈泽民在兄长茅盾的引领和五四爱国运动感召下,转而走向文学启蒙与救亡之路,并在兄长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翻译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如《讨论进行计划书》《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潘氏三兄弟更是典型代表,“老大潘梓年,是新文化运动的马前卒,创办《新华日报》,被誉为中共第一报人。老二潘菽,是‘五四’运动的斗士,中国心理学的奠基人,‘九三学社’创始人。老三潘汉年,20岁当《革命军日报》主编,任过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17]。在新思想冲击下,作为“弟”的个体在自我主体建立的过程中,在文化思想精神等方面与“兄”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兄弟怡怡”也得以延续,并逐渐完成兄弟共同政治理想与文化立场的价值建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兄弟和睦的宗法大家庭固然是一种令人向往的形式,但兄弟独立门户也是无可避免的事情。一般来说,在父辈主导家庭时,那种四世同堂乃至五世同堂的场景是身居世俗社会中的人们所神往的。在家庭结构上,周氏兄弟把母亲接到北京之前,他们便是一个由母亲支撑起来的大家庭,而他们的小家庭依然寄寓在这个大家庭之中。在把母亲接到北京之后一直到兄弟失和的这段时间里,他们依然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只不过这个大家庭是一个脱离了乡村与宗族制约的大家庭。鲁迅在变卖绍兴的族房时,家庭的经济权力主要在其母亲手里,后来则到了周作人的夫人手中。正如周建人所说:“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18]在传统伦理观看来,大家庭的一切权力应该归兄长所有,即便不归兄长所有,也难以轮到身为弟媳的信子。这便埋下了大家庭分崩离析的隐患。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周氏兄弟走出绍兴之后,建立在既有社会秩序法则之上的兄弟关系失去了应有的效能。这样,缺失了旧有社会规范制约的兄弟关系便显得愈发脆弱,不堪一击。
从中国传统家庭的发展规律来看,兄弟之间最终要独立门户。当既有的家庭分蘖为诸多小家庭时,兄弟分家、独立门户便是早晚的事情。实际上,独立门户不仅意味着兄弟之间从经济上割断了同胞关系,还意味着在社会地位、政治文化思想上也确立了自我独立的人格。至于在独立门户的过程中,如果兄弟之间的关系依然处于一种“怡怡”的状态,则意味着“兄友弟恭”的法则仍在起着应有的作用;如果兄弟之间的关系处于“失和”状态,则意味着“兄友弟恭”的法则已难以发挥作用。周氏兄弟的失和恰是这种兄弟关系逸出了传统“兄友弟恭”法则的某种结果。而这一切又与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确立了不同的主体性有一定关系。对此,站在传统文化立场上的周氏兄弟的母亲鲁瑞感到无法理喻:“这样要好的弟兄却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5]101
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法则无法有效阐释的兄弟失和事件置于五四新文化这一视角上透视,便会发现,周氏兄弟失和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的主体意识得以觉醒、个人从家庭这一物理空间的羁绊中走出并最终确立不同的主体性的历史必然,而且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带有某种普遍性的文化现象。固然,周氏兄弟在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而其失和的价值和意义便得到了格外的关注。其实,周氏兄弟失和仅只是这一历史时期诸多兄弟失和中的一个典型个案,类似实例比比皆是。只不过有些兄弟之间的对峙相对温和一些,如胡适、郭沫若、郁达夫、巴金等与兄长的关系;有些兄弟关系的对峙相对尖锐一些,如殷夫与其兄长徐培根、山东相州王氏家族三兄弟(王愿坚、王希坚、王意坚)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兄弟之间的关系应是兄为主、弟为辅,兄长的意见相对于弟弟而言并不是仅供参考,严格说来,在父权缺失的情形下,兄长具有支配弟弟行为的绝对权力。弟弟背离兄长的意见本身即便算不上“大逆不道”,起码也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但在新式教育的熏陶下,许多弟弟最终走出了兄长为其设定的人生藩篱,走上了一条迥异于兄长认同的人生道路,这虽然不一定会完全导致兄弟失和,但已绝不再是那种“兄弟怡怡”的传统关系所能涵盖的。
胡适的兄长期待他在铁路、矿冶方面有所建树,因此,为避免兄长失望,胡适以出国学习农业为己任,打算走“实业救国”之路,并由此获得了兄长们的认同。出国之后,胡适的主体性逐渐确立,最终走上倡导新文化的道路,成为开一代文学风气的人。同样,郭沫若后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也与兄长为他设计的人生之路截然相异。郭沫若的大哥郭开文是四川首批新式学堂的学生,对郭沫若接触新式教育起了重要作用。对此郭沫若曾回忆:“新学的书籍就由大哥的采集,像洪水一样,由成都流到我们家塾里来。甚么《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书报差不多是源源不绝地寄来,这是我们课外的书籍。”[19]但在郭开文心中,他更注重“富国强兵、实业救国”。日本现代医学作为迥异于中国医学的现代科学,具体展现了“实业”形象,学成回国后既能够谋取一个职位,为家庭解忧排难,也能够救治病人,为国效力。为此,郭沫若准备听从大哥的话到日本学医。但他最终还是背离了大哥为其设计的人生之路,走上了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的道路。
郁达夫的出国留学依托其兄长提携,其学医选择最初也是由兄长设定的,正如其自传体小说《沉沦》所表白:“他考入预科的时候,本来填的是文科,后来将在预科卒业的时候,他的长兄定要他改到医科去,他当时亦没有什么主见,就听了他长兄的话把文科改了。”[20]50后来,“他同他的北京的长兄,为了一些儿细事,竟生起龃龉来。他发了一封长长的信,寄到北京,同他的长兄绝了交”[20]63。郁达夫坦承,“其实这一次的决裂,是发始于他的”[20]63。这恰是其自我主体意识确立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他因为想复他长兄的仇,所以就把所学的医科丢弃了,改入文科里去。他的意思,以为医科是他长兄要他改的,仍旧改回文科,就是对他长兄宣战的一种明示”[20]64。郁达夫在此所明示的“宣战”,既有青春期反叛的因素,更有主体意识确立之后强调自我人生设计的因素。事实证明,郁达夫从想复他长兄的仇出发,最终走上文学道路。巴金走上文学道路也同样是背离了兄长为他谋划的人生道路,从兄弟人生发展道路来说可谓另一种形式的“失和”。出国前,巴金的兄长便为其谋划了一条“学一门学问”的人生之路,但他却背离了“家里的人又再三叮嘱”的路,“偏偏走了没有人给我安排的那一条”[21]。为此,他走上了小说创作之路:“为了自己(正如我在‘序言’中所说是写给我底哥哥读的),为了倾诉自己底悲哀而写小说。”[22]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申诉自己的悲哀的小说,竟然引起了时代的共鸣。巴金正是缘于他走出国门之后确立了自我的主体性,最终挣脱了包括兄长在内的家人的羁绊,进而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传统家庭关系中的“兄友弟恭”逐渐被消解,与此同时,随着外来文化思潮的影响,个人的主体性意识逐渐增强,不仅冲击了传统家庭的旧式关系体系,而且“骨肉亲情”的血缘关系也受到严重威胁。类似于断绝父子关系、兄弟反目并绝交的情形时有发生。最典型的莫过于殷夫与其兄长徐培根。左联诗人殷夫的大哥徐培根是国民党党员、高级将领,与弟弟站在两个截然对立的阶级立场,由此成为势不两立的兄弟。面对弟弟走上对抗国民党的道路,徐培根给殷夫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劝告信。殷夫不仅婉拒了兄长的“好意”,而且写了《别了,哥哥》一诗回复兄长,旗帜鲜明地表白了自己与兄长势不两立的阶级对峙,由此使得兄弟失和上升到了“向一个阶级的告别词”的高度。殷夫这样写道:“你诚意的教导使我感激,/你牺牲的培植使我钦佩,/但这不能留住我不向你告别,/我不能不向别方转变。”“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23]通过殷夫与哥哥的决裂可以看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兄弟失和还停留在文化理念深层冲突上的话,那么,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开始反抗国民党统治时,兄弟失和已不再停留于文化理念层面上,更进一步延展到政治信仰层面,甚至上升到了各自“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的层面。这便把兄弟失和推到了历史的极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已经确立了自我主体意识的个体,他们推崇的不再是那种“温情脉脉”的血缘关系,而是推崇政治上的志同道合。他们以自我所皈依的文化、政治等意识形态为导向,冲破了既有的家庭乃至家族的藩篱,由此而使得兄弟失和演变为兄弟之间的政治对抗,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面貌。周氏兄弟失和如果说发生于家庭内部的话,那么,有些基于血缘关系的兄弟则发生于家族之内。这种情形是家庭内兄弟失和的扩展形式。这种家族内部的兄弟失和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不乏其人,其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诸城相州镇的王氏兄弟,既有走上革命道路的王愿坚、王希坚,也有跟随国民党的姜贵(王意坚)。这三位“坚”字辈的“王氏家族三兄弟”,最终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他们已经不再是兄弟失和,而是直接的政治对峙与军事对决了。这便使文学由此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然而,“文学打上政治的烙印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文学的萎缩,但是,文学一旦成为政治的战斗武器,文学自身的属性便退到次要的位置,而文学的工具功能则得到了充分的发挥”[24]。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兄弟失和乃至兄弟对峙的情形还有很多,只不过周氏兄弟因在新文化运动中累积起了更大的社会声望,其兄弟失和更具有典型性罢了。在自我意识觉醒、个性主义开始张扬的现代社会,兄弟之间要再回到传统社会“兄弟怡怡”的状态,已经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实际上,不仅兄弟之间难以进入那种“兄弟怡怡”的状态,而且个人也难以进入那种“自我融洽”的状态了,这正如鲁迅所说:“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25]338在此情形下,我们再指望醒来的自我泯没个性顺从他者的意愿,单就自我的平衡来说已无法实现了,这也正是现代知识分子觉醒之后自我产生严重冲突的症结所在。在此意义上说,已经确立起了主体性的自我都难以达到平衡的状态,更何况觉醒的自我与其兄弟的平衡状态了。因此,我们对周氏兄弟的失和应该抱有“同情之理解”的态度,既不要惋惜他们从“兄弟怡怡”走向“兄弟反目”,也不要过分执拗于在兄弟失和这个问题上到底孰是孰非等所谓的终极价值判断。换言之,确立了自我主体性之后的兄弟失和是自然的,而他们继续保持“兄弟怡怡”反而是不自然的。这正应了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说:“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26]对周氏兄弟而言,在踏上了新式教育的征途之后,身处同一阵营的兄弟也许并没有想到,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节点上,因为某种偶然因素,兄弟最终走向失和,由此造成了与他们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
周氏兄弟失和是五四以后作为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中的人确立自我主体性的映射,也是中国社会伦理关系复杂局面的一个缩影,更是一种值得深入探究的社会现象。兄弟失和相对于周氏兄弟而言不仅不是悲剧,恰恰最终确立了自我的主体性。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兄弟失和或兄弟背离等现象,正是历史的车轮开动起来的表征,五四之后,新型家庭社会关系在历史的变迁中逐渐确立,标志着一个从未有过的新时代已经悄然而至。
-
兄弟失和对周氏兄弟各自主体精神和主体情感世界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造成的精神创伤和情感创伤也是难以愈合的,由此改变了他们两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进而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文学世界建构。具体来说,这对他们文学世界建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兄弟失和不仅使周氏兄弟情感破裂,而且改变了各自人生的发展轨迹。兄弟反目成仇,产生心理隔膜,各自人生场域拉开了一定的物理空间距离,使得周氏兄弟的文化坚守及其所皈依的文化道路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从历史发展来看,周氏兄弟早期所呈现出的“兄弟怡怡”之情,是因为两人的心理距离较近,甚至可谓志同道合,远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兄弟关系。鲁迅长周作人4岁,自然较之弟弟的社会化程度要高出一个层级,这就使其在早期的社会化过程中领先一步,并为周氏兄弟早期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种差异性还不足以发展到截然不同的层级,由此奠定了他们“兄弟怡怡”的生理基础。实际情形也的确如此。鲁迅与周作人在发蒙阶段,都受教于私塾先生,其身份甚至带有同学的性质,尤其是他们还曾一起赶考。且不说周氏兄弟的科举考试成绩孰高孰低,单就赶考本身来说,便天然地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鲁迅在南京求学后,周作人紧随其后到了南京求学,他们又先后到日本求学,这些经历不仅使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具有某种同构性,而且还使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具有统一性,这就为他们兄弟之间建立起平等而密切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周氏兄弟在个人社会化进程初步完成之后,那种兄强弟弱的态势便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扭转,这也为周氏兄弟的最后失和做了铺垫。在周氏兄弟离开绍兴之后到出国之前这段时间,周作人的社会化多是依赖鲁迅提携;留学日本之后,周作人逐渐确立起自我的主体性,这不仅体现为周作人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世界观,培育了自己的文学观,而且还建构起了自我的情感世界。这就使得周作人基本上走出了兄长的世界,开始了自我独立世界的建构。在婚姻问题上,作为兄长的鲁迅并未能主导自我的爱情与婚姻,最终屈从于母亲的意志,娶了自己并不喜爱的朱安女士,这使鲁迅的情感受到了严重伤害,长期无法得到治愈。有学生回忆说:“因为朱安和鲁迅一直是分居的,进鲁迅的书房要经过朱安的卧室,有一次几个学生开玩笑把鲁迅推进了朱安的卧室,笑容可掬的鲁迅出来之后怒不可遏,斥责学生说以后不准再开这样的玩笑。”[27]这一时期,鲁迅在给一个青年的回信中也深有同感地写道:“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25]337这说明,因为爱情缺失而导致的婚姻悲剧已成为鲁迅无法排遣的情感郁闷,也是其精神创伤迟迟得不到愈合的重要缘由。与鲁迅带着深深的精神创伤截然不同,周作人则建立了一个由自己主导的情感世界,他未曾经历过鲁迅那样的精神创伤。如果说在前期的社会化进程中周氏兄弟所走的人生道路基本相似,那么在周作人进入婚姻世界之后,他们深层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则循着截然不同的路径建构起来。这深刻影响了周氏兄弟之间的关系。在失和之前,周氏兄弟之间尽管并没有割断经济上的家庭联系,但在文化上却再也无法重拾那种其乐融融的手足情了。
鲁迅与周作人的兄弟关系,本应随着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声名鹊起而变得更加紧密,但实际情形恰好相反,他们的关系不仅没有更密切,反而走向了兄弟失和,这深刻影响了周氏兄弟各自的人生地理空间展开,也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鲁迅离开北京南下重新找寻自我人生赖以展开的地理空间,便与这种影响有一定的关系。鲁迅南下固然是多方面因素所促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已不复存在那种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有关,也与南方兴起的革命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中心南移有关;但他的南移还与所面临的独特困境有关,即与兄弟失和有直接关联。鲁迅在兄弟失和之后虽然搬出了八道湾,远离了周作人等家人,但由此情感上产生出犹如置身于荒原的感觉。从对抗这种人生体验出发,蛰伏于鲁迅情感深处的情愫得以复苏,鲁迅与许广平开始了相恋相爱的诗意人生。从对抗兄弟失和以及旧式婚姻的束缚出发,在完成了自我心理空间上远离周作人等家人的同时,再从物理空间上远离北京便成了鲁迅的不二选择,最终在上海长期租住下来。这种人生地理空间的选择对鲁迅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氏兄弟失和不仅对鲁迅的人生地理空间形式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周作人的人生地理空间形式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兄弟失和之后,周作人成为八道湾这个大家庭的主人,限定了周作人未来人生的地理展开空间。
在日军逼近北平之际,周作人未随南下师生一同进入大后方,因素固然很多,八道湾这个大家庭无疑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起码是对周作人的南下愿望起了延宕作用。这与周氏兄弟失和具有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当兄弟失和后的周作人日渐成为八道湾的留守主人后,八道湾对周作人来说已经不再是激励人生的物理空间,反而成为一种人生的累赘。这给周作人被拉下水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如果对那些身在沦陷区的文化名人加以考察便会发现,很多人为了保持个人名声,或采取隐姓埋名方式,或逃出沦陷区进入大后方;那些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文化名人要想保持民族气节,则要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么为求瓦全而舍弃民族大义。许多文化名人在这种生死抉择中选择了苟且偷生,走上了附逆的人生不归路。周作人在有可能南下的条件下,依然选择了滞留北平,固然由众多因素促成,但兄弟失和之后的八道湾大家庭的主人这一特殊身份,对其选择滞留北平还是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周作人在选择附逆之后,原来那种五四新文化战士的形象不复存在,所以,他只好躲在所谓的苦雨斋中谈天说地,这便促成了其文学创作转向没有多少战斗性的散文文体,而其早期的那种针砭时弊的杂文不复存在。此时的周作人,已经走上了一条完全背离其兄长鲁迅的人生之路和文学之路。遗憾的是,周作人走的这条路却是其人生和文学的不归路。
其二,兄弟失和致使在精神和行动上完成了“弟”对“兄”的完全脱离,从而促成周氏兄弟更加清晰地厘定自我的文化定位和文化立场,并以其各自皈依的角色身份拓展自我的文学空间和社会政治立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氏兄弟既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也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冲锋陷阵者和新文化遗产的受益者。这场新文化运动使得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周氏兄弟声名鹊起,成长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鲁迅担任教育部佥事,他身居官场,日常处理的大都是公务,日常接触到的大都是同事,这使鲁迅对生活感到厌倦和寂寞。为此,他投入钞古碑等工作,这种生活与鲁迅在东京留学时的文学梦相去甚远。东京时期,鲁迅就渴望从事文学创作,希冀自己的文字一经刊发便备受关注,正如他后来在回忆中所陈述的那样:“振臂一呼应者云集。”[28]但实际情况并不尽然。当他抱着启蒙的愿景翻译了《域外小说集》时,却竟然反响寥落,且不说应者云集,即便是起码的阅读者也不多,卖出的作品甚少,甚至连投入的本钱都没有收回。这种情形严重挫伤了鲁迅的文学创作激情。鲁迅回国后,尽管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教师,但时间不长便进入教育部,这使鲁迅与青年学生失去了接触的机缘,青年学生也难以获得认同乃至推崇鲁迅的渠道。这种情形随着鲁迅被有些学校聘任为兼课教师而有所改变,但从根本上说,作为兼课教师的鲁迅自然无法像身为教师的周作人那样,与学生有着长久的接触时间,其所拥有的学生拥趸以及志同道合的同人自然比周作人要少。有人回忆,周作人过年时,前来拜年的人高朋满座,鲁迅那里则寥落得很。这说明,周作人作为弟弟已“长大成人”,其社会地位和声望还大有反超其兄长的态势。这种冷暖对比在鲁迅本来就寂寥的情感世界里更增加了一分寂寥。
鲁迅是一名真的勇士,尽管会有“彷徨”,但更多的是“呐喊”。他敢于直面真实的人生,不管是进入“有物之阵”还是“无物之阵”,都抱着决绝的态度,毅然决然地前行。正是由此出发,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才动情地写道:“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29]作为真的猛士,鲁迅始终不宽恕任何一个怨敌。他在带有遗嘱性质的《死》中这样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30]鲁迅所说的“一个也都不宽恕”自然也包括周作人在内。与其他怨敌不同的是,周作人是怨敌,更是其血浓于水的胞弟,鲁迅与周作人的恩怨自然要比其他怨敌带给鲁迅情感与思想的影响要深刻得多,对鲁迅所建构的文学世界的影响自然也要深刻得多。
兄弟失和之前的周作人之所以能够进入北京大学任教,与鲁迅的提携分不开。在进入北京大学之前,周作人曾在浙江从事教学工作,尽管他也从事散文写作,但其影响相对有限。进入北京大学之后,周作人迅疾汇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和推动者的队伍,很快进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沿阵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周作人撰写的《人的文学》等文章,在理论上深化了五四新文化的思想,对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到了理论指南的作用。在诸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拥趸那里,周作人是与陈独秀、胡适齐名的理论先驱。当然,周作人的与众不同在于,他不仅是一位理论上卓有建树的倡导者,而且还是一位在文学创作实践上颇有影响的散文家。这一双重身份使得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成为深受学生崇敬的学者式作家。周作人不仅获得了更为显赫的学术影响力,而且还在文学创作上得到了众多学生的拥戴,并逐渐成长为京派的代表性人物,深刻地影响了废名等人的文学创作。
随着思想和情感的日渐成熟,周作人已不再是被兄长鲁迅遮蔽了光芒的小弟,而是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士,是引领思想解放的先驱,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对此,不妨结合鲁迅当年到中山大学任教时的一个海报加以说明。1927年,中山大学组织者在《民国日报》刊出鲁迅将要演讲的新闻,题目用了“新文学巨子”的这样的定语来修饰“鲁迅先生”,正文则说:“新文学大家鲁迅先生,即周树人,浙江人,为作人先生之令兄。其杰作如《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史略》,久已风行于世,而《阿Q正传》一篇,且译有三国文字,法文学家罗曼罗兰氏深为倾倒。”[31]这则演讲消息本意是招揽听众、提升学校声誉,对主讲者鲁迅不吝赞誉之词,难免会有夸饰之嫌,但就其根本来说,还是做到了“确有其事”。当时,鲁迅已经凭借新文学创作获得巨大声誉,称其为“新文学巨子”也不为过。而颇具意味的是,为了提升鲁迅的知名度,消息发布者还特别将鲁迅是周作人兄长的身份凸显出来。不难推断,作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周作人在学院内比鲁迅的学术声誉还要显赫[32]。由此看来,周作人在社会上享有较高声望,这种情形自然能助长周作人的自我意识逾越既有兄弟关系的藩篱,在完成对自我的文化定位的同时,促成了自我主体意识的最终确立。这也为与兄长鲁迅分庭抗礼埋下了伏笔。
自我主体意识的确立对个人“长大成人”固然有着不容小觑的价值和意义,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这种自我意识超越了一定的“度”时则会走向其反面。周作人的自我主体意识的得失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在确立了自我的主体意识、走出了长期以来被其兄长鲁迅所遮蔽的人生场域之后,周作人在文苑里自由驰骋,越来越走向了鲁迅的对立面,以至神往于日本的新村运动,甚至投向了日本人所谓的“东亚文化”。这正是周作人的自我主体意识在确立之后最终又走向迷失的真实写照,其端倪在兄弟失和中便开始显现出来了。
其三,不同文化立场对个性精神独立的渗透,致使周氏兄弟在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唯物史观等方面差异越来越大,越走越远,甚至发展到难以兼容的程度,这些变化无一不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散文和杂文文体的创作产生深刻影响。
周氏兄弟在失和之后,尽管“老死不相往来”,但他们在各自的文化世界和情感世界中占据的位置并没有随之而烟消云散。相反,兄弟失和本身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各自独立的文化诉求,使他们以对方为镜像,更加自觉地建构起属于自我的文学世界。如鲁迅依然关心甚至担心周作人能否在抗日救国之类重大事件上经得起历史的考验,1935年让三弟周建人转告周作人:“遇到抗日救国这类重大事件,切不可过于退后。”[33]对于周作人的文学创作,鲁迅并没有因为兄弟失和而彻底拒绝,相反,他还特别关注乃至关心周作人的文学创作,以至于周作人每每出版新作,必定会托人买来细读,据许广平的记录说:“对于他的创作,话又说回来,鲁迅虽然在上海,但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他的确是这样,不因为兄弟的不和睦,就连他的作品也抹煞。每逢周作人有新作品产生,出版了,他必定托人买来细读一遍,有时还通知我一同读。如1928年9月2日,日记上也曾记着:‘午后同三弟往北新书店,为广平补买《谈虎集》上一本,又《谈龙集》一本’。又1932年10月31日,买‘周作人散文钞一本’。”[34]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对周作人的文学创作仍然能够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正是基于这一点,鲁迅的文学创作才不会自我封闭,更不会剑走偏锋,而是循着正确的道路发展。
周氏兄弟失和对鲁迅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成了鲁迅的文学创作向杂文的偏重,杂文创作成为压倒其他文体创作的最重要的创作形式;二是使鲁迅早期那种更加关注社会现实的小说创作出现了偏转,开始了历史小说创作。1926年下半年,鲁迅放弃北京教育部公职,应聘到厦门大学担任专职教师,鲁迅小说创作开始转向历史题材。《故事新编》收录8篇小说,其中,创作于北京时期的仅有《补天》(1922年11月)一篇。此后,鲁迅在北京蛰居期间再也没有创作历史小说,而是关注社会现实的小说;但鲁迅离开北京之后,便于1926年10月创作了历史小说《铸剑》,两个月后的12月,又创作了历史小说《奔月》。此后,鲁迅主要精力放在杂文创作上,1934年8月,鲁迅才又创作了《非攻》,在1935年11月创作《理水》。1935年12月,鲁迅历史小说创作进入集中爆发期,相继创作了3篇历史小说即《采薇》《出关》《起死》。当然,鲁迅之所以相继创作3篇历史小说,和他要编历史小说集有直接关系。但从创作轨迹来看,这一时期鲁迅之所以把原未发表的《理水》《采薇》《非攻》《起死》4篇一并编入《故事新编》,恰好说明鲁迅在从事历史小说创作时抱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也能从另一维度说明鲁迅为什么会远离现实题材小说创作。其实,如果认真分析鲁迅的历史小说创作便可以发现,这些历史小说均打上了杂文的某些烙印,具有鲜明的杂文特质。对此,我们不仅要问,鲁迅创作的历史小说到底是先有了杂文的文体自觉然后才借助历史小说呢,还是先有了历史小说的文体自觉然后自觉输入了杂文的特质呢?本文认为,这一时期鲁迅创作的历史小说更多地带有杂文文体的某些特质,也就是说,鲁迅的历史小说创作属于借助历史题材从事的另一种形式的杂文创作。这正如鲁迅自己所说,“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35]。鲁迅在此使用的这一抓住一点铺排开去的文学写作笔法,恰是其杂文写作常用的笔法。
当然,周作人对鲁迅的文学创作尽管没有像鲁迅对他的文学创作那样关注,但也并没有完全置于其阅读视野之外。这表现为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走上了不同的文学道路。与鲁迅选择的杂文创作迥异,周作人逐渐走上了散文创作道路,更多地呈现为“平和冲淡”,这已经与其早期的“浮躁凌厉”有了很大区别。周氏兄弟因为在“浮躁凌厉”上既有性格气质类型的同一性,也有文化认同上的同构性,他们这对“好兄弟”开始“失和”便有了某种必然性。关于“浮躁凌厉”,周作人自己毫不讳言:“我其实倒还属于好事之徒一类的,历来因为喜欢闹事受过好些朋友的劝诫,直到现今还没有能够把这个脾气改过来,桌上仍旧备着纸笔预备乱写。”[36]基于这种“好事”的脾气,周作人撰写的文章大都触及社会“痛点”,引发人们关注:“我这些小文,大抵有点得罪人得罪社会,觉得好像是踏了老虎尾巴,私心不免惴惴,大有色变之虑。”[36]但周作人后来的文学创作逐渐脱离了这种战斗精神,开始向“平和冲淡”发展,甚至在文化认同上产生了某种偏差,如他认为“中日同是黄色的蒙古人种”,文化同一,“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37],在民族对峙的特殊时期,周作人的这种认同即便没有政治企图,起码也不符合现实情景,毕竟所谓“同种同文”的大和民族,并没有与我们命运一致,相反,我们民族的悲惨命运倒是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当然,周作人之所以走向这种极端的道路而不自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追根溯源,兄弟失和之后的分道扬镳不能不说是其中原因之一。
-
总的来看,如果从现代社会的主体性确立与传统社会的关系裂变维度,审视周氏兄弟失和便会发现,随着传统社会关系尤其是随着传统家庭关系的解构,“兄弟失和”已经成为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时期的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周氏兄弟失和不仅有其自身的原因,而且还具有时代的烙印,可谓是在文化转型时期的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冲突范式。实际上,自我主体性的确立和张扬,恰好带来了兄弟关系的深刻变革,由此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附属关系推进到平等关系,且无论是传统社会家庭关系的解构还是重构,都与五四以来新思想的传入是分不开的。同时,兄弟关系作为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的体现,对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代兄弟关系的建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从某种层面上对中国现代文化格局的确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这样的意义来看,周氏兄弟失和不仅承载着兄弟是非恩怨的个人历史,而且还折射了时代文化的变迁史,其在文化史上具有一定的的价值和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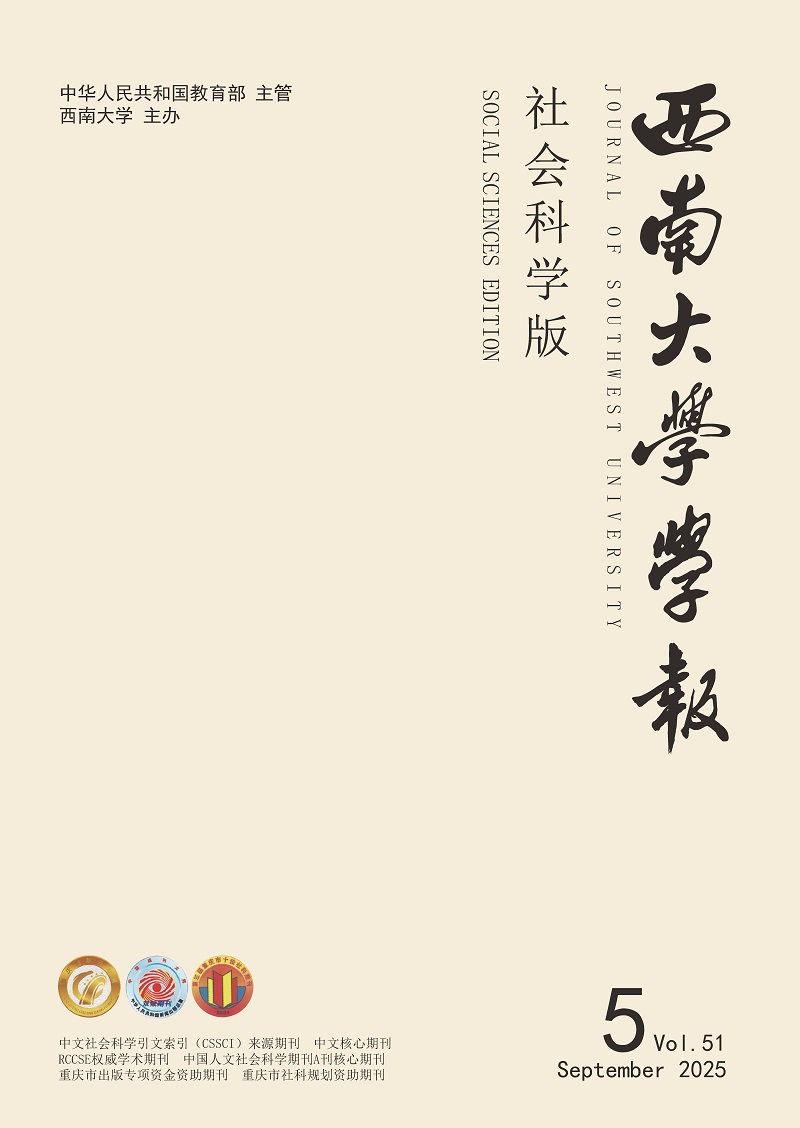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