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ML
-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乡土中国走向城乡中国的进程中。在中国基层社会版图中,城市社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城乡基层治理面临着新形势和新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要明显提高[1]。如何在城乡中国的时代背景下完善中国基层治理体系,弥补基层治理短板,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城市社区的空间形态是城市化过程塑造的产物,它迥然有别于村庄自然演化的空间形态。尤其是在城郊地带上演的城乡“拉锯战”深刻地塑造了城市化过程中社区的空间形态和治理格局,凸显了城镇治理的空间基础和空间生产的城乡联动,空间因而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属性。
事实上,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2],它不仅是治理的基础和对象,而且是权力实践的媒介[3]。而城市化是塑造空间的力量,为空间的反思性研究提供了经验基础[4]。当前城市空间研究主要沿着空间生产的市场逻辑与制度逻辑展开,分别呈现了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分化。一是空间生产的市场逻辑。中国城市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是影响城市空间的重要因素,并产生了社会分异[5]。不同阶层的居住空间与社会分层结构表现出高度的一致与契合,呈现出空间区隔与阶层隔离的特点[6-7]。另有学者进一步从“隔离社区”的视角揭示城市的空间分异,认为其代表着一种城市空间私有化的生活方式[8]。城市空间分异与空间区隔导致城市公共空间的失落[9]。二是空间生产的制度逻辑。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地开发导致人口城市化滞后于空间城市化,可能产生社会风险[10]。有研究者提出“半城市化”概念来概括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不协调的状态,认为在部分区位、禀赋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普遍发育形成的“似城非城”的空间格局实际上是大都市辐射、乡村工业化、城乡二元体制等多因素复合作用的产物[11]。“半城市化”导致“社区碎化”的空间格局。对此,有研究者基于规划的政治属性提出“空间治理”的可能路径,以促进城市更新和社区整合[12]。
可见,既有研究分别从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等不同层次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分化逻辑。以上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预设了城市空间的自主性,将城市空间视为资本与市场自由支配的要素。以此为参照,“半城市化”的空间破碎状态主要源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束缚,破除城乡二元制度壁垒因而被视为畅通城市空间转型路径、促进空间治理的出路。问题在于,既有研究忽视了土地的经济属性与空间属性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不兼容性。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土地本身不可移动,土地的经济属性与空间属性存在结构性张力,而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放大了经济属性与空间属性之间的紧张性,以至于束缚城市空间转型。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转变呈现出“去领域化”与“再领域化”的动态调整过程[13]。珠三角地区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先行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当地乡村社会相继卷入工业化浪潮,且实际形成了集体土地直接入市的发展模式。但是,当视野进入珠三角地区的城市边缘地带,浮现的则是与其经济发展程度并不匹配的城镇空间景象。尤其是破碎的城镇社区空间格局不仅抑制了当地城市化进程,而且影响城市基层治理能力,可能导致基层治理转型的空间困局。
事实上,土地不仅是经济要素,而且是空间生产和空间演化的基础。完善城乡中国时代的基层治理,需要立足城乡关系的视角。在城市化进程中,作为经济要素的土地面临着郊区农村社会利益结构的潜在约束,进而影响土地空间属性的表达。处于城乡交接地带的城镇空间转型不仅遵循城市空间转型的市场逻辑,而且受制于乡村社会的发展路径,尤其是土地开发模式。土地是空间的载体,其附着的政治经济关系定义了空间的社会学意涵,故应以开放的视野审视社区空间形态,将社区空间转型置于土地开发过程和地权调控过程。城镇社区是城市系统的末端,也是乡村城市化转型的前沿地带。社区空间生产不仅服从于城市内部的空间竞争和空间配置,而且直接依赖于土地开发秩序。土地开发秩序的核心是土地开发权的配置[14],它决定了土地利用和地利分配的方式。作为土地开发的重要主体,珠三角地区的村集体是基本发展单元。经济发展单元的集体锁定是社区陷入空间依附和治理困局的结构根源。本文将基于珠三角地区的土地开发模式,揭示城市化进程中社区空间转型的土地陷阱及其引发的治理困局,并从发展单元与治理单元的地权调控的层次反思超越土地陷阱的路径。
本文的田野资料主要来源于珠三角地区中山市S镇和东莞市H镇的田野经验①。需要说明的是,作为田野来源地的S镇与H镇其实属于“镇区”,而其隶属的中山和东莞都属于不设区的地级市,乡镇的行政等级较高。在珠三角地区,S镇和H镇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中等水平,其工业化进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X社区和Q社区分别是两个乡镇的唯一社区,社区的空间转型见证了当地的城市化历程。X社区和Q社区均是由乡镇原有的街区转化而来,其管辖范围主要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原初的老旧小区,二是分散在各个村庄的楼盘小区,后者主要承接了新增人口的流入。目前,中山S镇一共有55个楼盘小区,其中社区辖区范围内仅8个楼盘,其余47个楼盘分布在S镇的15个村庄中。东莞H镇社区的情况类似,H镇的居民人口分散居住在全镇范围内的40个楼盘小区。社区居民的居住空间与村民的居住空间形成混杂交错的插花格局,插花式的、分散的社区居民居住格局直观地反映了当地城镇社区空间转型的困局,深刻影响了社区治理效能。
① 笔者随同所在研究团队于2017年7月在中山市S镇调研20天,2019年4月在东莞H镇调研15天。调研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访谈对象包括普通农民、社区干部、村组干部、企业老板、乡镇干部,调研主题主要是土地开发与城乡基层治理。本文的田野资料来源于以上两次田野调研。
-
土地城市化是城市空间扩张和空间转型的主要路径,它具体体现为农村土地转变为城市土地的过程。土地城市化隐含了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基础的“中心—边缘”的空间格局。由于土地兼有经济属性和空间属性,社区空间生产逻辑贯穿于土地开发的空间要素配置过程,而土地开发的模式具体定义了社区的空间生产机制。根据中国现有土地制度的实践原则,城镇社区的空间形态通常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城镇人口集聚和土地性质变更的产物,进而形成以城镇为中心的辐射模式和空间格局,由此推动农村的社区化转型。在特殊历史背景和政策条件下,珠三角地区的村组集体广泛参与土地开发,集体主导的土地开发秩序强化了集体的经营性,农民和土地束缚在集体的发展单元之内,侵蚀了社区空间生产的自主性。社区空间生产因而依附于集体的土地经营逻辑,缺乏作为城镇空间的中心地位,难以实现土地要素的集聚与吸纳。以下将分别从集体的土地经营、利益吸附、责任排斥等三个方面阐述社区空间碎片化的物理形态、区隔化的社会形态与边缘化的制度形态,揭示社区空间的依附性生产逻辑。
-
中国农村实行集体土地所有制。《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土地因城市建设发生用途变更,须通过土地征用的方式转变为国有土地。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主要以土地财政的方式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不仅体现了“涨价归公”的宪法秩序,而且奠定了城市建设的经济基础和空间基础[15]。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地开发路径蕴含了土地经营主体的转变和发展单元层次的上移。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普遍形成集体自主开发土地的模式,其结果是农民与集体利益关联强化,进而锁定了土地要素的配置范围,束缚了农村土地要素的外溢和社区空间扩展,导致社区空间的碎片化。
20世纪80年代初期,珠三角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渐起步,地方政府鼓励各村集体自主开发土地,以吸引外资进入,发展集体经济。珠三角地区普遍形成集体土地直接入市的土地开发模式,集体分享了部分甚至全部土地的增值收益,并进一步强化了集体参与土地开发的动力和预期。根据集体所有权归属主体的差异,集体经营通常包含行政村和村民小组两个层次,因而形成“两级经济”的治理结构。集体深度参与土地开发过程,具有鲜明的经营属性,其经营目标是获取持续的土地租金收入,注重“细水长流”。所以,“一次性买断”的“征地”对于集体而言并非最佳选择,而自主开发物业发展租赁经济(即“筑巢引凤”,诸如建设工业厂房、商铺或公寓楼并向外出租)则是相对稳妥的经营方式。基于土地增值收益的高度自觉和长远预期,集体近乎本能地排斥地方政府的占地行为。事实上,即使是道路等公益性用地也普遍存在着地方政府与村组集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和讨价还价,这其中隐含的逻辑是“路通财通”。
案例1:在东莞H镇,道路修建的土地供给模式是,道路占用的土地由村集体供给,但道路建成后道路两侧的土地开发则由村镇两级协商分成(通常方案是“五五分成”)。土地开发产生的增值收益预期是集体让步的主要原因。不过,现实的情况往往更为复杂。例如,纵贯H镇的主干路宽度并不一样。两段道路的宽度差异源于道路占地涉及两个不同的村庄。其中一个村在土地占用后的补偿方案上与乡镇未能达成共识,不同意占用更多土地修路,于是造成当前不规则的道路格局。除了利用沿街的便利区位条件开发商铺之外,村组集体对于村庄内部的土地利用也具有较高自主性。尤其是对于土地溢价较高的商住用地,主要通过私人开发商向集体“买地”,并通过挂靠政府房地产公司,实现开发程序的合法化,而集体也得以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在村庄中于是形成了大量的楼盘小区,承接社区居民人口。城市化过程中新增的居民人口只能分流到村庄中的楼盘小区,难以实现居民人口与社区空间的有效匹配。例如,Q社区的人口规模从1997年的3 800人增长到2014年的8 000人,随着2014年东莞全面放开户籍政策,截至2019年调研时为止,已经迅速增加到1万3千人,但人口急增的同时社区空间格局却更为散乱。
集体的土地经营抑制了地方政府统筹土地开发的权力,社区空间趋于碎片化,社区居民与集体农民插花分布,逐渐形成“村中城”的低端格局。集体的土地经营分享了土地增值收益,导致了土地开发空间格局的低效锁定,呈现出混乱无序的特征。集体主要从村庄局部层次考虑土地利用和土地收益,缺乏全局性和总体性的规划意识。当地基层干部用“满山放羊”的说法形象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土地开发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地方政府的土地开发被农民视为侵占其土地利益的行为,因而与集体存在复杂的利益博弈和利益交换①。集体的土地经营逻辑切割了镇域空间的扩张和分化过程,随着一个个村庄成为自成一体的经济系统,土地的经济属性俘获了其空间属性,城镇社区因缺乏完整的空间实体而虚化。S镇建设局局长描述该乡镇是“一个特殊的、奇怪的乡镇,特殊之处在于没有镇区”。社区虽有自己的组织架构和治理对象,其空间形态却趋于碎片化,淹没在村庄之中。
① 2017年在中山S镇调研时,乡镇干部直言,在珠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中,中山市的土地开发算是比较规矩的,即开发建设的土地性质以国有土地为主。即便如此,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虽然大量集体土地变更为国有土地,但很少通过严格的征地程序实现。通常的情况是,集体先行开发,地方政府为集体的土地开发行为提供合法性的程序认证服务,并共同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形成当地惯用的“土办法”。
-
社区是居民集聚并共同生活的空间单元,城市化是农民从村庄进入城镇社区并转化为城镇居民的过程。一般而言,社区的空间生产内在于城市化过程,且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呈现出较大的包容性,这具有弥合城乡差异的社会整合功能。基于珠三角的经济区位条件,城市化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地方社会内部的城乡关系,二是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发达地区的城乡关系。集体的土地经营固化了本地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导致集体的福利化,集体不仅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而且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农民与集体的利益关联弱化了本地农民市民化的动力,束缚了“人的城市化”[16]。因此,社区新增居民人口主要来源于外地的流动人口,社区的空间转型因而蕴含着本地农民与外地市民的区隔化过程。
社区空间区隔化源于集体的利益吸纳。农民与集体的利益关联首先体现在农民可以凭借其集体成员的身份获得土地分红收入。由于区位条件和发展程度的差异,珠三角地区的分红收入存在较大差异,每股收入从一两千元到十几万元不等。S镇和H镇在珠三角地区均属于中等发达程度,除个别村庄之外,集体股份收入一般不超过5 000元/股。其次,除分红以外,出于资本积累需要和回应农民利益诉求,集体往往向农民有偿提供宅基地,农民自建房屋出租给外来流动人口而获得房租收入。这种方式既可提高集体资本积累的效率,而且营造了“家家有物业”的繁荣景象。以土地开发为基础的物业经济发展模式显化了农民地利分配的预期,强化了农民对集体的依赖,集体的利益吸纳和福利捆绑进一步弱化了当地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在调查中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珠三角当地农民进厂打工的情况还较为常见,随着集体经济发展和房屋租赁收入增加,本地农民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且农民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程度与其福利性收入呈现正相关性。当地村民缺乏市场竞争意识,普遍安于村庄无压力的悠闲生活。为了获得自由、体面、稳定的工作,中青年人宁可选择工资较低(每月3 000元左右)的办公室工作。因此,当地青年人既缺乏进入城镇买房的经济条件,也缺乏进城买房的动力。在具备经济条件的情况下,集体通过规划建设居住小区的方式引导农民从分散居住模式走向集中居住模式,在村庄中即可低成本地获得便利的公共服务。农民与集体的利益关联抑制了农民的城市化想象,迟滞了当地农村的社区化转型。社区居民身份对于本地农民而言并不具有显著优越性。
案例2:针对S镇目前城镇人口不足的情况,当地试图推动“村改居”,但由于涉及集体资产处置的难题,“村改居”的工作一直难以推进。2010年,S镇本来计划以各方面条件较好的L村为试点来推动“村改居”的相关工作。但是,在开村民代表会时,L村的村民不同意“村改居”。回顾当时事件,该村的副书记分析认为,群众主要有以下担忧:一是在现有集体体制下,户口迁入需经每个村民同意,难度较大。如果实行“村改居”,则需接纳社区居民户口,本村村民可能失去子女入学的优先权等集体福利。第二,集体资产虽然已经股份化,但是“村改居”意味着享受集体公共福利人员的范围扩大,也为集体资产的增值带来了更大的变数。
“村改居”的停滞典型地反映了社区空间转型的困局。集体的福利捆绑固化了城乡之间的社会差异。福利化集体不仅缓冲了市场化的风险,而且为集体成员提供了有效的生活保障,维系了村庄生活方式的稳定性。分散在各个村庄中的楼盘小区居民并非集体成员,他们既是土地开发的市场条件(作为消费者),又面临着集体的社会排斥。因此,集体成员不愿意转变为社区居民,而村庄中的社区居民也难以融入集体,社区空间生产缺乏本地人口、资源、关系的注入,难以打破集体与社区的社会区隔。扩展中的社区空间主要限于村庄中的楼盘小区,沦为“外来人”的生活空间。可见,作为社区居民潜在来源的本地农民因集体利益的吸纳而呈现出反城市化趋势,维持了村庄共同体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在这个意义上,社区空间的碎片形态和插花式格局难以构筑村居良性互动、城乡协调联动的平台,社区空间碎片化的物理形态逐渐沉淀为区隔化的社会形态。
-
社区空间不仅面临着物理分割与社会区隔,而且面临着治理体制的排斥。按照城市化的理想模式,社区是城镇人口集聚的核心,并吸引农村人口从相对边缘的村庄向城镇集聚。人口流动和空间集聚通常伴随着治理单元上移,而珠三角地区的土地开发模式在赋予集体较大经营空间的同时固化了集体的自主治理责任。因此,属地责任配置源于两个动因,一是集体共同体意识和宗族认同观念强化了村组干部的当家人角色,回应村民的福利需求、维护集体利益是“守土有责”的内在要求;二是地方政府在向集体让渡土地开发权的过程中向下压实属地责任,以调动基层治理动力。集体的内生动力与基层政府的治理定位相互呼应。需要注意的是,有效的属地管理依赖于治理单元空间范围的明确性和完整性,以便动员和整合治理资源。集体的属地责任与其土地开发权匹配,而社区则缺乏土地开发权。因此,锁定于基本治理单元(村庄和社区)的属地责任配置势必凸显城镇社区在治理体制中的边缘处境。
事实上,珠三角地区的基层干部通常将村级组织类比为“小政府”,村委会承担了诸多本应由基层政府承担的工作,例如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流动人口管理、学校(小学、幼儿园等)建设等。为了回应乡村工业化背景下的复杂治理需求,村委会的下设机构增多、职能分工细化。集体的属地责任与其土地经营匹配,后者不仅奠定了属地管理的经济基础,而且连带性地生产了属地治理内容。例如,集体需要为集体物业的承租者提供诸如秩序维持、关系协调等方面的服务,保障承租人的经营环境,协调租户与村民的关系。在镇域经济系统中,集体通过土地经营而成为事实上的基本发展单元,形成以集体为中心的资源集聚和责任配置模式,从而弱化了基层政府支持社区的能力和意愿。面对社区治理资源有限与空间格局分散的结构性张力,立足集体的属地责任配置的结果是社区空间的边缘化。
在应对属地责任的压力时,S镇与H镇的社区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S镇社区目前居委会工作人员5人,但归属于居委会名下的人口则有1.7万人,由于社区治理主要依赖乡镇政府有限的财政拨款,缺乏自主经营能力,庞大且分散的居民人口导致社区治理呈现出鲜明的维持型特征。然而,H镇的社区在其演变过程中却呈现出“类集体化”的趋势。
案例3:H镇Q社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政府鼓励下社区开始买地建厂房发展物业。90年代初期以3万/亩的价格向相邻的三个村买了12亩地。通过银行贷款、政府借款和民间集资等方式筹集资金,该社区自2003年开始相继建成共15 000 m2的厂房。目前两套厂房的租金收入有100多万,另外还有幼儿园每年70万元的租金收入,这两项费用合计近两百万。与周边村集体相比,这笔收入虽然不算高,但为社区居委会履行属地责任提供了一定的自主空间。该社区书记说:“我们社区能为居民解决的就给解决,政府的小事情是居民的大事情。一些路灯、巷道硬化等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能给钱最好,不能给我们就自己出了。毕竟政府的程序也麻烦,给钱要几个月时间,但是居民不理解,只说我们慢,反映好久也不回应。所以不如自己出钱搞,尤其是紧急的基础设施每年都会做一点。能帮他们做事,他们相信我们,我们有问题也好解决了,都互相理解,互相帮忙,不是你只坐那就完了的……小钱不能等政府,要自己给,对治理也有帮助,不然(群众)就投诉到市里省里了。”
事实上,案例3中Q社区的努力难以在根本上扭转治理责任的配置格局,却可能因脱卸基层政府治理责任而倒逼社区的经营行为,反而强化社区空间转型对于集体的依附性。可见,集体的属地治理塑造了政府的责任配置格局,导致社区空间在治理责任配置上的边缘化。对于社区而言,一方面要承担城市化进程中新增人口的持续涌入,这意味着治理事务和治理压力的增加;另一方面,属地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切割了社区治理内容:本应纳入社区治理的楼盘小区在制度上转化为属地村庄的治理对象,而社区常态治理主要局限于初始的老旧小区空间。更复杂的是,因集体的属地管理动力源于其自我界定,面对碎片化和区隔化的社区空间单元,集体倾向于采取策略性和选择性的治理逻辑。因此,属地化的责任配置蕴含了基层治理体制对于社区空间的排斥,从而在制度层面锁定了碎片化和区隔化的社区空间格局。
一. 集体的土地经营与社区空间的碎片化
二. 集体的利益吸纳与社区空间的区隔化
三. 集体的属地责任与社区空间的边缘化
-
社区空间具有复杂多维的属性。上文分别从社区空间的物理属性、社会属性和制度属性三个维度阐释了珠三角地区城市化转型中的社区空间生产逻辑。在城市化进程中,集体经营剥夺了社区的自主空间,造成了城乡的社会区隔,并在体制层面制造了社区治理真空。社区空间转型的依附性与集体经营的自主性形成鲜明的对照。土地兼具经济属性与空间属性,而集体经营逻辑释放了土地的经济属性,从而束缚了社区空间生长演化的载体,导致社区空间转型的土地陷阱。土地陷阱侵蚀了基层政府统筹配置治理资源的能力,从而锁定了属地责任配置格局①,凸显了社区空间存在的问题。作为治理媒介的社区空间日益问题化,且产生了大量的治理缝隙,影响社区治理效能。社区中细小琐碎的事务大量溢出,社区陷入治理困局。
① 在珠三角地区,属地管理是一种历史事实,具有内生的历史社会基础。这与当前自上而下“压实”属地责任的逻辑有所差异。
-
一般而言,治理单元是特定人群在特定范围空间中的聚合。空间不仅定义了治理的边界,而且,空间的塑造贯穿于治理过程之中[17]。由于城镇社区空间的碎片化、区隔化和边缘化,社区治理单元陷入分裂,社区的治理能力缺乏沉淀的稳固基础。如前所述,社区治理单元在空间上分裂为居委会有限的辖区范围和分散在村庄中的楼盘小区,呈现出“人户分离”的局面。作为一个治理单元,社区主要是居民人口的集合体,是基于人的制度身份的组织集合,缺乏实体的空间基础。社区对于楼盘小区的管理仅限于户籍、人口信息,对于社区居委会而言,居民是抽象的“人口”。问题是,社区的日常治理内容源于丰富具体的生活情境,不可能局限于人口治理。只有将“人口”置于具体的空间情境,才能触摸到居民的生活逻辑和交往模式,才能逐渐培育居民的社区认同,促进社区治理能力提升。
案例4:中山S镇社区辖区内居民仅占20%,居委会干部以及200多个党员分散在各个楼盘小区。2015年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时,临时动员了300个工作人员将100个流动票箱拿到每个村,由村委会负责协调和联系居民参与投票。更大的问题是,由于社区居民分布在全镇各个角落,社区干部难以深入掌握几十个楼盘小区的情况和面临的问题。因为社区居民分散,很多文体活动也不容易组织起来。对此,S镇社区书记认为:“一个是活动在哪里搞,地方不好兼顾,一个个小区搞,没有这个资源和精力,有选择性搞,效果又不明显。”
人户分离导致社区缺乏凝聚力,社区既区隔于当地乡村社会,又缺乏整合的空间基础。居民发生矛盾和纠纷也较少找居委会干部,居委会干部难以通过具体的群众工作来积累居民认同。可见,这种空间格局无助于培养社区内部的“积极分子”,干群关系缺乏连接纽带。社区干部虽然了解业主的户口信息,但治理单元的分裂导致社区对楼盘小区难以有效履行治理责任,无法及时回应群众需求。社区绝大部分新增人口分流至各个村庄中的楼盘小区,超出社区居委会的治理边界,社区日常治理主要局限于有限的辖区范围。对于社区居委会而言,即使采取向市场购买服务的方式,仍然面临如何发现和识别居民需求的难题。而且,空间分割与人口分散限制了服务的规模效益和溢出效应,降低了资源利用效率。
此外,由于楼盘小区主要由集体开发,集体之间存在着土地开发竞争,集体相对有限的土地储备、规划意识和短期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单个楼盘小区开发的规模和层次:一是压缩了单个楼盘小区的规模,在非熟人社会的场景中,过小的社会规模不利于培育小区内生自治组织;第二,集体之间的竞争性开发的核心目标是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而非公共服务配套。因此,楼盘小区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不足,且土地开发中的灰色空间往往为后续的小区治理埋下隐忧。
案例5:20世纪90年代以来,H镇和S镇都经历了楼盘小区开发过程。由于地方政府的保驾护航,集体通过私人进行的小产权房开发被合法化。一些私人开发商先囤地再开发,土地性质由集体土地慢慢转变为国有土地。有些开发商在还没有办下土地证时就开始售卖,导致一些房子没有产权证,或者是开发时对购房者做出虚假承诺,事后并未转变土地性质,容易带来上访问题。以H镇的Z小区为例,该小区是2009年开发的楼盘,600多户,2 000多人,矛盾的起因是对物业管理服务不满,主要是小区安全(大门失修、摄像头不足)、绿化和卫生等方面,人车出入的小门也直接被电动车撞坏,小区的绿化、清洁等做得也不到位。由于不满物业服务,小区业主有成立业委会诉求,其中少数人试图以成立业委会名义换掉现在的物业,插手小区事务,谋取利益。
可见,碎片化空间限制了社区治理能力的积累和增长。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涌现的楼盘小区不仅处于社区居委会的治理范围之外,而且其集体主导的开发模式为小区治理带来了挑战。集体经营的核心是土地开发经济收益而非楼盘小区的社会效益,土地开发成本部分地转嫁到小区日常治理实践,进一步增加了社区治理难度,消耗脆弱的社区治理能力。
-
治理单元并非孤立存在,不同治理单元基于权责配置而形成特定的治理系统。治理的有效性既取决于治理单元的空间构造,还取决于治理单元与治理系统的关系。治理系统从整体上定义了治理单元之间的权责配置模式。在城市化转型过程中,社区空间逐渐与村庄空间混杂,进而模糊了社区与村庄的权责边界。基层事务错综复杂,在治理单元边界模糊的情况下,过度依赖属地管理反而可能产生治理缝隙和“空白地带”,导致责任主体的模糊,治理内容在治理单元之间游移不定。可见,社区治理难题的根源在于,居民人口虽然归属社区管辖,却大量分布于村庄之中。社区的人口管理缺乏空间载体,而村庄的属地管理因缺乏制度通道而存在策略取向。楼盘小区的村庄属地和居民身份导致其陷入“社区管不到,村里不愿管、不好管”的状态。乡镇政府认为,楼盘小区位于村庄中,村委会对楼盘小区情况更为熟悉,理应履行属地管理责任。
案例6:在一些涉及需提供业主情况证明的情况时,通常由村委会出具证明,但村委会通常并不愿意开具这些证明。2017年在S镇L村调研时,该村的村干部直言:“小区是行政管理的真空。物业公司一般也不向我们反映情况。每个小区都有一个村的人口那么多,村里掌握不了,流动性太大。一些证明,例如居住证明,还要在我们村里开。居委会只管户籍、人口的证明,物业公司都不敢给他写个居住证明,反而要我们村里写?”
由于村委会并不能掌握楼盘小区居住人口的情况,为了规避治理风险,村委会对楼盘小区采取了消极治理的取向,其属地管理主要限于“不出事”的底线,诸如建筑安全和消防安全。即便如此,村委会对楼盘小区的属地管理也常常面临掣肘。事实上,在日常治理情境中,村委会与楼盘小区物业的管理范围存在空间交错和重叠,难免发生一些摩擦(如小区外围道路的环卫责任的扯皮),影响村委会与小区物业之间的协调。而且,由于村委会对于楼盘小区的定位主要是管理而非服务,物业对村委会工作往往比较排斥,认为村委会介入是没事找事。在治理体制上,楼盘小区的物业公司并不隶属于村委会,增加了村委会与物业对接的成本,这进一步约束了村委会对楼盘小区的属地管理。
案例7:S镇L村的土地开发高潮已经过去,截至调研时止,该村范围内有十多个楼盘小区。对于楼盘小区的管理,L村书记颇有抱怨:“我们只能与物业搞好关系了,多一点沟通。平时多一点宣传,政府有什么政策,让他们帮忙宣传,贴一下公告。他们没有责任,有时候也没有张贴,但是住户就可能打电话过来,说是我们没有张贴。”而且,一些事务的责任归属可能无法清晰界定。如居民有意见的垃圾、小广告,他们向村里反映,村里将责任推到建设局,建设局的局长无奈地说:“这个很头疼,我也很难管,我干脆也去投诉一下好了!物业公司只是在工商局登记,不是在建设局登记,很难管。”
可见,属地责任的配置面临着集体与社区的空间交错,进而激发了属地管理的策略性倾向。在治理资源有限和空间插花的情况下,社区治理主要局限于初始的属地范围(主要是老旧小区)。而分散在村庄中的楼盘小区则面临着集体属地管理责任的排斥。集体的属地管理并不能有效覆盖楼盘小区,反而显化了集体与社区空间治理的张力。城镇社区始终受限于碎片化和区隔化的空间治理格局。这样一来,地方政府越是依赖集体的属地责任,城镇社区越是不得不孤立地面对其破碎的空间格局,遭遇治理体制的排斥。
-
社区是最基层的治理单元,治理单元的完整性是社区治理有效的空间条件。事实上,在传统村庄,密集的社会关系编织起琐碎的治理事务,由此形成的整体性治理弱化了空间的规定性。与村庄不同的是,社区具有较强的建构性,其关系网络相对稀薄,凸显了空间作为关系网络拓展、治理权责界定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空间的完整性是整体性治理的隐秘基础。当前学界研究往往预设了治理单元的完整性,进而主要从组织结构的层次探究整体性治理的实现逻辑[18]。上文通过分析珠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空间转型逻辑发现,不完整的社区空间形态导致治理能力和治理责任的双重缺乏,从而在社区中形成治理缝隙。作为基层组织的社区居委会无法弥合这些治理缝隙,社区中细小琐碎的治理事务因而沿着这些缝隙溢出社区治理单元之外,而这些治理事务难以根据部门权责归类,沦为科层体制中的“剩余事务”。在两个乡镇调研时都发现,社区中大量的问题和矛盾都推到了建设局,建设局无奈地成为承接社区治理内容的“剩余部门”[19]。治理缝隙反映了珠三角地区城镇社区空间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治理困境。为了弥合社区的治理缝隙,破解社区治理困局,当地基层政府主要致力于从治理结构层面探索完善之道。结合S镇和H镇的情况来看,基层政府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探索方式。
S镇的思路是引导各个楼盘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即以业主自治的方式弥合社区治理缝隙。从2016年起,S镇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和尝试,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由于社区居委会缺乏协调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的能力,业主自治常常不是弥合而是扩大了治理缝隙。因此,S镇在推动成立业委会时采取了比较审慎的态度。业主自治思路在实践中存在的首要问题是,楼盘小区是否能够产生积极的且具有公益心的业委会成员?其次,即使成立了业委会,物业公司是否愿意进驻?楼盘小区居民的物业费用的承受能力和物业服务预期水平是否能够达成平衡,这都是影响物业服务主体进入的重要变量。在居委会相对缺场的治理空间中,业主自治可能蜕变为私人谋利的工具,导致业委会、物业公司之间关系的复杂化,这不仅难以弥合社区治理缝隙,反而进一步撕裂社区秩序。
H镇的思路是成立楼盘小组。2017年底,H镇在原有治理结构之外设立了一个管理小组(5个工作人员),由乡镇的政法办公室直接统筹,发挥其组织协调的中介角色。通过体制资源和行政权力的下沉建立外生性的组织体系,楼盘小组建构了弥合治理缝隙、上下联动的组织载体。楼盘小组的职能是发现和收集信息,反馈和协调问题,及时传达民情和政策。作为外生性组织,楼盘小组致力于发掘社区中的积极分子,培养自治组织,协调小区业主与物业的矛盾纠纷,将小矛盾小问题及时化解在基层社区之内,以提升楼盘小区的治理能力。
大体而言,弥合社区治理缝隙的两种思路分别体现了“向下”和“向上”两种倾向。无论是诉诸内生性的业主自治,还是诉诸外生性的楼盘小组,其共同点是尝试从组织结构层面弥合社区治理缝隙。相对于业主自主实践探索面临的不确定性,楼盘小组通过援引行政资源取得了更大效果,但这始终难以转化为社区的自主治理能力。因此,除了治理结构的组织再造和治理缝隙的体制修复,还有必要立足社区治理缝隙的形成逻辑,反思社区空间转型的制度调控机制,进而在治理单元的基础层次探索破解社区治理困局的方法。
一. 治理单元分裂与治理能力匮乏
二. 权责边界模糊与治理责任错位
三. 治理缝隙与治理结构的整合限度
-
上文结合珠三角地区城镇社区的发展与治理经验,立足集体经营逻辑分析了社区空间的依附性生产及其引发的治理困局。社区是中国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20]。相对于村庄空间的自发演化而言,社区空间受土地制度影响的程度更深,具有更强的建构性。当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阶段,社区空间转型内在于城市化的平面扩张过程。回顾珠三角地区社区空间转型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集体土地直接入市促成城市化转型中的空间竞争,并导致了空间的利益俘获。在这个意义上,土地陷阱源于发展单元的集体锁定。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土地要素主要服从集体支配,土地的空间属性难以超越集体经营逻辑的限定,进而抑制了城镇社区的空间生产。社区空间转型的土地陷阱是社区治理困局的根源。走出社区空间转型的土地陷阱,不仅依赖于空间治理技术,而且需要立足土地开发模式的土地制度调控,软化农民与土地、农民与集体的利益关系,进而形成集体与社区协调联动的空间生产机制,推动社区空间的有序转型。
空间是治理的载体,它界定了治理单元的边界和规模。作为城镇的基本治理单元,社区有效治理主要依赖如下空间特征:第一,空间边界的完整清晰。社区的人员流动性更大,相对完整的空间范围是降低日常互动成本、凝结社会资本、培育“积极分子”的重要条件。此外,完整的空间也有助于清晰界定治理单元与治理体系的关系、理顺治理关系、强化治理动力。第二,空间功能的合理配置。城镇社区的空间转型不仅是空间的平面扩张过程,而且是空间功能分化的过程。在多种功能构成的复合系统中,城镇社区的空间布局需要统筹规划空间用途,尽可能避免空间的割裂和插花,以降低空间中不同功能的外部性侵扰(例如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插花情况下产生的噪音、气味等污染),以缓解治理压力。
土地具有空间属性,它是社区空间建构的载体,而土地制度规定了空间配置的基本路径。土地城市化的制度路径设定了不同于集体经营的空间生产逻辑。土地虽然具有经济属性,但土地制度的调控可以软化农民与土地的利益关联。在制度规范层面,经济属性即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实现增值的属性,遵循“地尽其利”的原则;同时,土地要素配置需要服从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主要遵循“涨价归公”的政治原则。土地因而是治理单元和发展单元协调的基础。从珠三角地区的发展路径来看,较低的发展单元层次导致土地的经济属性侵蚀土地制度实践效能,强化了城乡之间的空间竞争与空间区隔,导致了空间转型的无序;反之,较高的发展单元层次为兼顾土地的经济属性与空间属性提供了可能,奠定了迈向城市化和社区化的空间生产路径。珠三角地区的城镇社区治理困境鲜明地反映了土地经济属性与空间属性之间的张力。集体主导的土地开发秩序锁定了发展单元的层次,俘获了社区空间转型的土地基础。由于社区空间生产缺乏充分的土地载体,社区难以实体化为一个有效的治理单元。
现有土地制度为发展单元与治理单元的调控提供了重要制度载体。依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凡涉及占用农村土地,地方政府须经征地程序将集体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并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在此过程中,用地主体向地方政府支付土地出让金,其中相当一部分转化为土地财政,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述土地开发模式体现了“涨价归公”的原则。“涨价归公”定义了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方式,蕴含了土地开发权上收和发展单元上移的制度取向,并且回应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空间扩张需求:第一,在地方政府主导土地开发权的情况下,城镇建设规划才能突破集体各自为战、分散开发的“低端”状态,为高品质城镇空间规划创造可能条件。这样一来,无论是楼盘开发还是产业布局,均可在“一盘棋”的指导思想下优化城镇空间功能布局,回应群众需求。第二,在土地发展权归属政府的情况下,土地征用剥离了农民与土地的利益关联,弱化了集体对于农民的福利捆绑效应,促进“村改居”的体制转型,从而将村庄社区化转型导入城镇社区的空间扩展脉络之中,形成城乡联动的发展格局。
-
珠三角地区是中国城市化的先行者,当地基层社会的发展模式与治理状态对处于城市化浪潮的中国基层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基于珠三角地区的发展路径,揭示了社区空间转型的土地陷阱。土地陷阱的概念旨在深入空间的经验基础,从城乡联动的视角呈现空间生产的政治性和空间转型的复杂性。空间生产逻辑服从于土地开发权的配置模式,且影响城镇社区的治理效能,空间因而是发展模式与治理效能的重要媒介。在这个意义上,城乡基层治理转型不仅是治理规则、治理技术的转型[21],而且是以城市(城镇)为中心的空间转型。自主、完整的空间是孕育治理能力、配置治理责任的根本前提。空间转型依赖于土地开发权配置和发展单元定位,发展单元层次越高,土地要素配置的弹性越大,越有利于在城乡统筹的基础上形成面向城市化的空间生产路径,从而奠定城镇社区有效治理的空间基础。
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性制度。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渐进过程,其中伴随着土地要素的配置重组,凸显了乡村对于城市化的限定。集体主导土地开发秩序是乡村社会内部刚性利益结构形成的根源,抑制了农民的城市化和空间的城市化。土地陷阱的实质是发展单元与治理单元缺乏制度协调的产物。社区的空间转型因而遭遇集体经营行为的扭曲,陷入碎片化、区隔化和边缘化的状态,社区治理缺乏完整有效的空间基础,广泛存在的治理缝隙导致社区治理陷入困局。在这个意义上,珠三角地区的土地利用存在一定的“先行劣势”[22]。破解珠三角地区城市化发展转型中面临的治理困境,需进一步完善土地制度,通过地权调控提升发展单元的层次,从而使土地开发和土地利用突破集体经营的路径,实现社区空间的主体性生成,恢复城镇社区的中心地位。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伴随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郊区逐渐纳入城市治理体系,因而城镇社区的治理成效关系到城市化进程的稳定性。总之,在土地开发和城市化转型过程中,需着眼于社区善治的空间基础,推动城镇空间的有序生产,形成人户匹配、城乡联动的空间格局。如此一来,城镇社区的空间转型才能跳出土地陷阱,奠定社区有效治理的空间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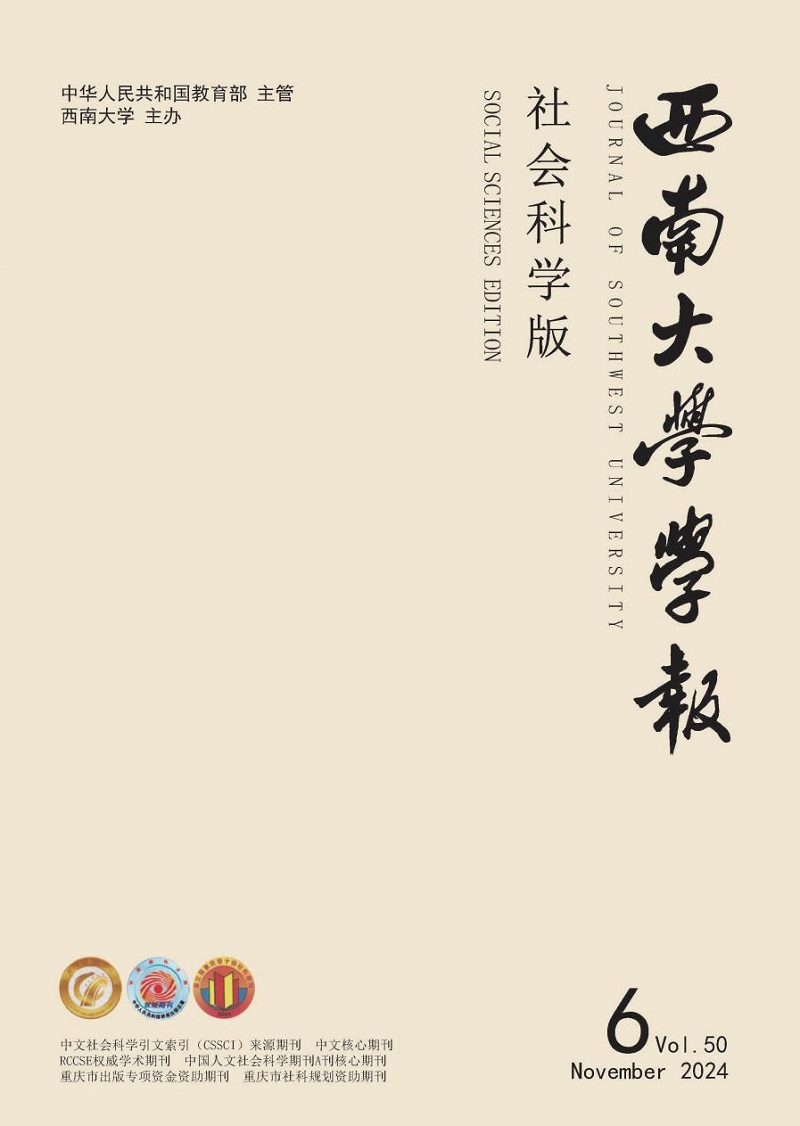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