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语》“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1]384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212被视为儒家乐教由“事神”之事转向“成人”之事的根本标志,这也是孔子删诗、践礼、正乐提拔礼乐教化的用意所在。在他看来,无论是政治理想的再现,还是文化命脉的续递,均须首先挺立一个再现政治理想或续递文化命脉的主体,正所谓“礼乐者,成人之事”[2]。
对于乐教成人,学界主要集中在:一梳理远古至春秋,乐教由事神→制度理性彰显与人文精神自觉→成人成德的演变历程[3]及孔子在“作乐”“奏乐”“赏乐”中对乐教传统的重建[4];二研探《诗经》以情感人[5]、《荀子·乐论》以乐化性[6]、《礼记·乐记》中乐与情之间的相因的环、嵇康《声无哀乐论》由乐引发人的欲望[7]及乐以“诗辞”“乐曲”“舞蹈”[8]等实现自身;三指出有善有恶说、性善说、性恶说、性朴说等人性基础说的差异实质实是未发的性善或性朴与已发的情性之差别[9];四考察《国语》乐教中的政治善治与个体完满[10]、《荀子·乐论》“化性起伪”下的“善民心”“厚人伦”“美风俗”[11]、古典儒家“和天下”[12]、《礼记·经解》“广博易良”[13]等功效。合起来看,生成传统是对儒家乐教成人背景的展现,以情成教与性之未发已发研讨是对成人过程情、性互成的描述,而个体完满与政治伦理功效则是对成人结果及目标的期望。显然,上述研究均以儒家的乐能够成教化人为前提所展开。由此,我们不免追问:儒家的乐究竟凭什么成教化人?情与性又是怎样互成并促成成人?也即,乐教成人的根据何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是确证乐教成人传统、实现、人性及功效的逻辑前提,更是助推乐教成人实践以至实现孔子乐教理想的理论奠基。故此,本文拟从真情、文理、和乐(lè)三维度探究儒家乐教的成人根据。
HTML
-
“乐”何以能以“情”成教化人?这有赖对“乐之情”的构成与属性的考察。对于“乐之情”的构成,《礼记》卷三十七和卷三十八在阐述“乐”的产生时,有这样三段表述: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14]976;二“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14]987;三“乐也者,动于内者也”[14]1031。第一段表述表明,涵括“音”的“乐”起于人心感物而动,这里的“物”可以是自然界里的原始声音,比如鸟鸣、水流之声;也可以是生活中的生死福祸,比如父母养育、生老病死,也即“乐”生于对自然声音的动心与日用悲喜的感发。据此,“乐之情”存在两种状态:一是未动之时,存于人心;二是已动之后,形于声音。第二段表述意指,“乐”是“中”的呈出,这里的“中”,依《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来看,是指喜怒哀乐未发之情,也即本有之情尚未呈出的状态,此时的“情”属“静”,与已发之“动”相应,朱熹将此未发之情集注为“其未发,则性也”[15]20。可见,未发之情实是本有之性,所谓“情蓄于中,无事物以感之,则情不呈”[16]是也。前两段表述合起来看,“乐”是“心”(未发之情或本有之性)感于外物而动的本有内在情(性)的呈出,因而第三段表述视“乐”为“动于内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徐复观先生说:“《乐记》之所谓‘心’,正指的是统性情之心而言。”[17]25据此,“乐之情”在心未动、情未发之时,首先是指“性”。本有未发的“静”“中”情性为感物已发的“动”“和”情欲奠定根基。
未发的“乐之情”是“性”,源于“心”(“中”),那么,由“中”(“心”)呈出的因物感动、形于声音的已发的“乐之情”是什么?“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14]984“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嘽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14]976-977哀、乐、喜、怒、敬、爱即是已发的“乐之情”,此六情,不再是未发之性,而是感物而动的自然情(欲)。父母去世,制(奏)乐者感于去世哀伤所作之乐自是“噍杀”之声,子女因此感受的是“噍杀”之“乐”所呈出的哀伤之情(欲);男婚女嫁,制(奏)乐者感于婚嫁喜悦所作之“乐”自是“发散”之声,嫁娶者因此感受的是“发散”之“乐”所呈出的喜悦之情(欲);同理,乐(lè)、怒、敬、爱等四情也是如此。显然,“乐”借助生活事为,通过已发的喜怒哀乐等情(欲),将制(奏)乐者与赏乐者的情(欲)共鸣在一起,实现“乐”“疏秽镇浮”教化。因此,荀子认定“琴瑟乐心”[18]370。
不仅如此,荀子还肯定“钟鼓道志”[18]370。《礼记·经解》以“广博易良,《乐》教也”[19]944阐明乐教功效。这里的“广博”被明确为:“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18]369由《雅》《颂》助成主体广博志意可知,已发的“乐之情”还是情志之情。制(奏)乐者借“乐”抒发自身情志,赏乐者通过此“乐”或建立、或共情自身情志,二者在“乐”所抒发的情志中同志知音,“乐”成教化人。事实上,孔子也早在自己的行乐(正乐、学琴、击缶、日歌)中反复表达“乐之情”有意情志托付。以击磬于卫国来说,“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1]406即是他对“荷匮”不能领会磬声抒发的卫灵公不用孔子之愁志的感叹。以此类推,“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嘽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14]998。“志微噍杀之音”建共主体思忧情志,“繁文简节之音”建共主体康乐情志,“奋末广贲之音”建共主体刚毅情志,“劲正庄诚之音”建共主体肃敬情志,“顺成和动之音”建共主体慈爱情志,“狄成涤滥之音”建共主体淫乱情志。合之,“乐之情”未发之时,是“性”;已发之后,指自然情欲(喜怒哀乐敬爱)与志意之情。
对于“乐之情”的属性,就未发的“乐”之情(性)而言,孟子讲“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20]310,程子将其注解为:“仁言,谓以仁厚之言加于民。仁声,谓仁闻,谓有仁之实而为众所称道也。此尤见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15]330在孟子、程子看来,“仁声之入人深”是因为“仁声”是深植仁性而制的“乐”,是“仁性”之实与“仁声”之形的呈出,民众能在仁声教化中唤起并相知自身本有“仁性”(“仁德之昭著”)。换言之,属“静”未发的“乐”之情(性)与人性之善(仁)是一致的。正是如此,孟子在论述华周杞梁之妻痛哭俗变时,独以“有诸内,必形诸外”说明乐教功效,而徐复观先生则以“‘静’的第一义是纯净”[17]26隐晦“乐”之情(性)至善纯净。
就已发的“乐”之喜怒哀乐等自然情(欲)看,《荀子·乐论》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18]368这里的“免”,郑玄注为:“犹自止也。”[14]1032据此,“不免”是指“不能自已”,“乐”所呈出的喜怒哀之情是人情之不能自已。既是人情不能自已之生发,故而真实自然。换言之,感物而动后,已发的“乐”之喜怒哀乐也同于人情之喜怒哀乐,因此《性自命出》将借助“声”表达自己的“乐”称作“凡声其出于情也信”[21]。“信”即“有诸己之谓信”[20]346,内里实有此性情,外表呈出此性情。据此,“有”的意蕴:一未发的“乐”之情性与本有的“人”之仁性相一致,二已发的“乐”之喜怒哀乐与自然流露的“人情”之喜怒哀乐相通无隔。前者为乐教成人确立人性根据,后者为乐教化人提供情感支撑。可以说,正是“有”的两层意蕴为“乐”成教化人提供可能,毕竟心性一致与情欲相通才可相知,相知才能习熏,习熏才得滋养,滋养才致化成。与此同时,无论是“乐”之情性的纯净至善还是“乐”之喜怒哀乐的“不免”与“信”,均表现出“真”的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乐记》以“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14]1006阐明诗、歌、舞之“乐”所承载的情“深”且“不可以为伪”。“深”是因为“乐”深植于“性”,“性”无穷竭,“乐之情性”的生发与流淌无止境;“不可以为伪”是由于“乐之情”的呈出及其呈出与否都是真实无虚的。
至于“乐”之情志,荀子先以“乐行而志清”阐明,“乐”在行进中所呈出的情志是清朗干净的。之后,程子又以“‘思无邪’者,诚也”[15]55意指“诗”(“乐”)兴起的志意是真实无妄的。近人郑浩则直以“夫子盖言《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即所谓‘《诗》言志’者”[22]67指明诗(乐)之情志无非人情之实泻。制(奏)诗(乐)者借“乐”所抒发的情志是至情实泻之志,赏诗(乐)者因诗(乐)所兴而鸣之志也是毫无伪托虚徐之意。因而,徐复观释朱子诗兴之“感发志意”为“由作者纯净真挚的感情,感染给读者”[17]28。正是在作者与读者的真志相遇相知中,读者起志化成。
总之,“乐”之情性(未发)、喜怒哀乐等情欲(已发)与情志(已发)三者同“真”并以“真”化成主体。以成“仁”来说,《论语》有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58包咸对它的注疏是:“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礼乐。”[22]142可见,仁心(性)是主体行乐的前提。反之,“人而不仁,则人心亡矣,其如礼乐何哉?言虽欲用之,而礼乐不为之用也”[15]62。主体须先打开本有仁心,继而与“乐”内含的至善纯净之情(性)相通,才可行进礼乐并在礼乐行进中化成“仁”。反过来说,如果主体仁心阻塞,那么即使行为上用乐(行乐),也必因仁心与“乐”之情性有隔而无法实现乐用之功效,甚至因此滥用,“八佾舞于庭”即是例证。
显然,打开仁心是主体成“仁”的开启。未发的“乐”之情性还必然外发为已发的喜怒哀乐敬爱等自然情欲,因此,成“仁”还需主体以真实六情会通“乐”的自然六情才可得达。以仁本孝亲来说,“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1]177-178。奔丧之日与失亲者一同真切哀戚,不得饱饭,当天只能恸哭,不可歌唱。丧礼所行之“乐”呈出的情肯定是悲痛哀戚的,奔丧主体在丧礼之“乐”的行进中所感受的情自然也是悲痛哀戚的,也即丧乐哀情的呈出与主体哀情的感受应同频共真,才可化成孝道。反之,丧乐不哀,抑或主体趋乐(lè),则哀伤之仁孝无法化成。简言之,“乐”之喜怒哀乐与主体之七情六欲需共真同频是已动的“乐之情”成教化人得以推进的关键,这在仁孝德性的化成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至于成“仁”之志,更是以真情兴成,孔子相当自谦却多次称赞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1]146。“三月”按照朱熹的注解是“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违仁者,无私欲而有其德也”[15]84。和他人“日月至焉”相比,颜回能长久地“不违仁”是因为他真心志于仁道而非私欲。正是真心志仁,因此他既能以超强的毅力坚守仁志、不为私欲所动,也能以永不放弃的精神面对实现仁志道路中的各种险阻。假设他并非真心志仁,则必因私欲或行道中的各种险阻而移志,更难谈“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1]149-150。显然,颜子志仁而乐仁安贫,没有志欲而乐欲移志,所以孔子尊他为仁者。这样看来,主体的本有仁心、真实仁情、真心仁志均需与“乐”之仁性、仁情、仁志相应地同真共鸣,才能助成主体达仁。也即“一个人只有在情上认取,‘直情而发’,他才具有成‘仁’的可能性”[23],“发于性的情最接近仁”[24]。成“仁”如此,成“义礼智信”“恭宽敏惠”皆是如此。正是出于本有真情,儒家被视为成己或为己之学,成就真情实意主体而非虚情假意“佞人”,孔子判定“巧言令色,鲜仁矣”[1]6,李泽厚认定乐教“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内在的引导”[25]。
-
“乐”以真情兴起真情实意主体。各主体的真情实意有所不同,因此“乐”所兴成的必是一个有别且多样的主体群:“伯夷以之廉,颜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辩给,万石以之讷慎。”[26]伯夷、颜回、比干、尾生、惠施、万石各怀不同实意,分成廉、仁、忠、信、辩、慎等各类人格。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一就情性本真流露看,人禽有相同之处,但“虎毒不食子”之亲爱与“敬养”之亲爱是迵然有异的,前者属动物本能,后者是充分自觉,动物本能与充分自觉表明流露真情的方式关乎夷雅。换言之,“乐”所呈出的真情是怎样唤起主体本真情性以“雅”而非“夷”的方式流露,进而区别人、禽或雅、夷?二真情兴起的各主体如何有序且互不妨碍地实现其情与志?出于真的,未必是“归于正”(合于道德)的,仅出于本真性情,可能会导致荀子所说的“心好利”“争乱起”而让各主体的“情志”均不得“达”,“欲求”均不得“通”,最终无法真正化成;三各主体兴起的多彩斑斓之真情实意是否需要立起根本与主流,以防其过流或有失,并在根本与主流中实现主体的普遍化与社会化?对此,“乐之文”就第一方面,“乐之理”就第二、三方面的问题分别予以了解决。
“乐之文”既体现在“声→音→乐”的形成中,也表现在制乐的“文采节奏”里。以“声→音”来说,“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14]976。各原始自然之“声”必须相互应和(“应”),依据一定的规律(“方”)加以处理才能形成“音”。“应”与“方”表明“音”是对原粗之“声”的人文打造。“音→乐”则需要“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14]1004及其“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14]989。显然,与“声→音”在声质上所作的不可见的匹配呼应相比,“音→乐”除却声质上的不可见匹配呼应外,还需要“琴瑟箫管”(乐器)、“羽旄干戚”(道具)、表演者及表演舞台等可见实物的凭借搭配,更有待表演者形式多变且富有节律的真切表演。琴瑟伴奏、干戚武舞、羽旄文舞、箫管伴奏以及舞者的屈伸身容、俯仰头容、缀兆走位、舒疾节奏①等多样文饰(“文采节奏”)的采纳与配合实是将“生于心”“感物而动”的“乐之真情”以文雅的方式呈出,从而让“乐”所唤起的主体之情以脱离动物本能及其粗俗发情的方式抒发出来,并在这一抒发中得以雅润。合之,“乐”之真情通过“声→音”的人文打造与“音→乐”的“文采节奏”,让主体真情得以高雅流露,实现“乐”之文教与成人。换言之,“乐”及其教是真情之质与文雅之形的合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156“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书,多闻习事,而诚或不足也。彬彬,犹班班,物相杂而适均之貌。”[15]86“物相杂,故曰文”[27],“文”即文彩斑斓、美丽可观。“乐”一面以真情之质唤起主体真实本性,一面以文采之形文雅主体斑斓情志,从而让主体在“乐”所营造的世界中化成文质合一且丰富多彩之人格。反之,如若缺乏本性真质,抑或少了相杂文采,主体均难完成,尤其难成彬彬君子。孔子讲“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1]383-384正是对臧武仲、公绰、卞庄子、冉求虽具“知”“不欲” “勇” “艺”之本性(“质”),但却仍需礼乐文饰(“形”)的苦心劝诫。也因为如此,《乐记》力主“声”必须以“文采节奏”成“音”,君子必须是能够恰当(“中”)文饰且表达其心动的本有性情者:“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14]1006
① 朱彬在《礼记训纂》中引方性夫之注曰:“管在堂下,磬在堂上。羽龠文舞,干戈武舞。屈伸,舞者之身容。俯仰,舞者之头容。缀、兆,其位也。舒疾,其节也。簠簋以盛地产,俎豆以薦天产。制度者,文章之法。文章者,制度之饰。升降言其行,上下言其等,周旋言其容,裼袭言其服,则礼乐之文与器,略见于此矣。”参见朱彬:《礼记训纂》(下),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68-569页。
“乐之理”不仅体现在制乐中,而且表现于用乐里。制乐中的“理”,《乐记》有言:“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14]976对此,孙希旦引孔颖达集解为:“声,谓凡宣于口者皆是也。声之别有五,其始形也,止一声而已。然既形则有不能自已之势,而其同者以类相应。有同必有异,故又有他声之杂焉,而变生矣。变之极而抑扬高下,五声备具,犹五色之交错而成文章,则成为歌曲而谓之音矣。然犹未足以为乐也,比次歌曲,而以乐器奏之,又以干戚、羽旄象其舞蹈以为舞,则声容毕具而谓之乐。”[14]976孙氏所引之解表明:“声→音”中的“应”是将同质的“声”相互呼应,“声→音”中的“方”是将异质的“五声”以“抑扬高下”为原则予以交错,而“音→乐”中的“比”则是辅“音”以声容舞蹈。其中,“抑扬高下”依“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19]442,“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徴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25]978,以“宫”为主,“商、角、徴、羽”依次递减相和而稳定(“不乱”)成“歌”,此即“声”“杂比”成“音”而“乐”。显然,“应”“方”“比”均直指“乐”的制成必循一定的规则(“理”),否则只是杂乱无序的“怗懘之音”。
用乐中的“理”,首先体现在乐器的悬挂上:“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19]444对此,郑司农的解释是:“宫县四面县,轩县去其一面,判县又去一面,特县又去一面。”[28]王、诸侯、卿大夫、士等不同身份所挂之乐器及其悬挂方式均有明确规制。其次,“乐”的演奏也十分讲究:“凡乐事,大祭祀,宿县,遂以声展之。王出入,则令奏《王夏》,尸出入,则令奏《肆夏》;牲出入,则令奏《昭夏》。帅国子而舞,大飨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驺虞》。诏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19]442王、尸、牲的出入及射、祭祀、大献等各事所奏之“乐”有专门分别。正是制乐用乐有制,因此“郑声”在制乐上内容淫邪、“八佾舞于庭”在用乐上不合身份均受到了孔子的愤怒斥责。一句话,制乐用乐实含“理”之规约。
制乐用乐暗含“理”表明“乐”的制定与使用旨在呈现秩序。“宫商角徴羽”依“抑扬高下”(秩序),则成悦耳之歌;不依“抑扬高下”(秩序),比如同取高音或同择下音,则成刺耳之声或低迷之音。文舞配以羽(毛)旄(尾)成其优美雅乐;配以干(盾)戚(斧),难免粗野失雅;武舞亦然。表演者以有别的形体声容表达不同的情境故事,则成良善之“乐”;反之,则成淫邪之“象”。王在王的位置,悬挂符合其身份、演奏合于其担当的“乐”;诸侯、大夫、士亦然;反之,王不是王,诸侯不是诸侯。婚丧嫁娶所用之“乐”应与婚嫁之喜同喜、丧礼之悲共悲,而非悲喜相反。总之,一切事为与人伦所制所用之“乐”均有其“分”并在“分”中呈现秩序。“乐”之秩序,就“五音”来说,“宫”“审一定和”,属主导(“君”);“商角徴羽”递减附和,是辅助(“臣”)。“君”“本”“臣”“末”,因此“五音”有其根本。
据此,旨在呈现秩序的“乐之理”意指:第一,“乐”及其呈出之有分(差别)让不同主体感于不同的物,生发不同的情(欲)志,志成不同的人格,也即各主体的各情志均在有分且多样的“乐”中得以通达;第二,有分的“乐”及其呈出对不同主体的不同事为、同一主体的不同事为以及同一主体同一事为的不同情景所感发的情(欲)志之抒发有着各不相同的相应规约,也即有分的“乐”及其呈出让各主体的各情(欲)志之抒发有所节制——免于过流或不及,而免于过流或不及之抒发恰好确保各主体有序且互不妨害地实现其情(欲)志及随后成人;第三,有分的“乐”及其呈出有其根本与主流,根本与主流的确立让多样庞杂的主体及其情(欲)志之抒发在保持多彩生动的同时,还秉持共同认可之标准,进而为各主体自觉遵守、践行社会情(欲)志的抒发奠定根基。与此同时,各主体在遵行社会情(欲)志的过程中,实现其社会化,将自身之特殊的情(欲)志与人格融合社会之普遍的情(欲)志与人格。从这个意义上看,“乐之理”因有分而呈出的教化恰如加达默尔所说“人类教化的一般本质就是使自身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谁沉湎于个别性,谁就是未受到教化的”[29]。也就是说,乐教之真情虽兴起各异多彩之个性化主体,但乐教之文理却将多彩个性之真情主体规约成兼具文雅、普遍与现实之社会化主体。正是在这一社会化中,主体体证“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20]263,也即纵使你我有再多的不同情(欲)志,但却无法否认我们拥有共通的情(欲)志并因此相互感化以至成就,这为各主体的情欲相通与“合和”确立了合法性。
实际上,“乐”之文理紧切“礼”之本旨。因为第一,“礼”文饰各“情”:“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7]359,“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30]。“礼”通过践行“道”,装饰悲、欢、敬、威各“情”,展现文雅。第二,“礼”中节各“情”:“礼之设所以治天下之情,或裁其过,或勉其不及,俾知天地之中而已矣。”[31]318第三,“礼”以“分”养“欲”:“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18]337第四,“礼”呈现秩序:“礼至,则于有杀有等,各止其分而靡不得。”[31]336合起来看,“礼”以“文”“中节”“分”让主体的个体情志得以文雅、节制、有差别、不紊乱的抒发,并在这一抒发中认定“礼”是“定之以为天下万世法”[31]318,立定根本与主流,实现主体社会化,此即“礼正乐”。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学者指出儒家伦理中的情感是“在社会场域中关照他人和环境后融入了理性成分的道德情感”[32]。
据此,兴起于“乐”之真情的主体通过“礼”对真情的文理规约与践行,化成于“乐”之文理。换言之,内含着真情与文理的“乐”之化成是基于主体自愿自觉地接受规约的化成,“它不是与自然性、感性相对峙或敌对,不是从外面来主宰、约束感性、自然性的理性和社会性,而是就在感性、自然性中来建立起理性、社会性”[25]。因此,徐复观谈到《雅》《颂》功用时说:“性与情,是人生命中的一股强大力量,不能仅靠‘制之于外’的礼的制约力,而须要由《雅》《颂》之声的功用,对性、情加以疏导、转化,使其能自然而然地发生与礼互相配合的作用,这便可以减轻礼的强迫性,而得与法家划定一条鸿沟。”[17]22不可否认,徐复观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儒、法两家教化旨趣的本质差异,但其就儒家“礼” “乐”关系的评判有失公允:从“乐”之真情→“乐”之文理逻辑看,“乐”所唤化的情及其节文始终是出于主体的真实性情,即便它接受“礼”的规约,但这一规约绝非“制之于外”的干瘪规约,而是饱藏丰润情意的“有于内”之自主自愿规约。这样看来,“礼”“乐”交互中的儒家之“礼”显然并非外在的背“性”强制,而是内在的顺“性”要求,“乐”因此成其出于自觉、温情满溢、顺从人性之教并以文理约成自觉、文雅、守理、有秩序之社会化主体。
-
“乐”以真情与文理化成真情实意、多样个性、文雅守理并融合社会的各主体。那么,各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是否需要与他人、社会以至万物和谐共生?显然,在矢志“生生不息”与“民胞物与”的儒家这里,这是必然的。由此,各主体如何在其社会化中和谐共生①?“乐”以“和”对此作出了解答。
① 和谐是指各主体在其社会化成人之路上与他者间的包容共存,共生是指各主体在其社会化成人之路上与他者间的滋养共进。
“乐之和”首先体现在“乐之情”内含的中和情性中(前文已述,不再赘述),其次还表现在制乐,是制乐“合和”形式的投射。“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19]441“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19]1430-1431“乐”是五声八音、六律六同、六舞九歌等的“合和”①,“乐”之“合和”正如调和酸甜苦辣各味、烹饪鱼肉蔬梅各菜一般,融合各类声音之清浊大小与各个形容之疾徐刚柔等异质或同质的各要素,是各声音、各形容等的相济相成。“乐”之“合和”不是简单地“同”同质的声音形容于一体,而是“以他平他”:“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无讲。”[33]“和合”是异质声音或形容间的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后产生的1+1>2的相互丰长与新生,“同”是同质声音或形容间的长短累积后得到的1+1=2的同质的量的增加,所成的是无长的同声,甚至因同声而“声”不得听,走向衰竭。可见,“以他平他”是各方以积极、包容与开放的姿态接受、吸纳、调和、平衡对方的优长与不足,在相互滋长中建立新的平衡,它从一开始即旨在和谐共生,而非战胜对方,强调多样的统一。显然,制乐中的“声”“方”“音”“比”与“形容”“屈伸俯仰”等正是“以他平他”,“乐”是声、音、形容等“以他平他”后的丰长新生。
① 合和是指异质的事物在一起,互济互生,进而产生出的1+1>2的和谐状态。
据此,在“乐之和”观照下的“乐”首先和成②的是主体自身的“志”与“气”。“气是生理作用,志是道德作用”[17]27,主体情性中的生理欲情属“气”,道德理性属“志”。“乐”先以内含的“中和”情性引发(唤起)主体情性本有的“中和”情志(“志”),再借外在“合和”声容疏导乃至澄清主体生理欲情(“气”)中的邪秽渣滓,使其“发而皆中节”(合于“志”),化成志与气、性与情、理与欲、心与身相和谐的统一体,“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14]1006。志气合一、性情一致、理欲相合、身心和谐下的主体,一面“因为志清,所以耳目聪明,血气和平,而‘足以感发人的善心’”[17]22,一面“和心在于行适”[34]而正当行为,在本有善心志意与行为正当实践中“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15]101。也即,“乐之和”化成志气既得、身心平和之仁义道德者,这是孔子“游于艺”之寄托,也是荀子“乐行志清”之写照。
② 和成是指“乐”以“和”和谐各相异主体,进而成就主体。
诚然,就单个主体看,“乐”和成志气无违、心平气和、理欲兼得、容颜和顺主体,这一主体如果不与他者往来、交流、分享,势必形成一个身心无戾却相互孤立的主体集合体。这一集合体长此下去的结果是:第一,不利于主体生存,因为受有限性所限,主体无法独自或完满满足自身全部欲求;第二,不能实现主体社会化,由于缺失人伦,主体无法融合社会,即使志气和谐为主体融合社会提供了极好的先决条件;第三,随着欲求匮乏的加剧,主体将因欲求无法满足,打破之前的志气平衡而害善暴行。总之,主体间的隔绝往来阻断了主体丰长新生的渠道。显然,无论缺失上述面向中的哪一面,主体均难以真正成人。因此,“成于乐”的“乐之和”在和成主体志气之后,必须致力主体(我)与他者(人)间的和谐及其互生。为此,孟子认定“与少乐乐…不若与众”[20]29,力主“与百姓同乐”[20]29。
“乐者,异文合爱者也。”[14]989“乐”在认同不同主体相异呈现(“异文”)的基础上,以其包含着“爱”的本有情性唤起各主体的本有情性,尤其是本有的“爱”情性,将相异呈现的各主体“合和”并相爱在一起。“乐之文殊,而爱之情则同。礼乐之文与事者其末,而爱敬之情者其本,末可变而本不可变。”[14]989“爱敬”作为各主体与“乐”同有的本有情性,虽然在各主体的现实生活中表现有异,但却正好在同样声容各异的“乐”中觅得了表现虽异却能相通的共情知音者①。换言之,不同主体“合和”是受“乐”内在中和情质与外在异文形式熏陶的结果,相爱是因“乐之情”唤起“异文”主体间的共情本质(尤其是“爱”本质)同鸣而爱。正是出于“爱”,在“乐之和”熏陶下的共情主体,心有灵犀且自愿自觉甚至“不亦乐乎”地打开自己,走出孤立,与他者分享并在分享中相互丰长同乐(lè)。与此同时,“乐之和”熏陶下的非共情主体,基于“以他平他”之包容与开放,一面求同存异地包容他者异处,与他者平和共处;一面胸怀大气地省思他者异处,在省思中或以他者之长弥补自身之短、或以自身之长扶助他者之短,共推人我成人。这样看来,无论是同志,还是异趣,各主体均能在“乐之和”的熏染中跨出孤立与独特,走向分享与普遍,因分享结成各类人伦,由普遍制成各种规则,实现社会化,并且这一实现是有爱、和平且共生的。据此,“乐”配称“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18]368。此即荀子主张“乐行”不仅“志清”而且“移风易俗”,《乐记》认可“乐行而伦清”[14]1005、“四海之内合敬同爱”[14]988的实质。
① 比如孝道之爱,有的主体以“敬养”表现,有的主体以“游必有方”表现,有的主体以“劳而无怨”表现等,但就孝爱本质来讲,“乐”与各主体,以及各主体之间是相同的,并且这一相同让“敬养”主体与“游必有方”主体均在“乐”所呈出的“孝爱”之情中共鸣相知。
这样看来,“仁”之忠恕实是“乐”和人我之实践。“忠”即“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则私意无所容而心德全矣”[15]126,具体表现是:“己恶饥寒焉,则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恶劳苦焉,则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恶衰乏焉,则知天下之欲富足也。”[35]“恕”即“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15]89。可见,“仁”也是基于对不同主体相同情性考量后的和爱,“仁之和”与“乐之和”同样志在多样的统一,包容异质欲求,彰显君子“和而不同”。甚至可以说,就“和”与“本心”而言,“仁”“乐”同质同构,“歌乐者,仁之和也”[14]1408,均视成人为发于仁心而终于社会及人我共生。总之,在“乐之和”的人我互推中,化成人我之仁,最终成就一个仁者和仁的社会。
此外,“乐”还和生②主体与万物。“乐”和生主体与万物首先源于构成“乐”的“声”来自自然界中的各类声音,这为“乐”和生主体与万物提供了先天条件;其次源于“乐”及乐器对自然万物及其生息的效仿,即“故鼓似天,钟似地,磬似水,竽笙、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万物”[18]372,钟、鼓、磬等乐器是模仿天地水、日月星辰及万物生息变化而制,并非单纯地发出声音。因此,“乐”展现雷电风雨、四时日月之和兴:“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14]993总之,“乐”与自然万物及其生息天然亲近,“大乐与天地同和”[14]988。再次乐和生主体与万物还是行乐主体忠恕万物的结果:“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14]1036行乐主体与万物同“和”最显著地体现于曾点。“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15]124朱子以为,与子路、冉有、公西赤相比,曾点通过鼓瑟达到从胸怀志气(内里)到容颜事为(外现)均与天地同和的至高境界,所以被孔子深许。曾点的境界启示“审美经验揭示了人类与世界的最深刻和最亲密的关系”[36]。也即,“乐”和万物化成上学天道、下达日用之和生人与万物的主体与主体共同体。
② 和生是指“乐”以“和”促进主体生长,进而化成主体。
据此,处于志气和生的主体既因“心必和平然后乐”[34],也因有朋志同而乐,还因和生万物而乐,并在乐中成人。乐的成人功效,孔子早已说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1]158对于知、好(去声)、乐(lè),朱熹引伊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乐之者,有所得而乐之也。”[15]86知“道”是视“道”于主体之外,主体去认识它;好(去声)“道”是主体基于知“道”而生出欲“道”之情,并由此促成行动(行“道”),但并非一定促成行动(行“道”)。一个始终仅是好(去声)“道”而不切行的主体是无法真实成人的,因为由好(去声)欲之情→人格完成必须经由“礼”约行“道”,即“学始于言,故兴于诗,中于行,故立于礼,终于德,故成于乐,礼乐者,成人之事也”[2]。经历“礼”约行“道”后的“乐”才是真正的成人之得,这一得起于主体真情实意之好(去声),自觉接受文理(“礼”)之规约,加之“乐”本身也呈出且引发快乐情欲,因而由心底生发快乐,也即成人之得合“成于乐(yue)”与“成于乐(lè)”于一。
“乐”之“乐(lè)”分为“乐欲之乐”与“乐道之乐”。“‘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18]371前者是指以感受“乐”所呈出且引发的感官快乐为“乐”的快乐;后者是指以感悟并践行“乐”所承载的“道”为“乐”的快乐[37]。“乐欲之乐”要不陶醉于“乐”炫技低俗之形式,要么沉溺于“乐”恣情纵欲之内容,郑声卫音即是代表,易成流漫鄙贱、溺志滥情之小人人格。“乐道之乐”出于真情善志,形式异文合爱,内容礼正体道,功效和生万物,雅乐正是代表,易成君子以至圣人人格,颜回是其表率。可见,“乐”之“乐”能够辨人分群,以不同的“乐”为“乐”自然化成不同的人格。总之,“乐”以“和乐”化成由内而外、由情及理至行、上学下达之志气平和、仁者和仁、和生万物的和乐主体、合爱社会与共生共同体。
-
不得不说,无论是“乐”以真情兴成真情实意主体,还是以文理约成文雅守理主体,抑或以和乐合成和生仁乐主体,贯穿三者的始终是“情”。但不同的是,“情”在“乐”之真情这里是根基,由其呈出的情性、情欲、情志因与受教者的情性、情欲、情志同真共频而兴成真情实意主体,这为“乐”之文理的约成奠定情意支撑、充沛来源与自主意愿。由此,“乐”之文理从一开始即不是外来之“理”的强制,而是内涌之“情”的需要,是“情→理”的内在情质与外在文理的合一。它因“文”而雅,因“理”有节,恰合“礼正乐”,将主体成人落实于“情”之中节、“行”之正当、“理”之普遍中,进而让主体由真情实意之个体走向多样有序之社会,更以“理”之普遍与“情”之中节为“乐”之和乐确立根据。如果说“乐”之真情为“乐”之和乐深植情性之本的话,那么“乐”之文理则为“乐”之和乐扎牢理性之末,二者一情一理地助成“乐”之和乐的实现。与此同时,“乐”之和乐对于主体成人来说,衍生为:情→理→再情之化成,由此主体化成真情实意、文雅守理、和生仁乐主体及人物共同体,乐教成其善民心、厚人伦、美风俗、共万物之效。
显然,以真情、文理、和乐成人的儒家乐教根植于性注定了它的无穷生机,从情出发彰显着它的温润养人,文理加持稳定着它的庄严节制,和乐禀性展现着它的大气包容。这一教化体系在当前多样化的人格养成中显得极其珍贵,毕竟基于真实情性的人格养成才是富有成效的,充满丰厚情意的人格教育才是感人至深的。更加难能的是,在多元文化便捷交流与多极竞争不断加剧的今天,旨在合爱同乐、超越人我、人物共生的教养志趣必将成为当今世界人们和谐共处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不可或缺的文化良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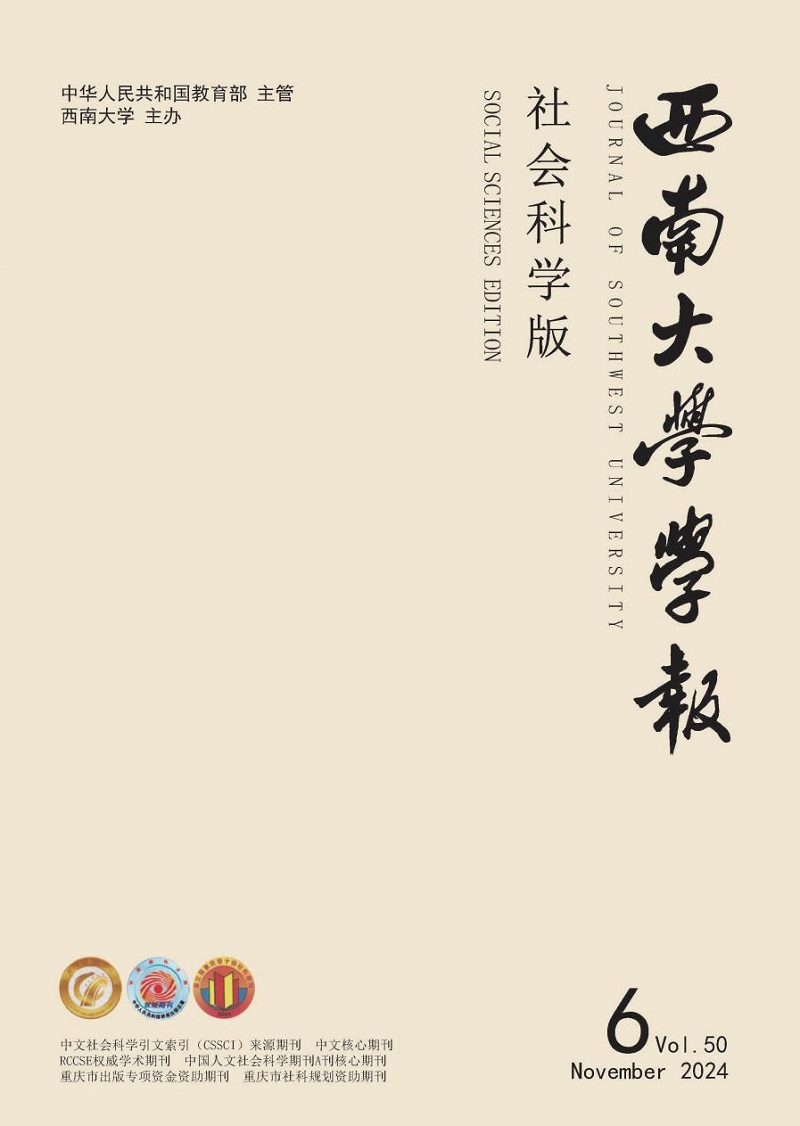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