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ML
-
“人类心灵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是构想和思考自己和他人的心灵。因为他人的心理状态完全隐匿在感官之外,所以只能被推断出来。”[1]著名发展心理学家Leslie的上述观点让笛卡尔时代以来的他心问题(problems of other mind)以“读心”(mindreading)谜题的形式在当代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中得以复兴。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的概念在读心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读心时会存取和调用我们大脑中的行为表征理论,这个假定的人类行为理论被称之为“常识心理学”。在另一些情况下,常识心理学也被指称为某种单一潜在的认知机制,它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的能力:(1)在一般情境中预测人类行为的能力;(2)把心理状态(mental states)归因(attribute)为人类的能力;(3)能够凭借人类拥有的心理状态来解释人类的行为的能力[2]。
在现实中,当我们要解释他人的行为时必须借用常识心理学来刻画他人的心理状态。例如,老王为什么会满脸笑容地从股票交易大厅里走出来,其实依据的无非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会因为自己愿望得到满足而拥有积极的情绪”的理论,即从他想要从股市获益的愿望得到满足推理出他脸上呈现出的积极情绪。当我们预测他人行为时,我们也需要利用常识心理学从过去和现在的目标环境和行为(包括言语行为)的表征中,去推理他人未来行为的表征。就像在电影《动物世界》一部以赌博游戏为故事线索的科幻片中,男主角就是采取赌博规则所依据的“想要赢的几率更大,留下的牌越均衡越可能使自己获得更大可能的胜利”这样一种理论,并由此去解释和预测他人出牌的选择。根据这种观点,读心本质上就是一种借助理论进行推理的练习。
在生活中,人们似乎很容易用自己的心理状态去描述其他人,同时也在不断地根据潜在的心理状态来归因他人的动作、姿势和面孔,试图弄清楚其他人的思想和感受,以及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这种读心能力根源于人们预测和解释他人行为的一种能力。常识心理学首次作为读心的科学问题出现在Premack和Woodruff在1978年发表的《黑猩猩是否具有心智理论》(Does the Chimpanzee Have a Theory of Mind?)一文中[3]。在该文中,他们探讨了非人灵长类动物在多大程度上能像人类意义上的理解和归因心理状态,并首次将这种理解他人行为背后思想的能力看作一种“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 以下简称ToM)的能力。之所以称这种能力为“理论”:“个体将心理状态归因于其自身以及他人(同类或其他生物体)。这样一种推理系统应被视作一种理论,首先是由于这类状态并非直接可见,其次是因为该系统不仅能够被用来预测自我的行为,还尤其能对其他生物体的行为加以预测。”[4]
随后,哲学家Morton将ToM作为读心理解和解释的取向,称之为“理论论”(Theory theory, 以下简称TT)[4]。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哲学家与心理学家将这种ToM能力运用到现实中去的过程称为心智化(mentalizing)。换言之,当人们使用ToM推测和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时,就实现了“心智化”。心智化系统在个体与他人打交道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使人们有能力去窥视他人的内心世界,去考虑他们的希望、恐惧、目标和意图,使得人们可以更加有效的互动。它还让人们有能力去猜测他人的心理特征,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预测出他人对未知情况的反应,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摩擦。利用这种能力,人们能够成功地实现与他人的合作,完成单凭个人力量无法做到的事情,同时也利用这些能力与周围的人进行策略性竞争。心智化还能够对接触到的所有信息进行筛选,筛选出最好的信息与他人分享,并且使人们知道如何与他人进行交流。
-
如果说读心是依靠一种理论,那么这种理论又是一种怎样的理论呢?Sellar认为精心编制的常识心理学的解释活动,十分类似于对复杂行为系统做出的各类科学解释过程。普通人具有的人类行为的信息体系在形式和内容上应该与科学理论相似,而获取常识心理学的过程类似于科学研究[5]。当然,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类似于复杂科学理论的常识心理学在我们生活中是十分少见的。但是站在一个宽泛的层面,常识理论就十分类似于由定律构成的科学理论。在“常识物理学”(folk physics)的框架下,物理事物的行为完全可以用物理力的影响来解释(至少在牛顿力学的范围中)。例如,用水平作用力扔出去的石块会以抛物线的方式下落。这里蕴含着一个具有类似因果推论定律的心理表征系统,用以解释或预测物理事件。同样的,它也应该可以用于对行为证据的解释和预测。例如,因为你的老板相信服用维生素C可以预防感冒,所以当你看到他走进药店时,你就会预计他会买一些维生素C片。
这种理论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并在很多时候无意识地发挥作用。那么这种读心的理论和能力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发展心理学家试图对此作出解释。Wimmer和Perner报告了“错误信念测试(false belief test)”的实验。在初始版本的测试中,实验者给儿童被试呈现一个木偶剧场景,介绍其中一个名叫Maxi的木偶,并向儿童被试展示Maxi有一块巧克力,然后将他的巧克力藏在“橱柜”——一个纸板箱里,并且宣称Maxi要出去玩并离开现场。此时再介绍第二个木偶入场,她是Maxi的妈妈。妈妈在柜子里找到巧克力,然后把它移到第二个盒子里,即“冰箱”。木偶剧的第三幕是妈妈离开,Maxi回来说要取回他的巧克力。随机暂停木偶剧,实验者会向儿童被试者提出一些控制问题,以检查他们是否理解在这个木偶剧中发生了什么。他们向儿童提问:Maxi会在哪个盒子里寻找他的巧克力?橱柜或冰箱?实验的结果非常有趣:大约四岁的孩子通常会回答说Maxi会在冰箱里寻找,而五岁以上的孩子通常会说Maxi会在橱柜里寻找。该实验解释,小于四岁的孩子一般缺乏作为一种心理状态的信念观念,或者只有一个很薄弱的信念观念,尤其是,他们并不理解信念,会去歪曲现实。他们认为Maxi会根据现实的状况行动(巧克力被转移到了“冰箱”),而不理解Maxi会根据他的错误信念行动(我不知道巧克力被转移了为止,所以我会去“橱柜”里找)。五岁以上儿童之所以能顺利通过这项测试,是因为儿童已经知道他人有思想和信念,对错取决于他人现在的知识,他人的行动是由他们自己心理状态产生的,而不是现实世界决定的[6]。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儿童的心智理论是不断在发展完善的。进一步的研究考察了这种理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并掀起了关于先天主义(nativism)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争论。
先天主义的重要支持者Gopnik提出了“小科学家的儿童观(child as little scientist view)”。该假说大胆猜测,驱动儿童常识心理学的发展机制就是驱动成人科学家科学理论发展的机制。她认为科学的进步模式在常识心理学上得到了重述,通过一种近乎普遍(near-universal)的发展途径来获取存在的近乎普遍的能力,常识心理学的发展受到儿童基因的深刻影响。幼儿的知识在结构上与科学理论相似,但不一定像科学家那样学习。这可能是因为大部分的知识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学习获得的,它们是由进化决定的,而不是从经验中推断出来的[7]。
在很大程度上,儿童就像科学家们所做的那样使用数据来制定和检验假设和理论。科学家从三个方面了解这个世界:他们分析数据中的统计模式,开展实验,并从其他科学家的数据和想法中学习。最近的研究表明,儿童也通过这些方式学习,他们往往像理想的贝叶斯学习者。概率模型对儿童的学习做出了准确而详细的预测。例如,Xu和Garcia的实验使用了一种被广泛用于研究婴儿认知的“观察时间”技术,即婴儿观察意外事件的时间更长。该实验给婴儿看了一个装满白球和红球的盒子。然后主试闭上眼睛,随意地从盒子里拿出一些球,放进另一个小盒子里。如果样本确实是随机的,那么箱子中的球的分布应该与盒子中的球的分布相匹配。婴儿会看到一个分布相匹配或不匹配的样本,他们对不匹配的样本进行了更长时间的观察(当实验者从一盒主要是白色的球中取了一个主要是红色的乒乓球样品时,婴儿观察的时间比从一盒主要是红色的球中取出主要是红色的球的时间要长)。在控制条件下,婴儿只看到相同的事件序列,但实验者将球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来,而不是从盒子里拿出来,这种情况下婴儿在观察时间上的差异消失了。该实验显示,八个月大的婴儿对统计抽样模式很敏感[8]。这暗示了人类在抽象的因果关系上的知识或许是先天的。五岁的孩子是卓越的读心者,因此必须具有一个广泛的常识心理学概念体系。但是,他们无法从环境中获取这些概念和信息——他们的环境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学习机会。因此,相当多的常识心理学必定是天生的。
与此相对,经验主义者阐述了后天环境的重要性。“认知生态位建构理论(epistemic niche construction)”提出者Sterelny认为,动物可以改变它们的环境去产生新的信息,使旧信息更加突出,并减少认知需求,有时这些环境的修改持续时间足以增强下一代的适应性。例如,一旦原始人发明了可以随身装水的工具,他们就能从日益干枯的自然环境所带来的选择压力中逃脱出来[9]。类似的,父母可以通过提升他们自身获取常识心理概念和信息的方式来改变他们孩子需要适应的环境。例如,父母的社会认知能力对儿童读心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其中,特别重要的两个因素分别是:(1)父母推断其婴儿心理状态的能力;(2)他们将婴儿视为具有独立心理状态的个体的能力。前一种能力即是“心智化”。后一种能力被称为“心智概念敏感性”(mind-mindedness),被认为是一种相关但更具体的概念[10]。尤其是在亲子关系中,它指父母倾向于将其婴儿看作“一个有心灵的个体,而不仅仅是必须满足需求的生物”[11]。具有较高心智概念敏感性的父母,会将儿童当做有心灵的谈话对象,而他们的孩子也会有更好的读心能力[12]。Hutto建议采用讲故事的方式提升心智化。在许多故事中人物的环境,心理状态和行为有明显的联系,因此可以促进孩子对这些联系的理解[13]。孩子要获得许多这些读心知识,但往往孩子们是不能直接经历的,父母就需要用间接的方法去帮助孩子掌握读心知识。例如,在给孩子读《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绘本时,当白雪公主要吃坏皇后给的毒苹果,坏皇后是知道苹果有毒的,但是白雪公主不知道这个苹果是有毒的。那父母就要传递白雪公主认为苹果是新鲜的并且可以吃的信念,即白雪公主的信念是错误的信息。此时,父母可以提“坏皇后想要干什么?”“白雪公主会认为这个苹果可以吃吗?”等问题。当孩子把信念、意图和愿望等心理状态和行为联系在一起时,我们发现那些孩子读到这会感同身受,他会为白雪公主要咬这个苹果而感到紧张。这些丰富的信息可以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实现。故事叙事是心智概念敏感性能力的重要载体。
-
上述讨论呈现了人类读心能力及其发生的复杂性,理论论将心智化预设成了一种理论形态的能力。虽然人类在学龄前就已经开始发展理解他人信念和观点的能力,但直到成年之后,人们在运用这种能力时仍然显得不够高效。尽管如此,心智化仍然是人类大脑发育的一个标志性成就,将人类和其他物种区分开来。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Baron-Cohen就曾提出人类有一个视觉方向探测器(eye-direction detector, EDD),可以探测到类似眼睛的刺激并计算注视方向。这种机制与意向性检测器(intentionality detector, ID)和共享注意机制(shared attention mechanism, SAM)相结合,触发了心智理论机制(Theory-of-Mind-Mechanism, ToMM)的发展,该机制帮助我们推断他人的心理状态,比如意图、信念和欲望[14]。因此,EDD、ID和SAM是一种先天预存于大脑中的心智化模块,这也部分支持了Gopnik提出的小科学家儿童观,但更多的神经科学证据则是指向了心智化的建构主义立场。
近来的ERP、MEG、fMRI以及fNRIS等脑成像研究表明,基于信念来理解和预测他人行为的基本神经结构可能在人类生命早期(大约七个月)就存在了[15]。这些脑区包括双侧内侧前额皮层、脑岛、次级感觉皮层、背侧前中部扣带回、颞顶联结、颞上沟等,统称为“心智化系统”(mentalizing system, MENT)[16]。心智化系统的设想将我们对他心进行推断的能力或心智理论视为一种封装的模块化(modularity)加工过程。
其中,心智化系统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是内侧前额皮层(MPFC)及颞顶联结(TPJ)。例如,在经典心智理论的任务中,要求被试对他人的意图和信念进行推断,激活了内侧前额皮层及颞顶联结。当我们对他人心理状态进行思索时,内侧前额皮层始终处于激活状态[17]。当我们对他人当前的信念进行推断,评价他人的长期心理特征和性情状况,以及我们对自己的心理状态进行思考时该区域也会激活。事实上,当我们对动物的心理进行推断时其也会激活内侧前额皮层[18]。总之,即便我们没有与外面世界进行互动,无论何时,只要我们对心理进行思考,内侧前额皮层就会产生自发的活动[19]。当我们产生有关自己或者他人心灵的认识时,后扣带回皮层也会被激活,在休息时该皮层显示出与内侧前额皮层功能性耦合的属性[20]。
为了更加逼真地模拟现实生活中社会互动的卷入性特征(engagement)(即被试作为互动的真实参与者而不仅仅是旁观者),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新的实验范式,让被试得以在接受脑部活动记录的同时,通过一个屏幕实时地看到另外一个由真人控制的虚拟形象的眼部活动。因为各自的眼部活动和注视的方位在实验中可以被对方看到,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第二人称的社会互动。被试在两种条件下进行这种互动,用自己的目光引领他人注视屏幕上三个物体中的一个,或者被试跟随他人的目光去注视三个物体中的一个,从而形成共同注意(joint attention)。在这两种条件下,有一些实验试次会让在互动中处于追随地位的那一方故意不配合,让实验中没有出现共同注意。研究人员预测在有归因关于他人心理状态时,内侧前额皮层会在任务中激活,并且神经活动在由自己引起的共同注意和他人引起的共同注意之间会有区别。实验结果支持了这些假设,在形成共同注意的条件下的确引发了内侧前额叶的激活,并且内侧前额叶的前部在由自己引发的共同注意中激活程度高于由他人引发的共同注意[21]。
Mar对86项fMRI研究的元分析显示,在人类大脑中用于理解故事的神经网络与用来引导我们与其他个体进行互动的神经网络存在大量重叠。例如,内侧前额皮层(mPFC)、双侧后侧颞上沟和颞顶联结(pSTS/TPJ)、双侧前颞区(anterior temporal areas)以及左侧额下回(IFG)等[22]。在社会互动中,我们试图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而叙事恰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让心智理论卷入其中。我们会尝试确认故事中角色的渴望和挫折,猜测他们隐藏的动机,追寻他们与朋友、敌人、邻居和爱人的遭遇。甚至,当研究者用计算机生成了圆形、方形、三角形等几何图形,并让它们随机互动,产生了各种毫无意义的情境,然后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被试去解释这些随机运动产生的原因。所有被试都能赋予这种无意义的情境以各种具体的叙事特征,并将这些图形视为有生命的(animate),带有某种意向性心理活动的个体[23]。近期的fMRI研究发现,人类大脑的右后部颞上沟(pSTS)、左侧顶内沟后部(aIPS)负责意向性检测,在将几何图形的运动感知成具有生命性的过程会产生激活[24]。这些心智化系统的组成部分与心智概念敏感性可能存在着某种交互作用,后者促进前者的成熟,成为讲故事之类叙事实践建构理论的重要基石。
颞上沟也是心智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区域与行为识别(behavioral identification)相联系,尤其是对于有意图的行为。观看以不同方式执行的具有相同意图的行为(例如,以不同方式抓握花生),激活了灵长类动物颞上沟中的相同神经元。然而,那些不带有意图的行为(例如,跌倒)却不能激活该脑区[25]。该脑区对于从知觉到的生物运动中提取可能的意图这一过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对几何图形的随机运动识别成生命性的脑成像研究中也发现了该脑区的激活,这表明其在从行为识别意图的过程中起着一种更一般的作用。当视频中的这些几何图形似乎在打架时,与人们真实的打架中观察到的生物运动在视觉上很少有共同点。然而,当被试观看这些视频剪辑时,他们想象到了真实的人类行为,并且以一种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方式激活了颞上沟。具体而言,复杂的生理活动携带的生命性(animacy)信号会激活高阶视觉区,该区域位于颞上皮层后部,是进行客体确认(包括梭状回面孔区)和视觉导向行为加工流的交界处[26]。该区域毗邻颞顶联结,并很有可能向颞顶联结输入信息,而颞顶联结参与到了当我们对他人的信念进行猜想时可以产生不同的空间视角以及对他人的不同理解中。
-
如果人人掌握这些理论,这就意味着我们都能成为有超能力的读心者?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种常识理论很少像科学理论一样能够被清楚地表述出来。理论论者试图努力阐明这个理论原理,但是一直没有为常识心理学定律找出合适的候选者。Carruthers曾尽可能地列出一些候选定律。例如,“有人想让q状态出现。他相信,如果p那么q,并相信自己有能力使p出现;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就会形成一个促使p出现的意图。若有人已经形成了意图,促使‘R出现,p就出现’得以实现,且他相信R会出现,因此,他就会采取能够促使p出现的行动”[27]。例如,小李想要向女友求婚,并且他相信“求婚仪式如果能够在一个美丽的小岛上举行,那么女友就会同意”。小李有能力在小岛上举行,那么他就会将求婚仪式举行在小岛上,来促使“女友答应求婚”愿望的实现。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常识心理学至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类似于定律的推论。这就使人怀疑,常识心理学是否能够明确地解释哪怕是最简单的社会互动过程。然而,即使我们对其描述是十分有限的、不足的,且通常是内隐的,但是常识心理学的解释能力却是十分世故练达的,并被我们在生活中无意识的熟练的加以应用。
考虑三个经典的情景,罗密欧以为喝下安眠药的朱丽叶已经死去因而伤心过度自杀;贾宝玉称新婚之夜为“天上人间第一件畅心满意的事”是因为他以为红盖头之下的是林黛玉;梁山伯在《十八相送》中对祝英台的诸多示爱置若罔闻是因为他相信祝英台是男的。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怀疑上述常识理论的可靠性。因为这种在大脑中的行为表征理论常常在许多方面表现的是不明确的,而且往往还包含着许多隐藏的条件。罗密欧只知道“爱人会因为无法得到爱情而殉情”,却忽略了“在没有其他情况下,例如朱丽叶已经找到了可以和爱人在一起的办法”。我们可以从这些理论在表述时常附带众多的条件句(如“所有情形都是相等的条件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等)看出来。这些理论对于所描述状态产生的条件无法给出精确定义,也无法对背后的动态机制给出明确而无例外的描述,它们只能对知觉、思维和行动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给出一般性描述。Wellman称这样的描述为“框架理论”(framework theories)。“框架理论”只能对相关研究领域的实体因果机制给出一般性的定义,而不能推论得出具体的、局部的、个性化的因果关系[28]。例如,即使一个简单的手势在不同的国家也都会带有自己地域特征的不同意义(用食指和拇指搭成圆圈一般示意“一切都好”,但在希腊或土耳其这却影射对方是同性恋或象征“滚开”),常识理论很可能是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来加以描述的。
至于奠基在常识心理学之上的读心理论究竟是如何产生、发展与成熟的,也仍然缺乏一种系统、精确的科学描述:“无论这一理论的成果如何丰富,它都存在着一个核心理论的模糊性。支撑理论的表征和支撑理论变革的学习机制都还不清楚。认知科学的基本观点是将大脑视为一种由进化设计来执行特定认知功能的计算机。发展认知科学的前景是我们可以发现发展背后的计算过程。与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一样,该理论也缺乏实现这一承诺的精确性。至关重要的是,它缺乏一个令人信服的计算方法来解释让理论发生变化的学习机制。这个理论的核心类比是儿童的理论就像科学理论一样。但这个类比只是第一步。我们需要理解理论变化在原则上是如何发生的,无论是在童年时期还是在科学领域。”[29]
在神经科学上,对读心理论论合理性的检验有赖于进一步研究与ToM理论变化相关的大脑结构/系统。例如,皮层中线结构(cortical mid-line structures)(包括内侧前额皮层、后内侧顶叶皮层、前扣带回喙侧区、后扣带回与楔前叶)以及颞顶联结,了解这些脑区的发育变化如何与促进ToM的理解相关联。也许在幼儿时期变化最大的系统或者显示出联结变化证据的系统是在推动概念变化方面发挥作用的系统。同样,已有研究发现经验提炼会塑造产生大脑白质联结的变化,这可以作为儿童经验驱动概念发展的研究证据[30]。我们可以预期,随着理论的修订和ToM理解中概念的发展,儿童时期的神经结构会发生变化。
迄今只有少数研究关注了ToM的概念变化是如何反映在神经机制上的,但研究人员可能会从其他神经成像领域获得灵感,在这些领域中概念变化和神经变化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了更全面的映射。例如,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的差异神经激活。事件相关电位在外显记忆检索和隐式记忆检索中表现出不同的时空成分[31]。内隐记忆检索依赖于前额叶、梭状回和纹外区,而外显记忆检索依赖于后扣带回、楔前叶和顶下小叶。上述例子或许适用于对ToM的早期形式或前体(precursor)的理解,这些心智化的早期形式在婴儿期或童年早期可能代表了一种内隐的心智化,而更多以言语形式呈现的心智化(例如,学龄前儿童的错误信念表现)可能代表一种外显的心智化[32]。
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内隐和外显的心智化过程可能依赖于部分独立的大脑网络,就像内隐和外显记忆过程一样。此外,伴随儿童的成长,对心理状态概念的理解在概念上的进步,也会发生从内隐到外显的转变。Wellman等发现,婴儿对有意行为的注意可以预测他们学龄前期对ToM的理解,这表明从内隐心智化到外显心智化之间存在联系[33]。然而,未来的神经证据是否可以支持理论论,我们需要确定的是:(1)内隐心智化和外显心智化是否如同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一样有着泾渭分明的神经基础。例如,将几何图形的随机活动视为生命性中产生激活的脑区(颞上沟),或许是内隐心智化系统的组成部分,而在错误信念任务中推断和预测Maxi行动意图激活的脑区(内侧前额叶与颞顶联结),则是外显心智化系统的组成部分。(2)心智化从内隐转变为外显的过程,是否伴随着神经活动的变化,尤其是两种心智化系统在脑区之间连接的形式是否发生了变化。
最后,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厘清是否存在支持不同类型的心智理论判断(例如,“信念归因”、“情绪归因”)的一般机制,或者不同的独立结构是否共存并支持每种类型的心智化推理[34]。例如,识别他人躯体感受状态(如饥饿、疼痛、痒)的功能和判断他人心理状态(如信念、愿望)的功能在脑机制上的差异。现有的研究已经发现,前者主要涉及双侧颞顶联结、前躯体感觉区、背侧前额皮层、中前额皮层和腹内侧前额皮层,后者主要涉及双侧内侧额叶、脑岛、次级感觉皮层、背侧前中部扣带回[35]。近期,Richardson等对122名3~12岁的儿童和33名成年人进行fMRI研究显示,心智理论网络内部区域之间的连接程度与心智理论测试任务成绩正相关,心智理论网络与疼痛脑网络之间的同步程度则与心智理论测试任务成绩负相关。这意味着儿童心智理论网络内部脑区之间的联系越紧密,同时心智理论与疼痛脑之间的功能越分离,其心智理论发展得越好[18]。因此,深入探索心智化系统与其他社会脑(social brain)网络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助于精细刻画作为常识心理学神经基础的心智化系统,从而激发有关读心问题的新的哲学争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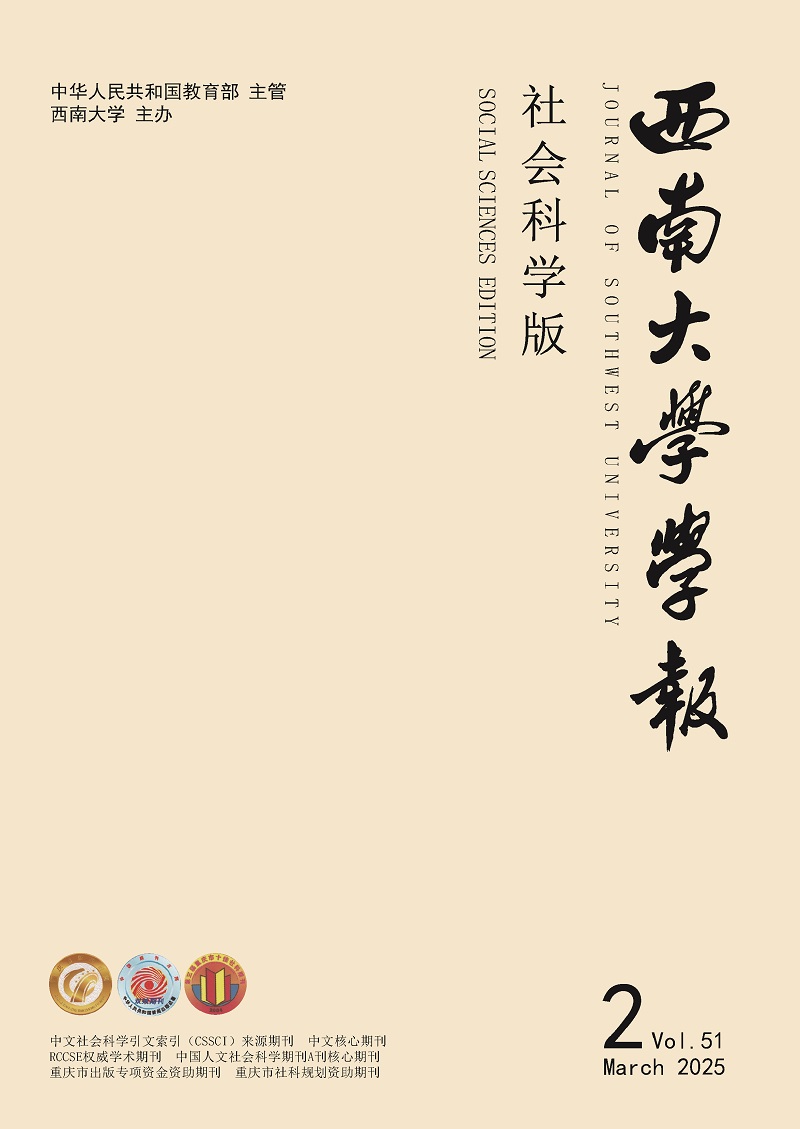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