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晚期罗马帝国历史上,曾多次暴发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这些传染病均具有突发性、传播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受到科技水平和医疗条件的限制,帝国民众对传染病的病因、致病机理、传播媒介等缺乏全面系统的认知。因此,在传染病突然大规模暴发之际,民众最直接的反映是畏惧与恐慌。在缺乏有效治疗和防御手段的情况下,民众极易陷入绝望情绪之中。面对传染病所造成的严重危机,在帝国政府救助不利之际,民众的恐慌、绝望情绪往往会出现恶化的趋势。
与大规模传染病数度暴发的同时,基督教在晚期罗马帝国治下的地中海地区迅速传播。民众开始将希望寄托于可以为其疑惑提供合理解释的基督教教义之上。出现于公元元年前后的基督教逐渐在晚期罗马帝国显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信教人数大幅度增加、教会组织更加严密。民众向基督教信仰的转变引起了晚期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注意,基督教可为民众提供精神慰藉,教会内部也出现对帝国统治者的迎合,而统治者出于精神领域治理国家的需要转向支持基督教的发展。此后,基督教于4世纪末成为帝国国教,同时在5、6世纪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此可见,晚期罗马帝国多次大规模传染病的发生与这一时期民众信仰的转型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对于晚期罗马帝国数度暴发的传染病以及基督教在这一时期展现出的强劲发展趋势,部分学者关注到传染病的流行对罗马民众的生活及社会习俗所产生的影响①,也有学者对传染病的发生与基督教的兴起进行了整体考察①。然而,有关晚期罗马帝国的传染病与民众信仰的关系问题,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有鉴于此,笔者以迪奥·卡西乌斯、尤西比乌斯、左西莫斯、普罗科比、埃瓦格里乌斯等史家的记载为基础,同时结合近现代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希望厘清晚期罗马帝国的传染病与民众信仰之间的关系。
① 马库斯·劳特曼指出,传染病的发生导致城市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并对传统习俗不利(Marcus Rautman, Daily life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Westport: The Greenwood Press, 2006, pp.67-68; p.78.)。迈克尔·安戈尔德以“查士丁尼瘟疫”的暴发为例,论述了传染病对民众精神层面所产生的影响(Michael Angold, Byzantium: The Bridge from Antiquity to the Middle Age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1, pp.25-26.)。约翰·莫尔黑德也对传染病所造成的精神恐慌进行分析(John Moorhead, Justinian,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ing, 1994, pp.99-100.)。
① 丹尼尔T.瑞夫认为传染病的发生与基督教兴起之间存在联系(Daniel T. Reff, Plagues, Priests, Demons: Sacred Narratives and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in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47-63.)。彼得·布朗将传染病作为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布的因素加以论述(Peter Brown, Authority and the Sacred: aspects of the Christianisation of the Roman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72.)。罗德尼·斯塔克认为传染病的流行促使了基督教的快速发展(罗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黄剑波,高民贵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87-91)。姬庆红曾就古罗马时期的大瘟疫与基督教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姬庆红.古罗马帝国中后期的瘟疫与基督教的兴起.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144-147)。
HTML
-
长期以来,作为地中海地区②的主宰者,罗马所统治的这一区域人口密集、商业发达、交通便利。同时,罗马统治的地中海地区因受到其所处地理位置与气候特点的影响,极易发生疫病。一旦疫病暴发,便会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瘟疫”曾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暴发之初发生在希腊世界最著名的城邦雅典,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对瘟疫的发生情况进行了详细记载[1]343。公元2世纪的“安东尼瘟疫”暴发于皇帝马可·奥里略(公元前161—180年在位)统治时期,地点同样位于地中海地区。此次瘟疫的最初传播与罗马帝国东部边疆的战争有关。在与安息国王进行激战后,卡西乌斯军队返回的途中,由于饥荒和疾病,大量士兵死亡,卡西乌斯带着幸存者们回到了叙利亚地区[2]5。在“安东尼瘟疫”流行过程中,罗马城受到瘟疫的打击尤其严重[3]73-75。相比之下,晚期罗马帝国时期出现的传染病,其发生规模似乎更大、影响区域也更广。公元3世纪中后期直至6世纪,罗马治下的地中海地区分别于250—265年、312—313年、451—454年、541—544年间发生了4次大规模传染病。
② J.唐纳德·休斯认为,地中海地区是对一个与海洋间紧密联系的地区进行的定义,而不是一个陆地区域的概念。地中海地区的居住环境是由这一地区的居民塑造的,而地中海地区的民众也伴随着他们周围的环境成长起来,并受到环境的极大影响(J. Donald Hughes, The Mediterranea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2005, pp.1-2.)。
从公元250年开始,罗马帝国境内暴发了一次严重传染病,这次传染病的流行前后持续了约15年,史称“西普里安瘟疫”。根据尤西比乌斯的记载,这次传染病最初是从埃及地区扩散到帝国境内[4]286。作为帝国的政治中心,罗马城在这次传染病流行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据记载,罗马城大规模暴发疫病后,城内每天的死亡人数高达5 000人[4]286。史家左西莫斯的记载有效补充了这次传染病的相关情况,左西莫斯指出:“在伽鲁斯(Gallus,251-253年)统治期间,251年前后,帝国境内的很多城市和村庄发生传染病,居民遭遇灭顶之灾。传染病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影响。”[5]8史家也关注到这次传染病导致受到蛮族③入侵之后的帝国诸多城市遭遇双重打击:当伊利里库姆地区受到斯基泰人入侵之时,帝国境内的几乎所有地区与城市都遭遇了一次突发疫情的影响。之前被蛮族占领的城市现在全部沦为空城[5]12。鉴于对“西普里安瘟疫”进行记载的史家均未提及患者感染疫病之后的症状,因此,这次传染病的病因难以确定。沃伦·特里高德认为,这次疫病的性质很可能是麻疹[6]7。
③“蛮族”一词的使用无关个人观点,而是基于约定俗成。
312—313年,罗马帝国再次发生大规模传染病,帝国东部地区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尤西比乌斯对这次疫病的原因及患者症状等进行了详尽记载。尤西比乌斯提到:“这一年的冬季并未像往常一样下雨,饥荒和疫病共同打击着人类。在无法获取充足的食物之时,民众便如同鬼魂般地蹒跚于街道之上,直到倒地身亡。由于长时间的食不果腹,部分民众趴在街道中间,用尽力气大喊‘好饿’。当城市内部遍布尸体后,疫病随之发生,无数的家庭受到影响。”[4]328以史家的记载为基础,我们发现,这次疫病的发生与长期的食物短缺有着密切联系。尤西比乌斯还补充道:“患者患病后的特征之一就是皮肤表面呈现出红色,并且突起形成了痈(carbuncle)。这种疾病非常可怕,一旦被感染,它会扩散至病人的全身,对眼睛的打击尤其严重,很多男人、女人和小孩染病之后出现失明的症状。”[4]327根据史家所提到的感染、失明、身体出现脓包的疫病症状判断,迪奥尼修斯·斯塔萨科普洛斯认为这次流行于帝国东部的传染病极有可能是天花[7]92。丹尼尔T.瑞夫也持相似观点[8]47。
在312—313年疑似天花的传染病发生100多年后,451—454年间,罗马帝国东部区域再度出现症状与天花高度相似的传染病。这次传染病的主要史料来源于埃瓦格里乌斯的《教会史》。与312—313年传染病相似的是,451年开始暴发于帝国东部的传染病也与食物短缺有着直接关系。埃瓦格里乌斯指出:“这次疫病的发生是由于帝国东部的弗里吉亚(Phrygia)、加拉提亚(Galatia)、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和西里西亚(Cilicia)等地区遭遇严重干旱。为了维系生命,这些城市的居民不得不食用一些无益于身体健康的食物。于是,疫病开始在城内蔓延。”[9]81-82长期的食物短缺导致大批民众因营养不良进而失去抵抗力,因此极易受到疾病的感染。埃瓦格里乌斯对患者症状进行了记载:食物的缺失造成了疾病的蔓延,炎症令身体发胀、眼睛失明,同时伴随着咳嗽。在患者出现这些症状后,死亡往往接踵而至[9]81-82。从患者症状来看,451年开始流行的传染病很可能是天花。
从541年起,地中海地区又一次暴发大规模传染病。传染病发生之时,正处于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Ⅰ,527-565年在位)统治时期,这次大规模的传染病被后世学者称为“查士丁尼瘟疫”。由于这次传染病的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之后在地中海世界多次复发,因此引起了同一时期多位史家的关注。“查士丁尼瘟疫”是晚期罗马帝国时期史料记载最详细的一次传染病。以史料记载为基础,我们发现,“查士丁尼瘟疫”在地中海地区最先出现的地点是位于亚历山大里亚东部的培留喜乌姆(Pelusium)。在培留喜乌姆暴发疫情后,传染病随着商贸与军事活动,沿水路和陆路向东、西在地中海世界进行广泛传播。亲历“查士丁尼瘟疫”的史家普罗科比曾宣称:民众的居住环境、生活习惯、兴趣活动均不相同,但是,这次疫病却对所有人均一视同仁[10]453。在541-544年间,“查士丁尼瘟疫”几乎传播至地中海周边的所有地区,对包括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罗马等在内的帝国重要城市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这次传染病的详细传播路线可参见笔者著作的图表部分[11]409。
在疫情出现于君士坦丁堡之后,繁华的首都变成了人间地狱,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创下了每天数千人死亡的可怕数字[10]453-471。由于君士坦丁堡城内人员死亡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掩埋尸体的速度,因此,遍布尸体的首都被尸体散发出的恶臭重重包围,生存环境极其恶劣[10]469。此次疫情直至544年过后才逐渐减弱。对这次传染病进行记载的史家们几乎都提到了相同的症状,即患者在感染疫病后普遍在腹股沟处出现脓包和肿块。普罗科比指出:“患者往往在染病之后出现腹股沟淋巴结的肿胀,肿胀的现象不仅会发生在腹股沟附近,也会出现在腋下。”[10]457-459除亲历传染病在君士坦丁堡大暴发的普罗科比外,长期居住在安条克的埃瓦格里乌斯也对患者的症状详加记载,他也提到患者身体的肿胀[9]231。米提尼的扎卡里亚的作品也有患者身体出现脓包的记载[12]313。根据多位同时代史家提到的患者腹股沟处肿块的症状,结合自然科学界对6世纪欧洲地区患者遗体的骨骼残骸的脱氧核糖核酸(DNA)的考察[13],541—544年流行于地中海地区的传染病极有可能是鼠疫在这一地区的首次暴发。
综上所述,晚期罗马帝国暴发的四次大规模传染病不仅影响范围广泛,而且持续时间长。地中海地区向来是人员密集且流动十分频繁的区域,加上晚期罗马帝国时期繁荣的商贸活动和多次发生的战争,导致传染病的影响范围往往突破了一个城市或地区的限制,在一段较长时期内不断地出现于帝国大部地区。
-
得益于科技及医疗水平的飞速发展,麻疹、天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的致病机理、传播方式等在当今社会已经不是秘密。但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对于当时的政府和民众而言,晚期罗马帝国四度暴发的传染病均是前所未有的未知病症。在暴发疫情后,民众最直接的反应是求生,因此,一旦发现受到感染,惊慌失措的民众便争相涌入当时的医疗场所寻求救治。然而,当时的医院、收容所等机构并无现代医疗手段与技术,对于这些传染病的病患并无对症之方,能够提供的仅仅是日常针对病患的基础性的照料与护理,难以应对大规模疫情的侵袭。以541年鼠疫的大规模暴发为例,由于医护人员从未见过这种病症,因此,对其致病机理和治疗方式茫无头绪。医护人员尝试按照常规方式治疗患者,但丝毫没有效果。虽然医护人员曾经解剖病患尸体上的肿块,但是也没有找到真正的病因。因此,鼠疫暴发后,面对患者数量的显著增加,医护工作者只有以极度耗费体力的方式对病患进行照料[10]461。
晚期罗马帝国不完备的医疗体系在面对大规模传染病之时的无所作为,进一步加重了传染病的恶劣影响。传染病在晚期罗马帝国的多次流行造成了作为帝国经济支柱的人口出现显著下滑的趋势。正因如此,我们能够看到史家所留下的触目惊心的人口死亡数字。尤西比乌斯指出,当“西普里安瘟疫”在帝国境内肆虐时,罗马城曾有每天5 000人死于瘟疫的记录[4]286。不仅如此,他补充道,“西普里安瘟疫”造成很多大城市人口的锐减,如今14~80岁之间的人口数量比从前40~70年龄段的人数还要少[4]267。4—5世纪发生的两次高度疑似天花的传染病也造成了严重的人口损失。在312-313年疫情蔓延期间,城市的各处都可以看到葬礼仪式,疫情几乎出现于每个家庭[4]328。根据普罗科比的记载,541年开始流行的鼠疫更是令君士坦丁堡曾出现每天数千,甚至上万人丧生的可怕数字[10]465。
由此可见,在晚期罗马帝国,当流行性传染病大规模暴发之时,由于传染病的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又难以在短期内找到病因并且对症下药,因此,患病的民众无法在医院得到有效治疗,生命朝不保夕。传染病所造成的人口损失往往以社会最基本单位——家庭为表现形式。在经历了“西普里安瘟疫”的打击之后,亚历山大里亚的每个家庭都不止出现一位死者[4]267。312—313年疑似“天花”的传染病流行期间的情况也十分相似,“疫病感染了几乎每个家庭,每个家庭在疫情中的平均死亡人数为2至3名家庭成员”[4]328。在541年鼠疫暴发及多次复发之际,史家埃瓦格里乌斯亲历了多位家人的先后离世。在埃瓦格里乌斯所记录的最新一次的疫情传播过程中,他又失去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外孙[9]231。家庭成员的损失令人们的绝望情绪倍增。
因此,在传染病流行之际,受到亲朋好友在未知病症的折磨下相继病逝的打击,终日处于死亡的阴影笼罩之下的民众普遍惶惶不可终日。此时的民众不禁会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可怕的病症?自己是否会像亲朋好友那样死去?除了通过观察传染病发生后所表现出的特点进而判断自己该采取何种保命手段外,民众别无他法。有多位家庭成员丧生于鼠疫疫情的埃瓦格里乌斯在心有余悸之余,将鼠疫的流行称为最大的灾难,其影响超过曾经出现过的一切灾难[9]232。同时,害怕感染的民众会出现对病患避之唯恐不及甚至极度冷漠的态度。由于害怕传染,民众人人自危,陷入恐惧之中。541年鼠疫流行之际,君士坦丁堡的民众都安静地待在家中不敢出门[10]465。
与此同时,传染病发生后,幸存民众的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威廉·H.麦克尼尔认为,传染病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往往比单一的人口损失更为严重。通常的情况是,幸存者变得意志消沉,对传统习俗和信仰失去信心,因为这些传统习俗没有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去应对这些灾难[14]43。“安东尼瘟疫”于250年在罗马境内暴发并持续了十余年的时间,史家指出,令当时民众极为不解的是,为什么无法摆脱疾病的困扰[4]267。在晚期罗马帝国,传染病的数度暴发令民众滋生恐慌和绝望情绪,严重扰乱了罗马民众的正常生活及精神世界,许多医护人员由于面对传染病毫无对策而对自己丧失了信心[15]26。
在帝国医疗体系面对疫情束手无策之际,晚期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各级官员均有在疫情中受到感染甚至死亡的记载,这对已濒临社会失序状态的晚期罗马帝国更为不利。史家左西莫斯指出,“西普里安瘟疫”的暴发是导致克劳狄二世(Caludius Ⅱ, 268-270年在位)死亡的直接原因[5]14。尤西比乌斯也有相同记载[4]287。根据尤西比乌斯大为夸张的说法,312—313年的瘟疫暴发期间,躲过了饥荒威胁的富裕者、统治阶层和官员们在传染病面前无一幸免[4]328。这种夸张说法之产生应当与传染病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关。无独有偶,查士丁尼一世也曾在鼠疫于君士坦丁堡大暴发之际染病,虽然他本人十分幸运地恢复了身体健康,但是皇帝染病却导致上层阶级出现了一次将军被控谋反并受到严厉惩处的事件,有碍于政局的稳定和帝国的对外战争表现[16]。
在实行集权统治的晚期罗马帝国大规模暴发疫情期间,被视为上帝代理人的皇帝的突然染病甚至死亡,会直接导致政治混乱从而加深民众的绝望情绪。官员的死亡以及为求自保的避疫也会对政府的正常运转造成不利影响。根据普罗科比的记载,在鼠疫疫情于542年出现于君士坦丁堡之时,城内的官员都静悄悄地待在家里,街上见不到身着官服之人[10]453-471。正因如此,在传染病发生后,晚期罗马帝国政府往往难以组织起有效的灾后救助。在“西普里安瘟疫”及312-313年、451-454年疫情暴发后,史家对疫情发生后尸横遍野的惨状进行了详尽地描述,然而,却没有提到任何来自于政府的救助。541年开始流行的鼠疫在君士坦丁堡大暴发后,除塞奥多鲁斯(Theodorus)奉命处理尸体的细节被记录在案之外,史家也未提及任何有效的应对举措。不仅如此,当死者尸体无法逐一处理时,塞奥多鲁斯采取了非常举措:挖坑就地掩埋、全部丢弃于塔楼、装入船只随风飘走。处理尸体时,也没有举行葬礼仪式[10]467-469。疫情危机之下的应急举措虽然是不得已之举,但是从客观效果来看,这不利于缓解民众的恐惧、绝望情绪,反而恶化了社会的道德秩序。正如约翰·莫尔黑德所指出的,对死者不敬的处理方式在鼠疫大暴发期间大行其道,势必对帝国的传统道德造成恶劣影响[17]99。
总而言之,对于晚期罗马帝国而言,数度暴发的传染病导致帝国人口在短期内出现剧烈下滑的趋势。民众不仅充当着纳税人、劳动力的角色,也是潜在的士兵来源,因此,帝国的整体实力不可避免遭到削弱。多位统治者在疫情期间染病甚至死亡进一步影响到政府灾后救助的实施。多次疫情暴发后,民众不仅难以得到及时的医治和救助,同时在极度恐惧和绝望的情绪影响下,逐渐丧失了对帝国政府的信心,变得无所依靠。此时的罗马民众能够寄予希望的似乎只有遥不可及的神明了。
-
在晚期罗马帝国时期,由于对传染病发生原因缺乏科学解释,当时的医疗技术在面对大规模传染病之时往往束手无策,因此,帝国民众在传染病的多次打击之下除了坐以待毙之外,唯有求助于宗教,以获得神灵保佑。沃伦·特里高德认为,作为宗教信仰,基督教与多神教完全不同。多神教是一个没有明确的教义、道德准则或组织机构完全不同的信仰和祭祀团体。多神教中的神明不仅数量多,而且较为随意,很多神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是极为相似的。这些神明赐予崇拜和祭祀者以福报,但难以对他们的道德行为进行规范[6]44。在治愈完全丧失信心且极度恐惧的民众心理方面,多神教的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民众对传统多神教的信仰势必受到其他宗教的挑战。
正当罗马民众普遍因传染病的多番侵扰而出现疑惑不解、恐慌、绝望情绪之际,基督教从心理到行动对他们进行了全方位的救助。从3世纪中后期开始,当流行于晚期罗马帝国各地的“西普里安瘟疫”、天花、鼠疫周期性暴发之际,基督教已经在帝国境内逐渐传布并快速流行起来。晚期罗马帝国多次暴发的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与基督教的同步流行在时间上的吻合不能仅仅用巧合来解释。基督教在这一时期的快速发展既与经济、政治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也无法排除多次大规模传染病流行的影响,传染病的暴发造就的民众信仰出现“真空”,为基督教的快速传布创造了契机。米斯卡·梅尔指出:“在古代社会中,灾害的发生被看作是一种预兆或不祥之兆。当时的人们对这些灾害的关注点与现代人不同,他们对灾难所导致的人员伤亡或灾害的破坏程度并不关心,而是着意揣摩神明在灾害发生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抑或上帝通过灾害所要传达给人类的信息。”[18]180
基督教以极快的速度在帝国民众中的流行与其教义密切相关。自诞生之日起,基督教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原罪说①及末世观,从宗教的角度对民众关注但又疑惑不解的问题——如现世中的诸多痛苦及死后生活——进行解释。在传染病大规模暴发所造成的极端危机之下,民众的恐惧及种种无助令基督教的教义变得更加令人信服。基督教会宣称,基督耶稣能够制服恶魔。恶魔虽然被赋予了无穷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恶魔代表着世间所有的邪恶力量;同时,他已被耶稣基督制服。基督徒坚信他们在天国已经打败了恶魔,而在世间所进行的仅是最后的收尾工作[19]54-55。部分民众随之将疫病的发生归为不可抗拒的力量,如恶魔的恶行。正如麦克穆伦所言,恐惧是加深信众虔诚的重要因素之一[20]11。迪奥尼修斯·斯塔萨科普洛斯也指出,对传染病的“超自然力”的解释十分有利于基督教势力的增长[7]75。
① 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触犯了上帝的禁令,被逐出伊甸园,从此,人类世世代代都有罪(《圣经》,创世纪3:1-24.)。“救赎说”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基督教认为,整个人类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原罪”,是无法自救的。人既然犯了罪,就要付出代价以补偿,而人又无力自己补偿,所以上帝就差遣其子耶稣基督为人类流出宝血以赎罪(《圣经》,出埃及记34)。“人只有信耶稣基督,才能免去一切罪。”“天堂地狱说”也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基督教认为,现实物质世界是有罪的,也是有限的,世界末日迟早会到来。人的肉体和人生是短暂的,最终都要死去,而人的灵魂则是永生的。人死后其灵魂将根据生前是否信仰耶稣决定上天堂或下地狱。
基督教对出生、苦难、死亡等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给予令当时人信服的解答,对深受传染病之苦的罗马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基督教的末世观认为,只要民众信任上帝,就可以在死后复活并且获得永生②。当流行性传染病在帝国境内蔓延之时,基督教关于死亡及现世痛苦的解释可以抚慰幸存者,民众一方面会因身边亲朋好友死后进入天堂的期许而深感欣慰,另一方面自己的绝望情绪也因染病而亡即进入天堂的幸福生活而得到些许宽慰。因此,在现世看不到希望的民众极易将希望寄托于来世,希望能够从上帝那里获得庇护和心理安慰的民众逐渐增多。有记载称,在鼠疫大规模蔓延期间,很多居民聚集在教堂之中夜以继日地祈祷[10]465。学者提到,在传染病发生之后,民众的直接反应除了逃走之外,就是变得更为虔诚[7]151-152。
② 基督教的末世观在《圣经》中有较多的体现,如《哥林多前书》15:1-54。
除了教义及理论对因传染病暴发而惶恐不安的罗马民众具有吸引力外,基督教教义中的“爱”要求对穷人及需要帮助的人给予援助,并在疫病流行之时给予众多患者及流亡人士以栖息之所和细致的照料,这成为促成罗马民众日益转变信仰的又一重要动因。在晚期罗马帝国多次传染病暴发之际,均出现了主教、基督徒们帮助病患的记录。3世纪中后期,“西普里安瘟疫”在帝国境内流行之时,有史家对基督徒的积极救助和非基督徒的恐惧与漠视进行了对比,声称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展现出了爱心与忠诚。基督徒们在疫情中帮助和照顾彼此,在照顾病患的时候毫不畏惧,并且一旦不幸染病,基督徒往往会毫无怨言地离开人世。很多基督徒因为照顾病人而失去生命。非基督徒的行为则刚好相反,他们远离染病的患者,甚至将一些垂死之人随意地丢弃在街上。为了远离致命的病症,他们对路上未掩埋的尸体敬而远之。但是,即便他们苦心孤诣地寻求活命,也最终难逃死亡的命运[4]269。
与此相同,312-313年,帝国东部发生疑似天花的传染病时,许多基督徒整日照顾病患,并参加死者的葬礼仪式。基督徒们的行为展现出了同情心和人性,另一些基督徒将面包分发给因饥饿而垂死之人。正因如此,基督徒们的善行大受称赞[4]328-329。不仅如此,经过前期的发展,在6世纪“查士丁尼瘟疫”大暴发之时,教会的神职人员展现出了更有组织性的救助行为。在君士坦丁堡暴发疫情后,长期生活于此的修道士马瑞(Mare)与其他修道士一起协助处理城内的尸体,马瑞最终染病而亡[21]146-147。在“查士丁尼瘟疫”随后的复发过程中,根据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记载,整个奥弗涅地区出现疫情蔓延之势,许多居民为躲避疫病外逃。但是,卡托神父从来不曾离开此地,他埋葬死者、勇敢地做弥撒。卡托神父非常慈爱、一心爱护穷人,他死于这次疫病[22]173-174。基督徒与教会的神职人员忘我投入到灾后救助的行为明显不同于政府相对不足的灾后救助活动,想必会对疫区民众的信仰造成极大的触动。
由此可见,基督教不仅对民众具有精神救助的功能,且从行动上为民众提供了切实的援助和救济。罗德尼·斯塔克认为,在没有基督教神学或基督教社会机构辅助的条件下,民众也忍受了数个世纪的传染病、地震等灾难。但是,一旦基督教出现,它解决这些痼疾的非同一般的能力很快便锋芒毕露了[23]194。在传染病大规模暴发所酿成的巨大危机之下,当晚期罗马帝国政府无力实施有效救助之时,教会神职人员和普通基督徒们承担了相当多的救灾工作,甚至部分替代了原本应属帝国政府的社会职责。丹尼尔·T.瑞夫指出,在传统医疗体系和信念难以为病患提供有效治疗之时,基督教在这一真空状态之中确定了地位,为病患提供一种新的有关疾病的理解和选择,并帮助民众恢复信心[8]67。在此基础上,普通民众极大增强了对于具有强大心理治愈能力的基督教的虔诚信仰,基督教成为越来越多罗马民众的精神寄托。
面对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希望将基督教会收为己用的晚期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一改帝国过去的政策。从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Ⅰ,307—337年在位)开始,皇帝与帝国政府对待基督徒的态度从无视或迫害转变为支持和保护。不仅如此,君士坦丁一世及之后的绝大多数晚期罗马皇帝均希望通过控制基督教会,借此加强对民众的精神统治。因此,从君士坦丁时代开始,晚期罗马帝国的皇帝逐渐被塑造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西里尔·曼戈指出,“一个上帝、一个帝国、一个宗教”是晚期罗马帝国政治思想理论的核心内容[24]88。
在皇帝集大权于一身的晚期罗马帝国,当权者通常通过捐赠地产、捐建教堂等方式支持教会的发展。在帝国多次暴发流行性传染病之时,即便直接针对疫情的物质救助几乎从未见诸史料,但是帝国官方支持的教堂建设活动却未曾停止。即便在财政紧缺之际,在皇帝的主导下,为了在精神上抚慰灾民并巩固统治,以教堂为中心的教会建筑的修建工作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J.A.S.伊文思认为,灾害的发生改变了民众的观念。教会与修道院逐步将富裕者曾经用于修建城市公共建筑的钱财收入囊中[25]230。教会建筑受到优先重视的情况在教会发展相对成熟的晚期罗马帝国的后期阶段尤为突出。根据普罗科比的记载,从6世纪开始,帝国境内教堂的数量明显增多,成为这一时期帝国主要的建筑形式。单从帝国政治中心来看,查士丁尼一世于6世纪在君士坦丁堡建设了多座教堂,包括圣索菲亚教堂、大天使迈克尔教堂、十二门徒教堂和圣巴克斯教堂等[26]9-30,43-45。除普罗科比外,同时代的史家尼基乌主教约翰也提到这一时期教会建筑的建设活动[27]139。史家埃瓦格里乌斯同样对皇帝极其关注帝国内部教会建设的情况进行了记载[9]233。在皇帝的主导下,支持教会发展的系列活动令晚期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程度大幅提升。戴维德·凯斯指出,从长远影响来看,传染病本身以及受其影响的教堂建设促使民众的基督教化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28]128。
综上所述,有鉴于数次传染病的大规模暴发及其破坏性影响,晚期罗马帝国的民众普遍产生了恐慌、害怕和绝望情绪,这是他们所以求助于宗教的关键。与长期流行于地中海世界的年代久远的多神教相比,作为一种“新型”的宗教,基督教组织的严密性、教义的普世性以及教徒实践的活跃性更易引起民众的普遍认同。一方面,面对民众在大规模疫情发生后千疮百孔的心理,基督教教义及理论不仅能够为处于疑惑之中的民众提供更加令其信服的解答,而且也能缓解惶惶不可终日的民众的紧张情绪。另一方面,大难当前之际,与政府不作为的灾后救助形成鲜明对比,教会神职人员与基督徒的积极救助行为赢得了大量罗马民众的感激与信赖,由此进一步推动了民众的信仰向基督教转变的进程。
民众信仰的转变引起了以皇帝为中心的帝国政府的关注。为了巩固统治,同时对受到疫情打击而伤痕累累的民众进行慰藉,帝国政府对教会的资金投入推动了民众虔诚信仰之寄托——教会建筑及教会活动的发展。因此,在大规模传染病、基督教会、帝国政府的多方推动下,晚期罗马帝国的民众信仰不可逆转地迈进向基督教转变的大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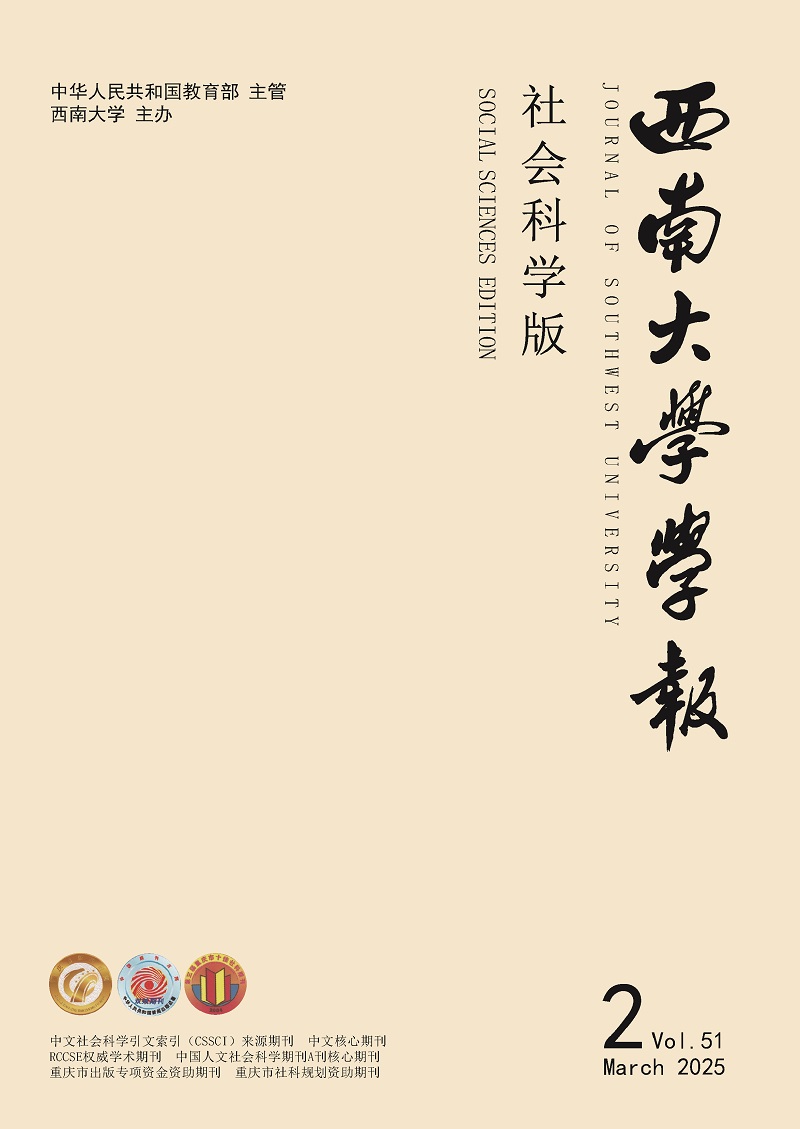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