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攘夺就是掠夺、夺取、强占的意思。顾名思义,“攘夺财物”,即是抢夺他人财物据为己有。宗室是明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血统高贵”,地位尊崇,经济待遇优渥。然而他们中的不少人却常常攘夺他人财物,且理直气壮,毫无羞耻之心。这一现象颇引人注意,在关于明代宗室犯罪的论著中多有涉及[1-8],但尚无专门研究,仍有一定的言说空间。本文拟借鉴犯罪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HTML
-
关于明代宗室攘夺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见诸多种史籍,但记载最为集中和详实的当属明代《实录》。兹仅据《明实录》做一粗略统计,制成附表《明代宗室攘夺财物案件统计表》。
附表显示,明代宗室攘夺财物的犯罪案件共41起。这些犯罪案件的时间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年份特征。明代绵延276年,“治隆唐宋”,共历16帝。宗室攘夺财物犯罪案件始发于弘治(1491),终于天启(1622),主要发生在明中后期的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6朝。各朝宗室攘夺财物犯罪案件的数量为:弘治朝5起,正德朝9起,嘉靖朝9起,隆庆朝5起,万历朝11起,泰昌朝1起,天启朝1起。绝对数量以万历朝为最多。但若计算年发案率,除泰昌帝在位仅一月不计外,弘治朝约0.28,正德朝约0.56,嘉靖朝0.2,隆庆朝约0.83,万历朝约0.23,天启朝约0.14,以隆庆朝为最高。(2)月份特征。在一年的十二个月中,明代宗室攘夺财物犯罪案件发生的月份分布为:一月0起,二月4起,三月6起,四月2起,五月4起,六月3起,七月3起,八月4起,九月3起,十月3起,十一月4起,十二月5起。阴历三月案件6起,数量最多;十二月次之,5起;二月、八月、十一月再次之,皆是4起;六、七、九、十月,皆是3起;四月、一月分别是2起、0起。如果按季节计算,春季(一、二、三月)10起,夏季(四、五、六月)9起,秋季(七、八、九月)10起,冬季(十、十一、十二月)12起,冬季案发最高。但总体呈均衡分布,各季节间的差距不是特别大。(3)钟点特征。关于案发的具体钟点,史料中很少记载。只有5起案件记载了案发的大致时间,3起发生在白天。如,正德十年(1515)五月,代藩潞城王府镇国将军聪泏、辅国将军聪涀“率群下白昼夺人财物”[9]卷125,正德十年五月丙申;嘉靖十三年(1534)十一月,晋藩庆成王府表栾遣人支禄,镇国将军表杜“白昼攫之于市”[10]卷169,嘉靖十三年十一月甲戌;天启二年(1622)七月,宁藩石城王府奉国中尉统锸“白昼强劫”财物[11]卷24,天启二年七月壬戌。发生在夜间的有2起。嘉靖三十一年八月,荆府辅国将军厚



明代宗室攘夺财物犯罪的空间特征也可从3个层面展开分析。(1)藩府分布特征。明代实封亲王65位,其中,因事被废,或因绝嗣除封31位,至明亡时尚存34位。据附表,发生宗室攘夺财物案件的藩府共13个。其中,晋藩最多,13起;代藩次之,7起;周藩6起;秦藩3起,韩、宁、靖江各2起,辽、荆、鲁、楚、赵、徽各1起。晋、代、周、秦4亲王府发生的宗室攘夺财物案件约占案件总数的71%。其他9个藩府发生的攘夺财物案件仅占总数的29%。(2)布政使司分布特征。明代的省级行政区划分为南北两直隶、十三布政使司,分封有藩王的布政使司有8个(迁徙者除外),即: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四川、湖广、江西、广西。在这8个布政使司中,除四川外,皆有宗室攘夺财物犯罪案件发生:山西20起,河南8起,陕西5起,湖广3起,山东1起,江西2起,广西2起。山西“独占鳌头”,所发生的宗室攘夺财物案约占案件总数的49%。(3)南北分布特征。中国以秦岭-淮河为地理分界线,分为南方和北方。南、北方在气候、物产、习俗以及人的性格等方面皆有很大的不同。明代发生的宗室攘夺财物的犯罪案件,北方4布政使司共34起,约占案件总数的83%,而又以山西、河南、陕西3布政使司为多。南方仅有7起,只约占案件总数的17%。明显是北方占据绝大多数。
-
明代宗室攘夺财物犯罪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根据每一案件犯罪行为主体的数量多少,可划分为个体犯罪和群体犯罪两大类。个体犯罪即是由单个人实施的犯罪,犯罪行为主体为个体。在明代宗室攘夺财物犯罪的41起案件中,个体犯罪的案例只有10起:弘治九年(1496)十二月,周王同镳世子安潢夺人宅第开张酒肆[12]卷120,弘治九年十二月丁丑;弘治十八年八月,周府胙城王府辅国将军同铋听从奸民拨置,“强以银物贷人,未及偿期,辄倍取其息”[9]卷4,弘治十八年八月戊寅;正德四年十二月,周府汝阳王府辅国将军同镯“强取人财”[9]卷58,正德四年十二月甲辰;正德十年五月,代府潞城王府辅国将军成环为群下拨置,“出市夺人财物”[9]卷125,正德十年五月戊申;嘉靖十九年十一月,晋府庶人知

群体犯罪即是由多个个体组成的群体实施的犯罪,犯罪行为主体为多人。这些犯罪群体的构成复杂。有的全是宗室成员;有的则是由宗室主导,并召集家人、校尉、无赖、盗贼,甚至亡命之徒组成的。总的来看,这些群体大多具有临时性,作案时结为一伙,作案后即作鸟兽散。但也有一些群体具有共同的犯罪意识,他们视攘夺为合理合法的事情,并在攘夺过程中,分工明确,有的负责谋划,有的负责实施。事发后,则有的知情不报,有的包庇主犯,甚至帮助罪犯逃脱监管、惩罚,毫无愧疚之心和羞恶之感,形成了鲜明的犯罪亚文化。这从下面列举的案件中可以明了。
在明代宗室攘夺财物的案件中,群体犯罪有31起,约占宗室攘夺财物案件总数的76%。其中,弘治朝发生3起:弘治四年十月,辽府镇国将军恩鑡、恩鏎、恩


正德朝7起。正德二年五月,晋府庆成王府辅国将军表





嘉靖朝7起。嘉靖十三年十一月,晋府庆成王府镇国将军表杜“嫡兄丧,表栾遣人支禄,白昼攫之于市。又率庶兄弟表枫、表樤、表榽出郭而夺其屯粮”[10]卷169,嘉靖十三年十一月甲戌。嘉靖二十四年三月,代府和川王府奉国将军充灼、潞城王府镇国中尉俊桭、昌化王府奉国将军俊桐、俊












万历朝11起。万历二年(1574)八月,楚府岳阳王府辅国中尉英琰、永安王府辅国中尉英爌“聚众抢夺伤人”[14]卷28,万历二年八月丁卯。万历四年八月,晋府阳曲王府辅国中尉新块,未请名封朱刘孙、朱赛儿、朱禄儿“纠众行劫,至于伤人”;中尉新壁“谋而未行,分赃有据”,参与谋划,未有行动,然分得赃物;中尉知






隆庆朝2起。隆庆元年七月,代府襄垣王府宗室俊言堂“私出禁城,聚众剽劫”[13]卷10,隆庆元年七月庚午;隆庆二年十月,晋府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新垣“与群盗通,劫掠商货”[13]卷23,隆庆二年十月庚辰。
泰昌朝1起。泰昌元年十一月,韩府褒城王府镇国中尉谟

从犯罪动因的角度分类,则可分为恶癖性犯罪、贫困性犯罪和精神异常性犯罪。恶癖性犯罪,即是指攘夺他人财物已成为癖好,乐此不疲,以此取乐,从中得到心理满足。如亲王世子、郡王,他们身居宗室上层,经济上无后顾之忧,他们攘夺他人财物不是为了生存的需要。但这种类型相对罕见,附表统计共有3起。贫困性犯罪即指因贫困而实施的犯罪。这部分宗室较多,且皆为将军、中尉及无名封宗室。精神异常性犯罪是指犯罪人因精神不正常而实施的犯罪。这在宗室中也有不小的一部分,他们动辄“行劫杀人”“杀人劫财”,甚至有的“纵子劫杀”,视鲜活的生命于无物,缺乏对生命的敬畏。这应与长期幽居封城而导致的心理变态有关。
在明代宗室攘夺财物犯罪的案件中,实施犯罪的主体无疑是宗室,个体犯罪自不必言。就是群体犯罪,家人、校尉、群小、凶徒乃至盗贼,也只是为虎作伥的参与者、跟随者。这也正是我们将这些攘夺财物的案件称为宗室攘夺财物案件的原因。也就是说,虽然犯罪人的阶层来源多样,但起主导作用的是宗室。而在宗室中,尤以中下层宗室为多。据附表统计,涉案宗室至少97人。其中,亲王世子1人,郡王2人,将军34人,中尉30人,庶宗8人,无名封宗室22人。参与宗室攘夺财物案的家人、校尉,特别是群小、凶徒、盗贼等的数量未有记载确数,难以统计。那么,这些犯罪人具有什么样的人格特征呢?史料中仅有对涉案宗室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简略记载,而对数量庞大的参与者则记载阙失。因此,这里仅对宗室犯罪人的人格特征稍加分析。宗室犯罪人的人格特征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凶狠残暴,伤风败伦。代藩怀仁王府辅国将军成鈚,父死尸骨未寒,即与嫡子成鈚争夺财产,并对嫡母无礼,率母叔、校尉多人闯入嫡母靳氏府中,抢夺金银器皿和田契,靳氏执杖驱除,成鈚无所畏惧,反将嫡母靳氏赶走[12]卷60,弘治五年二月丙寅。无法无天,财迷心窍。晋府庆成王府奇







二是迷财恋色,不顾伦常。周府汝阳王府辅国将军同镯“强取人财,狎近乐妇”[9]卷58,正德四年十二月甲辰。徽府景宁王载墋“烝父婢及强夺民产”[13]卷30,隆庆三年三月辛未。晋府永和王府辅国将军新壛,不仅“搜夺人财”,而且强占人女为妾[13]卷42,隆庆四年二月壬戌。不仅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而且疯狂逐色。高贵血统荡然无存,已没有了贵族的矜持和涵养,低级趣味充斥内心,行为十分龌龊。
三是混迹于亡命徒中,与盗贼、无赖为伍,沆瀣一气,完全站到明朝的对立面,异化成为明朝的异己力量,毁坏着明朝的根基。这方面的例子就更多了。如“招集恶少”“蓄养无赖”“与群盗通”“招纳亡命,同为劫盗”等。
-
在明代宗室攘夺财物的案件中,受侵害的对象,即被害人,从性别角度看,基本为男性。明确记载受害人为女性的只有两人。如弘治二年五月,代府发生的怀仁王府辅国将军成鈚抢夺嫡母靳氏金银器及田契案中的靳氏;另如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代府发生的昌化王府庶人俊






史料中对被害人在遭到侵害时的心理、性格有明确记述的并不多,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没有记载。难道他们在遭到无端侵害时,就没有任何心理和行为的激烈反应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但无论是宗室个人,还是宗室攘夺集团,他们都处于优越和强势的地位,“官私不能禁”,地方官府都拿他们没有办法,受侵害的个人还有什么法子呢?反抗只能是受到更深的伤害。代府怀仁王府辅国将军成鈚,其父去世,尸骨未寒,即伙同校尉等抢夺嫡母靳氏的金银器物和田契,靳氏愤而执杖反抗,最终还是被成鈚赶走,已经嚣张到何等程度!荆府辅国将军厚

-
明代朝廷非常重视亲亲之谊,对宗室的待遇优厚,亲王禄米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驸马与郡王同,郡主、郡君、县主、县君、乡君、仪宾与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同[15]。如按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的观点,明代一石约为今153.5市斤计算,亲王每年禄米为1 535 000斤,奉国中尉每年也有禄米30 700斤。除此,还有不定期的各种赏赐。赏赐物品范围甚广,从黄金、白银到绸缎、布匹、纸钞、鞍马、羊、酒,乃至商税,应有尽有,且每次赏赐的数额也不小。如在永乐朝,赐钞动辄数万贯,甚至个别时候达10万贯;赐绸缎、布匹也常至10匹,多者达40匹。这虽只是永乐初年的情况,但绝不仅限于永乐初年,其他时期也大致相仿,乃至有过之者。那么,宗室为什么还会攘夺他人财物呢?
我们认为,明代宗室这些行为的产生,首先应是“藩禁”政策导致的结果。何谓“藩禁”?“藩禁”即是对宗室的限制和禁锢,其由来已久。洪武时期,对宗室藩王甚为倚重,经济待遇优厚,政治地位崇高,即使是公侯、大臣也不能与之分庭抗礼,且予以统兵治政大权。永乐以后,“藩禁”渐兴,经宣德至弘治,禁网愈织愈密,“王亲不得任京职”,甚至二王不得相见,出城祭扫须请而后行,防闲过峻。宗室不官、不士、不商、不农,成为一群空享厚禄、无所事事的靠朝廷供养的“寄生虫”。那么,它和明代宗室的攘夺财物行为的产生有什么关系呢?一方面,明初,宗室人数少,国家财政也称丰裕,供给尚不成问题。但到明中叶后,情况发生变化,宗室人数剧增,国家财政紧张,宗室给养供给出现问题,至嘉、万年间,已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多位大臣振臂而呼,欲引起朝廷的重视,进而寻求破解之道。御史林润言:“今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国初,支庶不繁,……今……视昔时数百倍矣。”“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不啻倍之。即如山西,存留米一百五十二万石,而禄米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存留米八十四万三千石,而禄米一百九十二万石。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至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而诟有司。”[10]卷514,嘉靖四十一年十月乙亥河南抚按栗永禄、杨家相等言:“国初,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今则玉牒内见存者共二万八千九百二十四位,岁支禄米八百七十万石有奇,郡县主、君及仪宾不与焉,是较之国初殆数百倍矣。天下岁供京师者止四百万石,而宗室禄粮则不啻倍之,是每年竭国课之数不足以供宗室之半也。”[13]卷58,隆庆五年六月丁未礼科给事中石应岳言:“迩年以来,麟趾繁衍,载玉牒者四万,而存者可三万有奇,岁该禄米可九百万石,计各省存留之赋曾不足以供禄米之半。”[14]卷25,万历二年五月乙未宗室禄米不能按时发放,亲王、郡王“犹得厚享”,日子还过得不错,惨的是将军以下的宗室中下层。明中叶后宗室俸禄不能按时发放,中下层宗室陷于贫困化境地,生活来源断绝,不能自存,嗷嗷待哺,欲为普通百姓以求一饱而不能。他们不得不放下可贵的尊严,去为生命的存续而“战斗”——攘夺他人财物。事实上,涉案宗室也是以宗室中下层为主体。对满足最低限度物质需要的追求,是导致“罪恶”行为产生的内驱动力,是明代宗室攘夺财物行为发生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宗室身居封城,行动极不自由,形同幽禁,这不能不对其心理产生影响:一是生活空间狭窄,心理发生畸变,极度自私、偏狭、狠毒,产生了不少为常人难以理解的怪异行为,常常为了财物而伤及无辜人命;二是由于政府对其行为多有限制,剥夺了他们的统兵治政权、自由行动权,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日常生活中,都有一种严重的挫折感,郁结于胸,不得不发,但国家体制的力量太强大了,遂转而把对国家体制的愤恨向社会发泄,损害他人财物,与盗贼勾结,沆瀣一气。“挫折-侵犯”心理也是这些行为产生的一大因素,不全然是经济原因所致。
明代宗室群体攘夺财物行为的多发频发,与明朝政府对案件的处置态度和对宗室的处罚方式亦有密切的关系。宗室系天潢贵胄,宗室犯罪官员无权直接审判定罪,要奏闻皇帝,“取自上裁”。而皇帝为体亲亲之谊,处置无有章法,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处罚行为偏于宽软。明代对宗室攘夺财物行为的处罚大致有如下6种:降旨切责;革禄、停禄、夺禄;着本府严加管束;降为庶人,禁锢高墙或闲宅禁住;勒令自尽;秋后处决。前面4种较为常见。但后两种很少使用,我们在史料中仅见到二三例。前面4种较为常见。很明显,这些处罚措施对宗室缺乏足够的威慑力。另外,有的惩罚措施,如革禄、停禄、夺禄,根本就没有对症下药。不少宗室攘夺财物案的发生,导因于明中叶宗室中下层的绝对贫困,缘起于对物质财富的饥渴,而在其犯罪后,予以革禄、停禄、夺禄的处罚,无异于是令其雪上加霜,更加贫困。这就促使其为了自身及家庭成员的生存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的铤而走险。宗室群体对财物的攘夺,在当时的制度体系下,不但不会根除,而且从理论上讲,一定会愈演愈烈。
明代宗室攘夺财物已非完全是宗室的个人行为,从上引资料看,在某种程度上,已呈现出某些团伙化或集团化的特征——结党抢掠。其主要表现为:一是邀约同一王府的宗室集体谋划,共同作案;二是召集恶少、蓄养无赖、串通盗贼,以为其打手帮凶。通过这些特征,也让我们看到了,在明中叶,宗室群体中下层成员的流氓化、无赖化的过程。当然,明代宗室这些行为的产生是由明代宗室管理体制的不合理性因素所导致的,但其产生的影响具有极大的消极性和负面性。首先,给明代宗室群体的整体形象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为当时和后世的否定性评价提供了实证性的依据。至少从明末始,就对明代宗室的社会作用评价极差,称之为“名为天枝,实为弃物”。这一观点影响至深至远,以致当代学者中仍有持“弃物论者”,以废物视之。其次,明代宗室的攘夺财物行为给明朝的历史命运也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明代宗室攘夺,手段残忍,伤害人命,祸及民众,给百姓带来了财产,乃至生命的损失,激化了社会矛盾,并积累着民众对明朝国家的仇恨,把相当数量的民众推到了明朝国家的对立面,他们的行为起到了制造明朝掘墓人的作用。最终,明朝国家与宗室罪恶一起被农民起义的风暴无情埋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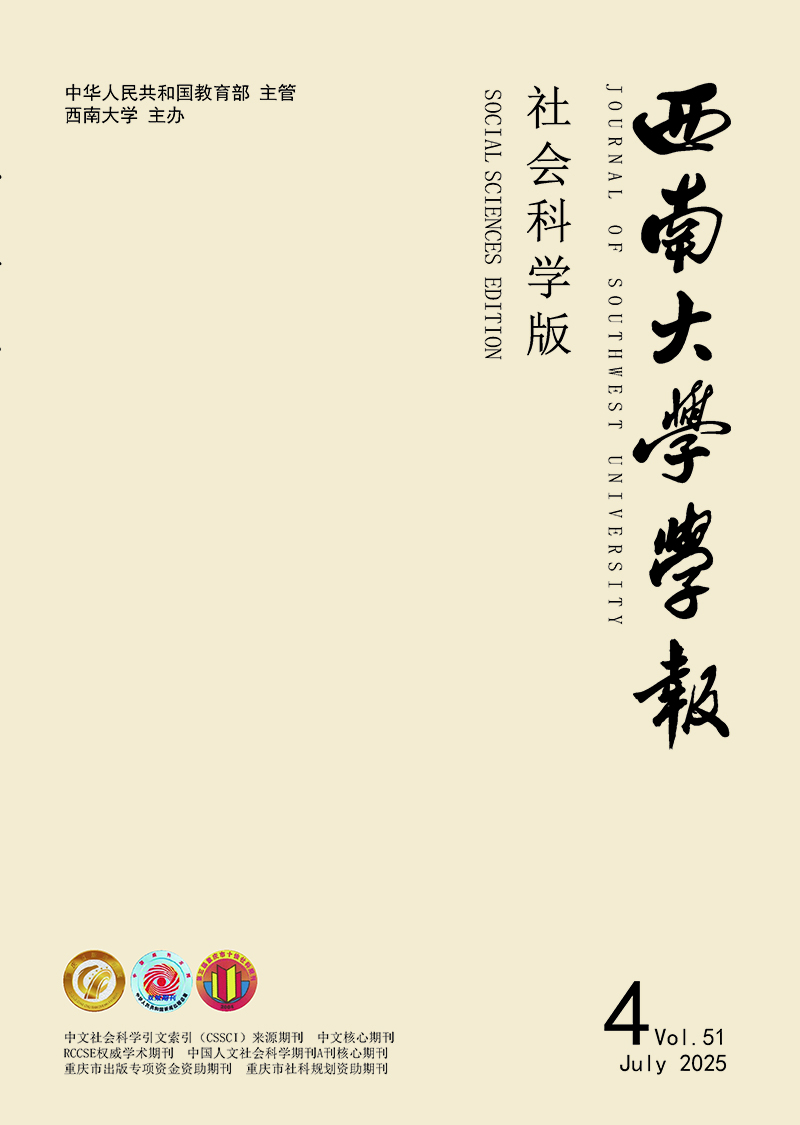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