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是一个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对语言问题的思考贯穿于哲学史的始终。分析哲学为我们探究语言问题(比如语言的本质、语言与意义、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等)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实用的方法。但语言哲学并非只有分析哲学一途,现象学也蕴含了丰富的语言哲学思想。
现象学是一种方法,也是一场运动,但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现象学家们对于语言的看法各不相同。例如,海德格尔从存在论角度提出“语言是存在的家”,列维纳斯从伦理学角度提出语言的本质是一种对于他者的呼唤。本文对现象学语言问题的讨论只限于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的语言分析思想。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内哲学界就已经开始关注胡塞尔的语言哲学,并注意到胡塞尔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有相通之处①。最近十几年来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图根特哈特(Ernst Tugendhat)的观点展开的。图根特哈特认为,现象学与语言分析的关系不是相互补充的,而是相互排斥的。例如,“意义”(Sinn)与“意指”(Meinen)是语言哲学的核心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分析中,“意指”对象的行为是意识的组成部分,“意义”处于意向性关系中;在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中,“意指”则是理解句子意义的一个因素,意识的组成部分就是对于句子意义的理解[1]。国内学者对此已有回应。例如,倪梁康先生基于意识哲学立场,指出图根特哈特对意识哲学的批判,无非是用“听的模式”取代了“看的模式”,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对意识进行内直观[2]684。郑辟瑞先生则回顾了图根特哈特对胡塞尔的批判,重新审视了意识哲学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指出语言分析并非通达自身意识的唯一途径[3]。笔者认为,图根特哈特对现象学的批判以及国内学者的回应最终指向的问题就是:一门作为意识哲学的语言哲学如何可能?具体到胡塞尔的现象学来说,笔者认为,应该从胡塞尔的文本出发,在胡塞尔现象学(主要是意识哲学)与语言哲学的共同问题域中阐明这一问题。首先,要阐明语言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的位置,这是语言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其次,要阐明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符号、含义和对象之间的意向性关联,这是意向分析与语言分析的关系问题;再次,要阐明如何通过判断的明见性之回溯,通达生活世界,这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进而,我们可以将分析哲学与胡塞尔现象学进行比较,思考胡塞尔现象学语言分析的特征,以及它对当代意识哲学与语言哲学之会通的启示。
① 关注这一问题的早期代表性论文有靳希平:《胡塞尔语言哲学简述》,《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63-66页;周国平:《胡塞尔与弗莱格的语言哲学思想比较》,《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第43-49页。
HTML
-
胡塞尔认为,现象学的研究对象是纯粹意识的本质结构及其意义构成[4]327。纯粹意识的本质结构需要用语言来描述,纯粹意识的意义构成需要用语言来表达。语言不同于言语,语言是一个共时性的“系统”,语言系统是符号系统的一个子集;而言语是一种历时性的“行为”,言语行为是符号行为的构成要素之一,符号行为是意识行为的构成要素之一。语言凭借言语表现自身,而言语的表现要遵循语言的规则。
胡塞尔将意识行为分为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两大类型,“客体化行为”指逻辑与认知行为,包括表象和判断,这些行为可以构造出客体;“非客体化行为”指价值与实践行为,包括情感、评价、意愿等,它们自身不能构造客体,只能以客体化行为构造出的客体为客体,故非客体化行为奠基于客体化行为之上。言语行为作为一种符号行为,首先属于客体化行为中的非直观行为,它奠基于直观行为(感知和想象)之上,并与图像行为和直观行为共同构成了表象行为;其次,由于每个判断行为都要以表象行为为基础,所以,语言也存在于判断行为之中。
现实生活中,语言不仅被用来表达判断(谓词判断:S是P),而且也被用来表达感知、想象、情感和意愿,故语言通过表达而贯穿于一切意识行为,或者说一切意识行为原则上都可以被语言表达出来。对于科学理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精神科学,判断(陈述)无疑是最基本的语言表达形式,判断是联结意识与语言、理论与世界的纽带。
总之,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言语行为以判断为主要形式,判断与其他意识行为共同构造对象和事态的意义。从结构上看,言语行为是意识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从属于意识系统;从发生学角度看,意识比语言更为本源,意向内容的存在先于意向内容的表达;从奠基关系上看,意识是语言之“体”,语言是意识之“用”①,即意识为语言奠基,这也是胡塞尔现象学的语言哲学不同于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的主要特征。
① 这里的“体”“用”只是一个权变的说法,从现象学观点看,对意识本身也不可作实体化理解。意识和语言都是行为,但各种行为是有层级差序的,意识行为,特别是直观行为与语言行为相比,处于奠基性层级中。
-
如上所述,从胡塞尔现象学角度探究语言问题,首先要注意语言问题是从属于意识问题的子问题,语言学根植于纯粹现象学。其次,我们要注意胡塞尔主张现象学是研究纯粹现象和纯粹意识体验的“本质”之学,因而现象学视域中的语言是普遍的,作为“种类”的语言,现象学对语言的阐释是本质性的阐释。
胡塞尔将语言看作意指对象或表达体验的符号系统。符号可以却不必然拥有含义或意义:“每个符号都是某种东西的符号,然而并非每个符号都具有一个‘含义’(Bedeutung)、一个借助于符号而‘表达’出来的‘意义’(Sinn)。”[4]331拥有含义或意义的符号与表达同义,或者说它可以把意义表达出来,进而意指对象或事态,即:
无含义的符号则只不过是“指号”而已。胡塞尔认为,指号就是有且仅有指示功能的符号:“在本真的意义上,一个东西只有当它确实作为对某物的指示而服务于一个思维着的生物时,它才能被称作指号。”[4]333 但是,“指号(Anzeichen)[或记号(Kennzeichen)、标号(Merkzeichen)等等]意义上的符号不表达任何东西;除非它在完成指示(Anzeigen)作用的同时还完成了一个意指(Bedeuten)作用”[4]331。即:
总之,有含义的符号就是表达,无含义的符号就是指号,前者具有意指功能,后者只有指示功能。一物总是以某种方式指示着另一物,那么,没有意义的“指号”是如何发挥“指示”功能的呢?胡塞尔认为指号的指示作用起源于联想,联想创造出现象学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意向的统一,它的根据不在被体验的内容中,也不在基于这些内容的抽象种属中,而在所显现对象,即现象的种属关系中。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
其一,之所以把指号和被指示物(对象或事态)都看作现象,是因为它们既可以是实存之物,也可以不是实存之物,正如胡塞尔所说:“指号的本质在于指出一个事实、一个此在,而被指称的对象根本不需要被看作是实存着的对象”[4]367。
其二,虽然指号的本质就在于指示某物,但一个指号和一个被指示物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指号必有所指,但又不定其指,因为让指号的指示功能得以可能的“联想”是“动机”的规律,而不是“逻辑”的规律,“逻辑”的规律具有必然性,而“动机”的规律只有或然性。
胡塞尔对符号与指号的区分是描述性的,一个符号是否具有含义不能一概而论,必须结合具体的语境和视域来讨论。意义的同一性是在诸符号、诸行为、诸对象或事态间的交织运作之中呈现的。如果认为对象或事态只能被“意指”,不能被“指示”,那就有可能把复杂的问题给简单化了。
-
表达、含义与对象三者之间的关系既是《逻辑研究》中“第一研究”的主题,也是贯穿于全部六个研究的线索,“唯有彻底地澄清表达、含义、含义意向和含义充实之间的现象学的本质关系,我们才能获得一个可靠的中间位置,语法分析和含义分析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必要的澄清”[4]319。
胡塞尔将表达分为两个方面:“表达”(即“表达式”,简称“表达”)和“表达行为”。“表达”根据其物理方面构造起自身,比如我们说出或写出“苹果”这个语词,它就以语音或文字的形式成为物理性的能指。“表达行为”给予表达以含义,构造起表达与被表达之物的对象性关联。例如,我们面对某人,指着一个苹果说:“这是一个苹果”,我们就以言说行为赋予了那个所指对象以确定的含义,并建构了表达与被表达对象的联系。正是凭借表达行为,表达与对象或事态之间拥有了可能的意指关系,表达获得了比语音或文字更多的东西。
表达之所以能够“意指”对象,是因为表达本身先天地具有含义,含义“作为意向的同一之物对表达本身来说是本质性的”[4]360。即使在日常表达中,语句中的含义难免有偏差(与直观不符),但含义本身始终是同一的,不因判断行为的不同而有差异。而含义之所以能保持自身同一性,其根据在于“所有认识问题中最后的权威” [4]409——明见性(Evidenz)。也就是说,含义能被“明见到”,并在诸对象、诸事态、诸行为、诸体验、诸命题中保持自身同一性,因为含义本质上不属于个体观念,而是属于种类观念,即“含义的观念性(Idealität)是种类一般观念性的一个特殊情况” [4]411,而且真正的同一性就是种类、观念的同一性,诸杂多的个别性被统摄于其中。
要理解表达、含义和对象三者间的关系不能离开“体验”(Erlibnis)。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体验是比表达和含义更高的属。从体验的本质性层面看,现象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合乎本质地描述意识的意向体验,即在相应的直观中描述表象行为和判断行为的特征,澄清表象和判断的概念,建立表象和判断的理论。从体验的描述性层面看,“表达的存在是一个在符号和符号所标志之物间的体验统一中的描述性因素”[4]348。含义和对象的意向统一构成了体验的意向内涵。如图所示:
综上所述,表达、含义与对象的关联是:
(1) 表达意指对象;
(2) 含义在诸对象中保持自身同一;
(3) 表达、含义与对象在体验中意向地统一。
当然,三者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简言之,即表达是主观体验的统一,含义是客观观念的统一;含义内在于表达之中,对象则是外在于表达的东西。
-
与符号和表达相似而又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指称问题。“指称”(reference)就是某种指代性的标志(如名称、心理状态和图像)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其中,对名称(name)和其他指称词项(referential terms)性质的探究,长期以来,一直是占据语言哲学中心的问题①。胡塞尔现象学也关注指称问题,因为指称指向语言之外的基本个体,比如物和人,“超出语言而通向语言的非语言性条件性的运动,也同样是现象学包含的运动”[5]398。
① 参见“斯坦福哲学百科”(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的“reference”条目,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reference/.
胡塞尔指出:“名称在任何情况下都指称着它的对象,也就是说,只要它意指着这个对象,它也就在指称这个对象。”[4]346具体说来,他把指称的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名称所传诉之物,即心理体验,另一类是名称所意指之物,包括所意指的意义、内容和所指对象。如图所示:
可见,对名称和指称问题的讨论是对符号以及表达、含义和对象问题之探究的延伸,“表达借助于它的含义来标示(指称)它的对象”[4]357。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含义和对象进行了区分,列举了名称与意义、对象的四种关联类型[4]355-356:
(1) 不同的名称具有相同的含义,指称同一对象,比如“伦敦” “Londres” “London”,以及“二”“2”“Zwei”“two”,具有同样的含义,指称相同的对象。胡塞尔将这种情况称为“同义词重复”。
(2) 不同的名称具有不同的含义,指称同一个对象,比如“耶拿的胜利者”和“滑铁卢的失败者”具有不同的含义,却都指称“拿破仑”这同一个对象;又如“等边三角形”和“等角三角形”含义(内涵)不同,但外延相同。
(3) 相同的名称具有相同的含义,指称不同的对象,比如“一匹马”无论在何种语境中出现都具有同一含义。但是,如果我某一次说“布塞法鲁斯是一匹马”,而另一次说“这匹拉车的马是一匹马”,则“一匹马”的含义未变,而其指称对象却不是同一匹马。
(4) 相同的名称可以具有不同的含义,指称不同对象,如“苏格拉底”是一个多义词,它可以指称古希腊那位著名哲学家,也可以指称葡萄牙前总理(Jose Socrates);又如“这个二”“这个红”,其含义和所指称的对象也要视语境而定。
上述四种情形涵盖了一般讨论指称问题所关涉的语言现象:通名、摹状词、专名和索引词[6]52。就胡塞尔上文所举例子(除了葡萄牙前总理的例子为笔者所加)而言,“一匹马”中的“一”和“马”即通名,“耶拿的胜利者”和“滑铁卢的失败者”即摹状词,“苏格拉底”即专名,“这个二”和“这个红”中的“这个”即索引词。
-
名称所指称的是对象,判断或命题所断定的是事态。对象是一个命题中主词的对应物,事态是真值形成者,命题是真值载体,事态的存立使得(被判断的)命题为真[7]134。从现象学观点看,对象和事态都是意向相关项,它们从属于一个更高的属——存在(Sein)。由于名称是判断的组成部分,对象是事态的组成部分,所以归根到底,“
一个存在只能在判断中被把握”[4]1021。 胡塞尔现象学的判断理论兼及判断所断定的事态的有效性,以及构成判断的语词含义的充实性。一方面,一个判断以陈述句(直言命题)的形式将一个事态的客观有效性表达出来,但事态的有效性并不依赖于我们的判断行为,事态本身是其所是。另一方面,一个判断就是对一个感知或想象的表达,表达就是“充实的行为显现为一种通过完整的表达而得到的表达行为”[4]347,充实就是表达中的含义意向与直观相合。因此,使一个判断“为真”的过程就是语词的概念本质,即含义被充实、被认识的过程,“判断活动(所有在确切意义上的现时认识活动)的所有明见性都以在直观上充实了的含义为前提”[4]380。
在《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重点探讨了两类判断:“最狭义的判断”和“最广义的判断”。“最狭义的判断”即传统的谓词判断,“即那些在陈述(Apophansis)中、在陈述句中获得自己语言积淀物的判断”;“最广义的判断”则把一切谓词和前谓词的模态都包含在了自身之中,“于是这种意义上的判断就成了
客观化的(对象化的) 自我行为的总体性的名称”[8]79。谓词判断是基于前谓词作用(比如知觉、联想等)建构出来的,即基于自我主动性的一个低级阶段建构出来的,谓词判断是一种已经实现出意义的作用。“最广义的判断”中的前谓词判断相当于自我主动性的接受性阶段,而作为“最狭义的判断”的谓词判断则相对于自我主动性的自发性阶段。与判断的结构、运作这些纯粹形式逻辑问题相比,胡塞尔更关心的是判断的现象学构造问题。 胡塞尔认为谓词判断的本质解释只能是现象学的解释,即对于谓词判断的起源从现象学上进行澄清。每个判断在形成之前,必须先有一个对象——与陈述相关的东西——预先被给予我们,而当这类对象“它们自身被给出之际,它们自身必须是明证的” [8]34。因此,判断的明见性(Evidenz,又译“明证性”)必须回溯到对象的明见性,即对象自身的原初被给予性。
因此,对象的明见性是谓词判断的明见性的前提,“一个对象作为可能判断的基底可以明见地被给予,而不必在一个谓词判断中加以判定。但是,如果它自己不是明见地被给予的话,那么对它作一个明见的谓词判断是不可能的”[8]35。例如,我们必须首先明见地看到一棵树,然后才能明见地判断这棵树是什么颜色,属于什么种类等。因此,明见性的问题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给定对象本身的明见性;二是谓词判断的明见性。形式逻辑只探究判断的明见性条件(真值条件),但并不探究对象明见性的被给予性条件,因此尚未进入第一个层次。现象学则追溯到最原始的明见性——对象的明见性——的起源(第一层次),从而使奠基于对象之明见性的判断的明见性得以可能(第二层次)。
那么,对象之明见性又来自哪里?胡塞尔认为,它来自“前谓词经验”。个体对象的明见性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构成了“经验”的概念,关于个体之物的判断就是经验判断。此外,经验还包括模态,如“猜测性”“或然性”“好像”等。我们可以比较以下两个命题:
A1:我看到一棵树。
A2:我
好像看到了一棵树。 事态A2比事态A1增加了模态“好像”,则在A1中,一棵树作为一个对象在
当下(Gegenwart)的 感知中被给予了我;而在A2中,一棵树作为一个对象在 当下化(Vergebenwärtigung)的 想象中被给予了我。模态使个体对象被给予方式的自由变更得以可能。 这些在谓词判断和知识形成之前,就总是已经预先被给予的个体对象及其模态,就是“前谓词经验”。“前谓词经验”是一个可能性领域,因为任何一个个体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处于一个开放的“视域”之中。“这种视域就是那些已知的、以及并不只是现实地被意识到而且也包括那些未知的、可能被经验且在将来被知悉的实在东西的视域。”[8]50我们对个体之物进行统觉和立义(Auffassung),使个体之物的意义存储(bestand)和积淀下来。这些已知之物的意义超越了个体之物本身,随着统觉的连续性延伸到新的未知之物。统觉和被统觉之物及其意义构成了一个综合统一的连续统。意义的超越性形成预期,使尚未被具体规定的未知之物作为已知之物的视域不断地超越着个体之物,并在具体化的过程中得到确证和充实。因此,一个处于某种视域之中的个体对象就是一个可能的经验统一体,任何一个经验都有自身的“经验视域”,而“经验视域”使经验指向可能性,使单个经验扩展为无限开放的、综合的经验统一体。此外,先于所有单个对象的经验被给予的普遍信念基础就是“世界存在”:“
世界作为存在着的世界是一切判断活动、一切加进来的理论兴趣的 普遍的被动的预先被给予性。”[8]46因此,从判断的明见性向前谓词经验的回溯就是向原始的生活世界或纯粹经验世界的回溯,生活世界的明见性是判断的明见性的终极来源。这个回溯一旦完成,传统的形式逻辑就转变成了“世界逻辑”。 以上论述可归纳为以下图示:
一. 符号:表达与指号
二. 表达、含义与对象
三. 指称问题
四. 判断及其明见性的起源:前谓词经验
-
综上所述,我们以《逻辑研究》和《经验与判断》等文本为依据,从符号与含义开始,到前谓词判断与生活世界为止,简要地重述了胡塞尔的语言分析思想,这一重述将我们引向一个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如果说,对语言本身的分析属于狭义的语言分析,那么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的分析则属于广义的语言分析。以下我们将以“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作为一个问题域,对比分析哲学的相关论述,阐明胡塞尔现象学语言分析的特征。
-
① 这一节是对本文第二部分第三节“指称问题”的进一步反思,亦即“名称意指对象”这一似乎是“自明”(self-evidence)的前提,在此处则成为一个需要被批判的命题。
名称属于语言,对象属于世界,因而“名称与对象的关系”问题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的一个子问题。在现代西方哲学中,首先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的是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哲学中的“名称”(或“指称”)理论首先进行较为系统研究的是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写道:“世界是事实(facts)的总和,而不是物(things)的总和。” [9]30 事实都是可说的,应该说清楚;除了事实和描述事实的自然科学命题,其他都是不可说的,我们应该保持沉默。我们之所以能够言说世界,是由于语言与世界遵循同一种语法,那就是“逻辑”。不仅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遵循逻辑规则,而且一切可能世界也都遵循逻辑规则。世界系统诸层次与语言系统诸层次具有如下对应关系:
对象——名称
原子事实——原子命题
事实——命题
世界——语言
这就是前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图像论”。其中,语言中最基本的元素是“名称”,世界最基本的元素是“对象”,二者的关系是:“名称意指(bedeutet)对象。对象是名称所意指之物” [9]46,“在命题中,名称代表对象” [9]48。名称可分为“专名”和“通名”两类。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曾专门讨论过通名和专名的差别。他认为,专名和通名一样,都可以把我们的兴趣引向被表象、被意指的对象本身,对象可以在陈述句中显现为被陈述的对象。专名可以直接意指对象,而通名则通过定语间接地意指对象[4]367-368。
专名直接意指对象,胡塞尔这一观点,与维特根斯坦的并无差别,与分析哲学的创始人弗雷格的也是一致的。但是,对于通名(弗雷格称为“概念词”)及其所指,胡塞尔与弗雷格的看法则不尽相同。1891年,弗雷格在写给胡塞尔的一封信中以一个图示表明了他与胡塞尔的分歧:
1.弗雷格的通名模式:
概念词
↓
概念词的含义
↓
概念词的意义(概念)→处于这个概念下的对象②
② 弗雷格完整的句子图示如下:
参见王路:《句子图示——一种弗雷格式的解释方式》,《求是学刊》,2014年第5期,第34页,引文略有改动。
2.胡塞尔的通名模式:
概念词
↓
概念词的含义(概念)
↓
处于这个概念下的对象[6]54
弗雷格解释道:“我从概念到对象横着画了最后一步,是为了表明:概念(与对象)占据了同一层的位置,对象和概念有同样的客观性。”[10]59当然,弗雷格对“处于同一层位置”的“概念”和“对象”也是做了区分的:“概念——如同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起谓词作用。相反,一个对象的名称,一个专名决不能用作语法谓词。”[11]77比如在“晨星是一颗行星”这个句子中,“晨星”是专名,“行星”概念词。在“晨星是金星”这个句子中,有两个专名——“晨星”和“金星”,“金星”不是谓词,“是金星”才是谓词,在这个句子中,“‘是’显然不是纯粹的连词,从内涵上说它是谓词的一个本质部分” [11]78。所以,作为“是金星”这个谓词一部分的“金星”是个专名,它的意义(意谓、所指)在“晨星是金星”这个句子中不能作为概念而出现,只能作为对象而出现。简言之,弗雷格认为
专名意指对象, 通名意指概念;而胡塞尔则认为 专名和通名都意指对象,只不过 专名意指 一个个体对象, 通名则普遍地意指一定对象范围中的 每一个个体对象,“即是说,它可以不以专有名称的方式通过专有名称来指称,而是以共有名称的方式通过分类来指称”[4]909-910。比如“人”就是一个通名,当我们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时,“人”作为一个通名就普遍地包含了一类对象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每一个个体都具有一个可能的专名,比如苏格拉底,同时也被“人”这个通名在“类”的层次上被指称,即被称为“ 一个人”。 在胡塞尔那里,通名(类概念)之所以可以直接意指对象,是因为他把直观的领域进行了扩展,不仅感性的个体之物可以在直观中被充实,而且范畴和形式也可以在直观(即“范畴直观”)中被充实。比如“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中的“是”“有”,“一个人”中的“一”,都是可以被直观、被充实、被意指、被指称的形式,即“范畴形式”,它们是在普遍直观中被给予的普遍对象。任何范畴形式都是构成对象和事态的组成部分,都可以在范畴直观或本质直观中被把握。从个别对象开始,我们就可以直观到普遍性、总体性的本质。所谓“普遍对象”的
总体性特征,就源于 个体性的观念化抽象,因此普遍对象奠基于个别对象,范畴直观奠基于感性直观,通名奠基于专名。 当然,无论是专名还是通名,其意义都必须结合语境来理解。弗雷格提出的“语境原则”也适用于现象学的语言哲学。所谓“语境原则”就是:必须结合语词所在的句子来研究语词的意义,而不可孤立地研究一个语词的意义。简言之,即:“一个词只有在句子中才有意义。”[12]84推而广之,一个句子就是一个词的语境,一个文本就是一个句子的语境。从现象学角度看,对象和事态属于视域,语词和句子属于语境,现象学在诸视域(horizons)和诸语境(contexts)交织的场域中来讨论语言和世界的关系。
-
如上所述,生活世界是判断的明见性的最终来源,是先于一切对象被给予的总体视域,不限于经验世界,更多的时候是指“可能世界”。在《逻辑研究》第一版中,胡塞尔就对作为感知和判断之意向相关项的世界做了这样的多重区分:“个别自我的世界、经验社会共同体的世界,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有知识者(Wissender)的观念共同体世界:(在观念上完善了的)科学的世界、自在的世界。”[4]702在《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对可能世界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所谓一个‘可能世界’是说:它虽然涉及一般世界的本质形式,但并不涉及我们这个事实的、现实的世界。”[8]68在现象学中,现实世界,即经验世界被看作可能世界的一个例子,可能性蕴涵着现实性,而且高于现实性。
从语义学层面看,“可能世界语义学”是用来刻画“多世界”的模态逻辑模型,“原则上可以给一个语言及其逻辑以多种不同的但具有等价效力的解释”[10]164。最早提出可能世界思想的是莱布尼茨,他认为,一个事态A是可能的,当且仅当A不包含逻辑矛盾。一个事态由A1,A2,A3,……构成是可能的,当且仅当A1,A2,A3,……推不出逻辑矛盾。凡是可以被无矛盾地想象的世界都是可能世界,现实世界是诸可能世界中的一个世界。从可能世界角度看:
D1一个命题是必然的,当且仅当,它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是真的;
D2一个命题是可能的,当且仅当,它在某些可能世界中是真的。[10]165
对于可能世界的存在论意义,逻辑学界主要有三种主张:
1.可能世界语言论:可能世界是语句极大一致的集合,其一致性可以从句法学上理解,也可以从语义学上理解,代表人物是欣迪卡。
2.可能世界概念论:可能世界是我们想象世界的不同方式,它是被规定的,而不是被发现的,代表人物是克里普克。
3.可能世界实在论:可能世界是完全独立于我们语言或思想的真实的、抽象的实体,代表人物是D.K.刘易斯。[13]235
胡塞尔现象学的世界观属于可能世界实在论。他主张:“这个世界,每一个可能的世界,都是实在性的大全,在这里被我们归入实在性的是所有那些在时空性这种世界形式中通过时空定位而被个体化了的对象。”[8]304根据可能世界理论,我们可以合理地解释意向对象的存在论地位:如果意向行为指向的意向对象是现实的,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意向对象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如果意向行为指向的意向对象是非现实的,我们就可以说它存在于某个可能世界之中[6]146-147,而这个可能世界和现实世界有同等的存在论地位。
综上所述可见,分析哲学从概念和命题出发,通往可能世界;而胡塞尔的现象学则基于“视域”理论来描述可能世界。一方面,任何对象都有其视域,世界作为一切对象的普遍视域先于一切个别对象被给予;另一方面,任何经验都有其视域结构,经验总是指向可能性,“并且是从自我出发指向某种‘使其可能’(Ver-möglichkeit)的”[8]48。
一. 名称是否意指对象?①
二. 从经验世界到可能世界
-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胡塞尔现象学的语言分析(以下简称“现象学的语言分析”)的主要特征有:
第一,现象学的语言分析从属于“意向分析”。胡塞尔的语言分析,并未单纯地把对象、事态和世界理解为语词和语言的所指,而是将其理解为意向性关系中的一个环节——意向相关项(Noema),它与意向行为(Noesis)是平行的,二者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密不可分,共属一体。
第二,现象学语言分析是一种本质分析。胡塞尔的现象学所关注的不是个别意识,甚至也不限于人类的意识,而是一切可能的理性存在者的“普遍意识”。因此,现象学的语言分析是先天的而非经验的,是本质的而非事实的,它所分析的语言是作为“观念语言”的理想语言,即“现象学用本质概念和规律性的本质陈述将那些在本质直观中直接被把握的本质和建立在这些本质中的本质联系描述性地、纯粹地表达出来。任何一个这样的本质陈述都是在最确切词义上的先天陈述” [4]306。与这种语言分析相应的世界就是上文所说的可能世界,也就是说,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东西,比如“飞马”“圆的方”等,作为可能被意向的对象依然是有意义的,而且这种意义是可被表达的。
第三,现象学的语言分析追求的是一种对世界的整全而融贯的理解。与分析哲学相比,胡塞尔现象学中语言哲学思想的独创性非常显著,它力图使作为整体的语言、领悟与在语言中得到表达的现实联系起来。比如,胡塞尔的《逻辑研究》通过纯粹逻辑学层次上意义的同一性识别出语言的意指功能,进而识别出更基础的,为一切经验所共有的意向功能,即“对某物的意识”[5]399。意向活动和意向对象密不可分,以意向性为主题的意向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的框架。因此,现象学的语言分析关注的不是世界作为现成的存在者如何被描述,而是世界作为非现成的现象如何在某一视域中由我们构成,向我们显现,被我们描述出来。这种描述当然要凭借语言来表达,但它的基础不是语言,而是意识及其意向性特征。
第四,现象学的语言分析在视角与方法上都别具一格。首先,与索绪尔式的语言学相比,现象学的语言分析更关注的不是语言的形式本体论,而是语言的交际作用及其意识本质[14]。其次,与传统的形而上学相比,现象学的语言分析更关注的不是语言的“显现物”(Erscheinendes)维度,而是语言的“显现”(Erscheinen)之维。符号系统、名称、命题等,都是作为“显现物”的语言;而符号的表达、指称行为、判断行为和前谓词经验等,则是语言的“显现”。再次,与现代的分析哲学相比,现象学语言分析的主要方法不是语义上行(semantic ascent),而是本质直观。正是凭借对范畴和形式的直观,通名可以指称普遍对象;而沿着我们如何使用“通名”这个词,即语义上行的思路前进,则会囿于语言本身而无法通达对象与世界。
第五,现象学的语言分析虽然别具一格,但它与分析哲学并非决然对立。艾耶尔曾说过,胡塞尔的“本质直观”在语言上虽令英美传统的学者感到陌生,但其实质不见得与摩尔的“概念分析”有多大差别,真正使他们区分开来的是胡塞尔的这样一种信念:“各种各样的本质的东西(entity)不仅是与意识相符合的,而且是由意识构设而成的”[15]244。同时,他认为胡塞尔这一日渐增强的唯心主义倾向使其最终走向了主观唯心论,且难以避免唯我论,而主观唯心论和唯我论与拒斥形而上学的分析哲学当然是不相容的。笔者以为,这里或许存在一些根本分歧,比如,对于“意向性”这个概念,分析哲学家大多只谈“指向性”,而现象学家则兼及“指向性”和“构造性”。又比如包括艾耶尔在内的许多分析哲学家,都忽视了胡塞尔晚期思想中“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向度。胡塞尔指出,“我”所经验的世界并不是“我”自己的意识综合的产物,而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经验,有他自己的显现及其统一体,有他自己的世界现象,同时,这个被经验到的自身也是相对于一切经验的主体及其现象世界而言的”[16]153。一方面,自我和他者共同构造了世界的现象,即诸先验自我之意识的意向构造的成就;另一方面,自我与他者形成了主体间性共同体,即语言-社会的共同体。总之,本质直观的方法、意向性的特征、主体间性的向度等,既可被运用于意向分析,也可被运用于语言分析,它们无论是在现象学中,还是在分析哲学中,都不可或缺。
-
综上所述,胡塞尔的现象学讨论了一系列重要的语言哲学问题,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对语言(符号)问题的分析,还是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的分析,胡塞尔都给出了较为系统的论证,可以说,他初步建构了一门作为意识哲学的语言哲学。这门语言哲学既探究了分析哲学所关心的一些重要议题,又提供了不同于分析哲学的视角与方法,为当代意识哲学与语言哲学之间的会通提供了一个范例。
所谓会通既非一方被另一方同化,亦非双方机械地杂糅,而是以现象学的视角与方法,激活分析哲学的思想资源,或者用分析哲学的视角与方法,激活现象学的思想资源,让二者在共同问题域中展开对话,形成两种哲学间的互动和互补。这种互动和互补对于当今哲学界仍是一个有待拓展的领域。随着这一领域日益深远的开拓,我们或许会更加清楚地看到:无论是朝向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还是面向作为事实总和的世界,多元的理解往往比单一的理解更能够接近事情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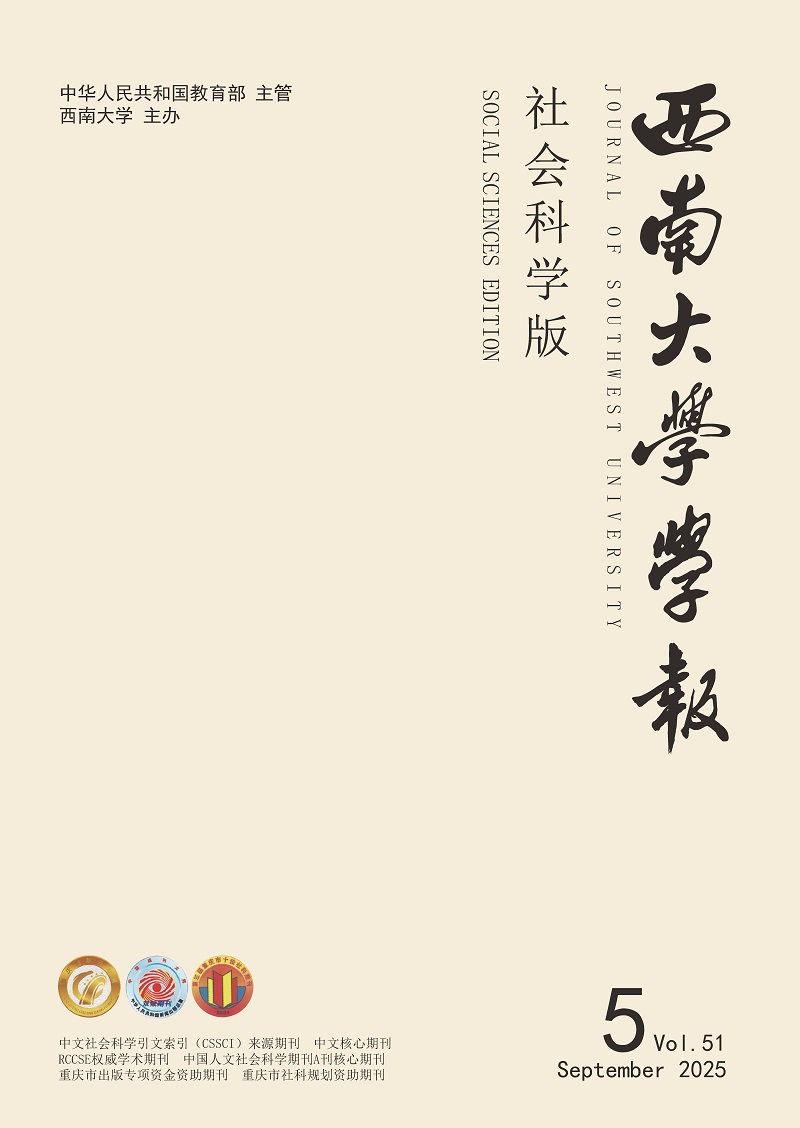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