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生命”一词指生物体所具有的活动能力,“张力”则是物体内部两侧因外部拉力而存在的相互牵引力;将两词组合来看,“生命张力”意在反映生命所具有的活力、韧性、质量及价值等特质,张扬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人文学科研究中,有时会借用“生命张力”一词来表现研究对象的生命特质,如《经典回归的永恒生命张力——〈尚书〉学文献整理研究及其当代价值》一文所展示的传世经典与时代互动的强大生命活力[1]。综观已有研究,文学作品分析研究常用“生命张力”来揭示生命的独特性,但有关历史过程中“生命张力”的研究并不多见。
然而,人类上万年的文明发展史就是一个个生命试图不断改善生存环境的历史,充满了生命的互动;人类历史过程中所蕴含的人类生存的经验教训、哲理智慧,充满了生命的灵性。正如法国历史哲学家雷蒙·阿隆说:“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2],也就是说,虽然历史学的对象是逝去的人与事,但其目的却是为“活着的人”更好地生存。历史课程关注生命活力当是应有之义。拟就此文旨在期待历史教育能够以一种回望的视角揭示人类的生命历程,以俯瞰之势启示人类的生存之道,更好地赋予历史课程灵动的生命张力,从而可以让今天“活着的人”更美好地生活。
HTML
-
历史是“人类”的历史,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不断抗争、创造、适应以求生存的历史。“人”如果没有“类”的存在,就无从讨论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问题。因此,讨论历史过程中的生命张力首先就需关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生存问题。
自人类诞生以来,生存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籍科普学者艾萨克·阿西莫夫轻而易举即列出了二十种威胁人类生存的危险[3],其中,除自然灾难外,还有人类活动种下的苦果——某些现代化的伴生物暗藏杀机,如工业污染所带来的生存环境恶化、核能利用所潜藏的毁灭性灾难、微生物实验所潜伏的致命细菌、军备竞赛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威胁、人口增长导致人类不惜代价疯狂攫取食物所造成的生态平衡被永久性破坏等等,不一而足。面对近代以来技术的强势扩张,马丁·海德格尔提出“空气被处置以生产氮气,土地被处置以生产矿石,矿石又被处置以生产铀,铀进一步被处置以生产原子能。这种能量释放出来,既可以为着毁灭,也可以为着和平”[4]。当代有学者直言,在“发展”成为主流话语大词的时代,应当看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只有一个太阳。因而,‘发展’存在着天然的限度。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将会由于这个限度的存在而崩溃”[5]。无疑,真正崩溃的不是社会,而是人类自己。
我们需要回头看历史才可能真正理解居安思危的深刻性。历史以纵贯洪荒与文明之势,展示了历史发展演变大势及人类跌宕起伏的命运交响曲。人类的历史进程虽以发展进步为主线,但也不乏人类自身酿成的令整个人类几遭灭顶的灾难,让人在震撼之余,不能不心忧人类的命运。被誉为近代以来最伟大历史学家之一的汤因比作了振聋发聩的分析,他提出:“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6]且不说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远古时代,只需观察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便不能不认同汤因比的担忧:疯狂的战争、对自然的无休止掠夺、污浊的环境、枯竭的资源、短缺的粮食、融化的冰川、核泄露的威胁……它们一次一次地将人类推向毁灭的边缘,历史发出叩问:人类将何去何从?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没有了人“类”,何谈单个的“人”?人类的生存课题与人类每个成员的生命休戚相关。但是,真正的麻烦在于目光深邃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能看到的生存危机,普通大众未必会有同样的切肤之感。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吉本在阐述罗马帝国衰亡历史时所言,“要让当代人的眼睛,在一片安居乐业的景象中观察到暗藏着的衰败腐化因素,那几乎是不可能的”[7]。面对芸芸众生,关于人类生存问题的教育启蒙显得迫切而重要。人类历史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便是最直观的教育素材,历史教育自当关注人类的生存问题。也可以说,渗透于历史课程的生命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引导学生关注“人类”的存在难题。
第一,启发人们从历史的角度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意义。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如何与自然相处的问题,并成为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要求历史教育应帮助学生“从历史的角度去了解和思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关注中华民族以及全人类的历史命运”[8]。纵览历史,一方面,人类能够顺自然之势利用好自然,为自己的生存发展谋求更适合的环境,如大禹顺水流之性而成功抑制水患、秦国都江堰水利工程因应自然之势方得“水旱从人”之利,今天习近平的“两山”理论更突显了对自然及人类命运的关切。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很多时候,自以为是的人类受贪欲所支配,无节制地掠夺自然,损毁赖以生存的环境,从而将自己推到了毁灭的危机边缘。譬如,远古楼兰古国的消失、近代伦敦上空“乌黑的、浑黄的、绛紫的,以致辛辣的、呛人的”(老舍语)伦敦雾、未来马尔代夫可能因气候问题而被海水吞噬的危机等等,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子。由于人口与资源需求的激增,今天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比任何时候都脆弱,也就更迫切地需要构成人类的每个个体关注生态文明。
历史教育当从大自然对人类无休止“掠夺”行为的惩罚中,引导人们认识自然的力量,学会敬畏自然,顺应自然,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具体到教育实践中,可以在呈现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相机启发学习者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例:在学习丝绸之路这一内容时,可设置探究问题:楼兰古国今何在?
楼兰古城位于罗布泊西北、孔雀河下游三角洲,本是一个“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9]逐水草而居的美丽小国。但根据考古发现,当年楼兰人为在罗布泊边筑造10多万平方米的楼兰城而砍伐了许多树木和芦苇,良好的植被受到严重破坏。人为破坏与世界干旱气候影响叠加,最终让楼兰古国消亡于大漠中。
历史课程在讲述两汉丝绸之路的开通时,便可首先以楼兰为知识点呈现当时西域绿洲的良好生态及繁荣景象,在学生充分感知自然与人文之美的基础上,设置“拓展探究”学习环节,介绍楼兰古国的考古发现过程,并引导学生追问“楼兰古国今何在”,再联系当今沙漠化问题尝试探寻楼兰消失之谜,进而启迪思考人类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实际上,诸如早期农业文明的刀耕火种、工业革命后的污染、中国20世纪50年代“向自然开炮”等等历史内容的教学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对人类生存环境问题的讨论,因为其中的历史教训必有助于启发历史学习者站在关怀人类命运的高度来审视人类生存的历史条件。
第二,从人类自己制造的战争灾难中意识到其对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树立珍爱和平的观念。人类文明自滥觞之时就伴随不计其数的大大小小的战争,战争的性质、战争的规模、战争的后果自是林林总总,千差万别,笔者无意说所有的战争都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也不会认为战争的发动者持有灭绝人类的主观动机,甚至有些战争根本就是以维护人类生存为使命的,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然而,在客观效果上,战争确是人类自我毁灭的方式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绞肉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势力灭绝人性的种族屠杀、记忆犹新的卢旺达种族大清洗等等,都是对人类生存权利的一次又一次挑战。历史上有无数的教训警醒世人:战争与和平问题关系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到整体的人类文明的兴衰。
今天,依托先进科学技术制造出来的战争武器杀伤力更强、破坏性更大,具有毁灭性打击能力的核武器就是其代表。1945年7月,当美国曼哈顿工程终于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中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核试验时,领导该项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J·罗伯特·奥本海默在震撼之余,引用了一句诗“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10],这个“世界的毁灭者”便是潜藏在核武器研究中的核战争。人类通过制造毁灭性武器将自己推入前所未有的“末日”风险中。当然,为了避免自我毁灭,核大国及核扩散国家间一直在寻求平衡之道,然而,当2019年8月3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退出美苏《中导条约》并拒绝延长《俄美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时,全世界都认识到了此前种种试图通向平衡的限制性措施都不堪一击,人类面临失去制约核战争的高风险。
为人类的生存计,历史教育需充分利用好课程中涉及战争的内容,引导学习者既充分理解那些为维护人类生存权而不得不战的战争,更深刻认识战争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威胁和破坏,树立珍爱和平、反对战争的价值观念,进而涵养关怀人类前途命运的情怀。
-
众所周知,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正是由过去所生存过的人及其活动所构成的。历史的丰富性正在于它包含着形形色色的人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快乐与痛苦、存在与死亡。将历史中各种生命经历与生命教育相结合,不难看到审视个体生命意义的两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是通过批判历史上一切草菅人命、践踏人性的行为,引导树立尊重、珍爱自己和他人生命的观念。本文缘于对近年屡屡出现的青少年漠视自己及他人生命现象的焦虑,因而迫切期待能借助历史过程中无所不在的“生命”存亡现象来强化青少年尊重生命的意识,重视人作为生物体的生命存在。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1],换言之,个体生命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由此,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存在理应成为生命教育的基本要求,也可以说是最低要求——它处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最低层,即基于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得到满足的生命存在。
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在历史教育素材的选择方面,应避免选用可能误导学习者生命认知的材料。不可否认,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充满暴力、血腥、杀戮、死亡,这些内容都可能暗含对生命的漠视。这样的历史内容客观存在,历史教育回避不了,但可以通过筛选材料及设计呈现方式来加以引导。比如,笔者曾在某初一历史教科书中看到过一幅与陈胜吴广起义配套的“大泽乡起义”插图(后来的新版教科书未再使用该图片,但在教师的授课PPT中还经常会见到),该插图的来源是中国邮政1991年发行的陈胜吴广起义2 200年纪念邮票,图片的主体部分是陈胜吴广手持大刀振臂高呼,图片右下角是一具躺在草丛中穿着戎装的秦兵尸体。起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起义人群杀死押送的官兵以及起义队伍群情激愤都是历史事实,因此,该图片作为邮票难以置喙;然而,将该图片用到初中课堂上则似欠妥,因为躺在草丛中的冰冷尸体与旁边热情激愤的人群形成了鲜明对照,将这样一幕场景放在尚未形成对生命有敬畏感的初中生面前,便有可能传达出诸如可以无视某种生命存在或某些人生命无足轻重这样的不良信息。更何况这只是一幅没有多少史料价值的想像画。总之,历史教育对历史材料的运用,需选择有利于育人向善的内容。从生命教育出发,历史课程教学在材料选择方面当有助于提升学习者对生命尊严的认知、认同。
此外,历史教育需旗帜鲜明地揭示并批判历史过程中那些草菅人命、践踏人性的行为,以示对生命的敬畏,维护人的尊严。古今中外的历史中都有反人类的戕害行为,如人类早期许多国家盛行过的人殉制度、战争中有组织的屠杀等等,它们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最黑暗一面。历史教育在直面这样的黑暗时,需要超越史事而唤起学生对生命本身的思考。例如,在有关“南京大屠杀”这一内容的教学中,许多老师倾向于借助图片呈现日军屠杀中残忍、血淋淋的场面,让学生直观感知日军暴行。这样做当然无可厚非。但笔者认为,止于批判侵略者的残暴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站在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立场,感受鲜活生命逝去的痛苦,认识日军反人类的本质。
第二个角度是关于生命价值的教育。历史教育要尊重人的生命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否定一切的牺牲。载入史册的历史人物的生命存在都蕴含着是非善恶之辨,附加有生命的价值选择,向后人展示了无论是存在还是逝去都值得永世铭记的生命力。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泰山”与“鸿毛”所关涉的便是生命的价值问题。史籍中也信手可拈关于生命价值选择的故事。譬如,春秋时期齐国太史三兄弟为直书“崔杼弑其君”而前仆后继献出生命的“死”及司马迁为完成《史记》而忍辱偷生的“生”,都昭示着堪为典范的生命价值选择。可见,人的生命存在还有质的要求,那就是展示生命的意义,追求存在的价值。诚如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所言,个体可以超越衣食无忧地、安全地“活着”这一生命存在的基本需要,而为尊严、信念等精神需求付出肉体的生命,提升生命的价值,使人真正“成人”。加入价值考量后,生命教育便从关注存在层面上升到追求更有价值的存在。笔者认为,这应当是历史课程中生命教育的根本追求,也可视为高级目标。
历史课程中诸多历史人物的人生选择都蕴含着对生存价值的诠释,都能够启发学生对生存意义的思考,为学生追求更有价值的生命存在提供榜样示范。这方面的一个经典案例是不少中学老师都遇到过的学生对谭嗣同之死的争论。
例:谭嗣同之死所引发的生命价值教育追问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本有机会像康有为那样远走他乡,伺机东山再起。但为唤醒民众,他以大无畏的凛然之气慷慨赴死。教师每每讲到此处,总有学生发出感叹:“谭嗣同太傻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应该爱惜生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归结到一点,就是谭嗣同不该选择赴死。
学生发出感叹之时,正是对学生进行生命价值(生存意义)教育之机。教师可以分三步对学生进行引导:
第一步,认可学生珍爱生命、惋惜生命逝去的情感,这是生命观教育的基础要义;第二步,明确指出,生命存在具有不可逆性,应当珍惜生命,但在历史上确实有许多人在生与死之间选择了死亡,如商周鼎革时期的伯夷叔齐为气节饿死首阳山、南宋文天祥拒元厚禄南面就死、近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誓言和行动、民主革命中无数为信仰而献身的先烈、大灾大难面前的逆行者等等;第三步,在将众多“向死”之史迹呈现在学生面前后,便可追问并讨论:为什么古往今来总有人在生死关头选择死亡呢?他们都傻吗?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选择了死亡?在学生的讨论中,教师即可引导学生领悟生命的价值及存在意义:求生是人的本能,但为所认定的理想信念而毅然赴死则彰显了生命的崇高,譬如谭嗣同选择死亡,便是怀揣用鲜血方能唤醒大众救国的信念。丹心照汗青,“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个体为了更多人的生存或更有价值的生存而舍生取义、从容就死是对一般意义上的“生存”的升华,这正是生命张力所在。
中学生处于人生观形成的关键阶段,以尊重生命、理解生命价值为核心的生命观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历史过程中已经积累了理解生命及其价值的丰富素材,关键在于历史教育工作者能否挖掘这一教育价值,有意识地引领学生思考“生存”这一人生的重大课题。
-
卢梭提出应对孩子们进行这样的生存教育:“教他成人后怎样保护他自己,教他经受得了命运的打击,教他不要把豪华和贫困看在眼里,教他在必要的时候在冰岛的冰天雪地里或者马耳他岛的灼热的岩石上也能够生活,问题不在于防止他死去,而在于教育他如何生活。”[12]智慧地生活也是生命教育的应有之义。
生活的智慧可从历史中析取,因为“历史是关于生活的学问——人的本质、人的处境及他们所有的考验与失败以及其最宝贵的成就”[13],智慧之光即闪耀于历史长河中。每个人的生存都是有限的,能看到的时代、地域也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空间中,总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视野和思维局限,而历史提供了突破此种局限的门径,因为“历史可以把迄今为止人类最美好的事物集中起来,供人们欣赏、使用”[14]。确实,历史向后人提供了多种历史时段、多种空间尺度的观察视角,可以让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超越当下来确定解决当下问题的坐标。毫无疑问地,历史中所蕴藏的做事做人智慧是其他任何一门课程所望尘莫及的。
怎样在历史教育中揭示生命的智慧呢?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
例:西安事变的两种教学旨趣。
第一种,讲授西安事变原因、经过、结果,穿插精彩的细节,让学生感受波诡云谲的时代风云和复杂微妙的政治博弈,激发对相关历史内容的探究兴趣。
第二种,在介绍西安事变的概况后,重点引导学生探讨: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放下了对蒋介石的复仇情绪(大革命中蒋介石分裂统一战线并屠杀革命群众)而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又为什么能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你做人做事有何启示?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至少可以让学生领会三方面的做人做事智慧:一是认识到武力绝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手段,谈判也有可能是更佳的选择——现实生活中不要总想用拳头解决问题;二是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能够审时度势,具有看清大局、把握大局的智慧——现实生活中能够不被“浮尘遮眼”,学会抓住本质和要害;三是感受谈判中的妥协智慧,妥协所展示的是各方知己知彼、洞察时局、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智慧,而不是简单的让步,西安事变的谈判及和平解决过程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妥协智慧。
以上两种教学设计中,前者可能让学习者在精彩的细节中折服于历史的魅力;而后者则能够进一步启发他们领悟解决问题的智慧。归结起来,历史课程中的历史智慧教育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在观念层面,充分理解历史过程中种种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明了其中蕴含的抉择智慧,并意识到其教育价值。诚如王家范所言,“历史实是人们不断选择自身存在方式的历史。曾经有过的历史选择,后人固无权苛责,但在今人选择时,检讨前人各种选择的得失成败,斟酌取舍,思远慎终,亦当是后来居上者应具备的智慧”[15]。成都武侯祠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说的正是这个“后来居上”智慧。
具体而言,在历史教育中,首先要明确所有的历史过程都是人们选择的结果;其次,要理解不同的选择可能带来不同的结局,得失成败取决于选择中的权衡智慧;最后,认识到今天回看前人的选择,其意不在褒贬臧否,而是寻找后来居上的智慧。比如,学习中国古代的治水传说这一内容时,要旨不在呈现大禹父子治水方法本身的不同,而是引导学生从大禹的治水方略中看到其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方面的智慧,即顺应自然,因势而导。在今天自然环境越来越恶化的背景下,让孩子们拥有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既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二是在操作层面,首倡深入历史、领悟历史智慧。实际上,进入历史人物的世界去体验历史的方法很早即是被倡导的治史学史方法。比如南宋吕祖谦就说过,“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16],东莱先生可谓要言不烦,切中肯綮;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神游冥想”“了解之同情”也大抵有着同样的意味。
而让学习者能够深入史中掩卷思考的捷径当数创设问题情境,让其站在历史人物的位置或处境中去抉择——选择是必备的人生智慧。比如,可以通过提出“他们面临怎样的历史难题”“如果是你处在那样的环境中,你将怎样抉择”“你的这种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历史人物为什么那样选择”等问题,引导学习者“思接千载”,领悟历史智慧;在学习者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聚焦分析不同的历史选择可能带来的不同的历史发展结果,以此拓展视野,并从中获取经验教训,如前述案例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选择。
在深入历史领悟智慧后,还需要跳出历史,从现实问题出发,运用历史智慧,尝试解决生活实践中的问题。譬如,运用历史中领悟的妥协智慧来认识和处理矛盾冲突,包括认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与妥协关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运用历史认识中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实证智慧去辨析今天铺天盖地网络信息的真伪良莠。一言蔽之,历史课程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学习者将历史过程与学习者的生命及生活经历建立起联系,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地将历史过程中所积淀的无穷智慧融入个体生命,从而为创造更美好生活奠基。
综上,回到历史中去观察,不难看到人类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是人类不断探索世界,运用智慧解决问题以谋求更美好生活的过程。历史集古今中外智慧于一身,若能启迪学习者领悟人类所积累的这些智慧,无疑有助于提升个体解决“如何表现自己,如何和别人进行交流,如何探索世界,而且学会如何继续不断地、自始至终地完善他自己”[17]等问题的能力,进而提升生命的品质。
-
“生命”是一个宏大的主题,笔者本无意触碰,但每每看到历史教学置“生命”于不顾,只给学习者一大堆需要记忆的时间、地点、人物、经过等一成不变的知识框架、一串串反映人口增减及经济涨落的数据以及程式化的应试方法和解题技巧时,再看看近年来的中小学生伤人及自伤事件,不由得不考虑学科教学渗透生命教育、救赎和敬佑生命的问题,这也切合了当前课程思政的基本理念。当然,生命教育不是新话题,对生命存在的关注早已有之,生存教育也早走进了课堂。在2020年5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有代表更是提出了把生命教育纳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议。实际上,生存教育及生命教育已然成为一个世纪性、世界性的课题。不过,多数学者认为生存教育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以培养和训练学生生存能力为主要目的的教育[18],如中小学广泛开展的安全教育、逃生自救训练等即是此类典型教育活动。这些关于生存技巧的教育固然重要,但笔者认为开展基于尊重生命存在、张扬生命价值、提升生活智慧的生存教育更有“生命力”。
如果留意一下史学大家们的笔墨所及定会发现,从修昔底德到汤因比,从司马迁到陈寅恪,无一不流露出对人、对人类处境的深切关注。马克·布洛赫在为历史学存在价值辩护时,特别指出“不可否认,如果一门科学最终不能以某种方式改善我们的生活,就会在人们眼中显得不那么完美……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19]。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大势面前,作为在史学与懵懂少年之间建立沟通桥梁的历史教师,也当以悲天悯人之情怀及对生命负责的职业操守,在史实中用心披沥,发掘生命教育的价值,引导孩子们关注“生存”这一人类大课题。此当为人类之大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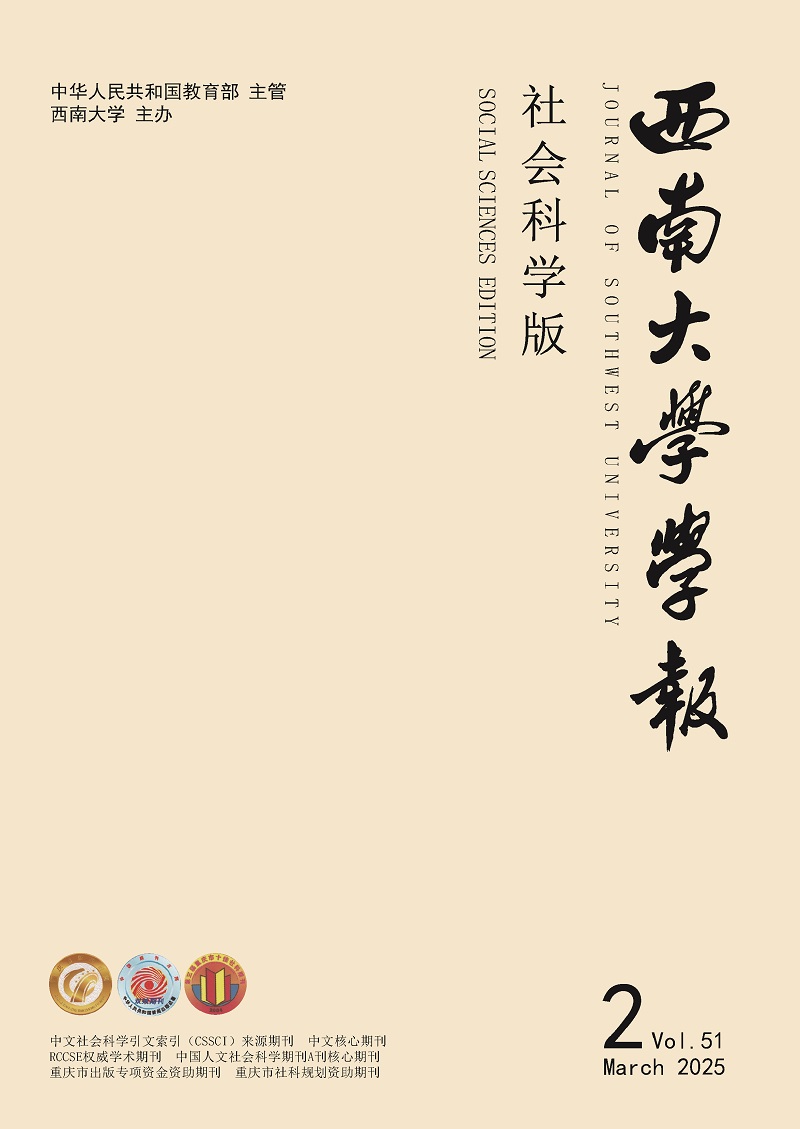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