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宅是里的基本构成单位,也是编户民最主要的生活空间。在古代,住宅问题的重要性仅次于土地问题。《论衡·诘术篇》载:“夫人之有宅,犹有田也,以田饮食,以宅居处……先田后宅,田重于宅也。”[1]1028因此,住宅问题也是考察秦汉历史比较关键的一把钥匙。目前关于秦汉住宅法律文献的研究,主要围绕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展开。这些研究往往是在讨论秦汉“名田宅制”时,附带论及住宅问题,表现出“重田不重宅”的特点。由于“名田宅制”涉及土地制度这一核心问题,学者们讨论热烈,成就斐然[2]123-138。这也使得秦和汉初与田制相关的住宅法律文献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其中杨振红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她认为当时的编户民有获得住宅以及继承、转让和买卖住宅等权利,同时也有在行使这些权利时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义务[3]。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与田制相关的住宅法律文献只占所有住宅法律文献的一小部分,剩余部分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同时,秦和汉初关于住宅的法律文献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丰富,比如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居住者有维护和修缮住宅的义务等。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秦汉住宅法律文献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以期获得整体认知。由于“法是权利义务之学”,故本文将从权利与义务两方面研究这些法律文献。
HTML
-
根据前人研究,秦和汉初编户民有从国家获得住宅的权利,相关研究已经比较成熟,故本文不再赘述。下面将重点讨论以下几种权利:
-
秦代关于住宅不受侵犯的法律规定,见《法律答问》:“小畜生入人室,室人以投(殳)梃伐杀之,所杀直(值)二百五十钱,可(何)论?当赀二甲。”[4]115据龙岗秦简[5]107、张家山汉简[6]15可知,秦和汉初法律规定:如果杀伤他人畜产,与盗同法。而《法律答问》记载:“(盗)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黥为城旦。”[4]93即故意杀伤他人牲畜,当其价值超过220钱而不满660钱时,行为人要处以黥为城旦刑。但如果牲畜因闯入他人住宅而被杀死,即使其价值超过220钱达到了250钱,也仅仅是处以罚二甲的惩罚。与黥为城旦相比,处罚非常轻,其原因就在于牲畜闯入他人住宅。目前虽然还没发现秦律对他人擅闯住宅的规定,但可以推测这样的规定一定是存在的。
《周礼·秋官司寇·朝士》云:“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郑众曰:“……若今时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7]878郑众以汉律解经,说明汉代有关于他人擅闯住宅的法律。所谓“牵引人”,孙诒让解释道“亦谓劫略良人也”[8]2831。因此贾公彦[7]878、沈家本[9]1473-1474、程树德[10]81均将该律条归入汉代《贼律》中。根据规定,当有人无故闯入他人住宅、登上他人车船以行劫掠之事时,主人可以即刻格杀进入者,不用承担法律后果。这里没有明确限定进入者的身份,说明其内容适用于所有身份的人。
另外,汉律中还有禁止官吏夜晚闯入他人住宅的规定,居延汉简载:“捕律:禁吏毋夜入人庐舍捕人。犯者,其室殴伤之,以毋故入人室律从事。”[11]551从这一记载可知,汉代制定有“毋故入人室律”来处罚擅闯住宅的人,上引《贼律》“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条当是其主要内容之一。从《捕律》的规定来看,官吏即使有正当理由(“捕人”)也不得在夜晚进入他人住宅。官吏尚且如此,其他身份的人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捕律》中的规定可以看作是对“毋故入人室律”的强调和补充。综合《贼律》《捕律》条文来看,实际上任何身份的人,在任何时间都不得无故进入他人住宅。
秦汉法律还对擅自撬开他人住宅门户的情形有规定,《法律答问》载:
“抉籥(钥),赎黥。”可(何)谓“抉籥(钥)”?抉籥(钥)者已抉启之乃为抉,且未启亦为抉?抉之弗能启即去,一日而得,论皆可(何)殹(也)?抉之且欲有盗,弗能启即去,若未启而得,当赎黥。抉之非欲盗殹(也),已启乃为抉,未启当赀二甲。[4]100
所谓“抉籥(钥)”就是撬他人住宅的门键。若行为人是为了盗窃,即使未撬开门键也应判赎黥刑;若行为人不是为了盗窃,门键已开才算撬,应判赎黥刑,若门键未开则罚二甲。张家山汉简中也有类似规定,《二年律令·杂律》载:“……及盗启门户,皆赎黥。”[6]33其内容与秦代关于“抉籥(钥)”的规定有明显继承关系。
沈家本认为汉代《贼律》中有“向人室庐道径射”条,其依据为《晋书·刑法志》“向人室庐道径射,不得为过失之禁也”[9]1474。该律条的意思是:向有人居住的住宅、有行人经过的道路射箭(而造成杀伤的),不得以过失罪减轻处罚。其目的是严惩此类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但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中,均找不到汉代存在此律条的证据。或许是因为晋律与汉律有明显的继承关系[12],沈氏才将其纳入汉律中。
从前文分析来看,无故进入住宅的主体无论是动物、人还是物,都存在损害住宅居住者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可能性。因此,秦汉时期关于擅闯住宅的法律规定的主要目的也在于保护这两项权利。而现代法学中,一般把住宅不受侵犯作为一个具有人格权、隐私权、财产权等诸多权利的集合体,并非只保护住宅居住者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13]45-51。因此,秦汉住宅不受侵犯的法律内涵与现代法学并不完全相同。
-
目前关于秦汉时期住宅不被毁损的法律文献,主要集中在与火灾相关的情形中。这种情形可分为两类:一是故意纵火造成他人住宅毁损,相当于现在的放火罪;二是因过失导致他人住宅着火毁损,相当于现在的失火罪。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可大致推断出秦汉关于住宅毁损的法律概况。
关于放火罪,龙岗秦简有“纵火而〼□”的律文残片[5]100,可知秦代有相关法律。《二年律令·贼律》载:
贼燔寺舍、民
室 屋 庐 舍 、积 
黥 为城旦舂。其失火延燔之,罚金四两,责 (债)所燔。乡部、官啬夫、吏主者弗得,罚金各二两。[6]8“贼燔”即故意放火焚烧。根据规定,放火毁损他人住宅将处以黥为城旦舂刑;若非有意为之,犯者处罚金四两并赔偿损失;若没有抓到行为人,相关官吏也会受罚。悬泉汉简载:“〼县官律曰:贼燔县官积……〼□火延燔之,罚金四两。” [14]517该律文虽不完整,但与上引《二年律令·贼律》对照可知二者内容基本相同。悬泉汉简的时代大致为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至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14]前言,3,说明汉初关于放火罪、失火罪的律文沿用时间较长。以上律文中,对于放火罪重点关注作案动机和对行为人的处罚;而对于失火罪,除重视动机和处罚外,也重视对住宅所有者的赔偿。
由于失火罪涉及赔偿他人损失的情形,所以会面临一些更复杂的问题,比如怎样确定赔偿金额,当失火者无力赔偿时又该如何处理等。关于这些问题,东汉初年的梁鸿失火案可以为我们提供线索,《后汉书》载:“(梁鸿)曾误遗火延及它舍,鸿乃寻访烧者,问所去失,悉以豕偿之。其主犹以为少。鸿曰:‘无它财,愿以身居作。’主人许之。”[15]2765火灾发生后,梁鸿与屋主以双方协商的方式确定赔偿金额;当梁鸿没有能力赔偿全部损失时,又以劳役的方式偿还。梁鸿与屋主的这些做法当是依据法律,并非随意为之。东汉初年忙于战事,其法律大多沿用西汉,梁鸿失火案的处理或可反映西汉的法律规定。
以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赔偿金额的方式,可能在东汉和帝时期就已经被改变。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载:
永元十
五 年(103年)十一月壬戌朔,十八日己卯,左部贼捕掾宫、游徼饶、庾亭长扶叩头死罪敢言之:谨移男子袁常失火所燔烧民家及官屋名直钱数如牒。[16]175袁常失火造成官、私房屋毁损后,由左部贼捕掾等官吏统计了损失金额。这说明确定赔偿金额的方式不再以双方当事人协商为主,而是由官方确定。同时,官方统计的不仅有房屋本身的损失,还包括房屋内其他财产的损失。如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载:“恭兄记不得,记伤晃,亡散,失火燔烧陏舍、财物。”[16]178这种由官方定损的方式更加合理,不仅有利于减少纠纷,还对失火者的赔偿行为有更好的督促作用。
由于火灾往往会严重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于是法律中也有了关于防火、救火的规定。如商鞅变法有“弃灰于道者黥”的规定,关于“灰”,《说文》云:“死火余烬也”[17]482,因为将灰烬丢弃在道路上有引起火灾的可能,故施以黥刑严惩。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中有“里中备火”的记载,“里中”即“同里的人……或指家中。”[18]109显示秦代对里中住宅火灾的预防和重视。《后汉书》载:
建初中,(廉范)迁蜀郡太守……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15]1103
文中“禁民夜作”“严使储水”皆为预防火灾的地方性法规。目前虽未发现汉代预防火灾的全国性规定,但这样的法律很可能是存在的。
住宅发生火灾后,民众该如何应对?出土文献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载:
中客匈匈,皆言火。浅与他俱起出户,之舍后,见火在更衣屋上,适康上屋捄火,令他取水。他即于井上汲水,火延燔着宾舍,不可复捄。他出器物,未悉得。火复着他等舍。不知火所从起。[16]157
这一案件中,康、他等人为什么积极救火?除了见义勇为的品德、防止火灾蔓延的现实考虑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韩非子》载:
(越王)于是遂焚宫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敌之赏;救火而不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之涂其体、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19]229
越王故意放火焚烧宫室,起初无人救火;当下令救火有赏,不救火受罚后,人们便积极救火。可知救火这一行为具有强制性。《唐律疏议·杂律》中也有类似规定:“诸见火起,应告不告,应救不救,减失火罪二等。” [20]1902当发生火灾时,如果袖手旁观会受到法律制裁。结合这两条史料来看,秦汉律令中可能存在关于遇见他人住宅着火时,人们应该如何处理的强制性规定。另外,根据秦汉法律的规定,同伍之人要相互帮助,否则会受到处罚[4]116。这或许也是人们(尤其是同伍之人)积极救火的原因之一。
以上关于因火灾造成他人住宅毁损的论述,涉及行为人的动机、刑罚、赔偿、毁损行为的预防以及发生过程中他人的义务等。这些都可以为我们了解秦汉时期关于住宅毁损的一般性法律规定提供参考。
-
秦代关于在住宅中经商的法律,主要见于岳麓秦简《金布律》:
金布律曰:市冲术者,没入其卖殹(也)于县官,吏循行弗得,赀一循〈盾〉。县官有卖殹(也),不用此律。有贩殹(也),旬以上必于市,不者令续〈赎〉


律文主要是对交易地点做出明确规定,其中可以在住宅中贩卖的主要是“瓦土


岳麓秦简《金布律》还规定:“黔首卖马牛勿献(谳)廷,县官其买殹(也),与和市若室,勿敢强。”[21]133政府如果向百姓购买马牛,可在市场或住宅内进行以双方自愿为前提的交易。
关于西汉时期是否允许在住宅中进行商业活动的问题,可与王莽改制中的相关规定一并考察。《汉书·食货志》载:
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24]1180-1181
“里区”即住宅区。王莽规定:对在住宅中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应收取利润的十分之一作为税贡;如果不申报或有所隐匿,则没收所得并罚作一年。显示当时住宅中也可以进行某些商业活动,只是目前无从得知可以经营哪些商品。王莽改制多仿《周礼》,考诸此书或许能有所收获。《周礼·地官司徒·载师》云:“凡任地……园廛二十而一”,郑玄注云:“廛,民居之区域也。……古之宅必树,而畺场有瓜。”贾公彦疏:“云‘古之宅必树’者,即《孟子》桑麻是也。”[7]725-726可知宅院中的土地可以用来种植桑麻等经济作物。由此推断,王莽对住宅区所收的商业税可能包括类似事项,而且税率远高于《周礼》的二十分之一。另外,《二年律令·户律》中有“民宅园户籍”[6]54,此处的“园”主要指宅院[25]218。这也暗示在西汉初期,政府可能已经开始对“园”征税。汉成帝时因用度不足,翟方进“奏请一切增赋,税城郭堧及园田”,张晏注:“一切,权时也。”[24]3423-3424即临时对园征税,说明汉朝曾经在吕后二年(前186年)之后的某一时期取消对园征税。结合上文关于王莽改制的记载来看,西汉至新朝对园征税的法律似乎时兴时废,并不稳定。
目前还没有史料直接记载东汉时期的住宅是否可以经营商业,但此时已经有农村市场,如里市、聚市,其中聚市是一个自然村的市场[26]149-150。作为自然村的“聚”,往往没有按照统一的规划修建住宅。聚的市场恐怕也不会有特定的规划,以及专门管理市场的官吏[26]154-155,周围的住宅从事商业活动当是可能的。
-
张家山汉简中发生于秦王政二年(前245年)的“讲盗牛案”[6]100-102、岳麓秦简中发生于秦王政十八年(前229年)的“识劫

汉初简牍中保存着大量关于田宅买卖的法律规定,如《二年律令·户律》载:“受田宅,予人若卖宅,不得更受。”[6]53这一简文不仅明确显示政府授予编户民的住宅可以卖给他人,还规定一旦卖出,原房主将不再享有政府授予住宅的权利。《二年律令·户律》载:“欲益买宅,不比其宅者,勿许。为吏及宦皇帝,得买舍室。”[6]53如果想在已有住宅的基础上另外购买住宅,那么所买住宅必须与原住宅比邻。之所以规定购买的住宅必须与自己原有住宅相比邻,可能是因为当时五大夫以下爵位的居民按照伍的组织来管理,如果在不同地区拥有房宅,将不便于管理[28]201。该律同时还规定官吏可以在任职的地方购买私宅,明显继承了秦律。《二年律令·户律》云:“代户、贸卖田宅,乡部、田啬夫、吏留弗为定籍,盈一日,罚金各二两。”[6]53如果买卖住宅,基层官吏必须及时登记确认,如延迟一天则罚金二两。综合来看,秦和汉初编户民在法律范围内享有买卖住宅的权利。
汉初以后至东汉,编户民买卖住宅的权利一直保留。如敦煌汉简载:“捐之道丈人前所卖宅耿孝所,贾钱千六百。”[29]79东汉五一广场简牍载:“当王、覆中分仲余财均调。覆得利里宅一区……王得竹遂里宅一区……”[30]188仲在利里、竹遂里各有一处住宅,显示关于住宅买卖的法律已经与西汉初期有所不同,不仅不再要求所买住宅必须与本宅相邻,甚至还可以在不同的里中购买住宅。与汉初相比,住宅买卖的限制变少了。
关于住宅的租赁,岳麓秦简“识劫

文献中还有房主在处分住宅过程中发生纠纷的案例。如汉武帝时期,周阳侯田祖因借轵侯的住宅不还,最后被剥夺侯爵[24]686。田祖的行为实际上构成侵占他人财产罪。关于“借宅不还”在汉代的罪名,沈家本认为是“当归宅不与”[9]1512,程树德则认为是“假借不廉”[10]74;他们均认为这一罪行属《杂律》。根据现存的汉律,目前还无法判断二人关于罪名的观点孰是孰非。按照汉律的原则,田祖的行为会“坐赃为盗”,即统计财产所值金额后,再按照《盗律》处罚。住宅的价值一般比较高,故而判罚也会较重。田祖为减轻惩罚,可能用爵位抵消部分或全部刑罚,因而最终被剥夺侯爵。
关于房屋租赁纠纷的记载,见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载:
永元七年(96年)十一月中,萧迎绥之雒。其月卅日通豢僦绥宅,约四岁直钱五万,交付,率岁直万二千五百。时充送绥,证见通以钱付绥,绥去后,通、良自还归。[31]198
整理者注释:“豢,以利益诱惑。”[31]198因为绥被萧接到洛阳居住,于是住宅空置,通以利益相引诱,租下绥的住宅,并付给绥四年的租金共五万钱。整段文字是某司法文书的一部分,反映了通与绥的房屋租赁纠纷,其中通至少在交易过程中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房屋租赁纠纷在东汉较为常见,如上引“定复僦圣珠宅”“僦赵明宅”均为某房屋租赁纠纷文书的一部分。
由于记载住宅处分纠纷的史料多有残缺,目前无法做进一步的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汉律中已经有了关于处理这类纠纷的律条,而且适用“坐赃为盗”、诚实信用等原则。
-
秦汉时期关于住宅的继承,主要有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两种。秦的法定继承制度尚不清晰,但可从汉初法律中管窥一二。杨振红对《二年律令》中法定继承的律条做了详细研究,她认为汉初法定继承一般遵循爵位减级继承原则,“死者的继承人‘后’有优先继承和选择死者田宅的权利,即所谓‘令其后先择田’。‘后’择田后如有剩余,其他儿子愿分户独立,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爵位占有相应的数额。”[3]总之,正常情况下的住宅法定继承是以立户或代户为前提,以身份(爵位)为标准进行的。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汉代的继承制度出现了变化。据《风俗通义》记载:汉宣帝时,在邴吉担任丞相期间,陈留郡一富家翁突然去世,没有留下遗嘱;其女儿和由妾所生的遗腹子因此产生财产继承纠纷,最后邴吉做出“因以财与儿”的判决[32]587。邴吉判小儿继承全部财产,说明此时的法定继承中已经取消了按照爵位减级继承田宅的原则。该原则与西汉“名田宅制”相配套,其废除时间应在汉文帝时期。
学界曾就秦汉时期是否存在遗嘱继承制度进行热烈讨论,但观点并不统一。姜密曾指出:“要正确认识中国古代遗嘱继承制度的存在及其特点,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当时家庭或家族共财制度的特点,特别是父祖尊长对财产的支配特权。”[33]从男性家长对家产分配的重要作用来看,秦汉时期无疑是存在遗嘱继承制度的,而且该制度还有不断演变、强化的趋势。关于秦的住宅继承,见岳麓秦简中的“识劫



汉初出土文献的记载也显示遗嘱在住宅继承中有重要作用,《二年律令·户律》载:
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参辨劵书之,辄上如户籍。有争者,以券书从事;毋券书,勿听。所分田宅,不为户,得有之,至八月书户,留难先令,弗为券书,罚金一两。[6]54
这里的遗嘱是书面遗嘱,官方的参与显示立书面遗嘱的严肃性。“有争者,以券书从事;毋券书,勿听”的规定,也使书面遗嘱比口头遗嘱更具权威性。
在西汉后期,遗嘱仍然在财产继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据《风俗通义》记载:汉成帝时期,沛郡一富家翁有一女一儿,他在死前召集族人立下遗嘱:“悉以财属女,但遗一剑与儿,年十五,以还付之。”[32]588在封建社会,儿子的法定继承顺序一直排在女儿之前。但根据父亲遗嘱,女儿仍然继承了除剑以外的全部财产,说明在财产继承中遗嘱继承的效力优先于法定继承,同时也显示在遗嘱继承中不再按照爵位减级原则继承财产。同法定继承一样,该原则在遗嘱继承中的废除时间也应在汉文帝时期。
江苏仪征出土的《先令券书》记载了西汉平帝元始五年(5年)朱凌立遗嘱为姊、妹和弟弟分配田地的事情[34]。该券书丰富了我们对汉代书面遗嘱的认识:首先,关于书面遗嘱的要素,主要有时间、地点、事由、公证人、指定继承人、财产的分配办法或份额、见证人。其次,西汉晚期的书面遗嘱,不仅要有乡啬夫亲临,还需要县乡三老、乡佐、“任知者”等。其中“任知者”即保任、见证者,一般由里正、立遗嘱者同伍之人或亲属充当。这些都说明西汉晚期遗嘱继承的相关规定比汉初更加完备、严格。朱凌的遗嘱以“先令券书明白,可以从事”结尾,也显示出此时书面遗嘱的权威性。
综合来看,“识劫

一. 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
二. 住宅不被毁损的权利
三. 在住宅中进行有限商业活动的权利
四. 买卖或租赁住宅的权利
五. 继承住宅的权利
-
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主体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义务。简单来说,义务是法律指令人们必须做或不做某种行为。秦汉时期的法律也规定了与住宅有关的义务,主要有以下几种:
-
所谓“逾制”,就是超过制度规定,逾越等级。关于秦的住宅逾制,主要见于商鞅变法。《商君书·境内篇》载:“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35]119《史记·商君列传》:“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隐》注曰:“谓各随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踰等也。”[36]2230-2231综合这些记载来看,秦的住宅逾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首先,占有的住宅面积或数量超过了自身爵位的受赐标准;其次,住宅的形制超出了自身的身份等级。有其中任何一种情况即构成“逾制罪”。
从《二年律令》的记载来看,汉初对于住宅逾制的规定主要体现在面积或数量方面。当住宅面积或数量超过户主爵位对应的数目时,多余部分会被国家收回。杨振红指出,文帝以后住宅逾制主要是指“装饰的豪华程度和建筑规格”[3]。笔者大致赞同其说,但文帝之后关于住宅面积逾制的规定也并未被彻底放弃。如汉安帝乳母的住宅“合两为一,连里竟街”[15]1764,汉灵帝时朱瑀等人的住宅“连里竟巷”[15]2526,这些都涉及住宅面积逾制。
关于住宅形制逾制的惩罚措施,可通过董贤、侯览等人的事迹了解。董贤父子兄弟并受汉哀帝宠幸,“治第宅,造冢圹,放效无极,不异王制”,他们因存在住宅、墓葬逾制和不敬使者等罪行,最后的处罚中有“没收财物县官”一项[24]3739-3740。汉桓帝时,侯览的住宅“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因为存在住宅、墓葬逾制,督邮张俭“遂破览冢宅,藉没资财”[15]2523。董贤、侯览等人的处罚中皆有没收财物一项,其中便包括住宅,这或许与住宅形制逾制有关。同样是汉桓帝时期,赵忠等人的住宅“拟则宫室”[15]2536,皇甫嵩“乃奏没入之”[15]2304。从这些记载来看,对住宅形制逾制的处罚可能比对面积逾制的处罚更加严厉。总之,无论是住宅面积还是形制逾制,其处罚的内容均至少包括针对住宅的处理。
-
关于“室人”,《法律答问》载:“‘室人’者,一室,尽当坐罪人之谓殹(也)。”[4]141据研究,室人“表示同处一室之所有人,主要指居住在同一室中的有血缘或婚姻关系的亲人,既不包括奴婢及其他家庭依附成员,也不包含析分出去单独立‘室’的成年兄弟。”[37]也就是说,室人是从住宅角度限定的家人。根据《法律答问》的记载可知,室人之间实行连坐制度,要相互监视和揭发,承担连带法律责任。
自商鞅变法后,秦汉时期就在编户民中确立以住宅为基础的什伍连坐制度,同伍之人有相互监视、检举的义务,这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皆有明确记载。相关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兹不赘述。
需要注意的是,秦汉时期的什伍制度除了有相互监视的作用外,也有助于他们相互帮助。如《法律答问》载:“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 [4]116“四邻”,就是指同伍之人。当有贼人入室行凶时,四邻有义务帮助受害者。再如火灾发生时,同伍之人应有救火之义务。
-
秦汉时期没有专门的房产税,但是有“訾税”,即根据财产多寡征收的一种税[38]。前引岳麓秦简“识劫


汉代也存在訾税,如居延汉简载礼忠家“凡訾直十五万”,其中包括住宅的价值一万钱[11]61,这里的“訾直”即与征收訾税有关。除此之外,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也记载有当时多个家庭登记家訾的“簿书”,主要涉及田、宅和奴婢三项。其中关于住宅的有“舍六区,直卌四万三千”“康眇楼舍,质五千”等[40]。这些记载均显示住宅是家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訾税的主要征收对象之一。
《续汉书·百官志》载:“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15]3624说明家訾不仅决定应缴纳税赋的多少,还决定了为役先后的顺序。这一政策当是继承了秦和西汉的做法,如岳麓秦简《徭律》规定:农忙时先征发富有贤人,农闲时征发贫者[21]149。汉初《徭律》云:“发传送,县官车牛不足,令大夫以下有訾(赀)者,以訾(赀)共出车牛;及益,令其毋訾(赀)者与共出牛食、约载具。”[25]248当政府车牛不足时,令大夫以下爵位的有訾者按家訾共同提供车牛;当物资仍有不足需要追加时,令无訾者提供牛食、为车牛配置载具。
-
早在先秦时期,统治者就十分关注民众的住宅状况。如《管子·轻重篇》载:“桓公问管子曰:‘民饥而无食,寒而无衣,应声之正无以给上,室屋漏而不居,墙垣坏而不筑,为之奈何?’”[41]1517齐桓公不仅关注黎民饥寒、赋役问题,还关注民众的住宅是否漏雨、墙体和院墙是否损坏。睡虎地秦简载:
廿五年(前252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〇告将军:叚(假)门逆


律文规定:如果“不治室屋”将被发配从军,在军中的饮食标准低于普通士兵,当攻城时也要承担十分危险的工作。该律文被纳入秦律中,说明秦也实行这一法律。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中也将“院垣

西汉平帝元始五年(5年)曾颁布“月令诏条”规定一年中每个月的活动,其中“孟夏月令”载:“继长增高,毋有坏隋。·谓垣墙□……”[43]5、21在孟夏之月要增修、加固垣墙,防止因大雨而坍塌。“仲冬月令”云:“·毋发室屋。·谓毋发室屋,以顺时气也,尽冬。”[43]7、31在仲冬之月禁止检修房顶,以防止因阳气发散开泄导致疾疫等严重后果。“诏条”具有法律效力,可知此时国家对住宅垣墙、屋顶的修缮时间均有规定。
王莽建新后也延续了要求民众修缮房屋的政策,《汉书·王莽传》载:“是时,长安民闻莽欲都雒阳,不肯缮治室宅,或颇彻之。莽曰:‘……其谨缮修常安之都,勿令坏败。敢有犯者,辄以名闻,请其罪。’”[24]4132根据文意来看,在当时“不肯缮治室宅”是一种不正常行为,长安地区尤为严重。最后王莽只得下诏要求居民及时修缮住宅,以达到“勿令坏败”的目的,若有犯令者则“请其罪”。
《昌言》曰:“柂落不完,垣墙不牢,扫除不净,笞之可也。”[44]412反映东汉对住宅维护、修缮情况的规定,其处罚比秦律轻。立于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四月的《史晨飨孔庙后碑》记载了鲁相史晨及属吏“补宗里中道之周左墙垣坏决,作屋涂色……”[45]24四月即孟夏,合于上引“孟夏月令”的规定,可见东汉关于修缮住宅的规定与西汉末年的月令诏条具有关联性。
-
在宅院种植桑麻瓜果之属是先秦时期的一种普遍做法,如《孟子·尽心章句上》云:“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46]2768从一些文献的记载来看,先秦时期在宅院种植桑麻瓜果也是一项强制性规定。《周礼·地官司徒·载师》载:“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郑司农云:“宅不毛者,谓不树桑麻也。”[7]726里布为住宅居住者因不在院中种桑麻而要额外缴纳的税。
秦汉时期在宅院种植桑麻瓜果的记载也常见于文献,如睡虎地秦简有“不可伐室中

有趣的是睡虎地秦简《封诊式·封守》中有“门桑十木”的记载,桑树被种在院门外[4]149;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的第三处住宅院墙外侧墙根下也种有桑树和榆树[47]65。但是《二年律令·田律》显示,里中一般只有里巷作为道路供人行走,居民不得侵占里巷(见下文)。在院门外种树,似与这一律文有矛盾。合理的解释是,院外一定距离内的土地仍属于住宅的范围,并不属于里巷。这一院外附属土地一般被称作“壖”,如汉文帝时晁错曾因侵占“太上皇庙堧垣”而犯罪,服虔注:“宫外垣余地也。”[24]2102从三杨庄住宅遗迹来看,一般住宅的壖地面积有限,与院墙的距离十分近。
院外之所以有“壖”这一附属土地,其原因就在于相邻权。所谓相邻权,是指“在相邻关系中,一方在使用或经营自己的不动产时,负有不得妨碍对方合理行使权利的义务,同时也有权要求对方不妨碍和侵犯自己权利的合理行使。”[48]137相邻关系的种类很多,如相邻用水、排水关系,相邻通行、通风、采光关系等。因此“壖”的出现,实际上是为了保障相邻权。古罗马的法律中就有关于相邻权的明确规定,《十二铜表法》载:“如〔设置〕围墙,则必须〔从近邻的地区起〕留出空地一呎,如果是住所,则留出二呎。”[49]28这里留出的一呎或二呎空地,就是我国传世文献中的“壖”。虽然目前在秦汉法律中还找不到像《十二铜表法》那么明确的规定,但是“壖”的普遍出现,说明当时很可能已经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相邻权。
-
上引商鞅变法有“弃灰于道者黥”的规定,“弃灰于道”本身就有向道路倾倒垃圾的含义,只是这种行为具有引起火灾的风险,故处罚较重。龙岗秦简载:“侵食道、千(阡)、

《二年律令·田律》简245载:“盗侵巷术、谷巷、树巷及貇(垦)食之,罚金二两。”注释云:“巷,《说文》:‘里中道’。”[6]42侵占里巷或在里巷上开垦种植则罚金二两。单就所罚黄金的重量来看,汉初与秦朝大致相当,体现出秦汉法律的延续性。但若从黄金与钱的比值来看,汉初金价仅为每两315钱[6]138,罚金二两共630钱,尚不及秦朝的一半。
若将《二年律令·田律》简245的记载与唐律比较,可以看出该律的一些特点。《唐律疏议·杂律》载:
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虽种植无所妨废者,不坐。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20]1822
对比可知,汉代的法律规定比较笼统,无论是侵占或开垦里巷,无论其行为是否有所“妨废”,均罚金二两;唐代则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规定。这种笼统的规定,也体现出汉代对禁止侵占或开垦里巷的坚决态度。其原因可能与当时的禁忌观念有关,银雀山汉简云:“无故而田其术巷及廷,是胃(谓)尽德,五

《说文》“水部”载:“



从前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先秦秦汉时期的院墙一般称做“垣”“墙”或“垣墙”。同时,秦汉时期关于住宅的诸多法律中,与院墙相关的内容颇多,显示出院墙对于住宅的特殊重要性。从文献记载来看,秦汉时期住宅院墙的功能主要有两点:一是作为住宅的防御设施,《释名》云:“垣,援也,人所依阻以为援卫也。”[52]274可见院墙是保护住宅居住者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一道防线;二是作为住宅的界线,《新序》载:“国有封疆,犹家之有垣墙”[53]349。院墙不仅是住宅的物理界线,更是基于住宅所产生的法律关系的界线,任何越过院墙的行为都有可能违法,可以说院墙是判定行为人是否违法的重要参考物。
-
从张家山汉简和岳麓秦简(肆)先后公布的《亡律》来看,犯罪主体既包括不同身份的逃亡者,也包括为逃亡者提供隐藏处所等便利的人;第二类主体的行为在秦汉时期一般称做“舍”或“匿”。
秦《亡律》中关于窝藏罪的法律被称做“舍匿罪人律”,见岳麓秦简《亡律》简006[21]40。关于此处“罪人”的含义,岳麓秦简《亡律》简075载:“取罪人、群亡人以为庸,智(知)其请(情),为匿之;不智(知)其请(情),取过五日以上,以舍罪人律论之。”[21]63可见“舍匿罪人律”中的“罪人”包括犯罪之后逃亡的人(“罪人亡”),以及没有犯罪而因某种原因逃亡的人(“亡人”)。张家山汉简中有“匿罪人律”,见《二年律令·亡律》:“取(娶)人妻及亡人以为妻,及为亡人妻,取(娶)及所取(娶),为谋(媒)者,智(知)其请(情),皆黥以为城旦舂。其真罪重,以匿罪人律论。弗智(知)者不〼。”[6]31“匿罪人律”的名称明显继承秦律。无论是“舍匿罪人”还是“匿罪人”,都包括将逃亡者藏匿在住宅中的犯罪。
关于“舍匿”,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解释为“匿于家中”[6]31。窝藏罪犯的场所当然可以是在家中,但显然也可以是其他地点,故整理小组的解释并不周全。从上引岳麓秦简《亡律》简075可知,“舍”指的是不知其为逃亡者而收留;“匿”指的是知道其为逃亡者而故意收留[54]。现今法律中,仅将第二种情况定义为窝藏罪[55]390,可见秦汉窝藏罪的适用范围更加广泛。
汉初还新增了“舍亡人律”,见于《二年律令·亡律》:“取亡罪人为庸,不智(知)其亡,以舍亡人律论之。”[6]31从简文内容上看,当收留者不知道被收留者是逃亡的罪犯时,也适用“舍亡人律”。即“舍亡人律”适用的情形有两种:一是因不知情而收留其他身份的逃亡者,二是因不知情而收留逃亡的罪犯。可见,秦代因不知情而收留逃亡罪犯的罪(“舍罪人”),在汉初时被合并到了“舍亡人”中。结合前文分析可知,秦代的“舍匿罪人律”到汉初至少已经分解为“匿罪人律”和“舍亡人律”。
据张伯元研究,《二年律令》中关于窝藏罪的律文沿用的时间很长,“约有将近百年”[56]117。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汉代关于窝藏罪的处罚出现了两大变化:
首先,自汉武帝时期开始加重对窝藏罪主犯的处罚。据《后汉书》载,汉武帝时“重首匿之科,著知从之律,以破朋党,以惩隐匿。”[15]1166“首匿”的处罚到底加重到说明程度呢,其实可以通过与以往法律的对比得出。《二年律令·亡律》载:“匿罪人,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与同罪。”[6]31汉武帝时期对窝藏罪的处罚应重于这一处罚原则。西汉后期,鲍宣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请逃亡的死刑犯辛兴吃了一顿饭,就触犯死罪被迫自杀[24]3094。可见对于窝藏重罪的人,一律与被藏匿者同罪。东汉安帝时期“盗贼连发,攻亭劫掠,多所伤杀”,陈忠认为应该严惩逃亡的盗贼和窝藏犯,并引用了汉律的相关规定:“故亡逃之科,宪令所急,至于通行饮食,罪致大辟。”[15]1558-1559这里针对的主要是犯下死罪的盗贼,只要为他们提供饮食或逃亡便利,即“与之同罪”。总之,汉武帝改革后的窝藏罪,很可能是窝藏者皆与被藏匿者同罪论处。
其次,自汉宣帝时期开始在窝藏罪中实行亲属相隐原则。地节四年(前66年)汉宣帝下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24]251这是关于窝藏罪的又一重大变化。
一. 住宅不得逾制的义务
二. 监视、帮助室人或伍人的义务
三. 承担与住宅有关的税和徭役的义务
四. 维护、修缮住宅的义务
五. 宅院必须种植桑麻瓜果之属的义务
六. 不得向院外倾倒垃圾或侵占里巷的义务
七. 不得舍匿罪人、亡人的义务
-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与住宅相关的权利主要有:一、秦和汉初编户民有从国家获得住宅的权利;二、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三、住宅不被毁损的权利;四、在住宅中进行有限商业活动的权利;五、买卖或租赁住宅的权利;六、继承住宅的权利。与住宅相关的义务主要有:一、住宅不得逾制的义务;二、监视、帮助室人或伍人的义务;三、承担与住宅有关的税和徭役的义务;四、维护、修缮住宅的义务;五、宅院必须种植桑麻瓜果之属的义务;六、不得向院外倾倒垃圾或侵占里巷的义务;七、不得舍匿罪人或亡人的义务。
除第一项权利在汉文帝时期随着“名田宅制”的名存实亡而消失外,其他五项权利和七项义务在秦汉时期一直存在。这些不仅说明住宅法律规定的涵盖范围比较广,也说明其具有较强的延续性。但是这些法律规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总体上在朝着更加完备、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比如住宅毁损后的定损方式、住宅遗嘱继承的程序等。法律中关于要求居住者必须维护、修缮住宅,必须在院子里种植桑麻瓜果等规定,也体现出政府对于编户民生活的强力干预。由此可以归纳出秦汉住宅法律规定的四个特点,即涵盖范围广、延续性强、日趋完备合理和干预力度大。
在秦汉住宅法律规定中,与院墙有关的内容比较多,显示出院墙在相关法律中的特殊作用。任何越过院墙的行为都有可能触犯法律,可以说院墙是秦汉法律判定行为人是否违法的重要参照物。
通过对秦汉住宅法律文献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秦汉法律和基层治理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住宅与田制密切相关。加大对住宅方面的研究,也可以为目前争论较多的秦汉土地制度问题提供新的思路或启示。比如学界主张秦和汉初实行土地国有制的观点,其依据之一就是政府对编户民的生产、生活都具有很强的监督机制和强制性,并常以行政、经济手段加以干预[57]39-41。但从住宅方面来看,自汉文帝废止“名田宅制”后,政府仍然对编户民的住宅采取了类似的政策。按照这一思路,汉初之后的住宅似乎也属于国家,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大符合。故而土地国有制与政府对编户民的生产、生活的强力介入并不具有必然联系。政府出于传统、道义、责任或者某种实际需要的考虑,都有可能表现出对于土地、住宅等事务的“过分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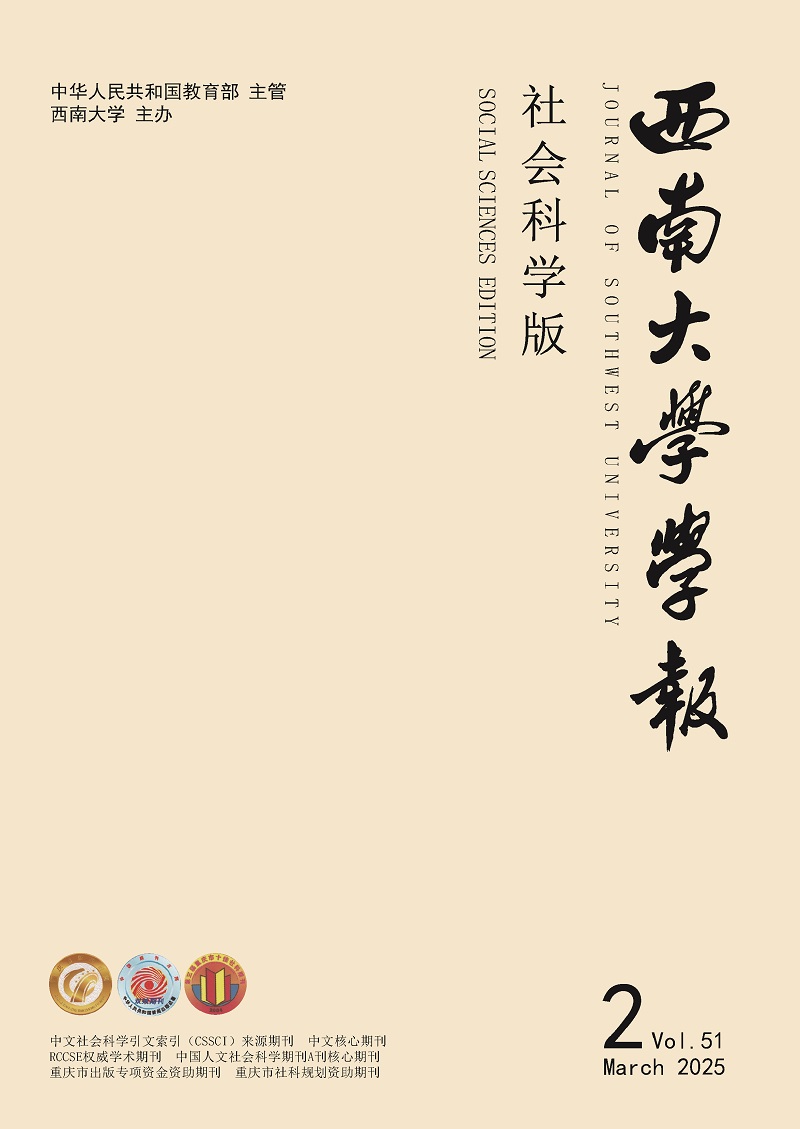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