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8年5月,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日本第三次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国民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令日本对华贸易遭受“最深”之打击[1]。国民党一方面为了给激愤的民众寻找情绪发泄出口,另一方面则希望利用抵制日货运动在对日外交中占据主动,故有条件地支持了这次运动。面对这种形势,日本外务省根据在华外交官搜集的有关情报,利用与国民政府进行济案交涉之机,谋求应对措施,旨在瓦解抵制日货运动。最终,日方以取缔抵货运动为重要条件与国民政府达成《济案协定》,后又利用改订商约谈判逼迫国民政府加速取缔运动,不久抵制日货运动便被镇压下去。
学界既往的研究成果注重考察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过程、参与力量、社会影响等[2-8],尚未见有关日本外务省如何应对济案后抵制日货运动的专题研究,而日方的应对措施恰是导致该运动被取缔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日本外务省官员的认识和行动为研究重点,利用日本外交档案、当事人回忆录与近代中日报刊等资料,探讨外务省因应济案后抵制日货运动的主要对策及其影响。
HTML
-
1928年5月3日,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此时中国爱国民众情绪激愤,纷纷走上街头,开展反日抵货斗争。5月6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中常会,商讨解决济南惨案的方针。会议通过了“‘五三惨案'应付方案”,正式提出通过支持抵制日货以“使日本经济力无法再垄断中国之市场”,并视之为“今日以及将来之要着”[9]104。会议同时还议定了“对日经济绝交办法大要”,规定由国民党“指导各种民众团体”,并“主持关于对日经济绝交一切事宜”[9]111。如是,在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下,抵制日货组织在全国各地相继建立,运动开始蓬勃发展。
此时日本朝野对中国爆发的抵制日货运动尚不以为意。因为自1908年由“二辰丸事件”中国掀起第一次全国性抵制日货运动以来,到1928年全国共掀起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7次,然而这些运动多系民众自发,持续时间短,打击效果有限,曾被批评为“局部的、表面的无组织之排斥日货”[10],甚至被嘲讽为“五分钟抵制热”[11],加之国民党内部始终意见不一,如张群就甚为担心“国民排日运动妨害北伐且必授人口实”[12]。故日本朝野对济案后的抵制日货普遍轻视,驻华日本外交官多认为此次抵货运动亦不会持久。
5月15日,日本驻上海代理商务参事官、副领事加藤日吉向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详细报告并分析了抵制日货运动的情势。加藤认为,日货多为生活必需品,抵制“绝非易事”,加之抵制最严重的6月日货进出口额也仅损失2340万日元,对日贸易打击“非常轻微”;他还根据“以往经验”断定抵制日货将“虎头蛇尾”,至多到八、九月便“偃旗息鼓”。同时,加藤也向田中提出了各种应对办法,譬如保护日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分化中国商人,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从金融、货运、仓储、保险等环节转嫁经济损失等等[13]840-848。此外,又有多位日本政商界人士频繁向媒体放话,宣传抵制日货运动“不足为惧”[14],试图引导舆论风向[15],提振日货交易信心。
然而加藤等人对抵制日货的判断实则大大低估了该运动的影响。济南惨案发生后不久,在国民党中央支持下,以上海、南京、南昌、汉口、天津等大城市为中心,各地先后成立了反对日军暴行委员会(即“反日会”)、外交后援会、经济绝交委员会等反日团体,迅速开展了有组织的抵制活动。[16]其效果非常明显,不久就出现了厦门等地“到港日货无人卸运”、广东日货交易“渐次减少”、长沙日商安全“颇受威胁”等现象[13]849-852。
由于国民党的组织、反日团体的参与,济案后的抵制日货运动很快呈现扩大趋势,明显不再是“五分钟热度”,这使得日本驻华外交官也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7月21日,即全国反日会召开第一次大会当天,加藤日吉一改往日的轻蔑态度,向田中坦陈抵货形势已不受控制:“因反日会的日货检查日趋严格,我国化工产品、纺织、精糖、肥皂、皮革、玻璃、印刷等贸易遭遇严重打击⋯⋯抵制日货运动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13]857-8587月3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致电田中,提出要根据此次抵货运动的“持续性”来制定新对策:“反日运动如此持续,定会有众多日商破产,万不能轻视⋯⋯只有使国府解散排日团体,或强行禁止抵制,否则难以中止。”[13]860-861
与此同时,其他地区的日本驻华使节也意识到抵制日货运动有持续发展倾向。不仅沿海城市和重要商埠,抵制日货运动业已扩大到中国内陆边陲。7月25日,日本驻云南代理领事中野勇吉致电田中,称云南反日会“有组织”地抵制日货令当地日货贸易形势严峻[13]858-859;日本驻汉口代理总领事原田忠一郎向田中报告运动有“相当持续性、组织性”,他还发现反日会得到公安局的“大力支持”[13]863-865。8月30日,原田在电文中忧心忡忡地说,此次抵货运动情势与以往全然不同,组织性之强将使日货市场遭受“沉重打击”[13]867-868。
抵制日货运动给各地日商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日益凸显。以汕头为例,经过3个月的抵制日货后,汕头日商的生意业已陷入“困境”,日货查扣禁运、货物囤积、不履行合同等情况比比皆是[13]865-867。反日甚为积极的上海、天津等地更可想而知,日商所受经济打击与加藤在5月的估计已大相径庭,驻上海领事馆武官清水芳次郎此时向田中报告日商大受打击,“已有两家行将倒闭”,并预计倒闭将会“络绎不绝”[13]868-870。
由此可见,抵制日货运动形势发展之迅猛、效果之明显已大大出乎日方预料。驻华官员对抵制日货的态度变化,直接影响着外务省对抵制日货运动的应对策略。从1928年7月起,外务省与国民政府围绕如何解决济南惨案展开谈判,通过济案外交交涉迫使国民政府取缔抵制日货亦成为外务省的重要目标。
-
在抵制日货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中日济案交涉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如上文所述,最初日本当局对抵制日货运动并不在意,但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外务省不得不开始重视抵制日货的影响,并意图利用济案交涉之机迫使国民政府取缔运动。然此时国民政府亦将其视作济案交涉的重要筹码,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就抵制日货运动进行了多次外交交锋。
1928年7月10日,田中义一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了《解决济南事件的条件》,是为日方济案谈判早期的指导方针。在上述“条件”中,田中没有对抵制日货运动予以太多关注,仅笼统提及“排日排外宣传一律禁止”[13]458-460。这与后期运动壮大后,日本在谈判中对于取缔抵货运动的细节都斤斤计较之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7月19日,日方济案谈判代表矢田七太郎与国民政府外长王正廷举行了第一次会谈。矢田在会谈中并未提及取缔抵制日货运动问题,只提出了军部坚持把济案责任推给国民政府、拒不道歉的“解决方案”,这令蒋介石大为光火。蒋随即通电国民党各省党部“一致援助国府”“当以完全之经济绝交对抗之”[17],抵制日货因而得到了更大支持。
8月,在华日商由于生意受损开始向日政府施压,加之抵货运动蓬勃发展,日方对其态度已悄然生变。此时,济案谈判正陷入停滞,田中开始指示驻华外交官向中方官员抗议反日抵货运动。驻南京领事冈本一策接受命令后,随即向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常务委员李烈钧等人抗议,要求国民政府发“正式公文”取缔运动。李烈钧以政府取缔反日运动的方针“没有变化”、反日会“只处罚中国商人”等理由辩解。9月8日,冈本在田中的指示下再次向李烈钧抗议,李仍持旧见,并称民众不满济案交涉使摩擦“难免发生”[13]871-872,以退为进催逼日方让步。
此时,日本政要业已观察到,国民政府正通过抵制日货运动这一“一流外交手段”不断推进济案交涉朝积极方向发展[18]。对国府更为有利的是,通过前期的厉行抵货,日本对华贸易损失日增,田中内阁正面临来自本国商人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一如上海反日会会长陈德徵一直主张的,通过开展“对日经济绝交”,依靠日本商界“纠正他们政府的谬举”[19]之效果已初步显现。9月11日,日本本土两大重要商业团体——日华实业协会与日华经济协会——共同向田中义一发出联名信施压[20]。田中的政治对手、前外相币原喜重郎也借抵货一事猛烈攻击田中内阁[21],号召更迭政权以促“排日停止”[22],所以田中已意识到势必要尽快解决抵制日货。于是,在后续的济案谈判中,抵制日货运动转而成为中日交涉的一个重点。
1928年10月19日,中日济案交涉重开,矢田七太郎与王正廷再行会晤。鉴于抵制日货运动形势逼人,矢田将取缔所谓“排日宣传及暴行”提升为日本从山东撤军的条件之一。对此,王则表示反日运动在日本撤兵后将“自然消解”,国民政府会负责监督并取缔[23]。次日,矢田再次强调国民政府应明确保证取缔“反日宣传和反日行为”,王正廷表态“国民政府将监督执行”。[24]前后两日的会谈中,王正廷对矢田提出的有关取缔抵货的要求都许以回应,双方将“取缔抵制日货运动”作为济案撤军条件基本达成一致。通过几次会谈,矢田与王正廷就解决济案其他事项的意见也趋于统一,济案离“解决”似乎为期不远。
10月23日,矢田与王正廷开始就具体协议文本进行讨论,但围绕取缔抵制日货运动的方式,双方分歧凸显。矢田得寸进尺地要求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向各地方政府及地方党部发出取缔抵制日货运动的公开命令,并以“公函”形式发送日方。对此,国民政府担忧激起民众反抗,不能接受。王正廷推说取缔抵货属中央党部工作范畴,政府不能发令,只能劝告,并担保“政府会负起责任”[25]。会后,矢田将与王正廷达成一致的若干内容上报田中,田中阅后认为矢田在交涉中缺乏“慎重考量”,严厉批评了矢田[13]505-506。因此,中日济案交涉再次陷入僵局,在当时本要被国民党取缔的抵制日货运动从而得到一线生机。
在矢田与王正廷谈判之际,外务省继续训令各驻华使节密切关注抵货运动,并采取适当措施。10月17日,田中指示驻南京领事冈本一策向王正廷和蒋介石抗议反日运动。冈本受命后,即向王抗议称国民政府“毫无取缔诚意”。冈本进一步警告称,抵制日货会使国民政府丧失对外信用,要求国民政府“厉行取缔”。对此,王正廷则强调“事出有因”,称两国关系改善才是“根本策略”。22日,冈本见蒋介石后亦抗议,并挑拨称共产党与反日会将逼蒋下台[13]878-880,企图以此刺激蒋介石取缔抵货运动。
济案交涉停摆后,国民政府计划继续依靠抵制日货运动在外交上抢占优势。在官方的支持下,各地反日会更积极开展活动以为“外交之武器”,使得日货生意受损日益严重。10月下旬,日资汉口泰安纺织厂被反日会封禁,引发了田中关切。他直接命令驻汉口总领事桑岛主计迅速处置:“要尽力阻止该厂商品运输售卖被妨害,今后本省将与你协同处理。”[13]88111月9日和15日,田中又相继接到济南、开封、郑州有关抵制日货更趋激烈的报告[13]884-886。驻济南领事西田耕一强调了国民党对运动的支持:“抵货日趋严峻,反日会已经将齐河、栾口、崮山等交通要道全部封锁,⋯⋯综合种种情报表明,国民党中央想通过抵货对解决济南事件进行急速有利的诱导。”[13]884-885桑岛认为“反日会背后有中央党部强有力的支持、有各地方党部的指挥。随着交涉日益深入,一旦中方受挫便设法推动反日运动”[13]895-896。驻杭州总领事米内山庸夫与西田、桑岛意见相近,认为杭州地区反日活动是对济南惨案的“报复”,提请外务省“注意”[13]897-898。
虽然驻华外交官们再三提醒田中,称解决济案才是根绝抵制日货运动的办法,但是田中仍然态度强硬,反而电令矢田短期内“不必强求”解决济案,以待中方“反省”[13]527-528。然而国民党也针锋相对地发动民众对抗,甚至一向对抵制不公开表态的蒋介石也借国货运动发声:“国民政府要提倡国货,要振兴实业,要挽回利权,使外国货在中国没有销路,大家都用国货,那么帝国主义就可以不打自倒”[26]。弦外之音,不言自明。
11月29日,汉口反日会向王正廷发出一封公开信,信中称“若不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日本签订平等条约,绝不停止反日”[13]891-892,充分表明反日会已经不单要求解决济案,连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成其努力目标。田中内阁则一味坚持强硬主张,其执政压力颇大:济案与改订新约交涉悬而未决,加之皇姑屯事件余波未平,日本各界对田中的对华政策愈加不满;日本对华贸易亦因持续近半年的抵制日货颇受打击,商界向政府陈情却不见措施奏效,导致商人们对田中内阁怨声载道[13]892-893。恰在此时,福州反日会处决了买卖日货的中国商人邹行贵,这更令日货商人噤若寒蝉,交易“几近断绝”[13]899。一时间,抵制日货运动的气势达到高峰,田中内阁内外压力与日俱增,只能重新考量抵制日货的解决之策并推进济案交涉。
1928年12月20日,外务省商务官首藤安人受命提交了一份应对抵货运动的建议书,指出外务省应努力“促进关系业者团结”“协调资金援助日商”“加大舆论宣传”“提起严重抗议”,并称国民政府“若不展示十分诚意则可随时中断济案交涉”[27]。1929年1月19日,田中派首藤到中国调查抵制日货运动情况。经过在上海、汉口等地的走访调查后,首藤认为“反日运动是国民党自身的运动,中央与地方正对其加以利用”“抗议也不会有效果”[28]538。
首藤报告为外务省应对抵货运动提供了所谓的“重要参考”。此时,恰逢济案交涉再次重启,经历约两月的停滞后,日方谈判代表换成了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在谈判开始前,日本外务省于16日交给芳泽新的“(济南)悬案交涉方针”,明确规定将交涉解决“国民党党部指导下的反日运动”等问题[28]417-422。
1月25日,王正廷与芳泽在南京开始新的谈判。谈判中,芳泽仍然坚持日方以往立场,要求国民政府声明取缔反日运动。王正廷则称,重复声明没有意义,对反日运动已经极力采取取缔措施,且会伴随济案解决而自然消解[28]427-430。1月26日的第二次谈判中,芳泽要求王发布保护外国人财产的命令并通报日本[28]431-434,王正廷居然没有表示异议。在第三次谈判中,王提出反日抵货的“病灶”在于日本驻军济南,称一旦撤兵“病即自愈”,且关系会更加“亲善”[28]439-442。纵观以上三次谈判,不难发现国民党对抵货运动的态度已悄然变化,王正廷不再围绕取缔抵制日货运动的方式、细节与日方展开较量。
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究其原因在于此时抵货运动自身发生变化,最重要的是运动有脱离国民党中央掌控之势。如某些地方党部借反日抵货与国民党中央对抗,反日会领导权多落入改组派之手,“基本不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支配”[29],这直接导致蒋介石对运动由有限支持变为高度戒备。加之抵制日货运动终究只是国民党在济案交涉中向日方施压的一枚筹码,而此时双方已在撤军等焦点问题上有了一致意向,所以此时国民党正好通过抛弃抵制日货运动,以换取日方在济案交涉中做出让步。
于是,在济案交涉的关键时刻,出现了这样一幅吊诡的图景:曾作为“政府后盾”的民众抵货运动遭到政府迫不及待地打压,反日团体亦被迫更名改组。2月15日,国民党将反日会改组为“中国国民救国会”,后又以反日工作“流弊日滋”“迹近苛扰”为由令军警严加镇压[30]。国民党此类“昏招”不一而足,无异于告知日方其无意再支持运动。在后续的济案交涉中,王正廷对日方取缔抵货要求几乎照单全收,还保证会“负责任”地取缔抵制日货运动[28]481-482,其立场倒退殊为明显。
1929年3月28日,中日正式签署《济案协定》,国民党以妥协退让换取了济案的所谓“解决”。《济案协定》中包含了日本要求取缔抵制日货的“会议录”,外长王正廷承诺取缔抵制日货运动之条款赫然在列:“此事本部长当以诚意,负责设法并商中央党部密令各地党部劝导,以期即行终熄排日排货之运动。”[31]在国民政府承诺取缔抵货运动的消息传回日本后,连一直对田中政策颇为不满的日本商界都赞誉有加[32],田中内阁的压力也随之纾解。
由上观之,日本外务省将取缔抵制日货运动作为条件与中方达成《济案协定》的策略,使其名义上实现了“解决济案”与瓦解抵制日货运动的双重外交目标,同时也使田中内阁暂时摆脱了执政危机。而反观国民政府,因忌惮民众而主动打压和取缔抵货的行为,不仅令其在外交上丧失筹码,更背上骂名。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反日因日本侵略而起,自应由日本放弃侵略而消弭,而在《济案协定》中,取缔反日运动却成了国民政府的义务⋯⋯取缔反日、‘排日'成为日本理直气壮的要求,国民政府则充当了反日运动的镇压者这种不光彩的角色。”[33]国民政府这一外交妥协不禁令人扼腕!
-
由于已将取缔抵制日货运动白纸黑字记入《济案协定》,故日本各界迫切期待国民政府履行所谓“承诺”镇压抵制日货运动。然而,该运动却并未如日本所望迅速消亡。由于爱国民众对国民政府在济案上的妥协外交不满,加之多地反日会拒不听从国民党中央指令,全国反日会甚至公开警告王正廷并表示“誓不承认政府以妥协外交的手段,向日方所订的济案协定”[34],所以抵制日货运动反有持续深入的趋势。
日本驻华外交官对抵制日货运动可能深化的态势并非毫无察觉。早在国民党着手打压抵制日货运动之时,新任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就曾预言:“改为救国会后,反日会将承担取缔日货和提倡国货两种职能,有组织的抵制日货运动仍会持续。”[28]546在《济案协定》签订当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村上义温也曾致电田中,对济案“解决”后香港地区的抵货缓和心存疑虑,认为协议内容已激怒港人,抵制日货运动的发展势头“不容乐观”[28]550。
抵制日货运动的反弹趋势很快凸显。北平、天津、河北、上海等地的反日组织相继开展更加严格的抵货活动。4月1日,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堀义贵向外务省反映,反日检查队查处日货力度正在加大,形势“毫无缓和”[28]550-551。日本驻天津代理总领事田代重德同样报告天津抵制日货运动愈发激扬[28]551-553。4月8日,重光葵也报称已更名为“国民救国会”的反日会正大力宣传“救国即反日,反日即救国”,致日货商人“踌躇观望”[28]559-561。
面对各地抵制日货运动更趋激烈的状况,外务省不断催促王正廷履行“承诺”。芳泽指责王正廷“阻止排日和解散反日会”不力,要求国民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措施[28]553-554。4月5日,冈本一策再向王正廷抗议,对国民党中央的命令“是否彻底传达”表示质疑。对此,王正廷解释称抵货运动“涉及面广,参与者众,事态复杂”,要日本“暂时忍耐”[28]554-556。
此时国民党取缔抵制日货运动的态度确未生变,但如王所言,此时欲即刻取缔抵货运动“尚有困难”也是事实。其一,民众对济案草草“解决”十分不满,当时正值群情激愤时刻,政府一味打压会酿成“事端”;其二,前已述及,反日会与地方党部、中央党部关系盘根错节,除上海等少数反日会外,多数反日会的领导权已落入国民党改组派或地方实力派之手,不受国民党中央约束。面临此种情势,外务省在严密监控反日抵货运动同时,又主动采取了若干应对举措。
第一,要求国民政府公开发布取缔抵制日货运动的命令。从4月开始,外务省以“已签署《济案协定》”为由多次要求国民政府颁布公开的取缔命令。日本外交官多次要求中方发布取缔命令,且要求日益严苛,连以往发布的密令都被要求一一公开[28]562-580。而国民政府因顾忌成为“众矢之的”[28]571,只能代之以发布所谓的《保障人权令》,[35]3346以“保障人权”之名,行取缔反日抵货运动之实。
第二,借撤军要挟国民政府取缔抵制日货运动。众所周知,解决济案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日本撤军问题。虽然双方签订协定,但“何时撤、如何撤、撤给谁”事实上仍由日本主导。1929年3月,蒋桂大战爆发,蒋介石极度担心日本撤军后山东地区落入地方实力派之手,所以希望日本待战事稳定后再将山东移交,这就使主动权再度交还到日本手中。4月中旬,王正廷向芳泽谦吉提出延缓撤兵时,芳泽借抵货问题惺惺作态:“目前抵制日货以日本撤兵为目标,此时延迟撤兵不是火上浇油吗?”王只好委曲求全,表态称政府将“加大取缔力度”[28]564-566。
第三,利用舆论武器攻讦抵制日货。抵货运动开始后,外务省始终与日媒“积极配合”,注重搜集国内外舆论情报[36],力图将抵货运动型塑成一场“非法运动”[37]。济案发生后,日当局制定了周密的“宣传实施方案”,其中详细规定如何利用舆论武器颠倒黑白,以污蔑反日抵货运动[38]771-778。济案议定后,日方又觉占得名义上的所谓“法理优势”,更加强了对抵货运动的舆论攻势。如1929年4月,当汉口反日组织罢工委员会正副会长曾觉先、王锦霞因组织反日被国民政府收押后,田中立即指示桑岛,要求以此事为线索搜集可资宣传反日会非法暴力之“证据”[39]。日方处心积虑地利用传媒营造抵制日货运动的负面形象并加以攻讦之对策,由此可见一斑。
第四,笼络列强共同向国民政府施压。4月9日,各国领事团会议在上海召开,重光葵抓住机会多方游说,试图促成一份反对抵货运动的联合协议。重光向田中报告,各国领事因本国日货交易被反日会阻滞而不满,故皆赞同以领事团名义向国民政府发电抗议[28]566。但事实上,因反日运动勃兴,英美等列强的货物反而取代了日货在华市场份额,所以日方如意算盘注定不会成功。5月2日,堀义贵就致电田中,坦陈难以出台联合协议:“领事团内部意见纷繁,加之1925年抵制英货运动时未有一致行动先例,此次也很困难;另,即使出台一致取缔要求,有无效果也值得怀疑”[28]581,日方欲联络列强向国民政府施压未能成事。
第五,安抚日本侨民不予中方以所谓“反日借口”。济案议定后,抵制日货运动未如日侨日商所愿迅速消弭,日本商民多认为是国民政府故意拖沓所致,故常向外务省控诉中国不履行承诺[28]589-590,甚至叫嚣组织武装自卫团[40]。外务省担忧日本商民过分刺激中国反使运动反弹,务求“不生事端免成反日口实”,遂加强了对商民的安抚,使其“渐渐缓和”[28]574-576,以避免刺激中国民众再次掀起反日高潮。
以上各种应对措施虽收效不一,但总体而言确使“排日货渐渐好转”[41]。此时,日方对国民党取缔抵货运动的力度非常不满,于是,国民政府标榜的“革命外交”最大目标——改订商约谈判——就成为外务省逼迫其取缔抵货运动的又一关键抓手。
1929年5月28日,老谋深算的堀义贵向田中献计:“在改订商约交涉中应该言明,当对方使用抵制日货运动为武器时就立即终止谈判。”[28]595-597几天后,重光葵也向田中表达类似意见:“我方应要求对方交出取缔抵制日货的实绩后再考虑改订商约。”[28]598此后,田中明确了将取缔抵制日货运动与改订新约谈判挂钩的方针。6月6日,田中向重光葵和芳泽谦吉发电:“南京曾承诺改订商约前将完全取缔抵制日货,故我方已以绝对诚意准备改订商约谈判,但未料中方在济南事件解决后不履行取缔约定,导致协商推迟。”田中尔后训令重光和芳泽,令他们将改订商约前“必先取缔反日”的要求传达给中方[28]600-601。
收令当日,芳泽即与王正廷会面,称如不显示“充分诚意”,则“不必期待”进行改订商约谈判。芳泽以天津、汉口、福州、厦门、苏州、汕头等地的反日情况仍然激烈为由,要求王采取“更彻底”的取缔措施[28]601-602。6月8日,芳泽再向田中进言,认为鉴于英国已开始与中国协商改订通商条约,因此已经无法完全漠视国民政府的改订要求,应以取缔抵货为借口等待机会中止谈判:“今日先埋下中止谈判之伏笔。不论今后反日如何发展、国民党是否拿出诚意,皆比一纸抗议更为有效。”[28]602-6046月13日,芳泽再向田中建议:“一旦发现有抵制日货发生,我方应断然要求对其取缔。如果对方不应,我方正可即时拒绝改订商约谈判。”[28]605-606除芳泽外,冈本一策等人也多次约见王正廷、戴季陶等,以停止商约谈判要挟中方取缔抵货运动。在与王正廷谈判中,冈本表现得咄咄逼人,直言王主张的“担忧严厉镇压反日造成运动反弹”是老调重弹,讥讽王“毫无权威”。他诘问称,国民党中央从不发布公开的取缔命令,实际是不是在“支持排日运动”?[28]606-607
7月8日,外务省亚洲局第一课出台了一份详细的《抵制日货运动的应对策》,其中指出:“中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以及抵制日货运动对改订商约造成阻滞一事断难容忍。⋯⋯对方不履行义务就应拒绝改订商约谈判”,并从国际法角度详细阐述了如何将拒绝谈判的责任归咎于中国[42]。该“应对策”将解决抵货运动的焦点锁定在改订商约一事上,充分表明了此时外务省应对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思路。
在日本威胁中止改订商约谈判的压力下,面对抵货运动可能失控的风险,国民政府加大了对抵制日货运动的镇压力度。7月10日,蒋介石直言反日会只是国民外交“临时应付之手段”,称开展抵制日货以来,国家司法行政权已受“相当之影响”,并警告称“鲁莽从事,中央是不答应的”[43]。蒋的表态实则已经宣告抵制日货运动将被取缔的命运。到7月下旬,国民政府取缔抵货运动已不再遮遮掩掩,开始发布公开禁令[44]。8月上旬起,国民政府又严禁反日团体开展抵制日货行动[45]。于是,在日本外务省的步步紧逼和国民政府的直接打压下,济案后轰轰烈烈的抵货爱国运动不得不偃旗息鼓。
-
济南惨案后兴起的抵制日货运动,彰显了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给日本在华贸易造成了“至为重大”之打击[46]。然而就是这样一场成绩斐然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历经一年有余的蓬勃发展后,却被国民政府无情地镇压下去。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的软弱妥协、对民众运动的敌视畏惧,固然是其镇压抵制日货运动的主要原因,但日本外务省针对抵制日货运动的各种应对措施,亦对取缔该运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回溯外务省应对抵制日货运动的过程,不难发现其应对策略随着运动形势发展而逐步调整。在抵制日货运动初起时,出于对中国民众抵货运动的轻视和所谓“经验”,外务省并未重视。当外务省察觉到运动背后有国民党支持,运动呈现组织性强、“破坏性大”、持续时间长等特点后,遂在济案谈判中迫使国民政府签订了含有取缔抵货运动条款的《济案协定》,意图假手国民政府消灭该运动。而后,当外务省发现济案议定后抵制日货运动依旧愈演愈烈,其又以改订商约问题为抓手,迫使国民政府加快取缔进程,最终导致抵制日货运动被镇压。
必须指出的是,济南惨案后,日本外务省应对抵制日货运动的诸般对策,皆服务于日本对华侵略扩张之根本目的,本质上就是用尽各种手段迫使中国民众放弃抵货抗日,消磨民众的爱国意志。此外,日本在济案交涉中,将犯下侵略罪行之责任,倒果为因地归咎于中国民众“排日”“反日”,正是日本法西斯强盗逻辑的最真实写照。殊不知,抵制日货运动被强行镇压,根本不代表日本侵略计划的得逞和中日民族矛盾的消弭,其背后反而酝酿着极为深刻的危机:日本国内的侵略扩张思潮进一步膨胀,狂妄自大的军国主义分子严重低估了中国民众抗日御侮的决心,开始变本加厉实施侵略,中国民众的抗日抵货运动因之延绵不绝。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仍宣称中国民众的“排日”“抗日”是中日冲突爆发的根源所在,[47]企图为日本侵略中国辩护。可以说,日本政府一贯的强盗逻辑和错误认知深刻影响了当时中日关系的走势,其对发动侵华战争、犯下深重侵略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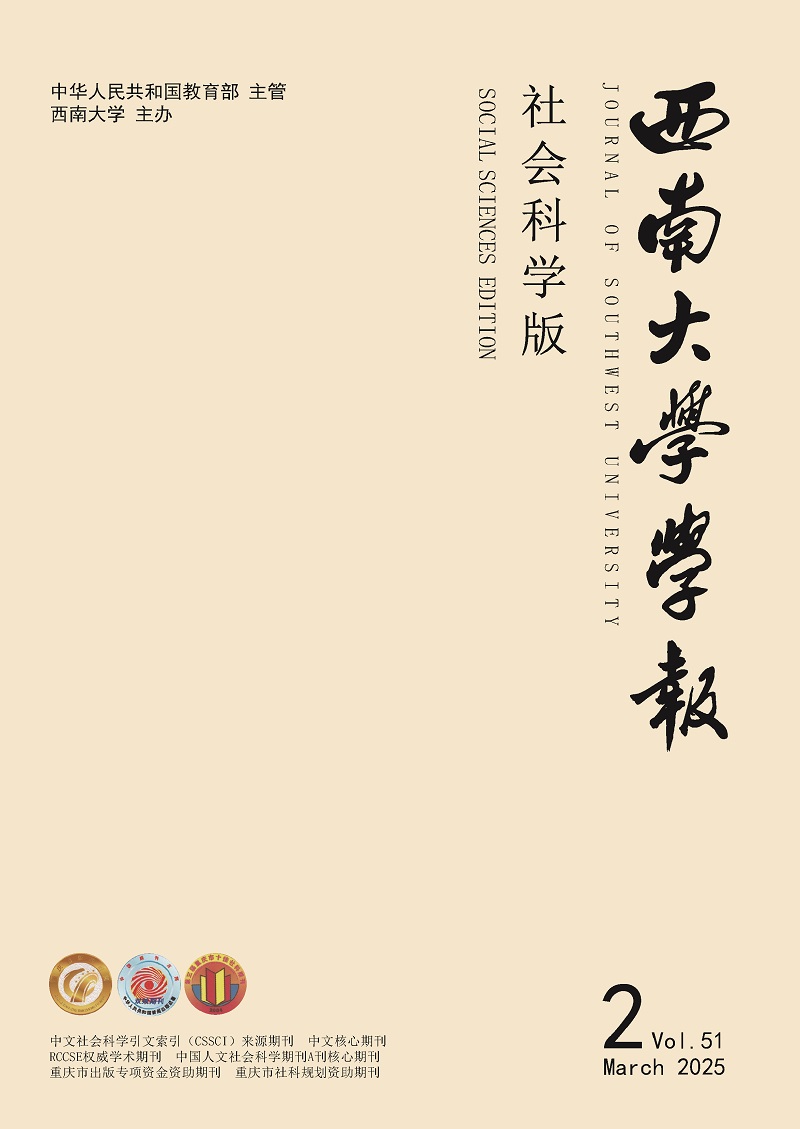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