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ML
-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以及国家近年来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探索,生态整体主义(ecological holism)作为一种强调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内在价值的哲学思想,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热点。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1],而传统意义上对生态整体主义的定义则依赖西方学界的生态批评理论,如将其定义为以利奥波德“大地共同体”生态伦理观、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奈斯人与自然最大化共生思想等为核心的生态思想[2]。国内生态整体论研究具有跨学科属性,主要分布在哲学、美学、文学和环境科学领域,与深生态学、生命共同体、生态文明等研究领域皆有重合,而其独特性主要体现为对西方二元论影响下的分离性世界观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强烈批判。正如杨文所说:“二元论导致了人与自然在形而上学上的分离,这种分离在现实中引起对自然的漠视。中外学者们一致同意,医治这种残酷病的方法是重塑整体以获得与自然的手足之情。由于宽泛地谈论与追求整体性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深入追踪整体性的组织方式。”[3]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生态整体主义进行阐释和探讨,形成了多维研究向度。在生态整体主义理论构建方面,龙静云深入分析了生态整体主义的基本观点,强调生命共同体的繁荣是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追求[4];孙开晗探讨了中国生态美学的独特价值,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向世界传递中国生态美学的声音[5];李映红等探讨了恩格斯生态整体主义自然价值观,指出其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6]。这些研究为国内生态整体主义理论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国内生态美学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学者们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探讨生态美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如曾繁仁梳理了我国自然生态美学的发展历程,强调了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7]。在文艺研究领域,生态整体主义得到广泛运用。如陈欣欣等对《文心雕龙·物色》的生态整体观进行探析,揭示了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的生态智慧[8]。段艳丽从人与自然共同体视角分析伍尔夫《在果园里》的生态整体观[9]。马特探讨惠特曼的城市想象与生态整体观,揭示其与中国古典道家思想的契合之处[10]。傅悦分析“波利尼西亚三部曲”之一《奥穆》中的三重生态观,揭示作品对生态整体主义的深刻反思[11]。这些研究丰富了生态整体主义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应用实践,为理解生态整体主义在文艺作品中的体现提供重要参考。一些学者还探讨了生态整体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如卢政论述两宋时期的生态整体主义美学观,揭示理学美学对生态整体主义的贡献[12]。王国成探讨传统文化生态整体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13]。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态整体主义在传统文化中的价值。
道家哲学作为一种古老而深刻的生态智慧,展现了与生态整体主义理念的深刻共鸣。道家强调“道法自然”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生态整体主义所倡导的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理念不谋而合。马特指出,惠特曼的城市想象与生态整体观及中国古典道家思想有着契合之处,体现了对自然与人类社会和谐共存的追求[10]。王宽等[14]和王国成[13]分别从西方生态伦理学和传统文化角度,探讨道家哲学对现代生态整体观的贡献。此外,李映红等[6]、崔文奎等[15]进一步分析了恩格斯生态整体主义自然价值观与中国佛教文化和马克思思想的共通点,揭示了东西方生态智慧在道家哲学这一交汇点上的融合。道家哲学倡导的“无为而治”“自然无为”等理念,为生态整体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促进了人类对生态系统整体性的深刻理解和尊重。综上所述,道家哲学与生态整体主义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和深刻的交融。这种跨文化的生态智慧,为我们理解和保护自然环境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生态哲学不断发展,当前生态整体论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矛盾焦点上。首先,整体主义虽然兼具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但目前在方法论层面缺少可行性。早在国内界定生态文学概念、梳理生态文学发展进程的奠基之作《欧美生态文学》中,王诺总结了对生态整体主义的三种批评:一是对整体利益的追求,违反了自由主义强调个体利益的原则;二是笼统地强调生态整体可能忽视人类在享有自然资源上的不公平,引发了对环境正义的担忧;三是生态整体主义对人性的超越难以实现[1]。这三种批评实质上反映了个体与整体的冲突,但“现代西方主流价值观无疑是个体主义的,而大地伦理主张整体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体主义”[16]。西方学界也有类似批评,如梅尔钱特批评传统生态整体论的本质缺陷,指出生态整体论忽视了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权力关系和冲突,主张超越单一的生态整体论视角,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17]。埃斯科瓦尔提出“多元宇宙”概念,批评生态整体论忽视了不同文化和知识体系的多元性,主张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探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激进的相互依存关系,以期建构一个更加包容、公正的生态秩序[18]。总的来说,这些批评实际上呼应了王诺的三点批评,即当前生态整体论研究面临着权力关系、文化差异、应用实践等多方面的挑战。生态整体论的整体性世界观与西方根深蒂固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之间存在矛盾,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割裂,如深层生态学的生态中心主义很难落实到批评和行动实践之上,布伊尔认为深层生态学当作本体论或美学更具说服力,而非伦理或实践的处方:“作为对人类同胞的呼吁的生态中心主义更具说服力,让其认识到人类与非人类之间不可避免、不管喜欢与否的相互依存关系,并更谨慎地对待地球,而不是作为一个实践计划。”[19]西方生态整体论的发达并未带来实践上的明显进步,这在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中可见一斑。相比而言,道家哲学的生态整体论长期指导着中国的生态批评实践,究其原因,主要是道家思想在中国拥有丰厚的文化土壤,而西方生态整体论所依托的19世纪以来的科学主义如进化论、人类学、生态学等却备受争议,虽然在理论层面上不断推陈出新,但大量新词的引入让人眼花缭乱,长期与各种生态思想博弈却难以占据主导地位,且往往忽视了历史维度的深厚积淀。
生态整体论体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可能呈现出平庸甚至败坏的人类形象,这与人的特殊性及其生态哲学意义相矛盾。生态整体主义区别于生态中心主义,基本前提是非中心化,强调整体内部联系,不把任何一部分作为中心,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形成了冲击。对此,虽然巴迪欧指出整体性是基于多元集合的操作结果,并通过“溢出”与“事件位”展示了人类在生态整体中的特殊性和主体性地位[20],但不可避免的是,生态整体主义对自然万物的平等态度,仍导致实践层面上的模糊性。杨文挖掘道家哲学的整体论资源,指出道家思想通过“道”的本源性将人与自然整合为一个整体,并使人的地位经历三重“相对化”,分别从目的、价值和质料入手,迫使人意识到自己只是自然全体的一部分,从而内在确立于整体性的自然中,但并不主张彻底的平均化。在道家哲学中,人不仅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同时还承担着超越其他生物的角色,促使人类有意识地保护和理解自然[3]。
道家生态哲学回应了生态整体论的两大矛盾,为生态整体论的实践问题提供了中国经验,可以有效指导生态批评。本文以中西乡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沈从文和哈代的小说为核心案例,探讨在城乡冲突激烈、生态矛盾显化的社会背景下,两位作家的文学作品如何建构湘西和威塞克斯的整体主义生态;同时进一步借助道家哲学的生态整体论,剖析这些作品反映的生态哲学如何跨越时空形成对话,在生态整体主义上达成中西文明交流互鉴。
-
美国学者金介甫认为沈从文直到1930年代都还是中国新兴知识界的局外人,他与1890年代“改革一代”的想法更为贴合,体现在他们共享诸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地方繁荣,以及形而上的整体性”等意识形态而非“物质主义或革命”[21]。金介甫的结论是沈从文的这些个人因素和倾向使他更容易接触到北京大学的前卫思想,即“试图整合理解人类的原始与复杂、善与恶、神话创造与科学分析”的现代思想,并在其激励下“跟随他的直觉,赞美故乡独特的神话、风俗、原始仪式,而不是去打压它”[21]。这段评论指出,对20世纪初中国主流中产阶级读者来说,沈从文是一位边缘化的作者,他与读者的关系是紧张的,这从沈从文重要作品序言对读者接受与其创作初衷存在偏差的描述中可见一斑。然而,这种边缘化恰恰促成了沈从文特有的写作资源,即一种在五四新文学中逆流而生的乡土群像。
沈从文的作品得益于其边缘化背景的一项特质便是“自然”,即金介甫所说“形而上的整体性”。同样,理查德·泰勒在哈代的“性格与环境小说”中定义了一种精神的相互作用(psychic interplay):“哈代对这一组小说的定义体现了他对自己小说的本质的认识要比通常社会对他的作品的定义更为深刻,这也解释了为何这类型中的一些小说相比另一些引起的反响更少。正是‘人物’与‘环境’的精神相互作用使读者对这组小说中的主要作品保持了深层兴趣,虽然哈代的其他作品也有相关特点,但它的效果往往被其他因素削弱。”[22]然而,泰勒并未详论这种“精神的相互作用”如何在文本中具现,以及除了其中的田园想象成分,它为何可以使城市读者对此保持长久的兴趣。
类似地,约翰·奥尔康提出了“自然者(naturist)”概念:“自然者更接近于弗洛伊德、荣格和威廉·詹姆士的以潜意识为中心的心理学,而非约翰·洛克的实证心理学;他们质疑任何把‘风景’哲学化的举动,也拒绝把自然当中的实证事件当成是产生抽象或普泛思想的场合。”[23]3奥尔康与泰勒不谋而合,都强调了哈代对环境与人物关系的特殊处理,而这一关系的整体性是其理论核心;但二者的批评都因受到英语“nature”一词意涵的限制,不能清晰表达这种形而上的“自然”概念。作为进一步的尝试,奥尔康论述了“自然者”的取向,即自然对于自然者来说是天然的、本体的,并指出这与禅学或道家哲学相通:“哈代塑造的人物就像中国屏风画中巨大空间里的微小个体,或者像正在砍荆豆的克林姆·伊尔布莱特(引者注:Clym Yeobright,哈代小说《还乡》中的人物),如蚱蜢一般渺小——这些人物本身就是风景的一部分。”[23]4“自然者”概念在道家哲学的生态整体观下更容易被理解,在哈代的作品中表现为“试图消除那个在观察、思考、感受的第一人称者”[23]4。奥尔康试图定义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但其论述始终无法摆脱一种客体化自然的语言系统,即英语中的“nature”在表示自然界时所代表的工具理性,例如他的讨论始终围绕“风景(landscape)”这一客体化概念,而显然道家哲学的“自然”概念更适合阐释这种生态观。即便如此,奥尔康的“自然者”概念承认通过语言以及其他抽象形式理解“自然”的局限,试图通过对潜意识的论证表明一种不分主客体的整体性自然观,为以道家哲学阐释哈代开辟了可能性,尤其是中国屏风画被奥尔康用来与《还乡》荆豆田中渺小的克林姆这一场景类比,可视为一个为道家自然观提供比较研究的前例。
以上对哈代作品中“自然”的把握都是基于对英语“nature”所代表的实体“自然界”的思考和超越,但无论“精神的相互作用”还是“自然者”,都没有清晰地解释这些作品中“nature”与人类的形而上整体性。针对此问题,本文借用道家“自然”的概念将这些批评推进一步。与哈代研究相似的是,张新颖在分析沈从文对“风景”一词的使用时,认为多数时候是沈从文的一种让步:他所谓的“风景”实际上是“自然”,与天地相连,拥有无穷的活力。张新颖指出,“风景”作为物化自然的概念是一种经过人类的眼睛或相机图像化处理的景象,是一种现代性的“自然”,由于传统对沈从文的阅读存在文化和自然二分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因而他提议用“天地”概念来阅读沈从文表现的自然[24]。从“风景”到“天地”的转向,抓住了中西比较文学生态批评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自然概念的异同。本文以哈代和沈从文的小说为例,探讨二者在自然概念上的相似性,人与自然的整体性是比较二者的核心问题,由此形成了中西生态整体观在文学建构上跨越时空的对话。
近年来对中文“自然”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道家哲学、山水概念、现代性三个方面,代表学者分别是刘笑敢、赵汀阳、王中江。刘笑敢立足于《道德经》原文的语义分析,定义自然是“人类文明社会中的自然而然的秩序”,即“人文自然”,强调老子之自然是一种价值、一种整体的理想秩序,区别于现代汉语所指的整个自然界,也区别于原始状态或人文主义的自然,具有独特性[25]。这一理论站在道家自然的角度,挖掘了人文自然观的整体性生态理念,其内核不再是欧美生态批评,而是带有中国“道法自然”意味的观念形态。在论述“道作为万物之整体”时,李若晖指出:“万物之整体非万物之总体,总体可以是单纯的杂多之个体之全部,而整体则必须具有内在联系。所以道实质是万物的整体性:道赋予万物以存在的可能性。整体性体现在万物的每一物存在的可能性依赖于其互相之间联系,万物之每一物互相之间的联系决定了万物每一物的存在。”[26]本文借用这一定义,挖掘沈从文与哈代建构的文学世界在差异性基础上的同一性,论证“自然”区别于英语“nature”在现代语境中的主客二分,其中包含生态整体观,其应用于生态批评能更准确地阐释这些小说中的主客统一。
沈从文在《水云》(1943)中提出“一种新的道家”[27]97-98,凌宇总结说:“佛教的人性向善、儒家的入世进取、道家的人与自然契合的思想要素被沈从文接受并吸纳。”[28]这一解释汇集了儒释道三种传统中国思想,其中对道家的概括集中在“天人合一”,即金介甫在沈从文作品中观察到的“形而上的整体性”。在中国哲学中,“自然”一词始见于《老子》[29]79。本文所用的道家自然概念,即为《老子》对“自然”的描述和解释,即“自己而然”“自己造就”[30]。崔晓姣在梳理近年来关于“自然”思想意涵的研究时,开篇强调“自然”为《老子》所创,书中“自然”一词作为名词和形容词共出现5次,其字面意思或基本意义为“自己如此”,并在脚注里澄清“自然”在《老子》中的意义绝不同于现代汉语中的“自然界”或“大自然”[31]。张岱年认为《老子》中的“自然”一词皆为“自己如此”之意,其中“道法自然”即是“道以自己为法”之意[29]79。本文所指道家自然观,关注“自然”在小说中展现的形而上的整体性,即在“自然”状态下人与环境的互动与统一。这一自然概念一方面阐明了作品中主客统一的叙事手法,另一方面澄清了作品的环境描写并非是人类中心的情感投射,而恰恰是对人之渺小脆弱的展现,即承认人事之“变”,以及人融入天地之“常”的道家美学。
-
《边城》以近五分之一篇幅描绘一座小城的生态,沈从文用“纯粹的诗”来形容《边城》,他在1936年重申:“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32]这暗示了沈从文在写作手法上的抽象性和抒情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自然”一词在沈从文创作意图的表达上得到反复强调,“纯粹”“人生的形式”“不悖乎人性”等表达的都是一种道家自然的态度,《边城》中的具体表现是人物没有具体的名字,老船夫的名字不曾出现,翠翠只是一个昵称,即使天保和傩送有正式的名字,在小说中也总是以大佬、二佬的称呼出现。命名是人类认识环境的独特语言功能,是符号思维逻辑理性的反映,使人从自然之中被异化。《边城》角色的“去名化”既体现了小镇社会关系的紧密和通融,也体现了普遍和抽象的人性,与这些人物的生活环境浑然一体。哈代《林地居民》也有抽象化人性的趋势。例如,约翰·索奥斯因为菲茨皮尔斯轻率地砍倒了寄托他精神的树而一命呜呼,小说叙述者点出在村子里还有众多和索尔斯一样对树有复杂感情的林地居民;又如,小说结尾马尔蒂在贾尔斯的墓前哀悼,叙述者说她变成了“抽象人性”的代表。
个体成为人性符号,是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表现。这种象征主义模糊了人与环境的主客体界限,在迈克尔·拉法格对道家的观察中得到回响,他指出道家“模糊了自然与人文的界限”[33],可以看作是另一种描述两部小说中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方式。格雷戈尔认为,哈代小说中“人与地的区别有趣地变小了”,而且“在威塞克斯界内我们看到了当地人的本质,风景变成了人脸,人脸成了风景”[34]。并非是风景被拟人化或人被风景化,而是“自然”在这部小说中成了一个灵动的存在,其本身的界限是模糊的。这些评论表达了同一种模糊自然与人文界限的理解,正可用来分析道家自然观在哈代小说中的体现。
进一步论证道家“自然”的文学阐释方法,需要理解这一理念的人文性及其与“nature”的区别。刘笑敢系统分析《老子》全部5处“自然”原文,指出自然“是道所体现的、人应该效法的最高的原则,是应该实现的最高价值和目标”,“这五处原文的相关语境都是关于圣人、道、万物和百姓,这就体现了老子之自然的哲学含义的第一个要点,就是最高的含义。道有实体义,也有价值义,但自然没有实体义,只有价值义”[25]。这一理解归纳了道家思想中“道”与“自然”的区别:道是本体的,而自然是美学的。安乐哲对道家思想的阐释与此呼应:他指出道家更关乎美学,而非科学或哲学。他用“关系美学”而非“形而上”来定义道家思想,原因是相对于宇宙第一定律,其更关乎如何做人、构建集群和创造世界等人类最基本的经验,这是一种审美体验而不是科学或哲学[35]。道家自然思想属于哲学还是美学范畴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但安乐哲的定义强调了道家自然观的整体主义原则,是本文论点的佐证。
米勒指出汉语中的“自然”与英语中的“nature”并不完全对等。米勒把汉语中的“自然”翻译为“self-so”,拉法格译为“naturalness”,都区别于“nature”。米勒分析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展现的三种基本存在维度(天、地、人)被交叠在“道”的“自然”发展中,没有借助任何完全外在的力量或至高无上的力量。道的自然运行并不仅限于生命或存在,它是贯穿一切活动的根本,不论是人类的、天体的、政治的、动物的或植物的[36]394。换言之,道家“自然”的概念对比英语表示自然界的“nature”更加广阔,也是一个超越实体的概念,本文采用“形而上的整体性”来进行描述。米勒还提出对道家“自然”理念的讨论是通过“界中人(person-within-the-world)”这一概念表达的,而不是通过类似“nature”或者“environment”这样的概念表达——后面两种表达指向一种人类可以利用的外在存在或物体[36]405。这一分析精确概括了道家“自然”对人与广义环境紧密联系的强调,也突出了其社会性和生态性,即道家意义上的“自然”不是自然界的实体性,而是一种整体协调性,是人与环境的关系。
相似地,帕克斯解释“自然”作为“nature”的翻译不完全对等,认为使之复杂化的原因之一是在道家概念里并不存在一个完全与英文“nature”对应的词汇,而是有一系列关系复杂的相关词汇,其中最重要的是“天”,尤其是“天地”这一复合词最接近西方文化概念里的自然世界[37]。王中江指出严复在接受日本翻译“nature”为“自然”之前将它理解为“天”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古代的‘天’、‘天地’、‘物’和‘万物’,相当于西方实体意义上的‘大自然’和‘自然界’,往往被用来表示客观物质世界中的实体、现实的‘实有’;中国的‘天’,特别是道家的‘天’,具有一切都非外力作用而是依自发性发生的意义。”[38]3这里明确分析了道家的“天”与西方的“自然界”更加对等,但“nature”不可直译为“天”,因为“nature”在英语中的意涵也是丰富多变的,正如“自然”在中文里一样。王中江指出民国初年有机械主义的自然观和人文自然观的对立,更有一种自然观的东西文明二分论,将西方的自然观单一化为自然与人的两分,将中国的自然观单一化为自然与人的合一,这样的严重误解“不仅将西方近代兴起的浪漫主义、生命主义以及抵制机械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思潮掩盖了,而且也将近代中国形成的机械主义和科学主义忽略不计了”[38]9。王中江对“自然”和“nature”的比较立足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融合演变,而本文对“自然”的定义取自《老子》原文的解释,立足于道家思想中“自然”的整体性,阐释沈从文与哈代乡土小说中自然概念的可比性。本文所采取的道家自然概念并非建立在东西文明二分论上,而是恰恰与之相反:分析沈从文和哈代小说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细腻刻画,辨析之前文学批评对两位作者的刻板印象,即王中江所论“自然观上的东西文明二分”,尤其是辨析之前在对“自然”一词阐释模糊的情况下作出的中西对比;以往对两位作家的生态批评比较研究集中在达尔文进化论意义上的实体自然和高度风格化的诗意自然这两种“自然”概念,未从形而上的角度细致研究过“自然”在这些作品中的人文性、社会性和生态整体性,这正是道家自然观可以作出贡献的地方。不可避免的是,以往的文学批评对两位作家作品中的“自然”定义模糊、指涉不清,需要长期研究以厘清其中的概念、辨析其中的意义,真正体现道家“自然”的广博性和适用性。这一研究过程也是对近代以来“自然”概念在中国文学批评中逐渐实体化的一个反过程,力图还原“自然”在道家意义上的形而上的整体性。本文接下来将着重比较沈从文与哈代文学作品体现的生态整体观,论证道家自然观对分析哈代和沈从文作品中的“自然”的阐明作用。
-
道家形而上的整体主义认为万事万物是在对比、对立中存在的,矛盾对立的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是世间事物永恒不变的规律。生态整体论认为生态关系决定了有机体的本性,而非有机体的本性决定了生态关系,强调关系先于实体,由此去除了二元论所依赖的实体论[16]。这一方面是因为生态整体主义并不剥夺个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是强调人与自然最大化共生;另一方面,作为生态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局部群体的生态危机具有辐射整体的破坏性,危害整个生态的可持续性。因此,生态整体主义使关系特征从从属走向核心地位,沈从文的《凤子》和哈代的《远离尘嚣》就充分展现了关系特征在整体性生态中的核心位置,尤其体现在人物的关系性自我意识。两部小说刻画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除了对立的一面,更有互相依存和转化的一面,人性在对自然的皈依中通向神性。
哈代和沈从文都显示了对原始泛神论的兴趣。哈代在笔记中写道:“特别是在艺术中,所有物体都是有生命的并且与人类休戚与共的原始信念,是非常适合激发理想性的。”[39]沈从文在《美与爱》中说:“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40]他们的小说阐释了整体性自然“宗教”,取代了现代世界疏远人类与自然的正统神学和工具哲学,而道家哲学可以为理解威塞克斯和湘西的这种自然宗教提供形而上学的基础。
沈从文的中篇小说《凤子》,前九章写于1932年,最后一章写于1937年,是关于一位湘西青年学者在中国北方城市教书的未完成的故事。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早年在湘西当过工程师的老隐士,他们一起谈论了老人对这个心爱的地方的记忆。沈从文之前也写过一些以湘西为背景的短篇小说,但《凤子》是第一部比较全面地介绍当地风土人情的作品。同样地,哈代在《远离尘嚣》的序言中解释说,他首先在这部小说中使用了“威塞克斯”[41]1这一地理概念,因此它标志着这一虚构空间的开始。正是从这部小说起,威塞克斯中人与自然共生的模式变得清晰起来,这一模式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形成了有趣的隔空对话,《远离尘嚣》和《凤子》都展现了一种本土自然宗教和关系性自我。
沈从文曾在《水云》中提及“我泛神的思想”,并声称“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光明赞颂”[27]128。显然,他在湘西小说中塑造的是一个有神的世界,但这个“神”不仅仅是当地宗教中的神,更是一种形而上的、有生命力的自然。他在小说中将宗教观念同质化为当地的泛神信仰和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状态,可视作一种自然宗教。在《凤子》中,沈从文通过精心并置的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物之间的对话,展现了湘西乡土的神性。《凤子》的前三章讲述了青年学者在城市的经历,他在海滩上遇见了凤子和她的同伴,并与经常路过的老人成了朋友;其余七章是青年学者记录的与老人的对话中老人对湘西的回忆,到了第十章的结尾,读者仍沉浸在老人的回忆中,这赋予了小说梦幻的色彩。在第七章中,老人回忆他在去矿井的路上与乡绅对当地“神即自然”信仰的讨论。他们在清晨观察蜘蛛网上的露珠,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这个“神圣”的景象。乡绅说,上帝创造了美,却让人类发明自己的方式来赞美它,语言的失败暴露了人类的无能。工程师要求乡绅解释他对自然与对科学的信仰之间明显的矛盾,因为乡绅邀请他通过现代技术改善采矿业。乡绅认为两者毫不矛盾,因为当地的神即为自然:“我们这地方的神不像基督教那个上帝那么顽固的。神的意义想我们这里只是‘自然’,一切生成的现象,不是人为的,由于他来处置。他常常是合理的,宽容的,美的。”[42]123他认为科学只与迷信冲突,但“我这里的神并无迷信,他不拒绝知识,他同科学无关。科学即或能在空中创造一条虹霓,但不过是人类因为历史进步聪明了一点,明白如何可以成一条虹,但原来那一条非人力的虹的价值还依然存在。人能模仿神迹,神应当同意而快乐的”[42]123。由此反映出当地泛神思想中对人与自然整体性的思考,反对现代性科学主义对人的异化。
《远离尘嚣》开篇描述夜空中的星座,这是主人公奥克所熟悉的,但超出了大多数奥克的同乡和读者的知识范围。接下来小说叙述转向对宇宙的抽象思考:“天空还是清朗的——格外的清朗——全体星星的一眨一眨,似乎是来自同一个躯体的阵阵搏动,是由一根共同的脉搏准确控制好的。”[41]10“躯体”和“搏动”将星星类比人体,使宇宙与众生融为一体,饱含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在人类与非人类世界之间经历了如此亲密的命运共同体之后,叙述者将这些乡村情感与“文明”情感区分开来,要领略这一史诗般的满足感“还是得在子夜时分站在山坡之上,首先要开阔胸襟,把自己同那些芸芸之众的文明人区别开来。那些人此刻睡梦正酣,哪里想得到这样的景象,而你,久久地静静地注视着自己穿越无数星辰的壮阔运动。经过这样一番夜间观测,很难再把思绪收回到红尘中,很难相信,人类那小小的方寸躯体之中,竟能意识到如此的宏伟飞动。”[41]10-11这个叙述非常恰当地解释了这部小说的标题——远离尘嚣,即远离“芸芸之众的文明人”。《远离尘嚣》展现了一种独特的乡土感受力,与19世纪英国小说的主流城市中产读者的经验拉开距离,但叙述者又强调了这种感受力本应是人类作为宇宙一体的共通感受。哈代通过奥克展示了“尊重自然”的含义:“有那么一会儿,他深深地感受到这个场景中栩栩如生的孤独,或者说,他感受到这个场景中没有一个人影,不闻一丝人声。人类的形体,人类的参与,人类的烦恼和欢乐,似乎都根本不存在。在夜幕覆盖着的地球这半边,除了他自己,似乎再没有一个有感知能力的生命存在;他简直可以想像,这些人已统统跑到阳光灿烂的那一边去了。”[41]14奥克与宇宙的联系似乎比与人类社会的联系更为紧密,人类维度的渺小与宇宙的浩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哈代用了一个矛盾的说法来强调这种印象,“栩栩如生的孤独(the speaking loneliness of the scene)”,人类的存在如此有限,但却实现了与宇宙的某种融合,最后一句的宏观视野超越了人类中心论,达到了人类命运与宇宙形而上的联系,整个场景是神圣的,奥克揭示了他与环境、宇宙的关系,而不是对外部创造者的依赖。这与《凤子》的世界观有相似之处——人类的知觉通过自然而接近神性,只有与自然相融合,人性才能完整。
通过共生中的自我,两位作家强调了相对主义所提供的丰富视角可以重新认识所谓的田园主义。《远离尘嚣》与《凤子》这两部小说都将田园风格视为一种透视艺术和社会批判,威塞克斯和湘西小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地方感和归属感,塑造了人物与地方的深度共生,以批评城市对乡村的误解以及现代制度的异化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疏离。
-
道家之道,不可感知却又确实存在,是所谓“无状之状,无物不象”。道的普遍规律支配现实世界的具体事物,掌握这种规律是了解具体事物的根本。哈代《林地居民》与沈从文《边城》中的“静”互相辉映,作为一种留白处理契合道家美学,体现了去人类中心主义。在整体主义生态的自然图景中,主客体的区分不是完全被取消了,而是被淡化了。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只在特定语境中才是有意义的,主客二分不能严整周延地划分宇宙万物[16]。两部作品对观察者与参与者视角的互融,彰显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
《边城》开篇介绍老船夫:“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那么老了,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43]9老船夫对渡口的坚守是“静静的”,而第一章后面描写翠翠喊正在渡人的老船夫配合她的吹奏唱歌时又写道:“爷爷到溪中央便很快乐的唱起来,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振荡在寂静空气里,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一些。实则歌声的来复,反而使一切更寂静。”[43]13这里既有对祖孙二人彼此陪伴的温馨描写,同时展现了小镇的淳朴民风,更重要的是一种“寂静”环境象征的天地运行之“常”在两个情境中折射出一种哀愁,也是沈从文提到的“美丽总是愁人的”的悲剧气质,而这一气质可以在道家思想对常与变的辩证思考中得到阐释。第十二章对环境之“静”的描写又有一个呼应:翠翠没有回复大佬派来的媒人,这使得老船夫陷入深思,隐约担心翠翠与她母亲命运相似:“一堆过去的事情蜂拥而来,不能再睡下去了,一个人便跑出门外,到那临溪高崖上去,望天上的星辰,听河边纺织娘以及一切虫类如雨的声音,许久许久还不睡觉。”[43]127老船夫为繁杂思绪所困跑到高崖上的情景,与《林地居民》中贾尔斯爬到树上思考的举动形成了奇妙的呼应,两个场景都包含角色与环境的互融以及“静”带来的巨大张力,即人物思考的复杂沉重和外部的沉寂形成强烈对比。《边城》这一场景虽然没有直接写静,但高远的星辰和如雨的虫鸣都反映了一种环境对人事的漠不关心,而又间接地在叙述者眼中连成一个网络。接下来叙述声音讲道:“不过一切皆得在一份时间中变化。这一家安静平凡的生活,也因了一堆接连而来的日子,在人事上把那安静空气完全打破了。”[43]127用“安静”形容“空气”,指的实际上是边城之“常”,即一种生态的稳定,并不区分环境与人事。以上三处写“静”皆可视为叙事上的留白,为人事之多变留下想象的空间;同时这些变化统一于整体性自然之“常”中,表现为后两个场景中静观其变的主体是模糊的、非人的,体现万事万物互相关联的关系美学,正如第二章的叙述:“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人民每个日子皆在这种寂寞里过去。一分安静增加了人对于‘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梦。”[43]19“静”既是一种“常”,也是面对“变”时能感受到万物相关联的美学思维。
《林地居民》的一个鲜明特色是哈代通过声音塑造了小汉托克这个小镇。相比大量出现的声音丰富的场景,一些突出静默的场景更应该引起读者的注意——声音的留白处理,却使人与环境的关系得到层次更为丰富的展现。菲茨皮尔斯与查曼德夫人私奔后发生意外,当他突然返回家中时,小说对妻子格蕾丝的惊异反应做了细致刻画,原本声色丰富的小汉托克突然在格蕾丝的想象中静默了,而她全部的听觉都集中在丈夫的接近中:格蕾丝“把头抵在窗户槛上,张着嘴听着”[44]268。不想见到丈夫、十分惊慌的格蕾丝选择逃入丛林,“她尽可能地不发出任何声响,避开树叶堆积的虚处,踏在无声的苔藓和草地上”[44]269。仓促中的格蕾丝没有留意到丛林的细微之处,而小说对此进行了描绘:仿佛同情格蕾丝的困境一般,丛林默默地配合着她的逃脱;这里对丛林的叙述颠倒了观察者与参与者的身份,仿佛不再是格蕾丝倾听丛林,而是丛林在倾听她:“光滑植被的平整表面就像虚弱的无眼睑的眼睛;有些像昏暗灯光下奇怪的脸庞或身影,游荡进了一种被笼罩的朦胧中;尽管不时地隐约从树干之间透出片状的天空,大树枝的尖端仿佛承载着模糊的、裂开的舌头。但格蕾丝此刻的恐惧既不是充满想象力的,也不是宗教的;所以她没有注意到任何这些印象。”[44]268-269这里把黄昏时刻的丛林描绘得十分诡异,尤其是用虚弱的人体器官比拟植物在晚夏傍晚的死气沉沉:人与地的区别、脸庞与景色的区别都被无限地缩小,此时的丛林成了一个生命体,与人互动。格蕾丝对这些叙述者的观察毫无所知,读者却跟随叙述者的视角注意到丛林的各种细节变化,似乎与丛林成了更紧密的共同体,与其一起注视着格蕾丝的行动,这使得观察者与参与者的身份再一次互换:不是格蕾丝作为故事的参与者在观察、叙述丛林,而是丛林直接参与了故事的构成和讲述,带领读者一直观察着格蕾丝。通过这样的叙述方式,哈代展现了人物与环境的互动性,从而揭示一种万物联系的“自然”状态;而格蕾丝在这种相互关系中不断变换的立场——她只有在忧郁时才对环境有一定的敏感度——反映了她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出生在乡村,受教育于城市)的尴尬身份。
在《边城》中,当老船夫告知翠翠她母亲的故事时,叙述者这样描述环境:“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篁竹在月光下皆成为黑色。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雨。间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忽然会有一只草莺‘嘘!’啭着它的喉咙,不久之间,这小鸟儿又好像明白这是半夜,不应当那么吵闹,便仍然闭着那小小眼儿安睡了。”[43]139-141此处翠翠沉重的思绪与环境形成互动关系,正如《林地居民》中格蕾丝与丛林的关系——环境既是观察者亦是参与者,而叙事上的留白增强了这种人与环境互动的丰富和不可言说,将抽象的万物关联变成似乎可感的形式,正如格雷戈尔提出哈代小说中存在着一种“不寻常之强化的生命流”[34],也强调了一种整体性自然观。在《林地居民》的第三章有一个绝对寂静的场景,当贾尔斯和马尔蒂“在一天前的孤独时刻”穿过树林时,叙述者说:“它们孤独的路线根本没有形成任何独立的设计,而是人类活动的伟大网络模式的一部分,彼时正在两个半球上编织,从白海到合恩角。”[44]20这一叙述的视角像摄像镜头一样逐渐拉远,两个人的身影逐渐浓缩成宇宙大网中的两个小点,而林地对于这种联系的发生至关重要,不是作为背景,而是作为存在。
以上描写中叙事声音上的“静”可以类比为道家绘画中的留白处理,看似未完成,实则是艺术家刻意为之,以表现“自然”之模糊和流动,也蕴含着自然之“常”。留白使观众成为作品的共同创造者,正如他们参与“自然”一样;空白的空间同样具有重要的批评价值,因为空白有独属于它的充实性,正是这种空白为人与环境的界限留出了想象空间,也揭示了自然形而上的整体性。同时,两部小说中人物与环境作为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位置转换,体现了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也揭示了一种生态整体观。
-
哈代和沈从文笔下的威塞克斯和湘西都展现了人与环境互动之整体自然观。本文梳理了以往文学批评对哈代和沈从文小说中“自然”概念的论述,阐明道家“自然”与英文“nature”的不同,提出以道家自然观分析两位作家对自然的灵动表现,为理解作品中人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整体性视角。这一思路可以更清晰地阐明威塞克斯小说和湘西小说在自然概念和生态整体观上的共鸣。生态整体主义作为一种强调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内在价值的哲学思想,为我们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文学生态批评提供了新的切入点,本文即为道家自然观在文学批评中的具体运用。但国内外研究在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方面存在差异,需要加强跨学科交流和合作,以推动生态整体主义研究的深入发展。同时,需加强对传统生态智慧的挖掘和整理,为生态整体主义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探索生态整体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互鉴与传播,进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并“体现为生态化目标贯穿中国现代化全过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贯穿生态文明建设全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全面践行的有机统一”[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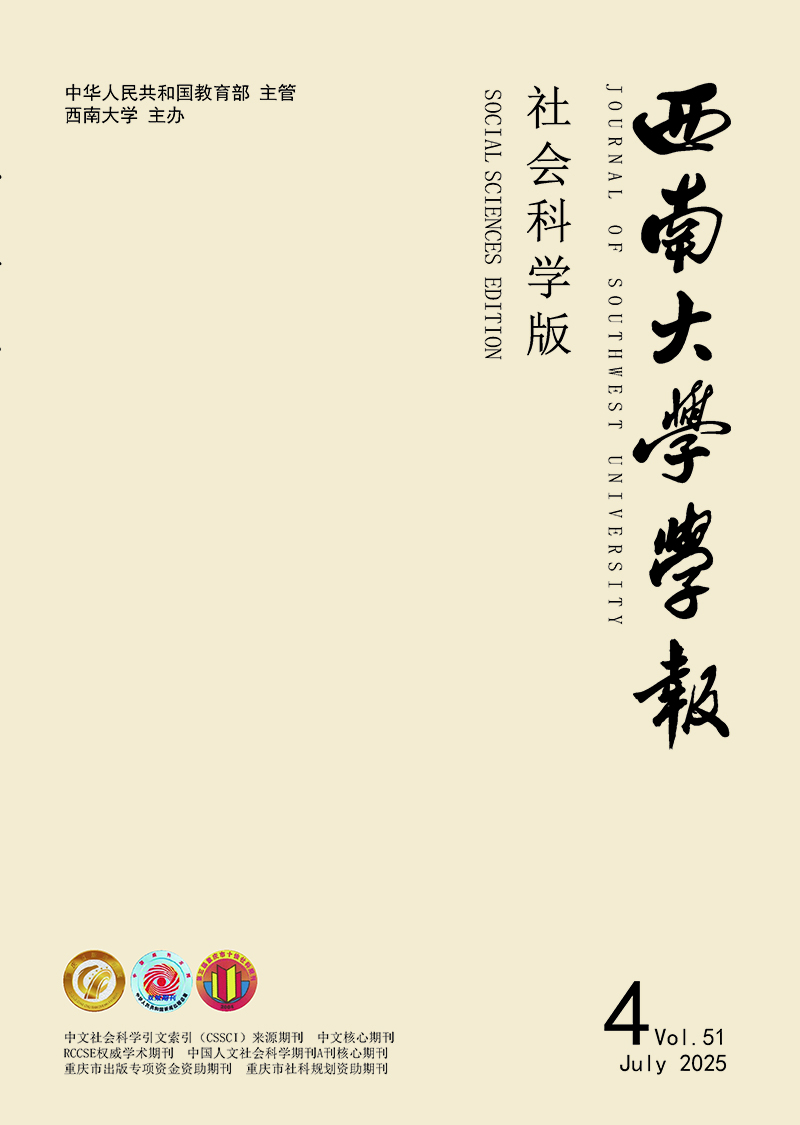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