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2]2023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讲好中华民族故事,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大力宣传中华民族的历史,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3]中华文化符号是彰显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对文学典籍中的中华文化符号的研究是探究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建历史的重要环节。
HTML
-
清代西域诗是继唐代边塞诗后的又一西域诗歌创作高潮,近年来其研究呈现出繁荣态势。中华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实践中所创造形成的表达情感的符号,蕴含、传递着中华民族精神。学界虽未对中华文化符号的内涵、构成等形成统一认识,但在其理论价值方面取得了共识。以中华文化符号为理论基础阐释清代西域诗的价值意义则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
-
围绕中华文化符号,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角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界定中华文化符号的内涵。田海林提出,“中华文化符号就是指在中华文化中那些能体现中华文化精神或意义的元素,当人们看到这样的元素时,不仅能直观地意识到这个元素是中华文化的,而且还能从中自觉体认出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与意义”[4];青觉、徐欣顺认为,“中华文化符号是对中华民族整体存续复兴怀以意义自觉的对象化表达和意象化呈现的显著标识”[5];冯月季则认为,“中华文化符号是由中华民族创造,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共享,承载中华文化价值,塑造中华民族形象的符号系统”[6]。中华文化符号概念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它是一个符号系统;其次,它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
二是对中华文化符号的构成类型进行划分。符号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分类方法也多种多样。对于中华文化符号类型,当代学者也多有分类。如冯月季根据符号与物质实践的关系将中华文化符号分为“自然存在物符号、人工制造物符号、艺术想象物符号”[6];方李莉根据文化符号的象征属性,把中华文化符号划分为“总概性象征、关键性象征、地域性象征”[7];胡仕坤则是依照文化符号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将中华文化符号分为“神话符号共同体、历史符号共同体、语言符号共同体、艺术符号共同体、民族自我意识符号”[8]。
三是对中华文化符号在助力中华民族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民族形象中所起的作用功能和意义探讨。如崔榕、赵智娜认为树立和强化中华文化符号认同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途径之一[9];冯月季、石刚提出文化符号承载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是凝聚中华民族情感认同的纽带,能够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反思[10]。
综上,当代学者都充分认识到了中华文化符号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的重要价值,充分认识到中华文化符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文化认同、构建中华民族形象等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
-
清代西域诗是我国西域诗研究的重镇,在西域诗歌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学史上对西域、西域诗的界定还存在不同理解,本文所指西域为《嘉庆大清一统志》中对西域范围的区划,“东至喀尔喀、瀚海及甘肃界,西至右哈萨克及葱岭界,南至拉藏界,北至俄罗斯及左右哈萨克界”[11]。本文所指的西域诗为亲自到过西域的诗人所写的有关西域的诗歌。意象是诗歌创作的重要艺术形象载体,也是诗歌研究的重要内容,意象研究对诗歌审美特征的整体把握具有重要意义。清代西域诗中的意象研究的当代学者以李彩云、张建春、任刚等为代表,他们的西域诗意象研究体现为以下特征:
一是对某一特定意象的研究。如对“天山”意象、“桃”意象、“瀚海”意象、“玉门关”意象的研究。
二是对某一诗人诗歌中多次出现的意象进行整理研究。如李彩云近年来对祁韵士诗歌中的“柳”意象、“沙漠”意象、“天山”意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
中国金石学发轫于宋代,在清代达到顶峰,在千年发展中积累了众多研究成果。碑刻是金石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有关它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大多为碑的书法艺术性研究、欣赏,针对“碑”意象的研究,与前者相比则略显不足。在知网以“碑意象”为主题进行搜索仅得《读碑、自啮与超越——试从“读碑”意象入手诠释鲁迅散文诗〈墓碣文〉》[12]与《陕西药王山造像碑意象艺术表现研究》[13]两篇学术论文,从侧面反映出学界对“碑”意象的研究较少,有待系统性研究。
基于此,从文化符号学角度研究清代西域诗的“碑”意象,不仅可以填补当前西域诗研究的相关空白,还可以揭示西域诗中“碑”意象所蕴含的大一统观念和中华民族精神,揭示作为文化记忆的“碑”意象在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价值和意义。
一. 中华文化符号研究现状
二. 清代西域诗意象研究现状
三. “碑”意象研究现状
-
“碑”字较早出现在《仪礼》中。《仪礼》是中国最早的关于礼仪的典籍,是儒家经邦治国的大典。古人将《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为“三礼”,而《仪礼》是礼的本经,故又称《礼经》。在《仪礼·聘礼》中较早出现了有关“碑”的记载,“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14]283。《仪礼·公食大夫礼》也有记载,“陈鼎于碑南,南面西上”[14]324。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提出,“碑,竖石也”[15]。郑玄《仪礼注疏》中注曰,“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16]。清代桂馥所著《说文解字义证》也采用了郑玄注的说法[17]。清代学者王筠在《说文释例》中阐释碑的作用认为,“古碑有三用:宫中之碑,识日景也;庙中之碑,以丽牲也;墓所之碑,以下棺也”[18]。从发展历史看,碑的早期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用以观日影测时;二是设置在祭祀场所,用以拴住祭祀的动物;三是将棺椁引入墓室[18]。其中《礼记·丧大记》在礼制上对不同等级的贵族在丧葬仪式上使用碑的数量做出了区分,“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国车,二綍,无碑,比出宫,御棺用功布。”[19]1775可见,碑在早期使用时并不是为了刻字。
儒家文化重视器物在礼制中的作用,提出“器以藏礼”这一概念。“器以藏礼”出自《左传·成公二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20]“器以藏礼”强调器物对于国家政治的重要性,是先秦时期礼制文化的反映。青铜礼器作为我国早期的礼器之一,其铭文具有纪事纪功之用。《礼记·祭统》记载:“铭者,论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19]1891至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制度遭到破坏,青铜礼器的礼器、纪事纪功德的功能也逐渐向碑刻转移。刘勰针对这一现象曾提出:“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21]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多次东巡,为了歌颂始自己的功德、昭示万代,分别在七地留下石刻。《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22]207,209到了东汉,人们开始在碑上刻字以纪事、纪功。
我国现代著名考古学家马衡在其所著《凡将斋金石丛稿》中认为东汉只是碑上刻字的开始,“碑之名始于周代,为致用而设。非刻辞之具。《记·祭义》‘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谓庙门之碑也。《记·檀弓》,‘公室视丰碑’,谓墓所之碑也。庙门之碑用石,以丽牲,以测日景。墓所之碑用木,以引绳下棺。……刻文于碑,为汉以后之事,非所论于古刻。然相传古刻亦有所谓碑者,故古刻之真伪,不可以不辨”[23]。
秦汉之后,碑的立石刻以颂德的功能愈加突出。到东汉后,大量带有文字的石碑出现,如为纪功颂德曹全镇压黄巾起义而立的《曹全碑》、为鲜于璜歌功颂德的《鲜于璜碑》和记载史晨功德的《史晨碑》等碑作。对于东汉石碑的大量产生,赵超在《中国古代石刻概论》中提出,促成东汉时期石碑大量产生和定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可能是“在汉代,标示墓葬的习惯逐渐普及成风;厚葬之风大肆盛行;歌功颂德扬名传世的思想与儒家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随着开通西域,西亚北非等地的文化逐渐传入等。这些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造就了在中国古代社会流行开来的重要石刻——碑”[24]121。在东汉时,刻石纪功在中央王朝的对外关系中开始出现,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窦宪大败匈奴后“勒铭燕然”。《后汉书》卷二十三记载,东汉永元元年(89),朝廷拜窦宪为车骑将军,率大军出塞,攻伐北匈奴,穷追北单于直至燕然山,获牲畜百万余头,降众前后二十余万人,“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班固撰铭以窦宪战功是“振大汉之天声……乃遂封山刊石,昭铭上德”,并以辞赞,“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25]245,246。据史书所载,燕然勒石是我国边塞纪功碑的起源,后世继承了窦宪勒铭燕然以纪功的行为,于边塞刊刻纪功碑的传统由此形成,并持续到清代。也有学者提出汉碑作为礼器蕴含着“儒家德政、孝悌、忠诚等观念”,是当时士人对“三不朽”追求的体现。其承载着集体记忆,使群体情感得以维系,个体身份得以确认。它所形成的公共空间,使得社会各阶层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润和影响。并成为崇儒尊孔和君主政权合法性两者构建联系的媒介。[26]
产生于春秋时期的碑,在东汉时基本定型,逐渐贴合社会政治经济乃至礼仪文化的实用需要,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固化为一种文化符号。一方面,碑有了稳定的制式要求,在东汉时碑由碑首、碑身、碑座构成。“它的形制主要是一件凿磨加工成长方形的竖立长石,即碑身,下部另接碑座。……以后在碑首增加了雕刻装饰,如刻旋纹,或刻有盘龙纹饰,逐渐形成一种以螭龙身躯为外轮廓的固定外形,习惯叫做螭首。以后随着碑石体积的增大,由蟠龙缠绕组成的螭首多雕刻成一件单独的碑首石,放置在碑身上面,与碑身明显地区分开来。由于负重增大,要求基座面积随之扩大,以保证碑石竖立稳固,所以碑座也由长方形的石座演变成龟趺形、须弥座形等体积较大、雕刻精美的形状,现在所见历代大型碑石的碑座大多采用龟趺。”[24]129,130碑以其形制具备了一定的符号象征功能。另一方面碑身上刊刻有文字。如汉朝开始,碑用以铭功纪事。清代学者叶昌炽认为:“综而论之,立碑之例,厥有四端。一曰述德,崇圣、嘉贤,表忠、旌孝,《稚子石阙》《鲜于里门》以逮郡邑长吏之德政碑是也。一曰铭功,东巡刻石,登岱勒崇,述圣、纪功、中兴、叡德,以逮边庭诸将之纪功碑是也。一曰纪事,《灵台》经始,《斯干》落成,自庙学营缮以逮二氏之宫是也。一曰纂言,官私文书,古今格论,自朝廷涣号以逮词人之作是也。”[27]89,90叶昌炽将碑刻铭文的作用概括为述德、铭功、纪事、纂言,认为这些刻文具有保存记忆、表达纪念、歌颂德行等作用。可以说,碑在形制上,具有符号载体性质,其形状逐渐体现了一定的象征意义,碑之刻文一般由文字、图像等构成,更是文化记忆符号的重要形式。以石刻字,以碑勒铭,是试图将思想、情感、价值以不朽的方式保留下来。
中国古代的“礼”往往具有符号的意味,碑在礼制方面的规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直保留。比如:自唐代肇始,丧葬礼制对碑的使用有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唐代官方以律法形式明确了依照社会成员生前官阶高低来使用相应的碑的制式和尺寸。《唐六典》卷四所载:“五品已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高不过九尺)七品已上立碣;(圭首方趺,趺上高不过四尺)若隐沦道素,孝义著闻,虽不仕,亦立碣。”[28]这一社会成员依照等级使用相应的碑的制式和尺寸的规定为后世所沿袭。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清朝历经康雍乾三帝,经过大小无数战役,最终完成国家疆域的确定。为表彰帝国伟业,述德铭功,清代皇帝多有立碑之事。如乾隆在平定西域诸战中,1755年第一次平准战争胜利后,立《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碑》《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1757年平定阿睦尔撒纳之乱后,立《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碑》。平定大小和卓的黑水营之战后,在叶尔羌(今莎车县)立《平定回部勒铭叶尔羌碑》,之后在“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后就地立《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尔碑》。同时有清一代,碑在礼制上生发出新意。清朝皇帝在完成统一国家的重要战役后,在孔庙将武功“立碑太学、告成天下”。如在北京孔庙现存7座清代告成太学碑:《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雍正三年,1725年);《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乾隆十四年,1749年);《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年);《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四年);《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乾隆四十一年);《平定回疆剿擒逆裔告成太学碑》(道光九年,1829年)。康熙皇帝在《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中提及:“朕劳心于邦本,尝欲以文德化成天下,顾兹武略,廷臣佥谓所以建威消萌,宜昭斯绩于有永也。朕不获辞,考之《礼·王制》有曰,‘天子将出征,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兹允廷臣之请,犹礼先师以告克之遗意,而于六经之指为相符合也。”[29]康熙皇帝指出告成太学是依据《礼记》之规定,是对周代礼仪制度的还原。魏源在《圣武记》中指出:“朔漠平,至京师御门受贺,上亲撰碑铭勒石太学。古帝王武功,或命将,或亲征,惟以告于庙社,未有告先师者,在泮献馘复古制,自我圣祖始。”[30]可见立碑太学是清代皇帝宣告实现国家领土完整、大一统的重要形式。康熙皇帝立告成碑于太学的行为被雍正、乾隆皇帝所继承,并形成礼法制度。《钦定大清通礼》是于乾隆朝修纂而成的官方礼书,为官方施行礼治的依据,当中规定:“御制碑铭,勒石太学,以告成功,编次亲征方略,宣付史馆。”[31]为军礼中凯旋班师的主要仪节之一。立碑太庙与国家仪式相联系,体现了军事礼仪的重建。有学者认为:“告成碑和释奠太学的仪式出现,反映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王朝在告成礼建置上登峰造极的状态。”[32]综上可见,这些以“碑”的形式出现的文化符号便是清代以及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维护国家统一,追求大一统的最好见证之一。并且随着碑的仪礼化,其礼制作用凸显在丧葬、纪事与纪功等方面,具有规范社会成员等级、宣扬大一统政权和宣告继承正统等礼制内涵。
赵毅衡认为,“符号化,即对感知进行意义解释,是人对付经验的基本方式”[33]。碑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其实说明了“碑”演变成了符号,碑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实践中所创造形成的表达情感的符号,蕴藏、传递着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符号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记忆的另一种形式是被记忆,即作为记忆的客体或载体,比如人、事或物象,如图片、档案、物件、博物馆、仪式等,由这些可见的实体性符号来承载一段过去。”[34]44碑作为实体性符号,不仅承载了中华民族渴望建立功业,以昭万世而谋求不朽的文化记忆与民族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明秩序、彰礼仪、表正统的礼乐文明,更是在历史接连的战争征伐中被赋予中华民族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共识。因此,“碑”在符号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化为中华文化符号。
-
据《西域碑铭录》记载:“立碑铭地区涉及清及新疆21个县、市,有碑铭104通(方)。”[35]基于《历代西域诗钞》《清代西域诗辑注》《清代西域诗研究》等著作,笔者统计了出现“碑”意象的近40首清代西域诗(广义上的碑由刻石、石碣、摩崖等组成,清代西域诗人有以“碣”指代碑刻者,故“石碣”意象也在本文统计范围内),这些诗歌中出现的碑刻有《汉张骞碑》《裴岑碑》《姜行本纪功碑》《焕彩沟汉碑》《刘平国碑》《金满县残碑》《阿史那社尔纪功碑》《张孝嵩纪功碑》《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碑》《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碑》《平定回部勒铭叶尔羌碑》以及其他碑刻。以下用表 1展现清代西域诗中出现的“碑”意象:
由表 1分析可得,《裴岑碑》与《姜行本纪功碑》在本文收录的出现碑意象的清代西域诗中出现频率较高,究其缘由有两点。一是此二碑在相当长的时间段位于哈密境内的北天山(唐时称其为时罗漫山。因山顶有姜行本纪功碑,元时称其为阔舍图岭或库舍图岭,阔舍图和库舍图为蒙古语,意为碑。又因其在巴里坤之南,清人称其为南山)上的关帝庙。《裴岑碑》于雍正七年被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发现于驻地巴里坤,后移至将军府,又移至天山关帝庙。《姜行本纪功碑》在雍正十一年由岳钟琪下令移至天山关帝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二碑运输至乌鲁木齐,现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王启明认为:天山关帝庙地处的北天山(即南山)位于官方要道的必经之地,位于天山南北的重要山间捷径之中,同时也是天山北路干线的重要一环,军队、官员在调遣流动时往往经过此地[43]。同时,金峰的《清代新疆西路台站(一)》一文也表明,北天山所在的乌鲁木齐北路营塘道路是哈密至迪化(今乌鲁木齐)的交通要道。从哈密底塘经由黑帐房塘至南山口塘翻越北天山,后经羊圈沟塘、松树塘、奎苏塘至巴里坤底塘,再由苏吉塘、肋巴泉塘、务涂水塘等十余地最终达到迪化底塘[44]。
在《姜行本纪功碑》和《裴岑碑》竖立于天山关帝庙近二百余年的岁月里,翻越北天山的文人不计其数,他们在行程的必经路上目睹此二碑,自然以其入诗。如颜检在其诗作《由南山口至松树塘》、陈庭学在其诗作《自松树塘至南山口》中记载了翻越北天山途中寻访姜行本纪功碑的经过。二是清朝于乾隆二十年至乾隆二十四年相继平定天山南北,完成国家统一的大任,记载了前人功绩的《姜行本纪功碑》和《裴岑碑》为西域属于中国固有领土的实证之一。诗人历经千里来到西域,得见遗迹,怀古伤今,感慨国家统一的艰辛与边地安宁稳定的重要性的同时,更生发出建功立业的豪情,选择以碑为意象是自然之举。
本文所收录的清代西域诗中的“碑”意象,大多为西域境内所立的纪功碑与纪事碑。并且同首诗作中往往有多个碑意象出现,如李銮宣的《塞上曲六首·其二》中“谁知石烂山枯后,犹有残碑纪汉唐”[38]144,145,诗人将《姜行本纪功碑》和《裴岑碑》作为一个整体写入诗中。史善长的《到巴里坤》中“摩挲残碣在,唐汉未销兵”[38]220,也是将《姜行本纪功碑》和《裴岑碑》二碑一起入诗。萧雄的《沙南侯获碑,刘平国碑》[37]369则叙述了《焕彩沟汉碑》与《刘平国碑》两块碑刻。
此外,“碑”意象通常和天山、雪等自然意象以及军事类意象一同出现。本文收录的碑刻除不可考的外,大多立于寺庙以及山顶。如《姜行本纪功碑》《裴岑碑》立于北天山之上的关帝庙,《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碑》位于昭苏县的格登山上,《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碑》立于伊犁宁远城(今新疆伊宁)东山岗上。碑所处的客观环境使得其和自然界中的事物间存在着联系,互相映照。山脉、雪等自然景物因碑增添了历史的沧桑之感,而碑在山脉等自然景物的映衬下又得添雄壮。毕沅在《访唐侯君集纪功碑》中就记录了访姜行本纪功碑而与天山近距离接触的场景,“黄云横压天山岭,闻有丰碑留绝顶。凌兢立马驻孱颜,倾岩仄磴遮松影”[39]191。黄云横压天山,诗人被其山岩倾斜的雄壮气势和险峻征服。且西域境内多雪,天山等处时有冰雪覆盖,这也使得雪意象常常与碑意象一同出现。如方士淦《登天山绝顶》的“石有灵碑奠风雨,山留古雪守蛟龙”[36]326;毕沅《观东汉永和二年裴岑纪功碑五首·其三》的“每到雪昏风横夜,烦冤新鬼哭残碑”[39]192。此外,因碑与自然环境的贴近,故本文收录的诗作中有较多的草、木、太阳等自然类意象与“碑”意象结合,进而描写客观环境,抒发作者情感。
-
“碑”意象在清代西域诗中的集中展现,一方面传承了中华文化符号中“碑”的文化意蕴;另一方面,清代西域诗中“碑”意象之“碑”多立于中国的西域地区,从立碑时间、背景看,其宣示国家主权之意明显。可以说,西域诗中的“碑意象”自带文化内涵、情感意蕴和文化记忆三重价值。
-
“大一统”观念在中华文明历史中有重要的政治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45]有关“大一统”的概念,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为其最早出现在《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的记载中:“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46]大一统的观念很早就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比如在《诗经·小雅·北山》中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将“大一统”视为国家、民族的发展目标。清代雍正皇帝认为:“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47]消除“华夷”之别,以“大一统”为核心国家观念,也成为清代统治者广泛宣传的重要理念。
“碑者,埤也。上古帝王,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21]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立碑以铭记历史、镌刻民族记忆,之后“碑”也有了标记国家边界,指示边界走向,勘定领土,确定国家领土主权的含义。如清朝政府在平定准噶尔与大小和卓叛乱后,先后立《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碑》《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碑》《平定回部勒铭叶尔羌碑》等以宣示对西域的管辖和领土主权。有学者提出清代皇帝通过下令在全国的官学内修建平定西域所立的纪功碑,如《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等碑刻,打造了一个覆盖全国的“宣传攻略”[48]。这个“宣传攻略”使得当时的士人们将现实中的西域与历史记忆和文学记忆中的汉唐西域联系起来,巩固了西域是中华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认知,是国家层面对大一统观念的再次强化。
清代西域诗中的“碑”意象也传达出士人意识中的“大一统”观念。如岳钟琪《天山》中写道,“偶立崇椒望,天山中外分。玉门千里月,盐泽一川云。峭壁遗唐篆,残碑纪汉军。未穷临眺意,大雪集征裙”[36]4。此诗写于诗人受命为宁远大将军前往新疆征讨准噶尔部时,诗人领军在巴里坤修建东西两城,囤积粮草,准备兵员,在当地发现了《裴岑碑》。在诗中诗人以《姜行本纪功碑》和《裴岑碑》所载的古人平定西域,统一河山的丰功伟绩激励自己,裴岑碑碑文“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艾安”一定引发了诗人内心共鸣,诗人身处边陲,整军待发,渴望能立军功,再现汉唐时期的西域盛况。曹麟开的《塞上竹枝词三十首·其一》:“永和贞观碣重重,博望残碑碧藓封。何似御铭平准绩,风云长护格登峰”[36]85,诗人连用《裴岑碑》《姜行本纪功碑》《汉张骞碑》《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碑》等四碑意象,将西域一千六百余年的历史串连起来,歌颂乾隆平定准噶尔的功绩,抒发了对国家统一由衷的自豪与喜悦之情。王曾翼的《回疆杂咏三十首选十·其五》是其探访小和卓霍集占旧巢时所写,“霍占巢穴剩荒基,断础零砖拾烬遗。扫荡凶氛归化宇,卿云长护御书碑”[36]137,诗人在诗中歌颂了乾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给当地民众带来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并希望“卿云”这一祥瑞能长久庇护树立《平定回部勒铭叶尔羌碑》的西域土地。
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清代西域诗人笔下,“碑”意象是自古以来中国对西域主权的强有力宣示的标志之一,西域诗中的“碑”意象蕴含着中华文化中的大一统观念。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49]。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现为国家认同,站在国家认同的高度领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增进民众的国家认同与国家自豪感,并且能提高民众维护国家统一的意识[50]。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面对外来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清政府节节败退,最终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华儿女受此屈辱,无不义愤填膺,鸦片战争结束后毓书任乌鲁木齐都统时写下《天山碑》,便是借助“碑”意象,表达了诗人反抗殖民势力,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嶻嶪丰碑纪有唐,当年君集破高昌。刀烧枉自夸寒热,日月旋看化雪霜。百载封圻空叹麴,千秋文笔却推姜。只今过客徘徊处,古迹依稀认战场”[36]389。诗中首联中的“丰碑”为《姜行本纪功碑》,是为纪念唐军平定高昌而立。诗中借用了《新唐书》中所载典故:“高昌不臣,拜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出讨。王麴文泰笑曰,‘唐去我七千里,碛卤二千里无水草,冬风裂肌,夏风如焚,行贾至者百之一,安能致大兵乎?使能顿吾城下一再旬,食尽当溃,吾且系而虏之。’”[51]3826和《新唐书》中所载当时高昌国的童谣:“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几何自殄灭。”[51]6222诗人以唐代侯君集破高昌的历史事件,以唐碑所载史实对照鸦片战争战败的屈辱,传达出维护国家统一的强烈爱国主义情感,以及殖民者分裂我边疆的图谋就像日月照耀下的雪霜那样终将破灭。
清代西域诗人还通过诗作中的“碑”意象表达了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如和瑛的《题巴里坤南山唐碑》:“库舍图岭天关壮,沙陀瀚海南北障。七十二盘转翠螺,马首车轮顶踵望。高昌昔并两车师,五世百年名号妄。雉伏于蒿鼠噍穴,骄而无礼不知量。寒风如刀热如烧,易而无备胥沦丧。贤哉柱国侯将军,王师堂堂革而当。吁嗟韩碑已仆段碑残,犹有姜碑勒青嶂。岂知日月霜雪今一家,俯仰骞岑共惆怅。”[40]诗人回顾了唐军平定高昌的历史往事,千年之后,英雄已逝,而唐碑依旧,在《姜行本纪功碑》的见证下,西域已从麴文泰口中的“寒风如刀热如烧”变为“日月霜雪今一家”,变化的不仅仅是自然景观与自然条件,更大的变化是西域地区各民族“今一家”的融合,这样的民族融合景象应该是前人所没有想到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52]“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保家卫国的“共同历史记忆”。清代西域边陲屡次发生叛乱,在维护西域稳定、国家统一的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不计其数。乾隆朝为表彰功臣,围绕“十全武功”曾四次绘制功臣像,共计280幅,其中统一西域功臣一百位,他们有的是满族、蒙古族、汉族、回族,有的属于厄鲁特部、回部等,清代为平定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叛乱所立的系列纪功碑便是由无数将士的鲜血染成,它们见证了中华民族为维护领土完整不怕牺牲,战胜分裂势力的历史。清代西域诗人也以碑为意象展开联想,书写了中华民族为国家统一所做的不懈努力。如曹麟开的《伊犁四首·其四》:“铭勋宸翰矗穹碑,立国乌孙认旧基。丽水源穿星宿出,格登峰作阵屏垂。汗封昧蔡徕天马,穴扫呼韩抵谷蠡。班鄂忠贞千古在,晴香风雨闪灵旗。”[37]257诗歌先回顾了乾隆首平准噶尔部,清军活捉其首领达瓦齐,乾隆亲笔为《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碑》撰写碑文的历史。后半部分借汉代常惠出击匈奴之典故,写清军征讨叛军阿睦尔撒纳,“班鄂”分别指在这次平叛中殉国的蒙古族将领班第和满族将领鄂容安等英雄。诗人以“碑”意象为想象的载体,表达了对领土统一的歌颂以及对殉难烈士的追怀,蕴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记忆。
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是由“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与“共同未来”联结起来的民族共同体[53]。中华民族在形成的过程中历经了大大小小的战争和灾难。上述清代西域诗人们对维护国家统一而牺牲的将领们多有感叹和悼念,“碑”意象凝聚了中华民族在西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历史记忆”。清代在各地官学中所立的太学碑、西域境内的纪功碑、清代西域诗中的“碑”意象共同组成了一个“记忆场”,形成了中华民族内在的心理归属和群体意识,“并在这个群体中学习、记忆、共享一种文化”[54]。
-
文化记忆“包含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其‘教化’作用服务于稳定和传达那个社会的自我形象”[55]。集体中的相关成员通过文化记忆,能够确定自我的形象,了解自己和外界成员的差异。文化记忆依赖于一定的载体实现,如碑、图片、象征物、博物馆等。清代西域诗中的“碑”意象作为中华文化符号,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
清代西域诗人根据历史上西域发生的战事,“写成”了有关碑符号的记忆文本,如李銮宣《巴里坤城北寻汉永和二年碑》:“竟断匈奴臂,穹碑勒此间。星弧弯夜月,铁马驻天山。斩馘诛呼衍,全师入汉关。至今扪古碣,血渍土花斑。”[38]149《裴岑碑》本是敦煌太守裴岑斩杀呼衍王后为纪念此次军事胜利而立,在千年后的诗人看来其更凝聚着征讨民族分裂势力,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记忆。前文中所述的王曾翼、和瑛、曹麟开等诗人,也是在一睹《平定回部勒铭叶尔羌碑》《姜行本纪功碑》《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碑》等碑刻后,用“碑”意象表达对国家大一统的歌颂。
“文化记忆被特定场域、特定主体激活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被特定权力主体所重构的过程。”[56]文化记忆借助文化符号等载体得以再现、传承和延续,在对由文化符号所构成的文化记忆进行解码解读时,也必将伴随着重构。
《姜行本纪功碑》在清代西域时人眼中充满着灵异,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道:“守将砌以砖石,不使人读,云读之则风雪立至,屡试皆不爽。”[57]清代诗人对此多有提及,如萧雄的《天山碑》:“丰功又见大唐年,赑屃高擎峻岭巅。却怪登临刚剔藓,读来风雪忽漫天。”[37]369诗人刚剔除掉碑刻上的苔藓,读了碑文后突然风雪大作。方希孟也在《度天山》中说道:“摩挲问碑碣,风雨恐来攻。”[36]433似乎只要和《姜行本纪功碑》有过言语交流,便会立刻招来风雨。毕沅在《访唐侯君集纪功碑》也提及《姜行本纪功碑》的灵异之处,“碑文特恶游人读,读则风雪随飞腾。……纪功垂远一例耳,奚为此石能通灵”[39]191。可见清人在对碑进行解码阐释时,也融入了新激活而建构的不能阅读《姜行本纪功碑》,否则顷刻风雪交加的记忆。
“记忆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谁在记忆’、‘记忆什么’以及‘如何记忆’或‘记忆如何可能’三个问题。”[34]40“谁在记忆”与“记忆什么”分别为记忆的主体与客体,“如何记忆”是前两者得以实现联系的媒介,即本文所述以“碑”意象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符号。“借助文化记忆,一个集体的成员建立并培养共同的身份和归属感”[58],各民族在由“碑”意象等中华文化符号为载体而构成的文化记忆中,就“谁在记忆”即“我是谁”和“记忆什么”取得共识。
一. 清代西域诗中的“碑”意象蕴含着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
二. 清代西域诗中的“碑”意象集中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意识,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
三. 清代西域诗中的“碑”意象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
-
作为中华文化符号的“碑”意象最初的作用是纪功留名,以昭万世,在历史的发展中其内涵不断升华,最终呈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与文化联系的纽带。清代西域诗歌中的“碑”意象鲜明展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质,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对大一统的追求,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意识,折射出中华民族由“自在”向“自觉”民族实体转变的历程。以“碑”意象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符号承载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记忆,构建起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精神认同空间,将中华民族这一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连接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处在这个文化符号共同体内的成员共享着一种相同的价值规范与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由此得以越发凝聚、牢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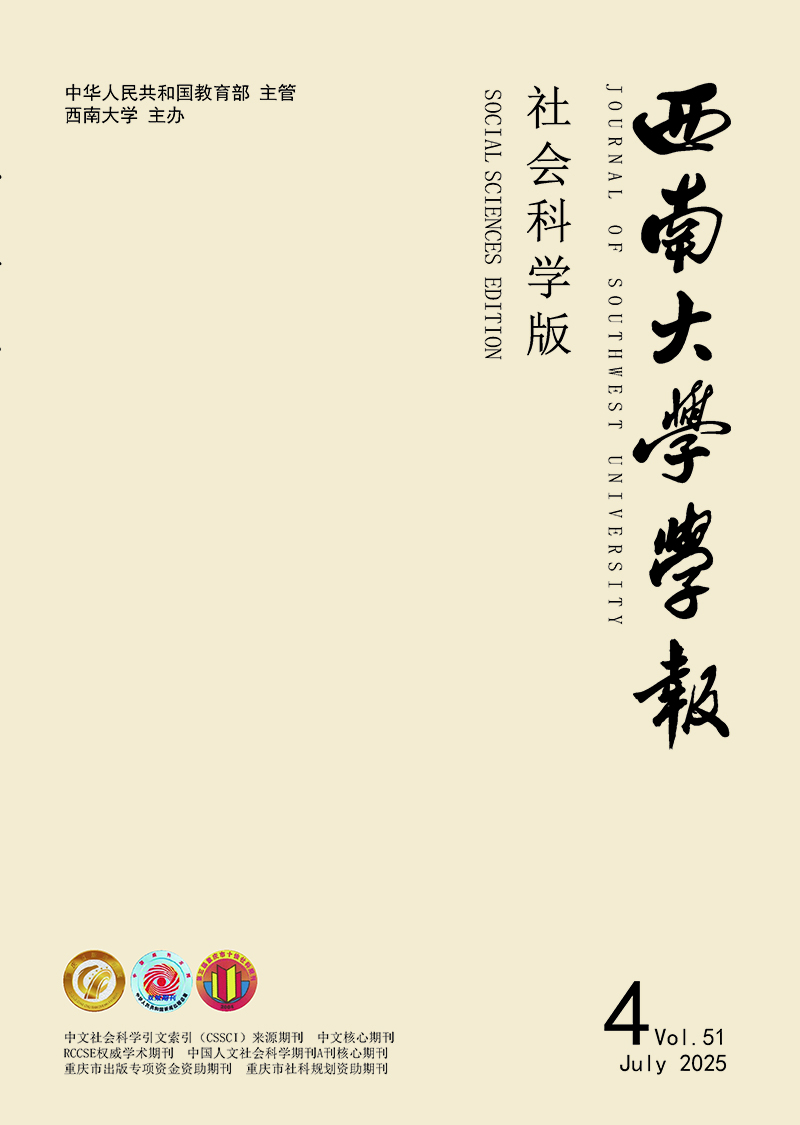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