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ML
-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本质上是一种间接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奴役关系下的直接奴隶制的混杂编码。”[1]如若传统意义上的殖民主义是“民族性的自然外溢”[2],脱胎于工业革命与资本勃兴的接榫,那么现代维度上的数字殖民则形塑于数字化革命与信息技术的同构。数字帝国借助数字技术延展的泛在性正在“吞噬这个世界”[3],垄断地占有全球数字空间,以“无所不在的、渗透到一切生存领域中的、总体性的、内在的”[4]隐性意识形态操纵和价值观侵蚀,构建了“不平等与以强凌弱”[5]的数字殖民体系。那么,数字殖民何以生成?实质指向何在?数字殖民与意识形态风险何以耦合?数字殖民以何开展意识形态渗透?如何破解数字殖民的意识形态渗透?应答这些问题既是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和巩固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需要,也是抵制数字帝国“数字霸权”压迫、防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使命。
“数字殖民”这一概念由英国学者吉姆·撒切尔(JimThatcher)在《通过剥夺积累的数字殖民:日常数据的新隐喻》一文中率先提出,但是撒切尔并未从新的观念框架层面阐释数字殖民,而仅将其视为“理解数据在社会中角色转换的隐喻”[6]。反之,英国社会学家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和美国学者乌利塞斯·梅加斯(Ulises Mejias),则认为“数字殖民不只是解读数据的意象隐喻,也并非传统殖民主义的简单延续”[7],而是将殖民主义的掠夺性剥削做法与计算机的抽象量化方法结合的新型殖民形式,其核心是通过侵占数据资源而攫取利益和控制人类生活。在《连接的代价:数据如何殖民人类生活并促使其为资本主义所占有》一书中,库尔德利与梅加斯以数据为切入点,围绕数据掠夺、数据关系、数据导向逻辑等内容,系统阐释了数字殖民的理论框架[8],开拓了殖民理论研究的数字化视野。数字殖民理论自提出之后,便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相较于库尔德利与梅加斯聚焦于数字日常生活殖民化的研究,迈克尔·奎特(Michael Kwet)则侧重于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在知识产权、国际产业链、全球监控和政治权力等国际问题方面,批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施行技术入侵和数字资本输出的殖民行径[9]。莫妮克·曼(Monique Mann)也在考察分析澳大利亚的信息帝国主义和数字殖民案例基础上,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以轴辐式小多边联盟的形式,构建辐射全球的数字殖民监视体系,实现对数据、知识、情报等资源的掠夺[10]。与此同时,芒福德(Densua Mumford)[11]、柯扎逊(Stefano Calzati)[12]和赛古拉德(Maria Soledad Segura)[13]等学者,也深刻批判了数字帝国依托技术入侵,进行劫掠财富、攫取资源和奴役数众的殖民行径,还就数字殖民的形成前提、解释范围和理论运用等方面展开了系统研究。
国内学者承续西方学界的研究,对数字殖民的探讨形成了三种学术进路。一是立足政治经济学视域。熊治东等从分析信息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生产与剥削方式的影响出发,在剖析数字殖民的本质、运行逻辑和基本形态的基础上,批判了数字殖民诱发的数字劳动剥削、数字收益不均和数字拜物教盛行等社会问题[14]。二是立足数字生命政治学视域。受福柯(Michel Foucault)生命政治理论的启发,蓝江围绕数字帝国殖民统治下的数字生命政治学,批判了被资本殖民化的数字平台将现实的人转化为档案化的“数字生命”所带来的新异化[15]。三是立足比较研究视域。肖峰等从概念辨析维度切入,廓清了数字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旧殖民主义等相关概念的异同,并指出数字殖民独有的叙事范式在于运用“数字化能力”,建构以垄断数据为核心的资本积累方式[16]。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结合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将殖民理论迁徙至数字化的语境之下予以探讨,进一步阐释了数字帝国殖民统治的新现象、新问题,为我们深入审思数字殖民的构序逻辑、衍生风险和破解之道等,提供了思想资源。然而,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应被聚焦审视却未被系统明辨的问题。其一,数字殖民的生成机理这一前置性问题还缺乏深入的逻辑阐释。其二,数字殖民在“物的掠夺”和“人的奴役”过程中如何进行“技术化遮蔽”,有待进一步开拓补充。其三,对数字殖民的研究多从数字技术与资本联袂的批判视角展开,在一定程度上隐遁了对数字技术运用的社会主义属性考察,且在如何打破数字帝国殖民霸权、实现世界平等的“数字化繁荣”与彰显社会主义数字文明的优越性方面仍需持续深耕。与此同时,数字殖民统治的显著范式在于借助数字技术延展的“泛在性”,施展隐性意识形态渗透,以维存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秩序,但是既有研究却鲜有将数字殖民置于意识形态的视野,探讨其带来的思想渗透、价值侵蚀和精神控制。因此,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以数字殖民为研究对象,从意识形态视角切入,旨在厘清数字殖民的生成机理与实质的基础上,窥探数字殖民与意识形态风险的耦合逻辑,洞悉数字殖民从“生产”运作到“消费”的意识形态渗透逻辑,进而解蔽数字殖民布展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迷障,为抵制数字帝国殖民压迫和推进数字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寻觅可能路径。
-
数字技术与殖民主义的联袂,解构了传统殖民活动野蛮的暴力压迫,转而构建了数字帝国隐而不宣的“幽灵般的统治”,以技术理性的面貌炮制了具有无形操控性的“数字霸权”,使得数字生命的维持成为“权力追逐的猎物”。显然,只有对何谓“数字殖民”有高度的认识自觉,才会有如何应对“数字殖民”的实践自觉。缕析“数字殖民”的生成脉络、揭示其实质,是理性应对其挑战的必要前提。
-
资本主义殖民史是一部满载血泪印记的掠夺史,展示的是“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17]861-862,“殖民扩张式文化”自西方文明形成之初就印刻在其生命基因之中。在西方文明萌芽的古希腊时期便有殖民的传统,面对城邦战乱中衍生的资源短缺危机,古希腊帝国将殖民触角伸向地中海、黑海和北非沿岸,劫掠财富、攫取资源,使“土著民”沦为奴隶制下“有生命的工具”。古希腊帝国“唯我”“唯利”的精神内核,内生出单赢、侵占和暴力,异化为“野蛮”,演变为以“恶”护“恶”,最终形成“外侵—征服—掠夺”的殖民思路,这也是后世西方殖民主义的思想雏形。
15世纪末,伴随新航路的开辟,“资本的贪欲”驱使殖民主义冲破了洲际的边界,“美洲的发现”和矿物宝藏的输入为资本原始积累创造了充分条件,人为接种的“过时”奴隶制成为当时欧洲“现代工业的枢纽”。马克思精辟地概括了这一时期的殖民现象,“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17]860-861,这段殖民史是建立在“文明”对“野蛮”的故意倒错之上,发生在野蛮掠夺、奴役盘剥和血腥杀戮的历程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这时殖民政策导致了几乎整个地球的瓜分”[18],物理空间的世界范围已无地遁逃帝国主义的势力,垄断与暴力成为帝国主义世界历史的核心构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深陷剥削、奴役和战争的祸结衅深漩涡。二战后,随着世界反帝反殖民运动的风起云涌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以“硬实力”军事侵占为手段的传统殖民秩序日渐土崩瓦解。然而,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放弃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殖民行径,反而以更加隐蔽的政治操纵、文化输送、价值重塑、媒介控制等方式对落后国家进行“软殖民”,由此“新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应运而生。
20世纪90年代以降,数字技术和信息网络浪潮席卷全球,当人们沉浸在技术革命“精心炮制的神话”时,数字技术却与殖民主义邪恶联姻,转而成为超地域权力构镜的隐蔽统治形式——数字殖民。在数字技术全面入侵日常生活的背景下,数字帝国依托技术垄断形成“数字霸权”,以“技术逻辑”为支撑展开隐性意识形态操纵和价值观侵蚀的殖民统治,从而实现持续性的数据资源掠夺、数字劳动奴役和数字资本增殖的过程,就是数字殖民。数字殖民的生成遵循着资本增殖、空间拓展和技术垄断的逻辑主线,这三条逻辑具有殊途同归的共契性,耦合演绎了数字时代殖民主义变奏曲。其一,资本增殖的内生逻辑。作为数字资本主义“衍生品”的数字殖民,其仍囿于资本的逐利本性,仍将持续性攫取剩余价值作为运转轴心。诚如,马克思所指,“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17]269,数字技术只是掩盖殖民逻辑剥削性和压迫性的遮羞布,即以“工具性合理”表征的外延形式来虚饰殖民本身“无度盘剥”的内在规定。其二,空间拓展的外扩逻辑。当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被工业资本盘剥殆尽之后,资产阶级的殖民统治便挣脱了自然地理边界的枷锁,以占领“控制数字生活世界的数字平台”为殖民疆域的“滩头阵地”。在数字帝国贪婪性的驱使下,数字技术“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17]699,业已把不断打破空间界限内置于心,殖民主义借助技术逻辑获得了体系化扩张力量,呈现为凡是数字科技所到之处,则为殖民掠夺必达之地。其三,技术垄断的权力逻辑。数字殖民的生成“依赖于从技术上将资本霸权运行于其中的整个社会关系领域进行重新建构”[19],具象为数字帝国依托技术垄断而构造了操控数字社会的“‘内面’的权力方式”[20]。换言之,技术(机器)“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21]198,在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有机接榫下,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与社会权力结构融为一体的自主性权力谱系,并逐渐固化为数字殖民支配人和统治人的权力载体。
-
数字殖民是大数据时代以数字技术垄断为核心的新型殖民形态。从数字殖民的实质寓目,它仍是通过对“物的掠夺”和对“人的奴役”而实现“资本增殖”的殖民行径,其“殖民芯”并未改变,仅在大数据时代换上了“新衣”。囿于数字技术对殖民过程中统摄、剥削和规训等环节的“技术化遮蔽”,故而对数字殖民实质的剖释,即是对这种遮蔽的有效“解蔽”。
-
数字殖民的实质依然是对“物的掠夺”。较之掠夺土地资源、生产原料和矿物宝藏等实体物质资源的殖民前史,数字殖民依然承续了“掠夺性积累”的殖民路线,将对实物的掠夺转向对抽象的数据资源的剥夺性占有。数据作为当代资本主义新的“特殊的以太”与“普照的光”,是“一种被提取、被精炼并以各种方式被使用的物质”[22],具有无限复制、重复利用的禀赋,被当成拥有持续积累和不断增殖能力的“物神”。人类数字化生存衍生的海量数据,早已被数字帝国垂涎和觊觎,从仅仅对“就在那里”的数据进行“地理大发现”,迅速过渡到资本的“主动作为”,数字帝国凭借技术垄断和数据圈地构建了一套聚敛数据资源的数字专制体系,将非结构性的基础性数据、内容性数据和过程性数据等“原始数据”标准化加工为“衍生数据”的“堆栈”,使得无论是“一般数据”还是“剩余数据”都成为了具有垄断权力的私有财产。为了实现数字殖民对数据资源侵吞的长期化和稳固化,数字帝国造就了隐身于服务器之中、表象在智能屏幕之上的“数据的提取装置”——数字平台。数字平台通过“电子订阅服务模式+终端用户许可协议”的授权,改写了数据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化身为“数据利维坦”,主宰着数字生产、数字分配、数字交换、数字消费等环节中的“数据他者”,在数字资本的积累过程中真正实现了对数据资源的掌控权。
-
数字殖民的实质依然是对“人的奴役”。“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21]188,呈现出“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17]743的颠倒情形。诚如,福克斯所说:“数字劳动与古典奴隶制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工作是无偿的,而且被高度剥削。”[23]换言之,数字技术的进步并未带来世界平等的“数字化繁荣”与人的自由解放,反而成为资本对劳动者的生命活动进行时空压缩的利器,使人们深陷数字化的“窠臼”,不仅肉体被剥削,思想亦被规训,在此“数字奴隶制”应世出场。一方面,是人的肉体受数字技术“摆置”。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人们受“半资产者”的监视被迫在标准化、批量化、垂直一体化的“血汗工厂”从事固定工作时间的体力劳动,时下数字劳动呈现为一种“弹性雇佣—诱导生产—数字监控”的全时段、全领域无限剥削,从上班的打卡报到和实时定位监视,到下班后智能手机的信息轰炸和时刻待命,人们工作与生活时间被混淆和模糊,在隐匿化的强制性数字劳动中献祭了自己的身体,成为资本主义祭坛上为资产阶级不断盘剥和榨取巨额利润的燔祭。另一方面,是人的精神受数字技术“促逼”。数字殖民的隐性规约对人的自由精神展现出一种解构、消解的态势,其核心旨趣在于通过数据系统这一“强有力的统治工具”[24]8深度操控人的意识,培植主动臣服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奴隶和附庸。高强度的数据信息轰炸将人们圈禁在数字帝国编织的“数字茧房”之中,成为无法抛弃数字社交平台的“囚徒”,人们的文化观念和思想理念被算法劫持,反抗意识和批判精神被降解,形成“默认的普遍意识”,从而沦为丧失独立性和思考性的“乌合群众”,最终深陷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座架”之中。
-
数字殖民的终极目的依然是“增殖”。服膺于数字帝国利益、服务于资产阶级统治、服从于数字资本逐利是贯穿剥夺性占有数据资源和全方位操控数字奴隶的根本原则。在数智革命编织的“自由、个性”的意识形态幻象下,数字帝国以“连接”为旗帜,布展了“中心—边缘”国家、“现实—虚拟”世界的数字殖民统治架构,形成了“原始数据—加工数据—数字商品—数字资本”的价值资源转化产业链,打造了俯视整个全球的猎取剩余价值的有效场域。数字技术与殖民主义的暧昧缠结,使得当代资本主义殖民者将数字技术迭代的力量纳为己用,以数字技术为“利器”遮蔽了“资本—国家”这组革命对象,掩盖了“资本—劳动”这对剥削关系,将对剩余价值的侵吞隐匿在数字算法建模之下。较之历史上充斥着血腥和暴力的殖民行径,数字殖民具有“悬置传统秩序”的意向,利用意识形态正面叙事,将人们的情感、意志和精神置于偏颇不易察觉的虚拟“真实”之中,以更加隐晦、低调、间接的“文明”方式,将数字资本的增殖机制美化得理所当然,使人们在悄无声息之中“心甘情愿”地成为资本增殖的俘虏,沦为丧失革命性和批判性的“提线木偶”。质言之,作为殖民主义数字化、信息化延展的数字殖民,虽然是“数字资本逻辑”的现实性彰显,但其仍受资产阶级昼夜不息地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最大化的本性所驱使。
一. 数字殖民的演进历程:从“殖民”到“数字殖民”的生成机理
二. 数字殖民的实质:数据资源掠夺—数字劳动奴役—数字资本增殖
1. 数据资源掠夺
2. 数字劳动奴役
3. 数字资本增殖
-
数字殖民作为数字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统治的新形式,受谋求资本增殖与扩展政治权力的运行逻辑支配,以“技术逻辑”为支撑与意识形态耦合,通过数字垄断催生“算法异化”、数字监视造就“共景监狱”、数字成瘾引致“精神空场”等方式诱发意识形态风险的产生。
-
万物互联、万物感知、万物智能皆以算法连接,算法控制的产生源于数字技术的垄断资本主义应用,在数字帝国的控制下,算法作为一种资本化的技术权力渗透在社会结构之中,成为社会生活的“架构”,以一种抽象的支配与控制力量,隐蔽而巧妙地施展着其意识形态功能。诚如马克思所指,“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17]508,即“算法异化”不在于算法本身,而在于算法的资本主义应用,在于算法成为被资本殖民化的数据平台用来牟利和控制主体的意识形态工具。“算法异化”呈现为技术理性优于价值理性、市场逻辑先于管理逻辑、利益原则驱逐道义原则,所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植根于经济、发端于思想、发酵于舆论、显现于政治。其一,技术理性优于价值理性。在哈贝马斯看来,“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25]39算法在设计之初就被作为技术架构的工艺装置嵌入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框架之中,并借助技术的“伪中立性”,不断强化资本主义的话语叙事和信息猎获。算法作为资本增殖逻辑的技术载体,将“信息茧房”转化为“价值茧房”,构造了“分节式、阶式化”的“偏见共同体”,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可见空间“被压缩”、议题设置“被悬浮”、话语叙事“被边缘”和价值引领“被弱化”。其二,市场逻辑先于管理逻辑。算法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在信息分类、数据取舍、模型构建、结果输出等过程中往往会以低俗化、庸俗化、媚俗化等内容“取悦”用户,而自动屏蔽具有崇高性、严肃性和学理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从而形成资源配置的市场逻辑优先于秩序构建的管理逻辑局面。其三,利益原则驱逐道义原则。正如,马克思所言,“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26]580。算法内在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尺度,决定了其服膺于资本主义国家利益、服务于资本增殖逻辑前提。基于经济利益的运行逻辑,使得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的内容成为算法推荐首选,蔑视理想、耻言道德、逃避崇高等极度追求物欲享受的信息占据用户“视听”世界,而科学、客观、理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却被遮蔽。
-
数字殖民的权力逻辑驱使“资本瞳仁”始终全景窥伺“数字囚徒”。“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24]9,技术力量成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数字帝国凭借数字监视实现了对人类社会的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的隐性控制,使数字空间变为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驱役的新殖民地、成为完全裸露于数字技术布控之下的“超级全景监狱”。诚如,韩炳哲所言,“数字的监控社会有着一种特殊的全景监狱式的结构”[27],是精神政治意义上的透明社会,并以幽灵般的精神权力实现了对主体的意识形态规训。一方面,数字帝国创设横亘国与国之间的“全景监狱”以实现“信息殖民”与“价值入侵”。数字帝国将数字技术优势转化为强大的意识形态攻势,通过政治操纵、文化渗透、媒介控制、价值重塑等方式进行“软殖民”,迫使诸多国家将资本主义理念、制度和道路奉为圭臬,最终在“和平演变”中丧失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在平台资本主义垄断的数字生态下,数字帝国透过“数字监视”洞察着数字空间的信息流向,并精准创设“全景监狱”,排挤、压缩和围剿一切异己思想,并将合乎其政治观、民主观、价值观、生活观的意识形态进行“靶向投射”,从而不断排挤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致使主流意识形态难以形成规模化的聚合效应。另一方面,数字帝国创设横亘人与人之间的“全景监狱”以实现精神殖民。数字帝国借助数字监视读懂并且控制人们的思想,进而对人们的情绪、情感、欲望等感性内容进行把控与调动,持续让空心化的数据洪流滋扰数字个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使个体的人从单纯的数字化生存的主体转变为数字化殖民的对象。圈禁于数字帝国布控的“全景监狱”之中的数字个体宛如置身在信息区隔和观念封闭的“孤岛”,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空间之外,时时刻刻戴着“数字镣铐”,其所思、所想、所言皆无法摆脱数字技术的监视,在不自觉中接受负面思潮的“喂养”、遭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询唤”,最终陷入认知视野被固化、理性思考被弱化、价值偏好被异化的境地,如同浮士德一般灵魂被掏空,承担精神异化之痛,仅留下被数字流量所监控的“数据躯壳”,成为资产阶级“精神殖民”的猎物。
-
“数字时代的环境和氛围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容易叫人上瘾”[28]3,数字帝国利用数字技术设计致瘾机制,布展着资本意识形态的无形权力,将“数字”转变为统治人的新力量,让数字个体只能在“倒立着的世界”[29]940徘徊,被迫接受数字资本权力的宰制。数字平台精确地释放着各类感官刺激和认知刺激——反复的、高强度的、交互式的文字、图像、视频等信息,采用无限刷新、界面操纵、滚动播放、极端推送等成瘾性技术对人们加以“屏幕控制”,使人们沉溺于数字资本所缔造的意识形态景观之中,陷入“前所未有”的精神空虚、异化与痛苦之困境。其一,数字成瘾带来认知窄化。诚如马尔库塞所言,人们难以区分传播媒介是“新闻与娱乐的工具”还是“灌输与操纵力量”[24]9。在数字媒介营造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单向度的“感官盛宴”之下,人们极易陷入“瘾性沉迷”而欲罢不能,沦为受数字资本与技术宰制的无意识俘虏,致使理性思考逐渐被非理性的感官愉悦左右,批判能力被精神快感蚕食,价值判断被思维惰性磨损,从而导致人们的认知发生偏差、精神空虚不断加深。其二,数字成瘾招致价值分化。数字致瘾机制与传统的药品成瘾机制不同,“不是直接把化学物质注入身体,但它们产生的效果相同——因为它们吸引力强,设计得当”[28]4。在对数字个体的价值形塑过程中,数字帝国隐藏着一套精心设计的“致瘾流程”,“透过散布‘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合法化既存体系”[30],促使数字个体迷失在西方价值观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所制造的意识形态幻象中,陷入与主流意识形态区隔的孤岛,其自主意识、价值选择等主体能动性皆在潜移默化中被数字资本钳制、操纵和支配。其三,数字成瘾造成精神异化。在资本逻辑的精心运作下,数字成瘾机制成为一种软性的“精神力量”,成为凝聚主流意识形态共识与引导人们精神世界良序的阻碍,它将人的生命、生活、情感、行为等一切社会性活动进行数字化重构,使得在现实意义上“社会关系的总和”[31]501转变为以数字为“中介”的新型的社会关系网络,人就此沦为数字的存在物、接受数字“摆置”,承受精神异化之痛。
一. 数字垄断内隐“算法异化”:遮蔽主流意识形态客观呈现的风险
二. 数字监视造就“全景监狱”:排挤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空间的风险
三. 数字成瘾引致“精神空场”:扰乱主流意识形态凝聚效力的风险
-
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行径主要表现为隐蔽而巧妙地施展意识形态渗透。基于从“生产”到“消费”布展的渗透逻辑,数字殖民以“颠倒观念”牧领、“编码构镜”虚饰、“软性叙事”侵蚀、“虚假需求”钳制等手段展开意识形态渗透。
-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29]940,在意识形态层面表现为“观念的错位”,并以“颠倒的世界意识”对“颠倒的世界”本身进行虚假重构和精神规训,使得所缔造的意识形态幻象已经成为无时无处不在的科学管理和牧领性治安。数字空间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所具有的蛊惑性,不仅表现为以普遍理性和公义之名进行“塑造认知-灌输观念-建构认同”的软殖民,还呈现在依托数字技术进行“僭越-拟真-划界”的意识形态生产所形成的“先验的结构”。一是生产文字内容堆砌“数字景观”。数字空间文字内容的生产依赖于符码编织和意义建构,在资本逻辑的宰制性支配下“意义内容有某种程度的固定,并使象征形式有某种程度的再生产”[32]14,构成具有政治性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景观。景观是当代资本主义合法性的“永久在场”,在现实性上文化景观是一种拥有真正的“催眠行为”和刺激力量的意识形态,资本家依靠控制景观的生成和变换来操纵整个社会生活。二是生产图像内容展开“视觉殖民”。诚如,贝尔(Daniel Bell)所指,“当代文化已渐渐成为视觉文化”[33]。视觉技术帮助数字个体从图像体认世界,在此基础上“世界被把握为图像”,衍生出西方意识形态视觉化统治。“图像把抽象的思想变为感性的材料,使概念动人心弦,令原则生机勃勃”[34],使大众在接受视觉符号的阐释过程中,潜在地遭遇图像的视觉化渗透和意识形态质询。数字帝国依托视觉感知技术,形塑了人们的视觉偏好、视觉经验和视觉体验的数字化症候,又赋予了电影、电视、广告、微视频、表情包等图像的美学性视觉符码,使人们被现实生活的“视觉幻象”包围和规训,而成为“视觉殖民”的俘虏。三是生产体验内容进行“具身控制”。在数字技术打造的“拟态环境”“超现实”空间中,数字个体能够实时操控数字分身,即时获得听觉、视觉和触觉的沉浸式数实交融的“具身”体验。譬如,数字帝国生产的电子游戏就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叙事,其指令结构象征着规训和编码。电子游戏通过环境渲染、场景设定、角色扮演等沉浸式“具身”体验,实现了对玩家的社会想象和意识形态进行塑造和影响,使其在不自觉中被游戏所隐含的极端个人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虚假普世主义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侵蚀。
-
在数字殖民统治下,我们看不到“身处鲜活世界的生命”,而是一个个被数字控制的灵魂。在此境遇下,数字帝国的数字化重构使“肉体人”转为“数字人”,进而衍生出“数字化生存”,使得人们社会生活每一方面都被仔细测量,心理状态、情绪状况、欲望需求等皆被窥探得一览无余。与之联袂而行的是,数字化调节意识形态的分配过程就是熔铸数字个体思想灵魂的过程,数字帝国借助编码机制和意识形态构镜塑造了整个言论和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领域,构建了编码规则要素及媒介技术操作的赝象,抢占了数字空间意识形态的分配权,将数字个体有限的注意力时间与“维存资本意志”的内容精准适配,导致精准推送的技术逻辑转变为曲意逢迎的意识形态渗透逻辑。一是锁定数字精英。普热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指出,一个国家或政权的更迭往往肇始于精英内部的分裂[35]。在数字霸权肆虐、“数字鸿沟”加剧的数字殖民统治下,“社会成员将被撕裂为1%的数字精英与99%的‘无用阶级’”[36]。因此,俘获数字精英,对其进行政治蛊惑、舆论洗脑和价值形塑成为数字帝国信息分配结构的“优先级高”。二是指向青年群体。青年正处于价值认知体系形成的“灌浆期”,政治辨别力和价值判断力较弱。“政治与掌握可见性的技巧密不可分”[32]18,数字帝国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造就成不容辩驳的既存秩序的先知,衍化为“完美程式”,通过垄断数字分配权操纵信息的“可见性”和“不可见性”,将青年圈禁于契合资本逻辑价值取向的“信息茧房”,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使其陷入价值困惑和精神纠葛的漩涡。三是瞄准异见人士。“和平演变”在于从意志操控和精神控制上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而“异见人士”极易被笼络、煽动,是数字帝国“撬开”目标国家变革之门、实现“不战而胜”的关键力量。数字帝国利用数字控制这“一种新的、重要的分配正义机制”[37],对各国“异见人士”进行精准的意识形态“投喂”,将他们豢养为“第五纵队”“网络水军”,培植为数字帝国的“利益代理人”和资本主义文化圈层忠实的信徒。
-
若要“使得控制关系合法化的逻辑真正要行之有效,就必须保持在隐藏状态”[38]。数字帝国借助数字技术延展的“泛在性”,构建了数字交互空间的“幽灵般统治”,将直接的政治压迫转变为无所不在的隐性意识形态侵蚀,在“无意识”的氛围中维存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价值秩序。一是以“制脑权”的争夺潜隐于数字交互的军事领域。物质力量无法触及之地,是意识形态开展掠夺的精神场域。数字帝国与“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26]34旧本体论殖民主义相剥离,凭借科技实力和传媒优势“在思想、理念、语言和生活方式上具有了主宰作用”[39]。数字帝国利用“深度伪造”“加速主义”等认知战套路进行“控脑性”价值形塑,从而解构他国共同信仰、篡改民族历史记忆,使得对精神征服的控制范围超越了它的国界。二是以“非政治化”面向渗透于数实交融的文化领域。技术变革与现代文化的联姻为数字帝国的意识形态谎言提供了温床,使文化沦为解构根本政治调性、实现社会问题非政治化的全新选择,并衍生出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要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未湮没于“非政治化”叙事的文化主题,而是在数字技术掩饰下以“合理化”的逻辑“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25]63。三是以“情感叙事”包装弥散于数字交往的生活领域。数字帝国的弥漫性统治体系将星丛式的数字个体聚合而形成数众,在数字“虚体”的掩饰下,数字交往纷繁复杂,数字个体的情感被固化为可供读写的符码,变成了一种可被观察和操控的对象。依赖于理性精神统驭情感关系的“胜利”,数字帝国利用数字交往将“默认的普遍意识”潜藏至日常生活、弥漫在生活意识、内嵌入社会心理、形成于社会情感之中,最终实现“生活世界的殖民”。
-
消费“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40]223,通过符号制造意义和“伪象征”,正是当代资本主义消费控制的秘密。正如,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言,“新的权力在于信息的符码(codes of information)与再现的意象(images of representation)”[41]。数字帝国的数字化消费叙事构建了紧密的筑模性欲望诱惑链,加速了“商品完全成功的殖民化(l'occupation)社会生活的时刻”[42]的到来,以意象性的符码关系与潜意识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驯服数字个体,诱使其臣服于消费物的逻辑,接受“虚假数字需求”的强制驱动。一是赋魅“数字仪式”刺激消费欲望肆意膨胀。平台资本主义创设了各类“全民狂欢”的数字仪式,通过“算法狡计”巧妙设置折扣赠品、凑单优惠、限时秒杀等营销叙事,催生和加剧着欲望无限和手段有限、诱惑无限和占有有限之间的不平衡,不断激发消费者欲望之无限的观念和欲求应当得以满足的意识,使之陷入“冲动、虚荣、攀比”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伪欲望”沟壑,沉醉于“种草”和囤货,进而成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单向度”“还款人”和“尾款人”。二是塑造“符号美学”诱发消费快感无限上升。在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看来,“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40]223。在数字化的侵袭下,消费渐次从“实物消费”走向“符号消费”,俨然成为迎合“身份彰显”与“快乐餍足”的“快感享受”。资本家想方设法地赋予商品以“美感”,在符号魅惑光影中的“审美商品”成为一种“技术假体”,进而使得个体审美的“自觉意识”被置于消费意识形态的虚假魅力之下而窒息。失落于资本营设的“审美幻境”中的数字个体近乎疯狂地购买“无关乎幸福与本真需要”的商品,妄图以消费的功能性快感来填充生命意义与灵魂荒芜,却在“楚门的世界”中沦为资本增殖的奴隶。三是营造“象征形态”加速消费主体精神沉沦。资本以“区别符号来生产价值社会编码”[43],将“权力”“尊严”“豪华”“成功”等象征内涵注入商品,让个体受到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蛊惑沉沦于身份跃迁的幻觉,为自我“象征形态”的满足而付费。数字技术的革新创造出更加逼真的消费拟态环境,使得个体被数字和符码进一步钳制,“思想的齿轮处于技术性的停转状态”[44],沉浸于虚荣性的精神盲流,盲目跟风消费的“他者欲望”,如同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浮尘,或在虚假幻想中泯灭,或在挣扎求真时溺毙。
一. “颠倒观念”牧领:“订制化”数字生产使意识形态渗透内容更具蛊惑性
二. “编码构镜”虚饰:“精准化”数字分配使意识形态渗透对象更具针对性
三. “软性叙事”侵蚀:“隐匿化”数字交换使意识形态渗透范围更具广泛性
四. “虚假需求”钳制:“符号化”数字消费使意识形态渗透方式更具灵活性
-
意识形态的批判在于破解数字殖民的逻辑悖谬,穿越其幻象、洞察其实质,廓清笼罩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想迷障。而“副本批判”终究要回归现实的变革,应走出“阿门塞斯冥国”映照现实,针对数字帝国主义的数字规训和价值入侵,需要在实践上“使现存世界革命化”[31]527,探索出一条超越数字殖民的数字觉解之道。
-
数字技术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掠夺所用,也可以作为解放人类的手段,为打开通往自由王国的大门添砖加瓦。诚如马克思所指,“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17]493。技术本身既非善亦非恶,数字时代暴露的与“技术异化”关联的社会问题、引发的“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1]156的现象,实则是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症候。质言之,唯有让数字技术从工具理性实现价值理性的复归,才能使数字技术摆脱资本逻辑的宰制而真正发挥改变世界的潜力。其一,优化数字技术设计以避免“技术滥用”。当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价值意义将被工具效用的扩张所侵蚀,人们则会在技术的滥用下沦为工具理性滥觞的客体。为了确保人的本质力量在数字空间获致多维度的解放,就应当对数字理性系统进行价值敏感性设计[45],将“公共价值、人类幸福”的价值理性融入数字技术研发、改造、应用和评估的全过程。其二,加强数字技术监管以规训“技术权力”。当数字技术屈从于资本权力时便形成新的权力样态,即“技术权力”,它展现出一种抽象的支配与控制力量。故而,必须铲除数字技术赖以生存的资本权力躯体,合理设置监管流程和把关机制,压制资本欲望“无止性”和逐利“贪婪性”劣根,“使它们受生产者共同监督”[46],在主客体的双向互构中实现价值理性的依归,进而更好地规避“技术权力”异化的症结。
-
“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它以物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资本中。”[21]187数字资本在极大限度地提升劳动生产效率、提高资源流转速度的同时,也造成了数字资本逻辑下的技术滥用,带来了技术错位生长的实存性“数智威胁”。故而,必须将数字技术从资本奴役的境遇中解放出来,使其不再是“幽灵般的对象”,而是能够带给人解放的“普照的光”,通过“人本—技术”的双向联合冲破“资本—技术”的“联袂”,进而回归于数字化革命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31]525的人本逻辑。其一,防止数字空间资本无序扩张。数字资本的“运行自由”与“运行责任”是对等的,应当设置数字资本“红绿灯”,以“放”“管”并进为导向,既应该对满足高质量发展要求和增进人民生活福祉的数字资本扩张开“绿灯”,又要为超出合理限度无序扩张的数字资本设置“红灯”,进而充分发挥数字资本的最大化社会效益。其二,健全数字空间资本准入政策。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将加剧经济结构失调,引导数字资本朝着有利于实现世界平等的“数字化繁荣”与人的自由解放方向良序发展是消解其负面效应的关键。对于关乎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必须明确数字资本准入标准,严格审核数字资本准入资质,建立健全数字资本扩张的负面清单,完善监管和惩戒责任体系,进而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底线。
-
数字帝国凭借对全球数字技术标准、生产和分配的垄断,将倾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应用程序、操作系统分发至世界各地,以期构建全球化的数字殖民体系实现对他国的数字化征服。而作为数字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统治的新形式的数字殖民,其核心在于施展意识形态渗透。因此,面对数字殖民下的战略攻势,我们要积极推进数字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构筑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保护屏障。其一,构建协同矩阵,打造治理多元化。我们要坚持以系统思维为指引,探寻由政党领导、政府牵头、多元协同的数字意识形态治理格局,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联动机制。其二,强化技术赋能,促进治理智能化。我们要在芯片研发、IP地址分配、通信主干线、域名解析等前沿技术方面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着力消除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技术性隐患。同时,善于发挥数字技术的智能优势,依托智能技术的并行计算和分布式计算能力,动态监测评估和精准标识预警数字意识形态的风险。其三,完善制度体系,推动治理法治化。法治化是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故而,我们要建立健全数字意识形态治理的法治规范体系、实施体系、监督体系和保障体系,推动数字意识形态治理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
数字帝国创生的“数字文明”被嵌套在资本逻辑的轭具之下,导致“人的独立性”深陷于“数字的依赖性”,使得阶级社会的“国家等等”成为“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虚假的共同体”[31]571。诚如,马克思所指,“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1]571,“真正的共同体”是以促进“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而非资产阶级利益的单向张扬。故而,勘破数字帝国的殖民统治,就要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导向,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形成适合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数字文明新形态。其一,指明新的价值立场,形成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主体自觉。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应从“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立场出发,尊重不同国家、民族的主体性,凝结各个主体特殊利益中的共同因素,在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共享、普惠”属性的过程中创造更多符合世界人民需要的现实利益。其二,提供新的价值愿景,汇聚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合力。面对数字帝国的殖民压迫和隐蔽剥削,需要数字个体“产生出一个合力”[47],摆脱“数字壁垒”、突破“数字封锁”,共同反叛数字帝国的“技术掣肘”,将“向往文明进步、憧憬发展繁荣、求得人类解放”作为愿景,共筑以人类共同价值为价值准则的数字命运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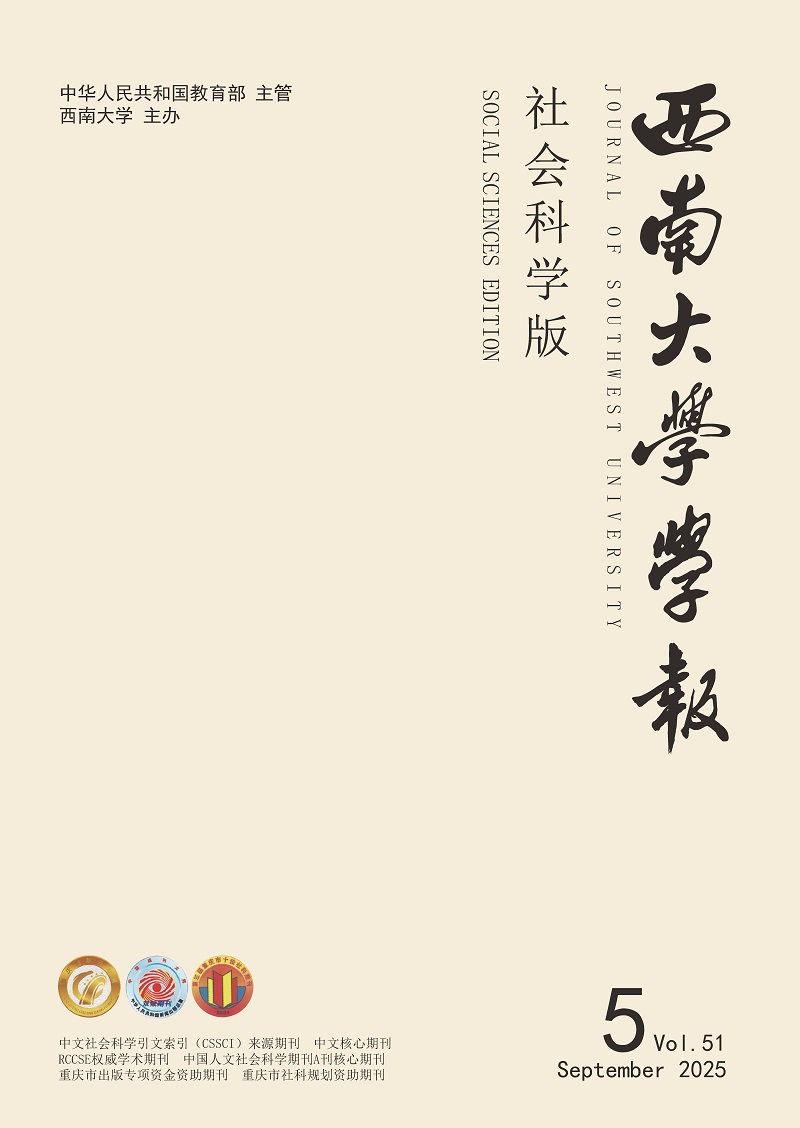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