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ML
-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根据2023年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我国正着力加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及推进数字产业化转型,从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驱动力。近年来,以一系列新兴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金融正在助益金融行业格局重塑,赋能实体经济发展[1],使其逐渐成为中国数字化发展浪潮中的引领者和佼佼者[2]。数字技术应用对金融行业结构的重塑,孕育出具备鲜明包容性与普惠性特征的数字金融。传统金融要素囿于地理位置,服务范围有限,而数字金融突破了这一藩篱,扩大了金融服务范围,引领中国普惠金融迅速高质量发展[3-4],从而对经济增长[5-6]、创新创业[7]、居民消费升级[8-9]等产生深远影响。不难发现,数字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在数字化浪潮中,准确挖掘数字金融对市场要素变革的关键影响,努力探索数字化赋能城市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方向,深入理解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讨论。
202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推进科技创新,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依靠创新提高发展质量。产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协调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不竭动力[10],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近年来,数字技术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助力塑造并健全具有高度包容性与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使其逐渐成为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新发展动能和激活创新要素的重要支点。数字金融发展的空间集聚性[11]与城市产业创新活动的集聚能够形成“双轮驱动”,通过高质量的金融要素与知识共享、匹配与溢出,能够进一步推动城市与产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与创新潜能的激发。
在现有的理论研究中,可以发现数字金融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是多维的。在微观层面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通过改造传统金融体系,创造了兼具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长尾效应的金融市场环境。一方面,数字金融能够提升金融机构识别与防范风险的能力[12],以及金融资源与创新要素在市场中的匹配效率[13-14],对于“草根”人群的创新创业活动产生积极影响[7]。另一方面,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抑制商业信用二次配置减少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系统性风险,拓宽企业创新发展的直接融资渠道,从而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积极影响[15],有效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在宏观层面上,一方面,数字金融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实现信息共享,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改善市场营商环境,进而促使市场创新资源与项目更好地匹配[16],并且有利于改善银行业竞争,提升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与实现居民消费升级,最终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17]。另一方面,由于地区禀赋条件差异的存在,数字金融在发展水平上本身就表现出显著差距[18],进而会拉大地区创新差距,产生“马太效应”[19]。相反,潘爽等的研究认为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高银行业竞争、推进市场化进程以及提高市场发展潜力弥补城市间的“创新鸿沟”[20]。上述研究主要是基于微观与宏观视角阐述数字金融对创新活动的积极效应,以产业创新发展为视角的中观层面探讨数字金融的“普惠创新效应”的研究较为缺乏,数字金融究竟怎样影响产业创新,以及通过何种作用机制发挥积极作用缺乏应有的梳理与论证。
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细致地剖析在城市内部不同行业中,数字金融助益产业创新的内在逻辑机理以及创新效应的异质性。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在研究立意上,不同于现有文献主要针对城市层面的研究,本文基于产业创新的角度,重点针对数字金融的区域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提供新的中观层面的参考。其二,在研究数据上,本文基于区域知识吸收能力、创业活跃度和城市多样性的视角,打开数字金融影响产业创新的机制黑箱,丰富和拓展已有文献。其三,在研究数据上,本文采用更为细致的产业创新指数数据,同时借助企业工商注册信息对创业活跃度进行度量,并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识别地级市金融科技企业数量,构建数字金融指数作为替代测量。相比已有研究,本研究能够多维度、全方位地准确分析数字金融影响产业创新的内在特征。其四,在研究策略上,结合工具变量法、大量稳健性检验和多维度异质性分析,加深关于数字金融对不同城市与产业创新影响的理解。同时引入“宽带中国”作为外生政策冲击,进一步增强结论的信度。
-
目前,中国金融体系发展尚不完善[21],传统金融要素的供需不匹配问题对各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开展产生很大的制约[22],这也是中国自主创新活动长期表现出“量大质低”和“策略性创新”特征的重要原因之一[23],但这一现实症结恰好为科技企业进入金融行业创造了契机,数字金融由此进入大众视野并获得蓬勃发展[6, 24-25]。与传统金融体系结构特征相比,数字金融具有鲜明的“存量优化”与“增量补充”的金融效益[14]。
一方面,数字金融极大地提升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了传统金融资源支持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助益产业创新。从直接效应来看,数字金融借助互联网的范围经济、长尾效应与平台效应,在重塑传统金融体系的同时,有效破除了创新过程中金融要素流动的时空限制,防止金融资源错配以增强金融服务可得性,弥补了传统金融支持不足的缺陷[17, 26],进而直接促进城市产业创新。从间接效应来看,数字金融是依托互联网技术衍生出来的新兴平台金融业态,平台式的信息共享与知识高效传播有利于不同部门之间创新主体的创新意识联动[27],充分利用产业间的知识溢出效应,对于产业结构优化[28]与消费升级[9]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间接推动产业创新水平的提升。
另一方面,囿于信息茧房效应,数字金融对创新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也因此而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从直接效应来看,其一,东部地区由于城市禀赋、地理位置以及城市生命周期潜能等因素,数字金融的创新普惠效应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17],从而形成区域创新差距[18]。其二,技术密集型与成长型企业的创新活动,往往需要更多的金融资源支持以缓解融资约束问题,而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金融资源的可得性,为这些企业创新提供必要的支持,特别是对于小规模企业,其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更为显著[27],从而直接提高了创新主体的创新主动性。从间接效应来看,数字金融在不同地区对经济活动的贡献程度也各有不同,地区间自身禀赋的差异使得数字金融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可能呈现出边际递减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字金融弥合区域创新差距的效果。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
研究假设H1:数字金融发展能助益城市产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产生普惠效应。
-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表明知识与其他一般生产要素不同,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是知识的鲜明特点,这就代表着知识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聚集与积累,从而作用于技术创新[29]。在产业创新发展质量持续提高的过程中,仅仅依靠区域自身本土化知识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本土化知识在整合过程中会出现边际递减的趋势,可能会严重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动能转变[30-31]。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是指区域内部对外部知识能够充分吸收、扩散和创造性应用到不同产业中的能力。拥有这一能力的区域,能够甄别、扩散和积累新知识和新技术,提高研发要素的流动速度,使各创新主体之间实现最大程度的思路碰撞与成果共享,进而提高知识外溢的效率[32]。数字金融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扫除地理距离的障碍[33],提高信息传播和交流的速度,降低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与信息获取成本[34],从而创造出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促进区域知识吸收能力的提升。一方面,区域知识吸收能力的提高能够畅通数字化信息的交流,通过整合数字化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模糊产业边界,降低不同行业之间的进入壁垒,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要素的流通效率[35]。同时,区域知识吸收能力的提升能够有效降低各部门之间联动的认知边际成本,提升各部门的运行效率,通过知识外溢的正外部性明显提升区域创新活跃度。另一方面,较强的区域知识吸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为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这些人力资本在各创新主体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桥梁”作用[36]。首先,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能够为城市提供多样化的人才储备,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其次,数字金融发展较好的地方对人才资源可能会产生“虹吸效应”,因为这些地区往往拥有金融资源优势,并以良好的市场环境与高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作为支撑,对产业创新产生深刻影响。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人才聚集产生的文化和知识碰撞、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会倒逼个人与企业实现有效知识交换以开展创新活动,提高创新研发投入与产出水平,进而作用于产业创新能力的提高。
与此同时,数字金融丰富的创业资源能够提高地区创业活跃度,从而促进产业创新发展。一方面,以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作为基础的数字金融,革新了传统商业模式中的支付方式、金融借贷业务和项目投资评估渠道,催生出与之匹配的商业模式,如共享经济、供应链经济、网络众筹等,能够有效满足创业者的金融服务需求,从而提高创业率和扩大创业规模,为产业创新提供较好的环境。另一方面,数字金融依托数字化信用评估风险体系为创业者提供了可比较、更全面、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提高了创业者的创业信贷成功率,有利于降低金融部门与创业者之间的资本错配和经济损失[37],使得社会就业机会均等化成为可能,实现包容性增长[38]。这推动了创新思维的产生、碰撞以及新兴数字技术的商业化应用,能够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的产业创新溢出红利。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2。
研究假设H2: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升区域知识吸收能力与创业活跃度,赋能产业创新绩效。
-
产业多样化与专业化集聚所带来的外部效应能够显著促进产业创新水平的提升[39]。城市为经济活动主体间相互接触与学习创造了平台与机会,激发了新思想的相互碰撞[40]。新经济地理理论将产业资源高度集聚视为城市产业多样化形成的重要条件[41]。首先,通过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数字金融能够对城市内不同产业形成辐射效应,增强地区产业发展的开放性、包容性与集聚性。一方面,产业多样化集聚能够降低单一产业、技术和制度等的路径依赖,形成区域内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从而提高企业技术独占性与降低获取互补性资源的成本[42],能够发挥出显著的创新范围经济效应,推动区域整体创新绩效的提升。另一方面,数字金融的空间集聚性所形成的金融增长极能够通过经济增长极效应提高社会闲散资金利用率、降低企业融资交易成本,促进金融资源在产业生产活动中的有效配置,促使相关企业基于区位比较优势进行空间重构,从而加速产业聚集效应的形成[22]。其次,数字金融在信息获取和风险识别上具有显著优势[43],为不同知识元素之间的组合、重组和累积形成“资金蓄水池”提供了可能。数字金融打破了金融资源空间流动的局限性,降低了企业搜寻金融资源的时间成本,产生的金融资源外溢效应不仅增加了企业跨行业的知识交流机会,也推动了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合作,特别是对关联产业的生产率提升作用更为显著,从而助推了地区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44]。
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城市专业化分工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45]。一方面,产业专业化集聚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创新要素的高度集聚[46],意味着技术知识的传播和扩散效率将更高,信息约束问题的缓解能够有效规避交易成本对创新活动的挤出效应,更好地发挥知识溢出的创新促进效应。另一方面,产业专业化集聚形成的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市场壁垒,提高了市场进入的门槛[47],限制了部分竞争者进入市场,在位企业的市场势力变得更强,从而可能演化成垄断。而根据不完全竞争理论,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润能够成为产业创新的经济基础与重要激励[21]。首先,已有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在推动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48],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服务对象提供更加便捷化和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人才集聚,为人力资本积累和结构优化创造良好的市场化环境[49]。人才资源在城市内部的集聚无疑为产业专业化和产业创新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产业专业化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专业化集聚规模的扩大,规模经济就愈发显著[30-31],以同行业溢出为代表的本地化经济能够逐渐显示出专业化优势与创新优势。其次,不同产业间的技术特征与生命周期具有鲜明差异,数字金融能够借助数字技术对某一产业的发展潜力与禀赋条件进行细致分析,引导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向技术密集型和成长型产业。这些行业越有动力通过研发创新来推动核心技术的成熟,越能够享受数字金融集聚带来的各种正向外部性,从而释放产业专业化的正向外部性,最终促使不同产业高度集聚,实现专业化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3。
研究假设H3: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升产业多样化与专业化水平发挥创新驱动效应。
一. 数字金融发展驱动产业创新的直接效应
二. 数字金融发展对产业创新的间接效应之一:基于知识吸收与创业溢出效应的视角
三. 数字金融发展对产业创新的间接效应之二:基于产业多样化与专业化集聚效应的视角
-
本文聚焦于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借鉴傅十和、Carlino等的研究思路[50-51],引入集聚与创新领域的经典创新生产函数:
其中,Y表示产业创新产出,K和L分别表示当期投入的创新研发资金和人力资本,F(A)则表示城市产业的集聚经济。本文进一步将数字金融发展纳入城市产业集聚经济F(A)中,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其中,i、j、t分别表示城市、四位数行业、年份。被解释变量innovijt表示各城市不同四位数行业在不同年份的产业创新绩效,核心解释变量DIFit表示各城市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Controls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集合。εjt表示行业—时间固定效应,控制四位数行业所属两位数行业层面随年份变化的影响因素,ζt则是指时间固定效应,吸收随时间变化的宏观冲击,vi是指城市固定效应,uijt为随机扰动项。α1为常数项,α2和γ为变量系数。同时,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均采用聚类至城市—行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被解释变量为产业创新绩效(innov)。在现有实证研究文献中,衡量城市、产业以及企业创新绩效往往利用专利申请数量等数据指标。然而仅仅只是简单地对专利数据进行求和得出总量,或者根据专利的引用量通过部分客观因素赋予相应的权重进行加权求和而得出总量,会导致不同专利的社会价值被忽视的问题[52]。另外,张杰等认为目前中国各创新主体在专利的申请与授权情况中存在较为严重的“泡沫”和“创新假象”问题,难以突出专利本身的价值[53]。特别是部分企业与区域为了迎合政策等,往往采取策略性人为增加专利数量的行为[54]。因此,以专利申请数量来衡量创新绩效容易出现偏差。
本文借鉴寇宗来等的研究[55],将城市层面四位数行业的创新指数作为产业创新绩效的测度指标,该指标的优点是能够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各城市中不同行业所申请的各项专利的真实价值①。此外,考虑到创新指数的平滑分布特征以及量纲统一问题,将创新指数采取自然对数处理,并从中剥离出制造业行业的数据,提取出约90万个时间—城市—四位数产业观测值。
① 数据来源于复旦大学创新与数字经济研究院、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2021》。复旦大学研究团队主要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到期专利的历史数据,利用专利更新模型估算出各发明专利的动态经济价值,并基于2001年全国专利价值总量对各年度的城市层面分产业的专利价值进行加总和标准化处理,从而得出各行业的创新指数。
-
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金融发展(DIF)。基于金融稳定理事会对金融科技的内涵界定,使用地级市金融科技企业数量构建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指数。首先,基于“数字金融”“金融科技”和“云计算”等关键词,利用Python在“天眼查”网站对相关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进行检索,获取其工商注册信息。其次,依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金融科技业务模式的分类准则,使用正则表达式对上述金融科技企业的具体经营领域以及“金融”“支付”等与金融相关的关键词进行模糊匹配,得到匹配成功的样本数据。同时,对经营状态异常的样本企业、经营范围包含特殊经营范围字段(如“严禁涉及……业务”等)的样本企业、经营时间不足一年的样本企业进行剔除。最后统计得出各地区不同年份的金融科技企业数量,该数值越大,说明当地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越高。
-
(1) 区域知识吸收能力(AC)与创业活跃度(Entrep)
区域知识吸收能力与创业活跃度对于推动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是理解区域外知识流入并将其转化为区域创新的重要方式[36]。本文借鉴刘晔等的研究思路[56],同时结合我国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采用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从业人员数目作为区域知识吸收能力的代理变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另外,社会创业率的提高和创业活动的广泛扩散渗透,有利于创业者之间的创新性思维的碰撞与创新资源的高效获取,为城市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本文借鉴叶文平和赵涛等的研究思路[57-58],从启信宝数据库中获取城市各年度的新增私营企业数量,同时借助15~64岁城市劳动力人口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最终计算出各城市的创业活跃度。
(2) 行业专业化(speciality)与行业多样化(diversity)
本文参考傅十和等的研究方法[50],基于2012—201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分行业就业数据来测度行业专业化程度的指标。具体而言,将城市某一行业总的就业人数与该城市就业总人数的比值作为行业专业化的代理变量,该指标反映了某一行业在当地的专业化程度,常用来反映马歇尔外部性或者行业内部专业化集聚经济。
另外,为了反映雅格布斯外部性,本文在各产业的赫芬达尔指数(HHI)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行业多样化指标(diversity)。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i、j、t分别表示城市、行业、年份。Xijt是指城市i中产业j在第t年的总就业人数与该城市所有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不难发现,该行业多样化指标的取值范围是[0, 1],如果diversity的值趋近于0,说明该城市行业多样性较低,只有少数行业作为主导;如果diversity的值趋近于1,说明该城市行业多样性较高,拥有众多不同的行业,且各行业中的就业人数所占比重相当。同时,本文参考王峤等的研究思路[59],对上述两个指数进行改进,剔除本行业的影响,进一步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行业演进的效应。此处的产业是依据一位数产业进行分类的,共计划分为19个行业。
-
为了更加全面地分析在城市产业创新发展过程中数字普惠金融的“金融加速器”溢出效应,还需要考虑部分对产业创新绩效可能会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具体为:创新资本投入(R&D)用城市科研支出与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edl)用劳动力平均工资水平(取对数)来衡量[60],其中劳动力平均工资是以2011年城市所属省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作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得出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fix)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road)用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edu)用高等院校在校生与地区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与此同时,还引入城市夏季均温(summer)和冬季均温(winter)等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特征变量,以进一步提高模型结果的准确性。
-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11—2020年中国25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城市样本)。相关数据来源为:《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2021》《中国数字金融普惠发展指数报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气象网。表 1是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城市产业创新绩效(innov)的均值为0.016 05,标准差为0.084 9,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4.055 8和0,表明目前中国城市的产业创新发展空间和潜力较大,不同产业间创新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为“马太效应”。数字金融发展(DIF)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2.469 2和0.195 3,标准差为0.514 3,说明区域间“数字鸿沟”问题比较突出,这很有可能引发新的“创新鸿沟”[18]。从控制变量上看,不同城市在创新资本投入(R&D)、经济发展水平(edl)、固定资产投资水平(fix)、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road)以及人力资本水平(edu)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差异。
一. 研究模型设定与实证策略
二. 变量测度与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2. 核心解释变量
3. 机制变量
4. 控制变量
三.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表 2为数字金融发展影响产业创新绩效的基准回归结果。表 2第(1)列仅包含数字金融发展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不加入控制变量和不控制任何固定效应的情况下,核心解释变量数字金融发展的估计系数为正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不考虑其他条件的情况下,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产业创新绩效的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前述的研究假设H1。第(2)列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入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的系数为正且仍保持显著。第(3)列回归中进一步控制时间、行业以及两位数行业与时间交互项的固定效应,此时核心估计系数α2的大小意味着两位数行业下四位数行业间的创新水平差异。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数字金融发展的系数仍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城市数字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其产业创新绩效就越高。从经济意义看,数字金融发展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使得产业创新绩效提升0.066 9%①。这说明,无论从统计意义还是从经济意义的角度上看,数字金融发展确实能够助益产业创新绩效的提升,随着数字技术赋能传统金融服务的深化,传统金融要素流动的时空阻滞障碍能被有效打破,从而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更加优渥的金融环境,同时带来了产业创新要素的不断积累和丰富,城市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也会随之增强,创新活动也因此而更加活跃。
①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绝对值偏小,可能主要原因在于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是城市分行业的创新指数,估计系数反映的是四位数行业层面的平均效应。
-
本文的核心目的在于捕捉数字金融发展与产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在前述的实证检验分析中,仍有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产业创新活动的开展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且由于结构、资源禀赋以及发展阶段等的不同,产业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些不可观测的影响因素往往是有可能被遗漏的。另一方面,虽然城市产业创新水平会受到数字金融发展的影响,但是产业创新绩效的进一步提升,或许会引导金融行业往共享性更高、数字化水平更高的方向发展。针对以上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识别因果效应。
本文借鉴黄群慧和赵涛等的研究思路[61, 58],选取1984年各城市每万人固定电话数量与滞后一期的全国互联网用户数的交乘项作为当期数字金融发展程度的工具变量。在以往发展过程中,各城市的通信方式会从技术水平和社会习惯等方面影响样本期内当地金融行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接受程度,满足相关性条件。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历史上固定电话数量对区域创新活动的影响日渐式微,满足排他性要求。
表 3为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CDW-F值和KPW-F值均大于Stock-Yogo弱工具变量识别F检验在10%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说明该工具变量是合理可靠的。表 3第(1)列显示了IV1作为工具变量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DIF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本文假设H1是成立的,可以得出本文核心结论:数字金融发展能助益城市产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产生普惠效应。
进一步借鉴张勋等的做法[5],本文采用该城市到杭州之间的球面距离与全国当年(除本市外)数字金融发展指数均值组成的交互项作为新的工具变量。表 3第(2)列报告了检验结果,可以发现DIF的系数为正且仍然保持显著,说明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产业创新绩效的提升。然而,杭州只是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重要城市之一,以当地与杭州的球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是否意味着北京、深圳、上海等地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还不如距离杭州更近的嘉兴呢?为了更加严谨地考虑该工具变量的结论,本文进一步借鉴郭家堂等的研究思路[62],采用样本期之前(即2005—2010年)各省份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根据表 3第(3)列的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本文核心结论成立且是稳健可靠的。
此外,本文进一步分别采用各地级市地形起伏度与汇率组成的交乘项、城市老字号企业数量作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工具变量进行辅助解释,结果均支持本文核心结论。限于篇幅,实证结果此处并未展示,备索。
-
(1) 核心解释变量的替代测量。目前学术界对于数字金融与金融科技之间的区别仍有分歧,两者虽然存在细微差异,但是本质内涵基本一致[3],故本文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市级层面的综合发展指数(Fintech)、市级层面数字金融覆盖广度(cover)和使用深度(use)作为替代性测量。表 4第(1)~(3)列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的增加,能够对产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产生积极的效用。
(2) 被解释变量的替代测量。鉴于此,本文进一步选取《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中2011—2020年的城市层面创新指数数据(innov2)进行稳健性检验①。根据表 4的第(4)列的结果显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后,本文核心结论依然保持稳健。
① 本部分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当年所申请发明专利的最终获批数目加1取对数,统计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31日。相关特征变量主要包括城市人均GDP水平(GDP)、城市产业结构水平(Ind)、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回报率(ROA)、是否是国有企业(SOE)、股权集中度(Topl)、托宾Q值(TQ)、现金比率(Cash)、固定资产增长率(Fix)、两职合一(Dual)、董事会规模(Bsize)、独立董事比例(Indep)与委员会个数(Cmote)等。
-
实际上,对于行业本身而言,创新水平和研发强度的提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需要一段时间的积淀,并且本文中的数字金融作为一种新兴金融业态也需要经历长期的发展,而创新指数更多的是反映短期波动的情况,有可能会导致估计偏误的问题。基于此,为了捕捉研究样本期间数字金融发展差异所导致的创新变化,分别采用2011年与2020年的数字金融数据对所有年份的创新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4第(5)和(6)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估计系数大小较为接近,说明数字金融在样本期内的发展变异,并没有导致创新指数发生较大程度的波动。
-
(1) 考虑中国四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的经济特殊性,剔除了直辖市的样本数据后再重新进行回归性检验。(2)控制其他因素。考虑到如城市资源禀赋、发展特征以及城市级别等因素都有可能会影响当地的产业创新水平,因此,本文借鉴王峤等的研究思路[59],在基准回归基础上,进一步加入城市是否为旅游城市(travel)、城市高程标准差(attstd)以及是否属于省会城市(capital)等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与时间固定效应的交互项,剥离这些因素的影响。(3)调整聚类尺度。在实证分析中均采用聚类至城市—四位数行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进行回归,出于稳健性考虑,进一步将聚类层面调整至31个两位数行业,采取两位数行业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重新检验。(4)考虑行业过于细分的问题。四位数行业创新指数可能存在零值堆积的问题,会导致对数字金融发展的产业创新绩效估计产生偏误,鉴于此,剔除了创新指数等于0的样本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5第(1)~(4)列依次列示了上述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DIF的估计系数仍然保持为正值且高度显著,再次印证了本文核心结论是稳健的。
-
通过微观上市企业数据再验证来增强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具体而言,将2011—2020年中国A股沪深两市上市企业财务数据与CNRDS的专利获批数据进行匹配,同时考虑专利获批存在时滞性,在控制城市层面和企业层面相关特征变量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微观企业创新产出(AG)的影响。表 5第(5)列显示了相应的估计结果,DIF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再次说明了本文核心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
事实上,城市产业创新活动往往会受到当地的营商环境、产业技术水平以及政策支持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为了更加稳健地评估数字金融发展对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借鉴赵涛等的研究思路[58],采用“宽带中国”试点的网络新基建升级作为外生政策冲击,利用双重差分法(DID)来进一步提高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另外,考虑到“宽带中国”试点城市的选取往往会受到诸如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创业创新环境、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先决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赵涛等的做法[58],将一系列先决因素①与时间趋势项组成交乘项,并加入到控制变量集合中,以控制城市的历史特征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模型的估计偏误。具体而言,通过设定多期DID模型探讨“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是否提高了城市产业创新水平,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① 先决因素变量包括:城市高程标准差、是否为省会城市、是否为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以及城市资源禀赋(2005年的城市人均蔬菜产量、高等院校数量、人均水产品产量与每百人电话拥有数量)等。
其中,BICit表示城市i在t年是否属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城市,如果是则为1,否则为0。其他变量定义均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表 5的第(6)列是平行趋势检验通过的前提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BICit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该政策显著促进了产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另外,为了进一步保证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还考虑了非观测因素的干扰,对模型进行了重复1 000次的安慰剂检验,结果显示“宽带中国”试点估计值的分布趋于0并且近似于正态分布,表明未被观测到的随机因素并不会对模型的估计结果产生显著影响,通过了安慰剂检验,表明本文核心结论是稳健的。
一. 数字金融发展对产业创新绩效的“金融加速器”效应
1. 基准回归结果
2. 工具变量回归
二. 稳健性检验
1. 考虑主要变量的稳健性
2. 考虑城市产业创新的滞后效应
3. 考虑部分影响因素
4. 基于微观数据的再验证
5. 外生政策冲击检验
-
上述研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了产业创新绩效。本文将通过直接考察数字金融发展与产业创新中“知识吸收与创业溢出效应”和“产业多样化与专业化集聚效应”两个传导机制的影响,从不同角度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产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应。对此,本文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数字金融发展是否会减少城市产业间知识的交流障碍,提升区域知识吸收能力,同时增强创业活跃度,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新动能?第二,数字金融发展能否提高集聚优势,提高产业多样性和专业性以促进其创新发展?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将分成两方面进行检验分析,表 6为相应的检验结果。
首先,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数字金融发展是否能够提高区域知识吸收能力与创业活跃度。表 6第(1)列显示了相应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数字金融发展(DIF)与区域知识吸收能力(AC)之间呈正相关,并在1%水平上保持显著,说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打破空间距离的壁垒,提高区域知识吸收能力,减少知识溢出和要素集聚的障碍。第(2)列是以创业活跃度(Entrep)作为机制变量,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其的影响。从第(2)列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并在1%水平上保持正向影响。说明随着数字金融在社会经济不同领域的广泛渗透与持续扩散,创业机会的均等化使得创业者更容易获取相应的创新创业资源,充分释放了互联网的创新溢出红利。因此,假设H2得以验证,即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升区域知识吸收能力与创业活跃度,赋能产业创新绩效。
其次,检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影响产业多样化与专业化集聚水平激励产业创新的理论机制。表 6第(3)列是以行业多样化(diversify)作为机制变量,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产业多样化发展的影响。从第(3)列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数字金融发展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的雅各布斯外部性会显著受到数字金融发展的正向影响,数字金融发展有效减少了行业间资金、人力资本以及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通障碍,提高了城市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的互动性,拓宽了产业链布局,更有可能发挥行业多样化发展对生态环境优化、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正向外部性。第(4)列则是以行业专业化(specialty)作为机制变量,直接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其的影响。从第(4)列的结果可以看出,数字金融发展与行业专业化之间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说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市行业的专业化水平,使得专业化的集聚优势得到更加充分的释放。城市内部各产业的专业化发展也进一步增强了城市内部的马歇尔外部性。在数字金融发展与产业自身寻求专业化发展的双重正向激励的作用下,行业专业化的综合净收益得到进一步提升。因此,假设H3得以验证,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升产业多样化与专业化水平发挥创新驱动效应。
-
(1) 互联网普及率。不同区域间的互联网普及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数字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互联网接入成本问题,互联网的普及差异是“数字鸿沟”现象存在的重要原因,并由此引发“马太效应”[19]。基于此,根据全国互联网普及率的平均值设置虚拟变量互联网普及net(如果城市互联网普及率高于平均值取值为1,反之则取值为0),进一步讨论城市互联网发展差异在数字金融发展对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是否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点,将net以及交乘项DIF×net加入模型中进行检验。根据表 7第(1)列的估计结果,数字金融发展(DIF)与交乘项DIF×net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相比于互联网普及率较低的城市而言,数字金融发展对互联网普及率较高城市的产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这主要是由于数字金融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数字接入情况,互联网发展较好的城市能够突破数字接入成本的“空间束缚”,从而推动产业创新绩效的提升。
(2) 城市等级。考虑到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在生产要素、资源吸收和流动等方面的差异较大,因此,将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划分为中心城市,其他城市划分为外围城市,设置虚拟变量center(中心城市取值为1,否则为0),将center以及交乘项DIF×center加入模型中进行检验。表 7第(2)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DIF)和DIF×center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相较于外围城市而言,数字金融发展对于中心城市产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可能是因为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资源和要素整合的配置效率更高,更能够借助数字化发展助推产业创新。
(3) 城市生命周期。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产业创新会受到区域资源、发展阶段以及产业兴衰更迭的影响,所以城市也存在自身的发展生命周期,比如东北地区的部分老工业城市就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的局面。因此以数字金融发展为契机,为产业创新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或许是较好的转型方案。基于此,根据201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年)的通知》中的城市名单,将样本城市划分为老工业城市与非老工业城市,设置虚拟变量old(老工业城市取值为1,否则为0),将old以及交乘项DIF×old加入模型中进行检验,以分析不同生命周期的城市发展异质性。表 7第(3)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DIF)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DIF×old的估计系数则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与老工业城市相比,数字金融发展对于非老工业创新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原因可能是非老工业城市与老工业城市相比,具备更好的创新发展基础条件和各方面优势。
-
(1) 行业技术密集度。参考王峤等的做法[59],按照现有文献的分类准则,将本文制造业样本划分为技术密集型行业(8个)与非技术密集型行业(20个),同时设置虚拟变量tech(技术密集型行业取值为1,否则为0),将tech以及交乘项DIF×tech加入模型中进行异质性识别。表 7第(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DIF)与交互项DIF×tech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对于非技术密集型行业而言,数字金融发展对技术密集型行业产业创新绩效的推动作用更强。原因在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对金融资源的依赖程度更高,数字金融的“长尾效应”与“梅特卡夫效应”能够有效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也更强。
(2) 产业生命周期。借鉴沈体雁等的行业分类[63],根据生命周期将28个制造业行业划分为成长型产业(逆成长型产业和成长型产业)与成熟稳定型产业,同时设置虚拟变量circle(成熟稳定型产业取值为1,否则为0),将circle以及交乘项DIF×circle加入模型中进行异质性识别。表 7第(5)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DIF×circle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相较于成熟稳定型产业而言,数字金融发展对于成长型产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在高速发展进程中,成熟稳定型行业不一定比“后发”行业具有更多的技术积累和成本优势,反而可能由于长期处于技术更迭和融合中而相对缺乏灵活性,而数字金融作为新兴金融业态,可能与“后发”的成长性产业的技术契合度更高,更能驱动这类产业实现创新发展。
一. 影响机制分析
二. 异质性分析
1. 基于城市禀赋的异质性分析
2. 基于行业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框架下,中国特色创新型城市与数字化建设的协同推进,构成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在当前中国城市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切实提升城市与产业创新能力,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基于此,本文从“知识吸收与创业溢出效应”和“产业多样化与专业化集聚效应”的视角切入,基于中国257个地级市2011—2020年城市—行业—时间维度的创新指数与数字金融数据,在理论机制分析基础上,利用多种计量方法实证解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助益产业创新绩效的提升,该结论在工具变量法、“宽带中国”外生政策冲击和文本识别法构建金融科技指数作为替代测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的纵深和长足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集聚进程,促进区域知识吸收能力和创业活跃度的提高,从而对产业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从产业层面看,数字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提高城市内部行业多样化与专业化的正外部性进而促进产业创新绩效提升。另外,从城市禀赋异质性角度看,数字金融发展对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在互联网普及率更高城市、中心城市以及非老工业城市更为明显;从行业特征异质性角度看,数字金融发展对技术密集型行业与成长型行业的创新激励效应更为显著。
-
第一,充分发挥数字红利效应,纵深发展数字金融。正确审视数字金融对产业创新的积极作用,依靠政府扶持,充分发挥数字化的创新红利效应,使数字金融向着纵深方向发展。具体而言,一方面,借助5G等新基建的数字化发展浪潮,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从而鼓励更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完善金融监管相关法律法规,为城市产业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支持与制度环境。
第二,充分释放知识溢出红利,实行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改善金融结构,为创新活动提供相对较优的金融结构和生产要素配置结构,有利于金融资源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逐步提升城市行业的专业化与多样化水平以及区域间创新要素的配置效率。一方面,各城市要充分认识并发挥自身优势,出台差异化的人才吸引激励政策,释放数字金融发展的知识溢出红利;另一方面,把握城市内部产业多样化与专业化的正外部性,依据比较优势调整并优化产业结构,通过产业的差异化战略定位与布局、培育创新创业产业园区等举措,提高对创新产业的扶持力度。
第三,充分考虑城市与行业异质性,实现因地制宜高质量创新发展。根据城市禀赋与行业性质,制定差异化、动态化的数字金融创新激励政策。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数字鸿沟”现象是我国目前数字金融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需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倾斜与政策倾斜,同时使其与数字金融发展较好地区形成互联互通,在区域内部发挥“传帮带”的辐射和溢出作用,努力建设产业创新孵化器,保证产业间的良性互动与数字化创新优势红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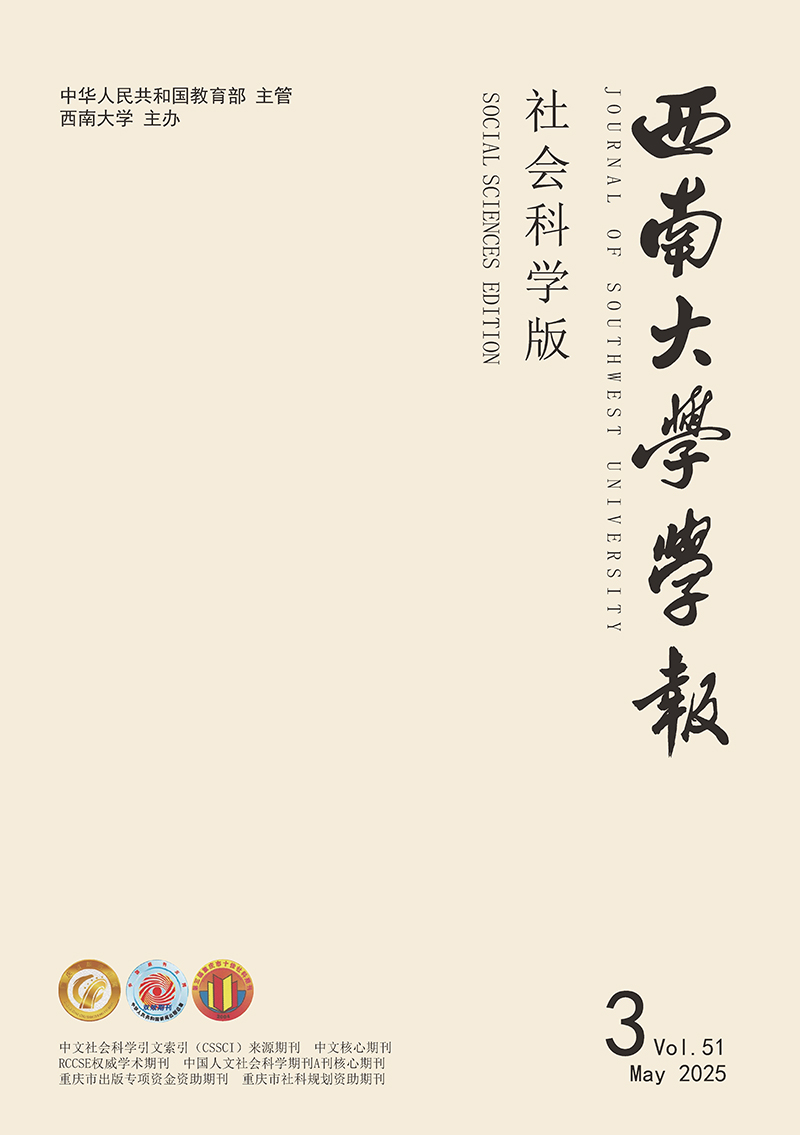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