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ML
-
历史上,各朝君王对“政治”有着较为广泛的定义:既包括军事、经济、外交等治国经略,同样也包括象征帝王及帝国身份、地位的形象塑造这一重要方面。帝王的形象塑造,不仅体现着皇帝本人强烈的政治参与感,是其实现权力展示、显露身份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其做为王朝统治者精心策划、有计划、有组织地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
清前期几位皇帝在建构“大一统”王朝时,为了彰显政治合法性与合理性,均会以特定的方式尊崇其域内各种文化、宗教,为自己装扮上各种文化的“外衣”,通过成功的帝王形象塑造实现对域内信持各种文化的族群统治。其中,尤以皇太极与玄烨最具代表性、典型性。
皇太极通过满蒙联姻、崇奉藏传佛教等举措,成功将自己塑造成受蒙古人敬仰的博格达汗,实现统合蒙古,完成满蒙政治、文化共同体建构;康熙皇帝通过祭孔、开设经筵、御制儒家典籍等表达自己尊儒重道的决心,完成了“圣贤明君”的形象塑造,保证清王朝顺理成章地继承自秦汉以来历代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传承。二者成功的帝王形象塑造确能有效帮助清王朝统治者实现对域内信持各种文化的族群的统御,进而有助于“大一统”王朝建构。
但无论是皇太极、还是玄烨,他们的皇帝身份与文化形象并非如此单一,而是多面的、立体的(例如,在面对旗人时,他们是八旗共主;在面对蒙古诸部时,他们是受蒙古人敬仰的博格达汗;在面对广大汉族时,他们崇儒重道,维系道统,是一个理想化的王朝天子形象)。皇帝形象塑造方面有所区别、有所侧重,是根据其所处王朝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民族环境不同和王朝不同的政治需要决定的。皇太极时期,王朝新立,问鼎中原的机会尚未成熟,与蒙古的关系也并未牢不可破,因此,他才会选择遵循“蒙古之道”,树立并强化“博格达汗王”的形象塑造,笼络蒙古;及至康熙朝,满蒙政治、文化共同体已初步形成,且渐趋稳定。康熙皇帝只需承袭前朝的对蒙政策,他便可得到蒙古的承认,继承“博格达汗王”的形象。因此,此时他急需解决的是在清王朝入主中原后,如何得到汉臣的认可,如何完成中原道统王朝继承者存在的合理性解释的问题。所以,康熙皇帝选择了崇儒重道以及祭典过程中的一系列程式化的仪式、语言及其衍生出来的道统论述体制来塑造并丰满自己“圣贤明君”的形象。从而实现清王朝顺理成章地继承自秦汉以来历代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传承。正是经过二者的不懈努力和精心塑造,清朝皇帝天下共主的形象不断丰满起来。其后的清朝统治者只需遵循前朝政策,便可自然承袭已获得的帝王形象。
皇太极、康熙成功塑造帝王形象的宝贵经验,为乾隆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例,以解决随着王朝疆域的不断拓展而出现的新的民族、宗教问题。当乾隆皇帝面对西藏以及广大信仰藏传佛教的地区时,其选择菩萨王形象塑造,完成“大一统”王朝的建构,便成为必然。
-
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亲赴京城朝觐,并在回程途中上请安奏书,以示感谢,在奏书中第一次称清帝为“文殊大皇帝”。奏书所言之清朝皇帝是“从天而降的谨慎圣主”,统领着佛国世界的四大部洲,令普天下的众生沐浴在其光辉之下,这是对尊崇藏传佛教,护持宗教的认可,肯定清朝皇帝佛菩萨的宗教地位,认定清帝世系为文殊菩萨的转世。这一方面是对清政府统治汉地的承认,另一方面也是遵从藏地传统。顺治之后清代诸帝均被视为文殊菩萨,只是佛号形形色色。例如,康熙二十九年(1690)五月,准噶尔部偷袭喀尔喀蒙古,康熙皇帝领兵亲征,八月大败准噶尔部于乌兰布通。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哲布尊丹巴率众内附。从喀尔喀蒙古所做《喀尔喀归附天朝之歌》以及表达对康熙皇帝感谢的《叩谢圣恩之歌》[1]中称康熙皇帝为“我神奇之文殊师利呼毕勒罕皇帝”,可以看出在喀尔喀蒙古部众的眼中,康熙皇帝俨然就是弘扬佛法、拯救苦难生灵的“文殊师利皇帝”。雍正皇帝是“文殊菩萨戏化为人主的世宗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为“文殊菩萨化现的乾隆皇帝”[2]。
一. 乾隆朝以前清帝形象塑造概述
二. 西藏政教传统与“文殊大皇帝”称号赠予
-
乾隆皇帝为深入了解藏传佛教,塑造藏传佛教护持者的形象,特接受了三世章嘉活佛的灌顶,开始修行密宗。同时,还在皇宫、三山五园内兴修佛堂,制作佛像。举凡乾隆朝宫中佛堂的建造,乾隆皇帝均有参与[3]222。清宫中修建的六品佛楼以及佛楼中供奉的莲花部众诸神佛,都与乾隆皇帝修习密法有着必然联系。
-
藏传佛教密宗修习重修持,讲究宗教实践的重要性。在经典学习、修习次第、仪轨制度、传承等方面都独具特点。藏密的仪轨复杂,所以,社坛、供养、诵咒等都有着严格的规定,而且必须经阿阁黎(导师)的秘密传授。
乾隆皇帝在接受三世章嘉的灌顶后,开始修习密宗。随着对密教理解的加深,以及三世章嘉的指导,乾隆皇帝开始在清宫内实践对藏传佛教密宗四部及其神系思想的完整、系统地呈现。如果说乾隆十四年(1749)年的雨花阁修建是对密宗四部供奉,以及宣示教理的简单尝试,那么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记录的“六品佛楼”的修建及供奉,就是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密宗四部及其神系思想呈现的进一步完善。
所谓“六品”,是藏传佛教根据密宗修习者的根机,也即所谓灵性、悟性,将密宗修行根据其内容的难易、成就的大小分为四个层次,也就是密宗修行中的四个次第。根据宗喀巴著《密宗道次第广论》中所论“于下说事部续,彼上无事行,瑜伽上有情,再上无上行”的解释可知,下品根机者修事部秘法,中品根机者修行部秘法,上品根机者修瑜伽部密法,上上品根机者修无上瑜伽部密法。其中无上瑜伽部又分为父续部和母续部,加上大乘佛教(即显宗,又称般若部),共为六部。
根据罗文华[4]64对故宫中佛堂建筑的实地考察并结合档案记载,确定了清宫中的六品佛楼均修建于乾隆时期,其共同特点是:佛楼内共七间,包括楼上楼下两部分,明间上供宗喀巴大师像,下供佛龛,塔或者旃檀佛像;左右两边各三间,是六品间,楼上分别供奉着各部经典以及经典所出诸尊及法器,楼下间分别供奉各式佛塔一座。分别是:宫廷内的慧曜楼、宝相楼、淡远楼、梵华楼;承德的众香楼、须弥福寿寺六品佛楼、普陀宗乘寺的六品佛楼;圆明园内的梵香楼,共八座[4]64-73。其中慧曜楼是清宫中最早出现的六品佛楼。
慧曜楼位于紫禁城建福花园内静怡轩后,面阔七间,进深仅为一间,贴北墙而建,与西边的吉云楼共享一个楼梯[5]。明清两朝,建福宫一带多为皇太子居住之地,乾隆未登宸极之时,就居住于此。登基之后,其原来所住宫殿改为重华宫(前文已述),乾隆二十二年(1757)西四、五所就改建为建福宫花园,并增盖后花园楼。笔者梳理《清宫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时发现,在乾隆二十二年五月的杂录档中发现有修造般若、无上阳体(父续部)、无上阴体(母续部)、瑜伽、德行、功行六品诸佛的记载,而这恰恰与文献中记载的慧曜楼修建时间相吻合: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杂录)十一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将造办处做得玻璃欢门紫檀木柜格六对着交中正殿摆佛,其隔断如不相对,改做……
于六月十二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将画匠喇嘛画得般若品第一、第二佛样张内,第一张现有佛三尊,应造佛三十八尊;第二张现有佛八尊,应造佛三十三尊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除现有佛外,其余之佛准照纸样拨蜡样呈览,将第一张内站像佛四尊不用,亦改坐佛像,另画样呈览。
于六月十八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将画匠喇嘛画得无上阳体根本第一、第二佛样张内,第一张现有佛四尊,应造佛三十七尊;第二张现有佛四尊,应造佛三十七尊持进。奉旨,准照纸样拨蜡样呈览。
于七月初六日郎中白世杰、员外郎金辉将现有般若铜佛三尊,照纸样拨得蜡样佛四尊,无上阳体铜佛八尊,照纸样拨得蜡样六尊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蜡样佛照样准造,其现有铜佛不合堂,仍交中正殿俱按原画纸样上佛样一样铸造,在佛堂上刻大清乾隆年敬造款,先贴样呈览。[6]780-782
从记载来看,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佛堂中本就有铜佛若干,只是因为并非六品佛,因此被撤除,交由中正殿重新铸造。这表明乾隆在修行密宗后对宫廷内佛堂及供奉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改造;其次,乾隆帝对任何造像的规格、样式、大小以及站像或者坐像都要“先贴样呈览”,亲自过目审核,符合要求后,才按样制造。乾隆皇帝此等的亲历亲为在以后的几处六品佛楼修造的记载中也是频频出现,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他对藏传佛教以及密宗的尊崇。
乾隆皇帝对修建六品佛楼格外重视,因此,一旦内务府造办处的工作人员有延误造像进度,或在造像中出现闪失,乾隆皇帝都会毫不留情地严厉责罚[6]793。在乾隆皇帝这样地督促下,慧曜楼内六品佛的供奉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渐渐初具规模: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分(大器作)十五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来说,太监胡世杰交挂像佛塔一轴,传旨:照挂像佛塔一样成做金台撒塔一座,再照含经堂现供藤子塔一样成做银塔一座。
于十月十三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将画得金塔罩纸样香几一张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不必配罩,着照洒沙子石座样配石座,石座上配紫檀木座,座上安金塔,要与铜塔一般高,再做银塔一座、铜塔一座、掐丝珐琅塔一座、紫檀木塔一座,着喇嘛拟四方、六方圆的样式俱照金塔一样高成做,得时在慧曜楼供。
……
于六月二十六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拨得金塔内主佛蜡像一尊,银塔内主佛蜡样一尊并银塔周围小塔内佛塔蜡样八尊呈览,奉旨,准样准做,其金塔内造金佛、银塔内造银佛,得时,脸像泥金,染青发。钦此。于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降造的紫檀木塔内药师佛七尊呈览。奉旨:着镀金。[7]
慧曜楼六品佛楼中六品诸佛的供奉大致完成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佛楼供奉的点点滴滴都倾注了乾隆帝无数的心血。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随着乾隆皇帝对密宗了解的不断深入,宫中六品佛楼的修建增多,乾隆皇帝努力实践着对密宗的修行。
-
对于佛教信徒而言,每日念诵经卷是种功德,但修造佛像并加以供奉更是一种福田。因此,清宫佛堂中供奉着大量造办处专为满足乾隆皇帝及皇室宗亲祈福之用的无量寿佛、白伞盖佛母、救度佛母佛像。这也是乾隆皇帝践行修身为佛的另一表现形式。
1.无量寿佛
无量寿佛是佛教中古老的信仰,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中都有着深厚的信仰基础和广泛的受众。对无量寿佛的信仰包括延长在世生命和对死后精神安详与往生极乐世界两种诉求。对于乾隆皇帝而言,除以上两点外,还有帝祚绵延这样的愿望,所以在清宫各处佛堂建筑中都有无量寿佛的身影: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金玉作)十五日,员外郎四德、五德催长大达色来说,太监鄂鲁里交金连三无量寿佛一尊、手持金刚一尊、珊瑚枝大小三支、珊瑚佛头两个,传旨交出珊瑚枝佛头照无量寿佛法身成造金镶珊瑚佛二尊。
于三月十九日员外郎四德、五德等来说,太监鄂鲁里交镶松石有背光铜佛一尊,系佛堂妆供。传旨,现造金镶珊瑚无量寿佛二尊,照此佛衣妆手镯、佛冠一样成造。[8]391,393
于五十五年七月三十日将所造得紫金璃玛无量寿佛九尊安在奉三无私呈进,交宁寿宫讫。
于五十六年正月初七日将造得高六寸六分红铜胎钑镀金背光座紫金璃玛铜无量寿佛三尊安在大合斋呈览,奉旨:着持进交佛堂。
于五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将造得高二尺五寸六分红铜镀金背光座紫金璃玛铜无量寿佛九尊安在养心殿呈览,奉旨:着交首领赵进忠看地方安供。[9]
从档案记载来看:首先,佛堂中所供佛像数多为“九”尊或者“九”的倍数,这应该与供奉的神佛,祈祷长寿的目的相同,寓意清朝政权与皇家成员“长长久久”的寓意;其次,乾隆朝所造佛像下均贴有“大清乾隆年敬造”款,但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后,所造佛像俱按年分刻款,以示年成。据此推断,这许是宫中每年所造佛像数量剧增的缘故,为了便于乾隆皇帝区分以及清楚地指导内务府造办处才实行此项制度;再次,从所造佛像尺寸来看,宫中无量寿佛像有大有小,大者许尺,小者几寸见长,应是为便于佛堂、佛楼、佛龛各处供奉所造。因此,举凡宫中礼佛之处,均有无量寿佛的身影;最后,从佛像材质来看,乾隆皇帝偏爱紫金璃玛①铜佛像,紫金璃玛合金技术属于“舶来品”,以此工艺制成的佛像多为西藏方面进贡之物,清朝宫廷内务府的工匠并未掌握此种合金工艺。当此铜像供奉于皇宫后,便受到乾隆皇帝的青睐。
① 紫金璃玛,特指一种由多种贵金属冶炼而成的珍贵合金材料,是自尼泊尔引进的一种合金工艺。“璃玛”是藏文“li-ma”的音译,在《藏汉大辞典》中的解释,“li”指用于制造器物的铜合金,也译为响铜。“li-ma”指响铜的器物。紫金璃玛的珍贵之处在于用料极为名贵,不仅有我们今天看起来仍十分名贵的金、银等金属,还有从西洋进口的五色玻璃面等。
不仅宫中各佛堂、佛楼中大量供奉着大小不一、材质不同的无量寿佛像已是稀松平常,而且每逢乾隆皇帝寿诞之际,无量寿佛的造像以及绘画也是必不可少的,据《内务府庆典成案》记载,每年乾隆帝和孝圣皇太后万寿节(逢五或十的整寿)时,内务府会根据往年惯例成造佛像,而其中无量寿佛是必不可少的,且数目较大。例如,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总管内务府谨奏:据钦派总理造佛事务处文开添造无量寿佛一千尊,需用赤金叶一百八十三两,贤界千佛一千尊,需用赤金叶四百六十七两[10]16。自乾隆五十岁寿诞之后的每个逢五或十的整寿的万寿节,宫中造佛处均会增加无量寿佛成造数量。例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七十寿诞时,内务府恭造“无量寿佛一万一千尊,贤界千佛一千尊”[10]18。不仅无量寿佛像的数量增加了一万座之多,而且朝中满汉文武大臣以及蒙古王公贵族为表孝心还纷纷上书认造无量寿佛,恭贺皇帝寿诞[10]18-25。朝臣们对圣意的迎合,也恰恰说明乾隆皇帝对无量寿佛的信持。
2.度母
早期佛教对于女性是排斥的,其神佛系统中更不可能出现女性神。公元400年后,随着大乘佛教的发展壮大,佛教神佛中才出现了度母、般若母、佛母等女尊。而度母位列莲花部众与无量寿佛一样成为祈求长寿的寿神,是在公元700年后以五方佛②为核心的金刚乘佛教建立发展起来之后。
② 五方佛是揉合佛教诸神与外来神佛形成的一个综合神系,共分为毗卢佛(佛部)为中心,统率阿閦佛(居东方)、宝生佛(居南方)、阿弥陀佛(居西方)、不空成就佛(居北方),五佛各有着自己的菩萨、明妃、护法等,形成了五个次神系。阿閦佛属金刚部,因其威猛的特点,很多护法神都出自此系统;宝生佛属宝部,其部诸神佛具有财富神的特性;阿弥陀佛属莲花部,与寿有关,如,无量寿佛、度母等。
在藏传佛教里,度母③的净土就是“极乐世界”,因此信仰度母,修持度母就是希望脱离苦难的人生,去往没有生、老、病、死的极乐世界。也正是因为信徒多种的宗教需求,所以度母才被赋予了众多宗教功能和权力,也就形成了多种颜色、多种形态的度母形象。也就是《佛说多罗菩萨经》中所讲的:“是多罗菩萨,本从阿字生。或生诸行相,不生亦不灭。是相如虚空,虚空性生故。随应现本相,相一多无碍。色相现无边,善寂体纯一。常现幻化相,密语真实语。”[11]在众多度母形象中,尤以绿度母与白度母最为著名。
③ 度母,全称圣救度佛母,我国古代称多罗菩萨、多罗观音,度母有许多不同的化现,包括有二十一度母、五百度母等等,皆为观世音菩萨之化身。
绿度母作为度母主尊,总摄其余二十尊化身之所有功德。她能救八种苦难,如狮难、象难、蛇难、水难、牢狱难、贼难、非人难,因此,又被称为“救八难度母绿度母”;白度母,又称“增寿救度佛母”,是无量寿物的眷属之一。在藏区,她与无量寿佛、尊胜佛母三尊合称为“三长寿”,是备受尊崇的寿神组合。但是在清宫佛楼的造像及绘画中,尊胜佛母被白伞盖佛母所替代,这种组合的出现表明清朝帝王希望“三长寿”的无边法力不仅仅局限于为皇家祈寿,更希望能够推及帝祚长久、国泰民安等更为广泛的范围。
因此,《清宫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出现度母造像的记载也是顺理成章的: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铸炉处)初四日库掌四德、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铜绿救度母一尊(有宣德款,右),铜弥勒佛一尊(中),铜不动菩萨一尊(左,胳膊上有磕处),传旨:着喇嘛认看,应添执事者添配,缺金处找镀金,厢(镶)嵌有不齐全处添配齐全,其有宣德款佛一尊将款刮去,并无款佛二尊,俱刻大清乾隆年敬造款。[12]723
乾隆四十一年五月(铸炉处)初五日员外郎四德、库掌五德、福庆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铜镀金文殊菩萨一尊,铜镀金绿救度佛母一尊,传旨:着照铜佛样款法身大小配造无量寿佛一尊成一堂,其铜佛二尊上金色,有不齐全处找镀齐全。
于二十三日将画得配造无量寿佛纸样一张冰原教处就有文书披萨、率救度佛母各画得样一张由报发往热河呈览,奉旨:无量寿佛照画样准做,其原交出旧有佛二尊上旧年款着照新造之佛一样刻大清乾隆年敬造。[13]
从档案记载来看:首先,乾隆朝以前,甚至在乾隆朝中前期,清宫内供奉藏传佛教诸神佛并未形成系统,多沿用明代宫廷供奉佛像为己用,只是经过简单地磨去款式后,对已有佛像进行修复和补镀金,来满足宫廷礼佛的需要。其次,经过三世章嘉活佛对藏传佛教神佛系统梳理和完善后,乾隆朝中后期的清宫造像和供奉,已经开始按照神佛部众陈设并加以供奉,如,无量寿佛、文殊菩萨以及度母的组合为一堂供奉。而且,此时的清宫造像工艺也得到了发展,造像程序从画样、做模到最后的成造,已经极其规范且有序,并加做年款以示区分。再次,如前文所述,紫金璃玛工艺传入前,清宫造像多用铜或者红铜料制造佛像,只是在完成后以金镀其表面。
3.白伞盖佛母
白伞盖佛母是印藏佛教中流行的“寿神”,可能是八宝中伞宝的神圣化[14]。西藏僧众相信其法力无边,只要站在其伞下便能祛除病痛。不仅如此,白伞盖佛母还能消灭魔障,破除恶咒,遏制灾难等法力[15]。由于白伞盖佛母具有赐福、延寿、消弭灾祸的法力,不仅在民间有着广泛信众,自元代开始,高居殿堂之上的帝王也颇为信持,信奉之风日盛。
《清宫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等清宫档案中关于白伞盖佛母成造与供奉的记载不胜枚举。例如:
乾隆三十八年(随园进哨)初十日,库掌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如意舟法林寺正殿内悬山上现释迦牟尼佛、无量寿佛、白伞盖等二十四尊现穿佛衣佛陀的衣服称之为袈裟。在佛教中,袈裟功德殊胜,凡有袈裟所在,一切天龙善神皆会给予守护。糙旧,着向四执事要妆贮红洋锦做佛衣牙子二道。[12]223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灯裁作)二十日,员外郎四德、库掌五德、福庆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画像佛四十四张,传旨照养性殿西暖阁楼上现供佛像一样镶边成做在养性殿西暖阁楼上供,钦此。
计开,五方佛五张、白勇保护法一张、六臂护法一张、尊胜佛母一张、白伞盖一张……[16]
正是由于清朝皇帝对白伞盖佛母的信奉,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进京朝觐期间就曾奉乾隆皇帝圣谕,撰写《白伞盖佛之祭祀坛城例式经》:
小僧章嘉呼图克图谨奏:为奏闻事。……小僧前来时,曾奉圣谕:俟班禅额尔德尼来后,若编制一部可供众人唪诵吉祥经,则利于诸事。钦此。小僧告于班禅额尔德尼,弟子吾思之,喇嘛沿途可行,若编制一部经书为善。
言毕,班禅额尔德尼云,编制殊颂《白伞盖佛之祭祀坛城例式经》,翻译为满、蒙、汉文,若众人讽诵,可愈兴政事。即可保佑地方年丰,亦可消弭灾祸,增加福瑞。[17]943
除奉旨编制《白伞盖佛之祭祀坛城例式经》外,在京期间,六世班禅还在参观圆明园时,为园中太监喇嘛讲授《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18]
-
乾隆皇帝接受三世章嘉活佛的建议,于乾隆十四年(1749),仿西藏托林寺坛城殿,修建雨花阁。佛楼中供奉密宗四部。雨花阁与清宫中其他功利性的烧香念佛的佛楼不同,它具有浓重的宣示教理的意图,这是对藏传佛教密宗四部及其神系思想的完整、系统地呈现。作为清宫中最重要的佛堂建筑,受弥陀净土思想影响,为皇室祈福延寿这一诉求而修造的西方极乐世界道场必然会在雨花阁佛楼建筑中有所体现[19]。根据档案记载来看,乾隆九年(1745),雨花阁佛楼建筑及其供奉已初具规模。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安养道场位于雨花阁佛楼第一层“智珠心印”殿内,除了仙楼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安养道场”的横条指示外,佛龛中供奉的无量寿佛、四臂观世音菩萨、尊胜佛母、白救度佛母、积光佛母、大悲观世音菩萨、绿救度佛母、随求佛母、白伞盖佛母等莲花部座诸神佛,以及在正龛两侧的题记中提到的“应念无量寿佛经”,都体现着对无量寿佛的信仰和为皇室祈福延寿的宗教思想。总之,向往西方极乐世界的思想作为雨花阁佛楼所要表达的重要主题之一,在布局与陈设中对其有着淋漓尽致地体现。
在乾隆皇帝心中始终认为五福中的寿康安宁均授于天,只有德行备至之人才能够成为上天眷顾的幸运儿,接受上天的福赐。在他看来,天地万物的气与春天,天理与仁政才是匹配的。只有君主修仁心、施仁政,才能够真正做到普度天下苍生,共享西方极乐世界的无欲、无忧。就此而言,乾隆皇帝藏传佛教的弥勒净土信仰修行中已经渗透有中国传统儒家的“德”的思想。
一. “六品佛楼”与密法修行
二. “莲花部”神佛供奉与修行祈福
三. 精神归宿与“西方极乐世界道场”
-
佛寺既是喇嘛生活起居之处,也是开展宗教活动的场所。雍正皇帝曾说“演教之地愈多,则佛法之流布愈广,而番夷之向善者益众”[20]。清前期的几位帝王为合内外蒙藏之心,实现帝国的千秋大业,频繁出资新建或者修缮帝国域内的藏传佛教寺院,其目的就是为彰显尊崇黄教和优礼高僧。主要是在北京、承德、五台山这三个中原地区,其中尤以北京为甚。
清朝入关后,在京中见于记载的、最早修建的藏传佛教寺庙当属慈度寺:“慈度寺建于本朝初年,在功德林之东北隅。俗名黑寺,以其与双黄寺同为喇嘛所居,此覆以青瓦,故有是称”[21]。顺治二年(1645),察罕喇嘛从盛京赶至京中,于正黄旗校场以北选址建庙,因位于慈度寺后方,故又被称为“后黑寺”[22]。
根据《钦定理藩部则例·喇嘛事例》记载来看,自顺治元年起,至乾隆年间,为弘扬佛法,几位清帝下诏在北京新建、翻修寺庙就多达30余座:雍和宫、东黄寺、西黄寺、弘仁寺、嵩祝寺、福佑寺、妙应寺、梵香寺、大隆善护国寺、嘛哈噶喇寺、长泰寺、普度寺、普胜寺、慧昭寺、化成寺、隆福寺、净住寺、三宝寺、三佛寺、圣化寺、慈佑寺、永幕寺、大正觉寺、阐福寺、同福寺、宝谛寺、正觉寺、功德寺等。而仅乾隆一朝就新建、维修藏传佛教寺庙10多座[23]。
乾隆皇帝在京中修建的众多藏传佛教寺庙中,尤以雍和宫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乾隆九年(1743),为了更好地发挥北京的宗教影响力,感召更多的蒙古地区藏传佛教信众,乾隆皇帝决定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庙,并建立扎仓和四大经院,改变藏传佛教寺院及高僧分布不均的局面,使北京成为黄教的中心,以及信众尊崇的佛教圣地:
推究佛学之广博精深,归于喇嘛之勤奋。西昭(引者注:此处应指西藏)乃自古以来传播佛学,创立黄教之地。其于佛学理论、习经以及戒律等,甚属严谨,为各地佛学之典范。……其中北京地域宽广,更应按照西昭之例创立学院,教习喇嘛,以弘扬黄教。惟所有寺庙之喇嘛,本土人居多,除遵守戒律、诵经外,辩经、坐禅、传授佛学高深理论者无多。朕念雍和宫乃甚属吉祥伟大之所,今在闲置,依照宫殿之坐落、样式,稍加修缮,辟为大杜罔,作为供佛及喇嘛会集之场所。[17]2
三世章嘉活佛领命负责雍和宫的改建工程,按照藏传佛教寺庙的规制和建筑风格,拆除影壁、牌楼等带有明显汉式传统建筑风格元素,改造或翻建雍和门殿、雍和宫大殿、永佑殿、法轮殿、讲经殿等殿堂。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世班禅进京为恭贺乾隆七十大寿,从扎什伦布寺启程,并于次年九月抵达京城。为迎接六世班禅,乾隆皇帝还特意修缮雍和宫中的班禅楼、戒台楼、法轮殿,以为班禅莅临雍和宫礼佛时休息与讲经之用。六世班禅在抵京后,与三世章嘉一同在雍和宫戒台楼为乾隆皇帝讲解《迅捷智慧六臂依怙随许经》[3]280。
雍和宫改建为寺不仅进行了上述大规模翻修改建工程外,在彩画装饰、成造佛像及佛像装严①等方面也颇为用心,所用各种金、银、铜、铁、锡等各种金属多达千、万两,例如,在《总管内务府大臣三和奏请支领雍和宫正塔等项镀金所需赤金折》中就对雍和宫殿宇彩画及寺庙内及佛堂内佛塔所需镀金情况有着详细记载[17]178。大量地使用金、银等金属,不仅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对雍和宫改建寺庙的重视,同时也是清朝国力强盛以及丰富物质的一种反映。雍和宫改建为寺后,在整个乾隆一朝还历经了数次的维修和新增建筑,这在《雍和宫满文档案》中也有多处记载[17]285-286。
① 又称“装藏”或“装脏”,在藏传佛教中,佛像必须依传承的仪轨如法制作及装藏开光才能供在佛堂,由具德金刚上师依传承依轨开光,迎请智慧佛与三昧耶佛无二融入佛像,这时才具足了诸佛本尊的加持,一尊如法装藏的佛像其加持是不可思议的,可作为世代相传的珍宝。
雍和宫经学院的设立引起了西藏宗教上层和蒙古各部宗教领袖的强烈反响,在达赖和班禅眼中,雍和宫改建为寺庙的举措是乾隆皇帝尊崇藏传佛教的又一重大举措,藏传佛教学校的建立令他们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当年元朝崇佛的盛景,心中无比的喜悦,遂纷纷上书表示感谢[17]173。在他们看来,西藏高僧驻京讲授藏传佛教,既可弘扬佛法,增强宗教影响力。同时,还可以通过高僧大德的宗教影响力形成良好的宗教氛围,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帝国统治者情感倾向,甚至是帝国决策制定。
除此之外,乾隆皇帝还在宫廷内和皇家园林中、五台山、承德,以及归化、宁远、青海等处兴修藏传佛教寺庙。
-
时至乾隆朝,汉、藏、蒙文《大藏经》无论在体例还是内容编译上都已相当成熟,作为基础,可为满文《大藏经》的编译者所借鉴,此为其一;其二,身为国师的三世章嘉活佛领命负责此项编译工程,其个人不仅精通佛理,而且通晓梵、蒙、藏各种文字;其三,当时的北京早已被乾隆皇帝营造成相对于西藏的另一个藏传佛教“中心”,吸引着大量的蒙藏高僧大德驻留。综合以上三个因素,满文《大藏经》的编译工作紧张但有序地开展起来。
落实到操作层面,如此大部头的佛教典籍汇编在具体的编译工作中佛教典籍的取舍、编译的原则等具体问题又是如何操作的,依据又是什么?这在《乾隆朝上谕档》中都能找到答案:
将藏经所有蒙古字、汉字两种细心校核,按部翻做清文,并命章嘉国师董其事,每得一卷即令审正进呈,俟朕裁定。今据章嘉国师奏称,唐古特《甘珠尔经》一百八部俱系佛经,其《丹珠尔经》内有额纳特珂可(引者注:此为印度)得道大喇嘛所传经二百二十五部,至汉字《甘珠尔经》则西方喇嘛及中国僧人所撰全行列入,今拟将《大般若》、《大宝积》、《大般涅盘》、《中阿含》等经及大乘律全部翻译,其五大部支派等经八种,并小乘律皆西土圣贤撰集,但内多重复,似应删繁就简。[24]282
编译工作是汇聚在京的诸多蒙藏大德在三世章嘉活佛的指导下,按佛经名录,分部翻译的。在具体操作中,以汉文版《大藏经》为基础,以蒙文版为辅,进行校刊、核对,通过与已经出版的汉文、蒙文《大藏经》比对,来处理一些专有名词的翻译技术问题,从而保证编译的准确性和质量。每翻译出一卷,均要交由乾隆裁定,确认无误后,方可刊印。
在编译佛经的选择上,除了“唐古特《甘珠尔经》一百八部俱系佛经,其《丹珠尔经》内有额纳特珂可得道大喇嘛所传经二百二十五部,至汉字《甘珠尔经》则西方喇嘛及中国僧人所撰全行列入”之外,乾隆皇帝还将《大般若》、《大宝积》、《大般涅盘》、《中阿含》等佛经以及大乘佛教律部佛经和五大部支派等经八种,以及“小乘律皆西土圣贤撰集”,列为翻译内容。经过筛选后,去除重复的内容,删繁就简后,得到大乘论、小乘论佛经共三千六百七十六卷[24]283。高明道根据《满文大藏经》的汉文目录[25]拟出其内容体系,并指出:从佛经内容显示,大部分为汉文经典的重译,且更多承袭汉文《大藏经》的组织只是受到藏传佛教传统的影响,将“密教部”独立出来。[26]
到了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一月二十五日,满文《大藏经》中《大般若经》第一函已经编译完毕并呈乾隆皇帝预览:
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记事录)初四日,笔帖式和宁持来军机处抄来堂抄,内开臣等谨奏,臣馆前经奉旨:将《大般若经》上紧装潢一部赏班禅额尔德尼。钦此。钦遵,臣等与章嘉呼图克图商酌,照依妙应寺供奉之蒙古秘密经式样,现将《大般若经》首套二十八卷装潢一套,完竣时即行呈览等因,奏闻在案。今谨将装潢完竣之《大般若经》首套二十八卷恭呈御览,俟命下,臣等会同造办处将《大般若经》四百卷计十四套照式上紧装潢,以备赏给,为此谨奏等因,缮折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呈览,奉旨:知道了。其经首大签上应添写西番、蒙古字样,堆字上金应再加亮。钦此。
于二十七日……今查《大般若经》共计四百卷,应装潢十四套,本处现在将经卷上紧刊刻刷表赶办外,至此经首套已装潢完毕。……至绘画佛像、经边、堆砌字体系本处行走僧人承办。[8]583-584
资料显示,清字经馆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奉命加急赶制、装潢已编译完成的《大般若经》,其目的是为馈赠来年抵达北京的六世班禅。因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适逢乾隆帝七十大寿,这对清王朝来讲是极其重大的庆典活动。前来参加此次乾隆帝万寿节庆典活动的除蒙古诸王公和外国使节之外,还有六世班禅这位来自西藏的贵宾。他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从西藏出发,乾隆皇帝对他的到来尤其重视,除降旨命驻藏大臣及随行扈从陪其东行,还令沿途各站悉心照顾,小心护送其至承德。为了保证在其到来之前能够见到帝国精心编译的满文《大藏经》,所以,乾隆皇帝才命清字经馆加紧刊刻、装潢已完成的《大般若经》一部,以备赏赐班禅之用。
乾隆皇帝不仅要亲自审阅内容,他还针对满文《大藏经》的装潢格外重视,力求精美与华丽。除了简单的命造办处在“经首大签上应添写西番、蒙古字样”,经卷护经板上绘制藏传佛教尊神并将“堆字上金应再加亮”之外,其实装潢的每道程序都记录在《清宫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成为一种范式[27]。
-
西藏方面给予清朝皇帝“文殊菩萨”的尊号,虽是其政教传统,但也是一种正视清朝力量后的一种政治交易。面对达赖喇嘛和藏地僧众如此称颂,乾隆皇帝内心是喜悦的。例如,雍和宫中的巨幅绘画《乾隆坐禅图》呈现的就是乾隆皇帝头戴黄色桃形帽,身穿黄色法衣,披红色哈达,做西藏格鲁派喇嘛的打扮高座莲花台座上,在台座的左右和上下有成千上百的带有明显印度风格的菩萨和藏地喇嘛围绕在其左右,有的站、有的跪、有的隐现在云间、有的亦坐于莲花台座上,据记载,这些藏地喇嘛形象大多是以乾隆朝驻京各蒙藏呼图克图、札萨克达喇嘛为原形,绘画中还有一首藏文所写像赞诗作。金梁对其进行翻译,并记载于在《雍和宫志略》中对其进行了详细描述,并翻译诗作:“睿哲文殊圣,应化为人主。广大难思议,善哉大法王。安住金刚寨,坚固不退转。随意大自在,殊胜世间尊。”[28]诗作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乾隆皇帝这位世俗世界的“人主”与智慧的化身“文殊菩萨”之间有着应化的关系。正是由于文殊菩萨化身入凡尘行法、布道时往往有多种法身,未有定数。因此,此诗中所描述的文殊菩萨就化身为“世间尊”,也就是在乾隆皇帝统治时间内。结合前诗来看,此赞诗直接表达了乾隆即文殊菩萨在人间的化身,不似殊像寺题诗中那般含蓄,前后风格不统一,应不是出自乾隆本人,但能够呈现在画像上,当是得到乾隆的默认。
乾隆皇帝既然已经在名义上认可这种来自西藏方面的尊号,那么,将世间的“皇帝”等同于宗教中的“文殊”,将二者形象结合经艺术加工后,使之实体化,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乾隆朝供奉在北京雍和宫与西藏布达拉宫的“乾隆御容佛装像”唐卡画、挂轴画,以及佛经中乾隆皇帝的御容画正是这样的尝试。
唐卡这种绘画形式是藏传佛教艺术所独有的艺术表现形式,是藏传佛教中最为常见的宗教宣传品、法物,因其具有极强的佛教象征意义,所以多用于藏传佛教佛法宣传以及、服务于修行的信众。早在元代,将皇帝形象绘入唐卡当中就已出现,但因元代皇帝多以虔诚的佛教信徒的身份出现,在唐卡中也多以供养人的形象出现,以侍上师。乾隆皇帝则突破这一点,在欣然接受西藏方面赠予的“文殊师利皇帝”称号后,以文殊菩萨转世于世间统治者形象出现在佛经及唐卡中。例如,《清宫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记载的乾隆三十七年(1772)所成“画依勒尔经御容佛像”:
乾隆三十七年四月(金玉作)初三日,库掌四德、五德,笔帖式福庆来说,太监厄勒里传旨:中正殿现画依勒尔经御容佛像,着查库贮亮玻璃一块呈览。[30]
但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还是乾隆皇帝的御容佛装像唐卡。综观现存于世的乾隆佛装像唐卡发现,乾隆皇帝居唐卡中心,作为祖师形象,带僧帽,着袈裟,左右手分施法印,双肩莲心有象征文殊菩萨特征的智慧剑和梵荚。在画像中,还有本尊、罗汉、菩萨、护法等佛教诸神,围绕其上下左右。这是对他自诩文殊在世圣主形象的完美诠释,体现其护持佛法、拯救苍生的责任。
具有此极强表征意义的御容佛装像唐卡的绘制,在《清宫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的记载中较为少见,只有一幅供奉在养心殿中画像的记载,特摘录如下,以图管中窥豹:
乾隆四十三年三月(灯裁作)二十日,员外郎四德、五德来说,太监厄勒里交御容佛像一张(系中正殿佛像喇嘛伊什画),传旨:着照养心殿东暖阁大案上箱内挂像佛一样镶边成做。
于四月一日,员外郎四德、五德来将御容佛像一张照养心殿东暖阁大案上箱内挂佛像一样镶边挑得内库万寿灯笼锦一块做牙子,挑得红黄绿石青片金各一块,白片金因内库无存,挑得月白金片一块,交太监厄鲁里呈览,奉旨,俱准用。配白檀香楣杆、卷杆,铜镀金厄其里轴头。
于九月十六日,员外郎四德、催长大达色、副福来将御容佛像一轴,配得鞴皮画金箱盛装,交太监鄂鲁里呈览。奉旨:着交佛堂。[30]
乾隆御容佛装像唐卡,这种将菩萨形象与皇帝形象完美结合并具体化、实体化的表现形式出现在北京雍和宫与西藏布达拉宫这些地位显著、影响力极大的政教中心,表明清帝在面对蒙藏信徒时的一种信心,这种仪式化、艺术化的表现能够使蒙藏信众在皈依信仰、虔诚敬佛的同时,也对帝国的君主产生敬畏之心。这样一种较为符合西藏传统政教结合的方式,有助于清朝皇帝在蒙藏广大信教地区建立威望,催生蒙藏民众与上层高僧心中对强大帝国的向心力。
-
跳布扎,在清代典籍中多被称为“打鬼”,是藏传佛教中一种驱魔散祟、祈福迎祥的法事活动,因以边诵经边舞蹈的形式呈现,也被后世称为“金刚驱魔舞”。此法事活动是随着清代宫廷对藏传佛教的尊崇而广为奉行。正如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的记载,最先流行于京中各寺,雍和宫改寺后,每年除夕在中正殿前和正月里在雍和宫举行的法事活动,成为定制[31]。这种流行于宫中与雍和宫的驱邪祈福的法事活动流程鲜见于史籍记载中,只能够从笔记以及档案的零星记载中,对其大概规制、流程和所需服饰、法器等有个初步了解:
以长教喇嘛披黄锦衣乘车持钵,诸侍从各执仪仗法器拥护;又以小番僧名班第者,衣彩胄,戴黑白头盔,手执彩棒,随意挥洒白沙;前以鼓吹导引,众番僧执曲锤柄鼓,鸣锣吹角,演念经文,绕寺周匝,迎祥驱祟。念五日,德胜门外黄寺行亦如之。[32]
在《和硕庄亲王允禄奏闻遵旨询问章嘉呼图克图如何应用新造跳布扎饰物片》中记载了清代雍和宫跳布扎,诵念时轮王佛、上乐王佛、秘密佛三种佛经时的部分服饰情况:
(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遵旨询问章嘉呼图克图如何应用新造跳布扎饰物,呼图克图告知,此新造使用饰物者,有时轮王佛、上乐王佛、秘密佛、财宝天王四种,现若欲使用,诵财宝天王经时要用护法饰物。诵时轮王佛、上乐王佛、秘密佛时,使用天女玲珑饰物。[17]385-386
不难发现,整个跳布扎法事活动中的服饰并非一成不变,参加表演的喇嘛所穿服装与使用的法器,是与不同章目的舞蹈表演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佛经诵念相配套。单就此段记载来看,跳布扎活动的每个流程中需准备的相关服饰、法器都是是相当繁杂的。在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清代帝王会及时寻求答案,力求做到原汁原味,可见其对此事的重视。
不仅如此,对整个法事活动的参与者的培训,乾隆皇帝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从乾隆十八年(1735)五月十六日多尔济上奏乾隆的奏折中,可以看到乾隆皇帝向西藏方面寻求精通跳布扎的喇嘛高僧前往京中传授跳布扎舞蹈的信息[17]374。这些从西藏远道而来的传授者,多选自于跳布扎的起源地——扎什伦布寺,此外,还有哲蚌寺、夏鲁寺、宁塘寺中精于此舞的年轻喇嘛。正是由于他们这些藏传佛教文化使者的悉心教授,和乾隆皇帝的重视与严格要求,古藏地古朴、神秘的金刚驱魔舞才得以在汉地原汁原味地呈现。对于这些传授者辛劳最好的认可或许就是帝王的封赏: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查得,前次正式念经做道场时,参与之呼图克图、喇嘛等皆与赏。此次不过是训练,按理尚不至赏赐,虽圣主特施恩,赏赐伊等学得快者,亦唯应议赏跳布扎之小喇嘛等。臣等看伊等审查送来之册,皆得议赏,似为不妥。既然惟应赏跳布扎之小喇嘛,则赏跳布扎一百三喇嘛每人银各二两。此内领跳者一人,跳鹿一人,加倍各赏四两,教习五人每人各赏五两。赏银从广储司支领。[17]451
正是由于乾隆皇帝对金刚驱魔舞驱魔其古朴、神秘的艺术特点的欣赏以及对其散祟、祈福迎祥的寓意偏好,有清一代,雍和宫的“金刚驱魔舞”从未停止过,直至清末。也正是实物资料和法事活动的参与者的存世,才使得这一清宫中最重要的法事活动的原貌为后世所了解。
一. 广建佛塔与寺庙
二. 诠释佛法与编印满文《大藏经》
三. 实体化的佛法宣传:唐卡绘画
四. “跳布扎”:藏地传统法事活动的皇家再现
-
在借鉴前朝成功经验和的合理且行之有效地政策、理论框架基础上,乾隆皇帝运用成功的菩萨王形象塑造,以及合理运用藏传佛教的宗教力量助力清王朝最终实现对蒙藏的统治。通过乾隆皇帝的不懈努力,包括满、蒙、藏在内的文化、政治共同体在乾隆朝最终得以完成。
-
从努尔哈赤开始,皇太极到玄烨、胤祯乃至弘历,这些清王朝的统治者在对待明显优于自身的文化时,从未表现出统治者的傲慢,以及狭隘的地域、民族、文化偏见。相反,清初的几位皇帝非常能够掌握情势,借用各民族传统、文化或宗教上的优点来统治人民,推动政务。
乾隆朝是清王朝疆域不断拓展,更加多元的民族、文化、信仰共存的局面形成的时代。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统治者,乾隆皇帝既要保持自己的满洲萨满信仰习俗以维护自身的文化特征与统治民族地位,又要推崇儒家文明以笼络汉人士大夫来统治中原,同时,还要包容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文化与宗教资源,安定帝国王朝的西、北部边疆。这种尊重和利用不同信仰、文化,构建一种多重的、统一的内在统治理念和外在的皇权形象是乾隆皇帝统治智慧的产物。
在每个不同的文化架构中,都有其独一无二的文化核心,这个核心有助于接受该文化的群体成员能够认清自身的政治、社会地位,这个核心也就随之会成为文化、社会和政治汇聚的所在地,这就是所谓的“文化架构”或“主导性虚构”。[33]这种文化架构被认为是永恒不朽的“传统”,其合理性无需辩驳,便以成立。将此理论置于传统的中国历史社会中,传统的、至高至上的宗教领袖以及皇权天授的帝王形象都是其文化架构中的核心。作为这一文化核心既有整合文化形象、文化符号,维系政治、社会的作用,同时也能够确立和维持正统性的核心作用。从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取得“文殊菩萨”形象的乾隆皇帝实际上就成了藏传佛教这一文化的核心。
乾隆皇帝从修行佛法、佛法弘传等方面塑造与完善来自藏地的“文殊菩萨”称号,以及转轮王的化身身份认同。建构起了一个蒙藏文化圈最能认同、接受的“朕即佛祖”的象征符号,激发蒙藏人民赋予自己最大的权威。利用这一形象极强的宗教影响力来左右蒙藏信徒思想,亲自介入藏传佛教宗教事务:改建雍和宫为藏传佛教寺院并设立四大经学院,广招蒙古喇嘛入京学法;在承德修建藏传佛教寺院,将避暑山庄建成蒙古各部首领朝觐和礼佛的中心,将蒙古各部的注意力从西藏转移到了承德。从而在内地最终形成了北京、承德、五台山三个以王朝为中心的藏传佛教中心。
金瓶掣签制度的确立不仅使得清王朝更加有效地参与到藏地政治、宗教事务中,增强了对藏传佛教的控制力;此举还奠定了雍和宫藏传佛教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弱化拉萨对蒙古地区的影响,使得蒙古地区宗教上层领袖更加倾心于清王朝。而设置驻藏大臣以及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实现了清王朝对西藏地方政治事务的直接管控。其中尤以《章程》更能体现乾隆皇帝几十年治藏的经验,它使得清朝对西藏的治理规范化、法制化,成为指导和规范西藏政府执政的“行动指南”。
-
清王朝自入关后,便以整个“中国”的统治者自居,但直至乾隆时期,才真正意义上完成“天下一统”。这不仅使后金政权摆脱了原有的区域化的“内部朝圣”现象,而且使其政治朝圣行为更多地转向中原核心地区(北京与承德),从而构建起一个整体性的“中华”的概念。这种“天下一统”不仅包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即满、蒙、回、藏、汉多个民族在疆域内共存、共生。同时也包括多民族共同孕育、发展光辉璀璨的中华文化。尽管在此过程中,清朝皇帝从未间断对其“满洲根本”建设,但他们仍旧就不断努力、尝试弥合与蒙、藏、甚至是与汉之间的差异,希望得到各个族群对其政治、文化的认同。
因着蒙古的关系,清王朝的视线投向藏传佛教的圣地——西藏。藏传佛教文化是以一整套艺术形象和艺术手段为信仰服务的宗教文化,在宗教观念和精神的同时不失审美价值。对于乾隆皇帝而言,藏传佛教及其文化内涵是外来的、极具吸引力的。在与藏传佛教的长期互动中,他自然而然地就会受到藏传佛教文化的浸润,倡导并大力发展。
首先,满文《大藏经》的编纂与刊印,解决了藏传佛教语言的译释问题。将蒙、藏佛教语言、词汇翻译为满文,即改变了《大藏经》“外邦之物”的形象,也改变了乾隆皇帝及广大满人信徒个体思维习惯的不适应性,有利于藏传佛教文化在满人中广泛传播。同时,也为清王朝的宗教、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其次,藏传佛教造像及绘画艺术在清宫中得以繁荣发展,这是多民族共同参与的结果,是杂糅多民族文化元素与独特技艺的产物。有了满、蒙、藏、汉,甚至是外邦人士的参与,藏传佛教文化的形象、工艺、审美特点不再单一,打破了原有的“区域化”特点,从而呈现出多族共创、多族共荣的文化特点。再次,以无量寿佛、白伞盖佛母、救度佛母为代表的藏传佛教“莲花部”神佛形象深入传统祈福文化,在丰富中国传统祈福文化内涵的同时,它们也渐渐深入人心,作为独具特色的清王朝祈福文化的一部分被接受与传承。
正是由于乾隆皇帝的接受、吸纳和大力发展,藏传佛教文化才不再滞留于清朝宫廷文化的表层,渐渐扎根于清朝宫廷宗教文化深层结构中,成为清王朝文化中另一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化”其实就是以清王朝为主导的融合疆域内各民族文化于一体的王朝共同文化。乾隆皇帝通过这样的共同文化建构,目的在于形成是一种各族共荣“中华”的局面,以及各族共有的“中华”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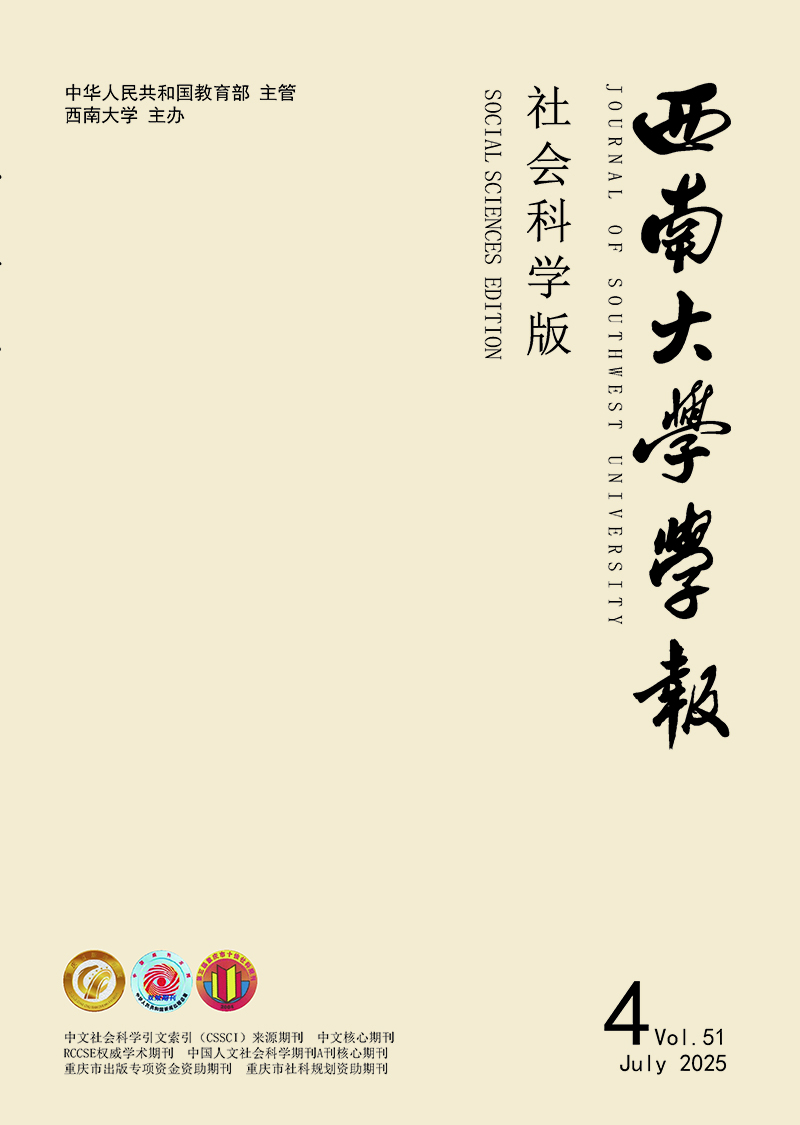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