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ML
-
回顾早期语文课堂,诗歌进入课文是随着民国新学制开始的,而在更早的晚清新学“癸卯学制”中,诗歌与文学教育无缘。1904年颁布《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学堂章程》,其中涉及文学教育的仅为“读经讲经”“中国文学”两门课程。“读经讲经”课程即“《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初等小学必读之经”,“《诗经》《书经》《易经》及《仪礼》之一篇为高等小学必读之经”,而中学则读“《春秋左传》及《周礼》两部”。“中国文学”课程,高等小学“即教以作文之法……兼使学作日用浅近文字”,中学则“年已渐长,文理略已明通,作文自不可缓”②。可见当时的文学教育,一重儒家经典,二重作文,似与诗歌无涉[1]。文学观念和语文观念的局限,导致诗歌不能进入课堂教学,李白、杜甫虽在此时早已确立其在中国诗坛的崇高地位,但同样被拒之于学堂之外。
② 本文所有清末和民国官方教育文献,不单独出注者,均出自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下册,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
现代学制必然与真正的现代社会紧密相连。帝制灭亡,共和制来临,具有真正新学意义的新学堂随之问世。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全国基础教育使用教育部审定的中小学国文教科书,这就意味着新学的开始。由此带来的是文学观念大变,语体文教学突破旧时读经与作文之法。《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1912年初版开始收录诗歌,李白、杜甫诗歌正式进入到中小学中国文学教育课堂。
李白、杜甫诗歌入选课本的最早时间是1912年,即民国元年。民国成立之初,各学段课本还只是急就章,李杜诗入选情况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12年,李白诗《东海有勇妇》《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游洞庭湖》、杜甫诗《前出塞(磨刀呜咽水)(单于寇我垒)》《后出塞(男儿生世间)(朝进东门营)》同时出现在小学二年级[2],杜甫《义鹘诗》入选小学三年级[3],李白《从军行(百战沙场碎铁衣)(从军玉门道)》出现在小学四年级[4]。李白诗入选中学课文,最早的是《玉阶怨》《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作》《春思》出现在初中一年级[5],《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入选中学二年级[6]。同年,该社初中一册选入杜诗《后出塞(男儿生世间)》[5],初中二册全选杜甫组诗《秋兴》完整的八首而非某一首[7]。这样选诗极具个性,虽是属于孤篇性质的选文,也见得民国学生的语文接受度相当之高。
从民国期间语文课文入选的李杜作品总量看,二人的诗文入选均在1930年代进入高峰。以首次入选时间统计,分别为李白98首、杜甫83首。
民国时期李白作品入选课文按诗题计有84题,其中有组诗8组、22首,按首计共98首。从目前收集的材料看,在不同教材(以下不一一注明)中最早入选的情况见表 1:
民国时期杜甫作品入选课文按诗题计52题,其中组诗9组、40首,按首计83首,详见表 2:
由上可知,李杜诗入选课文在1930年代有明显增长,此时期的篇目增加多是在一些有个性的读物中。也即是说,通过近20年的教学实践及各方反馈的意见、学术界的影响等,李杜诗篇入选基础教材的范围大体确定。
再看近70年大陆教材历年曾入选的李杜诗(表 3):
由此基本可以确定,百年间在不同教材中入选的李白诗文有103篇、杜诗有90篇。在这样一个总篇目下,不同时期或学段的学生,在课文中最多接触到十余首李杜诗,这构成了百年间国人对李杜其人其诗的初步认识。
从学术方面考察,可以肯定,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教育学界、中小学教材研究界及出版界,还是古代文学研究界,对于百年间李杜作品入选语文教材的研究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入选教材的研究均是空白,尚未见到相关研究成果。而对百年间入选现代学制的中小学语文课文的古典作品进行统计和比较研究,从中小学生语言接受度方面研究历来选编情况,并从提升国民国学素养短板角度,对中小学课文的难易度、古典作品入选量和学段关联性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并对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入选篇目提出建议,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文化自信的当下,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
-
这样一个广泛的李杜诗篇目,是在什么样的教育背景下进入中小学课文的呢?这涉及百年间前后期教材使用的时代特点。
从癸卯学制到民国新学,官方均颁布教学大纲。民国教育部对各学段语文教学的目的、意义及内容作出了相应规定,还重点对一些教材进行了审定,出现了注有“教育部审定”字样的教材,即部定教材。教育部也允许地域性教材和自编教材同时出版发行,并由学校选用。如中华书局1935年版《初中国文教科书》就注明“遵照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新课程标准,广东省教育厅颁布教学进度大纲编定”,可见是为广东省编写的具有地方统编意味的教材,其《实验高中国文》亦具有实验性质。注明与部颁标准和省教育厅规定的教学进度的关系,说明也具有半官方性质。与之相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教材由省市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导,同样要根据部颁大纲来编写。
由于民国时期的大学录取不是全国统考,故教材指挥棒作用相对弱化。当然,教育部审定的教材应是多数学校的首选。以《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为例,由庄俞、沈颐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教育部审定,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6月初版,高等小学校学生春季始业用,到1913年12月已重印99次,其影响力可见一斑。对民国时期主要教材进行分析,发现主导基础教材的出版社集中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等几家,原因是教育部审定的语文教科书主要由这几家出版发行。从李杜诗的入选看,这几家的教材也起着主导作用(数据详后)。
世界书局在民国时期是有影响力的书局之一,但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相比,其出版物除《高中国文》《初中国文》用的是通行的中学课本名称之外,其他更类同于教辅或个性化特色鲜明的读本,如《高级国语文读本教学法》《新主义国语读本》《朱氏初中国文》(朱剑芒编),《创造国文读本》《言文对照国文读本》《杜韩两氏高中国文》(杜天縻、韩楚原编)。世界书局的各种教材共选李白诗16首、杜甫诗12首。立达书局教材所选杜诗13首、李诗8首,由罗根泽、高远公编,黎锦熙校订,是典型的名家编教材,重点是为中学生编读本,书名为《初中国文选本》《高中国文选本》,1933年出版,杜诗长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首次入选高中读本,李白《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入选初中选本。相同的情况还有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相关中学生读物有《初级中学北新文选》(姜亮夫、赵景深选注)、《高中混合国文》(赵景深编)、《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赵景深编)。
地方性的统编教材还有南京书店出版的《新学制中学国文教科书高中国文》,徐公美等编注,江苏省立中学国文学科会议联合会校订;中学生书局《高中标准国文》,由江苏省教育厅修订。《高中当代国文》由柳亚子校订、薛无竞注,是典型的名人挂帅。文艺书局的《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注明“依照教育部颁行之二十二年度国文课程新标准编辑”,见出半官方性质。
一些有影响的名校也有自编教材。南开中学自编《初中国文》,北师大附中选订《初中国文读本》,由文化学社出版。中化书局、福州国光社均有自编课本。震东印书局印行的《国文读本》,由志成中学国文学科编辑委员会审定。
上述出版机构都在其课文或读本中选入了李杜作品。由于民国时期教材具有现代学制之初的探索性、多元性,编者个性化特征鲜明,只在某一教材出现一次的李杜作品在入选总量中占有不小的比例。据现有资料,各出版社在其教材课文中入选李杜诗的数量见表 4:
在各出版社的李杜诗入选语文课文中,各家首选的意义似更重要。首次选入是需要学术眼光和胆识的,前无古人难,后有来者易。对作家作品的选择体现了选者的水准,从课文的入选和首选也可以感知编者的学术眼光和对李杜诗的态度,能够了解出版社的立场并评估其学术史价值。在上举各教材中,各家首选李杜诗的情况见表 5(由于篇幅原因,不一一对应作品和相关年级):
其余书店或出版社,虽选有李杜诗但无首选作品。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遥遥领先,足见在基础教育阶段承担部颁教材的出版单位对国学传承以及对李杜诗进入课文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从部颁教材看,杜诗有这些作品:小学有《前出塞(磨刀呜咽水)(挽弓当挽强)(单于寇我垒)》《后出塞(男儿生世间)(朝进东门营)》《赠卫八处士》《独步寻花》;小学、初中、高中均入选有《石壕吏》;高中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佳人》《羌村三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李白作品,小学无,初中有《送从侄耑游庐山序》《峨眉山月歌》《早发白帝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高中有《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把酒问月》《月下独酌》《采莲曲》《忆秦娥》《菩萨蛮》。
民国虽有部颁教材,但却不是一统天下。民国教材的多样性与教育体制尤其是升学体制密切相关,大学招生不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而由各校自主命题,这就决定了教材多样性的可能。关于大学考试命题,所知最特殊的例子是清华大学1932年由陈寅恪先生命题的语文考题,以“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人比黄花瘦”等为上联而要求学生对出下联,还有“梦游清华园”的作文题等,此事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北平《世界日报》连续两周刊载各种意见,天津《大公报》亦跟进讨论[8]。这些“怪题偏题”,重点在于考察学生的基础知识,检测其阅读面和灵感、才华等,看似简单或“奇怪”,却可以考查学生文史基础知识把握程度和思维敏捷度。学生通过课本学习或经老师辅导能学到什么应考的秘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腹有诗书,博物洽闻,到此自可发挥优势,以不变应万变。而从专家和出版社角度看,能编出受学校欢迎的教材,则是名利双收的事,何乐而不为呢?在今天的学术评价体系中,自编教材只要未进入“部颁”或未经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许可,就可能无缘进入各类学校课堂。成为基础教育领域的教材一定是具有官方背景的编纂团体的成果,“自编教材”只能游离于国民教育体系之外或成为可有可无的辅导读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学课本长期以人教社统编教材为主。新时期实施高考制度改革,有限扩大地方高考自主命题,也就允许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根据部颁教学大纲组织编写教材。但从古典诗文及李杜诗选看,部分地方教材的选目基本上是在人教社课文基础上的调整,即减少原有篇目,增加地方历史文化的知识点。从李杜诗文的入选看,数量有减无增。这也是本文不再对地方教材进行统计的原因。
-
由于教材编写的多元化,自然而然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同一首作品会被不同编者安排在不同学段。最有意思的是,一首作品,有的在小学,有的在高中,还有的小学、初中、高中均曾经入选。
同一首杜诗被不同学段选为课文,在民国教材中十分突出,主要原因是教材的多样性,即编者的不同和出版社的不同。民国时期各学段重复的杜诗可谓五花八门,不同的教材因编者的认识不同,或高或低,入选不同学段,这几乎成了一个普遍现象,是典型的“见仁见智”。所以,无必要讨论某诗在不同教材、不同学段的现象,值得关注的是相同出版社或同一作者的态度,因为对同一篇目进行学段调整,反映的是编者的相应思考。以民国教育部审定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9]对杜甫《前出塞》《后出塞》的篇目选择为例,在1913年6月版的小学课文中,有《前出塞》的“磨刀呜咽水”“挽弓当挽强”“单于寇我垒”和《后出塞》的“朝进东门营”;在同年11月的修订本中,《前出塞》三篇中撤下了“单于寇我垒”,《后出塞》一篇不变,新增了“男儿生世间”;1913年12月版回到1913年6月版的原状;1919年5月又调回1913年11月版的前后《出塞》各二首,并增加了《赠卫八处士》;到1922年,小学课文中的这一杜诗选目仍未变化。这一过程反映出编者在前后《出塞》篇目选择上的态度,以及在小学阶段选何诗入课文为宜的认识,态度的反反复复见出其探究精神,也反映了教师和学生的认知态度。
这样的调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材修订中同样存在。以人教社教材为例,某些作品的学段安排出现了反复调整,反映出编者对诗歌的理解和对学生接受度的判断。以下具体分析杜甫诗入选课文的几次变动。
杜诗《绝句(两个黄鹂)》1956年入选初中一册,1961年调整到小学五年级(十册),之后一直在小学四年级《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实验本)语文》第七册。
《江畔寻花(黄四娘家)》一首,1982年入选初中一年级(一册),1987年置于初中附录“古代诗歌”中。在《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实验本)语文》中入选第十册,在《义务九年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语文》(试用修订本)中入选三年级(第五册)。
《石壕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两首诗歌变化较大。《石壕吏》1952年入选高中一年级(二册),1956年入选初中二年级(三册),1958年入选初中二年级(四册),1963年入选初中二年级(三册),1978年入选高中一年级(二册),1982年入选初中二年级(四册),1987年仍保留在初中,1993年再降至初中一年级(二册)。一首诗在40年间呈现出高一到初二再到高一再回初二最后到初一的变化,反映的是编者对作品接受度的判断,明显有时代的影响。如1978年“文革”结束,对于当时的高中生而言,传统文化的学习在此前基本中断,把此前的初中选文编入,符合当时学生的文化程度。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最早在1952年入选高中一年级(二册),1956年入选初中二年级(三册),1961年调整到初中三年级(五册),1978年仍在初三,1982年再入选高中二年级(三册),1990年变为高二下(四册),出现了不断“走高”调向高年级的趋势。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在人教社课文中调整的学段变化最大,且出入更大。此诗最早是在1956年入选初级中学文学课本第六册(第二课),1961年进入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三册(第十课)。1978年仍在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四册(第二十一课),作“七律二首”。1982年回到初中语文课本第六册(第三十课),作“诗词曲六首”。1987年仍在初级中学语文课本,但作为附录“古代诗歌”。再后来进入小学六年级,出现在《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实验本)语文》第十二册和《义务九年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语文(试用修订本)》第十二册。呈现出初中(三)到高中(二)到初中(三)再到小学(六)的变化,最后确定在小学,见出“下放”的趋势。这一过程反映的是不同时期编者对这首诗的接受度的思考,目前最新版已取消。
杜诗同一作品在小学和初中先后出现的有《绝句(两个黄鹂)》《江畔独步(黄四娘家)》。在初中和高中之间变动的有《石壕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夜喜雨》《旅夜书怀》《后出塞(朝进东门营)》。只在初中或高中出现的杜甫诗有:初中《江南逢李龟年》《水槛遣心》《月夜》《登楼》,高中《羌村三首》《兵车行》《登高》《客至》《登岳阳楼》。
相对而言,李白诗在学段上有较为明显的少龄化特点,各学段变化情况较杜诗为少,这既反映在民国时期的教材中,也反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材中。民国期间入选各学段的李白诗90余首,被各学段重复入选的有30余首,有60首是单独被各学段选入。
只入选小学的篇目有《从军行(百战沙场碎铁衣)》《东海有勇妇》。
只入选初中的篇目有《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春夜洛城闻笛》《古风(北溟有巨鱼)》《与韩荆州书》《登高丘而望远海》《赤壁歌送别》《望庐山瀑布(西登香炉峰)》《峨眉山月歌》《远别离》《鸣皋歌送岑征君》《关山月》《题东溪公幽居》《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王昭君》《于阗采花》《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玉阶怨》《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作(刬却君山好)》《江上吟》《早春于江夏送蔡十还家云梦序》《春于姑熟送赵四流炎方序》《出自蓟北门行》。
只入选高中的篇目有《古风(庄周梦胡蝶)(胡关饶风沙)》《送友人》《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独漉篇》《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客自长安来)》《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大道如青天)(有耳莫洗颍川水)》《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暮从碧山下)》《敬亭独坐(众鸟高飞尽)》《忆秦娥》《采莲曲(若耶溪旁采莲女)》《愁阳春赋(东风归来,见碧草而知春)》《送别(寻阳五溪水)》《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胡无人》《司马将军歌》《猛虎行》《醉后赠从外甥高镇》《上三峡(巫山夹青天)》《听蜀僧濬弹琴(蜀僧抱绿绮)》《白云歌送刘十六还山(秦山楚山皆白云)》《渡荆门(渡远荆门外)》《春日醉起言志(处世若大梦)》《寄远(本作一行书)》《菩萨蛮》《登金陵凤凰台》《短歌行(白日何短短)》《悲歌行(悲来乎)》《估客乐(海客乘天风)》《长干行(妾发初覆额)(忆妾深闺里)》《笑行歌》《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客中行》《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其二(南湖秋水夜无烟)》《灞陵行送别》。
被各学段重复入选的有30余首,其中的分布颇有意味:该时期没有一首李白诗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均入选的现象。这本来就是学段中较难区分的一个时间段,比如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其程度的差别有多大,是很难区别的。但小学、初中、高中选入同一作品的倒有二首,即《静夜思(床前明月光)》《早发白帝城》(又名《下江陵》)。甚至还有只在小学和高中教材选入的,如《望天门山》《从军行(从军玉门道)》和《游洞庭湖》(又名《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游洞庭湖》组诗题目有异,入选的情况也很奇特,《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之“洞庭西望楚江分”一首入选高中,而《游洞庭湖》之“南湖秋水夜无烟”则入选小学。这几首诗有如此大的学段跨越,反映的是艺术特点在学者眼中的不同层次。也有对初小语文教学语言文字的把控问题,如《游洞庭湖》对小学生来说似乎稍深,而高中阶段对李白诗也有更多的选择。更有意思的是,此诗在小学和高中阶段的入选均具有试水的意义,因为其他版本小学和中学均未再次选入。
初中和高中阶段被同时选入不同版本课文的李白诗,表现的是李白诗在接受程度上学段的差别不大。下面这些作品就是证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将进酒》《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赠汪伦》《子夜吴歌·春歌》《子夜吴歌·夏歌》《子夜吴歌·秋歌》《子夜吴歌·冬歌》《蜀道难》《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梦游天姥吟留别》《山中问答》《古风(齐有倜傥生)》《古风(黄河走东溟)》《襄阳歌(落日欲没岘山西)》《日出入行》《送从侄耑游庐山序》《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犬吠水声中)》《谢公亭(谢公离别处)》《横江词(人道横江好)》《夜泊牛渚怀古》《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春思(燕草碧如丝)》《上安州裴长史书》。这些作品构成了李白诗歌在基础教育阶段较为重要的篇章。
从入选作品与时代背景的关系考察,亦能感知语文课文的确定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在杜诗入选的内容上表现十分鲜明。民国年间长期处于动荡之中,这样的局势对学者和民众的影响都是明显的,就教材而言,对“非战”的呼唤在课文中有明显的表现。第一次将杜诗选为语文课文的中小学教材是1912年1月出版的《中华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所选的《出塞》即为著名的“非战”诗。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入选中小学课文及读本最多的杜诗为《石壕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兵车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出塞》等,其中《石壕吏》《兵车行》《出塞》是典型的“非战”诗,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表达的是战争胜利结束的狂喜,仍有明显的“非战”意味。“三吏三别”中的《新安吏》《潼关吏》《无家别》《垂老别》《新婚别》等也有较高入选率,加之《羌村》《春望》《同谷七歌》《哀江头》《喜达行在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大量杜甫的“非战”诗入选民国时期中小学语文教材与读本,足见杜诗在民国时期的关注度所在,这显然与民国时期动荡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人教社课文70年来在杜诗选择上的最大变化,就是非战诗的减少和人民性的突显。以“三吏三别”这两组最著名的“非战”诗为例,在社会稳定的1949年以后,除《石壕吏》外,其余五首诗几乎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完全消失。其他一些之前入选频率本来就不高的“非战”诗,诸如《同谷七歌》《哀江头》《喜达行在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自然不再进入中小学课文。在大学中文系教材中,这些作品基本保留,见出其影响的深入和持续。虽然这并不表示当代中国人不再需要杜甫的“非战”诗,也不表示当代中国中小学教育对杜甫“非战”诗的漠视,但通过杜甫“非战”诗在中小学课文中的变化,能够看到不同社会背景下政府、学者和民众通过教育所传达的意愿和诉求。杜甫“非战”诗的入选与社会现实紧密关联,还可以从中小学教材对其他课文的选择中得到印证。除了杜甫的“非战”诗外,民国时期还有许多教材课文与读本选文都能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如《侯将军奋勇剿倭寇》、苏轼《教战守策》、黄遵宪《军中歌》《旋军歌》、孙文《黄花岗烈士事略序》、张骞《致日本外务大臣诘问宇治军舰阑入书》、章炳麟《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刘复《反日底忍与做》,甚至有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自序》。这些课文在无外敌入侵的1949年后的人教社教材中都没有再出现过,可见当时所选杜甫“非战”诗或《木兰诗》《从军行》之类战争题材作品,看重的不仅仅是诗歌的艺术价值,更反映出强烈的社会需求和特定的时代审美风尚。
从文体特征和语文教学的认知发展看,清末民初语文界对语文教学和课文的文化价值和文学传承功能的认知还在探索时期,民国建立之初学人对基础教育的建构也处在探索期,在这个较长的现代转型期,语文课文要从古代走入现代,必然有早期的模糊性。清末民初编写的课文,作者多是前清文人,明显还有桐城古文的影响。也正因如此,姚鼐《登泰山记》方能在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文中和其他经典散文作品相比雄踞榜首[10]。随着白话运动兴起,民国的课文选择有了很大变化,像《义鹘诗》这类较为古拗的作品,就自然退出小学生视野了,即使在大学中文系的教材中,这首诗也基本上不再入选。
-
因为基础教育时间限制和课文篇幅的原因,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内,如何将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作品呈现给学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大课题。我们也深知,即使是全国统编教材,最终还是由一批学者来完成的,所以,担任总编或主编的专家,其个人的专业学识和审美趣尚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下,总会对作品的选择作出个性化的选择。因此,不定期改版的教材,即便主编不变,其选文也总会有相应差异,遑论不同主编。同时,要求世世代代的学生读同一种教材和固定篇目也是不太现实的。这就决定了教材的选文不可能像一些优秀的诗文选本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一样,一旦问世就能够以不变应万变,或许最好的办法是在课文之外尽可能有一定数量的推荐篇目或阅读篇目。这样,一个好学的学生,只要精力足够,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基本能将中华文化中最优秀的文史篇章了然于心,应该说这才是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这个篇目与考试无关,但与国民素养有关。
不同时期的课文,既有不同时期学术的影响,体现当代学者和读者对古代经典的发现,也受该时期编者个人学术视野和兴趣爱好的制约。而某一作品入选课文,意味着进入成为“经典”的过程。但最后是否为社会所接受,需要漫长的时间来证明。如前所述,最早进入课文的李杜诗,有相当多的篇目是“从一而终”的,某次入选,以后再无,无论是编者自己还是其他编者或出版社后来都已放弃。放弃本身也是选择的结果,一首作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断入选教材,成为课文,则一定含有某一时期被认可的因素,是其艺术性和思想性被该时期的社会思潮、审美风尚认可的表现。而一首作品能在不同时期被认可、被解读,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显示其内涵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性和超越时代的强大生命力,继而形成在一个民族文化中的恒定价值,最终成为文化共识,就可能成为代表一个民族和文化的经典。语文课文和重要选本对一首经典的形成是具有这样的作用的。
作为提升国民素养作用最大的语文课文,其选文的确定可谓意义重大,编者能不慎乎!而有心的学者更应该贡献智慧,为提升国民素养而建言献策。本文之所以关注李白、杜甫诗文入选与国民认知的关系,是因为涉及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中小学生对一个伟大的中国诗人,有无可能通过对其最具代表性作品的学习,由此对其文化精神、艺术贡献有相当的了解?答案是明确的:能,应该,必须。而在国民基础教育中,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精华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该如何呈现?如何让国民在基础教育阶段对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有基础性的认识?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语文教科书的内容如何关注与采信文史研究的成果。到目前为止,客观地讲,彼此的关系还未达到理想状态。这不是谁的责任问题,而是学术界对研究成果的推广宣传不够,基础教育界对当下的学术进展关注也不够,二者的互动似乎不够积极。对此,我曾有过思考:“一个学者从事学术工作,一定有多种动力推动,有生存需求的考量,有兴趣爱好的寄托,有文化托命的志向,也有立言不朽的追求,或综合产生激励作用。但有一点也是肯定的,即学术研究的观点和结论,理想状态应是让成果成为常识,我认为这甚至可能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对于经典作品研究与基础教育的关系,我认为“是对课程和入选作品的确定。这是最重要的工作。宜有相关研究,确定能够建构国人国学素养乃至精神谱系的课程和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作品。其学习时间和入选课文,可以确定足以补齐国学短板”[11]。本文的初衷,正是以具体问题来推进这一工作。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经典作家灿若星辰,优秀作品琳琅满目。要对几千年来的优秀作家进行代表性作品的选择,看似不易,其实也不是太难,因为很多作家的代表作显示度很高。国人耳熟能详的,如屈原《离骚》、陶渊明《桃花源记》、郦道元《三峡》、李密《陈情表》、诸葛亮《出师表》、贺知章《回乡偶书》、王之涣《登鹳雀楼》、孟浩然《春晓》、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崔颢《黄鹤楼》、张继《枫桥夜泊》、王安石《泊船瓜洲》、文天祥《过零丁洋》、马致远《天净沙·秋思》、周敦颐《爱莲说》、姚鼐《登泰山记》……,这些作家的这些作品,有相当高的显示度。一个原因是在历代的作品选或课文中是常见篇目。再则,和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大家相比,他们具有显示度的作品相对要少一些。李白、杜甫等大诗人,作品多,思想内涵丰富,艺术成就突出,代表作也很难仅仅列出几首便可以较为完整体现。所以,在百年之间,其作品的入选会出现前面所呈现的“见仁见智”现象。而我以为,这正是李杜二人的魅力所在。虽不能用绝对的数量来确定究竟该选多少进入课文,但尽可能将其能够代表其个性、思想、艺术特征的作品呈现给学生,在完成对二人基本了解的基础上,构成对李杜乃至唐诗的印象,是完全应该的,这也是学术成果影响大众教育的尝试。
从百年课文中李杜诗的入选史看,形成了一个较为集中的范围,百年间的入选率,可以作为参考。结合人教社选文亦可看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如前所述,在七十年间的十余次改版中,人教社新增(首选)了杜甫诗7首、李白诗5首,其余作品与民国选文相同。换言之,人教社的课文中,李白、杜甫诗的多数篇目在百年间都或多或少地进入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课本。再以人教社自身的选文进行对比,或许还能说明一些问题。最新公布的中小学生需要背诵的作品,李白诗有9篇、杜甫诗7篇(另有4首课外阅读),从总量看,在古代作家中作品入选中小学阶段的课文是最多的两位。民国时期李杜作品入选课文虽在百篇左右,但因教材的多样性,民国期间完成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在课文中接触到的李杜作品也分别只在十篇左右。如从当时的部定教材看,总量甚至少于人教社的篇目。现在要讨论的是新版课文中李杜作品篇目的代表性问题,即对李杜的总体把握是否完整的问题。虽然不能完全依靠基础教育的内容来完成对两位伟大作家的认识,但考虑到绝大多数国民的国学素养就是来自中小学课文的,那么通过不太多的作品将中国文学史上“双子星座”的形象表现得尽可能完整,也是学术界和教育界的题中应有之义。
历代课文或诗文选本,会体现出一个特定时期编者或出版者的审美尺度和价值观。在历史长河中,总会有一些相对固定的内容被认可、被传扬,一些内容被边缘化甚至被否定。二者又不是绝对的,一些作品会随着时代思潮和审美意识的变化或沉入底层或浮出水面。但对一个伟大作家来讲,一定是有一些作品会永远被认可的,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审美意识和阅读趣味如何变化,因为人类的基本价值总是有一个不能偏离的主线,那就是具有最大公约数的核心理念。这些内容在一个伟大作家笔下总会有不同的呈现,几百年几千年的积淀,又一定会形成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的共识,从而汇聚成核心价值。对李杜诗在百年间课文中的入选的研究,正是希望解决这个问题。答案也是明显的,这是可以有一个最大公约数的认知范围,基本汇聚了一个作家最适合基础教育阶段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通过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了解这些作品,则是传承优秀文化的最佳途径。
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共识,因而,确定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入选基础教育的课文,是文化传承的重中之重,是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共同责任。在今天,结合目前人教社的选文,在有限的篇幅内,李杜作品的呈现还有无可以讨论的余地呢?答案是明确的。针对新版课文,在现有课文所选李白杜甫作品的基础上,还可关注以下问题:一是篇目的适当增加,使之能够基本反映两位伟大诗人的风貌。这是奠定国民对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了解的最重要的途径。如果课文篇幅有限,也可在选修或阅读篇目中加以体现。二是对李杜作品核心价值的判断及相关作品的选择。如李白的反抗权贵、自由精神、浪漫情怀、瑰丽想象、夸张排比的艺术表达,杜甫的悲天悯人情怀、民胞物与精神、深厚的人道主义、精深博大的艺术成就和杜诗的叙事性特点,都应该有适当的内容。具体而言,结合人教社的70年选文,参考百年间选文情况,还有这些未进入课文的李杜作品是值得关注的——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送友人》《蜀道难》《将进酒》《峨眉山月歌》;杜甫《石壕吏》《羌村三首》《兵车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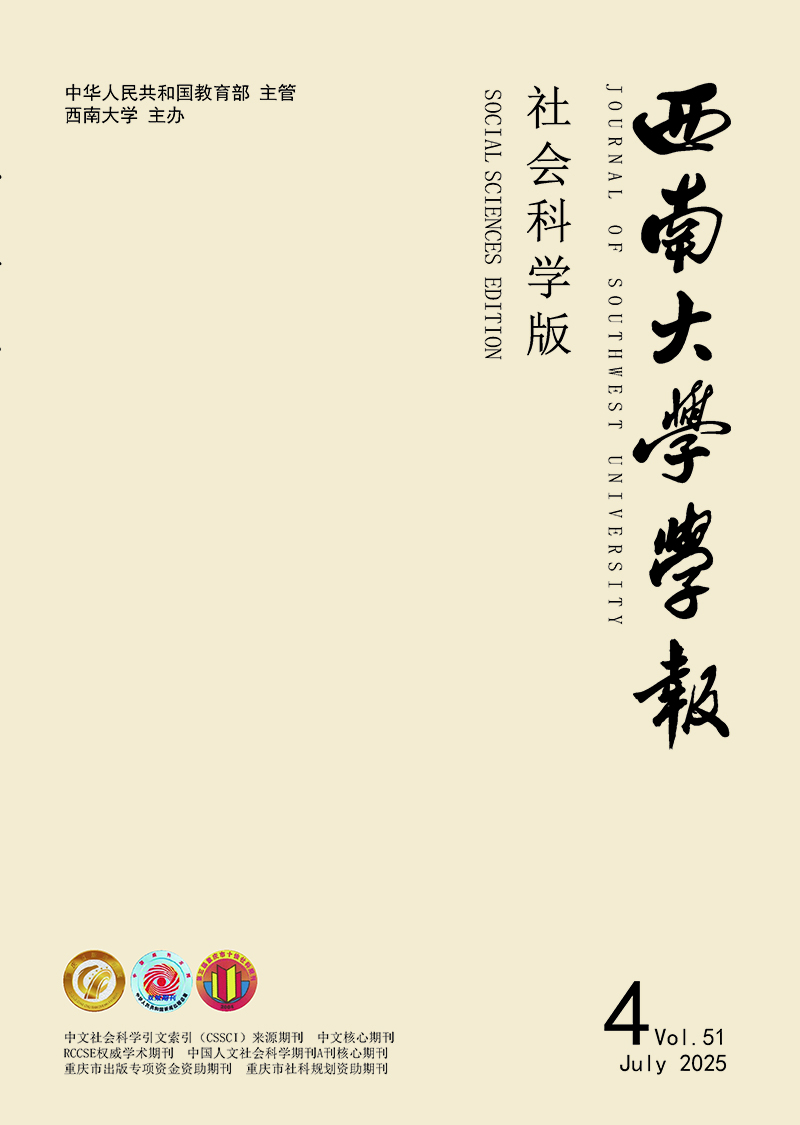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