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商人-商业史研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一环,上世纪中叶以来,学术界在该领域已取得丰硕成果①。学者们在广泛发掘并有效运用史传、谱牒、方志、文集、档案、传状等传世文献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明清时期商人群体的产生背景、物流条件、活动范围和营业项目,以及商人资本蓄积的过程和经营诸形态等问题,使得人们对明清时期商人-商业的基本概况及其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整体地位有了大体科学的认识。然而近二十年来,明清商人-商业史研究却鲜有大作问世,究其原因,史料的制约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贱商传统的影响,官修正史对商人事迹讳莫如深,其他传世文献如史志、谱牒、文集、笔记虽然保有可观的商人、商业信息,但也存在陈旧、重复、讹误等缺陷。史料问题成为制约中国古代商业史、社会经济史研究深入发展的重大瓶颈,而近几十年来大量出土的商贾墓志则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新出路。墓志是碑刻的一种,它深埋于圹中,记载墓主的世系、名讳、婚姻、行迹、寿年等信息,“以为异时陵谷变迁之防”[1],为行商坐贾埋置的墓志可称为商贾墓志。墓志原先埋于地下,非经考古发掘,则不会现世流传,因而它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围绕墓志又形成一种规范的文体,称为墓志铭,所谓志铭,“称扬其先祖之美,而名著之后世者也”[2]。墓志铭记载孝子贤孙最为珍视、最想传示给后人的墓主事迹,因而是时代价值和民间观念的集中体现。笔者拟以墓志资料为中心,从价值观念与商业经营互动的角度,探讨明清时期商人阶层的社会构成与资本来源、经营方式及其特征等问题,不足之处,望请斧正。
① 较为突出的成就有傅衣凌:《明代徽商考——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稿之一》,《研究汇报》1947年第2期;藤井宏1953年发表论文《新安商人的研究》,傅衣凌、黄焕宗将其译成中文后分为七章,分三次发表于《安徽历史学报》1958年第2期,《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1期及第2期;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明富:《明清商人文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HTML
-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鄙视商贾的传统观念明显转变,人们对商业本身的社会价值也有全新的考量。如东林党人赵南星提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3]卷10,255的说法,清初大儒黄宗羲亦有“工商皆本”的论述[4]财计三,41。在明清思想界,商业“本业”地位逐步确立,而民间的日常伦理观念也出现某些有利于商业的“创造性转化”[5],这一切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持筹握算,商人的社会来源由此日趋复杂和多元。就商贾墓志提供的信息看,明清商人主要有以下几种成分:
-
孔子有云:“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6]学而,42在儒家看来,延续家风、不改父业乃是人子尽孝的本分。明清时期不乏世代经商的商贾世家,而商人子弟投身贸易的最有力理由就是要尽孝。如咸阳人王之鼎,其父王弘世“贸迁迂滞,留圁阴者三载,未遑脂车”,他慨然决定为父分劳:“一室琴书自误,千里尚有赋雨雪之征人,天下安有不服劳之子哉?”于是“置蠹鱼事,躬亲负贩”[7]720。宣化人郭祯,原本垂志儒业,他的父亲郭佑当时在淮阳经商,“会边务倥偬,需刍粟孔棘”,其父恰在征役之列,淮阳商贾纷纷逃遁,郭祯则毅然“以身代父”“肆力于贾”[8]197。又如咸阳人寇复准,“以大父讳信吾公常经商渝城”,寇氏“欲缵父志,年未弱冠,遂弃儒就商,凡有持筹,无不亿中”[7]638。其实孝养尊亲还有很多其他方法,但明清时轻商、贱商的社会心理已发生重大转变,继承先辈“遗橐”不仅完全正当,而且还被赋予了深刻的道德涵义,“孝”的观念成为延续商业传承的重要动力。
不仅商人子弟以继承商业为尚,明清许多商贾世家也把贸易经商当作为家族传统中的核心价值,晋商王文显就认为:“各守其业,天之鉴也。”[9]卷46,420不少商人子弟自幼就受到家族长辈的栽培历练,有计划地积累社会经验和经商技能,从而为他们继承家族事业铺平道路。如陕西韩城人王登云,“年甫十余,随父直赴灵州,贸易于秦填堡”。后以“父亲年迈”,于是他“请父回家”,自己独自留下经营[10]330。山西解州人杜钟,“少从伯父盂辉公游淮扬,事商业”,“数年致千金归第”[11]。如兰州人戴廷仁,“弱冠,从先大人治鹾务,往来张掖、酒泉间,操盈缩、算缗钱锱铢不爽”[12]。如山西人张永灏,“幼随二三两伯父贸易彰德,操奇赢握胜□,南越楚邓,北抵燕京,所至之处靡不令人敬服”[13]。
有的商人子弟继承家业却并不顺利,他们是在父辈早逝、家运飘摇时仓促接手的。如山东济南人高龙,其父病逝时,他才十四岁,“人咸以孤弱虑之,即能查考账历,典检货财,应缓应急,人情事务悉得其当。”高龙少年老成,颇有威信,据说连高家的“门下老贾”都相互告诫说:“幸勿以少年易视之!”[14]127山西寿阳人刘瑞五,“十四岁丧父,弱冠袭先人遗业,服贾辽东,数十年间,称素封焉”[15]。还有如山西阳城人王重新,“七岁而孤,年十四即挈父遗橐,行贾长芦、天津间,俯拾仰取,不数载遂至不訾”[16]。尽管缺乏心理与经验上的准备,商人子弟仍然会自觉承担延续家族经商传统、张大祖业的使命,商贾墓志对此类事迹也往往会不吝赞美之词,充分体现了明清时期商业观念的转变。
-
早在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就发现了财富积累的一般规律:“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17]尽管古人普遍尊奉“农本商末”的教条,但农业的收益率无法与工商业相提并论,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晚明时人们进一步认为:“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18]卷20,江南八在明清人眼中,务农与经商不仅有“贫”与“富”的差别,还且还是愚人与智者的分野。农、商价值的互换,使得许多家境贫寒但志存高远的农家子弟弃本服贾。如咸阳人李珊,“工书,顾弃而业农,已,又去为商,商蜀中”[7]548。北京人朱景,“家世力农”,他“稍长与其同母兄吴黾勉治生”,“挟货贿商游四方者愈三十年”[19]。如陕西韩城人梁养凤,“幼而贫寒,豁达勤敏,不事农业,即就贾,善权利,尝游宁夏汉沔间,为大贾”[20]。
不过也有农家子弟并非是因为家境贫寒而选择经商,他们只是把商业作为自己出人头地、实现人生志向的平台。西安人白锡,“力农圃,尤精种树,积资镒”,他以“丈夫当志四方”自励,“商环庆,历江右、湖、饶而淮扬,居多三十载,而成大贾”[10]152。陕西耀州人古昌,“既壮,有负郭田,尝尽力农事”,“奈三试棘闱弗售,顾亲老,两弟幼”,于是他“习计然术,备物养志”[10]291。
-
明清科举之路,狭窄而又艰辛,业儒高中者寥寥无几,经商致富者却如过江之鲫,当时有“士而成功者十之一,贾而成功者十之九”[21]的说法。士人的清苦无望与商人的志得意满形成鲜明对比,加之有“良贾何负闳儒”[22]卷55,1146、“四民异业而同道”[23]等新观念流行,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儒生便毅然弃经籍而操筹算。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科场不顺,对仕进丧失信心,不得已弃儒就商。如南京人贝珙,“治举子业,已而落落弗遇,去游江湖,为居积贸迁之事,不数年,累赀巨万,犹叹曰:‘弃儒而就商,非本志也。’”[24]86河南汲县人王宝卿,“年二十八始以第一人补县学附生,乡试报罢,慨然曰:‘富贵,命也,吾将兼为商,以养吾亲矣。’”[25]江苏人吴於惠,“两试于学,使者未售,归而力田,以耕以读,继复从事盐鹾,家日隆起”[26]159。山西曲沃县人杨儒国,“屡试不售,命实绌甚,迨太公年迈,家政无人料理,遂就计然术,往来风尘中者三十余年”[27]248。苏州人王师晋,“少困场屋,辍举业习计然术,赞其父资政公及兄朝佐”[28]106。
二是家境贫困,无力仕进,不得已改业经商。如南京人吴宗周,“入学,周揽编籍,通知大义,亡何家益贫”,“乃弃载籍,徙治贾”[29]399。山西沁水县人李维翰“年弱冠,补博士弟子员,有声庠序”,“后以食指繁,弃儒就贾”[30]383。陕西华阴人朱建基,“妙年入庠,翘楚黉序,识者以大器目之,后以家计所迫,贸易江淮间”[31]370。陕西富平人孟尽先,“因两兄早卒,家计无依,奋然弃儒而远服贾于陕右之陇数十年”[32]。
三是因为父母老迈,家中需要顶梁柱。陕西榆林人孙殷,其父孙子春官拜按察佥事,孙殷自幼便随父宦游,力学继志。孙子春年老致仕,召集家人说:“今率居一业为秀才事,则吾终养,其谁赖乎?”孙殷“以父命为尊,遂投笔,贾于四方,果获大利”[33]271。云南大理人杨瑊,“与伯仲公同事铅椠,抱青紫志”,而后因兄弟业儒有成,不得已从父命肩挑家业,“出服贾仅十六龄耳,即恪供子职,牵车牛权子母者十一载”[34]。如陕西高陵人张尧召,“初业儒,同兄从塬北王静节先生学”。后来他的父亲对他说:“尔兄已补廪,且家贫,菽水不充,我年渐老,门户差徭繁重。古云:‘学先治生。尔业为生计,亦便供给尔兄弟。’”父命不可违,他于是“纯艺黍稷,肇牵车牛,登临巩,涉淮泗,以图洗腆”[35]186。父母长辈对子孙业儒仕进自然是很支持的,但既然家中已有人业儒有成,自己又年老力衰,因而会主动劝导子孙经商用以家人用度,这和徽商代言人汪道昆所提出的“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22]卷52,1099的儒贾并用观是一致的。
四是因为身体原因。明清科举以“身言书判”量材授官,凡是身体残疾或者容貌有缺陷者,纵才华再高也难以入仕,明清商人中就有不少人因健康状况不佳而被迫弃儒。如北京人曾铨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长兄曾镒,“累功拜明威将军、虎贲卫指挥佥事”,次兄曾鉴,“登进士第,累官资政大夫、工部尚书、赠太子太保”。他本来也立志儒业,“然体素羸,父封君怜之,命弃去,乃敖业贾”[36]187。河北衡水人曹泽,“少从师游,绝有进益,后以羸疾废学,从事于商贾之业”[37]。山西曲沃人杨端章,“以疾遂弃儒就商,客于河北延邑”[27]215。又有河北满城人孙希哲,“习举子业,颇望于众,陇西(孙父)爱之,卒以疾不果,去事生产”[38]156。
古语说:“上医医国,其次疾人。”[39]在古人眼中,“医儒同道”,业儒与行医有着近似的伦理价值。许多商人虽因种种原因弃儒,但对功名仍抱有深深眷恋,因而会在持筹握算之余,通过学医、行医来弥补业儒不售的遗憾。如南京人张缙,“少尝读儒书,为京庠生,会病免去而业医”,“家故赀厚,既居善药以售人,而尤自制剂以治疗人”[22]明故竹庵处士张君墓志铭,136陕西安康人胡新烜,“以贫故,弃儒业贸”,又“善眼科”“好施药剂”,“无不投之辄效”[40]。咸阳人寇复准,弃儒就商,又“好岐黄术,于医书手不停披,焚膏继晷,至夜半方就寝,常设药以活人”[6]638。江苏海州人张兼三,屡困场屋,“思范文正公良相良医之旨,一意于医,攻岐黄家言,活人无算,折而之他,遁入货殖,与陶朱之业历有年所”[26]214。又有如南京人李仟,“游贾人亦之淮扬间”,又“雅善炼术,能活人,与缙绅先生交游,声价籍重”[29]397。可以看出,商人学医、行医,有借此交结缙绅、扩充人脉的意图在内,所以明清时期“贾”“医”“儒”三者融合互用是商业文化中一个突出的现象。
-
这部分商人多是因为仕途不顺或是厌恶官场的险恶倾轧而挂冠经商的。如北京人吴学仁,“年十三入为县学生”,后因“司训有易卷之弊,置之劣等”导致乡试落榜。吴氏深受刺激,遂“入粟授九原丞,后一月不任罄折,即解官归之”,罢职后,他对官场彻底失望,“挟资往来江淮间,锐意以廉自守,不为诸贾欺”[41]。山西永济人韩楫,以“第二甲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的身份跻身官场,原本前途无量,因恩师高拱遭张居正、冯保构陷罢黜,他愤然拒绝张居正的多次笼络,请辞还乡。韩楫自思“家本寒约,设不中进士,不做官,将束手毙”,于是“置田百亩,可以糊口,市肆一局,可给诸费”[42]94。
一. 承袭祖、父业者
二. 弃农经商者
三. 弃儒服贾者
四. 弃官经商者
-
韩非子有云:“长袖善舞,多钱善贾。”[43]置办货物的前提条件就是拥有一定数量的资本,资本规模越大,商业经营所获得的利润就可能越丰厚,商人阶层对此一定心知肚明。然而古人历来奉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对于财富来源的正当性和安全性极为敏感,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外财不发命穷人,不义之财不可取”即是此意。因此商人的资本筹集方式直接反映他们的财富观念,商贾墓志记录和认可的资本来源尤其具有价值评判的意义。为便于考察,笔者将其分为自有资本、共同资本、借贷资本和委托资本四大类型。
-
简单地说,自有资本即归经营者个人所有和自由支配的资本。具体而言,自有资本又有以下几种来源:
一是来源于长辈馈赠或遗产。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明清商人中不乏出身豪门富户者,他们经商的启动资金往往来源于父、祖的资助或继承遗产。如山西怀仁人潘铭,“承祖业而扩充之,创立基业,治家殷勤,中年为名商,自持慷慨”[44]。洛阳商人韩敬,父母双亡后与胞兄相依为命,“后兄欲异居”,“中分其财田庐臧获”,韩敬“引荒顿老弱者取之”[45]。又如山西垣曲人杨尚瑜,“有从堂兄尚玺,幼与刘亲公请来归,视如同胞,产业均分,诚人所难及者,即其弃儒就商”[42]232。
子孙继承遗产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商贾墓志之所以要记录此事,除为表现墓主在分家产时“不争”的德行外,更是为渲染墓主继承产业后经商发家的才能。特别显著的例子,如河南虞城人范椿,“乃父暮年,尽以赀财巨万、田六万亩均分六子”,范椿不愿坐吃山空,“乃殖货财,乃通贸易,数年耕稼,数年生放,指掌转盼之间,一日而田连阡陌,遍地流泉”[46]。又如山西临汾人姜彬,“先是有旧业在京师,鼎革后几至废弛”,姜彬“未弱冠,学业垂成,不得已弃儒就商,至京三十余年未尝旋里,殚精竭虑,补旧增新,创置字号,广延伙友”[47]。
二是来源于婚姻关系。通过婚姻关系获得的商业资本,称之为婚姻资本,藤井宏将婚姻资本分为“妻的嫁妆转化”和“妻家直接提供”两种[48]。婚姻资本的受益方无一例外都是男性,第一种如陕西人马文质,“始以配张簪珥微金贸易起家,至富有”[7]537。还有如南京人贝鹏,“治举子业,以数奇弗遇”,他有意改业经商,妻子毛氏深明大义,当即表示支持:“吾意也,请以资装助君。”贝鹏于是“逐时贸迁,遂致巨富”[24]191。第二种往往是指男方入赘女家,通过继承女方的家产获得经营资本。如天津人刘得全,“以兵故,西抵武清,时年渐壮,闻柳林屯孟公有女,乃求媒妁,入门作赘”,“遂受廛为氓于此”[49]168。又如《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父亲吴锐,“弱冠婚于徐氏,徐氏世卖彩缕文縠”,于是他“袭徐氏业,坐肆中”[50]。
三是劳动收入所得。有些商人的经营资本是靠自己挥洒汗水、辛苦积攒而成的,细分起来,又有三种途径:第一,务农致富,再转化为商业资本。如山西沁水人刘得保,“生而食贫,用恳田力穑自给,稍充,去而贾行盐铁江淮间”[51]296。又如北京人常文璐,“佐叔父务耕种畜牧,数岁用渐裕”,后来又“益置田产,采石炭”,“如是者几二十年,数至千金,称素封焉”[52]103。第二,佣工于富户,积攒工资。如山西忻州人称“胡油王”的宫文瑞,“半世为人家佣,每年工薪仅堪自给,恶衣恶食,刻苦成家”[53]。郑州人荆秉方,“见父母艰窘,遂废学,佐人贸易,博赀养亲”,先是“在史某银铺内充伙,后史歇业”,荆秉方“乃自立铺面,家渐充盈”[54]414。第三,小商贩积蓄。济南人刘龙,“自髫岁,服小贾,又十岁,成中贾,又二十岁,成大贾”[14]201。陕西高陵人刘锡,“少时贫窭,以制□面罗为生”,等到“内外勤俭有蓄”之后,“遂商于三边、两淮间,裕矣”[35]149。陕西户县人张维钦,“常作小贾,为高堂甘旨”,“铢积层累,稍有赢余”,“迨后精白圭、计然术,而药室生涯”[55]537。
-
共同资本即合伙人共同出资、共同参与经营的资本。在商贾墓志中,共同资本是靠经营者的“信”“义”观念才得以产生并维系的。如洛阳人韩敬,“与里人张仲节、刘用和同财货殖五十余年,其三家冠婚丧祭并恤患难,济贫苦,一钱一帛之施,悉取□于公”[44]。如南京人姜华,“贸易江湖,与鲍宗悦为通财交,凡四十有余年,相视若同胞然”[56]。又如陕西大荔县人唐可才,“三原魏姓者,多君(唐可才)义侠,尝出百金为管鲍计,廿余年矣”[57]270。
-
如陕西人王才,“贫不能堪,日营微利,以资奉养”,后来“贷富人资,贩木陇右诸山中”,“不数年,家日富”[58]。河北宁晋人高凌烟,“去之学贾,贷子母钱,逐什一之利,嗣是家稍进。”且有“衡水赵姓者,拥巨赀,重公(高凌烟)谊,不惜千金贷之”[38]297。北京人黄善胤,“家际连丧,岁遭大侵,若考伯兄而外,庭除四顾,寂无余人,茕茕然日依为命”,后来伯兄又入邑庠,为支持兄长举业,黄善胤“贷数十金画什一,蓄旨备乏,恒中其指”[52]15。在古代,借贷是一项极受人诟病忌讳的事情,所谓“一年借,十年还,几辈子,还不完”的民谚就是告诫世人不可误入借贷陷阱。商贾墓志不仅记录墓主资本来自借贷,而且全是经商致富的正面事例,其中所蕴含的伦理观念以及社会变迁的信息是十分引人深思的。
-
委托资本与集资共伙非常类似,二者最大的差异,就是委托出资方一般不参与资本的运营,但会坐享红利与分成。就墓志资料提供的信息,明清商人所获得的委托投资有以下三种来源:
第一,来自宗族亲属的委托投资。山西沁水人刘用信,“母常染疾不起,与兄拮据用事,举无废礼,族伯大司空尝奇之曰:‘今之计研也,不腆菟裘,在彼盍往?’”在“族伯大司空”的呼吁下,刘家的其他长辈纷纷响应,“捡括以付,一切米盐泉布之属,悉归权衡。”刘用信“为之经营调度,相土宜,趋物候,百不失一”[30]108。山西沁水人贾体升,“从叔父广文公合阳先生徙居坪上,广文公嘉其心计,深器之,授以赀财,代为经理,与兄贸易淮梁间”[51]324。山西阳城人王重新,“事母以孝闻,又推其孝母者,厚其舅氏以及其内兄弟,为代理其赀本,因以渐裕”[16]。
第二,来自富商地主的委托投资。苏州人薛琛,“弱冠因代人理生,不卒业”,“巨商富室深相结纳,遂取居停之利,家既裕而名亦起”[28]94。陕西高陵人刘扶,经商扬州,当地豪门巨室多与之往还,“至出数千金相托,曾不窥窬于尺寸之间”[35]173。陕西大荔人唐可才,“邑士李察其能,约为兄弟,出赀数百金,恣其货殖”[57]270。
第三,来自官僚贵族的委托投资。明清时期,商人热衷交结官僚权贵已是公开的秘密。李贽曾经说过:“(商贾)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59]为换取政治势力的庇护,商人们乐意接受官僚、贵族的委托,代理他们的资本。如陕西人周堂,整个家族依附秦藩惠简王府。周堂曾担任王世子的伴读,惠简王“一切委任,出纳惟谨,奏闻京师,货殖江湖,悉其托也”[60]。河北宣化人史胜,有“都督霍亚绅者,知君(史胜)克□,或以其弟子及婿出资而托之,誓有所获”[38]130。又如河北人段鉴,“隐于贾,游清源、济、徐间”,由于他“占会百物,亿而屡中,人皆尊信”,因此有“李公者,锦衣挥使也,贸易江湖,金帛动以万计,悉托公(段鉴)总摄”[61]第1册,38。官僚委托与一般的商业投资有着根本的不同,官僚贵族不仅授予商人资本,更会赋予他们经营上的种种特权,因而带有浓厚的“权力寻租”色彩。商贾墓志不但不以官僚委托为忌,反而视为墓主的“德善”加以宣扬,明清商业文化发达与开放由此可见一斑。
一. 自有资本
二. 共同资本
三. 借贷资本
四. 委托资本
-
当明清商人通过各种方式筹集到足够的资本后,便会依照各自的经营理念开展商业活动。上世纪初,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儒教和道教》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中国传统的主流价值体系——儒家伦理无法产生类似于西方清教式的禁欲主义和天职观念,因而阻碍了资本主义的产生[62]。此论一出,立即引发经久不衰的论战①。笔者在考察明清时期商贾墓志资料时,发现其资本运营方式确实普遍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韦伯的假说。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① 中国学者对“韦伯命题”多采取质疑和驳难的态度,反驳最有力的见余英时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余英时借用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某些观点和方法来解读中国儒、释、道三教与商人伦理的关系,核心观点是明清商人并不缺乏“入世苦行”的精神,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根源在于中国近世制度没有经历过“理性化的过程”。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张震、林志:《对马克斯·韦伯命题的质疑——兼论儒家伦理是否阻碍了家族企业的发展》,《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宋寒冰:《反思韦伯儒教伦理观》,《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钟海燕:《文化误读的幻象——对韦伯中国观批判的反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陶绍兴:《资本主义精神的阙如?——徽商转型失败及其对韦伯问题的证伪》,《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许凤英、张培观:《对韦伯儒释道三教观的反思》,《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等等。
-
对安定与安全的需求是全人类的共性,而中国古人对安全的重视更是上升到了政治伦理的高度。孔子有云:“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6]季氏商业经营原本就是一项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事业,如何追逐利润、规避风险,明清商人采取的措施是相当传统和保守的,他们把“患不安”作为压倒一切的经营理念。
1.行商转为坐贾
以商业经营活动的方式为标准,商人可以分为行商和坐贾两种,“负而贩卖,属于行动者曰商,设肆坐以行售者曰贾”[63]。行商坐贾共同构成了商品流通体系,二者并无优劣之分。但行商必然辗转流徙、居无定所,无法满足“求安”的心理需求,因而明清商人中普遍存在轻行商、重坐贾的风气。如陕西人蒙学谦,“曾贸易南方”,若干年后,“觉获金可以业家,遂装载而归,嗣开张于敷水镇,以为子孙永远谋”[31]381。山西曲沃人杨胜任,“弃案牍谋生理,□□□于陕西,继往来于山东,山川跋涉,备尝艰辛,而又以边境路遥不可以久□,□□□南省,得滑县黄大镇而创设当店焉”[27]158。河南沁阳人梁王卿,先是“业于崇义岑村诸集镇,往来贩布”,后“稍裕,乃于本镇开钱店,坐权子母,少舒劳瘁矣”[54]188。坐店销售经营场所固定,生活安逸但利润也小;长途贩运利用地区差价贱取贵卖,虽然获利丰厚,但也有跋山涉水、风险不测的弊端。明清商人两相权衡,提出的解决之道是,“行贩致富,坐店守成”,长途贩运只是为将来开店营业筹集资本的方式而已。
行商转为坐贾,不仅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而且还有传统伦理作为心理支撑。孔子曰:“父母在,不远游。”[6]里仁长途贩运必须远离桑梓,在伦理上是有违孝道的。明清有不少人就是因为不忍远离父母而拒绝经商,如陕西高陵人薛承荣,曾有巨商以厚利邀请他涉海贩货,薛氏当即拒绝:“利可欲也,走险而闻,二人能无戚乎?吾不可以饵利,而烦二人忧。”[10]238行商要想在治生与尽孝上两全齐美,最好的办法就是转为坐贾。在这方面,如陕西户县人阎永连,“服贾汉南,又以母年高,戚远别,乃设肆于郿之槐芽镇”[55]553。山西寿阳人赵宗明,“初缘家贫,业商于神池之八角堡,继因亲老,遂贸易于邑之宗艾焉”[64]。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行商转为坐贾,通常都意味着商品流通规模的缩小和人脉资源的流失,他们的经营心态也会由开拓转为守成。在商品经济还不甚发达的前工业化时代,缺乏开拓精神的中国商人显然是无法与西方争夺世界市场的。
2.“以末致财,用本守之”
在“农本商末”“安土重迁”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明清商人在发家致富后,普遍热衷于将商业利润用于赎买良田房产,形成所谓“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的局面。如河北人李敖,“出奔完城,商贾生活,其利若鬼运神输,勃然成家”,他在经商成功后,“买宅于城中,甲完邑;置田于河口,驾祖产”[38]198。陕西渭南人徐兆璜,经商在外,认为“富贵不归故里,如锦衣行”,归乡后“置良田数顷,建新屋几院”,成“子孙利赖之业”[65]。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买田置地,而是在于商人在购置田宅后如何处理农业与商业的关系。有一种做法是农商兼营,两不相废。如陕西咸阳人陈翰,“家虽商,犹雅爱耕锄,乃恳山田弥望,令无业者力其中而入租,间徒步一观之”[7]555。江西泰和人孔淙,“既长,□商旅于江湖,督农□于田亩”[66]。又如陕西高陵人赵琦,“才裕持筹,善操奇赢,并督家人,勤于耕作”[33]196。可见商人在购买土地后,并没有采取商业化的大农场经营,而是继续延用出佃收租的落后方式,从经济效益角度来讲是对商业资本的虚耗。另一种做法更为保守,商人逐渐把生活重心转移到农业上,有的甚至直接弃商归农。如山西芮城人李丙育,“迁城内钟楼巷,多得文人,且易于图商”,“居数年,因不便农,复迁居东关”[42]244。西安人王英,“蚤年抵淮扬事煮海,与子姓同力于彼,累赀至巨万,正德乙卯春西归,乐业田园,究意农圃种植之法”[10]154。山西高平人李浚功,“挟资贾苏越间,精敏有心计,若荚货情会,币息赢缩,即巧力不如也,寻厌锥刀之末,力本督耕,田无荒圳”[67]。从商人的逐利天性来讲,“商业利润最直接的投入应该是商业经营”[68]。小农经济分散而又脆弱,经济效益无法与经商相提并论。商业资本流向土地乃至商人最后弃商归农,本质上都是先进的商品经济向落后的自然经济倒退。
3.“以商致富,以宦贵之”
明清商人尽管富甲天下,却没有形成自己的阶层意识,他们对于自己的商人身份有着天生的不安全感。为了长保富贵,明清商人在商业经营之外,还热衷于政治投资。一种做法是直接攀附封建势力,投其所好,以构筑官商关系网。如南京商人贝珙,与吏部尚书倪岳“有同窗之雅”,贝珙见倪岳“居第在崇礼街,隘弗能新”,于是“损橐金千为之改创,而未尝有德色”[24]186。商人为朝廷命官赠资建房,如此明目张胆地行贿受贿,商贾墓志中仅见一例。而明清两朝捐纳制度的推行,又为商贾的政治经营开辟了一条捷径。在这方面,如陕西大荔商人成大受,“捐数千金以助军饷,蒙恩议叙郎中”[57]326。广州牙商叶廷勋,“值国家有急,历输台湾、廓尔喀军粮,永定河、南河石工,计累巨万,天子褒之,加至盐运使司衔”[69]。上海商人李缙,“尝效卜式,输财实边,义授散官承信郎”[47]66。商贾墓志中关于商人斥巨资购买官职的记载不胜枚举,商人醉心买官不仅是为保护经营活动,也可能是为履行传统的伦理义务。如南京商人梁瑄,“输粟若干石于官,以助国课”,得获有司“冠带荣身之典”,此后他“遇朔望,具冠带以谒祖宗,见大宾客亦然”[24]174。又如陕西华阴县商人张仲笙,自思“虽能致富而裕吾后,不克致贵而光吾前,吾不为也”,为此他捐官多次但均告失败,最后终于“遵中牟大工例,由豫报捐藩经历,指分山西即补”,得偿所愿后叹道:“吾今日暂可对我先祖于泉下矣!”[31]427事实上商人所购得的官职大多都是毫无实权的虚衔,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借此满足光宗耀祖的心理需要。当然明清商人投资政治最大也最普遍的支出还是培育同族子弟攻考科举。明代学者王士性曾指出:“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70]深谙此道的商人常常以“读书万倍利”[61]第2册,942来训示子侄,为了帮助子弟走上科举为官之路,不惜投入巨资。如浙江慈溪商人宓彰孝,“创立义塾,名曰畲经堂,仿宋范文正公义田法,购良田千亩,延名师,课读宗族中之孤寒无力者”[71]。山西平遥商人刘庆和,“设家塾、义塾,延名师以教,宗族乡党子弟、村社尽熏为善良”[72]。为让后辈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有的商人不惜弃商归隐。安邑人刘泽“挟弟演濬中盐淮上”,他有子年十二即习举子业,且有大成气象。刘泽于是生出弃商之念:“幸有子贤,奈何用区区蝇利,萍浮蓬飞然哉?”在确认儿子确有天赋后,刘泽大喜道:“吾族书香有属矣,急归,以成吾子!”[42]71刘泽归乡时还把他人拖欠的债务一笔勾销,以示弃商决心。官本位思想在明清商人中普遍存在,他们把保财发家的希望寄托在寻求封建特权上,以致在商业活动中忽视了人才培养和资本优化,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
-
家族性、宗族性是中国传统商业组织的共同特征,这是由中国农、商结合的自然经济形态所决定的。范金民曾指出:“传统中国商界具有浓厚的家族意识和地缘意识,通常以血缘以及姻亲关系,甚而地缘关系建立商业网络。”[73]明清商人初入市廛,他能信赖和依靠的助力往往就来自于他的家庭和宗族。商贾墓志对这方面的事例无不津津乐道,如山西永济县人张东顺“业商中州”,妻赵氏在家“经纪内外,能勤不懈,且上笔札,钱货出入,手自历记”[42]180。山西沁水人柳茂中,其父柳圣和“秉睢阳鹾政,兼办典务”,因“佐理乏人”,将其召至跟前听用,柳茂中“遂弃笔砚,游河洛间,游刃有余”[51]348。厦门人杜尚安,“偕诸功兄怀弟泛棹东宁,经营于后垄、竹堑间”[74]。又如陕西人王元泰,“以堂叔经亭公贸易兴镇,遂藉以权子母于典商”,王元泰“以年少主事,小事专之,大事仍禀命于经亭公而后行”[10]皇清例授修职郎明经进士福田王公墓志铭,337。这四则墓志材料代表着明清商业组织的核心构成,“夫妇-父子-兄弟-同宗”。无论是夫唱妇随,亦或是父子兄弟协作经营,家族商业的经营资格以及管理权限都不是来自出资多寡或者管理上的经验、技能,而是取决于在家族体系中的尊卑辈分和血缘亲疏,这种商业模式注定带有浓厚的保守性和排他性。
《礼记·中庸》指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家族式商业把经济共同体建立在血缘共同体之上,用儒家“孝悌”“忠恕”之道解决商业成员之间的信任、和睦问题,然而却往往必须牺牲掉效率和收益。这方面的例子,如河北宣化人李玉,“尝以白金若干,命侄文清辈行货,而所获稍不如意,侄辈不自安”,李玉不但没有小惩大戒,还好言劝慰:“宜安命,富贵不可卒致也。”[8]139陕西高陵人程希仁,举家经商,其弟“每数奇,权利无余息,甚至母金且尽”,程希仁“亦不为介意,而情好愈至”[35]177。北京人郑承宗,“时季弟承宪因贾失意”,郑承宗“助以缗镪,更授心计,什一而息之,稍稍充伏腊矣”[36]286。“择人而任时”是商业成功的重要条件,然而建立在血缘纽带之上的商业组织难以完全按经济规律实行优胜劣汰,相反在伦理上还必须包容家族成员中的无能者和失利者。
另外,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是商业企业赖以发展壮大的基石,而儒家伦理却以“同居共财”为尚,家族成员没有经济自主权,维护家族财产共同体的人将会受到赞扬。商贾墓志多有这方面的例子,如陕西人纪溁,“壮强时,商游淮、扬间,克力干蛊,家日饶裕焉”,“尝慨然以万金让其昆弟”[33]269。福州人林宗炜,“凡跋涉江淮间二十年许,挟重资,分给伯子与季弟,而□无私积”[75]。山西晋城人苗志达,“凡有货财不私于己,若弟若侄尽知其数,有所取用,不分尔我,人咸服其义,则曰:‘财自我得,费自家用,吾弟即吾,吾侄即子,何必计较?’”[76]商贾墓志中大量充斥着对商人“无私藏”“无私积”“不私”等行为的记录和赞美,墓志的价值倾向显然体现的是民间的主流价值。但这种家庭伦理观念显然是与经济规律相违背的,而且它也不能消泯“共财”体制下的重重矛盾,商贾墓志对此也不是完全回避。在这方面,如河南汤阴县人吴从众,“营运稍丰,置田数百亩,与伯共之,毫无吝色,比析居,伯疑其私藏,谕令发誓”。为自证清白,吴从众“竟慨然自誓”[54]37。
另外,在宗族观念的支配下,明清商人对于建祠堂、修族谱、置祀田、辟义庄等一些宗族事务抱有极大的热情。福建泉州商人黄志商,“鸠资兴建田洋黄氏家庙,有声望前哲,发祥遐域,振采宇内”[77]。苏州商人唐文槚,“割上腴田五百亩至义庄,其规制仿范文正公家法,又自祖父以上,皆于域兆之左右,置祭田以供墓祭”[78]。苏州商人王师晋,“置义宅于盛泽新桥,置义庄、建宗祠于苏城花桥巷,以蒇先志”[28]107。又如浙江苍南商人刘运堪,“于宗族尤大有功,咸丰戊午,以宗祠为飓风所坏,鸠工庀材,佥议重建,壬戌再建前进及两庑,丙寅,复谋砌石涂塈、茨施丹雘”[79]。宗族设施一方面耗费大量的商业资本,另一方面成为家族聚会、维系宗族认同的场所,这就进一步强化了明清商业的宗族性和封建性。
综上所述,商贾墓志不仅有志墓的实用功能,它还记录了大量经济活动与价值观念互动的信息。就商贾墓志来看,明清时期人们关于商业和财富的观念与传统伦理实现了良性的融合,因此商人群体的人员结构以及资本筹集方式均呈现广泛化、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与此相对,明清商人的资本运营理念却较多地保留了传统伦理中的落后因素,因而无法完全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低效与保守的弊端也难以消除。因此,传统伦理对于明清商业的影响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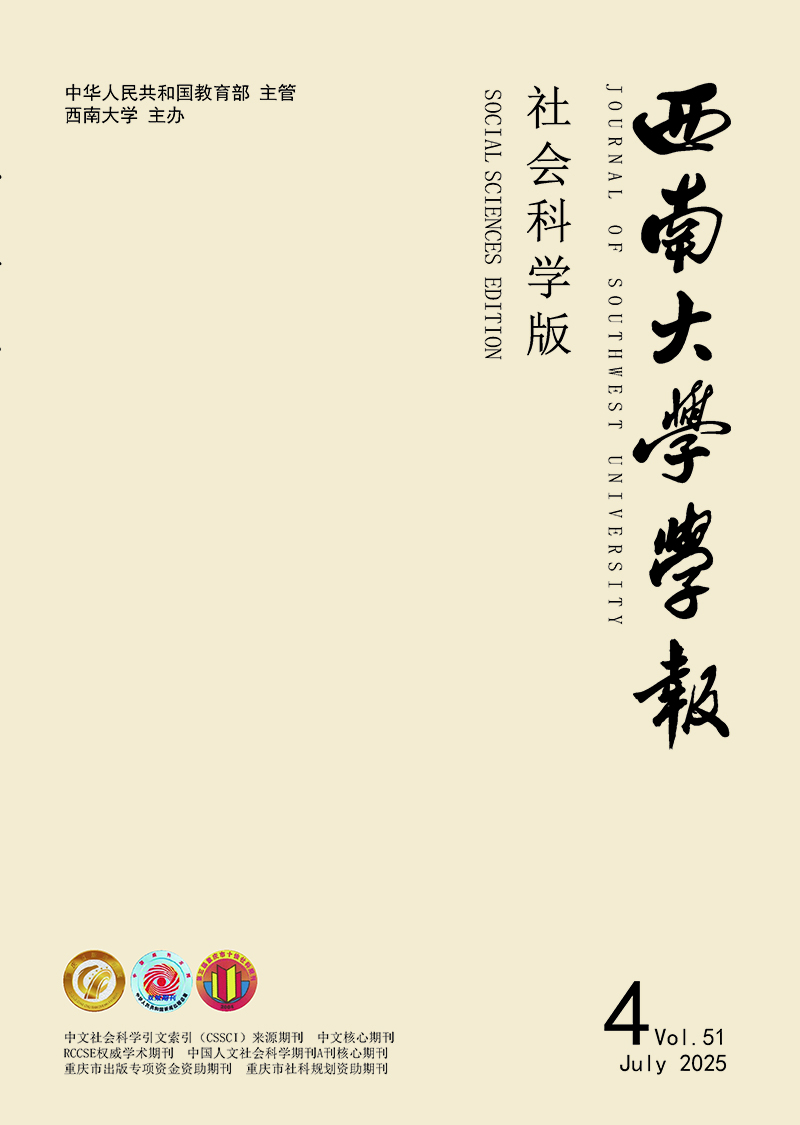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