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现代性与现代文学中城乡书写的关系研究获得了很大进展,而对于19世纪俄国文学的研究视域则正在持续拓展中,尤其是对于俄国文学中密集的城乡书写对本国现代性的探询鲜有深入研究。19世纪俄国文学在从农奴制的“乡村夜话”和半资本主义的“都市神话”的交互体验中,既表现了资本主义文明在俄罗斯城市与乡村急徐悬殊的发展特点,也呈现出俄国现代人紧张、矛盾的思想经历。其中,托尔斯泰涵盖了整个19世纪后半期的文学创作对俄国城乡的书写,无论是时间跨度、思想深度还是现代性思辨的复杂程度,都是历史的最强音。对此问题的研究本应成为当代托尔斯泰研究不可忽略的核心问题之一,却未得到中国学界的明显关注。本文以托尔斯泰在小说中与同时代人迥异的城市书写策略、独具匠心的隐含结构和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为典型文学案例,考察19世纪俄国思想界对自身现代性建构的思辨与展望,也兼以此“镜像”为中国现代性提供一个观照和借鉴的角度。
HTML
-
“现代性”是一个极具争议性、包容性和含混性的概念,却是研究国家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文学的重要视角。笔者认为,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现代性概念分为“可见的现代性”和“隐蔽的现代性”两个层面,将会相对清晰地厘清文学现代性的研究思路。“可见的现代性”是指观察可见的“许多不同进程和历史凝缩的结果”[1],包括政治层面上遵从社会契约建立世俗化现代国家和自由民主政体的确立;经济层面上机器化的工业主义、市场化的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的崩溃;社会层面上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农村和传统文化凋敝、现代化大都市飞速发展、权力和理性计划配置而成的社会组织不断出现和完善,以及上述所有的功能联系。现代文学的叙事空间从传统乡村转向现代都市恰恰是对前述诸特征的综合反映,俄罗斯文学也不例外。
“隐蔽的现代性”可认为是支持或质疑“可见的现代性”的对立观念。前者是启蒙思想家强调的现代性精神的核心“理性”“秩序”和“求新”,进入现代性就是进入理性支配的统一的社会和文化;这种现代性观念认为,“越是新的,就越是现代的。它为一种进步主义和发展主义所主宰”[2],当其成为“霸权”之时,它就背离了真正的理性。于是另一种与之对抗的现代性观念对举而生,即“本质上属论战式的美学现代性”,它“以各种文化上反动的(往往是极端保守的)传统主义的形式出现,或者在更高的哲学层次上说,以一种对现代性的悲观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批评的形式出现”[3]343-344。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文学即为美学现代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它以现代性体验为表现对象,以传统宗法制乡村的衰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都市的兴起为历史语境,呈现现代人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不确定性的感受和反思。这正是“隐蔽的现代性”中的对立观念在书写“可见的现代性”时的互搏。
可见的现代性问题愈是复杂和纠结,隐蔽的现代性层面就搏斗得愈是激烈,其文学表现就愈是富有张力和吸引力。19世纪俄国文学正是以其对本国尤其复杂和纠结的现代性的深刻思辨与论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经历了文艺复兴、基督教改革、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等完整现代化思想洗礼的西欧国家在面对现代性问题时,主要是作为主体的自我批判;而现代化后发国家则首先面临着在现代性的强烈冲击下,自身传统价值体系和社会运行规范解体的危机。马歇尔·伯曼一直关注空间叙事中的现代性思想,他将19世纪的俄罗斯(帝俄晚期)的现代主义称为欠发达的现代主义:一方面,俄国毋庸置疑地出现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现代主义思潮,另一方面,“从19世纪20年代一直到苏联时代,落后与欠发达所负载的痛苦在俄罗斯的政治与文化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我们可以把19世纪的俄罗斯视为正在浮现的20世纪第三世界的原型”[4]。而“正是由于这种现代化本身的欠发达性加之俄国知识界立场的复杂性,使得现代性观念进入俄国语境时与传统文化思想产生了一系列异常尖锐的冲突”[5],这一冲突因为1836年恰达耶夫发表的《哲学书简》而被迅速激化。恰达耶夫提出俄罗斯“会因与西方相像而感到幸福,会因西方迁就地同意将我们纳入其行列而感到骄傲”[6]的主张全盘西化的观点,正式拉开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两大阵营旷日持久的论战大幕,“论战的文学实践则构成了俄国现代性的叙事基础”[5]。
半个世纪后的中国,以梁启超、胡适为代表的西方派和以梁漱溟、章士钊为代表的保守派也开始了以现代性问题为核心的东西文化论战,并由此启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自1917年以来的现代文学,从整体上看也是以追求现代性为根本目的,和中国社会主流构成相互感应、谐振的关系”,但“自1917年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之日起,它就和现代性、反现代性纠缠在一起”[7]。可见,两个地缘亲近的封建专制大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理念随着武力和殖民席卷全球的过程中,在同样面临救亡图存的历史境遇中,都不得不开始接受现代性。但同样作为以非自主性姿态被抛入现代性浪潮的国家,中俄两国思想界在理解现代性和寻找进入现代性适当路径的过程中,又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纠结和坎坷。由此看来,深谙中西现代文化思潮的鲁迅所谓“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绝不仅指俄国“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可以和命运相似的中国人“一同烧起希望”和“一同感到悲哀”,而是直言两国近代以来被动遭遇现代性的惊人相似的思想史,以及现代化早发于中国的俄国在文学上充分的现代性思辨对中国“切实的指示”[8]。而这个“指示”,正是围绕着后发国家如何“在这个世界中获得自身的主体身份认同感”和如何“从客体化到主体性复归的历史进程”[9]这两个现代性问题展开的。作为现代化探求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俄罗斯文学的引介并不仅仅是纯粹的文学翻译活动,而是充满了复杂的权力交锋、意识形态冲突和主体性危机的历史性场域”[10]。如果我们以现代性视阈切入19世纪俄国文学,将对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极有启发。
卡林内斯库说:“在重构现代性历史的过程中,有趣的是探讨那些对立面之间无穷无尽的平行对应关系——新/旧,更新/革新,模仿/创造,连续/断裂,进化/革命,等等。”[3]2现代文学中的城市书写和乡村书写就是这样一组“有趣的平行对应关系”,应当成为文学现代性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文学的力量不仅在于见证了现代化的发生及其所带来的空间变换,而且在于文学参与了现代化的进程,参与了地理和空间的重建”[11],作家们的视线从乡村转向城市,再从城市回顾乡村,这种视线移动所呈现出的,绝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变化,更多的是寄托于其上的情感经验的变化:“一边是即将过去的丰美人生,一边是逗人而可能落空的未来。”[12]
贵族们一方面想冲向城市成为官僚机构中的一员,一方面又怀念乡绅懒散诗意的寄生生活;平民知识分子们则在先进而冷漠的城市文明与落后而温暖的乡村生活之间挣扎。当这两类人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生产者的时候,现代性的焦虑就集中地从城乡叙事空间相互转换中浮现出来。
-
多数现代作家的城市书写都有大量典型的城市外部景观描绘,因为高楼、大道、广场、纪念碑等,都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城市化的典型表征。从文学表现的角度来看,似乎只有将城市外部景观与乡村田园风光相对照,才能更加凸显出城市生活的进步、紧张、机械与不确定性等现代性特征。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亦是如此:普希金的《青铜骑士》对彼得堡城市建筑的虚弱根基发出的疑问,果戈理在《涅瓦大街》中呈现出城市夜景的光声色影和纸醉金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在街道上的“游荡”和对权力的冲撞等,都是在城市外部景观的映照下来表达现代人在令人“眩晕”的都市空间中的身份焦虑。但托尔斯泰却是个例外,他的城市文本中几乎看不到外部景观,这种与众不同的城市书写策略与其对俄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思考紧密相关。
-
托尔斯泰的小说基本遮蔽了城市外部景观,他眼中的“风光”都在乡村。乡村的森林耕地、房舍道路、猪圈马厩等等外部空间均是他不吝笔墨的描写对象。而一旦转向城市,故事就变成了一幕幕“室内剧”:贵族之家、舞会、剧院、办公室、宫廷……那些在奥涅金、柯瓦廖夫、拉斯科尔尼科夫们的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的城市外部景观几乎从未成为托尔斯泰的关注点。只是短篇小说聚焦于单独的乡村或城市场景,而在三大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中,则以城乡对立的结构突出了“城市无景观、乡村全景画”的特点。即便是极少的“例外”,也都出现在主人公要告别现有生活的时候。比如《哥萨克》的开头:“莫斯科万籁俱寂。冬天的街上难得听到辘辘的车声。窗子里已没有灯光,街灯也熄灭了。但教堂里却传出当当的钟声,钟声荡漾在沉睡的城市上空,报道着黎明的降临。”[13]157再如《阿尔贝特》的后半部:“天上没有星星,没有曙光,没有月亮,街上也没有路灯,但各种物体却显得清清楚楚。那座矗立在街头的建筑物,窗内灯火通明,但那些灯火却像倒影似的不断晃动。这座建筑物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阿尔倍特面前。”[13]53最典型的是《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尾:“现在是下午三点钟,街上最热闹的时候。……窗外清新的空气中一个个景象在迅速地变换……这些街道我完全不认识。一座座山似的,全是房子呀,房子……这些房子里全住着人啊,人……有多少人啊,没完没了的人,他们全都在互相仇恨。……一切都是虚假的,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罪恶……”[14]773-783
《哥萨克》中的青年贵族奥列宁厌倦了城市生活,打算离开莫斯科去哥萨克服役,“等他离开莫斯科,就将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过这种生活不会再犯错误,不会有悔恨,只会有幸福”[13]163。《阿尔倍特》中酗酒成性的天才小提琴家阿尔倍特酒瘾发作,遭到上流社会的集体唾弃。冬季的夜晚,无家可归的阿尔倍特唯一一次注意到了街景,却是他醉死前的幻觉。《安娜·卡列尼娜》更是如此。安娜的视野中只有家庭、社交和爱情,她第一次如此细致地观察城市外景,却是在自杀的路上对虚伪和谎言的控诉。
由此看来,托翁这三处“例外”的城市景观倒像是为其他被遮蔽掉的景观做了一个注解:城市里没有真正的生活,它充满了假象和造作,只值得离开之前的最后一瞥。这种城市观在其早期的短篇小说《卢塞恩》中便可见端倪。
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公爵去瑞士小城卢塞恩旅行,起初他惊叹于“湖光、山色和天宇的美”,但当他看到旅馆楼下的湖滨街时,感觉立刻反转了:“可是这儿,在我的窗前,在这浑然天成的自然美景中,却俗不可耐地横着一条笔直的湖滨街、用支柱撑着的菩提树和漆成绿色的长凳。这些粗劣俗气的人工产物,不仅不像远处别墅和倾圮的古堡那样融合在和谐统一的美景中,而且粗暴地将它破坏了。我的视线老是不由自主地同那条直得可怕的湖滨街相撞,我真想把它推开、毁掉,就像抹掉眼睛下面鼻子上的黑斑那样;可是英国人散步的那条湖滨街始终留在原地。我不得不另找一个看不见它的视角。”[13]4以“现代”的观点看来,湖光山色围绕着的小城里,有一条林荫道上的湖滨街,应该是一幅静谧的美景。即使街道是“笔直的”,菩提树“用支柱撑着”,长凳“漆成绿色”,也不至于“粗劣俗气”。相反,这恰恰是现代城市的景观设计理念:自然与人工融为一体,让人们同时体会城市生活的便利与美。可聂赫留朵夫却认为远处的别墅与倾圮的古堡才能与自然美景和谐统一,笔直得可怕的林荫道和油漆长凳是对大自然“粗暴的破坏”。
罗札诺夫在比较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观时就注意到:“托尔斯泰实质上有自己的艺术理论,他就以这种理论与所有其他的理论斗争,这一理论也推动他走向斗争。这种理论确信,没有什么东西比事物本来面目更好的了。”[15]87也就是说,托尔斯泰喜欢一切天然的东西,讨厌人工和矫饰,尤其是在艺术视野中。因此,作为托尔斯泰“第二自我(alter ego)”[15]156的聂赫留朵夫对城市林荫道的否定等于是在说:典型的城市外部景观都像这条笔直的滨河街一样,是“虚假和讨厌的臆造”;是低俗的人工产物,不应该成为艺术作品描绘的对象。这些“艺术的黑点激怒了托尔斯泰”[15]89,于是在《卢塞恩》之后的城市书写中,他果然把城市人工景观“推开、毁掉”,从作品中抹掉了这些“眼睛下面鼻子上的黑斑”,另找了一个“看不见它的视角”。
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文明和对现代“理性化美学”的批判,是贯穿于他一生创作中的。俄国文学史家米尔斯基早就发现:“对现代文明及其‘人为’备增的需求之轻蔑,对国家和社会所有功能和规约的深刻鄙视,对各种约定俗成观点、各种科学和文学‘完美形式’的毫不理会,以及显而易见的教谕倾向……这些互不关联地散见于其早期作品的成分,在他思想转向之后却融汇成一种内涵明确、一以贯之的学说,它渗透进每个细节。”[16]城市景观无疑正是米尔斯基所形容的“人为备增的需求”,是建筑、交通、电力等科学的“完美形式”之展现,而这些要素在托尔斯泰看来恰恰是背离了自然本来面目的虚假产物,于是他选择了“轻蔑”“鄙视”和“毫不理会”。
-
尽管托尔斯泰刻意遮蔽了城市景观,但对城市生活的着墨却毫不减弱。甚至作为比较和批判的对象,城市总是其作品中首先亮相的空间。混乱的生活和虚假的人际关系裹挟其中,似乎唯有如此才更利于以宁静的乡村生活结束他那些史诗般的故事:《战争与和平》以宫廷女官安娜·巴甫洛夫娜的盛大舞会和别祖霍夫公爵去世两个大场景开头,故事所有主人公悉数登场,热闹非凡却各怀心事。《安娜·卡列尼娜》以彼得堡的奥博隆斯基家“一切都乱了”的室内场景开局。《复活》的开场则成为托尔斯泰城市观的著名总结:“尽管好几十万人聚居在一小块地方,竭力把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肆意把石头砸进地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尽管他们除尽刚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在城市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唯独成年人,却一直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春色迷人的早晨,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所创造的人间的美,那种使万物趋向和平、协调、互爱的美;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17]1再来看结尾的写法:《战争与和平》的结局,是尼古拉和玛丽、彼埃尔和娜塔莎两个家庭都在乡间过上了平静幸福的家庭生活。《安娜》的最后13章也全都是乡村场景。当列文失去人生方向想要自杀的时候,是一位农民告诉他:“为灵魂活着,要记得上帝。”最终列文回到了他的庄园,在农事活动和家庭生活中获得了精神的宁静和生活的力量。《复活》的最后,聂赫留朵夫在陪伴玛丝洛娃流放的西伯利亚乡村中真正领悟了《圣经》的救赎希望。
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故事从混乱的城市生活开始,然后城市的一幕幕室内剧和乡村的一首首田园曲交错呈现,最终以和谐的乡村生活结束——这个空间叙事排布策略形成了托尔斯泰三大长篇的基本结构。只是《战争与和平》由于叙述宏大、人物关系复杂、场景极多而导致读者容易忽略首尾的空间策略;《复活》则更倾向于主人公的精神复活历程,不易使人在意人物所处的物理空间;唯有《安娜·卡列尼娜》两条清晰的并行故事线索,提醒我们注意到了托尔斯泰对城市和乡村的着意书写。
一. 总体美学观:城市里没有真正的生活和美
二. 固定隐含结构:从城市的负面形象开始,以乡村的美好生活结束
-
托尔斯泰十分关注家庭生活,典型的俄国贵族家庭生活不仅构建起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家庭幸福》等中长篇小说的主要情节,还明显形成了城乡对立的两大阵营,以正反两面承担起了托尔斯泰道德教化的任务。在《战争与和平》中,老包尔康斯基公爵的正直、勤勉、忠诚的庄园贵族父权家庭,温暖奢侈又入不敷出的罗斯托夫一家,工于心计、淫荡堕落的库拉金公爵一家,是父辈家庭;安德烈与丽莎、彼埃尔与海伦、彼埃尔与娜塔莎、尼古拉与玛利亚公爵小姐则组成了几个错综复杂的子辈家庭。从城乡视角来看,具有庄园(乡村)贵族基因的家庭都是(虽有问题却)彼此忠诚而幸福的,而宫廷(城市)贵族之家却多为“偶合家庭”。“偶合家庭”的说法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即家庭成员虽有亲缘关系,却彼此疏离、想法各异,甚至相互仇恨,传统的宗法制度下和谐的家庭关系已荡然无存。可见,“偶合”的意义也适用于托尔斯泰笔下的家庭关系。
这种家庭观更加明显地体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小说写了五组城市家庭关系,却没有一组是幸福的:奥博隆斯基与多丽家、谢尔巴茨基家(多丽和吉蒂的娘家)、安娜和卡列宁家、沃伦斯基和他母亲,以及列文和两位亲哥哥。奥博隆斯基与家庭教师偷情被妻子发觉,这个家的“所有家庭成员和上下老小都觉得,他们大家生活在一起已经毫无意义”[14]3。妹妹安娜从彼得堡来莫斯科调解哥哥的家庭纠纷,却因遇到沃伦斯基而弄散了自己的家庭。老式都市贵族谢尔巴茨基家的两个女儿,都以地位和财产为择偶标准;唯一怀揣爱情来求婚的乡村贵族列文则遭到了全家鄙视,直到小女儿被沃伦斯基抛弃,家人才意识到列文的可贵。沃伦斯基一直鄙视其母的放荡,却继承了她的生活方式。母子之间毫无亲情,只在乎从对方身上获取的利益。列文的两位兄长都生活在莫斯科,但很少来往。二哥尼古拉搞民粹活动失败,成了贫困潦倒的酒鬼。大哥谢尔盖是高官,谙熟经济理论,却不理解列文的农业实践活动。三兄弟各自不认同对方的价值观,亲情疏离。
托尔斯泰用五个城市家庭的例子来说明“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幸福家庭”为何“彼此相似”?他只举了一例:定居乡村的列文与吉蒂之家。也就是说,乡村生活是家庭幸福的唯一模型。《安娜·卡列尼娜》中这著名的开篇第一句,一旦与托翁的城乡对立观联系在一起,意思就更加清晰了。
-
“舞会”是托尔斯泰城市叙事中最典型的社交空间。它是上流社会的名利场,耀眼的灯光与标准的社交礼仪之下,隐藏着无数的秘密,涌动着稠密的欲望,经营着各种肮脏的交易。虽然舞会本身并不是现代性的产物,但其中反映出的人际关系、政治话题和资本秘密却都是极具时代感的主题。从《战争与和平》的宫廷舞会、英格兰俱乐部的盛大宴会,到后期短篇《舞会之后》的贵族家庭舞会,人们读到的全是奢靡和堕落。
莫斯科的那场舞会成为吉蒂成长的第一课:“在吉蒂的心灵中,整个舞会,整个世界全都罩上了一层迷雾。”[14]82-83舞会更是安娜踏入悲剧的第一步。托尔斯泰通过吉蒂在舞会上被沃伦斯基冷遇的感受,暗示了安娜爱上沃伦斯基的悲剧性。但这一点并不是托尔斯泰热衷描写舞会的首要目的。乔治·斯坦纳认为:“在托尔斯泰的词汇中,舞会具有模糊不清的言外之意;它既是展现优美和高雅的场所,又是典型的人为之物的象征。……奢华的场面,巨大的浪费,主人与奴仆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一切如芒刺在喉,堵在托尔斯泰的心上。”[18]75
在数部小说的大量舞会场景中,托尔斯泰写出了上流社会的众生相,但却从未挑明舞会的“言外之意”。直到晚年,当他经过了大量对莫斯科城市贫民生活状况的实地调查之后,才在长篇政论文《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中写出了舞会的本质:“所有这一切,从马具、车辆、树胶轮子、车夫的呢子大袍,直到袜子、皮鞋、鲜花、丝绒、手套和香水——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些有的醉倒在卧室的铺板上,有的在夜店里和妓女同宿,有的已被发送到监狱去的人制作出来的。这些赴舞会的人从他们身边驶过,穿的全都是他们的东西,用的也全都是他们的东西,脑子里却不曾想到在他们去参加的舞会和这些正被他们的车夫严厉呵斥的醉汉之间会有什么联系。——他们用这种娱乐毁掉成千上万人的折磨人的劳动,这不但不是欺负任何人,而且正好是用这娱乐养活穷人。”[19]206-209
托尔斯泰发现了舞会的现代性秘密:舞会中所有可见的奢侈品,都来自于工人的劳动,工人则由虽被解放却更加贫困的农民组成,因此舞会的辉煌皮相归根结底来自于富人对穷人的压榨和城市资本家对农民的剥削。而那些上等人自以为拥有的教养和慈悲,比穷人的醉酒和嫖妓更加无耻和虚伪。
-
“火车就像很多诞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类创造物——如远洋巨轮、摩天大楼一样,汇聚了这一美好的愿景。它是科学、技术、进步、平等、自由等现代性宏大叙事的代名词,是我们立在铁轨上的‘自由女神’和‘埃菲尔铁塔’,展示出人类改天换地的信念。”[20]1834年,在英国开始大规模铁路建设后不到十年,俄国境内就首次出现了火车,1837年第一条铁路建成[21]。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的惨败更是激发了沙皇政府建立庞大铁路系统的决心,俄国铁路建设进入飞速发展时期。在俄国追赶西方的道路上,铁路成了俄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先锋。托尔斯泰写作《战争与和平》和《安娜》的时期,就正值俄国处于如此“激动人心的全新环境”之时,西方派认为:“这是一片发生着经济与社会巨变的天地,这些变革可以归结为不同的名称,叫做‘现代化’、‘工业化’或‘资本主义发展’。”[22]保守却异常敏感的托尔斯泰自然不会忽略铁路这个现代化象征,于是俄国第一条铁路莫斯科-彼得堡铁路,就成了安娜从传统的家庭生活出发奔向自由爱情的不归路。
在到达莫斯科的站台上,安娜首次亮相:“仿佛有一种什么从她身上满溢出来的东西正不由自主地时而在那目光的闪耀中,时而在那微微一笑中显现出来。她有意想把她眼睛中的光芒熄灭掉,然而那光芒却事与愿违地又在她隐隐的笑容中闪露出来。”[14]64这“不由自主的”“事与愿违的”光芒,恰如托尔斯泰对铁路的认识:现代化的进程无法遏止,即使他并不欢迎。钢铁的道路和飞速的火车显然比土路和马车先进,但在托尔斯泰眼中却失掉了泥土的温度和情感。火车的速度和动力正像是安娜那“无法克制的盎然生气”,她身上“满溢出来的东西”,就是自我意识,是现代人的标志。安娜的觉醒和自我怀疑也是在从莫斯科回彼得堡的火车上:“在这晃动着的昏暗之中,一切的形象、一切的声音都变得特别地鲜亮,令她惊异。她不停地一阵阵在怀疑,火车是在向前开呢,还是向后退,还是根本就没有动。”[14]102
这就是托尔斯泰式的质疑:现代化带来的新奇感,像是冲破了传统生活的迷雾,可俄国的“自我”,是打算向前走,还是向后退,或是维持一种暧昧的现状?“在19世纪,除了铁路之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作为现代性更生动、更引人注目的标志了。科学家和政客与资本家们携起手来,推动机车成为‘进步’的引擎,作为对一种即将来临的乌托邦的许诺。”[23]特拉赫滕贝格序2而俄国人对“乌托邦”的信仰却面临着传统的巨大挑战:“然而接着一切又都含混不清了……这个穿长腰身外套的农民去墙上啃着什么东西了,那位老太太把腿伸得有整个车厢长,弄得到处乌云密布;接着有个东西怕人地轧轧响起来、敲打起来,好像把什么人碾得粉碎;接着一片红色的火光耀得她睁不开眼,接着一切都被一堵墙给挡住了。安娜觉得,她在往下沉。”[14]103红色的火光像是卧轨瞬间喷出的鲜血,伸长了腿的老太太就是充满谣言的保守的上流社会,敲打铁皮的人是死神,她的生活最终被堵死,她由铁轨走向地狱。“铁路是新世界的象征:它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同时把旧的生活摧毁。”[24]托尔斯泰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在缺乏完整现代性精神的社会语境中,某种孤独的现代化冲动只会毁了传统的平静生活。
火车在《复活》中继续成为女主人公爱情破碎的助推器:卡秋莎听说聂赫留朵夫会乘火车经过此地,就想去乡村火车站追上他并告知自己怀孕的消息。但她无论怎样奔跑,都无法赶上火车的速度,眼睁睁地看着聂赫留朵夫与她擦肩而过:“火车加快了速度。卡秋莎加快脚步紧紧跟着,可是火车越开越快,……卡秋莎落在后面了,可是她还一个劲儿地在湿漉漉的站台木板上跑着;……她还在跑,但是头等车厢已经远远跑到前面去了。……头巾被风吹掉了,可是她还一个劲儿地在跑。”[17]131“铁路消灭了旧有的空间与时间的观念……传统的空间——时间连续体,是旧式运输技术的特点,在人们的体验中它正在被消灭。”[23]60托尔斯泰显然是感受到了这一点,才让聂赫留朵夫坐上了火车。如果他乘坐的是马车,也许所有的后续故事都要被颠覆了,托尔斯泰就无法继续“忏悔贵族”的复活之旅。
安娜和卡秋莎的悲剧都跟火车脱不开干系,但时代的变化已然显现。1870年代的安娜们,看到火车迎面而来,那个时代的城市贵族感觉自己是迎头撞上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而1890年代的玛丝洛娃们,就已经追不上火车的速度了,乡下底层人眼睁睁看着不属于他们的进步擦身飞过。两代女性面对相似悲剧也都想过“卧轨自杀”。安娜这样做了,卡秋莎也这样想过:“再有火车开过来,往轮子底下一趴,就完了。”[17]131但贵族和农民对生命的热爱能力却在时代悲剧到来的时候显示出巨大的差异:两个遗留的子女都未能拦住贵族安娜奔向铁轨,而一次胎动就让农民卡秋莎放弃了自杀的念头。火车也是考验生命力的象征。
传统的婚姻、稳定的家庭和社会关系,都因为冲动的现代意识而崩溃,正如铁路破坏了俄国封闭的宁静生活和传统的贸易方式一样。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给传统社会带来的最大问题是:“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5]铁路(火车站)成为托尔斯泰城市书写的关键词,意义正在于此。
从已无法提供幸福的“家庭”到资本、欲望和剥削的共同结晶——“舞会”,再到科技进步的代表——“铁路”,托尔斯泰直接剥去了都市现代化景观的华丽外衣,让读者看到了机器般冰冷的城市灵魂。为何从社交到家庭,城市生活充满了疏离而虚伪的“偶合性”?为何人性没有随着西式启蒙教育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更加高尚?托尔斯泰独特的城市书写策略和鲜明的“反城市”观背后,是他从清晰的城乡对立观念出发对俄国现代性问题长久而深刻的思考。
一. 家庭:宗法制乡村家庭幸福相似,现代城市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二. 舞会:资本罪恶的虚伪皮相
三. 铁路:以“进步”摧毁“传统”
-
城里的人不劳而获,农民却劳而不获。这是托尔斯泰对城乡差别的第一层认识,也是他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印象:“我记得成千上万个城里人,有的日子过得不错,有的很穷。——大家无一例外地对我说,他们是从农村到这里来谋生的,说莫斯科人不种也不收,日子却过得很富……可是要知道,只有农村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只有那里才有真正的财富:庄稼、森林、马匹,等等。究竟为什么要到城里来获取农村有的东西呢?”[19]128晚年的托尔斯泰亲自参与莫斯科的城市人口普查之后做了系统而理论化的分析:“生产者的财富转到了非生产者的手里,并且聚集在城市里。——农村居民为了满足对他提出的种种要求和摆在他眼前的种种诱惑不得不交出这一切,而他交出自己的财富以后自己却不够用了,因此他必须到他的财富被运往的那个地方去,在那里一方面努力挣回为满足他在农村的第一需要必不可少的金钱,一方面自己也迷恋于城市的种种诱惑,就和别人一起共享聚集在那里的财富。”[19]128
托尔斯泰认为,城市的富足和发达建立在剥夺农民的基础上,被剥夺的农民只能进城务工,但又遭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形成了二次贫困,成了城市贫民。城市越来越富,农村越来越穷,而所有的一切都起因于富人们对奢侈享乐的不懈追求:“仔细推究了我对之无能为力的城市贫困的性质之后,我看到这种贫困的第一个原因是我夺走了农村居民的必需品并把这一切运到了城里。第二个原因是当我在这里,在城里享用我在农村搜刮来的东西时,我用自己的穷奢极侈诱惑并且腐化了那些为了设法取回他们在农村被夺走的东西而跟着我来到这里的农村居民。”[19]132-133
尽管托尔斯泰认为,在“收获”的手段上,贵族和资本家没什么区别,都是未经体力劳动的“不劳而获”,城市愈富乡村就愈穷主要在于这些不劳而获的人的欲望,其实他谈到的“种和收”的经济模型,正是资本在现代化城市中的聚集方式和城乡居民均被资本重新奴化的过程。托尔斯泰已经看到了现代化进程中资本的城市化和乡村在现代生产中的边缘化,都市和乡村的二元结构矛盾也越来越激烈,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有机联系在资本空间的重组中遭到了扭曲,消费的意义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对需求的满足,而是为了加强新一轮资本的积累。马克思认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存在完全隶属于资本,经济的道德取代了人的道德”[26]。我们看到,托尔斯泰将城市和乡村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于人性的堕落,在作品中直接进入对人的形而上的道德判断和价值观重建,似乎忽略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考察,实际上他的想法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路不谋而合:即从资本主义生产空间批判转移到社会道德空间的批判。
-
基于人性堕落导致富人剥削穷人、城市剥削乡村这一认知,托尔斯泰进入了对城乡问题思考的第二个层面。在他看来,城市是道德败坏的沃壤,乡村则是淳朴道德的根基和价值重建的良田。从《战争与和平》到《复活》,尼古拉、列文和聂赫留朵夫分别是经历了1812年俄法战争、1861年农奴制改革和1880年代俄国思想界纷纭动荡的19世纪俄国最典型的三代贵族。而这三代人都没能从城市中受到良好的熏陶。不忠诚的婚姻、利欲熏心的宫廷斗争、奢侈享乐的生活与不作为的官僚机构……这样的城市道德状况居然近一个世纪都没有改观,而乡村生活最终拯救了三代俄国人的灵魂。
《战争与和平》里的老沃尔康斯基是托尔斯泰心目中美好的乡村贵族典范,他在童山庄园的隐退岁月是“美好生活”的代名词。生长于童山的安德烈和玛丽亚则是整部作品中道德水准最高、人格最健全的形象。《复活》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中,乡村和城市对人性的影响得到了总结性的呈现。对聂赫留朵夫来说,乡村意味着诚实而有自我牺牲精神、美好的事业、秘密的自然世界、哲学和诗歌以及纯真的爱情;而城市则充满了荒淫放荡、彻底的利己主义、现实的环境、人为的规章制度和赤裸裸的情欲。精神“复活”后的聂赫留朵夫决定彻底放弃城市生活,放弃土地所有权,在西伯利亚乡村的自我流放中清洗兽性,重建道德观。
乔治·斯坦纳说:“托尔斯泰使用了意象和暗喻,以便将他最关注的两个层面——即农村和城市——的经验联系起来,进行对比。在这一点上,我们触及的可能是他的艺术核心。其原因在于,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之间的区别具有启迪性;对托尔斯泰来说,这是善良与邪恶之间的根本区分,是非自然和不人道的城市生活准则与田园生活的黄金时代之间的区分。这种基本的二元论是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形成双重或三重结构的动机之一,并且最终在托尔斯泰的伦理体系中得以定型。”[18]77
可见,我们前面总结的三大长篇中固定的隐含结构:故事从城市开始,以乡村结束,就是在影射俄国的问题——从城市的堕落开始,希望在乡村得到救赎。这是托尔斯泰对俄国现代化问题的终极思考:俄罗斯民族应该以何种姿态加入到世界的现代化洪流中去?是以其与西欧无异的城市化建设,还是以保留在乡村的村社制度和东正教信仰来重建的民族自信心?显然他给出的答案是后者。
-
“卢梭主义”是托尔斯泰的精神架构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或形成原因,他曾明确承认:“我读过卢梭的全部著作,……我对他绝不单单怀有激情,我崇敬他。我对他的几段话非常熟悉,我觉得好像都是我自己写的。”[27]20托马斯·曼将托尔斯泰的自然观与卢梭倡导的18世纪自然神论联系在一起:“他的乌托邦倾向,他对文明的憎恨,他对乡居田园生活,对心灵牧歌般宁静的偏爱——一种高尚的偏爱、一个贵族主人的偏爱——同样可被认为属于十八世纪,即法国的十八世纪。”[27]19“对他而言,人化就意味着去自然化,从此,他一生的斗争便是经受与自然的分离,与一切自然的,尤其对于他是自然的东西的分离。”[27]39-40以赛亚·伯林说:“近代作家中,他(托尔斯泰)最喜爱、最佩服的是卢梭的看法。如同卢梭,他排斥原罪之说,相信人生而纯洁,只是被自己的恶劣建制所毁——其中为害尤劣者,即文明人所谓教育。”[28]
人化、去自然化、文明化,就是人变成现代人、乡下人变成城里人的过程,亦是乡村的凋敝和城市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对资本积累的追求使得个人对权利和财富的追求成为新的价值导向,而“个人权利的启蒙却无法提供政治共同体所必需的社会德性”[29,于是卢梭追问:“一旦人们不惜任何代价只求发财致富,德性会变成什么样子呢?”[30]这个问题迫使他“打算从重建启蒙与道德的关系上寻找突破口。……正是在这一点上,卢梭对现代性发起了第一次攻击”[29。与卢梭的疑问和意图高度一致的托尔斯泰,便试图从回归自然和乡村来恢复启蒙的本意,重建个人道德与社会德性。他对现代性的攻击并没有回避原初的启蒙精神,而是面对绝对理性化的启蒙后果,以反启蒙的姿态从卢梭主义直接走向了民粹主义。
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使“西欧派”核心人物赫尔岑告别了“西化”梦想,将俄国希望转到了传统的村社制度上。他分析了俄国村社的优越性:每个社员都有土地,土地属于社会,村社内部自治,并相信“俄国农民公社已经寓有一个公道且平等的社会”,在此基石上建成的自治联盟才是真正具有俄国社会“最深的道德本能与传统价值”[31]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赫尔岑的思想影响了两代俄国知识分子,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后,遍布全俄的民粹主义运动开始。民粹主义者既反对斯拉夫派以维持沙皇专制统治为前提的保守化改良方案,亦看清了启蒙运动一个世纪之后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化暴露出的种种弊端,他们“认为俄国经济制度具有独特性,特别是认为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农民村社被看作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好的东西”[32]。俄国民粹主义寻求的是一条超越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主张的,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的道路,“而这条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基础和可行性则必须在俄国社会内部中寻找,从俄国的特殊性中寻找,其答案就是尚未瓦解的农民村社”[33]。民粹主义的思路与托尔斯泰的城乡观念不谋而合,他终于意识到俄国村社制度才是真正可以安放自己信仰的宗教,他在给表弟的信中说:“这就是我生命的全部,这就是我的修道院,是我能逃离焦虑,远离生命中的疑虑和诱惑,寻求平安的庇护所。”[34]
托尔斯泰对西方启蒙思想和本土民粹运动的认识,绝不仅仅来自私人体验和流行观念,而是经过了对基督教神学、黑格尔、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哲学以及当时流行的西欧社会学、经济学著作的认真研究,并结合深入的社会调查之后的深思熟虑。在他看来,基督教的传播、启蒙思想家的研究成果都掩饰了对人类不平等根源的本质认知。千百年来,不同时代的非体力劳动群体先后总结出了以上三种为国民洗脑的“教义”:基督教以上帝的旨意为名义,古典哲学以存在即合理为名义,实则都是掩盖了强权对弱势的奴役与暴力的谎言。之后,托尔斯泰将怀疑的目光投向理性、科学启蒙、资本主义与现代化——这种“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教义”,他指出:“目前为我们时代的国务界、工业界、科学界和艺术界的先进分子们的辩护词充作基础的东西,乃是一种科学的教义。但这里的科学二字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一般的知识,而是指一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十分特殊并被称为科学的知识。在我们的时代,使得游手好闲的人看不到他们已背叛自己的使命的辩护词主要是依靠这种新的教义才能存在。”[19]225-226
托尔斯泰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更多的人脱离体力劳动,用更加具有隐蔽性的手段去奴役和剥夺体力劳动者的过程。这无疑正是城市与乡村对立的根本原因。他将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新兴资产阶级视为既不依靠体力劳动也不依靠宗教机关、政府机构和国家暴力机关的“游手好闲的人”。而正是这些“游手好闲的人”将自然科学、启蒙哲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变成了这个时代新的信仰。这些思想看上去似乎比基督教神学和形而上的黑格尔哲学更“进步”,其实却是比前两者更为巧妙地在为脱离体力劳动而辩护,为新的剥削方式寻找新的合法性。
要彻底改变这种奴役和剥削,就不能再寄希望于为奴役和剥削辩护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主要空间载体——城市,而是要在先进知识分子的领导下回归乡村,改良村社制度。这正是俄国民粹主义的核心观念:“由先进知识分子领导农民,避开或者说跳过资本主义,在村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33]他还总结道:“宪法、保护关税、常备军队,所有这一切把西方民族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抛弃农业,与农业疏远,在城市,工厂里生产大部分并不需要的产品,被派到军队去干形形色色的暴行和掠夺。他们的状况初看起来无论怎样耀眼,其实是没有出路的。只要他们不改变目前的欺骗、腐化和掠夺农业民族为基础的生活制度,他们就免不了毁灭。……我们必须而又可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并且是最简单的事:过和平的、农耕的生活,忍受可能施加于我们的暴力,不以武力对抗暴力,也不参与暴力。”[35]
一. 乡下人“种”,城里人“收”
二. 城市的堕落和乡村的拯救
三. 从卢梭主义到民粹主义
-
从历史语境看,自1812年俄法战争、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1848年欧洲革命和1853年俄国克里米亚战争惨败,到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1870年代民粹派运动到1880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以及贯穿了整个19世纪的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有俄国现代性标志事件都引发了托尔斯泰对城市化进程和农业变革举步维艰的沉思。从个人的思想路径看,托尔斯泰本人对乡村和大自然与生俱来的热爱与亲近、他深入血液的东正教信仰、对西方思想史的研读和对东方哲学的兴趣,都使他在对待资本主义文明、理性、科学以及流行的政治观念时,保持了独立的认识。如此历时性思想变迁和共时性坚定信仰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张张力十足而底线明朗的大网,几乎能够捕捞起19世纪所有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体验和思辨。
作为现代性后发的国家,俄国知识分子往往更能够以西欧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出现的负面问题为戒,在资本主义还未在俄国发展成熟的时候,就先注意到它的缺陷;而作为农业人口占十分之九的国家,俄国思想界也总是会去乡村寻找出路。托尔斯泰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他更清楚更宏观地意识到“城市现代化并未真正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景,未真正为人们提供具有价值和尊严的栖居,反而消化掉了人的主体性”[36]。城里的富人成了金钱的奴隶,穷人成了富人的奴隶,乡下人成了城里人的奴隶,所有的人都丧失了主体性。托尔斯泰反对的并不是城市本身,而是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人性危机。他肯定的也不是停滞落后的农业现状,而是俄国传统农业国优势和农民式的道德根基。若在废除农奴制之后将传统村社制度完善至理想境界,那么在自足的农耕生活中,俄国人不但会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更会经历“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博爱”这一社会整体道德的重建,俄国民族的“聚合性”精神将得以修复。到那个时候,城市也终将改变“欺骗、腐化和掠夺农业民族为基础的生活制度”,重新确立它的使命。托尔斯泰的读者常常会迷失于他清晰的“故事”与复杂的“思想”之中。但由上述梳理便可发现,“城乡对立”是他小说文本的“任督二脉”,以“隐蔽的现代性”为“气”将这二者打通,便有豁然开朗之效:原来“托尔斯泰主义”的核心内容,正是在他对俄国的现代性问题反复思辨和持续的城乡书写中最终形成的。
从“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开始,到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新启蒙运动”,再到2010年前后“东西之争”战火重燃,在资本现代性话语霸权的背景下,作为后发民族国家的“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主要是由三方面因素决定的:中国传统观念和体制的保守性,中国近代以来的特殊历史进程,中国广大的地域以及政策原因造成的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37]。中国遭遇的现代性困境与俄国何其相似!正如鲁迅所言:“中俄两国间好像有一种不期然的关系,他们的文化和经验好像有一种共同的关系……中国现时社会的奋斗,正是以前俄国小说家所遇着的奋斗。”[38]当下,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四个自信”为中国现代性指明了方向,但思想界对于“现代性”的含混理解仍然需要“他山之石”的经验以助厘清。尤其是“文化自信”,作为“一个民族基于对自身文化的理性认知而形成的对于文化的高度认同、自觉意识和积极心理状态,这些对于一个民族在选择自身要走的道路时具有重要的影响”[39]。托尔斯泰为俄国现代性困境给出的救赎方案,恰恰是在强调俄国的“文化自信”与对本民族的自信,他在一个多世纪之前超越了本国“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二元对立局限的现代性思辨与文学表现的力量,至今仍能给中国读者以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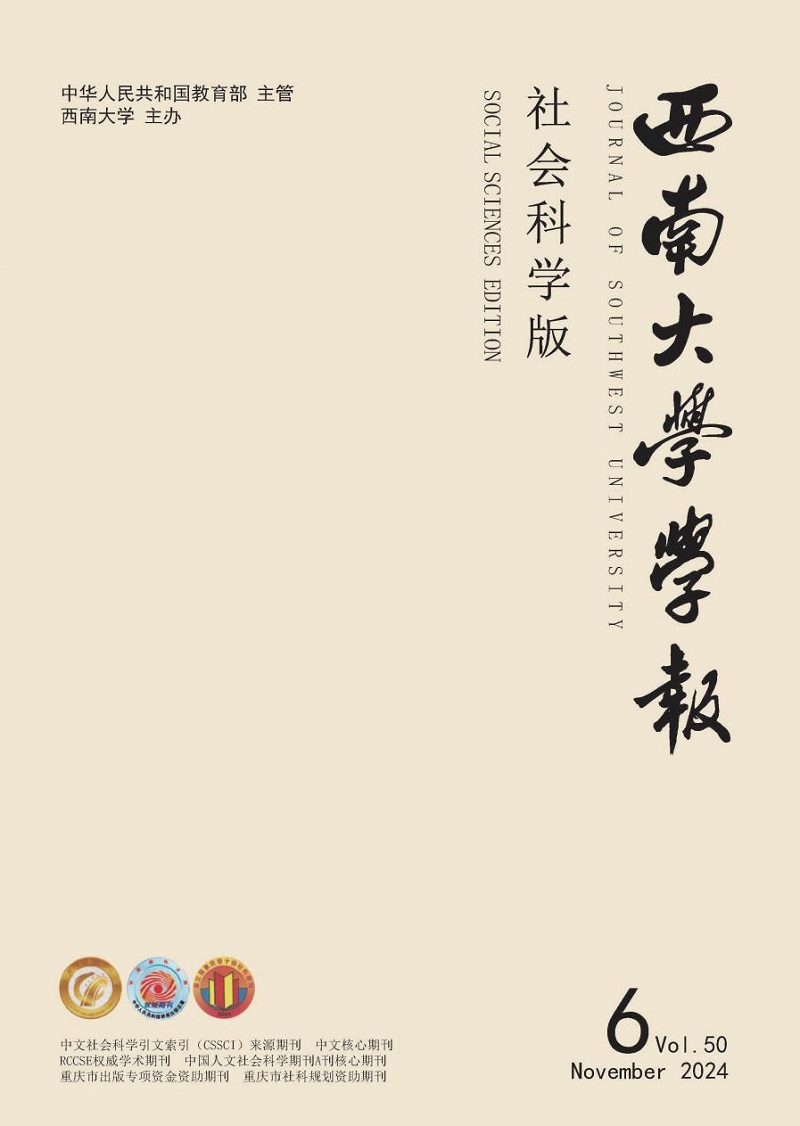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