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ML
-
教材作为英语学习者语言输入的重要来源,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我国是以课堂教学为主的英语学习环境,教材对英语学习的影响更大。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材先由教师在备课阶段予以解读,之后在课堂上讲授给学生。因此,探究英语教师如何评价教材,这对英语课堂教学有重要意义——既关乎教材作用的发挥,更关乎学生的学习效果。
国内外已有的英语教材评价研究,主要从4个方面展开。
第一,对教材评估体系进行研究。比如:以Cunningsworth、Mcdonough、Shaw、Breen和Candlin为代表西方教材评估体系的提出[1];Sheldon设计了涵盖教材文化偏见、真实性、效度、价值等多项指标的教材评估表[2];James从教材促进语境迁移角度出发,提出了一套教材评估标准[3];张伟年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出发,提出了包含意识形态、语类、文化模式和评价理论的教材综合评价框架[4];郭剑晶对法律英语教材的评价量表进行探讨[5]。
第二,对教材某一特定内容进行研究。比如:教材的真实性[6]、教材话题和真实生活话题的差别[7]、跨文化交际知识[8]、英语写作教材模板的负面作用[9]、教材中的性别歧视[10]、教材活动设计的合理性[11]、教材的文化内容[12]、教材如何体现语言学理论[13]、教材的词汇分布[14]、教材的语用知识[15],等等。
第三,从使用者角度进行教材评价研究。比如:不同教学经验的英语教师,在教材评价时表现出不同的评估能力[16];学生对网络和纸质版英语教材的态度[17];师生的教材需求等[18-19]。
第四,对不同类型或来源的教材进行对比或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研究。比如:专业英语和普通英语教材的比较[20],国外英语教材的本土化[21],等等。
虽然已有的关于研究教材评价的文献呈现出内容较丰富、视角较多样化等优点,但仍存在几个不足:(1)研究者提出的教材评估框架,虽出发点和研究背景各不相同,但往往都偏重于主观[1],应用起来并非易事;(2)研究者多集中于对评估体系的客观性、科学性或对教材内容的正确性等方面进行探讨,较少关注教师是如何评价教材的;(3)研究对象大多以整本或整套教材内容为评价对象,而鲜有关注教师对教材中具体语料是如何评价的。本文认为,一项关于紧密联系英语课堂教学实践的教材研究,应从关注英语教师对教材所持有的态度出发,并聚焦教师课堂教学的具体语言材料。目前,在引进国外和我国主编的英语教材数量激增的趋势下,研究英语教师对国内外教材的看法,可对教学实践和教材编写提供启示。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3个研究问题:(1)英语教师对教材中的语言材料进行评价时的关注点是什么;(2)英语教师的教材评价模式具有什么特点或存在什么问题;(3)英语教师对国内和国外教材的态度有什么差别。
-
受访者是9名工作在教学一线并拥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全职英语教师,分别来自我国小学、中学和大学。他们的平均教龄为13年,其中6位女性、3位男性,所有教师的母语均为汉语。研究力求采集最自然的教师评价语料,因而未设置任何引导性问题,仅要求教师们结合自身教学经历,对4段选自英语教材的口语对话进行评价。其中,对话(1)和对话(2)来自国外引进版教材《走遍美国》[22],对话(3)和对话(4)分别选自我国主编的英语教材《英语(Go for it)》[23]和《英语》(三年级起点)[24]。为便于比较,所有对话的内容均是关于“问路”。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对教材优劣的评判,仅从普及性的角度出发,选择了在校学生或英语自学者广泛使用的英语教材。4段对话的难度和篇幅无明显差异。教师的评价均使用汉语,对评价的内容、时间、篇幅、形式(口头或书面)均无要求,最终得到口头评价7段、书面评价2段。对口头评价语料转为电子文档以备分析,对书面评价语料则直接进行分析。
-
本文采取的认知语篇分析法(CODA),是英国班戈大学语言学院Tenbrink教授于2015年在国际语言学权威期刊《语言和认知》(Language and Cognition)上发表的“Cogn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accessing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and processes through language data”一文时,正式提出的[25]。该方法是一套融合了语言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相关知识并通过语言来探索思维表征的跨学科语篇分析方法,主要涉及对语篇的内容分析和语言分析两大层面,现已被用于探索人类思维和认知心理活动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在通过语言揭示人类的空间认知模式方面,影响更大。因此,不同于以往的教材评价研究,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分析教师对教材中具体语言表达的评价语料来揭示教师对教材的评价模式,而不是为了建立一种教材评价体系[1-5],也不是为了考量英语教师在教材评估方面是否专业[16]或通过问卷调查等方法了解教师对教材的需求[18-19]。
一. 研究对象
二. 分析方法
-
本部分以CODA[25]为指导原则,借鉴Krippendorff的语料处理方法[26],对语料分割和评价焦点分布两个方面的内容进行分析。首先,根据一个完整评价焦点归为一类的原则,将语料分割成若干单元(unit);其次,根据语料内容的切分结果,统计各评价焦点所包含的总单元数量;最后,比较各焦点所含单元数的量化分布情况,揭示教师对英语教材对话语料的关注点。
-
通过对全部评价语料的内容进行解读,结果发现,教师的教材评价中出现了5个焦点,即语言、语境、教学、偏好及其他。各焦点单元的定义及示例,见表 1。需要说明的是,语料分割后的每个焦点单元所包含的句数是不等的,有的只包含一个句子,有的则由几个句子组成。它们的共同点是:均包含一段完整的思维,均体现了一个评价焦点。表 1中的所有示例,均为完整的评价焦点单元。
-
首先,以上文的5类焦点为标准,1名研究者对全部语料进行分割和编码。为保证其可信度,邀请另1名研究助理按上文焦点类别的标准对20个单元(大约占全部语料22%的内容),再次进行编码。然后,按照Krippendorff提出的SPSS Macro[27],计算两个编码者间的信度Krippendorff Alpha值。结果显示,整体互信度良好(α=.88),即在对语料的评价焦点分类和编码上,两名研究者的结果高度一致,具有可靠性。合计有3 086个汉字的评价语料库,经过分割后得到92个焦点单元。其中:16个单元属于书面评价,包含318个汉字,占总字数的10.3%;76个单元由口语评价组成,包含2 768个汉字,占总字数的89.7%。各位教师的总评价单元数范围为:最少7个单元,最多21个单元。除去教师评价中与教材内容不相关的“其他”类所包含的5个单元外,剩余4个焦点所包含的单元数、参与各评价焦点的教师人数及其所占总人数百分比的结果,见图 1。
首先,评价焦点的单元数明显随参与评价的教师人数增加而增多。9名教师都对教材语料的语言表达进行了评价,占总人数的100%,包含44个单元,占全部单元量的47.8%。有8位教师表达了对语境的关注,占总人数的88.9%,包含26个单元,占全部单元量的28.3%。从英语教学角度对教材进行评价的教师有3名,占总人数的33.3%,其中包含12个单元,占全部单元量的13.0%。对教材偏好的教师有2名,占总人数的22.2%,其中包含5个单元,仅占全部单元量的5.4%。由此可以看出,教师对教材的语言表达最为关注,其次为语境,对教学的关注和对教材偏好的关注均较弱。
-
通过内容分析,发现了教师在评价教材时的关注点。但教师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述这些焦点的呢?能否通过教师的评价语料洞察他们对教材的态度呢?为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人际功能角度出发,借鉴Halliday提出的人际元功能情态系统理论[28]和Martin及White的评价系统理论[29],对语料进行深入分析。
-
情态的表达方式多样,通过对情态的分析,可以发现说话人言语中流露出的肯定或否定的态度。情态可进一步分为语态和意态,前者包含可能性阶和通常性阶,后者包括道义阶和倾向性阶,每一个阶还可根据其值分为低值、中值和高值[30]。本部分的情态分析仅针对全部教师评价语料的可能性阶的表达方式展开,不涉及对情态表达的词类区分。分析的目的是揭示教师对自己评价内容的确定性程度。阶值的确定立足本研究语料的语境,并参考了英语和汉语情态研究的相关文献[30-31],阶值越高表明说话人对自己的评价越确定,阶值越低则越不确定。从全部语料中,共识别出68个表达可能性阶的情态词汇,其实现方式及出现频率的统计结果,见表 2。持可能性态度的高阶值情态词汇在语料中仅出现了4次;持保留态度的中阶值情态词汇出现了35次;持不确定态度的低阶值情态词汇出现了29次。因此,从语料的情态表达来看,教师在评价教材时持有较高程度的不确定态度。
-
评价系统包含态度、介入和级差3个层次。本研究的对象是态度系统,其中包含情感、判断和鉴赏3个次系统和子系统中肯定和否定两个维度[29, 32]。本部分以探析教师对教材的态度为目的,仅从肯定和否定两个维度,对体现教师态度的评价词汇进行分类和量化,不涉及对其子系统的进一步区分。全部评价语料中共出现129个评价词汇,包含70个肯定词汇和59个否定词汇,其分布及出现频次的情况,见表 3。
从总体来看,好像没有一个对话语料是令教师完全满意的,因为每一个对话语料都同时得到了教师积极和消极的评价。这说明,教师在评价国内、外两个版本的教材语料时存在意见分歧。但总体来说,国内教材受到的负面评价少、得到的正面评价多,这说明国内教材更受教师的青睐。从否定评价词汇看,《走遍美国》中的两段对话收到了40个负面评价词汇,占全部否定评价词汇的67.8%。相比之下,国内主编的教材得到的负面评价词汇较少,共计19个,占全部否定评价词汇的32.2%。从肯定评价词汇看,国外主编的教材得到了28个肯定评价,占全部肯定评价词汇的40.0%,远少于国内教材的42个,占到了肯定评价词汇的60.0%。以国内外教材对话和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为两个类变量,以评价词汇的词频为加权变量,进行了2×2列联表Pearson卡方检验。结果如下:χ2(1,N=129)=9.93,p=.002,Cramer's V=.27。这表明教材的变化使教师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另外,教师们并没有认为像《走遍美国》这样的国外引进教材中的语言更真实。综观所有的评价词汇不难发现,教师评价的关注点很多集中在对教材语言的真实性方面。但是,不少教师认为,国外教材中的语言是“教材式的”“汉式英语”“不自然”,而国内教材却得到了“自然”“常用”“生活化”等肯定评价。虽然也有少部分教师认为,国内主编的教材“不真实”,但其出现的频率比对国外教材的评价明显更少。此外,对教材语言的正确性评价也占据了一定比重。很多教师认为国外教材的语言表达“不清楚”“不明白”“太难”等,而认为国内主编教材中的会话“非常清楚”“合适”“便于记忆”,而且为教学提供了“好模板”。
一. 内容分析
1. 语料分割
2. 评价焦点分布
二. 语言分析
1. 情态分析
2. 评价词汇分析
-
Johnson等人的研究认为,教学经验越丰富的教师,在教材评价中的表现也越专业[16]。本研究中的所有教师均有丰富的英语教学经验,不过从评价语料中的情态表达来看,他们仍然表现出对教材内容的不确定性。产生这种不确定性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教师的说话风格所致,他们习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持更为含蓄和谨慎的态度;二是教师并非英语本族语使用者,因此不同于Johnson等人的研究中的英语教师,本研究中的英语教师虽然教学经验丰富,但面对非母语的语言表达方式,他们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对其进行评价[16]。Johnson等人认为应该通过培训,提升教师的教材评估能力[16]。教师培训对于母语为英语的教师来说,可以较快地提升他们的教材评价能力。但是,对于母语为非英语的我国英语教师,提升教材评价能力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则是广泛接触更多的真实语料和各类教材语料。因为只有这样,教师们才会更加深入地了解目的语的真实使用情况与教材中语言表达之间的异同,从而对自己的教材内容作出更加确定的评价。随着语言学语料库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英语语料服务于课堂教学。这对教师来说,无疑是一个接触真实语言信息的高效途径。如果教师出现对某一教材语言不确定的情况,则可以在语料库中查找相应语境下的例证,然后进行比较分析。这既能为教师提供系统地接触和分析真实语料的机会,又能提升教师对教材语言的评价能力,进而促进外语教学的发展。
-
本研究中的所有教师都对教材对话中的语言使用情况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他们对语言的关注点与教材研究专家的关注点存在较大的不同。比如:尽管教师们对教材语言的真实性、正确性等方面的关注几乎占到整个评价语料的一半,但他们的评价大多仅涉及宏观层面。无论是像“不自然”“不适合”“非生活”等对教材语言的负面评价,还是认为教材“生活化”“自然”“口语化”等的正面评价,大多均未指出产生该评价的具体原因,或者什么具体特征使得语言表达产生如此的评价。然而,Gilmore针对教材对话展开的真实性研究,明确指出了影响语言表达真实性的口语特征是重复、停顿、犹豫、词汇密度低等[6]。教师的评价和专业教材研究者之间存在区别的原因可能是:(1)教师在评价时,基本上是凭借自身语感作出直觉判断,尚未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2)专业的教材评价需要有语言学和教育学等专业学科的背景知识,这一问题又和上文提到的教师培训及广泛接触真实的语料有很大联系。
-
教师评价语料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他们将教材和教学相结合的评价很少。为什么大多教师都未从自己的英语课堂教学或者学生角度对教材进行评价呢?针对这一问题Johnson等人认为:英语教师越有教学经验,在教材评价时就越会关注语言使用的合理性;只有缺乏教学经验的教师,才会过分关注教材和教学的关系,以便顺利展开课堂教学[16]。其实,不仅是本研究中的教师在教材评价时忽略了教学,大多数教材研究专家提出的教材评估体系,往往也缺乏对教师和学生以及课堂教学实践的关注。Littlejohn提出的教材评估模式认为,教材评价标准应置于特定的教学环境中,才能做到因地制宜,兼顾教师和学生的实际需求[33]。但问题是,如何让专业的教材评价和实际的英语教学相结合,这才是研究者面临的一个不小的挑战。因而,更多关于教师和学生对教材的评价研究,会对此提供启示。
-
本研究中只有2名教师明确表达了对教材对话的偏好。而且,如果仅从词汇的评价结果来看,教师们对4段对话中哪一个表达更好,并未达成一致的看法。然而,评价词汇的肯定和否定的量化分布显示,教师们更青睐国内主编的英语教材。这或许是因为,尽管从国外引进的教材,其语言更加接近本族语使用者,但是国内主编教材中的语言表达或情景设计,对英语教师来说更为熟悉,更符合现阶段我国的英语教学环境和学生需求。那么,这样会不会导致我国英语学习者所习得的英语和目的语使用者的语言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影响我们的跨语言交际呢?Widdowson认为教材中的语言都是非真实的,脱离了语境的真实语言是无法直接进入教材的,所以课堂教材不需要完全接近母语的真实表达,而应该更多从适合性角度出发,考虑教材的使用环境[34]。正如上文Littlejohn所提出的,任何教材的评价模式都应该按照特定的教学环境进行“修改”[33]。国际化的英语教材引进后,如果不根据教学大纲和教学目标作出调整,那么无法适应本土的教学环境。郁凯元等学者对机械制造和自动化专业本科生使用美国原版教材的情况进行了研究[21];张玉梅学者对国外幼儿英语教材的本土化进行了研究[35]。二者均认为使用国外英语教材时要联系实际教学情况。因此,教材评估、教材编写和教材研究是一项需要专家、一线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的任务。
一. 评价的不确定性
二. 语言关注
三. 教学关注
四. 教材偏好
-
本文从探索英语教师的教材评价及其意义出发,选择了国内外英语教材中的一小部分对话文本,采集了英语教师对其的评价语料,将教师与教材研究相结合。这是国际教材研究专家McGrath提到的一种研究途径,也是现今外语教材研究所缺乏的一项探索[36]。本文的主要启示在于:(1)研究使用的认知语篇分析法,不仅可以用于探索教师的教材评价模式,也可以用于研究学生和教材编写者对教材的态度;(2)研究所发现的教材评价焦点和问题,可以对英语教材的编写和课堂教学提供启示。本文仅是针对英语教师对教材评价的一个小范围进行研究,未来研究还应针对更多的教师和学生,以便发现他们在评价教材时的差异及特点。此外,还需要从使用者角度出发,对教材承担的培养阅读、写作、口语等英语技能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从而形成对教材适用性的全面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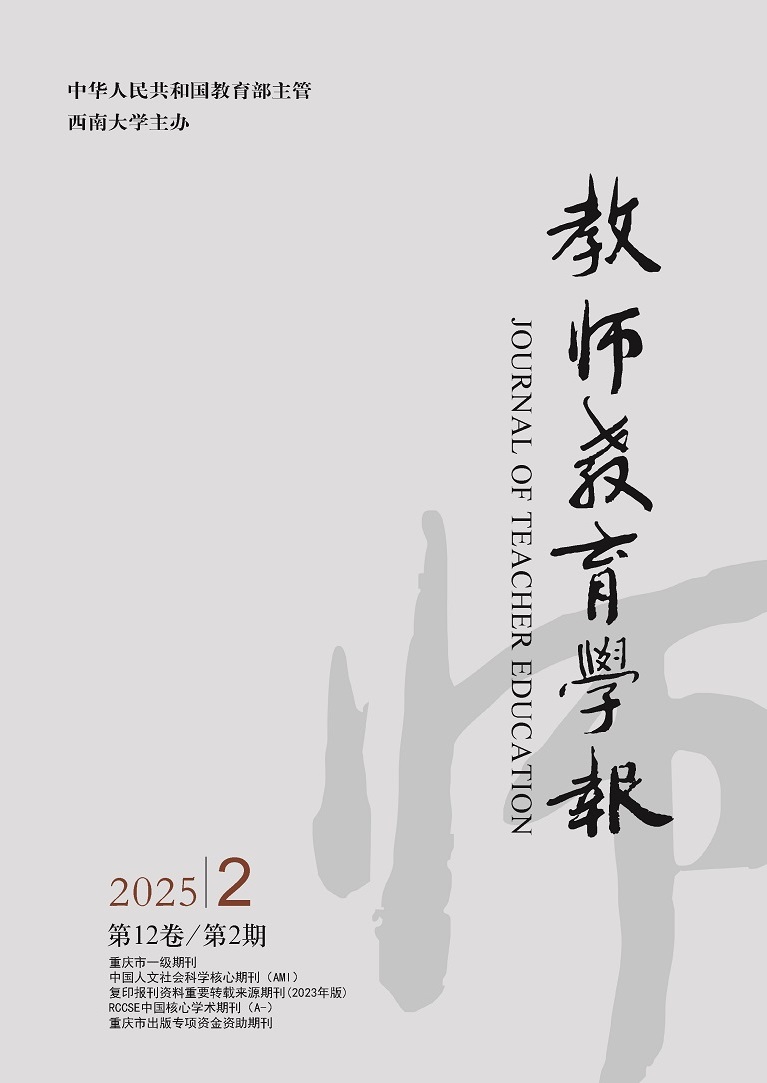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