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电影产业化的当下,武侠电影的发展不再只是简单的娱乐行为,更是在深刻的多种意识形态力量(比如消费意识形态、后冷战国家意识形态、中产价值观意识形态、美学修辞术等)交互作用的复杂序列中,构成了整个产业发展的关键一环。对于武侠电影研究来讲,上述意识形态的影响、全球化的深入、中国崛起论的语境、好莱坞电影模式的侵袭等等,使得武侠电影研究愈来愈多地溢出了之前较为封闭和单一的政治语境/市场环境,甚至远远溢出了局限于审美价值、江湖文化、侠义内涵、传奇叙事、暴力美学等传统范畴的阐释框架,从而拥有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范围。尹鸿[1]、傅谨[2]、张颐武[3]等分别从武侠电影与产业品牌、与传统文化互动、与意识形态耦合的单个切入点进入展开了精彩的解读;陈林侠[4-5]、史可扬[6]、王一川[7]、张振华[8]、倪万和吴园军[9]、黄式宪[10]、贺桂梅[11]169-208等,则从大片角度对新世纪武侠电影的一些新变化、全球化的影响以及2000年以来武侠电影在创作实践上的得与失进行了研究。学界的研究虽没有直接涉及本文的话题,但都在研究方法与视野上带给本文以启示。
荣格曾说,一个民族“如果失掉了神话,不论在哪里,即使在文明社会中,也总是一场道德灾难”[12]。“武侠”的存在正如钱理群所言,既是“人类古老的英雄梦在工业社会的延续,又是羁縻于世俗社会中的现代人试图超越具体时空限制的替代性投射,而虚拟的超现实的江湖世界,则是人类永恒的乌托邦幻想的本能在现代文明的体现”[13]。在当下电影市场各种利益权力争锋的背后,武侠影片十几年的转型实践与传统武侠题材中的历史、神话乌托邦等遗产的分离,以及因此而导致的武侠历史文化积淀的各种正能量的衰退,正在日益凸显。主导政治、产业利益、大资本权力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对武侠领域资源和空间的各种抢占,以及这种抢占对作为历史文化积淀的“江湖”“侠义”改造和意义结构挪移,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武侠电影自身的发展。
HTML
-
从中国武侠文化的发展过程来看,武侠文化得益于“历史”以及“历史意识”这一指代民族、国家、集体等公共记忆对武侠叙事的深度参与。由于武侠文化特定的快意恩仇、行侠仗义的江湖写照,自觉承担起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道义责任和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国家/人民主流意识形态制高点”[14],以及作为正义与理想之生存秩序象征的武侠,对“庙堂”压迫剥削机制的固有反叛等,使得武侠文类的叙事和行侠逻辑往往相悖于“庙堂/现实”的价值立场与处事原则,因其虚拟空间的想象而与当下现实拉开距离,而历史时空的悠远和跨度弹性也恰恰能为武侠的腾挪跌宕提供最佳的空间和想象。武侠与历史的碰撞嫁接以及相契相合就显示出多重意义:其一,历史感不仅能够把侠客的个人恩怨与私人情仇接续到民族国家大义的高度,赋予武侠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精神品质,而且历史元素的介入,为武侠表现人性的深度、广度以及武侠与大众文化背景的多层次链接提供了可能性的空间。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能够开创一个武侠新时代,使得武侠登堂入室,站在与精英文学相对应的地位上,恰恰就是因为金庸小说里浓重的历史情结。这种情结不仅表现为对真实历史境遇的调度式使用,更体现在将侠客的人格魅力、行侠动力、叙事推进甚至对“华/夷”“满/汉”“种族/国家”等身份认同意识接续进具体的历史事件中,从而让小说呈现出主题上的多重繁复以及武侠文化的“寄托遥深”之处,“通过这样的处理,金庸正好把皇权政治、国家兴旺纳入武侠小说的视野里。他的‘江湖’不是一个单纯的正邪斗法的所在,而是存在于中国特定历史时刻的一个虚拟社会”[15]。其二,历史对武侠的型塑,也能从根底上将武侠文化接纳进历史底蕴中,调和两者在轻盈与沉重、虚拟与真实、奇幻想象与深厚宏大之间的间距,有效拓展、开掘武侠命题的表现方式和表达手法,也能使武侠精神的内核传承与民族想象、群体记忆的演变同步和谐。比如在《天龙八部》中,小说一方面讲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大理、宋、辽、西夏、吐蕃等“国”之间的“多国演义”,一方面又在这种民族冲突和群雄竞争的历史风云中,融入萧峰揭秘身世的江湖悬疑故事,虚竹勘破珍珑棋局的传奇桥段,以及段誉在众多女性面前的儿女情长,不仅有效调节了历史元素的沉重与武侠传奇的轻盈之间的矛盾,同时通过塑造超越民族纷争的“以身饲虎”般化解“种族、民族、国家”冲突的大英雄——萧峰的形象,“以一种有力的象征性形式,消解了中国性中的古今、中西、官民、正邪等二元对立模式以及相应的中国中心幻觉和中优外劣心态,而呼唤新的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中华性的生成”[16]。这就是谈到武侠文化总是离不开中国历史文化积淀的原因,也是西方总是把武侠文化当作中国文化特色与代表的原因。
然而,真实历史或历史真实细节并非武侠小说/影视题材的必要元素,“历史”以及“历史”元素的进入,更是一种涉及民族精神的历史无意识,“纵观古今中外被奉为经典的小说,绝大多数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取向,对于人的生存状态及人的命运的思考。人物关于现实的认识带有历史积淀的痕迹,人的一切社会意识都具有历史性。历史观是人的世界观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读者喜欢看小说,而且尤其喜欢看武侠小说,在相当程度上由此驱动”[17]。“武/侠”作为民族情感和集体无意识的表征,正是依靠民族历史的传承和记忆实现着全球华人对中华民族及中国国家概念的认同。尤其是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无论是《书剑恩仇录》《碧血剑》《鹿鼎记》对历史上满汉矛盾的多元呈现,还是《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对多民族沧桑战事的复杂“演义”,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多元文化交杂共生时代里,金庸正是通过对“中华民族内部的扬夏抑夷传统的反省,形象性地揭示了中国在现代积弱和衰败的心理根源或集体无意识,为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格局中的复兴方式提供了一种象征性借鉴”,激起了无数华人对于“中华性的文化认同和想象”[16]。
自唐宋豪侠传奇出现以来,“侠客”二字与历史英雄、绿林好汉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武侠”与深度历史的分道扬镳,乃是现代性发生以来娱乐性得以正名的一种逻辑演变,是在武侠小说“从启蒙现代性走向审美现代性”过程中,“在社会现代性的文化路向遭到挫败之后,必然会出现审美现代性的必要形式”,从而出现“审美现代性对社会现代性的反拨”[18]。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侠客”和“功夫”正是中华历代文人与百姓可以共享的典型文化想象,路见不平的侠义精神和虚拟驰骋的江湖情结,不仅延续着《史记·游侠列传》盛赞的高贵品德,任性、逍遥的独立人格也往往承载着民族个体独特的“感情指向”和“价值期许”。正如邵氏开启的武侠世纪,“此时正值内陆‘文革十年’的浩劫,台湾也在白色恐怖的‘戒严’时期,邵氏电影的‘国语电影’主流势力至少填补或提供了全球华人世界一个‘文化中国’的憧憬”[19]。事实上,正是这种憧憬,比如对“飞檐走壁”的热衷,对超越身体极限的武术追求,对影片中不畏强权、自强自立的中国功夫的自信,才有可能跨越当时政治观念和地域时间的差异,成为“一种辩证的修辞,(一种)对本雅明的借鉴:它试图通过一个同时的水平面重新连接过去和当下”[20]253。当然,也正是借助这种修辞,武侠影片中展开的“江湖”以及发生在“江湖”内的恩怨、反抗与民族情怀,才具有了“重塑一种流行的想象和乌托邦的集体欲望”[20]302。
-
在全球化进程中,历史文化的同质化潜移默化地消减了历史的深度,也消减了民族/国家概念以及集体的共同记忆和想象。如果说在金庸武侠小说中,宋、元、明、清的一些史实是在一些恰当时机被组接进武侠叙事层面,那么历史事件本身的扑朔迷离与武侠小说的神话传奇,相互转换与交叉缠绕所产生的侠史情节和似真似幻的传奇故事,就使得金庸小说形成了历史与武侠和谐共生的良性循环关系。有学者认为金庸小说的精深之处是在“‘历史’与‘小说’交错相关的寓言结构里,在‘真实’与‘虚构’的同走江湖的武林人物谱系中,搭建了一个具体而又抽象的小说世界,并借助男女侠客对于荒诞状况的清醒意识和实际行动,对现实达成了想象的批判”[21]。
在新世纪武侠电影中,创造了一个个票房神话的古装武侠“大片”无一例外地经历着“越骂越看”“越看越骂”的现实语境。其取材种类繁多,包括“刺客”暗杀(《英雄》《十面埋伏》《血滴子》《绣春刀》)、神仙鬼怪(《画皮》《画壁》)、江湖侠客(《七剑下天山》《剑雨》《武侠》《龙门飞甲》)、历史传说(《赤壁》《赵氏孤儿》《夜宴》及《神探狄仁杰》《四大名捕》系列)、魔幻大剧(《蜀山传》《无极》)、人物传奇(《精武门》及《叶问》《黄飞鸿》系列)等等,文本主题从儿女情长到宗族伦理、从门派恩怨到家仇国恨、从历史传说到魔幻传奇等等,几乎横跨了整个中华历史文明,有些影片的制作水准并不逊色于好莱坞影片。吊诡的是,作为主要以“古代中国”为背景(部分功夫片以近现代中国为背景)、以“历史实事”为基点(部分是虚构的故事)、以“神话传说”为框架、以凝结了浓重的传统中国伦理价值观的“故事”为蓝本的经典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电影类型,再次出现在银幕上时,那些曾打动过无数华人的故事与人物、曾存在于无数华人心目中的侠客/江湖意象,却并未从心理上激发观众的深度共鸣,而是被讥讽为既缺“武”又少“侠”,不仅骨质疏松而且精神贫血。这不仅是在当下工业、美学意义上对中国现阶段古装武侠片的疑惑,而且还隐含着一个关于“为何中国人看不懂自己的故事”的文化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逻辑与价值系统正在遭受一定程度的改写与颠覆。例如,《英雄》中原本“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和弱小者反抗强权统治的文化,被改写成了为“天下”而放弃刺秦的想象;《赵氏孤儿》曾经是一曲歌颂壮士忍辱负重慨当以慷的悲歌,却被替换为一场关于“人性”的权衡;《赤壁》中家喻户晓、斗智斗勇的战争故事,被改写为两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中国版“特洛伊”;《王的盛宴》不再是一场英雄豪杰揭竿而起践行理想救百姓于水火的较量,而是被替换为关于“欲望”的厮杀;《龙门飞甲》将仁人志士匡扶正义惩奸除恶的快意恩仇,替换为一场“追名逐利”的沙漠肉搏;《绣春刀》在“‘侠’与‘江湖’这两个最传统的武侠片要义上却做出了勇敢的尝试:根本不存在‘江湖’,更不存在‘侠’”[22];“《道士下山》则更进一步在宏大叙事传统上消解了崇高、悲壮、英雄人物、侠、江湖儿女的情义,从而走向情感关系的虚无化”[23]。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度发掘和知性表达,不仅在武侠影视作品中遭遇淡化,甚至也正在淡出历史影视剧的视野。真正有典型意义的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和底蕴,不仅对武侠电影的主创者来说显得陌生,对当下观影群体来讲更是被斥为保守、落后而不屑一顾。
从理论上讲,新世纪基于新历史主义等后现代理论的深度介入,影像书写方式出现了新的探索,某种程度上会增加影像叙事中对“历史”及“历史意识”呈现的可能性和多样性,尤其是如果创作者能在对武侠传奇的虚构中点出丰厚的历史人文意蕴,或者传达出某种指向未来的探索性意旨,创作者的任何改写或重构或许都能起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功能。但是,新世纪武侠电影对传统伦理价值和历史观的改写,带来的却是一个尖锐的悲剧事实,改写中的被替代物诸如弱者的反抗、正邪冲突中突显的悲壮、匡扶正义的精神内核等价值取向,并没有在影像呈现中得到认同进而流转传承,其经典的历史文化意义仍旧被封闭在旧有的文本(小说、话本、戏曲)之中。民族历史的神话、传奇乃至传统的历史观不再成为武侠叙事所仰赖借重的传统资源,历史成了逃逸和被悬置的对象,或被处理成具有象征意义的背景,或被颠覆为后现代影像碎片拼贴的景观。比如《七剑下天山》《武侠》《剑雨》中历史背景的模糊逃逸,又如《英雄》《天地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四大名捕》《天降雄师》《绣春刀》等虽有明确历史背景却明显呈现出来的“去江湖化”。这就不仅与传统武侠世界缺乏意义关联,而且无意识地折射出政治资本与市场资本合谋编织的消费符号,以及对观影群体的催眠与抚慰。即使是如《霍元甲》《叶问》等以历史人物为主角的电影,虽然演绎了人物命运与家国恩怨,但历史背景多少由于应和消费意识形态而成为影片主题表达的借用。这些影片中的朝代背景,并没有因为武侠文化历史底蕴的挖掘而提升武侠价值,而是被当作观赏性的历史景观或视觉元素,这里的历史与其说是为电影叙事提供的拟真氛围和叙事空间,还不如说是演绎现代人性、情欲、恩怨、争斗等等的抽象背景,也成为电影暴露、展演中国文化景观诸如服装、宫廷、市井、艺术、武功的噱头。也就是说,“在处理眼前社会的诸般景物时,电影不是透过其自身的‘艺术语言’组成‘摹拟体’的世界,而是利用‘拼凑法’重现一些昔日时光的陈腔滥调”[24]462。遗憾的是,“这种崭新美感模式的产生,却正是历史特性在我们这个时代逐渐消褪的最大症状。我们仿佛不能再正面地体察到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历史关系,不能再具体地经验历史(特性)了”[24]462。当下武侠影片这种对“历史”碎片进行拼合乃至“戏说”的创作本质,应和了大众文化的娱乐至上的游戏精神,作为一种影像“符号”建构的“拟像”环境,武侠影片就被降格为迎合受众心理的消费文化存在。
历史感或历史文化这一表征民族、国家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积淀和传承方式,被新世纪武侠电影主创者集体略过或无意改写(尽管并非有意),已成为审视当下武侠电影软骨症的一个症候。应该说,历史感在武侠影片中逐渐衰退的原因之复杂,非专文不能尽述,除却后现代、读图时代及大众传媒对历史深度的削平、拒斥等人所共知的原因外,本文主要聚焦于全球化、资本构成、电影自身的叙述与奇观等不同方面。
其一是“全球化”对武侠电影历史深度的抹平。
“全球化”作为20世纪末出现的一个新的充满张力和对抗的意识形态空间,它所袒露出来的复杂性、关联性和由此折射打开的众多问题场域,已经成为当下文化研究的一个全新面向。“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文化全球化,它使得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渗透到其他国家,在文化上出现趋同现象,它模糊了原有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征。”[25]同时,美国好莱坞电影成熟的运作模式,“更代表着一种导致全球文化单向性、趋同性危机的文化模式”[26]。让·米歇尔·傅冬指出:“好莱坞就是通过其成熟的复杂的市场技巧让全世界的大脑同步,它是一种商业化和专断化,最终将导致多样化的消失。”[27]武侠尽管以民族性、历史感为想象来构建自己的江湖文化,但跨国资本的文化普适性必然会对其做出调整。因此,对武侠电影来说,全球化的深入、跨国资本的注入、普世价值观的强行渗透,不仅在上游改变着武侠电影的资本构成,为电影创作提供新的创作方向和审美原则,同时也将会取消武侠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类型性和民族性特征,甚至为了顺利进军国际市场,消减西方视野对中国历史的隔膜感,武侠文化中积淀最深的历史感也势必会随之消减乃至改写。有人认为:“国际影视传播必须立足于人类生活中的共同情感。任何具有民族个性的影视作品,必须首先立足于全人类共同的情感,才能找到转换代码。否则,就难以进行跨文化传播。”[28]可以说,新世纪武侠电影历史感的缺失,以及在制作观念、创作态势、文化传播、精神价值上发生的诸多变化及由此敞开的矛盾与困惑,都是对此的回应。
其二是作为“一个策略”出现的新世纪武侠电影的先天贫血导致了其历史感的中空。
世纪之交,中国电影产业濒临危机。在经济、政治与文化高度全球化的现实语境中,新世纪武侠电影类型突然勃兴,并非电影在自身发展脉络中的合理取向,而是在《卧虎藏龙》的示范效应下,在亟盼“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热诚呼唤中,甚至在“奥斯卡”情结的诱导之下,恰逢其时地作为一个理想的载体,融合资本权力、知识精英、意识形态和观影大众多方力量的话语诉求,以民族化对抗全球化的高调姿态正式出场的。之后,武侠电影隆重盛放乃至在2007年之前一枝独大,迅速改变了中国电影的历史走向,进而推动了中国电影产业格局的重组。
有意思的是,武侠电影此时的辉煌,承担的并不是如何复兴武侠电影、寻求武侠文类在新世纪新表达的责任,而是被相当程度地当作拯救电影产业于水火之中进而实现中国电影全球化的一个借用策略。在这种策略之下,几部武侠电影大片无一例外遭遇了“边骂边看”式的奇特景观。当然,这也是新世纪武侠电影在经历传统/现代、历史/现实、东方/西方、艺术/商业转型期的中国电影生态的特殊症候。更吊诡的是,武侠命题内在的“武/侠”元素、“江湖/庙堂”的对抗精神、以弱抗暴/快意恩仇/自由逍遥等精神内核,却显然相悖于新世纪急切渴求官民“和谐/强盛/统一”的整体社会情绪。种种相悖的价值取向,与上述近乎“错爱”的策略借用,注定了武侠电影在叙事上的犹疑、价值取向上的矛盾以及对历史深度的无暇顾及。种种撕裂感似乎让人不难理解,新世纪武侠电影为何连一个完整流畅的叙事也无法给出,为何它们只能表现为夸张的视听奇观、极端唯美的古典元素,以此去创造看似充满东方奇观而实则价值混乱、历史感缺失、主体中空的全球同质化想象空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很多评论和媒体非常容易把这种价值贫瘠、历史缺失当作中国电影“襁褓”时期的必经阶段而加以原谅,或者直接略过思想历史内容的层面,欣喜于中国电影在票房、产量、院线等方面持续攀高的数字幻影。倘若此时再次返观新世纪武侠电影的出场,或许忧虑就会多于欣喜,从体制改革向商业性的大开洞门到导演心态、媒体评论向商业性的全方位位移,从对好莱坞商业运作的多面模仿到《卧虎藏龙》的成功实践,从《英雄》的虚张声势到《无极》的口水战,武侠电影作为新世纪中国电影产业化的排头兵,一种重振文化产业雄风的策略选择,无形中显示了武侠电影在新世纪的现实走向和历史迷失。
其三是资本构成的变动对武侠电影历史轻质化的影响。
虽然经济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因,但在对当下电影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的考察上,却很少有人认真分析资本构成在其中更隐蔽也更重要的影响。“电影,远非仅仅只要满足银幕前的观众,它更是涉及其他很多种人需要的工业。制片厂、银行、政府、投资老板、制片经理、技术发明家、导演……一种类似家族族谱似的关系,影响着电影的生产。每一格胶片上的所有因素——人物、色彩、声音、构图、背景、道具,经过仔细的观察,都可以看到隐藏在其后的端倪,这些因素都是来自各方面条件妥协的结果。”[29]新世纪中国电影美学(不仅仅是武侠电影)的一系列变化,某种程度上正是电影工业在资本变动中主体位置和功能变动的隐秘折射。“美国电影产业遵循了一条以文化产业运作来达到经济获利(‘量’的积累)的目的,继而在国际范围内完成意识形态的传播(‘质’的飞跃),那么,中国文化产业则呈现出在政治资本大力推动下经济资本获得前所未有的强势地位,从而引发经济权力话语越界、位移,并促使电影这一文化场域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态势。”[5]新世纪的中国电影资本结构,大致包括三种主要投资模式:政府资本、民间资本和境外大资本。各种资本主体的不同投资理念在影片制作中的冲撞、妥协,最终导致影片在美学上呈现出纷繁杂糅的裂隙和复杂性。2000年之前,武侠电影的投资主体多来自官方资本;2000年之后,民营资本迅速崛起以及境外资本和热钱的大量涌入,急切催促着武侠电影向大众消费乃至西方普世价值倾斜,使其对于影片的商业性、利益性的追求和官方对意识形态正确的追求方面,产生了某种复杂耦合的扭结,而这种扭结无疑也会影响武侠电影对历史深度的追求。
其四是在电影美学层面,奇观对叙事的压榨也是造成历史感中空的原因。
新世纪武侠电影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奇观化”的突然崛起。周宪将电影划分为“叙事电影”和“奇观电影”,“叙事电影这个概念本身昭示了叙事性在电影中的核心地位,它是依照叙事的要求来结构的。因此,电影如何展示情节、塑造人物、编写对白等,成为叙事电影的基本要求”,而“奇观电影”则变成了以视觉、图像生产为主导的电影创作,“即是说,奇观电影的首要任务是通过画面的组接来传递具有视觉吸引力和快感的影像”[30]。从默片时代到有声电影再到图像霸权,电影艺术逻辑一直遵循着媒体演化定律——媒体霸权的形成与反霸权的补充形式,因此,奇观电影的兴起只是演化定律的一次调整,“没有某种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最好的艺术,没有某种生产、演奏或经验感受是艺术唯一正确的方法”[31]412。电影艺术在任何奇观(技巧)和叙事(意义)方面的开拓,都要最终符合电影自身发展的“两极运动律”,用门罗的话说,就是“指每种文化形态,都是由两极对立动态地构成的两极对立或交替出现,或同时并存,并不断地发生冲撞和抗击,双方都有向对立面反方向运动的趋势,而一极又为另一极所牵制,因而在对立的两极中便形成了一种张力平衡场,其效应就转化为文化发展变迁的内部动力”[31]413。但是,当下武侠电影制作者对奇观化的过度热衷,破坏了电影艺术自身的平衡,使得影片在摄影机机位的选择、焦距的使用、后期的剪辑、画面的设计、视角焦点的选择、帧数的多少快慢、明星特写的部位等方面,因为服务于展现奇观的目的而造成对叙事的延宕、破坏,乃至牺牲语言叙事的完整性和历史意义的追问,甚至造成“形式”大于“内容”以及“奇观支配叙事”等严重问题,比如热衷于用特技奇观渲染功夫之“快/密”、兵器之“利/炫”,用高速摄影实现对“快”的速度追求与观影者对“快”的刺激需要,和现时代一切都求“快”的无意识不谋而合,事事都“快”的功利性想象和影片对“速度”的狂热迷恋,必然会与历史探究所要求的“慢/深”之间形成矛盾,进而阻塞影片对历史深度的进入。
-
对历史价值深度追求的放逐和对侠义精神深层叩问的放弃,使得武侠影片只能在征调自然景观或历史景观的装饰性上努力。如果说1980年以来的武侠电影借用历史来勾连虚构的江湖和当下的现实处境,而新世纪以来却是用景观“自然”来接通过去与现在,这个变化曾被詹姆逊一眼看穿:“大陆电影工作者对风土景物的一再肯定和台湾及香港的电影工作者对空间的处理和经验大为不同。”[32]这种变化的逻辑在于:利用景观拥有的仿像性,实现浅表化“自然”对空间性“历史”的替代,这种便宜便捷、唾手可得的平面直观呈现,不仅符合后现代语境读图时代对历史深度意义的消解趋势,也彰显着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资本的强势形成对获取精神意义的可能性愿望的压抑和阻塞。因此,在借助历史场域构架武侠电影的江湖空间时,对历史的开发普遍采取了一种以“自然”或“景观”来替代历史文化的取巧做法。比如《英雄》《十面埋伏》《大兵小将》《神话》《七剑》《龙门飞甲》《新少林寺》《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四大名捕》等,普遍切碎了自然完整的历史空间,从巍峨雄壮的秦朝宫殿到富丽堂皇的唐代器具,从飘渺毓秀的武当辗转到漫卷西风的大漠,从小桥流水的清代江南到美不胜收的唐代竹海等等,武侠电影虽然以形态各异的景观呈现了各个朝代最具美感的自然风景,但过于抢眼的视觉奇观却凝固化、符号化了作为朝代的历史,拼贴组合的快速翻转也取消了对本土地域和朝代历史的纵深进入。
这些看似纯粹客观的“自然”在渐趋同质化的全球化语境中,正在代替历史深度,成为漂浮于本土民族、家国意识之上的形成自我认同与辨识自我身份的简单符号。由此带来的是用视觉体验取代历史深度和民族个性的心理倾向,这可能会造成与历史文化进行对话和沟通的障碍。贺桂梅借鉴柄古行人关于“风景”是一种认知性装置的理论,认为:“只有当银幕上的‘中国’影响能够与个体(也是观影主体所占的位置)的内在欲望构成‘能指’与‘所指’的深度关系时,中国风景才可以成为‘被看见’的对象。”[11]187在新世纪众多武侠大片中,奇观展示成了控制影片叙事和抒情的外在力量,当自然风景的过度堆积不能唤起观影者的历史感和集体经验、无法建构起影片叙事的“内在主体”时,“外面”的风景与内在主体/欲望之间的对应法则就被破坏了。马克·弗里曼说:“传统文化与历史叙述并非是从外部强加给大众的生活,而是直接地编织到他们的某种回忆的情绪与经验结构之中。种种关乎文化记述与个人情感历史的‘储备材料’,是以‘深层回忆’的方式构成了人们内在体验的沉积。”[33]而当深层回忆不能与影像试图传达的文化“储备材料”构成内在式共鸣时,历史景观就会被编码的“所指”符号也就是与大众依赖的“前理解”对其“能指”解码形成断裂,大众观看影片的过程就仅仅成为一个对历史影像表层“符号”的消费过程,这就是观看《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无极》《夜宴》《七剑》《锦衣卫》《道士下山》等大片时,所普遍感觉到的叙事与景观的分离。
按照詹姆逊对自然景观与全球化美学关系的深度探究,还必须承认,我们对一个社会的偏爱和歧见,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我们通过景观展现的地域化、碎片式的直观信息积聚或浮光掠影式的感性判断,而不是基于历史真实意义的深度探究。因此,对于仅仅通过影片来认识中国的海外观众来讲,假若我们对历史文化的对外传播只是依赖于这样的景观堆砌,那么异域观众对中国历史景观的误解和成见或许就是必然的。同时,历史的景观化呈现也为“资本”与“自然”的结合提供了更方便的可能。新世纪武侠电影中普遍出现对自然景观极端化和唯美化的偏爱,根源于“自然”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的积极参与,也根源于这种极端“自然”与消费审美的共生,“资本已经完全侵入了审美和艺术的领域,审美已经构成资本的一部分,成为资本本身的表现”[34]。当然,需要警惕的是,这种自然的极端化和唯美化,并非是自然景观的真实展现,而是用影像过度包装过的“自然”。
在当代仿像文化背景下,武侠电影是以大众文化商品化的消费逻辑,表达着对历史的理解和利用,使得“历史”由往日的严肃、神秘、崇高逐步趋向世俗和碎片,以满足大众眼球消费的欲望。而电影以其与生俱来的商品特性和视觉影像,更是成为后现代仿像文化渗透的载体,以虚构的江湖和历史为题材,结合电脑特技视觉渲染的武侠大片尤为典型。特别是当武侠影片对本土历史文化资源的征调依然停留在“东方风情”渲染和“文化符码”堆积之上时,反倒会更深地撕裂由武侠精神、江湖传奇、影戏传统为主要表征的本土历史性。很多武侠大片呈现的关于历史、地域、文化的形象,仅仅是其自身的仿像符号,并不能让我们将其对接进这些景观的历史深处。比如《英雄》中关于秦王宫殿的色彩和气氛渲染、红色迷离中的书馆、棋馆厮杀、黄树林决斗、九寨沟湖面对打等恢宏唯美的场景布置,《满城尽带黄金甲》《十面埋伏》中对红色、黄色、鼓、竹、菊花等中国元素的过度使用,《血滴子》《绣春刀》中对明代特务服饰、器械的夸张展示,《无极》中对中国传统神话的高蹈空灵之渲染等,因其脱离了与影片展示的历史背景、传统叙事伦理的接续,给予观影者的感觉是先于其指涉物存在的,即鲍德里亚所言的“仿像的先在性”。尽管吴宇森在拍《赤壁》时强调:“我很注重视觉艺术,很喜欢以景寓意,以物传神,……能够把我国美丽的景色、古迹,哪怕是一草一木,峡谷小径都写入场景之中,务求表达出诗画一般的中国。”[35]但当中国风景与历史伦理被隐蔽地替换成为好莱坞意义上的“两个男人的博弈”即周瑜、曹操为了争夺小乔时,“图像的意义本身既可以作为某种基本真实的反映,也可能在呈现时发生掩盖和篡改某种基本真实的现象。甚至最为极端之时,图像还可能掩盖某种基本真实的出场,与任何真实都没有联系而纯粹是自身的一种拟像”[36]。
当武侠影片展示的古典中国与沉淀在集体无意识中的真实历史场景无法构成内在的对应关系时,影片的景观展演就有可能脱离它的表达功能和意义显现,这就可能意味着景观会呈现一种用于“其他目的”的拟像欺骗,也即景观的催眠术,指向的是消费主义利益观或权力意识形态表达。“电影以风格重组来建立一系列新的文化论述,其最终目的在利用它把我们眼前的现实重重包围,利用它把刚逝去的往昔也重重包围起来;利用它,把当前文化所难以触及的‘历史’时光、把一个早已远离我们、早已超离社会具体记忆的‘历史’重新孤立、团团包围起来。”[24]458这种被呈现出来的场景风格,通过对中国风景的包装,不仅左右着观影者对真实风景的理解和意义阐释,也通过对历史的改装而实现了对历史的消费,这成为电影精神虚空的一个代表性症候。
对武侠题材来讲,要求其对历史进行深度探究并非武侠电影的本意,对历史的适当消费是其商业化与娱乐化的本性,新世纪武侠电影也正是借助于对历史的消费推行其全球营销的商业战略。但是,武侠作为特定类型,武/侠的存在依然离不开历史成为景观和动作展演的深层铺垫。如果说1990年之前武侠电影的缺点是过于坐实了历史,历史空间的狭小限制了武侠文化想象力和创新度的延伸,使武侠电影过于胶柱鼓瑟而显得沉重和呆板,那么新世纪的武侠电影却矫枉过正了,让历史过度视觉化,在眼球经济效应之后不仅带来了西方审美的疲劳,对武侠缺乏深度内涵的厌倦,也削弱了本土武侠电影中承载民族与集体意识的能力,部分丧失了大众对武侠电影的期待。
-
值得警惕的是,历史意识逃逸之后,武侠电影对浓烈和肆意的景观性演出的迷恋,从本质上来看更容易沦落为一种被消费资本和权力意识形态制造和控制的幻象,或者说是一种看似自由选择,却是大众“对于具有高等阶级形式、风尚和符号的某种虚幻文化参与”[37]的替代性假象,这种幻象正如德波所认为的,因其表象的去历史化、去政治化和不干预原则,实际上实现了对观影者最深刻的意识形态灌输。比如在《叶问》1、2中,当叶问用暴雨般的重拳肆意击打外国武士时,擂台下面、影厅观影者的雷动掌声和秘而不宣的民族自豪感渲染出的爱国主义激情,以及煽动起来的民族情绪,既是一种对庸常繁冗的日常生活与犬儒现实的宣泄,也是对中国民众无比熟悉的旧日集体主义、民族主义信仰的情感重温。再如《绣春刀》中作为“基层公务员”的三个小人物在政治腐败与倾轧之下进行艰难的生存选择时,影片对他们反抗秩序之侠性的消解,以及推动三人对体制内生存规则和现实交易进行隐蔽认同时,激起观影群体的不是对不公正体制和腐败秩序的反抗勇气,而是掩饰在兄弟温情下的对极权政治的犬儒式认同。如果说《绣春刀》表达的是官场乃至职场小人物对政治权力的犬儒姿态和主创人员对历史反思的主动退行,那么《道士下山》本是想通过一个小道士下山/上山的轮回,试图阐释道家境遇下中国“何安下”的生存哲学,通过对“执道诱尘怨,迷叹玄义禅”的认识领悟从而完成对修行的阐释,但影片阐释佛道境界的野心和文本推演逻辑的混乱,却导致了影片价值观的错位,一个本是演绎“不择手段非豪杰,不改初衷真英雄”的故事,被改写成一出对浮世繁华的江湖背后冰冷的道德现实服膺的现实主义残酷剧。影片中的自我戏谑、对批判对象的宽容等,无形中助长着影片所呈现的现世主义犬儒倾向。
在这个意义上,或许需要承认徐岱虽然偏激但却敏锐的发现:“民族主义狂热和集团性认同都是自恋人格的扩大化,这些现象的非理性和偏狭性形成了对人性的封闭与扼杀,自然也就毫无真正的美感可言。”[38]事实上,无论是爱国的激情掩饰、兄弟友情的遮蔽还是爱情脉脉的外衣,一直“在影像中充当着(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政党的)旧意识形态降格的、廉价的情感和价值,来承担情绪缓释器的作用,通过一种替代性的满足,为真正的意识形态的出场做着美学的护航”[39]。当下“景观对大众的控制不是暴力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具有深刻奴役性的隐形控制,这种控制由外在转向了大众内在对自我的控制,由被殖民转向了自我殖民”[40]。这种景观的催眠术对大众最深的奴役正是把权力、资本以及意识形态对个体的殖民掠夺,内在化为大众在景观面前的自我殖民。当我们坐在影院中欣然愉悦甚至激愤地享受着影像带来的安慰与想象或怨念的抚平时,我们对影片价值观、画面框定的视角和摄影机镜头的认同,却是在无意识地接受着资本、权力或意识形态的招安,会从内心屈从于意识形态对个人话语或集体话语裂隙的勉强缝合,会艳羡景观所建构起来的或华丽、或怀旧的中产生活方式,甚至会甘愿沉溺于强权资本或政治对自我个性自由的压制。因为影像中的这种基于虚拟的“形象”“符号”会削平历史空间与当下现实的客观距离,它在影视学的本质上是一种“超真实”的“纯粹拟像”。而在这种“拟像”播放的过程中,荧幕上的“形象”可以完全脱离它的“所指”,而以纯粹性的“符号”进入观影者的心理结构中,进而让生活于现实环境中的大众产生迷幻感觉。在不期然抚慰现代人创伤的同时,使人遗忘甚或失去掌控现代生活和命运的自主性。大众这种被无意识催眠的认同,或许已“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个人的文化品味问题,而是涉及社会意识形态、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体验等多方面的因素”[41]。
-
武侠电影这种思想制作的匮乏、政治姿态的妥协、制作观念的他者化、过度奇观化、历史感的缺失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悖逆和扭曲等系列问题,在过度透支了武侠类型片的传统势能之后,无论是在观众满意度上还是票房成绩上,都似乎难续辉煌。根据《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2014年到2015年的相关数据,观众虽然在最喜欢/最期待的国产类型片调查中,依然把第三名投给了武侠/动作片(第一、二名分别是喜剧片、爱情片,但在2013年的此项调查中,武侠/动作片以71.2%的优势成为观众最喜欢的影片类型)。武侠/动作类型一直无限度消耗着大众的心理期待,模糊着大众的情感认知与价值判断,不仅内力尽失,且大有淡出主流电影市场擂台之嫌。“武侠电影‘产量锐减、票房低迷,好作品寥寥’的论断似乎正成为现实。”[42]“2016年《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显示,在一项针对当下中国电影观众类型偏好的调查中,观众对武侠片的偏好迅速降至2.2%,在14种列出的类型片中居倒数第二。”[42]这些数据说明,观众对武侠/动作影片的满意度急速下滑,武侠/动作片对年度票房的贡献率也大幅度跌落(从2008年的超过40%到2015年的不足20%),2011年,中国市场一共有18部国产电影票房过亿元,其中武侠电影有9部。但到了2016年8月1日,当年的票房排行榜前50名中,只有《叶问3》和《卧虎藏龙2:青冥宝剑》分别占据年度第11名和第29名。
自2013年起,《一代宗师》《刺客聂隐娘》《危城》《师父》《卧虎藏龙2:青冥宝剑》等武侠动作影片已经开始偏离商业化的粗放型制作,形成了“武侠片作者化”的现象。虽然对这些武侠影片整体呈现的“作者化”倾向之努力,以及这些努力所表现出来的创作者的态度之诚恳、制作之严肃等成绩抱有极大的肯定、期许乃至展望,但“作者化”能否成为武侠/动作影片的创新或转型之路,依然是值得讨论的话题。《聂隐娘》将过于隐晦的现代“孤独/寻找”主题隐藏在一个叙事上更为隐晦甚至逻辑断裂的“刺杀/不杀”的刺客故事中,过于强烈的作者风格化情结,展现和映射的不仅是侯孝贤对侠的生存困境的理解——“侠的末路是隐匿与孤独”,更是普通大众对影片死活读不懂、看不下去的尴尬。在《师父》中,虽然徐皓峰通过情节设置给了主人公陈识一个面对江湖险恶、功利与残酷的观察者的凝视者视角,让他能够从这一视角进行反向思考:当武术、功夫无涉于传说中的正义勇敢、济世利民而成为个人野心、争夺名利的丛林战场时,人物追求武术/功夫的动机就会由伸张正义转变为对自身思想行为的质疑和内心意义的拷问。陈识最后与武林众生一一过招时动作的凌厉致命,也是其意识到只有这样,自己才不再受困于“动作”的枷锁。“‘动作’是为了不再‘动作’,《师父》终于达到了一个少见的中国动作电影的境界。而如是人物对于自我的困惑、痛苦和自醒将一部以‘功夫’为形式的影片从功夫片的类型中‘拔出’而捧到了带有‘作者’意味的艺术影片的高度。”[43]
影片对武林宗师的阴谋算计、尔虞我诈之演绎太过真实,在徐皓峰对民国武林的历史研究中,正如他自己坦言:那个世界那个武术“带给一个民族的,不是自信、而是自欺”。片中想要着力表现的正是武林规矩的真实存在与江湖法则的血腥残酷。稍感遗憾的是,片中对人物行为逻辑褒贬不定的暧昧立场,对真实武林世界爱恨并存的犹疑彷徨,相当程度妨碍了大众真正理解剧中描述的武术界真相的价值立场,不知该不该同情,也不知该同情哪一个。《师父》在把武术动作从虚拟的单纯观赏性与娱乐性视觉景观中释放出来进而赋予动作本身以情感、道德和反思的努力上,被认为是开创了“武术电影”的新类型。但片中过于有板有眼的武术分寸和规则展现,以及过分拘泥于人物在“武”的层面上的写实,不仅使得整个影片在意境和气韵上的开阖能力不够,而且也有放逐“侠”之超越性与精神永恒性之嫌疑。毕竟无论是传统武侠片还是变种后的功夫片,武侠作为一种超越人性恶以及追求公平正义秩序的精神,不仅守护着人对突破自身及意识形态幻象的一种想象,同时也守护着数代华人对武侠精神深刻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不光是过去时间在我们脑里打下的印记;它是一个看护人,守护着那些对我们最深切的希望和最深切的恐惧、有意义的时刻”[44]。
武侠影片近几年在大众口碑与票房上的双重失利,使得我们更理性地看待近年电影实践的各种转型策略和突破方式,作为最具本土特色的“原产类型”,武侠影片是应该偏离商业类型的轨道而整体走向作者化,还是如《天下第二》《龙凤店》《魔侠传之堂吉诃德》《大笑江湖》《财神客栈》《大话天仙》等更有喜剧娱乐的本性,或是探索商业化与作者化的更好结合?种种实践之得失,也许并不能在短期内定出褒贬。正如前文所述,无论武侠类型片走何种道路,是嬉笑怒骂还是慷慨悲壮,是名利攻心还是大义凛然,主创者对武侠涵义的理解及传达,都是为了更准确地揭示“武/侠”这一历史文化存在的特定含义,是为了促进武侠精神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良性互动,并试图通过武侠去发现和改变实存秩序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所以,尽管不同的电影叙事对“武/侠”的内涵和理解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我们倾向于将侠诠释为一种道德或超道德的英雄。这不仅仅是肯定历代文人知识分子对侠的文化创造以及赋予其中的正义人格力量,而且是为了注重保存和发扬这些始终交错互动的历史诠释、文学想象、正义迷思和英雄崇拜在侠的观念意义中积淀下来的道德价值和社会良知等人文精神”[45]。从这个方向看,《一代宗师》作为在商业与作者化、侠义精神的延续与传承两结合方面的尝试,应该能够作为一个参照,尽管这个参照也在诸多方面如讲故事的逻辑、剪辑快慢的对接及商业取向与文艺腔缝合等方面被人诟病,但影片对叙事与奇观、真实与虚构、历史与现实、商业和艺术之间平衡点的把握和尺度的掌控,却展现了有益的探索。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在武侠精神的传递上,并非仅仅止步于“见天地、见众生”的武侠境界构建,更是传达了将“武/侠”精神和道义“从见招式到见人,从见人到见武林,再从见武林到见众生”的薪火相传之胸怀与气度。《一代宗师》虽然名为“武侠+宗师”,但隐含在这两个关键词背后的依然是武侠精神的生存之道——“有一口气、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比如影片最后交代一线天逃亡之后,借开理发店的同时,在香港秘密传授八极拳。叶问更是传灯无数,正如他的武术观,“武术是大同的,千拳归一路。到头来,就两个字:一横一竖”。倘若把这种大同思想运用到对武术的理解里,那么即使在现在的研究者看来,理想的武林,也应是宽广的、平等的、互相分享的、互相进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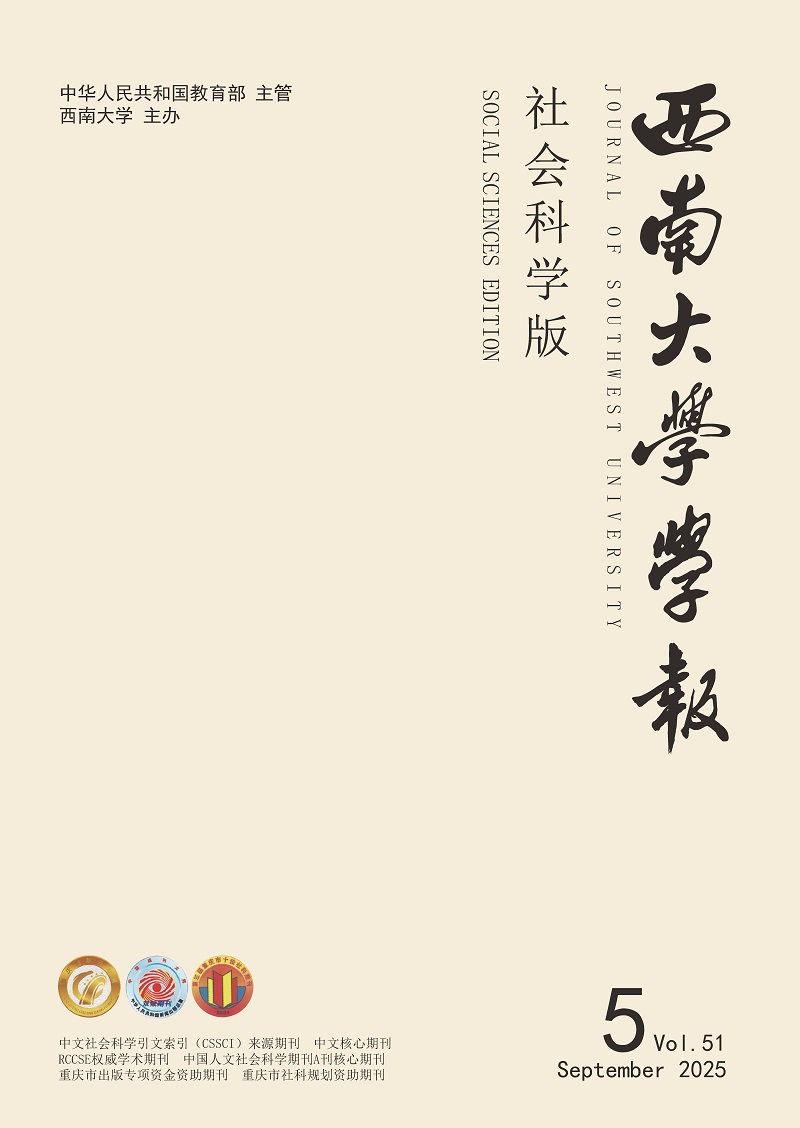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