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五四”命名的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以及学生爱国运动,不仅开启了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和文学嬗变的新纪元,更在近百年的历史蓄积中不断净化、纯化,凝聚成一束高能量光源,在历史的各个关口起到了探路和照亮的作用。“五四”的“高能化”固然增强了探照的力度和强度,但也窄化了其作为能量场的宽度和深度,弱化了作为一个政治、思想、文化交锋地带所应有的驳杂与丰富。在重新认知、反思五四的大潮中,有些学者已经逐渐意识到,五四的“反对派”不仅仅具有负面价值,同时也是五四的“另类”参与者,“其质疑、诘难、否定、批评从不同方面推进了五四新文学的历史进程”[1]。如果说这种认知还是完全立足于五四新文学立场的发言,那么,“谁的五四”提问者则站到了一个双边的立场上:“将五四遗产简化为《新青年》与五四新文化派,这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化启端的丰富而复杂的内涵的发掘,也给一些望文生义的指摘留下了可能。在作为历史发动火车头的五四新文化派的背景上,存在着一个更为广阔的‘五四文化圈’,它由新文化的倡导者、质疑者、反对者与其他讨论者共同组成,他们彼此关系有疏有密,但远非思想交锋之时的紧张和可怕,他们彼此的砥砺和碰撞……一起保证了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能量和稳定,属于我们重新检视的‘五四遗产’。”[2]可见,学界已经从更为理性的角度审视五四。笔者认为,全面理解五四,不仅仅要把强化为一元浓缩为“点”的五四,拓展为多元的“面”的五四,化解固化的意识形态壁垒,还应破解认知模式上的迷思,去除以“进步与落后”“激进与保守”“革命与反动”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构成的一元价值取舍,以“了解之同情”重新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反对派”。检视五四反对派被“固化”乃至“丑化”的历史,还原其被遮蔽的正面形象和有效价值,并非压抑或削弱了“五四精神”,而是全面理解“五四”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一思路下,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发动期的头号反对派人物林纾及其“反动小说”《荆生》和《妖梦》,就成为首先要直面的问题。与学界对其他五四反对派如学衡派、甲寅派、辜鸿铭等不断做出的正面价值重估相比,在对待林纾尤其是其借用小说攻击五四这一问题上,研究界的结论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坚决捍卫五四新文学价值的主流学派自不待言,即便是一些认为应该理性、辩证地看待林纾等五四反对派的学者,也毫不含糊地认定:“林纾攻讦新文化阵营的小说《荆生》、《妖梦》毫无水准,大失风度,是可悲复可笑的败笔。”[1]林纾及其“反动小说”《荆生》和《妖梦》几成不容置疑的历史定案乃至铁案。实际上,《荆生》和《妖梦》的出现,原本是“性好谐谑”的林纾所写的“游戏文字”,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严肃小说,最终上升并定性为“反动文本”,乃是五四新文化派有意建构的结果,并成为五四新青年批判林纾的关键一击。《荆生》和《妖梦》是正、反双方都确认的反对派攻击五四的铁证。因此,重回历史现场,考察这一“反动文本”的历史生成过程,对于重估五四反对派并全面认知“五四”有着重要作用。
HTML
-
五四新青年与林纾的论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旧思想的首次交锋。林纾从“双簧信”开始卷入论战,到他发表《荆生》和《妖梦》时,招致新青年乃至新学界的集体批判,最终高挂免战牌,如陈独秀所说“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人的错误”[3]。至此,五四新青年初战告捷,而林纾作为新文化运动反动派的身份和失败者的可悲下场,遂成新文学史定案。在此后的新文学史叙事中,林纾作为顽固的卫道者和绝望的失败者的形象,不断得到强化。在阶级意识形态笼罩下的“革命文学史”阶段,林纾作为“阶级反动派”的形象自不待言,但时至20世纪80年代,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重新修撰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林纾固化的形象依旧没变,仍然被描述为一个绝望的乃至充满仇恨的反动派角色:“首先跳出来反扑的是林纾,他在近代翻译外国小说方面成就斐然,但毕竟是‘桐城派’的嫡传弟子和干将,终于充当了‘拼我残年极力卫道’的悲剧角色。”[4]林纾的这两篇小说,遂成为他作为反动派的有力证据:“林纾还发表拙劣的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含沙射影咒骂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和支持者,阴险地暗示握有实权的‘伟丈夫’出来干预镇压,暴露出封建士大夫丧失世袭领地时的仇恨的心理。”[4]在这一具有代表性并拥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史著作中,林纾被塑造成一个阴险的、充满仇恨的、绝望的卫道者形象。以此为代表,中国新文学史形塑的林纾,包括对这一论争事件的定性,深刻地影响到后来力图以同情的心态和客观的眼光看待林纾并力图重塑林纾正面形象的研究者,比如张俊才先生在《林纾评传》中即带着认同、理解之情评价林纾:“他是一个有‘义心’、有责任感的人,是一个生性耿直,注重‘节操’,但脾气又有些‘燥烈’的人。”[5]222这种评价较之新文学史站在“敌我”立场上的“阴险论”“仇恨论”,更接近实际。但当论及林纾在五四新旧思潮激战时的行为时,张俊才也认为,林纾自幼木强多怒的性格,致使他对新文化阵营的“反击”难免是情绪化的,即便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的具体做法实际上也堕入了非道德的‘恶趣’之中”,“《荆生》《妖梦》确属过分情绪化地编造荒唐的故事来向对手泼污水”[5]226-227。可见,即便是在林纾的正论者、辩护者眼中,《荆生》《妖梦》的出现也是令林纾的“人品”与“文品”大打折扣的污点。显然,这仍是一种典型的“五四新青年派”的基本价值立场。当然,强调林纾木强多怒、好骂人、刚直、倔强、不屈人下的性情,突出其心地坦荡而非假道学的君子品性,固然化解了以往新文学史对林纾的“矮化”乃至“丑化”,但这却使得五四时期的这场新旧论争更趋于严肃化和严重化。在这一过程中,《荆生》和《妖梦》作为“骂战”的产物,“嫚骂”“影射”的反动文本特征也就愈发鲜明。
林纾在“木强多怒”的性情之外,还有另一副面相——好谐谑。两种性情二者合一,才是全面理解林纾以及《荆生》和《妖梦》的关键所在。陈声暨在林纾去世后的挽诗中评价:“我性本嫉俗,有声寄之诗。诗成常请益,丈为动须眉。张目毕怒骂,解颐事诙谐。”[6]卷三,p4“诙谐”与“怒骂”是林纾性格的两个方面。正所谓“文章通于性情”,林纾好谐谑的性情渗透到其著、译的小说中,则形成了幽默诙谐的风格。夏敬观在挽诗中曾比较过严复和林纾著述文字的特征:“闽士严与林,等以著述老,林书极诙谐,严书太玄草。”[6]卷三,p4可见,林纾的诗文小说能够风靡一时,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其笔墨的幽默诙诡,令人有拊掌的快感。郭沫若等读着林纾小说成长起来的新文学家们,对林纾的这一幽默风格感受很深,甚至颇为醉心。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中回忆说:“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所嗜好的一种读物……Lamb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林琴南译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也使我感受着无上的兴趣。它无形之间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后来我虽然也读过《Tempest》、《Hamlet》、《Romeo and Juliet》等莎氏的原作,但总觉得没有小时所读的那种童话式的译述来得更亲切了。”[7]钱钟书更是从读者和学者的双重角度,高度评价了林纾的翻译:“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8]22钱钟书就此进一步深究,发现林译小说中那些不忠实于原著的翻译,曾备受五四新青年批评和嘲笑的“颠倒讹脱”,有时恰是林译的魅力所在,林纾对原文的有意加工,往往比原文更有趣味,比照而读,原著有时反倒叫人失望,其深层次原因即在于林纾自身笔调的风趣和幽默。因此,钱钟书认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承认林纾颇能表达迭更司的风趣,这种评价远远是不够的,实际情况则是林纾“往往是捐助自己的‘谐谑’,为迭更司的幽默加油加酱”[8]25。胡适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肯定了林纾这一独特风格的贡献和价值,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对林纾有两次“平心而论”的评判,指出林纾以文言翻译西洋小说的贡献之一,即是增加了古文滑稽的风味:“平心而论,林译的小说往往有他自己的风味;他对于原书的诙谐风趣,往往有一种深刻的体会,故他对于这种地方,往往更用力气,更见精彩。”“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9]胡适等新文学倡导者,大多看重林译小说,并从翻译的角度肯定林纾古文体现出来的幽默诙谐风采。钱基博更进一步认为,林纾的这一风格不仅体现在译著上,而且是他的整体文风,钱基博以林纾的《冷红生传记》《徐景颜传》《赵聋子小传》为例指出:“纾之文工为叙事抒情,杂以诙诡,婉媚动人,实前古所未有。固不仅以译述为能事也。”[10]168
-
林纾偶然译述《巴黎茶花女遗事》却“不胫走万本”,他从此踏上小说翻译的“不归路”。但从根本上来讲,林纾并不看重他的小说家、翻译家身份,他所看重的仍是身为“古文家”的名声。“古文”与“小说”在林纾心目中始终有着不同的价值等级。钱基博在其所著文学史中曾多次谈到林纾写作古文与译著小说时的不同状态:“及自为文,则矜持异甚。或经月不得一字,或涉旬始成一篇。独其译书,则运笔如风落霓转,而造次咸有裁制,不加点窜。盖古文者,创作自我,造境为难;而译书则意境现成,涉笔成趣已。”[10]165-166为文与译书迥然不同的状态,一方面表明林纾在创作小说方面的天赋,因而译起来毫不费力;另一方面也见出在林纾心目中,小说和古文具有截然不同的分量。译小说和作古文的两种状态所体现的是两种心态。作古文时“矜持异甚”,是林纾对古文遣词造句的一种慎重,同时也暗示出他对古文所持的一种近乎神圣的敬畏。张僖在《畏庐文集》序言中也道出了林纾对“诗”“文”“小说”的不同态度:“畏庐,忠孝人也,为文出之血性。光绪甲申之变,有诗百余首,类少陵天宝离乱之作,逾年则尽焚之,独其所为文颇秘惜,然时时以为不足藏,摧落如秋叶,余深用为憾。”林纾对待自己所写的文章近乎苛刻:“时文稿已有数十篇,日汲汲焉索其纰缪,时时若就焚者,余夺付吏人,令庄书成帙。”[11]与对待古文的审慎态度相比,林纾对待小说则很随意,任其散落于报端,不屑一顾:“畏庐先生著铁笛亭琐记,不下千余条,然颇不甚爱惜,经余之所收者,十之二三耳。先生尚不欲梓行,余以为可惜。”[12]卷二,p18林纾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也曾谈到:“石遗言吾诗将与吾文并肩,吾又不服,痛争一小时。石遗门外汉,安知文之奥妙!……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持吾诗相较,特狗吠驴鸣。”[8]50林纾认为和他的古文相比,其“诗”乃为“狗吠驴鸣”,更不要说小说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了。正是出于这种心态,林纾对于世人只以小说家看待自己很不以为然,在《鹰梯小豪杰》序言中曾说:“余笃老无事,日以译著自娱。……本非小说家,而海内知交,咸目我以此,余只能安之而已。”[12]卷三,p8-9其情形正如高凤岐在林纾著《技击余闻》的序言中所讲:“琴南齐年,以说部名海内,生平所学,实不止此,此其余事耳。”[12]卷二,p17把译著“小说”看作林纾的“余事”以区别其著述,这恐怕是对林纾最为知心的评价。
众所周知,林纾翻译泰西小说是怀着“改良社会、激劝人心”的至高目标的,他在《不如归》的序言中曾自述:“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恒于小说序中,摅其胸臆。”[12]卷三,p37但是,即便在小说中寄托着如此深重的家国情怀,也并不妨碍林纾依旧把小说视为“小道”。与同时代的梁启超等人把小说提升为“文学之最上乘”相比,林纾则视“小说”为“余事”,实际上,这才是一种更为“正统”也更守“传统小说家法”的理解。自古以来,中国小说之“小”,正是通过轶事琐语以资“谈助”,与“资治”的正史相对应。当然,小说与正史之间又并非井水不犯河水,高文典册的正史为官家所修,严格受制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难免东涂西抹、行迹可疑乃至面目可憎,而本来无关宏旨的小说则又成了必不可少的补充,其意义是至深至大的。“小说”自古虽为“小道”却能绵延不息,为历代文人所青睐,原因之一即在于此。林纾在《畏庐漫录》自序中道出了自己的“小说观”:“余年六十以外,万事皆视若传舍。幸自少至老,不曾为官,自谓无益于民国,而亦未尝有害。屏居穷巷,日以卖文为生,然不喜论政。故着意为小说。计小说一道,自唐迄宋,百家辈出,而余特重唐之段柯古。柯古为文昌子,文笔奇古,乃过其父,浅学者几不能句读其书,斯诚小说之翘楚矣。宋人如江邻几,为欧公所赏识者,其书乃似古而非古,胶沓绵覆,不审何以有名于时。宛陵梅叟诗笔,为余服膺,而碧云马騢一书,至诋毁名辈,大不类圣俞之为人。吾恒举邻几杂志,疑为伪作。盖小说一道,虽别于史传,然间有纪实之作,转可备史家之采摭。如段氏之玉格天尺,唐书多有取者。余伏匿穷巷,即有闻见,或具出诸传讹,然皆笔而藏之,能否中于史官,则不敢知。然畅所欲言,亦足为敝帚之飨。”[12]卷二,p18林纾推崇“文笔奇古”的小说表述方式,他的笔记小说自然也以雅正为旨归,讲求正统的笔记小说所具有的词旨简淡、文词古雅的书卷气,是典型的“著述者之笔”而非“才子之笔”。正是在这一点上,《平报》主笔臧荫松评价林纾的笔记小说已经大大超出了蒲松龄而直追史汉:“夫短篇小说之体,往往坠于蒲留仙之臼窠,不能自脱。翁熟于史记汉书,造语古简而切挚,篇法亦变幻莫测,是真不囿于蒲留仙者也……余谓真小说家,非史家亦莫造其极。段柯古之笔,实过其父,则真得史家之三昧矣。然好言鬼神,以叙鬼神事,易于声色。若翁之书,则但言人事,不言鬼事,即言之,亦偶然耳。其能款款动人处,闭目思之,亦似确有其事。则翁之善于史汉,故造言之精如是。”[12]卷二,p18臧荫松虽为林纾好友,但上述评价却十分中肯,并非过誉之辞。
中国自古以来以“资谈助”为旨归的笔记小说,作者往往自我标榜为“弄笔潜日”的消闲之作,风趣幽默诙谐为其标志化风格之一,林纾善谐谑的性情更使其在创作笔记小说时随心所欲,妙趣天成。臧荫松酷爱林纾的笔记小说,曾经把散落于报纸中的“铁笛亭琐记”收集了十分之二三,付梓刊行,并在历代笔记小说的整体历史脉络中给予林纾笔记小说以高度肯定,进行了中肯的定位:“古来作者如林,而唐宋二代,为笔记者独多。有明太祖雄猜,自高青丘之狱,明人做诗颇留意,则私家记载,益形敛退。前清入关,文字之狱大猖,一字之不检,至赤其族,矧敢作笔记,以招忌者之谗,贡身自膏于斧质耶。南山集初无失检,而赵申乔锻成其狱。方望溪大儒,至以是出塞,小人之凶焰,可畏甚矣。纪文达之阅微草堂笔记,多谐谑,兼及鬼事,聊斋则专言狐鬼,故得无事。若稍涉时政者,族矣。今先生所记多趣语,又多征引故实,可资谈助者。至笔墨之超妙,读者自能辨之。”[12]卷二,p18就“资谈助”而言,林纾的“谈人事”比蒲松龄、纪晓岚等的“谈鬼狐”显然需要更大的直面现实、无畏文网的勇气,谈人情而能幽默诙谐,正说明林纾的笔记小说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其超拔的一面。
如果说林纾的“笔记小说”以古雅、诙诡、婉媚动人的风格在中国笔记小说史上占据一席之地,那么,五四文学革命发生之后,在五四新青年的眼中,则彻底失落了价值。被林纾视为“余事”的笔记小说和新青年所持的启蒙主义现代“小说观”,有着“古今中外”的落差。胡适在《论短篇小说》中给出的“短篇小说”定义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13]这一定义所使用的标准有二:一是西方,二是白话。胡适以都德的《最后一课》《柏林之围》和莫泊桑的《二渔夫》为短篇小说的典范,几乎全盘否定了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自汉到唐这几百年中,出了许多‘杂记’体的书,却都不配称做‘短篇小说’。最下流的如《神仙传》和《搜神记》之类,不用说了。最高的如《世说新语》,其中所记,有许多很有‘短篇小说’的意味,却没有‘短篇小说’的体裁。”[13]对于“今日的文人”,胡适更是表现出了鄙斥的态度:“中国今日的文人大概不懂‘短篇小说’是什么东西。现在的报纸杂志里面,凡是笔记杂纂,不成长篇的小说,都可以叫做‘短篇小说’。所以现在那些‘某生,某处人,幼负异才……一日,游某园,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一派的滥调小说,居然都称为‘短篇小说’!其实这是大错的。”胡适还以不点名的方式揶揄了林纾:“那些古文家和‘聊斋滥调’的小说家,只会记‘某时到某地,遇某人,作某事’的死账,毫不懂状物写情是全靠琐屑节目的。”[13]胡适以西方短篇小说的观念和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小说,自然得出中国传统小说“无”且“错”且“滥”的结论,这是一种典型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五四新青年敢于趾高气扬地批判嘲笑林纾及其笔记小说,除了年轻气盛无所畏惧之外,更是出于对自身所持观念“先进性”的一种高度自信。把旧文学、旧思想彻底扫除,为新文学、新思想开拓空间,既是五四新青年的一种策略,也是五四新青年不容他人质疑的信念。
-
《新申报》因为刊载林纾的《荆生》和《妖梦》,一度背上了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恶名。《新申报》创刊于1916年,为报人席子佩转卖《申报》后另辟门户之举。《新申报》副刊聘请原《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笔王钝根担任编辑,初名为“自由新语”,后更名为“小申报”。1919年,《新申报》副刊“自由新语”登出广告:“己未年自由新语当增材料如左:林琴南先生之小说,天虚我生之小说,歇浦潮续稿,中西笑话,悬奖征对。”由此,以“蠡叟丛谈”命名的林琴南小说开始刊载。王钝根编辑《新申报·自由新语》延续了《申报·自由谈》的编辑思想,同时也是王钝根一贯的理念——游戏其文字,救世其精神,因而对滑稽诙谐但具有讽世意味的文字情有独钟。王钝根通过张厚载请林纾为副刊写小说,一方面固然是看重林纾在文坛的名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林纾善谐谑的风格与其宗旨相符。在开篇《安娜》中,林纾对“蠡叟丛谈”这一栏目中的文字进行了说明:“蠡叟,年七十矣,木然如枯僧。世变如沸,叟耳目若聋若聩,初不知觉。……忽一日,门人张生厚载述本报主笔之言,请余为短篇小说,以虱报阑,意以供诸君喷饭也。余曰:‘论说非我所长,且不愿为狂嗥之声,以乱耳听。唯小说足排茶前酒后之闷闷。’因拾吾七十年所见者,著之于编,命曰《蠡叟丛谈》。”[14]显而易见,林纾称“蠡叟丛谈”的小说是用来“解闷”“喷饭”的,虽是自谦之词,但也是笔记小说的固有定位——以“消闲、娱乐”为旨归。以“蠡叟丛谈”命名的这批笔记小说,也延续了林纾笔记小说一贯的劝惩意图,即对纲常礼教、忠孝节义的维护。在新文化运动浪潮之初,新青年提倡的“家庭革命”尤其让林纾不满,重申“孝”的重大意义在林纾此时期的诗、文、小说中愈发鲜明,而林纾这种极力卫道的固执在新青年的眼中也就愈发刺眼。《荆生》和《妖梦》确实是针对新青年们所提倡的新文化、新思想、新文学主张而作,但戏谑调侃的意味是十足的。替林纾传递这两篇小说的张厚载,也在致蔡元培的私信中说:“先生大度包容,对于林先生之游戏笔墨,当亦不甚介意也。”[15]但正是这两篇小说被新青年们抓住了把柄和时机,“游戏笔墨”最终成了“示众”的材料。
《荆生》1919年2月17-18日连载于《新申报》,3月9日转载于《每周评论》12期“杂录”栏目,3月11日又被《国民公报》转载。两报转载时都加了按语,尤以《每周评论》的按语意义重大,直接名为《想用强权压倒公理的表示》:“近来有一派学者主张用国语著作文学,本报也赞成这种主张的。但是国内一班古文家骈文家,和那些古典派的诗人词人都极力反对这种国语文学的主张。我们仔细调查,却又寻不出什么有理由有根据的议论。甚至于有人想借武人政治的威权来禁压这种鼓吹。前几天上海新申报上登出一篇古文家林纾的梦想小说就是代表这种武力压制的政策的。所以我们把他转抄在此,请大家赏鉴赏鉴这位古文家的论调。”《国民公报》的按语则直接指责林纾“将崇拜权势的心理,和盘托出”[16]。原本是《新申报·自由新语》中用以“虱报栏”“供喷饭”的游戏文字,一经由新文化运动主力报刊和支持者转载,其性质和身份立即发生了变化。转录自《晨报》的李大钊的犀利文字《新旧思潮之激战》被置于《每周评论》所载《荆生》篇后,等于直接把这篇小说纳入到新旧思想激战的时代潮头。李大钊的义正词严使得事件迅速升格:“我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你们若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17]这几篇重磅评论,为此后展开的“林纾批判”定下了基调——旧派力图靠强暴武力压制新思想,借武人政治遏制新文化的鼓吹。众所周知,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伟丈夫荆生”很快便被对号入座,被指称为北洋政府干将“徐树铮”。陈独秀以笔名“只眼”在《关于北京大学之谣言》中讥讽道:“林琴南怀恨新青年,就因为他们反对孔教和旧文学。其实林琴南所作的笔记和所译的小说,在真正旧文学家看起来,也就不旧不雅了。他所崇拜所希望的那位伟丈夫荆生,正是孔夫子不愿会见的阳货一流人物。这两件事,要请林先生拿出良心来仔细思量!”[18]随后陈独秀又在《林纾的留声机》中描述了有关林纾的传言,进一步扩大事态及其影响:“林纾本来想藉重武力压倒新派的人,哪晓得他的伟丈夫不替他做主,他老羞成怒,听说他又去运动他同乡的国会议员,在国会里提出弹劾案,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无论哪国的万能国会,也没有干涉国民信仰言论自由的道理。我想稍有常识的议员,都不见得肯做林纾的留声机吧?”[19]正是这种升华和链接,使得新思想、新文化提倡者得到了学界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并把北京大学教员陈独秀、胡适等人被驱逐的传闻和教育总长弹劾案等,统统融合在一起,遂致一时群情激奋。林纾作为妄图以武力强权压迫新思想的守旧派代表,则成了思想界批判的靶心。《每周评论》第17期、第19期“特别附录”了《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共摘录了京、沪等地报纸的26篇评论,除个别三四家报纸的言论是奉劝新旧两派去除成见从而进行心平气和的思想论争外,其余言论都是批判“妄图以政治武力摧残新思想”的荒谬和卑劣。在这次对林纾的大批判中,固然也有“二古”先生以中学教师的名义逐字逐句批改《荆生》的文字,继续走《新青年》“双簧信”的路子,嘲讽其古文的低劣,揶揄林纾学问不到家,乃是“婢学夫人”,但与前面罗列的“罪状”相比,这一讥讽已微不足道。以林纾为代表的旧派妄图借政治势力打压新思想的卑劣行径,几乎已经是“路人皆知”了。
《荆生》的姊妹篇《妖梦》于1919年3月19-23日刊于《新申报》,虽然没有像《荆生》那样被新文化报刊媒体转载,但《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1日刊载了张厚载与蔡元培有关《妖梦》的通信,不啻于使林纾对蔡、陈、胡等人的攻击有了真凭实据,其示众效果同样强烈。张厚载在信中说:“《新申报》所载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悉由鄙处转寄。近更有《妖梦》一篇攻击陈、胡两先生并有牵涉先生之处。稿发后而林先生来函,谓先生已乞彼为刘应秋文集做序,《妖梦》当可勿登。但稿已寄至上海,殊难终止,不日即可登出。倘有渎犯先生之语,务乞归罪于生。先生大度包容,对于林先生之游戏笔墨,当不甚介意也。又林先生致先生一函,先生对之有若何感想,曾做复函否?生以为此实研究思潮变迁最有趣味之材料,务肯先生将对于此事之态度与意见赐示。”[15]信末还特别说明自己与林纾的师生之谊,张厚载天真地以为这一切都可以作为研究思潮变迁最有趣的材料,他实在是错估了形势。新旧观念的论战一开始就不是在“幽默”“有趣”的范畴内进行的,蔡元培的复信简洁明了、义正词严:“得书知林琴南君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均由兄转寄新申报,在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循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仆生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15]相较于蔡元培这封正气凛然的信,林纾的谩骂,愈发显得“轻薄”“失德”。陈平原评价说:“无论新派、老派,读这两段文字,都会觉得林纾骂人不对,蔡元培修养很好。这一局,林纾输得很惨。”[20]
虽然在这场论战中,新青年派对于林纾的批判所用的过激言论乃至谩骂丑诋,与林纾难分伯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最终还是林纾为自己的骂人而写信公开道歉:“世杰先生足下,承君自神州报中指摘仆之短处,经敝同乡林姓托言黄姓者,将尊札寄示,外加丑诋,仆一笑置之。唯尊论痛快淋漓,切责老朽之不慎,于论说中有过激骂詈之言,吾知过矣……综而言之,天下人观人甚明,观己则暗。仆今自承过激之斥,后此永永改过,想不为暗。然敝国伦常及孔子之道,仍必力争,当敬听尊谕,以和平出之,不复谩骂。”[21]林纾对自己将招致新青年的批判和攻击早有预料,他最初也确实是把小说《荆生》和《妖梦》当作是对五四新青年的一种戏谑,同时也道出了自己的深层隐忧和苦衷:“吾译小说百余种,无言弃置父母且斥父母为无恩之言,而此辈何以有此。吾与此辈无仇,寸心天日可表。若云争名,我名亦略为海内所知,若云争利,则我卖文卖画本可自活,与彼异途。且吾年七十,而此辈不过三十,年岁悬殊。我即老悖癫狂,亦不至猵衷狭量至此,而况且并无仇怨,何必苦苦跟追,盖所争者天理,非闲气也。……前日偶作荆生一传,稍与戏谑,乃得每周日刊主笔,力加丑诋,吹毛求疵,斥为不通。读之大笑。夫不通无罪于名教,以得罪名教之人,斥我不通,则愈不通愈好。”[22]“昨日寓书谆劝老友蔡鹤卿,嘱其向此辈道意,能听与否,则不敢知。至于将来受一场毒骂,在我意中。我老廉颇顽皮憨力,尚能挽五石之弓,不汝惧也,来来来。”[23]显然,七十岁的林纾做好了挨一场小辈青年毒骂的准备,且为了维护“天理”,甘愿如此。与林纾在新旧论战中所写的《致蔡鹤卿太史书》《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腐解》等严肃论说文相比,林纾作《荆生》《妖梦》时的戏谑心态是显而易见的,而他以“老廉颇”自比,也显示出一种“狂生老少年”的性情色彩。
无论是林纾的道歉还是陈独秀的点赞,抑或是林纾逝世之后胡适、郑振铎等五四新青年们给予林纾的重新评价,都无法改变中国新文学史对林纾的定位。1936年,《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出版,《荆生》和《妖梦》分别附录于《文学论争集》和《理论建设集》之后,郑振铎在导言中继续了“五四新青年”的说法:“古文家的林纾来放反对的第一炮……他卫道‘正’文的热情,又在另一个方向找到出路了。他连续的在报纸上写了两篇小说:一篇是《荆生》,一篇是《妖梦》,两篇的意思很相同;不过一望之侠士,一托之鬼神罢了;而他希望有一种‘外力’来制裁,来压伏这个新的运动却是两篇一致的精神。谩骂之不已,且继之以诅咒了。”[24]至此,林纾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动派,《荆生》和《妖梦》作为“反动文本”已经正式进入文学史,并且在此后的新文学史著作、五四人的回忆以及有关新文学的研究中不断得到延续和强化。一直到近百年后,才有学者重新缕析当年的混战,努力澄清一些事实,如“伟丈夫”“荆生”是否为“徐树铮”的问题,又如驱逐并逮捕陈、胡等四名大学教员的传言是否与林纾有关等等,这些都已经与林纾脱离了干系,澄清了当时和历史上对林纾有意或无意的误解。情况恰似林纾当年所预言的那样:“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辩之者,请诸君拭目俟之。”[25]但是,就近20年来学界对林纾及五四新青年论争的重新评判而言,这仍然是一场迄未终结的论争,有的学者主张对林纾应有“了解之同情”,有的学者则坚决反对给林纾做翻案文章,认为林纾这样的人不可原谅:“对林纾整个一生功过是非的评价是一回事,对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的评价又是另外一回事。只要意识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有文化专制主义的影响的存在,只要意识到文化专制主义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只要意识到像林纾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就会依傍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而反对那些背绳墨、离规矩、在权威话语的词典里找不到依据的出格言论,我们就不能以任何的理由原谅林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表现,也不能以任何的理由减轻他的过失。这些人,失败了也不会有多大实际的损失,胜利了则会给对方造成难以忍受的痛苦,甚至会毁掉人的一生。原谅了林纾,也就原谅了这类知识分子的这类行径,中国知识分子就永远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26]说到底,如何评说林纾,这最终涉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的立场和态度问题,而“五四”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圣地,维护其价值和精神,已经成为职责、本能和潜意识。
-
从对林纾及其“反动文本”的史实梳理与价值评析,可以得到关于“五四反对派”研究方法论的一些启示。
-
近些年来,多重原因促成了学界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反对派”(亦称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守成主义)的研究热潮,取得的成果颇为引人注目。应该说,无论出于何种动因,这些研究都颇有成效地描述了一个原本复杂而丰富的“五四”,同时也在思维模式上对以往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单向度历史价值认知有所化解。但是,一个近乎趋同的研究方式也不容忽视,面对这些反对派,研究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无罪辩护”式研究,在开脱其“罪责”的同时努力证明其“无罪”乃至“有功”,一个典型的方式即对这些保守派、守旧派进行比附于“五四”的理解,或者发掘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先导色彩或者启示作用,或挖掘其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立场的一致性,寻找其历史进步性的证据,目的即在化解历史上已经固化的“守旧派”“反对派”乃至“反动派”的面相。
在林纾研究中,研究界便着力发掘其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学意义,论证林纾作为新文学“不祧之祖”的进步意义。又如对“甲寅派”的研究,学界则倾向于进行“前”“后”分期处理,并在此基础上肯定以《甲寅》月刊为标志的“前期甲寅派”的进步意义,认定其为“五四新文学”的先声。同样,对于“学衡派”,则被认为是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种潮流。与20世纪世界思潮相对应,“学衡派”是属于陈独秀所代表的激进主义、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以外的保守主义一维。这些研究,无疑还都是以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为价值参照系而做出的评判和论断。从根本上讲,“五四”已经内化为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一种内在评判尺度,“五四”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不仅意味着显性的“价值立场”,更意味着隐性的“情感依恋”甚至“道德皈依”。因此,在对待反对派的问题上,看似做出了一分为二甚至偏向于“反对派”的评判,而骨子里却始终脱离不了“无罪辩护”的意味,潜意识里还是把反对派置于被告席上的。对于五四反对派的这种“趋新式”理解,既违背了五四文化保守主义者们的本意,同时也进一步导致了文化保守主义所守成的“旧”依然被划归为“零价值”或“负价值”。因此,看似从新旧、得失两方面理解中国文学现代进程的意图,仍然是一个单向度的循环。
学界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反对派的研究,之所以亟亟挖掘其“进步”“趋新”的一面,关键原因在于还无法从思维模式乃至情感道德上摆脱进化论框架乃至“斗争哲学”所笼罩下的“新与旧”“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二元模式,因而也就无法正视所谓“旧”或者“保守”所具有的实际意义和正面价值。笔者认为,对于五四时期的这些反对派而言,“守旧”“保守”恰是其本色,相反,研究者努力发掘出的对于新文化/新文学的“开新”或者“奠基”之功却并非其本意。与后来研究者为其努力洗刷“反动派”之“罪名”的做法相反,他们往往公开、主动甚至凛然地以新文化/新文学的“反动派”自居。林纾即是以卫道者的姿态主动站出来挑战五四新青年,公然表明自己“卫道”的决心;“甲寅派”领袖章士钊也是不介意做“反动派”,意在“立乎中流”“平视新旧两域”衡量其是非得失。“学衡派”也同样有着明确的“反对派”意识和主张,力图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起到一种“整理收束”之功,以期达到“正负质济”的作用。而实际上,新文化阵营对这些反对者也并非采取一概否定、漠视的态度,徐志摩在批判章士钊的文章《守旧与“玩旧”》中即从正面意义上肯定了章士钊及其《甲寅》周刊作为反动派的价值,称他是一个值得敬仰的“合格的敌人”与“一个认真严肃的敌人”,他说:“在他的思想里,我们看了一个中国传统精神的秉承者,牢牢的抱住几条大纲,几则经义,决心在‘邪说横行’的时代里替往古争回一个地盘;在他严刻的批评里新派觉悟了许多一向不曾省察到的虚陷与弱点。”[27]因此,这些“反对派”,无论是在中国现代历史文化结构中,还是在实际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制衡作用,恰恰正在于其“守旧”而不是“趋新”。
-
五四时期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历史时代,传统思想、道德、文化、文学的分裂蜕变与新思想、道德、文化、文学的萌蘖滋生相伴而生,这其中既伴随着新生的喜悦也难掩失落和撕裂的痛苦,既有开拓思想新境的勇毅也有卫护旧有精神家园的执著。中国思想、文化、文学的现代转型并不仅仅是一个“拿来”并“获得”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丢弃”和“失落”的过程。对于“获得”的部分,研究界已经投入了持久的关注热情,对于“失落的”部分则明显关注不足。当我们单从新文化/新文学的立场言说“五四”的时候,其开拓历史的力度、打破旧物的强度都获得了展示。与此相对应,作为其对立面的“卫道士”“顽固派”“守旧者”的对抗,往往被看作是一种否定的、负面的价值,尤其是从新文化/新文学最终胜利的历史结果回望过去,这些曾经存在过而最终以失败告终的“阻力”与“对抗”,似乎只能作为“胜利者”的注脚。这是以单向度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看待“五四”和“新文学史”最容易直接得出的结论。
如果不把“五四”仅仅看作“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五四”,而是作为一个多元价值共享并存的历史时空,那么在这一思想、文化和文学的大转折时期,“守旧者”“保守派”所持守的传统思想、文化和文学的时代境遇就不应被漠视。中国自近代以来即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亡国灭种的危机使得中国近代以来再难有绝对的守旧者,“求变”成为走出历史困局的公认途径,只不过变革速度的快慢、变革尺度的大小、变革内容的不同而已。新、旧两派并非是在“变”与“不变”的根本问题上论争,而是在变革的手段上争执不下,究竟是“破旧立新”“弃旧图新”还是“新旧相衔”“孕新于旧”更符合文化的变革规律、更适应中国国情?这恐怕才是新旧两派的真正分歧。由“新与旧”的激战所构成的对抗、对话、混融、交往等等的复杂关系,正昭示着“五四”思想变革的深度和广度。
当我们超越“五四人”的立场,走出论争式的二元对立思维,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和健全的文化、文学生态去看待“守旧派”“保守派”与五四新文化/文学阵营的对抗/对话时,就会发现其作用并不仅仅是消极的,毋宁说,“守旧”构成了“开新”的必要阻力。作为开拓者的新文化派及其反对派,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现代转型的两翼,因此,即便是“失落”与“丢弃”,它也同样是“现代转型”的构成部分。进一步讲,中国“古已有之”的思想文化和文学传统,经由“五四”到底失落了哪些?是怎样失落的?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在现代进程中失落的传统?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深刻省思。
-
五四是新旧思想文化交锋论战的大时代,其不朽的精神魅力即体现为这种论争的勇气和交锋的锐气,这种魅力的生成不仅仅来自“革命派”的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五四新青年荡涤旧物、开辟新境的力度,也来自那些身为“保守派”的林纾、辜鸿铭、章士钊等固守其价值体系而毫不妥协的强度。新青年以对旧物“尽数扫除”的决绝姿态(钱玄同语)和“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陈独秀语)的强悍和霸气,显示了新青年淋漓的生气和革命的斗志。然而,林纾“拼我残年,极力卫道”的倔强也毫不逊色:“苟能俯而听之,存此一线之伦纪于宇宙之间,吾甘断吾头,而付诸樊於期之函,裂吾胸,为安金藏之剖其心肝。皇天后土,是临是鉴。”[28]辜鸿铭更是以坚守“发辫”“尊孔”等奇言怪行,被视为最保守的文化守成主义者:一方面是五四新青年派对顽固守旧者的指斥,周作人直指辜鸿铭为“北大顶古怪的人”;另一方面是同道者如罗振玉称其为“警世之木铎”“沉疴之药石”,更有丹麦学者勃兰兑斯肯定这种执著的精神为“自立脚跟,坚确求道”[29],甚至同时代的日本学者清水三安也称赞辜鸿铭备受世人讥讽的发辫“是一种精神的源泉”[30]。确切地说,“固执”正是五四反对派的正面价值所在。无疑,诸如辜鸿铭、林纾等都是热忱的卫道者,他们对孔教及古文的捍卫是出自真诚的信仰,用《中庸》所谓“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来评价他们是不为过的。郑振铎曾总结当时的五四新青年是“扎硬寨,打死战”的精神,这同样也适用于反对派。如果除去双方所持守价值的新旧不论,就其精神风范而言,都是值得钦佩的,陈独秀所讲“林琴南很可佩服”并不是出于揶揄,而是发自真心。正是新旧双方对自身价值的顽强持守与确信,才构成了五四时期健康的言论生态和有效的言说空间。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有了反对派的“坚持”和“固守”,才保障了这一思想论争场域的有效张力。郑振铎从积极的角度评价五四反对派的存在价值,他说:“在革新运动里,没有不遇到阻力的;阻力愈大,愈足以坚定斗士的勇气,扎硬寨,打死战,不退让,不妥协,便都是斗士们的精神的表现。不要怕‘反动’。‘反动’却正是某一种必然情势的表现,而正足以更正确表示我们的主张的机会。”[24]可以说,也正是论战双方的这种“坚持”和“固守”,才使五四有了更重大与更深刻的意义,正如有论者所指出:“五四文学产生的文学意义,不仅局限在对新文学新思想的倡导,更是打破了古代文学与近现代文学间对话的隔膜,搭建了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间的沟通桥梁,实现了文学自身现代意义的转型。”[31]因此,从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待这一新旧双方共同构成的思想战场,无论是革命派还是守旧派,无论是独踞虎溪者还是螳臂当车者,他们都有身为战士的可敬可爱之处。百年后回望五四,后人理应拥有这样的理性和从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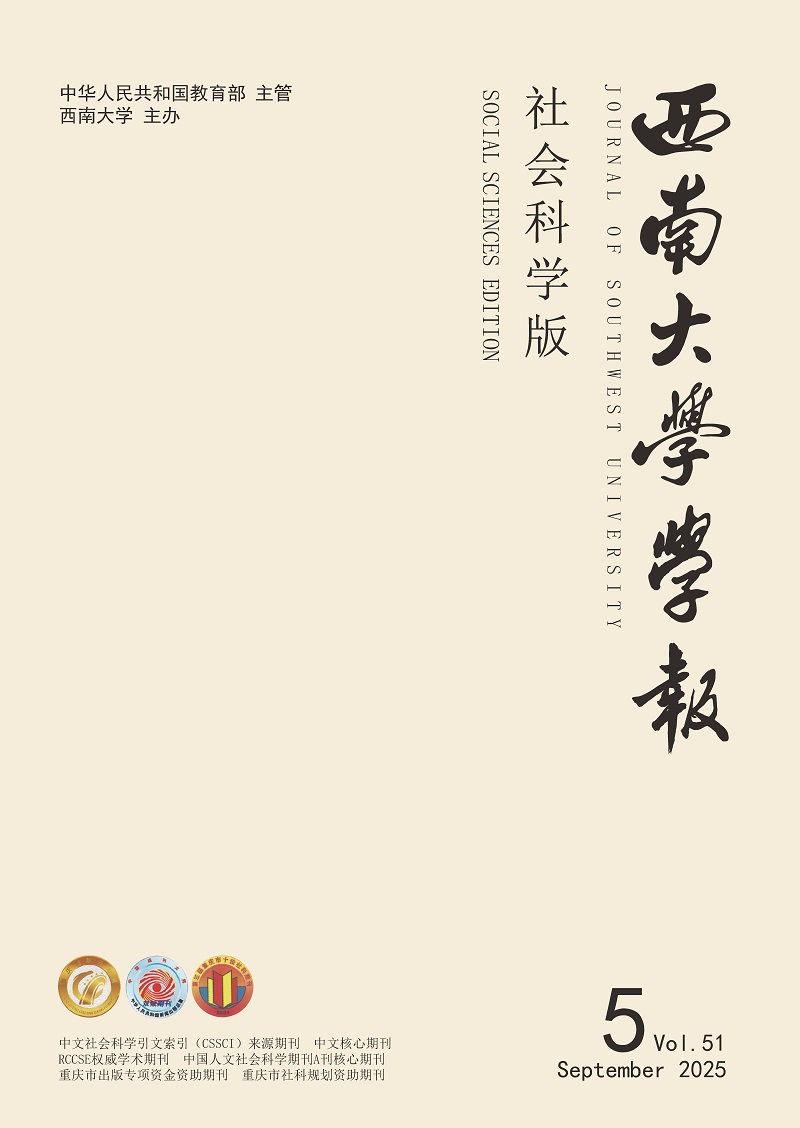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