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颁布南洋禁航令:
凡客商船只仍令照旧在沿海五省及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喇吧等处一概不许内地商船前去贸易,于南澳等地方截住。……其外国夹板船有来贸易者,照旧准其贸易,并令地方文武严加防范看守,不许生事……一切出海船只初造时,即令报明海关监督并地方官,及造完时地方官必亲验印烙,取船主甘结,方许给照,不许租与匪人,倘舵水人等私带粮米私卖外国,将船主一并治罪……如所造船只卖与外国者,查出将造船之人与卖船之人即行立斩,如所出去之人留在外国者,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个月,杖一百,该督抚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即行立斩。[1]丁编(下),康熙五十六年兵部禁止南洋原案,p353-356
南洋禁航令是指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 至雍正五年(1727) 十余年间清廷禁止中国商民前往吕宋、噶喇吧等南洋地区进行贸易的禁令。作为十八世纪初期中国海疆政策的一次重大变动,史学界对此颇为关注,对于南洋禁航令实施原因更是众说纷纭,笔者稍加梳理,主要有“勾夷”说、“文化冲突”说①、“粮荒”说②、“国际关系”说③等几种观点。其中,“勾夷”之说最为盛行。如刘凤云教授指出禁防“民夷交错”是康熙帝禁止南洋贸易的首要原因;[2]56-70何瑜教授认为“在西方殖民势力步步紧逼、沿海汉人不易管理的严峻形势之下,清朝统治阶级的戒备心理与日俱增,尤其是惧怕外国人与汉人频繁接触,相互勾结”;[3]郭成康教授也认为“禁南洋的实质是禁止闽广江浙商民前往‘红毛’、‘西洋’占据的噶喇吧和吕宋,同时严防已经定居南洋的华侨返回祖国。质言之,是对汉人与‘西洋’勾结颠覆满清统治的严密防范”。[4]持此论者颇多,①在此不一一陈述。
① 如王日根教授认为天主教传教士招集匪类,居心叵测,对清代海疆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见王日根.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155-156;刘凤云教授也认为康熙帝与罗马教廷的紧张关系趋于明朗化也对南洋禁航令产生了重要影响,见刘凤云.清康熙朝的禁海、开海与禁止南洋贸易[C]//故宫博物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56-70。
② 郭成康教授则认为康熙晚年特旨禁南洋贸易的根据之一是内地之米透漏出洋,卖与外洋海贼,见郭成康.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1997(1)。
③ 刘凤云教授指出禁防“民夷交错”是这项政策实施的首要原因,此外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策妄阿喇布坦正准备入侵西藏和康熙帝与罗马教廷的紧张关系趋于明朗化,都对南洋禁航令产生了重要影响,见刘凤云.清康熙朝的禁海、开海与禁止南洋贸易[C]//故宫博物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56-70。
① 持此论者还有卢建一教授,认为“居统治地位的满洲贵族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一直怀着戒备心理,才是采取部分海禁的真正原因”,参见卢建一.明清海疆政策与东南海岛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48;王日根教授认为康熙后期海疆政策转变的原因之一就是清廷担心沿海奸民下南洋与外敌勾结,参见王日根.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P155-156;冯立军也认为“他们害怕出外经商之汉人由于居住于国外,便与外人勾结串通,组成反清力量以对抗清政府的统治”,参见冯立军.“禁止南洋贸易”后果之我见[J].东南亚,2011(4);李金明教授也认为“担心移居国外之人与外国人互相勾结,共同反抗清政府的统治……才是康熙禁止南洋贸易的真正目的所在”,李金明.清康熙时期开海与禁海的目的初探[J].南洋问题研究,1992(2)。
“勾夷”之说如此盛行并不意外,雍正初年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在密折中谈到“臣查从前禁止商船前往西南各洋,原为防范外国夷人起见”。[5]第3册,298号,闽浙总督满保奏陈严禁商船出洋贸易折,p404-405雍正四年(1726) 闽浙总督高其倬在奏折中指出:“福、兴、漳、泉、汀五府地狭人稠,无田可耕,民且去而为盗。出海贸易,富者为船主、为商人,贫者为头舵、为水手,一舟养百人,且得余利归赡其家属,曩者设禁例,如虑盗米出洋,则外洋皆产米地;如虑漏消息,今广东贾舟许出外国,何独严于福建?如虑私贩船料,中国船小,外国得之不足资其用。臣请弛禁便。”[6]卷297,高其倬传,p10303其中“何独严于福建”可谓一语中的。
乾隆七年(1742),两广总督庆复在谈及南洋禁航问题时指出:“康熙五十六年,因吕宋、噶喇巴等口岸多聚汉人,圣祖仁皇帝谕令内省商船禁止南洋贸易”,[7]乾隆年间福建靖南人庄亨阳更是以“吾民作奸勾夷”[8]庄亨阳·禁洋私议第3册,卷87·海禁,p227六字来概括南洋禁航令实施之原因。仔细推敲庄亨阳的“吾民作奸勾夷”一语,“吾民”是指包含福建民众在内的中国沿海民众,“作奸”是指沿海民众造船违例、出洋携带违禁物品、滞留海外不归、接济海盗以及下海为盗等行为,“勾夷”则是指勾结洋人图谋不轨。诸多关于“勾夷”的史料联系在一起,“勾夷”之说似成确论。
HTML
-
禁航令在明清两朝并不罕见。清初,顺治和康熙时期共实施了五次“禁海”、三次“迁界”,②但是“南洋”禁航显得颇为诡异。清初的禁海、迁界涉及到鲁、江、浙、闽、粤濒海地区,中国海疆边民无一遗漏,“南洋禁航令”从表面上看是禁止中国所有地区的“客商船”前去南洋地区进行海洋贸易,实际却并不尽然。
② 清政府于顺治十二年(1655)、顺治十三年(1656) 二次颁布“禁海令”,顺治十八年(1661) 发布“迁界令”;康熙四年(1665)、十一年(1672)、十四年(1675) 共三次颁布“禁海令”,康熙十一年(1672) 和十七年(1678) 两次发布“迁界令”。
南洋禁航令出台之前,东南海疆问题已引起清廷高度关注。康熙五十五年(1716) 十月二十五日,康熙曾言道:“朕意内地商船,东洋行走犹可,南洋不许行走。即在海坛、南澳地方可以截住,至于外国商船,听其自来。”[9]第3册,p2233次日,康熙再次指出:“出海贸易,海路或七八更,远亦不过二十更,所带之米,适用而止,不应令其多带。再东洋,可使贸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第当如红毛等船,听其自来耳。”[10]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条上述所引史料中,“南洋”“海坛”“南澳”“匪人”“红毛”以及外国商船“照旧准其贸易”等词汇成为解读南洋禁航令的关键。
第一,福建商民是中国南洋贸易的主力。福建是中国早期与东洋、南洋各国开展海洋贸易的地区之一,南宋时与泉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达五十八个,元代与泉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已达九十七个,[11]358可见福建地区海洋贸易之盛和福建民众对海洋经济颇为倚重。南洋禁航之前,中国实行四口通商,江、浙、闽、粤各地海商可以进行沿海贸易以及东洋、西洋和南洋等远洋贸易。开海初期的对日贸易中,福建是首要之区。据学者统计,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 开海贸易后的四十余年间,赴日商船中福建640艘、浙江608艘、江苏524艘、广东187艘。[12]222康熙二十八年(1689),日本开始将赴日贸易船只限定为70艘,其中福建25艘、江浙15艘、江苏10艘、广东10艘、东南亚10艘,福建的对日贸易逐渐萎缩,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 日本颁布正德新令,将中国对日贸易船只定额为30艘,其中江苏10艘、浙江11艘、福建4艘、广东2艘,其余为东南亚各国船只。[13]25由此可知,由于日本政策变化,福建对日贸易在开海后的短期繁盛后迅速走向没落。自此之后,江、浙地区多集中于对日贸易,闽、粤则集中于南洋贸易,其中闽商又较粤商更为活跃。据日本《华夷变态》所载:“1686年,56号咬留吧(巴达维亚)船报告,当年从福州、厦门前往咬留吧的商船有10多艘;1687年,104号麻六甲(马六甲)船报告,当年从福州、厦门前往麻六甲的大小船舶有30多艘。”[14]208-209“满清朝廷很清楚,海外贸易对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和政治秩序是很重要的”,[15]118-119福建地区也不例外。禁南洋而不禁东洋,实则是禁闽商而不禁江、浙、粤三地海商。
第二,“在海坛、南澳地方可以截住”一语针对福建人的意味尤为强烈。海坛、南澳位于闽粤交界之地,除却沿海贸易外,江浙地区多去日本进行海外贸易,自然不会经过海坛、南澳等地,南洋禁航对其影响不大;广东地区则因“安南国与内地毗邻”,经两广总督杨琳奏请,广粤海商得以继续前往安南国等进行海外贸易,并且可以通过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地区进行商品贸易,南洋禁航对广东的影响也极为有限。日本正德新令(1715) 实施之后,闽商对日贸易急剧萎缩,而对于南洋的倚重愈发明显,因此在南洋禁航令实施之前,去南洋贸易以闽商居多。因此,在“海坛、南澳”可以截住的不是江、浙、粤商民,而是福建商民。
第三,康熙五十五年(1716),康熙帝在谕旨中指出:“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往年由福建运米广东所雇民船三四百只,每只约用三四十人,通计即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台湾之人时与吕宋地方人互相往来,亦须预为措置……不可不深思远虑。”[10]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条这道谕旨中“汉人难治……海贼之薮”、“福建……数千人聚集海上”、“台湾之人时与吕宋地方人互相往来”等语再次指向了“福建海盗”。所谓明代“海贼之薮”应是指郑氏集团余党前往南洋定居;而福建海域数千人聚集海上成为一大不稳定因素,台湾府作为福建省孤悬海外一府,清廷难以实现有效控制,这也再次证明了南洋禁航令实则是针对福建而设。
-
福建靖南人庄亨阳[6]卷267,儒林一·庄亨阳传,p13139-13140在《禁洋私议》一文中曾以“吾民作奸勾夷”来表述清王朝实施南洋禁航令的原因,虽是寥寥数语,却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勾夷”二字之人。“作奸勾夷”可有两种解释:一是理解为“作奸”与“勾夷”二种并列行为,二是认为该语是偏正结构,其重心是“勾夷”。
福建人的“勾夷”行为由来已久。在明代倭寇之患中,福建沿海商民的“勾夷”问题就十分突出。屠仲律在《御倭五事疏》中指出:“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宁、绍十五,漳、泉、福人十九。”[16]卷282,屠仲律,御倭五事疏,p56-60可见福建漳州、泉州和福州地区假扮倭寇以及“勾夷”的民众之多。嘉靖年间,“有佛郎机船载货泊浯屿,漳、泉贾人往贸易焉。巡海使者柯乔发兵攻夷船,而贩者不止”。[17]卷七,饷税考,p131另有著名的福建籍海盗李光头“出没诸番,分航剽掠”,[18]卷五,浙江倭变记,p322谢和“诱倭三千余人,船泊浯屿……贩海通番为奸利”,[19]卷453,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乙卯条吴平“寻入倭中为别哨,遂肆掠劫”。[20]卷38,征抚,p936明清交替之际,福建海患再起,既有以郑芝龙、李魁奇、刘香等海盗为代表的福建盗商团伙,又有以荷兰人为主的西洋海盗在中国沿海肆意劫掠,内外联合在所难免,这也会被清廷视为福建人的“勾夷”行为。然而,要想实现“勾夷”首先要有“夷”的存在方能实现联合。入清之后,真正发生过“勾夷”行为的反而是清廷,其曾经借助于荷兰之手打败了亦商亦盗的郑氏海上武装力量。此后,随着开海贸易,福建沿海民众的“勾夷”行为已不多见。
外国商船“照旧准其贸易”,表明清廷并不担心“夷”人和“夷”船前来中国。中国与南洋地区的海洋贸易中,闽粤地区相对江浙地区更为便捷,因而商贸往来也较多。但是闽粤二地有所不同,福建是中国商民出洋集中地,而广东则是南洋、西洋商船来华集中地。据统计,康熙四十二年(1693) 前,共有62艘外国商船(英国49艘、荷兰13艘)[21]到福建贸易,自此之后,“闽省数年以来竟绝无一至”。[22]第6册,p68因此,如果说清廷担心“勾夷”行为发生,为何对广东的南洋贸易不加禁止,其不怕广东“勾夷”行为发生吗?如果是担心闽人外出“勾夷”,为何不担心“夷”人来闽“勾”人,反而“照旧准其贸易”?由此可见,在清廷看来,“夷”并不是需要担心之事。
“作奸”与“勾夷”相比,无论是在词序和词意上面,都是“作奸”在前“勾夷”在后。就词意而言,“勾夷”是“作奸”的进一步行为,没有“作奸”就没有“勾夷”,且“作奸”较“勾夷”更为常见和多发。值得关注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作奸”行为都会带来严重后果,船只违规、携带违禁物品等行为虽然违背了清廷相关制度,只是海洋辽阔,此种行为实在难以禁绝,而且并不会对清廷的政治安全产生直接威胁,清廷对此也是不置可否,禁而不止遂成常态。而对于福建沿海商民接济海盗、下海为盗等行为,清廷则甚为重视,一则是有清初郑氏集团的前车之鉴,二来是其对社会的危害甚巨。“南洋禁航令”出台前,清廷担心的并非福建商民的“勾夷”行为,而是“作奸”行为。
-
实际上,令政府头疼的实则是福建沿海民众的“作奸”行为,无论是从发生的频率还是危害性来看,“作奸”行为都要远远超过“勾夷”行为。对于清政府而言,“作奸”行为虽有多种,但其破坏性亦有轻重之别。中国沿海商民出洋贸易,滞留不归在所难免,但是福建地区此种现象尤为突出。康熙二十四年(1685),即开海贸易后的第二个年头,靖海侯施琅就曾上奏称:“船户刘仕明赶缯船一只,给关票出口往吕宋经纪,其船甚小,所载货无多,附搭人数共一百三十三名……一船如此,余概可知……节次搭载而往,恐内地渐见日稀。”[23]卷下,海疆底定疏,p133福建沿海民众移民海外问题引起清廷关注,据史料记载,1686年,有11艘中国商船从福建开往巴达维亚,同船随行的还有800余名福建劳动力[24]。康熙五十六年(1717) 禁止南洋贸易时规定:“入洋贸易人民,三年之内,准其回籍,其五十六年以后私去者,不得徇纵入口。”[1]丁编(下),康熙五十六年兵部禁止南洋原案,p353-356滞留南洋不归对清廷而言较为严重,不仅会导致内地劳动力减少,更为严重的是南洋历来是中国海盗以及对抗政府者逃逸避难之所,如明代广东海洋巨盗林凤因受到广东水师追剿而率众远征菲律宾吕宋岛、广东潮州海盗林道乾逃亡柬埔寨,等等。明清之际,大批汉人移居南洋,耶稣会传教士塔卡德神父曾提及在巴达维亚地区约有四千至五千中国人居住,“其中多数是当鞑靼人统治中国后因不愿向其臣服到巴达维亚定居下来的”。[25]67清廷收复台湾后,“郑氏虽亡,其魁杰不愿入内地,仍留台湾,而赫赫为清人注目者,均乘船赴小吕宋、转至爪哇、马六甲等处”。[26]91至1700年,“约有一万名中国人居住在巴达维亚及其邻近地区”。[27]143如果仅仅是郑氏集团余党聚集南洋也还无妨,而在实施南洋禁航令后,福建民众偷渡南洋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这才是清廷最为担忧之处。雍正五年(1727),浙闽总督高其倬还曾奏报偷渡出洋问题:出洋商船每船皆私载200~300人,到彼之后,照外多出之人俱存留不归,更有一种嗜利船户,竟将游手之人偷载至400~500人之多,每人索银8两至10两,载往彼地即行留住,此等人大约闽省占60%~70%。[22]第46册,p27福建地区偷渡出洋问题仍是相当严重。
康熙二十三年(1684) 开海贸易后,由于出洋商船“无分大小,络绎而发,只数繁多”,[22]第46册,p40清廷即对船只大小、携带米粮、武器等进行了严格限制。规定虽然严苛,但是不易操作,不免流于形式,因而违规造船、携带违禁物品在南洋禁航之前已是常态,福建海商违禁出洋之事时有发生,清廷对此心知肚明。康熙帝就曾指出:“闻泛海者,凡遇风浪及鱼虾等物,还须用炮。海岛外国既有火炮,有何禁止之处?”[9]第2册,p1322同时,其他省份也都存在此类问题,并不拘限于福建一省。如“许用载五百石以下船出海贸易”,[28]卷239,官税“若有违禁将硝磺、军器等物私载在船出洋贸易者,仍照律处分”,[10]卷117,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丁巳条“内地贸易船只防护火炮军器等项,照船只大小、人数多少,该督抚酌量定数,起程时交与收海税官员并防守海口官员查照定数,准其带往,回时照原数查验,其一应禁物不许私行夹带等”。[29]丁编,第8本,康熙三十三年户部禁止商人在外国造船带军器原案,p756然而,为了追求更多利益,福建商人与浙江商人闹出了“有伤体面”的“信牌案”。[30]1715年日本实施正德新令,正德新令也被看作是优待江南商人、打压福建商人的禁令。其规定对赴日贸易的中国船只实行“信牌”制度,对来自中国沿海的江浙闽粤等地的船只数量进行限制和配给,其中对福建商船影响甚大,1715年赴日船只只有1艘,1716年只有2艘。康熙五十五年(1716),未领到信牌的福建籍船头庄运卿、刘以玖、谢叶运等人起诉浙江部分船只接受带有日本年号的信牌,实属忤逆朝廷而追随日本。由于利益纠葛,此案拖延三年未决。正德新令也导致福建商人不得不从与日贸易中退出,愈发依赖南洋贸易。
康熙曾言:“吕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处藏匿盗贼甚多,内地之民希图获利,往往船上载米带去,并卖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处之人,粮食、船只、人员外流严重。”[9]第3册,p2324康熙五十五年(1716),清政府得到地方政府报告,称大米大量出口以及出洋船只出多回少,基于此,康熙认为:“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多至千余,出洋贸易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皆卖在海外,赍银而归。”[1]丁编(下),康熙五十六年兵部禁止南洋原案,p353-356康熙五十七年(1718),福建浙江总督满保称:“海洋大弊,全在船只之混淆、米粮之接济;商贩行私偷越,奸民贪利窃留。”[10]卷277,康熙五十七年二月甲申条
-
福建民众“作奸”行为最为严重的应属沿海民众接济海盗或下海为盗两种情形。清初,清廷曾三番五次实行禁海迁界政策,康熙帝直陈该政策与海盗问题有关:“江南、福建、广东濒海地方,逼近贼巢,海逆不时侵犯,以致生民不获安宁,故尽令迁移内地。”[10]卷4,顺治十八年八月乙未条清初名臣姚启圣(1624-1683) 也表达了同样观点:“福建海贼猖獗而议迁界”,又因“贼势蔓延,迁福建一省不足困贼,故并迁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五省之界。”[31]293深受康熙欣赏的近臣杜臻也指出迁界禁海是因为“海寇陆梁”问题。[32]史部,传记类,第460册,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1,p955由此可见,中国海盗尤其是福建地区的海盗行为是引起清初顺治与康熙两朝“禁海”与“迁界”政策的直接原因,也是主要原因。
福建地区沿海民众接济海盗的“作奸”行为由来已久。《宋会要》记载:
二广及泉、福州,多有海贼啸聚,其始皆由居民停藏资给,日月既久,党众渐炽,遂为海盗之害。如福州山门、潮州沙尾、惠州潀落,广州大奚山、高州、碙州,皆停泊之所。官兵未至,村民为贼耳目者往往前期报告,遂至出没不常,无从擒捕。[33]兵13之22-23,p6978-6979
明代仇俊卿曾云:“沿海地方人趋重利,接济之人在出皆有。”[8]第3册,卷87,海防·事宜,p219在福建漳州的诏安梅岭地区:“有林、田、傅三大姓,共一千余家,男不耕作,而食必粱肉;女不蚕织,而衣皆锦绮,莫非自通番接济为盗行劫中得来?”[34]卷2,呈福建军门秋厓朱公揭,伍辑20-111“一村约有万家,寇回家皆云做客回,邻居者皆来相贺,又聚数千,其冬夏至柘林,今春又满载仍回漳州去矣。”[35]卷4此中亦隐约透露出漳泉民众下海为盗信息。
清初,以郑成功为首的海上抗清活动持续不止。清廷认为郑氏集团之所以如此顽抗,根本原因在于福建沿海民众的接济等“作奸”行为。“海寇盘踞厦门诸处,勾连山贼煽乱地方,皆由闽地濒海居民为之藉也。”[32]史部,纪事本末类,第354册,平定三逆方略,卷36,p252“一切需用粮米、铁、木、物料皆系陆地所产,若无奸民交通,商贩潜为资助,则逆贼坐困可待。向因濒海各处奸民、商贩暗与交通,互相贸易,将内地各项物资供送逆贼……凡杉、桅、桐油、铁器、硝黄、湖丝、紬绫、粮米一切应用之物,俱恣行贩卖,供送海逆,海逆郑成功贼党于濒海各地方私通商贩如此类者,实繁有徒。”[1]丁编(上),严禁通海敕谕,p257
康雍年间福建漳浦人蓝鼎元(1680-1733) 曾指出,海盗常在海上行走,粮米物食、火药军器等必需接济,“匪赖逃藏外洋,非能不食而操舟,徒手而行劫,由内地奸人接济之也……出没无时,贼与小旗为号,瞭见即为接应。”[36]卷83兵政十四·海防上,严如煜,沿海团练说,p262福建安溪人李光坡(1651—1723) 也认为:“……舰船必资料粮,伺掠米商能得几何?所恃渔舟,阴载内米,与之交通”。[36]卷83,兵政十四·海防上,李光坡,防海,p256蓝鼎元进一步指出,“向来南澳地方,皆守港哨船接济,如东陇港、南洋港、樟林港、澄海港、沙汕头、海山、柘林、井洲,各处哨船,无一不接济者。而东陇、海山、南洋三处为尤甚”,因而发出感慨:“民船犯禁,官兵可缉;官船作弊,孰敢撄锋?”[36]卷85,兵政十六·海防下,蓝鼎元,论镇守南澳事宜书,p289-290由于接济行为的隐蔽性和广泛性,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清政府为之头疼不已。
-
福建沿海民众“作奸”的极端行为即是下海为盗。海盗与海洋贸易活动如影随形,福建地区发达的海洋贸易必然吸引来大批的海盗,无论是在海洋贸易的起始地还是沿途航线,都可见到福建海盗活动的身影。
康熙二十年(1681),福建巡抚吴兴祚奏请开海贸易,但被康熙所拒绝,其理由是“海寇未靖”。[10]卷112,康熙二十二年十月丙辰条康熙二十二年(1683) 收复台湾后,康熙即准备开海贸易:“先是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10]卷115,康熙二十三年七月乙亥条福建的海盗问题成为清廷衡量“开海”与“禁海”政策的重要因素,福建海盗问题与清廷海疆政策关联之深可见一斑。
开海贸易之后,对于福建海盗问题,康熙起初并未在意。康熙四十三年(1704),部分大臣针对东南海疆有海盗“春冬啸聚海岛、秋夏扬帆出掠”之事,提出禁海的解决方案,康熙皇帝却一口回绝:“朕初以海寇故,欲严海禁,后思若辈游魂,何难扫除,禁洋反张其声势,是以中止。”[10]卷215,康熙四十三年正月辛酉条康熙四十七年(1708),都察院都御史劳之辩上疏:“江浙米价腾贵,皆由内地之米为奸商贩往外洋所致……申严海禁,暂撤海关,一概不许商船往来……私贩绝而米价平。”康熙皇帝再次拒绝海禁:“闻内地之米贩往外洋者甚多,查获私贩之米,姑免治罪,米俱入关。”[10]卷232,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庚午条康熙五十年(1711),给事中王懿以海上有盗请禁海洋贸易,康熙帝仍然不允:“海盗盗劫与内地江湖盗案不同,该管地方文武官如能加意稽查,尽力搜缉,匪类自无所容。岂可因海洋偶有失事,遂禁绝商贾贸易!”[10]卷245,康熙五十年正月乙卯条康熙五十二年(1713) 三月,户部尚书张鹏翮上疏:“闽省沿海地方,值春秋二季,令该总兵官亲身巡查,有海贼逃匿者,即行文广东、江南、浙江等处地方协力擒剿”。五十三年(1714),巡抚张伯行也屡次上奏海中有贼,并请严出海船只的稽察,凡出海商船与渔船,一律在船身和篷上刻写“商渔”字样。[8]第3册,卷87,海防·疏议·巡抚张伯行商渔船只编号疏,p233-234由此可知,直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虽然大臣屡奏海盗事并要求实行海禁,但康熙帝并不认为海盗已对海疆构成威胁,也不主张因此禁止海洋贸易。有学者基于此而做出结论,“康熙对海上劫盗以及贩米出洋并不以为意,因此,其所述禁洋理由,并非其真正目的,只不过是他禁洋的托辞而已”[37]。
康熙后期,随着海上贸易日渐繁多,福建海盗渐趋活跃,其活动范围之大超出了康熙帝的容忍底线。
康熙四十二年(1703) 九月,康熙帝在敕谕大学士时讲到:
山东地方称有海贼坐鸟船二只行劫,朕思山东不能造鸟船,必从福建、浙江、江南造成而来。历年福建商船于六月内到天津,候十月北风始回。朕因欲明晰海道,令人坐商船前往,将地方所经之路绘图以进,知之甚悉。今欲知海贼之源,但令往福建、浙江及江南崇明等处察访即得之,若在山东察访必不能得。目下冬令将届,正值北风,海贼不能久留于直隶山东,必已向浙闽路去。俟明岁船只可行时,令有水师海船之省入各海岛搜剿。[10]卷213,康熙四十二年九月戊午条
据康熙帝所言,鸟船是由福建、浙江、江南等地制造而成。日本学者松浦章考证鸟船为清代四大帆船之一,是福建沿海民众开发出来的海船[38]110。以此推测,福建海盗已来到了山东省海面进行抢劫活动。在山东地方志文献资料中,也有相关记载:
康熙四十一年(1702),海贼寇威海卫。
康熙四十二年(1703) 七月,海贼寇威海卫,总兵王文雄躬往调度,放炮一日,贼于船中演剧自若。文登营副将张陈武欲乘舟火攻,文雄不许,相持数日贼自扬去。
康熙四十四年(1705) 八月十二日,贼舟数只泊灵山卫前,欲犯卫城,次日,胶州营副将金国正领兵至,以炮击之,寻遁去。
康熙四十八年(1709) 六月,风雨坏贼舟于黑石阑,贼首杨阿大等觅食近村,内有为其所虏者,潜报卫汛,饬营兵乡勇拿获十九人。同年秋,山东水师出洋巡哨,逮捕海盗五十八人。
康熙五十一年(1712) 十月十七日,海贼抵文登之鸡鸣岛,水师后营游击腾国祥率舟捕之,贼艇围攻纵火,国祥死战,力竭死之。[39]222
康熙四十九年(1710) 八月二十五日,文登营副将报称.“有北来鸟船七只,沙船一只,泊成山头外洋等处,二十六日,贼船移入棉花岛,官兵攻打,又遁出外洋。”[40]57-37
虽然多数史料并未提及出现在山东洋面海盗的籍贯,但是却提到了海盗所乘船只为“鸟船”,因此可以确定这些海盗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福建地区。
另有部分资料则直接提及福建籍海盗:
康熙四十三年十月,籍贯福建漳州平和县的海盗徐容等人被捕;[8]第7册,卷268,杂录·国朝外纪,p519
康熙四十八年七月,九名福建海贼抢劫宁波商人船只;[41]26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宁波知府蒋学和象山知县逮捕到二十六名海贼,其中福建籍的有七人;[41]34
康熙四十九年,福建漳平籍海盗陈五显聚众二千余人谋乱;[8]第7册,卷268,杂录·国朝外纪,p519
康熙四十九年,福建海盗郑尽心及同伙百余人被捕;
康熙五十年三月,福建海贼同党余国梁及同伙八十余人被捕;[10]卷245,康熙五十年三月丙申条
康熙五十一年,招抚福建海盗团伙陈尚义等百余人。[6]列传263,循吏一·陈汝咸传,p12976
海盗问题虽然日趋严重,但是康熙帝并未马上关闭海洋贸易,而是寄希望于招抚和剿杀两种策略。然而在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清廷遇到了极大麻烦。首先,在剿杀海盗过程中,清廷水师官兵缉捕海盗能力之低下暴露无遗,与海盗作战无法取胜,“官兵出哨,或贼船四、五只,官兵船一、二只,势不能敌,舵工又不奋力向前,将领亦无可如何,不过尾随而已,何能剿灭耶?”[10]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条其次,水师官兵的贪腐行为也渐趋严重,“横索钱财,方令入口”。[10]卷256,康熙五十二年十月丙子条水师官兵如此不堪重用,清廷只得采用招抚之策。福建海盗郑尽心、陈尚义、陈五显等先后被清廷招抚后,陈尚义被安插至盛京水师营中“看守地方,巡防海洋”。[10]卷255,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乙卯条招抚之策初见成效,然而康熙帝没有料到,这些福建海盗“不思悔改”,公然抢劫军器并杀死官兵,再次下海为盗,这对于标榜“为政尚宽”的康熙帝而言,不啻是莫大嘲讽,对其打击也非同小可。同时,“陈君元一船逃至广东外洋,不知踪迹”,清廷必然会怀疑其是否逃避到南洋地区,而这也极有可能会导致其海疆政策突变。
与此同时,在福建厦门地区发生了一起“夷人”抢劫事件。闽浙总督满保曾奏报称:“福建厦门地方……旺交料国一商船贸易完毕返回之时,因商人黄骤欠其所买丝未来交货,便强行劫持李德兴商船,出大旦海口而去,提督施世骠派兵追之,却毫无踪迹。”[42]1079洋人抢劫汉人事件虽属个案,但是清廷则需未雨绸缪。仅仅福建一地的海盗就让清廷费劲周折,而现在夷盗再起,“勾夷”已是祸在眼前,清廷自然无法置之不理。
-
南洋禁航令自颁布实施后就受到各方质疑与反对,雍正继位之初则继续贯彻执行,并赞曰:“十数年来海洋平静,最为得法,惟宜遵照定例,不可更张。”[5]第3册,298号,闽浙总督满保奏陈严禁商船出洋贸易折,p404-405不难看出,“海洋平静”才是清王朝关心的重点,而且正是由于南洋禁航令的实施才带来了“十数年来海洋平静”。福建与同处于沿海地带的浙江和广东相比,海疆安全问题最为突出,无论是明清之际的东南海寇,还是与清廷对抗了数十年的郑氏集团,这些来自于福建的海上力量均对清王朝的统治构成了较大威胁,十八世纪初期的福建海盗虽然无法与明清之际相提并论,但是清廷对福建海盗的警惕之心却难以解除。
南洋禁航令出台之时,福建海盗活动有加剧之势,至南洋禁航令废止时,福建海盗活动处于低谷。正如山贼不会完全从社会中消失一样,偶发的海盗事件对政府、沿海社会以及海洋贸易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雍正年间,中国前往巴达维亚的商船数量已达20余艘,甚至超过了禁南洋之前16艘的规模[43]。商船数量的变化,也再次证明了南洋禁航令实施的原因并不是来自“夷”的威胁以及海洋贸易的管理难度,福建海盗才是清王朝实施南洋禁航令的根本原因。正如乾隆年间福建人蔡新所言:“南洋之禁,不过谓各口岸多聚汉人,恐酿海贼之阶,非恶南洋也。”[44]卷4,答方望溪先生议禁南洋商贩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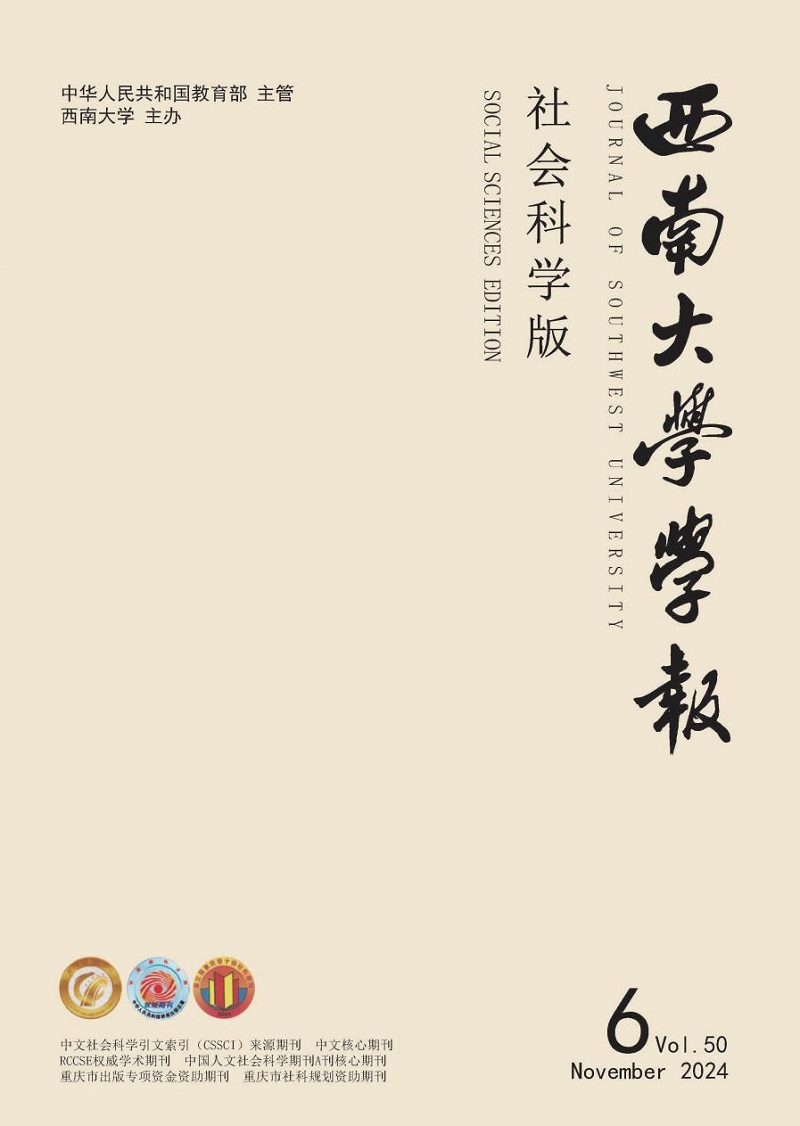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