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经济到文化、从生态到心理、从阶级到性别,当代西方左翼思潮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都提出了激进看法。围绕这些论题形成的大量新话语,从后福特制批评、后殖民研究再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学等,在全球知识界广泛扩散,亦受到国内相关领域的追捧。然而,在这一现象背后,存在着一个需要追问的事实:激进话语的增生扩散恰恰掩盖了政治上的退却。不复存在一种以改造世界为旨趣的统一的左派知识纲领,左翼思潮内部的巨大争论甚至使得“左翼”本身成为“不和”的符号。我们将之称为当代西方左派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困境。左翼思潮从资本主义替代到现代性批判之旨趣转换,以及在深层理论逻辑上,反本质主义立场造成的在基本价值和理论前提上的共识缺乏,乃这一困境的基本原因。因此,解决这一困境的基本思路是,回到马克思主义,通过当代重大政治议题回到解放议程,凝聚新的政治承诺。
HTML
-
一般认为,1968年法国以学生运动为代表的文化造反失利,标志着传统左派的困境以及卢卡奇奠定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僵局。在这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多样化的探索。在新的探索过程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1973年)和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1979年),非常明确地宣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过时”,从而为后马克思主义激进理论打开了新的理论视域。前者通过危机问题指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社会诊断的无能[1],后者则通过阐明宏大历史叙事的失效而宣布进入后现代历史[2]。新的动态非常明显地给左翼事业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用利奥塔的话来说,“从革命思想和行动那里继承下来的政治从此失业”[3]。其后,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公开出版,直接拉开了“后马克思主义”大幕。该书在理论逻辑上以承认哈贝马斯和利奥塔为前提,主张通过民主政治(即现存制度)“激进化”(即“彻底化”)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是尴尬的,所以引发了重大争论。然而,争论不仅没有结果,而且从理论上展示了一种重大问题,即西方左派在理论前提、现实判断和“革命”战略上都缺乏共识,西方马克思主义陷入了激烈的多元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前苏东的瓦解加剧了这一理论状况,以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为标志①。
① 关于这一变迁历程的描述,参阅胡大平:《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节奏和变奏》,《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0-14页。
综观当代西方左翼激进理论,多元化乃是其显著表象。特别是大量来自社会空间和城市研究、地理学、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左翼学者主张放弃传统马克思主义立场而以多元价值作为新的前提。例如,来自地理研究的阿明和斯瑞夫特便主张左派没有固定不变的立场,必须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兼容一切差异和多元诉求,从而为争取再分配的斗争建立更宽泛的基础[4]。然而,这带来了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共识困难,西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定义政治的能力,从而仅仅维持了不切实际的“左派”虚名。作为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戴维·哈维就认为,在这种状况下,“左/右(激进/反动、进步/保守、革命/反革命)的修辞在今天就没有多大用途”[5]。实际上,主张包容一切的多元主义立场和告别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主张在政治和逻辑上并没有多大差异。
通过各种争论可以发现,真正的问题是:在今天如何理解政治。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游移,不仅见证了由于缺乏直接干预当代资本主义的机会而面临的实践困境,亦表明了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反本质主义理解的逻辑难题。这个难题位于为反本质主义和反主体性哲学提供支撑的结构主义思潮的内核之上。当然,这也是一个矛盾。我们看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所称的“历史”,福柯所称的“社会”,拉康所称的“主体”,都不是本质主义意义上的“物”,这为反现代性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并因此成为当代激进理论的核心资源。但是,在重新寻找改变世界策略的过程中,这也同时使得任何维持在既定目标上的价值诉求(例如传统的“乌托邦”和社会主义等)都不再可能实现。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语境中生发出来的,他们非常明确地强调,具有本质规定的“社会”(society)概念是不可能的,而主张以属性规定的“社会”(Thesoical)术语来替代它;在他们看来,“社会”是包含着对抗的不可能性目标[6]。这在齐泽克那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他借助于拉康反本质主义逻辑把“不可能性”或“基本对抗”置于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学的前提之上[7]。这意味着左派的事业成为无止无尽的批判,再也与建设无缘。拉克劳、墨菲、齐泽克、阿明和斯瑞夫特,以及更广泛的各种以差异、多元和少数名义进行批判的激进社会理论家无不如此。
没有前提保证的理论必然产生没有实际承诺的政治诉求,这正是当代西方激进左派面临的最重要难题。关于这个难题,也不是没有人意识到和讨论过。戴维·哈维重提“革命人道主义”的政治实践设想[8],布若威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社会学等,都是具有纠偏意义的重要动向。朗西埃则从理论上阐明,“重新定义政治”乃是新左翼的基本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朗西埃以学院化的方式指出后马克思主义反本质主义“政治”的虚假性,从而提出左翼理论重新政治化的构想,同时亦表明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左派反“共识”之命运。在朗西埃看来,与主流民主政治一样,主张从“政治”(名词)走向“政治的”(形容词)后现代政治学,其核心都在于取消了承诺,从而从根本上取消了政治本身。因此,他重新提出政治哲学所面对的基本主题,试图以此重建激进左翼的政治。在朗西埃看来,真正的问题是通过政治哲学的预设来回应取消政治本身的共识性实践(即权力实践),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应当具有自己的位置[9]。
那么,如何走出这种困境,以便重新把握政治呢?在我们看来,这就需要深入当代重要的政治议题,解释社会变迁逻辑,从而打开新的历史视野和斗争地平线。
-
新的政治实践首先总是与新的政治议题而不是与元理论进展联系在一起的,后者往往是适应于前者而变化的。那么,如何理解当代最重要的变迁呢?在总体上,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几乎说遍了所有能够政治化的议题,从跨国生产到金融危机,从种族歧视到性别歧视甚至性取向,从自然(生态)到文化多样性,等等,这使得理论看起来十分激进,也使得世界看起来愈发需要改造。在国内相关研究中,不仅生态、性别等已经成为主流论题和立场,而且包括齐泽克、阿甘本、巴迪欧等古灵精怪的新学院激进话语也都得到相当多的关注。不过,我们也已看到,这些话语中的多数,不是被权力收编成为“政治上正确”的话语(如生态、性别、性和种族等),就是与实际政治过程无涉(如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等)。也就是说,要么左派无力主导这些议题的发展,要么不能使其政治化。因此可以说,这些虽然是左翼话语,但它们却不是左翼能够主宰的直接政治议题。套用鲍曼的话来说:“弥漫于公共领域中的个别怨气充斥着私人的苦恼与焦虑,它们仅仅展现于公共领域之中,却无法转变成公共问题。”[10]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左派理论家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寻找政治”的呼声一直很高,从传统左派要求“阶级政治的回归”,到左派新锐“回归正义”的呼吁,虽然内容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重建政治承诺。在此语境中,鲍曼的《寻找政治》别有意味。在鲍曼看来,政治乃是公共的事业,当现代性丧失自己的承诺,政治事业便需要重建新的承诺,而重建包括三个至关重要维度:定义公共空间、掌握政治议程和清晰表达新的愿景。我们在此选择当代激进左翼思潮提出的四个重要但仍没有得到国内研究充分重视的议题予以简单的分析。在我们看来,这些议题分别从技术(生产力)、全球化(共同体)、地方(差异和平等)以及阶级四个维度描述了当代政治面临的核心问题。
-
这个问题的揭示,是法国当代思想家维希留的最杰出贡献。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维希留一直关注速度。在他看来,速度(或效率)乃是人类的存在原则,交通通讯技术不断地改变人类的存在状况和刷新人们的时空经验。在今天,不断加速的技术革新最终造成了以“实时”为支配原则的运动,而远程行动同时消灭了地点和时差,创造出远程在场。这种状态展现出这个逻辑,即“速度乃时间之光”“纯粹速度同时成为高度和长度,成为绝对权力的全部”[11]。在此背景中,此时此地概念消失了,代之一种远程客观性(teleobjectivity),世界成了“别处”;地球则被远程技术污染,被它压缩和还原到零,世界成为荒漠[12];而人则成为为了安全而等待死亡的人。所以,在维希留看来,人类处在速度虚无主义氛围之中,而新的速度虚无主义对世界真实面貌的破坏远比技术虚无主义要大[13]。这就深化了从海德格尔到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社会技术统治的批判,阐明了当今世界暴力的实质。可以说,维希留极为准确地捕捉了为效率而不断“进步”的技术持续刷新人类存在根基的逻辑,并且描述了其终极图景:速度的暴力已经变成了世界的命运和目的[14]。维希留从新的角度解释了虚无,一种在尼采之后形成的“新虚无”。这种虚无不再是最高价值的贬值,而是平凡事物的贬值,即世界的垃圾化。就这一点而言,维希留从技术发展的谱系和逻辑说明了今天何以普遍产生了当下不真实和生活在别处的感觉,在整个20世纪技术批判史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拓展。这种拓展提出了我们今天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技术本身已经趋于它的极限,从而突破了发展它们的人类控制。
-
关于全球化或全球治理,已经成为一个持续了20多年的陈词滥调,但鲍曼对于这个话题的分析却令人眼前一亮。他不仅基于流动的现代性思想分析了全球化带来的阶层冲突和个人流离失所的命运,而且从不同维度提出了通过知识介入而重建政治的构想。前述“寻找政治”框架代表着其提出重建公共性(政治)的完整逻辑。在鲍曼看来,今天是一个高速度和加速度的时代,是一个缩短承诺期限的时代,是一个灵活多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保质期”也大大缩短。因此,我们丧失了文明的确定性,丧失了它承诺要提供给我们的更多可靠性,代表集体的公共空间销蚀了,“共同体”成为一个问题,成为一个悖论性观念,既是失去的天堂,又是重回天堂的路。与本能地诉诸多元主义价值和抓住生活政治的许多激进左派不一样,鲍曼尖锐地指出,市场法则和当代权力性质造成了权力本身与现行政治的分离,个体从政治公民转变为市场消费者,并且最终导致个人生活的碎片化和共同体的瓦解。因此,他要求从政治机制的角度把握议程和法则,并把定义公共空间作为焦点问题。这样,鲍曼实际上便描述了重建共同体的过程,而不是流于公共价值的空洞呼吁。就此而言,他的分析比绝大多数左翼学派都具有深度,同时又更接地气。这也就不难理解,正是在他这里,被许多左翼理论家奉为圭臬的文化多元主义和生活政治遭到了最强烈的质疑。鲍曼认为,文化多元主义乃是“知识分子适应新的现实的一种调适方法。它是一个屈服性的和解宣言:人们屈服于新的现实,而不是去挑战和质疑这种现实——他们听任事物‘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15]。也就是说,如果今天的政治问题是缺乏共识,那么文化多元主义恰恰是在抗议名义下巩固现行的制度。
虽然鲍曼的讨论在语气上相当温和,但其分析从来不缺乏力度,并且对问题本身的判断极为深刻和具有感染力。可以说,鲍曼禀承了法兰克福学派以解放为最高目标的社会批判思路,并且提供了一个通过知识介入来推动解放议程深入的卓越案例。他承认,今天人类解放的前景与马克思清晰地描述的人类解放前景是大为不同的,不过,他强调:“卡尔·马克思几乎两个世纪前对资本的双重指控——它的浪费与道德上的不公正——都没有失去任何话题性。发生变化的只是浪费与不公正的幅度:两者如今都已获得了全球范围之规模。解放之艰巨任务也同样如此;正是这一解放的迫切性,促使了半个多世纪前法兰克福研究所的建成,并继续为它的劳作引领导航。”[16]换句话说,统治依旧,解放诉求依旧,改变的只是问题的严重性和解放的紧迫性。鲍曼主张,在今天必须从人类生存和全球尺度来考虑“命运共同体”这个根本问题,这就为全球化时代的左翼政治确定了核心议题。
-
在全球化语境中,地方观念在不同的领域——从人类学到地理学和文学——不断得到重申,因为它似乎是另类现代性之源。不过,现实的困境是,当我们依赖地方想象另类现代性时,同样见证了基于普遍维度建设另类现代性的困难,即不能直接想象在全球层次上创造与现行资本主义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然而,这正是全球化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如果不面对这个困难,将可能产生对地方意义的误读。从文化或传统角度为地方辩护的文化现代性或者文化多元主义的问题便出在这里。鲍曼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批评已经指认了这一点。当然,这并不是否定地方的意义。勿宁说,重新理解地方构成当前左翼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
许多左派理论家认为,在今天,现代性本身已经处于散逸状态,它在各地的经验并不均衡。或许,各地以自己的方式构建自己的现代性,这正是全球化带来的基本后果。换句话说,全球化是一种历史的、不平衡的乃至于地方化的进程。正是这一原因,在今天,地方的生产成为至关重要的政治。诸如阿尔君·阿帕杜莱的“消散的现代性”(modernity at large)和德里克的“全球现代性”概念,都是捕捉这个问题的不同努力。它们共同的地方在于试图通过全球交流真正瓦解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遗产,不同的是,前者以细腻的人类学笔触描述来自印度和散居的经历,而后者则更关注包含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社会历程。
在阿帕杜莱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回到本质化的地方,而是提出地方性生产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困难[17]。阿帕杜莱以印度的经验说明,地方能够打破自身的狭隘性加入全球共同事务,从而创造不一样的全球机制。这个思想在德里克那里得到响应。在德里克看来,尽管现代性源自欧洲,它的扩展经历了殖民过程,但在今天却形成了一种包容了前殖民地和边缘化人民的全球现代性,即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一方面,非欧美社会的问题同时是欧美社会的内部问题;另一方面,当以文化名义挑战欧洲的统治地位时,欧洲中心主义早已是其他社会现代性的一个问题。因此,需要不断质疑现代性的边界,即现代性的场域[18]。这是站在超越地方的普遍主义立场上重新审视现代性的尝试。这种视角的关键之一便是,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乃是欧洲现代性的产物,因此对它们的反思便成为真正站在普遍立场思考非资本主义现代性之理论前提。也因此,在这种视角中,“非殖民化不应仅限于从欧美殖民主义中逃脱出来,而躲进某种想象出来的民族文化当中去,它应该进一步质疑由民族国家权力所支持的民族文化观念的殖民内涵”[19]。德里克认为,不能以另一种中心视角或民族主义立场来设想对现代性的替代,真正的政治乃是全球现代性的探索。
近年来,来自非洲的马姆达尼的相关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通过非洲和美国历史经验的对比,马姆达尼认为,原住民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政治的结果。在今天,新型的殖民统治不再是传统的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而是定而治之(define and rule),即将原住民分割成不同人群,并定义和规划他们的文化传统和主体性。基于这一点,他提出了对非欧国家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否通过移植所谓西方先进经验就能够实现落后民族的繁荣与自由。在他看来,“替代方案是思考我们自己的企望,不只是从外头引进理论,视之为另一种技术转移式的发展计划,而是换上了不同的且更高的目标:理论化我们自己的现实”[20]。因此,他致力于对移住民关于世界多元主义声称和原住民对起源与本真性迷恋的批判[21],试图推动第三世界在全球化条件下独立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思考。
上述例子都是在全球化语境化下重新审视地方性的努力,与过去不一样的是,他们不再试图回到假想的本质化的地方,而是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独立自主创造地方未来这个重要的问题。
-
1968年4月,霍克海默在自己的文集《批判理论》序言中写道:“二次大战结束后,那种认为工人的贫困在不断增长的观念……早就成为抽象的东西或幻想,至少被年青人鄙弃为过时的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时代劳工和雇工的生活条件是赤裸裸压迫的结果。今天,它们则成了工联组织的主要课题,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集团之间讨论的话题。无产阶级的革命冲动,早就变成了在社会框架内的现实主义行为。至少在人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已被溶合到社会中去了。”[22]在某种意义上,这为1968年5月巴黎的学生运动做出了一个注释:学生而不是传统的工人成为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主体。因为这一势态,在理论上,告别阶级重新寻找革命主体和道路的探索构成20世纪60年代以来激进左派思潮的政治诉求。在某种意义上,阿尔都塞研究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问题,列斐伏尔谈论空间政治学,还有各种文化政治学,都是试图在工厂或直接生产过程之外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秘密并打开新的斗争空间的努力。然而,无产阶级为什么不革命了,以及工厂将在新的斗争中具有何种可能的表现,这些基础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
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若威在某种意义上曾打开过这个话题。布若威困惑于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新的世界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以极端的方式呈现,另一方面反抗却“悖谬般地消失了”。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通过深入非洲、东欧以及美国的工厂,他在1979年完成了题为《制造同意》的分析著作,揭示了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劳动力内部市场中,利益何以造成竞争并产生对规则本身的同意;在企业层次上,劳动代表对企业事务的参与如何使控制从专制形式转变成霸权形式;等等。在总体上,他认为正是企业实际运行和劳动过程的变化造成了工人阶级的同意和资本家的霸权。在他看来,国家、学校、家庭、文化以及个性并非不重要,但唯有通过把劳动过程的转变作为起点,它们的重要性才能被评估。同时,他认为,超越直接利益的工厂内部的意识形态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强调说:“意识形态斗争带领我们超越资本主义、超越需求的专政。它们是斗争,但不是针对业绩讨价还价的形式的斗争,而是针对业绩报酬这一概念的斗争;不是针对生产中的关系(relations in production)的斗争,而是针对生产关系的基础的(basis in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斗争。”[23]
从布若威的讨论看,不是阶级生产政治以及与此相伴的阶级斗争消失了,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机制造成了更复杂的态势。如果不回应这些复杂的态势,我们就不能在既有的政治框架中将其重新政治化。
上述四个议题,可以说,乃是文明发展和人类解放面临的永恒性的基础问题,只是现代性或资本主义变化使这些问题的性质、强度、幅度以及解决它们的难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在技术问题上,正如维希留阐明的那样,技术改变了人类活动的时空框架,呈现出突破人类控制的趋势。在这一语境中,问题在普遍层次上为我们所有的地球人直接遭遇。也因为这一点,它们成为各个国家和不同人士的共同关注。就左派来说,上述例子所表现的深度说明,它们不缺乏洞察的眼光和提出问题的能力。那么,如何通过这些议题打开今天的左派实践呢?这就必然涉及新的政治承诺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解放议程问题。
一. 速度暴政与速度虚无主义
二. 全球化与共同体重塑
三. 地方、原住民与另类现代性探索
四. 重新关注生产政治
-
我们分别以技术、全球共同体、地方发展和劳动过程四个方面的例子阐明,在激进左翼理论中不乏政治议题,但就是这四个方面的例子,亦没有直接产生与之相关的重要政治实践。就个案来说,每一个都有直接的理由。例如,维希留明显地表现出悲观主义的情绪,他极少谈乌托邦方案,在他那里,技术批判揭示了当代问题的深度但并不产生直接的政治诉求;而替代资本主义方案的地方道路则有赖于政府和民众的合作,需要开辟新的政治实践。在每一个例子上,都存在理论不能承受之责任。毕竟,我们不能要求每一种理论都直接兑现自身。但是,我们也同样可以说,激进批判必须具有自身的政治承诺以及实现这种承诺的政治想象和条件分析。就这一点来说,上述例子中,鲍曼是最自觉的一位。他不仅始终围绕共同体的重构进行批判,而且对其进入议程的政治实践也曾有过分析。
本文不能完整展开对既有激进左翼现代性批判的诊断,通过对其政治困境的逻辑分析和部分例子的观察,我们试图重新提出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回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历史条件,如果缺乏解放议程的承诺,批判本身将成为无意义的知识满足,激进立场则流为纯粹空洞的姿态。在谈到激进政治学之根时,鲍曼强调,激进政治学的实质乃如马克思所言,创造自己的历史,尽管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开端[24]。这个强调是值得我们回味的。当代激进左翼的政治困境见证了创造历史的困难,但这种困难不仅不是政治退却的理由,而恰恰是必须深入那个不能选择的“开端”(即资本主义)的原因。当代激进左翼批判思想的理论学院化和立场边缘化,见证了左派本身的政治迷失。这也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即回到马克思主义,基于解放议程重新思考资本主义替代。
在此语境中来审视今天激进批判的异常的多元化发展将是有意义的。在波德里亚看来,今天激进左派试图理论化的那些层出不穷的问题,它们的产生本身就表明,世界已经开始以过度的方式运行。他说:“所有批判的激进性都已失效,所有否定性都已在一个假装认清其自身的世界中得以解决,而批判精神已在社会学中颐养天年,欲望的效应则已被消耗殆尽,还有什么能够将事物带回其谜样的零点?”[25]在这里,正如伊格尔顿正确指出的那样,之所以会产生各种批判,乃是因为这个世界存在着需要批判的地方,然而如果批判本身不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思路而满足于自身的理论建构,那理论将会有什么意义?正是基于这种思考,他批评流行的文化理论(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思潮)遗忘了政治,并且认为,“对左派而言,政治滑坡反而高度集中了理论才思,或者至少可以说导致了创造力的偏斜,这也许是一个精选的历史反讽”[26]。正是在这一背景中,他再度重提“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为马克思主义进行辩护,试图重新打开左翼思想政治化的道路。我们认为,伊格尔顿这一路向值得赞赏。因为,重建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共识和可行的政治承诺,正是当代西方左翼思想重新政治化的前提,而马克思正是迄今为止不能超越的现代批判之地平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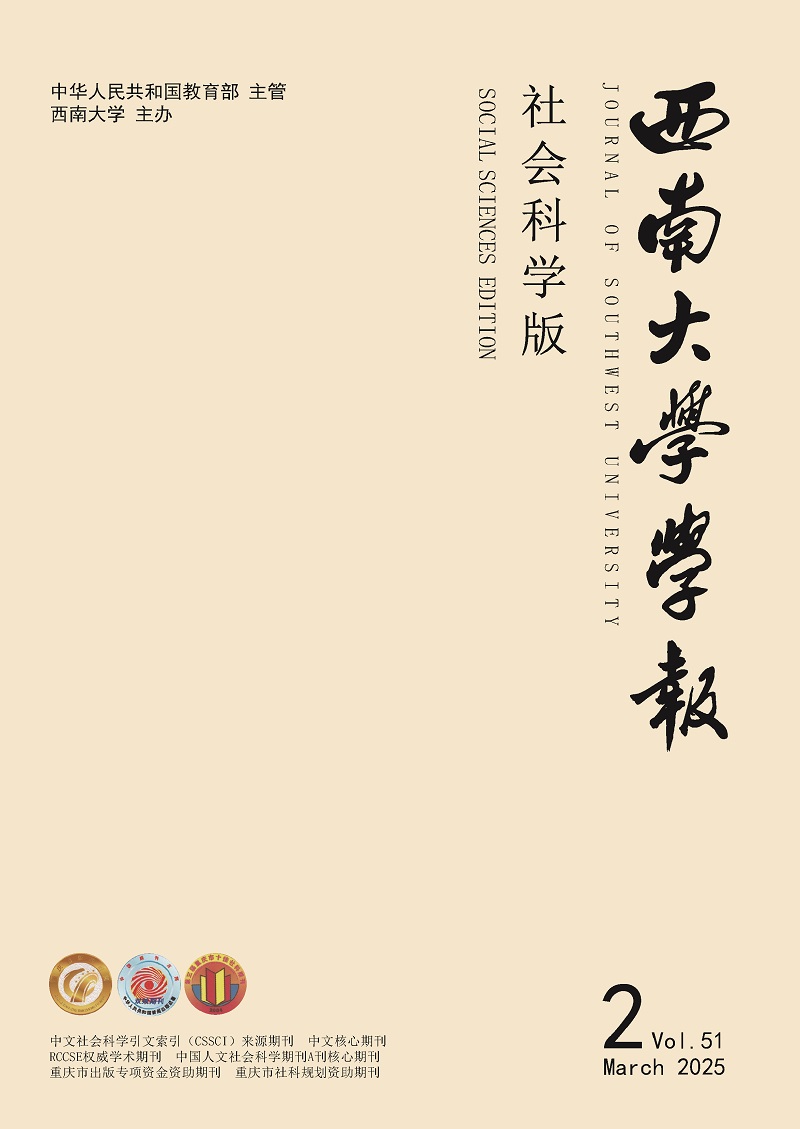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