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经说过:“对欧洲哲学传统的最保险的一般性描绘莫过于:它不过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1]我们都从怀特海低调的赞美中看到了柏拉图之于整个西方哲学的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却似乎很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这个漫长而又复杂的传统中,有太多不同主张、不同立场、不同信仰的人们都在援引柏拉图的这种或那种观点作为自己的先驱和后盾,每个人都坚信自己理解与继承的是真正的柏拉图的思想,而他们的阐释也为我们塑造出了全然不同的柏拉图形象。
对于欧洲哲学史上那些伟大的阐释者来说,诠释柏拉图并不单单是为其做注释,他们所要做的不仅是揭示某种思想的历史背景与影响,或者还原作者当时的心理状态,更是要重新创造、重新生发出这一思想本身[2]。每个时代都有哲学家试图通过对柏拉图的诠释来展开自己关于某些普遍和永恒的哲学问题的思考,这使柏拉图能够始终活跃在每一代哲学家的当下。也正因如此,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们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问题、理想与方法带入到了对柏拉图的解读之中。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诠释范式和柏拉图研究中的主题,比如理念论、本原问题、灵魂不朽、分离问题、通种论以及柏拉图的二元论及其前后期思想的转变等[3],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代的哲学家们为了回应当时特殊的哲学问题而有意无意地塑造出来的,但这些由特殊的论题和特殊的观念所塑造的诠释范式如今又反过来变成了我们研究柏拉图的某种不言自明的前提、预设和视角。
近年来,除了直接以对话作品为中心来讨论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之外,国内柏拉图研究者也开始注意到,对于不同的诠释方法和进路的选择,同样影响着读者对柏拉图的理解和认识。因此,近几年连续出现了多篇以辨析和划分柏拉图研究的进路与范式为主题的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出发,对现代流行的解读方法进行了分类和反思,侧重于围绕着文体学研究、发展论与统一论、戏剧诠释等研究方式进行讨论①。不过,这些作品大多只考察了各种诠释范式自身的内容和特点,却忽略了这些诠释之所以会出现的哲学上的原因及其对柏拉图形象的重塑与改造,尤其是当下人们习以为常的将理念论视为典型的二元论的观点,更是与康德对柏拉图的特殊理解密不可分。
① 国内学界关于柏拉图哲学的诠释进路和解读范式的研究,可参见:李致远.现代柏拉图解读路向管窥[J].求是学刊,2009(2):6-9;詹文杰.柏拉图诠释的进路之争——统一论、演变论与戏剧阐释[J].哲学动态,2010(8):59-67;黄俊松.如何进入柏拉图对话?[J].现代哲学,2018(1):91-98。
本文将以康德的柏拉图诠释为切入点,系统地考察康德是如何借助对柏拉图理念论的重新解读来阐发其先验观念论哲学的基本构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康德的柏拉图诠释对新康德主义者关于柏拉图的哲学研究,以及近现代学者们关于柏拉图的文体学和年代学研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以此彰显康德的理性批判及其观念论哲学在确立现代西方柏拉图研究的经典范式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HTML
-
严格意义上的柏拉图哲学研究开始于德国观念论哲学家们,当代德国哲学家吕迪格·布伯纳(Rüdiger Bubner)指出,“早期观念论者重新发现的柏拉图远非用新形式呈现那些人们熟悉的、传统的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元素的混合物,因为事实上它方才第一次展开了柏拉图哲学的资源本身”,而“早期观念论哲学家如此标新立异的复兴的革命性意义,一方面来源于他们的信念,即确信他们能够从传统的重负中解放出来,并提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哲学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来源于这样的事实,即他们的前辈们已经提供了必要的文献编纂方面的支持”[4]。无论是在哲学思想内部的需要上,还是历史与文献资料的充分性上,德国古典哲学都已然具备了深入理解柏拉图的条件。正是在这样的潮流之下,柏拉图哲学才迎来了真正的复兴。
康德不仅是德国观念论的开山鼻祖,而且他对柏拉图的理解,甚至他本人的哲学思想都成为了“后来所有德国学者讨论柏拉图理念论的根基”[5]。尽管康德并没有直接读过柏拉图的任何原著,但仅仅通过阅读布鲁克尔(Johann Jakob Brucker)等人的哲学史著作,他便以惊人的敏锐发现了这位古希腊哲学家对自己的思考所具有的典范意义。无论康德本人是否明确地意识到,他所身处的时代和形而上学在这个时代中的艰难处境,都与公元前5世纪那场哲学运动有着根本上的相似之处。正是面对智者们的这种挑战,捍卫真理和道德的绝对性与普遍必然性便成为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师生二人的根本目标,而这也直接促使了这个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传统的出现。当这个传统再次因类似的原因而面临危机时,必须有人站出来继承这项虽伟大却充满艰辛的事业。从这个角度来看,包括康德哲学在内的这一时期的德国哲学之所为被誉为“古典的”(classical),乃是因为他们怀着满腔热忱执着地在一个崇尚感觉的时代高扬理性,在一个碎片化的时代追求统一,在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寻找永恒不朽的常道,在一个经验主义的时代坚持形而上学对于人类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因为只有这些东西才是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承载者。因此,康德与柏拉图的相遇足以成为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而康德在先验观念论的视域之下,从一个迥异于新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传统的角度,对柏拉图理念论所进行的重新诠释,依然深刻地影响着现代西方的柏拉图研究。
康德对柏拉图的解读并不是一种纯粹学者式的研究,而是从他对理性自身的审查出发,通过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性阐释来证明我们关于无条件者(即超验的形而上学对象)的思考具有合乎理性的必然性,并最终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就像康德自己表明的那样,他对柏拉图的诠释和引用,并不想涉足文字上的考证,由此来确定柏拉图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他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是,“不论是在通常的谈话中还是在文章中,通过对一个作者关于他的对象所表明的那些思想加以比较,甚至就能比他理解自己还要更好地理解他,这根本不是什么奇谈怪论,因为他并不曾充分规定他的概念,因而有时谈话乃至于思考都违背了自己的本意”[6]270。换言之,康德无意于成为一名柏拉图研究专家,但是他认为通过充分规定柏拉图所使用的概念,自己能够比柏拉图本人更好地理解柏拉图。
这样一个具有深刻诠释学意义的观点,至少包含着两层非常重要的意思。一方面,在对抗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道路上,康德的确将柏拉图视为自己的同道,柏拉图的理念论,尤其是他关于理念与现象的二分,为康德的先验观念论提供了一个直接的范本。但另一方面,康德也发现,作为一个“没有完全理解自己”的作者,柏拉图正是独断论形而上学家的一个典型代表:他不满足于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二分,而是更进一步超出可感世界的范围,去寻求关于理念世界(即无条件者)的思辨的知识,并且在对这些理念的神秘演绎中,将这些理念“实体化”了[6]271。在康德看来,这些恰恰就是传统形而上学之所以沦为独断论、饱受怀疑主义攻击的重要原因。所以在第一批判的导言中,康德就以柏拉图为例对那些完全脱离经验来认识无条件者的旧形而上学提出了批评,他说:“轻灵的鸽子在自由地飞翔时分开空气并感到空气的阻力,它也许会想像在没有空气的空间里它还会飞得更加轻灵。同样,柏拉图也因为感官世界对知性设置了这样严格的限制而抛弃了它,并鼓起理念的两翼冒险飞向感官世界的彼岸,进入纯粹知性的真空。他没有发觉,他尽其努力而一无进展,因为他没有任何支撑物可以作为基础,以便他能撑起自己,能够在上面用力,从而使知性发动起来。”[6]7根据康德所提出的解释原则,我们不难看出,康德眼中的柏拉图虽然正确地指出了“理念”作为非物质性实体所具有的合理性,但是他对“理念”(eidos/idea)缺乏充分的规定,并试图完全不借助任何经验来认识“理念”,这就导致形而上学本身陷入矛盾和谬误,使得理念论自身的合理性被掩盖起来,而柏拉图遂成为旧的独断论形而上学的始作俑者。
因此对康德来说,“比柏拉图本人更好地理解柏拉图”就意味着,通过对理性自身的“批判”(Kritik)将柏拉图的理念论从独断论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并将其更好地阐释成一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问题的二元论哲学或者说“科学的形而上学”,这一柏拉图诠释与康德批判哲学的形而上学旨趣是完全吻合的[7]。由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康德眼中,柏拉图那包罗万象的哲学当中,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诸如新柏拉图主义所讨论的本原及其流溢,也不是基督教哲学家们关心的创世和灵魂不朽的观念等传统形而上学会感兴趣的问题,而是柏拉图的理念论(Ideenlehre),这样一个通过理念与现象的二分来证成理念的绝对性和理性的自主性,并且能够借此重新为形而上学奠基的主题。康德将自己的哲学称为“先验观念论”(transzendentaler Idealismus),无疑也表达了他对柏拉图的理解与再现实化。
康德对柏拉图理念论最重要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辩证论”部分,在这一部分中,康德通过重新阐释柏拉图“理念”概念的内涵及其关于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二分,提出了一种新的理性与合理性概念。在康德看来,近代以来人们主要是从工具理性或计算理性的意义上来理解“理性”概念的,而这样一种“理性”被康德称为“知性”(Verstand)。对他来说,“知性”为作为科学研究和认识(erkennen)对象的自然提供了规则,在这个领域中,一个判断或命题只要有经验性的证据,同时不违反逻辑或数学的规则,它就是合理的。但是,“理性”的工具论意义并不是其内涵的全部,而且如果“知性”被无限放大,以致于超出其有效的范围,理性的反思将导致理性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即关于全体和目的的规定被消解,最终导致与理性和自由相背离的机械决定论、怀疑主义和物质主义[8]。所以在“辩证论”的部分,康德试图恢复一种作为目的能力的“理性”(Vernunft),它涉及到有理性的人必然超出可能经验的范围而试图去认识无条件者的那种冲动,而康德将这些涉及全体与目的的概念称为纯粹理性概念或者说“理念”(Ideen)。在这方面给予康德最大启发的无疑是柏拉图:“柏拉图这样来使用理念这种表达,以致于人们清楚看到,他是将它理解为某种不仅永远也不由感官中借来、而且甚至远远超出亚里士多德所研究的那些知性概念之上的东西,因为在经验中永远也找不到与之相符的东西。理念在他那里是事物本身的蓝本,而不像范畴那样只不过是开启可能经验的钥匙。”[6]270对康德而言,这些无法通过经验来证明的“理念”之所以是重要的,不仅仅因为它们是传统形而上学所讨论的对象,更在于它们为人类在一个自然科学的时代、在一个具有机械因果必然性的世界中坚持做道德的事情,并证明对人而言是道德而非自利具有真正的合理性,提供了最终的根据。虽然这些“理念”不是认识的对象,也不具有可以被认识的真实性(Wirklichkeit),但它们以及与它们一道被思考(denken)的一个完全不同于经验自然(即可感世界,Sinnenwelt / mundus sensibilis)的理知世界(intelligibel Welt / mundus intelligibilis),却是关系到人类的自由、尊严、道德乃至政治的正义性不可动摇的根基。
事实上,牛顿(Isaac Newton)这位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从一开始就是康德理解和认识现象世界的典范,而通过对柏拉图理念论的赞美,康德希望能够阐明理性向往本体世界的这样一种更高层次的需要,完全具有合乎理性的必然性[9]350。正是基于对从伽利略到牛顿以来近代科学所塑造的世界观的接受,康德必须清除柏拉图思想中那些神秘主义的因素,以及柏拉图对可感世界的消极态度。对康德来说确定无疑的是近代物理科学所塑造的这个经验世界或自然,而不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wirklich)。但另一方面,康德也深刻地意识到,这个机械论自然观和可感世界的原则将对人的道德和理性的自主性构成致命的打击,是他必须想方设法努力扬弃的东西。“因为在对自然的考察中,经验把规则提交给我们,它就是真理的源泉;但在道德律中经验却(可惜!)是幻相之母,而最大的耻辱就是从被做着的事情中取得有关我应当做的事情的法则,或想由前者来限制后者。”[6]273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实践旨趣,康德借助柏拉图的理念论来阐发自己关于实然(Sein)与应然(Sollen)的二元论主张。
就像他指出的那样:“柏拉图最初是在一切实践的东西中,就是说,在一切以自由为依据的东西中,发现他的理念的,而自由本身则是从属于那些作为理性之一种特有产物的知识之下的。谁要从经验中汲取德行的概念,……他就会把德行变成一种可依时间和情境改变的、丝毫也不能用作规则的暧昧荒唐的东西。相反,每个人都会发觉,当某人作为德行的典范被树立在他面前时,他却始终只在他自己的头脑里拥有那种他用来与这个所谓典范相比较、并仅仅据此对之加以评估的真实原本。但这个原本就是德行的理念。……一切有关道德上的价值或无价值的判断仍然只有借助于这一理念才是可能的。”[6]271在这里,柏拉图的理念体现了人类关于德行和实践法则的“典范”(Muster)与“原型”(Urbild),正是这个在人的理性当中被树立起来的原型,而不是那随着时间和情境而改变的经验,构成了道德之为道德的本质规定。在康德看来,根据启蒙的理性(知性)概念所建构的那个遵循机械因果必然性的自然(作为可能经验的领域),虽然是我们的唯一合法的认识对象,但是,这种机械论的一元论不可避免地会从根本上取消人的理性和自由,将道德还原成单纯的自利和自保倾向。康德对柏拉图的倚重与柏拉图本人的出发点一样,都是出于这种深刻的实践旨趣,而康德也从柏拉图的“两个世界”那里看到了将道德与偏好、应然与实然、价值与事实进行严格区分的依据。当康德宣称自己是“站在两个世界的公民”时,他显然是在将柏拉图作为自己效仿的对象。
不仅如此,康德还从《蒂迈欧篇》(Timaeus)的创世神话中看到了一种不同于机械论自然观的更高的自然观念。他认为,“就自然界本身而言,柏拉图也正当地看出了自然从理念中的起源的明白的证据。一株植物,一个动物,这个世界的有规则地安排好的结构……,都清楚地表明它们只有按照理念才是可能的;表明虽然没有任何个别的生物在其存有的那些个别条件下会与它的种类的最完善者的理念相重合,……然而那些理念在最高知性中却是个别的、不可改变的、彻底规定了的,并且是事物的本源的原因,而只有事物在宇宙中联结的那个整体才是独一无二地与那个理念完全相符合的。……这位哲学家从对世界秩序的物理事物所作的描摹性的考察提升到按照目的、即按照理念对世界秩序作建筑术的连结,这股精神的冲劲是一种值得敬重和仿效的努力。”[6]273在康德那里,这个具有合目的性(Zweckmässigkeit)的自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观念。对康德来说,仅仅证明德行属于一个不同于实然的规范性领域,还不足以从根本上回应怀疑主义对理性和普遍原则的实在性的消解。因为经验主义者和怀疑主义者可以承认道德法则属于应然的领域,并且具有某种绝对性,但是作为生活在这个按照机械因果必然性来运作的世界中,真正有效的和合理的仍然是基于感觉和情感的经验性的准则。所以,为了证明理性本身具有实践性的力量,康德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将道德的本质规定与这个现实世界的经验性原则区分开来,而且还必须证明一个并非按照机械因果必然性来运作,而是按照目的和事物本身的理念来建构的世界,即一个作为原型(Urbild)和目的(Zweck)的最高的自然,其具有合乎理性的必然性与实在性(Realität)[9]。通过这个目的论的一元论将实然与应然的二分重新统一于无条件者的理念。
康德进一步将这个目的论意义上的“理念”(Idee)称为“理想”(Ideal),并同样借助柏拉图来阐发这个“理想”的意义:“凡对我们是一个理想的东西,在柏拉图看来就是一个神圣知性的理念,一个在神圣知性的纯粹直观中的单独的对象,即可能存在者的每一类中的那个最完善者,以及现象中一切摹本的那个原始根据。”[6]456实际上,“理想”(Ideal)在18世纪通常是与美学思想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比如,想象力所构造的图像就是一种理想),而康德则赋予这个概念以强烈的道德-政治含义:它指向以至善(hchsten Gut)作为目标的奋进[9]。更为重要的是,康德希望通过恢复这样一种目的论的自然观念,提出一种新的“道德世界观”(moralische Weltanschauung)[10],只有确立这样一种以道德理性为标准的合理性模式和世界图景,才能够抗衡近代科学世界观对理性、道德和人类尊严所造成的冲击。不过,这个“理想”虽然具有实践性的力量并为道德行动的可完善性提供了根据;但是,基于康德对牛顿世界观的认同,这个“理想”只能够作为一种调节性的原则(regulatives Prinzip)发挥作用,那个作为原型的世界并不是客观的实存(objektive Existenz),而只具有主观的实在性(subjektive Realität)。不得不说,康德对“理念”所做出的这一系列限制,着实与柏拉图本人赋予理念的崇高地位有着巨大的差距。
在康德的巨大影响之下,柏拉图哲学迎来了它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全面复兴。不过,通过康德极具创造力的哲学阐释,柏拉图虽然重新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但是这个主体主义哲学的框架也使得柏拉图思想中一些更为深刻的洞见被掩盖起来,甚至被作为非理性的独断因素而抛弃[11]。康德式的观念论几乎成为人们理解柏拉图理念论(Ideenlehre)的一个基本范式,而本体(Noumena)与现象(Phänomena)、可感世界(Sinnenwelt / mundus sensibilis)与理知世界(intelligibel Welt / mundus intelligibilis)、理念世界(Ideenwelt)与现象世界(Erscheinungswelt)、原型(Urbild)与摹本(Nachbild),这样一些成对的、极具康德二元论色彩的概念逐渐被人们用来解释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并建构起一个现代柏拉图诠释的话语系统。也正是从康德开始,柏拉图才被明确地塑造成一个二元论者,一个理性主义的柏拉图,他为柏拉图的理念与现象设下了无法抹去的界限,而他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目的论实际上更加凸显了理念论所导致的分离问题的严重性,而就是这个几乎与康德式观念论合为一体的柏拉图形象,变成了那些深受康德哲学影响的后世学者研究柏拉图哲学的基本立场和毋庸置疑的前提。
康德的确凭其一己之力建构起了19世纪之后柏拉图研究的基本范式,我们能够想到的大部分解释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康德所建构的话语体系与思考方式,以康德的观念论哲学作为研究柏拉图的生平、著作及其思想的重要指导。虽然这个柏拉图完全是为了先验观念论而诞生的,但它的影响早已超出了先验观念论哲学本身。在康德之后,有两条不同侧重的路向都直接将他的柏拉图诠释奉为圭臬,一条是由新康德主义,尤其是马堡学派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哲学阐释;另一条则是由滕涅曼所开创的语文学和年代学的研究进路,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当代。
-
柏拉图理念论的再现实化不仅没有在康德之后淡出人们的视野,反而在德国观念论的进一步推动下,成为新一代哲学家们所依傍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尽管像施莱尔马赫、谢林、施莱格尔、黑格尔等人对柏拉图的具体阐释不尽相同,但是柏拉图对德国哲学所发挥的内在的、深刻的影响,在康德之后渐渐发展成为燎原之势。然而,当黑格尔去世之后,实证主义、心理主义、历史主义与自然主义这些曾被观念论哲学所压制和批判的思想又卷土重来,甚至隐隐有取而代之之势。于是,对心理主义、实证主义等思潮的反制催生了又一场重要的哲学运动的兴起,这个倾向在德国古典哲学的余韵——特伦德楞堡(Friedrich Adolf Trendelenburg)与洛采(Hermann Lozte)的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两位哲学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虽不及他们的观念论的前辈,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只是狗尾续貂而已。相反,他们对那个时代所流行的实证主义、心理主义和自然主义保持了敏锐的洞见和警惕,他们对观念论传统的理解和坚持,使得19世纪下半叶乃至20世纪的哲学与那个追求理性和世界的统一性的观念论传统继续保持着内在的关联。面对着时代的挑战,他们两人和康德一样也从柏拉图哲学那里获得了重要的启发。
作为晚期浪漫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执教于柏林长达四十余年的特伦德楞堡将自己视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在现代世界的代言人。在他的《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中,特伦德楞堡提出,哲学的目标就是对抗现代的自然主义和物质主义,捍卫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所描述的“有机世界观”。实际上,特伦德楞堡是以他的亚里士多德研究而闻名,尤其是他对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的考证和重新编辑被视为亚里士多德研究的一项重要成就,而他本人也被看作是现代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但他总是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从根本上说仍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哲学。作为19世纪中期观念论哲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在哥廷根执教三十五年的洛采同样致力于维护有机论的世界观,来遏制日益壮大的自然主义和物质主义。在他的《小宇宙》(Mikrokosmus)一书中,洛采借助对柏拉图理念论的解读来强调宇宙的规范性维度,这个规范性维度是不能被还原为机械因果必然性的现实的力量。通过洛采的努力,柏拉图几乎成为了一位对抗现代物质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勇士。在1874年出版的《逻辑学》(Logik)一书中,洛采在真理或有效性的领域(Geltungsphre)与实存(Existenz)的领域之间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区分,并将柏拉图的理念完完全全地置于真理或有效性的领域。他认为,柏拉图理念论的关键就在于对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做出区分。因此,理念不应当被理解为某种实体,而应将其理解为一种规范性的真理,而它的有效性超出了那个受自然主义和物质主义原则支配的实存的领域。通过特伦德楞堡和洛采我们可以看到,在康德之后,哲学家们对柏拉图的倚重愈发明显起来,而康德关于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区分,以及由此出发所塑造的“观念论的柏拉图”形象也随着观念论哲学传统的延续和发展而更加深入人心[12]。
在洛采与特伦德楞堡的影响下,以“回到康德去!”(Zurückzu Kant!)为理想的新康德主义应运而生,但是他们并非想要如实地理解康德具体的哲学主张和论断,而是致力于继承康德的精神,进而在康德的精神中展开新的哲学思辨[13]。其中,马堡学派(Marburger Schule)由于对观念论和知识问题的关注而延续了康德对柏拉图的先验观念论式解读。马堡学派认为,想要获得关于一切事物的普遍且真实的认识,其前提乃是找到一种确定可靠的方法,而在柯亨(Hermann Cohen)与那托普(Paul Gerhard Natorp)看来,柏拉图的理念论正是这种方法在哲学史上的第一次出现。作为马堡学派的奠基者,柯亨受柏拉图的影响最为显著,以致于卡西尔(Ernst Cassirer)曾经毫不夸张地将柯亨视为“哲学史上最坚定的柏拉图主义者之一”。柯亨明确地将柏拉图看做“观念论的创始人”[14],而且“观念论就是柏拉图理念意义上的观念论”(Der Idealismus ist der Idealismus der Platonischen Idee),而康德则是柏拉图的现代诠释者和传承者[15]。虽说柯亨将康德视为柏拉图的诠释者,但他实际上却是透过康德的眼睛来看待柏拉图的。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与数学》(Platos Ideenlehre und die Mathematik)等早期著述中,柯亨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理解柏拉图的理念。他将柏拉图的理念解释为先天的“法则”(Gesetzen),这些法则乃是经验事物的可能性条件,它们给予经验杂多以某种确定的规则或秩序,使它们成为科学认识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理念不是实体或者具体的事物,而是作为思维与认识的首要原则的“设定”(hypotheses)。因此柯亨认为,先验方法所要处理的真正对象不是经验事物,而恰恰是这些法则,因为正是这些法则,而不是感性经验才是真正的实在。“天空中的星星并不是教授我们去思考并认识它们的(先验)方法的对象;相反,天文学运算这种科学实在的事实才是需要被解释的‘现实’,……法则才是事实、才是对象,而不是星星那种东西”[16]。正是出于这种方法论诉求,柯亨将柏拉图的理念理解为法则,而理念论则是他的意义上的先验方法[17]。不难看出,柯亨对柏拉图理念论的解读,明显受到康德先验哲学的影响。在柯亨那里,法则作为建构经验对象、赋予经验杂多以规则的“设定”,其作用实际上正相当于康德第一批判的“先验分析论”部分中,作为对感性直观杂多进行先天综合统一并赋予其规则(Regel)的纯粹知性概念或“范畴”(Kategorie)所发挥的作用。当我们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理解柏拉图的理念论时,柯亨的解读其实非常具有代表性。但这种解读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一方面,将理念理解为“设定”或者“法则”,已经预设了法则(一)与经验(多)之间的对立,从这个角度来看柏拉图,当然会将其视为一个典型的二元论者。另一方面,理念在柏拉图那里绝不仅仅是一种方法或规则,而是真正的实体,这一点被柯亨的方法论旨趣所掩盖了。所以在柯亨晚年的著作《纯粹思想的逻辑》(Die Logikdes reinen Denkens)中,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从而更加侧重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阐发理念的意义,恢复理念的形而上学地位,因为理念不仅仅是思维与认识的原则,更是存在本身的原则。
那托普的《柏拉图的理念论》(Platos Ideenlehre)对后世的柏拉图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更加自觉地将自己看作是柏拉图哲学在当代的代言人。在这部著作中,那托普不仅按照柯亨的进路来考察柏拉图思想的发展,对柏拉图的20篇对话进行了细致的解读,而且正如该书的副标题“观念论导论”(eine Einführung in den Idealismus)所表明的那样,那托普非常真诚地相信“在柏拉图那里有着原始的、仿佛土生土长的观念论”,“柏拉图的理念论乃是观念论在人类历史上的诞生”[18]v。不过这里的观念论带有极强的康德色彩,但康德观念论对理念论的重新塑造以及二者之间的一些根本性差异并没有得到学者们的充分辨识。这样一来,那托普的柏拉图诠释“将希腊的开端与康德和先验哲学调和并等同起来——由此,那托普把柏拉图变成了一个康德之前的康德主义者”[19]。和柯亨相似,那托普同样将理念视为先天的法则,法则作为像数学公理那样的理性设定,所强调的正是理性的自发性与主动性,它们是经验得以可能的条件,而不是后天经验的产物。在此基础上,那托普进一步将柏拉图的辩证法理解为对前提的设定(hypothesis),设定前提即是奠定基础(Grund-legung),辩证法通过将先验的法则(理念)确定为感性杂多的基础与前提,使得后者具有逻辑的形式(Gestalt)并成为可以被理解和认识的经验对象[20]。换言之,理念论与辩证法一起构成了追求完全确定的永恒目的的科学方法——这种完全确定的、永恒不变的最终目的被那托普称作“原型”(Urbild),它是一切对象最完美的典范;而经验世界中的现象物则被称为“摹本”(Abbild),它们是对原型的有缺陷的模仿。通过将这种理解运用于对《斐多篇》的解读,那托普构建起了理解柏拉图“摹仿说”(mimēsis)的基本思路[18]129-167。
新康德主义者所面对的是比休谟式的怀疑主义更为棘手、也更为严峻的物质主义和自然主义,因此他们不仅继承了康德先验哲学的基本思路,而且在康德的影响下,同样发现了柏拉图理念论对于证成一种非物质性实体的存在,并且在这个自然科学的时代为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真理进行辩护,具有最经典的范本性的意义。所以对新康德主义者而言,诠释柏拉图不单单是一项学院式的研究工作,更是他们关于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柏拉图的理念论不仅为新康德主义者们在规范性的真理与自然的实存之间做出区分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更使他们找到了突破康德对理性理念的限制的契机。对康德来说,“理念”作为目的原则是理性的一种调节性而非建构性的运用,因此理念是不具有现实性的,它只是我们希望和信仰的对象,而不是一个恰当的认识对象。这一限制导致康德必然得出“物自体”不可知的结论,但这种不可知论在新康德主义者们看来恰恰为新的怀疑主义留下了可乘之机,只有证明理念自身的现实性才能够从根本上克服物质主义和怀疑主义。所以,新康德主义者一方面继承了康德对柏拉图的二元论式的解读,却又不安于康德关于本体与现象、自由与自然的二分。他们不满足将柏拉图的理念理解成一种康德式的、调节性的“理想”,而是通过将它解释成一种积极的、建构性的法则,为一种不同于自然物的实存的有效性或规范性真理找到了根据,由此超越了康德的物自体观念。可以说,康德借助对柏拉图的解读所发展出来的先验哲学是新康德主义哲学最重要的范本,而新康德主义者们也从柏拉图的理念论中找到了克服康德哲学内在困难的思想资源。
-
除了新康德主义继承了观念论式柏拉图解读之外,康德的观念论及其哲学体系的构想还以另一种方式影响着人们对柏拉图的研究。传统的人文主义的诠释方法在18世纪末期之后被“批判性”的语文学研究方法所取代,著名的柏拉图学者滕涅曼(Wilhelm Gottlieb Tennemann)的工作为这种诠释路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他的《柏拉图哲学的体系》(System der Platonischen Philosophie)一书中,滕涅曼几乎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要对传世的柏拉图作品进行批判性考察,将伪作与不可信的内容排除出去以确保对话作品的纯粹性与真实性。在他看来,经过这种去伪存真的提纯之后,人们便能够在剩下的真实的柏拉图对话中发现一个与康德的原则相吻合的哲学体系。作为康德的同时代人,滕涅曼对柏拉图文本的熟悉和了解,相较于主要通过哲学史著作来了解柏拉图思想的康德来说,要远为丰富得多。他承认柏拉图的作品而非任何秘传的或者新柏拉图主义的改造,它是了解柏拉图思想的唯一合法资源。但是,由于滕涅曼同样不加思索地接受了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对柏拉图的固定认识,即柏拉图有一个确定的、成体系的“学说”,对话作为柏拉图思考哲学问题的形式其本身的意义就大大降低了。所以当他发现在柏拉图的对话作品中,从头到尾找不到一个哲学之整体时,滕涅曼不得不认为柏拉图有所谓的“双重哲学”:一个是对话作品中的不成体系的思想,另一个则是在对话作品之外传授的体系性的学说。他无法拒绝秘传学说的传统,但又不愿意为其赋予新柏拉图主义的内容,而是将康德式的观念论视为柏拉图哲学的隐秘主张[21]。
无论如何,滕涅曼的柏拉图研究在学术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开启了19世纪德国学界考查分析柏拉图作品中的伪作的热潮,其贡献和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另一方面,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找到康德式的体系哲学的讲法,虽然很像后来马堡学派的做法,但事实上二者具有极大的差异:马堡学派将柏拉图看做第一位有意识地提出观念论哲学的先驱和最伟大的观念论者,但是滕涅曼想要提取出来的乃是一种与作者相分离的体系学说,它是体现在作品中的作者思想的客观发展,这种客观的发展虽然是作者本人的,但后者并不能任意地改变它的顺序与进程。正是这样的主张推进了对柏拉图对话的年代顺序的研究,例如深受浪漫派与观念论影响的语文学家K·F·赫尔曼(Karl Friedrich Hermann)便是如此,他在未完成的著作《柏拉图哲学的历史与体系》(Geschichte und System der Platonischen Philosophie)与六卷本的《柏拉图对话》(Platonis Dialogi)中明确指出,对话的顺序反应的正是思想按照一定的原则所展开的客观的发展进程,作者既无法决定也无法改变,因此,研究柏拉图思想的前提是确定对话录的年代顺序。同样是在观念论哲学的影响下,赫尔曼提出了一个被大多数19世纪的演变论者(developmentalists)①所接受的年代顺序:《理想国》与其他一些典型的理念论对话一起,被确定为柏拉图的“中期”对话,这一时期因其鲜明的思想特征而被认为是柏拉图思想发展中受麦加拉学派(School of Megara)影响较大的一个阶段;以中期的理念论对话为界,所谓“早期”对话就是在苏格拉底影响下所创造的一系列苏格拉底式对话,它们被看作是通往中期理念论对话的准备性阶段;而柏拉图的“晚期”对话则包括其他一些具有逻辑学倾向的作品[22]。通过关于柏拉图对话年代顺序的考察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康德一些具体的哲学观点在年代学研究中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但是观念论哲学的精神和基本的立场仍然潜在地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直到今天,无论是关于对话的年代学顺序,还是真伪作的讨论,仍然还在继续着,这个问题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根本无法最终达到一种统一的结论,因为当人们从关于柏拉图作品的某种学理上的认识出发时,任何关于真伪作品的判断和排序本身都是一种对柏拉图的重新解释。人们很难避免从自己对柏拉图学说的理解出发来进行判断,例如克罗恩(August A. Krohn)竟然极端地主张除《理想国》之外的所有对话都是伪作[23],而这种重构所反映出来的恰恰就是康德所提出的“比柏拉图理解自己更好地理解柏拉图”那样一种解释原则。
① “演变论”(developmentalism)是一种关于柏拉图作品的顺序以及解读的理论,它是在现代文体学研究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强调柏拉图哲学有一个随着时间和思想的变化而逐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与之相对的“统一论”(unitarianism)作为一种古代的解读进路,则相信在柏拉图的所有对话当中,存在着一个体系性的统一的柏拉图学说。关于演变论的相关内容,可参考ANNAS J. Platonic Ethics: Old and New[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5;詹文杰.柏拉图诠释的进路之争——统一论、演变论与戏剧阐释[J].哲学动态,2010(8):59-67。
19世纪上半叶对柏拉图对话的年代顺序的确定,基本上都是依据某种历史与学说相结合的方式,而到了19世纪下半叶,在英国逐渐兴起了将文体学(stylometry)运用于对柏拉图对话进行考查的研究方式,其中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当属坎贝尔(Lewis Campbell)的工作。1867年坎贝尔出版了由他编注的《柏拉图的〈智者篇〉与〈政治家篇〉》(The“Sophistes”and“Politicus”of Plato),他在该书中指出,能够确定为柏拉图最后一篇作品的《法篇》与其他五篇对话(即《智者篇》《政治家篇》《斐莱布篇》《蒂迈欧篇》与《克里底亚篇》),在措辞与行文规则上具有极为密切的关联,而且由于这几篇对话在他看来与其他作品的差异较大,所以他将这六篇对话视为柏拉图晚年的作品[24]。在此基础上坎贝尔提出了一个与文体变化相应的内容上的大胆猜测,他认为,晚年的柏拉图已经放弃了他在《理想国》中所坚持的理念论,无论在政治思想上还是在形而上学主张上,柏拉图都做出了明显的妥协和让步,他的后期思想变得更加现实也更加实际了。虽然当时坎贝尔的方法并没有立刻对欧洲大陆产生影响,但到了1896年,德国语文学家迪滕伯格(Wilhelm Dittenberger)也独立地使用了文体分析的方法来确定对话的年代顺序[25],他极为细致地统计了kai、mēn、alla mēn、ti mēn、alla……mēn等不同用法的小品词的出现频率,在此基础上为对话作品分类分期。此后尚茨(Martin Schanz)、里特(Constantin Ritter)、卢托斯拉夫斯基(Wincenty Lutoslawski)、W·D·罗斯(William David Ross)等学者都纷纷开始加入到年代学的研究之中,一直到现在,文体学都基本上被公认为是研究这一问题最科学有效的方法。而由坎贝尔在1867年基于文体学研究提出的这个将柏拉图思想划分为三个时期的猜想,直到今天仍然是许多柏拉图研究者习惯性的预设,但关于这一观点的历史起源及其科学性还是缺乏一个较为充分的批判性考察。
进入20世纪之后,斯坦泽尔(Julius Stenzel)在年代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学理上讨论了柏拉图思想的发展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会被提出,主要是由于那几篇所谓晚期对话的内容和研究方法,与人们所熟悉的理念论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为了能够连贯地解释这种差异,斯坦泽尔指出柏拉图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坚持着理念论的思想,但后来他发现其中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明确指出,当理念论想要讨论德性与数学概念之外的问题时便会出现重重困难,因此在之后的作品中柏拉图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即二分法(diairesis),并进而将其发展成为理念数论[26]。斯坦泽尔的理念数论对后来的图宾根学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他关于柏拉图思想的发展问题的讨论则直接影响到了弗拉斯托斯对柏拉图的理解。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古希腊哲学研究者,弗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在坎贝尔等人的基础上,首次以早、中、晚这种明确的时间顺序将柏拉图对话分为三个时期,并且第一次提出了“苏格拉底式对话”(Socratic dialogues)这个说法。他认为,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乃是对苏格拉底言行比较忠实的记录,因此也是他第一次提出要从柏拉图的早期作品中概括出历史上的苏格拉底本人的思想[27];以《斐多篇》《理想国》为代表的则是典型的柏拉图理念论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借老师之口讲出来罢了,这些对话中的苏格拉底与早期对话中的苏格拉底不尽相同,而是更多地成了柏拉图的代言人;弗拉斯托斯同样将坎贝尔所说的那六篇对话视为柏拉图的晚期作品,认为经过《巴门尼德篇》的过渡之后,晚年的柏拉图开始在形而上学、政治学等诸领域以各种方式修改、更正之前的理念论主张[28]。除了这些几乎已经成为教科书里最权威的理解之外,他还首先将分析哲学的方法和问题引入对柏拉图哲学的讨论,例如著名的《巴门尼德篇》里的“第三者论证”(Third Man Argument)问题。此后,分析哲学式的解读成为20世纪中后期的柏拉图研究的显学。作为美国柏拉图研究的开创者,弗拉斯托斯奠定了现代美国柏拉图研究的基本范式和主要论题,不仅切尼斯(Harold Fredrik Cherniss)、欧文(Gwilym Ellis Lane Owen)等同时代或稍晚于他的学者们深受他的影响,而且克劳特(Richard Kraut)、阿纳斯(Julia Annas)、厄文(Terence Irwin),乃至与他们意见相左的卡恩(Charles H. Kahn)等当代英美学者,都仍在弗拉斯托斯所开创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之内讨论柏拉图哲学。
从坎贝尔基于文体学研究的大胆猜想,到弗拉斯托斯结合文学、文体学考察以及哲学论证的三阶段说,再到今天在分析哲学的研究范式中非常流行的“演变论”,理念论的出现或者缺席逐渐成为判断柏拉图对话分期的唯一标准。这表面上是一个关于柏拉图作品的创作顺序和思想发展过程的实证性研究,但实际上却隐含着深刻的哲学观念的转变。“演变论”被分析哲学进路的哲学家们广泛接受,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因为“演变论”最具影响的版本从一开始就是由限制或削弱柏拉图的理念论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所推动的,这个关于柏拉图思想发展史的问题与分析哲学传统中的反形而上学倾向紧密结合在一起。其实自古以来,“统一论”都是理解柏拉图思想的主流观点,他们认为理念论是柏拉图哲学最显著和最具有生命力的特征,是将柏拉图所有对话统一起来的体系性学说。然而从20世纪中叶开始,这一观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一些学者将《巴门尼德篇》中对理念论的批判看作是对这一理论的驳斥[29],或者至少意味着理念论必须做出重大的修改[30]。这种演变论要求对基于文体学研究的三组对话的划分进行修正,其策略就是将理念论或者至少是他们所反对的那个版本的理念论限制在中期对话当中。基于这种解释,“中期对话”就成了标准的理念论对话。为了完成这个以理念论为标准的划分,就必须将那三篇从文体学上看属于第一组的对话,即《克拉底鲁篇》《斐多篇》和《会饮篇》放到中期对话中去;而第一组当中剩下的那些对话则被贴上了“苏格拉底对话”或者“早期对话”的标签,将它们归到苏格拉底哲学的名下。这些苏格拉底对话在内容方面被认为是讨论纯粹伦理学问题,不涉及任何理念论的内容。在文体学上属于第二组的两篇对话《泰阿泰德篇》和《巴门尼德篇》被认为是对中期对话里的理念论的批判,所以被一些学者置于晚期的“批判性”对话当中。更有甚者,因为《蒂迈欧篇》当中包含了典型的理念论的内容,而将这篇明显属于晚期对话的作品强行归到中期对话当中。
这种流行的演变论与其说是在通过考察柏拉图思想的发展来理解柏拉图,不如说是通过解释柏拉图来反对由柏拉图所代表的那个形而上学传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形而上学的策略非常独特,他们没有站到柏拉图的对立面,而是希望借柏拉图来反对柏拉图自己。我们有理由将这样一种独特的策略追溯到康德。在康德所描绘的形而上学的“战场”上,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智者篇》当中巨人与诸神之战的再现。在康德眼中,柏拉图作为一个已经死去并被埋葬了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创始人,当然属于后者的阵营。当康德宣称我们完全能够“比柏拉图理解自己更好地理解柏拉图”时,和这些现当代的演进论者一样,他也希望通过重新诠释柏拉图,将思辨形而上学彻底抛弃,同时把那个能够与自然科学时代的理性概念相容的柏拉图留下来为我们所用。正是从康德开始,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不再需要通过直接攻击、驳斥或者反对柏拉图的方式来进行;人们发现,当我们能够颠倒柏拉图的思想,让柏拉图自己来反对自己,或者借助对柏拉图的重新诠释来超越柏拉图时,思辨形而上学可以通过这种将其吸纳进现代科学世界观的方式,而被更为彻底地消解。康德对于现代柏拉图诠释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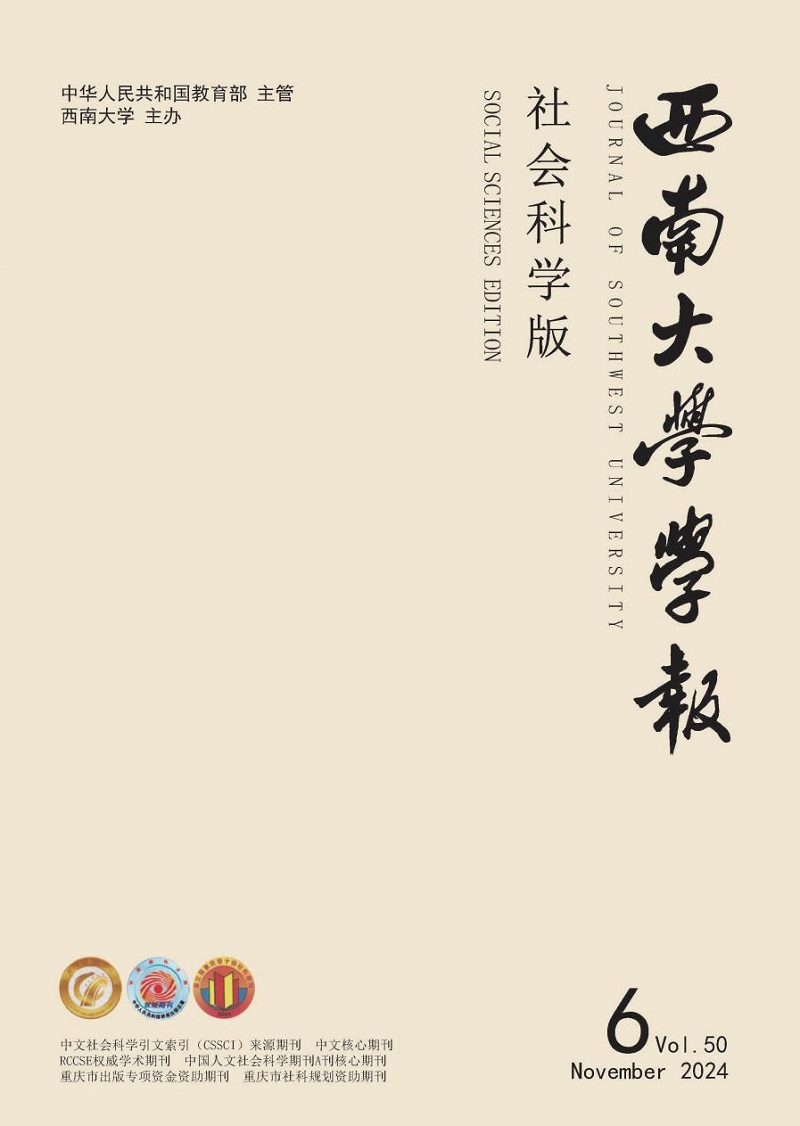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