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ML
-
伴随AIGC等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未来可能会超越其工具属性,摆脱人的束缚,升级成为宰制人的新主体,“机器是人”“AI主体”“智能主宰”等颠覆未来社会主客体关系的声音此起彼伏。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于2022年底发布的ChatGPT,让AI第一次展现出“类人对话”能力。2024年初发布的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展示了“像人类一样观看”[1]的巨大潜能,其能够探索与模拟人类思维过程与认知模式,并通过强大算力将人类想象力转换为动态画面,将文字描述转化为视觉盛宴,实现由虚拟思维世界模拟器向现实物理世界模拟器的转化,呈现出一种“比真实更真实”的状态,但亦进一步激起人类对未来人机协同社会的多重忧思。国内AI创业公司于2025年初推出的DeepSeek、Manus,引发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浪潮。其中,作为全球首款通用Agent(自主智能体)的产品Manus,能够从规划到执行全流程自主完成任务,真正拥有了“具象化思考”的能力。简言之,从ChatGPT的“语言专家”到Manus的“数字打工人”,AI完成由“脑”到“手”的进化。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在Twitter上直言“gg humans”,认为人类已输或游戏终结。人类如何看待这一系列事件?AI既然什么都会,还要人类干什么?如何破解这一困局?被学界誉为“极端性预言家”与“知识恐怖主义者”的法国哲学家、现代社会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基于对高科技媒介技术的敏锐洞察,早在40年前就已然关注到未来社会主体生存的可能现状,并对传统的主客体关系进行了理论重构,提出激进且具批判色彩的“客体策略”:高科技加持的客体不再是主体改造的对象,而是摆脱被主体奴役的命运,对主体发起挑战与复仇并获得自主权的客体。拥有自主权的狡黠客体依循“符号之物—拟像之物—纯粹客体”的反叛过程使自身逐步增殖至极限,在叠加自身潜力的过程中开启对人类主体的“水晶复仇”,诱惑主体在客体架构的“超真实”①世界中消亡。一言以蔽之,鲍德里亚面对高科技手段对主体持续进行的诱惑、缠绕、遮蔽,试图以物的反攻来破除长久以来存续的“主体中心主义”“唯我论”,以客体“反叛”倒逼主体走向“末路”,对重思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① 超真实,即比真实还真实。在拟真阶段,真实和非真实之间的差别已经无法区分,超真实是一种按照模型产生出来的真实。鲍德里亚常用迪士尼乐园作为范例,他认为迪士尼乐园中的美国模型要比世界中的真实美国更为真实。
鲍德里亚的思想理论将“物的逻辑”贯穿始终,其关涉主客体问题的分析亦由早期的“物体系”转向晚期的“客体策略”。关于鲍德里亚对“物(Object)”的分析,学界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鲍德里亚以“物”作为逻辑起点,指出科学技术作为一种自动化,将“物”纳入封闭体系;中期鲍德里亚分析了“物体系”的符号化特征,揭示当代科学技术以符号统治为手段,对主体实施更深层次的操控;晚期鲍德里亚抛弃传统哲学的主体模式,走向物体支配一切的阶段,提出物或客体对人或主体报复的策略问题[2],即“客体策略”。值得关注的是,由于鲍德里亚研究领域的转向,他的理论身份亦随之被重新认定。学界普遍认为他在学术生涯早期是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在晚期被视作“后现代先驱中的第一人”[3]。“客体策略”颠覆常规化批判路径的特点亦塑造了晚期鲍德里亚的理论特征:一是脱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二是宣告主体走向终结,最终投身于“虚无主义”的怀抱。
目前,国外学界关于鲍德里亚“客体策略”的研究大多持批判态度,认为这是一种悲观激进的宿命论。例如,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认为晚期鲍德里亚的思想发生了形而上学的转向,将“客体策略”视为一种“机会主义”[4];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对鲍德里亚客体中的“大众客体”进行重点考察,认为“大众的沉默”是宿命性的[5];威廉·帕莱特(William Pawlett)认为鲍德里亚的“客体策略”是对科学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全面攻击,“欲试图重新发挥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作用”[6]。国内学者关于鲍德里亚“客体策略”的研究散见于媒介技术批判与技术哲学研究领域:孔明安对鲍德里亚“客体策略”的核心概念进行解析,指出客体是一种“命定之物”[7]115;张劲松梳理了鲍德里亚“客体策略”中主体的形态变化,指出主体失去了肉身的存在和理性的本质[8];刘翔将“客体策略”解读为反主体主义,认为客体发展到极限后会迎来主客交融的状态,即“象征交换秩序”的复归[9];黄玮杰追溯了鲍德里亚“客体策略”的思想渊源,指认鲍德里亚通过挪用拉康(Jacques Lacan)精神分析中关于主客体关系的讨论,提出从主体革命走向客体策略的革命主张[10]。
总体而言,“客体策略”作为晚期鲍德里亚提出的核心思想,在学界关注度日益提升,但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既有研究主要针对鲍德里亚“客体策略”的概念与范畴进行了阐释性研究,而对其具体内容关注较少,亦缺乏对该理论的综合性反思,即站在一个更加客观的视角对其进行揭示和评价。因此,基于鲍德里亚的相关理论基础与“Sora”的现实背景,逐层分析“客体策略”的建构过程,并对其展开客观性的综合评析,是推进人—机和谐共处,深化理解鲍德里亚晚期哲学思想的有益进路。
-
鲍德里亚曾谈及两个重要概念,即“平庸策略”与“客体策略”。“平庸策略”指涉“主体优于客体”“主体征服客体”的传统哲学立场。“客体策略”作为鲍德里亚晚期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指客体无限增殖至极限,在叠加自身潜力的过程中实现对主体超越[11]。这一“主体消失、客体胜利”的过程,抛掉“平庸策略”的传统思维,以客体的反叛倒逼主体走向末路,被喻称为“以退出游戏的方式参与游戏”[12]。
-
“平庸策略”始终基于主体立场审思客体,坚信主体比客体更为强大、狡猾。在“平庸策略”中,主客体二元对立,主体将权威、愿望和意志作用于客体,实现对客体的征服与操控,而“客体仅仅是主体性的康庄大道上一个微不足道的迂回”[13]159。伴随主体将自身设置为最高极点后而引发的“唯我论”“人类中心论”等一系列现实困境,“消解主体性”“超越主体性”“主体性黄昏”等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声音络绎不绝,人类主体或将面临统治地位丧失的震荡危机。
溯源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家对主体性的孜孜探究从未中断。古希腊时期,主体性思想尚处于潜在萌芽阶段: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将思维向度引向主体;苏格拉底(Socrates)主张“思维着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实现由关注自然向关注人的转变;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实体就是主体”,基于实体视角重新界定人。进入中世纪,宗教神学一统天下,一切事物“唯上帝马首是瞻”,哲学沦为神学婢女,人沦为神的奴仆。近代以降,文艺复兴敲响中世纪宗教神学的丧钟,压抑已久的主体性从神学枷锁中解放出来。从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Immanuel Kant)的“人为自然立法”,再到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实体即主体”,一系列观点的提出充分发挥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并将西方哲学的基础从预设的外在实体(如神或上帝)转向主体的自明,开启了主客体二元对立与主体统摄并支配客体的历史。但诸如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的“绝对自我”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思想主张亦逐渐推动主体将自身设置为主客体关系的“最高极点”,轻视否定除人以外的存在物的价值,最终在理论与实践上深陷“唯我论”与“人类中心论”的怪圈。
“平庸策略”由最初对主体性的高扬走向对主体性的戕害。首先,“主体”难以保持对自然的敬畏。自然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14],能够为主体提供赖以生存发展的生活资料。既往的“平庸策略”片面执着于主体的理性力量、需求与目的,认为主体生而拥有宰制自然的绝对权威,对自然进行肆意“剪裁”,引发生态失衡、资源匮乏等环境问题,造成人与自然原初关系的紧张与断裂。其次,“主体”难以保持对他者的包容。人类中心主义秉持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观念,认为“‘他者’意味着‘贬低’,差异则是消极的,差异之中的他者没有主体地位而只是镜像般的存在”[15]。最后,“主体”难以保持自身的“自在”与“自由”。主体在欲望的引导下会效力于某种全然不为他们所知的更崇高的世界历史目的[16],以对待“物”的方式对待自身,造成“本真之我”的失落。
伴随现代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认为主体性观念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旧观念,支撑西方现代化的传统主体性原则也不过是一场虚幻神话,并针对主体异化与客体反主体化等现象提出一系列关涉“消解主体”或是“拯救主体”还是“重建主体”的相关论断。作为“后现代精神解剖的执刀者”的鲍德里亚将主体困境的起因归结于笛卡尔对主体的设置,认为立于主体视角解决主体性危机已不再可能,并宣告曾作为“现代哲学宠儿”的主体走向失败。
-
在鲍德里亚看来,近代哲学家们对主体性的探究与反思是一种“照镜子”的行为,非但不能澄清主体性困境,反而使主体走向失落。“若想弃置某种以认识论为中心(即以主体性为中心)的哲学,势必先行弃置主体的这种镜式本质。”[17]但鲍德里亚绝不满足于弃置镜式本质,而是摒弃“主体统治并支配客体”的传统视角,将主体困境阐发为“物的围困”,并试图以“物的逻辑”攻破镜子本身。
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平庸策略”的传统之道立于主客二分建构形而上学的理性大厦,认为“客体”是相对于“主体”的辩证存在。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处于矛盾对立的两极相互斗争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并在自在自为存在的差别中涵括“同一性”。但在“客体策略”中,客体被赋予“命定(Fatal)”前缀,主客体之间不再具有辩证意味:二者向极端趋势发展,直至其中一方无限扩张至自身极限,完全失去平衡。基于此,鲍德里亚认为“世界不再是辩证的,它肯定要走向极端,而不是平衡;它肯定走向激进的对立,而不是调和或综合”[7]114。
主体立场已不再稳固,唯一可能的策略是客体策略[13]162。在被称为“真实沙漠”的现代社会,“客体”吸纳“主体”力量逐渐进入“迷狂”状态,以一种无须主体参与的新生产方式进行运转。鲍德里亚预感到“客体迷狂”时代的到来,并尝试采取“以退为进”的方式,以“客体逻辑”取代“主体逻辑”,彻底颠倒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哲学,消解主客二元的理论架构,构筑应对主体性危机的“客体策略”,即客体追逐某种运动或遵从自身的发展逻辑至极限状态,甚至突破其界限的一种方式,例如癌细胞的扩散、媒体信息的内爆等。在“客体策略”中,客体营造出一个“比真实更真实”的虚拟空间,即“超真实”空间,亦建构出愈趋于完美、愈独立于人类的闭环逻辑。在客体逻辑主导下,主体跟随客体的节奏而生活,并在客体控制下逐渐丧失自身命运的掌控权,其权威、力量与优越性亦沦为幻象。
一般而言,“策略”通常是由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提出,鲍德里亚却将这一策略赋予“客体”。这是由于“客体策略”中的客体不再是主体改造的日常生活之物,而是具有人化特征,甚至拥有自身独立的发展体系,通过自主的独立思考来反叛主体的“纯粹客体”。从表面上看,客体任由主体“掩埋”“肢解”和“装扮”,但主体在疯狂榨取客体价值的同时亦无力招架客体诱惑抛来的筹码,注定难逃“死亡”宿命。客体比主体更为精巧、更为足智多谋。鲍德里亚常用一个公式即“比X更X”来阐释,他认为客体的发展是“比真还真,比漂亮还漂亮,比实在还实在”[18]。就丑陋与美丽这对矛盾而言,不是以丑陋来对抗美丽,反而是寻找比丑陋更丑陋的客体,这就是客体的“狡黠”所在。
一. “平庸策略”:“主体统治并支配客体”的传统思维
二. “客体策略”:“客体挑战并反叛主体”的未来方案
-
“无尽的压迫必然会带来反抗。”[19]究竟客体如何反抗主体?鲍德里亚在关于“物”的逻辑分析中,以“符号之物—拟像之物—纯粹客体”的逻辑一步步对主体实施解构,并在其晚期哲学思想的“客体策略”中指出拟真模式推动生成的“纯粹客体”,正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沉默姿态包围着主体,在“超真实”世界发动“水晶复仇”。
-
鲍德里亚认为“物”虚化为符号,实现真实“功能物”向虚拟“符号物”的转变,是客体复仇的初始形态。客体从传统的象征维度解放出来,并找到贴合自身的神话形象——符号。此时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转变为“痴迷”与“操纵”。在符号秩序不断完善的进程中,主体愈感孤独无力,仅存的“伪主体性”愈是苟延残喘。
-
“把物虚化,抽象为一种形式符号,这是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运行方式。”[20]由于生产的高密度设计与消费需求的日益升级,主体的欲望诉求由对物的需求转为对符号的需求,符号成为诱惑和控制人们争先恐后追逐财富的幽灵[21]。在鲍德里亚看来,物已不再是过去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或工具,而是将自身从特有的功能中抽象出来,成为一种纯粹符号。此时,主体购买商品的首要考虑因素不再是“使用价值”,而是“符号价值”,即商品所具有的某种象征性的符码意义。消费的逻辑即“符号和差异的逻辑”[22]。同样功能的商品,因被赋予奢侈品牌的标识就会成为财富、地位的象征,是主体表面跻身于上流阶层的通行证,鲍德里亚将其称为“原始人心态”[23]。以品牌的符号价值为例,主体为彰显自身的身份地位,将“Hermès”“LV”“DIOR”等奢侈名牌视为衡量财富与地位的标志;咖啡不再是单纯解渴提神的饮品,以“星巴克”为代表的咖啡成为表征生活美学与文艺品位的符号。
-
符号消费作为资本增殖的“麻醉剂”,牵引着主体无意识地跟读资本主义符号游戏规则,造成主体产生“为物痴狂、为物所控”的精神依恋,最终陷于精神荒原无法自拔。与异化劳动的肉体束缚相比,“符号消费”作为一种非实质性的存在,在被主体感知的瞬间渗透于主体心灵,凝结成无限渴望,似“精神鸦片”般在血液中迅速扩散,促进消费主体在与符号客体的相互交融中生发出美好意象,自愿地接受资本主义隐形、甜蜜的意识控制。物欲充斥着整个消费社会,助长着主体的虚荣贪婪,蚕食着主体的精神世界。电子媒介亦不断地向主体灌输“消费即是一切”的观念,诱导主体通过消费符号获得幸福感、存在感,寻求精神上的“世外桃源”,拥抱物质带来的“虚假满足”。但“符号消费”最终并未带来真正的幸福与满足,主体只是在暂时的符号麻醉下丧失生活的真实体验与幸福的真切感。
-
“拟像之物”是“符号之物”向“纯粹客体”转变的中间桥梁,它借助拟真模型的编码执行着对主体的反讽与复仇策略,使主体从最初的“我思故我在”升级为“我符号故我在”后,衍生出“我拟真故我在”的思想认知,心甘情愿地接受拟真模型的施魅,按部就班依照编码的定义生活。
-
拟像徘徊于“像”与原型之间,指涉没有原型的“像”。伴随媒介对真实空间再生产精细化程度的不断跃升,鲍德里亚将“物”的“拟像化”过程划分为三个等级序列,即“仿造(Counterfeit)”“生产(Production)”和“拟真(Simulation)”。在他看来,“物”的“拟像化”从根本上来看就是非人化,是对主体表象化的重构。
“拟像”的第一序列始于文艺复兴终至工业革命,以“仿造”形式出现。它并非凭空想象而来,而是在遵循“自然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物进行直接模仿,与原型共同存在,力求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工业革命后的“机械复制时代”使“拟像”进入第二序列的“生产”。它遵循“市场价值规律”,促成大量复制品在没有原型的基础上被无差别地批量生产,加速“拟像”的规模化发展,意图通过大量的机器生产清除真实,遮蔽主体对真实的感知。伴随电子计算机、虚拟现实等高科技手段的发展,第三序列的“拟像”进入被代码主宰的“拟真”阶段,其通过自动控制、差异调制、模型生成、问答等模式运行。它遵循“结构价值规律”,借助数字编码将所有问题、答案等现实因素转换为“0”与“1”的二元对立关系。
在前两个阶段,主体仍能区分现实与图像,例如看到神庙立柱上的雕刻花卉能够联想到真实花卉。进入拟真阶段则意味着表象与现实之间的界限被模糊,拟像物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并决定着主体的认知。此时,主体迷失于模型和符码的技术操控中,逐渐被“超真实”中的形象所蛊惑,成为DNA序列的合成物与可以预先被置换或牺牲掉的模型和符码。
-
现代社会完全处于模型和编码的控制之中,这是鲍德里亚在拟真阶段对主客体关系的最新认知。拟真模型的生产实践是鲍德里亚为真实退场与主体性消退而谱写的一曲“挽歌”:伴随实时技术(如全息投影、VR技术)的发展,虚拟现实技术通过模型、符码营造出一个“比真实更真实”的拟真世界,使主体被整合为大众中的原子,沦为一堆死寂符码。正如黑格尔在论述主奴关系时谈道:主人由于依赖奴隶而失去其自身的独立性,成为“奴隶的奴隶”[24]。
相较于鲍德里亚所处的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借助更为隐匿的拟真模型对主体实施操控。此时,拟真世界里的DNA与0/1数字被赋予本体论意义,主体诞生不再仅是生物体生育的结果,而是越来越成为人工合成、虚拟技术的产物。主体在数字孪生及仿真模拟等高科技手段的操控下成为一种“技术综合体”,或是虚拟数字人,抑或是仿真机器人。在Sora创建的世界模型中,每一个“NPC”都被AI赋予独立的人格,并在一串串“0”和“1”组成的跳动字符中生成不同记忆,生存于虚拟世界中,甚至将现实记忆带入虚拟世界,实现虚拟与真实的相结合。当肉体终将灭亡的时候,生命也将在虚拟世界长存,由碳基生物转化为硅基生物,开启数字化生命。可见,在拟真技术建构的模型集群,肉身在技术化媒介下只不过是一副无器官的躯壳,徜徉在荧屏所构筑的虚幻世界。
-
在“客体策略”中,鲍德里亚多次提及“纯粹客体(Pure Object)”概念,并提出替代主体逻辑的“客体逻辑”(或称“宿命逻辑”)。他以批判性姿态审视高科技社会的“人造物”,揭示人类主体已不再占据统治优势,注定难逃被技术客体消解的宿命。
-
在符号社会,客体脱离使用价值,被赋予符号价值,找到了自身的主动权,使主体沉溺于符号营造的虚假幻象,无意识地陷入精神荒原;进入模型与符码架构的拟真空间,客体获得自主权,通过无限复制与模型编码,设置真实缺席的“超真实”世界,使主体丧失肉身存在,被解构为一串串空洞符码。可见,客体已逐渐取代主体的统治地位,成为主体消失的地平线。而能承担起“主体”工作的也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客体对象,它同样伴随着技术不断进化发展,是一种非异化且不带有任何主体改造色彩,拥有自主权并反叛主体的“纯粹客体”。它遵循“强化版”拟真模式的原则,是客体策略的“灵魂”。
在鲍德里亚看来,客体世界独立发展且日渐兴盛,逐渐主宰着社会的运行。由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们设计出来的工业流程、机器体系或技术环节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运行的王国。其中,商品、信息、技术的精密性和功能性也被推向完美发展的极端程度,达到爆破点而内爆。这并不是依靠批判主体或颠覆力量发生的,而是由客体在纯粹、单一的过度增长后出现的“自动翻转”。此时,“物”进入“拟像”的第四序列——纯粹拟像,即“价值的碎形阶段”。这一阶段的客体似细胞分裂般无限增殖,并以癌细胞扩散的速度发展。
-
伴随主客体的颠倒与主体性丧失,“物”一改以往受人役使、摆布的被动命运,主动发起反叛进攻,开展对主体颠覆性报复,被鲍德里亚称为“水晶复仇”。何谓“水晶”?它是一种真空、无瑕、全透明的晶体。鲍德里亚借助“水晶复仇”来隐喻客体反叛主体的进程与逻辑,是因为“水晶”作为一种沉默客体,代表着纯客体、纯事件,是不再具有起源与终结(主体附加给客体的意义)的事物,亦是鲍德里亚心目中的“理想客体”。
“客体几乎在激情燃烧,或至少它想拥有自己的生命。”[25]根据鲍德里亚的设想,“水晶复仇”的步骤主要分为三步:第一,客体借助拟真模型的编码摆脱主体控制,披上“自愿奴性”的外衣,逐渐向“纯粹客体”转化;第二,客体自主彰显被主体所压抑、遮蔽的特质;第三,设置主体离场,发挥自身的纯粹性与自主性。“纯粹客体”的复仇若是成功,其结果便是俘获挫败主体的自主权,迫使主体走向终结的宿命,从此世界变成以客体意识为出发点的、全然属于客体的世界。
一. 符号之物:客体“复仇”的初始形态
1. “物”的符号化
2. “符号消费”培植“符号信徒”
二. 拟像之物:客体“复仇”的中间形态
1. “物”的拟像三重奏
2. “拟真模型”规训“奴隶的奴隶”
三. 纯粹客体:客体“复仇”的最终形态
1. “物”的终极形态:纯粹客体
2. “纯粹客体”设置“水晶复仇”
-
客体策略的深层逻辑是“物极必反”,它借助诱惑手段助推客体无限增殖至“迷狂”状态,不断超越假设与极限,促使主体尽快达到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提出的“死亡之点(Dead Point)”[26],也就是主体死亡或客体增殖的临界点。即使“客体策略”带来的后果可能会是灾难性的,导致主体、社会、历史、艺术终结甚至一切意义的消失,却是鲍德里亚为重建主客体新的关系模式创设的契机。他试图通过构建“象征交换”的美好境域,即一种抛弃传统的使用价值尺度和等价交换原则的理想社会,以实现物我和谐交融的美好救赎,是“客体策略”的终极目的所在。
-
“诱惑(Seduce)”作为鲍德里亚的核心原创概念之一,借鉴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理论,又被赋予全新内涵。在鲍德里亚看来,诱惑所指一词含有迷惑、怂恿、教唆之意,它并不仅是通常意义上两性之间的身体诱惑,更多指代一种仪式的游戏模型,是客体为表达自身而消解主体的一种手段。
主体的崩溃始于“诱惑”。在欲望哲学中,主体保持绝对优势,但没有正确理解“诱惑”甚至放弃“诱惑”的主动权,最终深陷“欲望泥潭”。换言之,伴随资本这部“欲望永(涌)动机”[27]的持续压榨,主体在欲望异化的驱使下逐渐失能,而客体以其无欲无求的“策略”,逐渐成为支配世界的隐形统治者。于是,鲍德里亚立于客体视角,颠倒主客体间支配与被支配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主体的优势已经褪去,而客体正以沉默的诱惑与绝对必然性,悄然瓦解主体的霸权,最终实现由“惟主体欲求”向“惟客体诱惑”的转化。
诱惑的施魅过程在形式上反映为客体逻辑。在客体诱惑的“游戏模型”中,不再是主体释放欲求,而是客体主动诱惑。客体诱惑具有“温柔暴政”的特征,虽表面看似“柔弱”,实则暗含计谋,以不经意的游戏方式使主体陷入游戏模型,沦为客体诱惑的“牺牲品”。“在诱惑中,人变成了客体,在客体中迷失自己,只是为了回过头更好地诱惑它。”[28]但对于已经被诱惑的主体而言,最终却难以从客体的诱惑陷阱中逃脱出来。以虚拟网络游戏为例,主体一旦进入虚拟网络世界,并试图控制或战胜虚拟客体,客体便开始施展诱惑的“黑色魔力”[29],释放“电子海洛因”,将主体捕获为虚拟网游的俘虏。鲍德里亚指出,客体的胜利在于让人类自愿成为自己的囚徒,沉迷于客体编织的舒适幻觉。
诱惑性的场景是幻想的,并非真实的。伴随AIGC技术的日益勃兴,以Sora为代表的视频模型为人类建构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虚拟实践空间。当用户与Sora进行交互时,用户看似掌握着创作的主动权,实则已沦为客体诱惑机制的傀儡。Sora通过生成高度逼真、真假难辨的视频愚弄用户,满足用户的猎奇心、求知欲、体验感,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边界,使主体在感官刺激中逐渐丧失对真实的判断力。当人们沉醉于Sora构建的虚拟世界,享受着即时满足的快感时,其主体性也在虚拟狂欢中逐渐湮灭。
质言之,Sora生成的虚拟视频不仅是技术的产物,更是数字客体实施诱惑策略的具象载体。这预示着一个被算法与数据支配的未来,即当真实被解构,主体被消解时,人类将彻底沦为客体诱惑机制下的“数字囚徒”,在无限循环的虚拟满足中,见证旧认知秩序的崩塌与新技术霸权的崛起。
-
“迷狂(Mania)”在希腊语中含有热情、疯狂、超越感官经验的灵感而陷入狂热状态[30]的意蕴。柏拉图(Platon)在《斐德若篇》将“迷狂”归属于神祇,并将其划分为四类:预言的迷狂、教仪的迷狂、诗歌的迷狂及爱情的迷狂[31]。鲍德里亚却将迷狂归属于客体,描述客体在无限增殖的过程中达到的不可控甚至逼近临界点的极端状态。
迷狂于客体而言是霸权的获得与统治权的巩固,是通往新阶段的“高速公路”;于主体而言则是死亡的逼近与支配权的丧失。鲍德里亚认为现实世界陷入“迷狂”是一种失去控制的持续自旋过程,并以癌细胞增生和体重飙升来描述迷狂,以彰显社会中空洞膨胀的事物——时尚、审美、大众等都已进入全面“谵妄”状态。可见,鲍德里亚企图通过客体的无限增殖来挤占主体的生存空间,顺势助长客体走向极端崩溃,主体走向边缘终结。在技术和符号的控制和操作下,客体会迅速繁殖增长,对主体产生压制性的优势,最终达到狂热程度。当客体无限增殖到超越“熵”的临界点,人类主体的力量在“内爆”①中被彻底消解而转为惰性、沉默的状态,成为“沉默的大众”。鲍德里亚认为主体在大众媒介营造的虚幻场景,仅停留于碎片化、肤浅化的“视觉表层”,在支离破碎的叙事方式下滋生惰性,放弃对历史事件深层意义的追问。换言之,面对无须思索的“精神快感”,主体沉溺于由信息广告狂轰滥炸的乌托邦中,享受着符号带来的虚假幸福感,并无限趋近于卡内蒂所描述的“死亡之点”。
① 内爆是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中的核心概念,鲍德里亚借用此概念意指拟真社会中所有界线都已消失,社会系统完全类同。
伴随Sora技术的持续迭代升级,其生成内容的丰富性与拟真度呈指数级攀升,将用户卷入“流量迷狂”的漩涡。“流量迷狂”的发生也并非偶然,其本质上是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共谋的产物——借助算法精准投喂碎片化、高刺激的“信息糖霜”(如流量算法催生的猎奇视频),蓄意将大众推向鲍德里亚笔下的“谵妄状态”。以自媒体创作者为例,其借助Sora等智能技术生成“吸睛”的视频内容,将“流量密码”转化为操纵大众情绪的利器,通过制造信息茧房、渲染焦虑情绪、炮制话题狂欢等方式将用户驯化为可收割的“情感韭菜”。“人人皆可成为创作者”的许诺异化为“人人皆可被流量收割”的现实。用户在无意识中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其主体性亦在“流量迷狂”的浪潮中逐渐消解。
-
“‘终结’是贯穿鲍德里亚一生学术研究的隐秘线索”[32],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与一切意义的消失,是“客体逻辑”演绎到极致的必然结果,也是狡黠客体复仇的“恶的原则”。鲍德里亚描绘的未来现代生活已被计算机符码的“0”和“1”所覆盖,并预判21世纪是数字化的时代景观,即由大数据主宰的、以数字资本和数字智能化技术控制的“数字化世界”[33]。
技术的演进常被看作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但鲍德里亚却敏锐捕捉到其背后潜藏的巨大危机。面对技术的狂飙式发展,鲍德里亚认为技术社会背后隐藏着一场可怖的社会灾难:“客体的增长最终压垮主体,主体被淹没在信息和媒体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边主体(大众)寻找的不再是意义,而是一种‘景观’或者说‘奇观’。”[34]洞悉现代社会,作为技术物的客体被赋予拟人化的自主权,拥有自身发展的极限逻辑,以一种无害的、中立的角色潜伏在主体身边,透明无声地实现对主体的奴役,开启对主体的“水晶复仇”。当技术客体突破工具属性的桎梏,以自主逻辑反噬人类主体性时,主体便走向终结。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指数级的进化速度,加速这一预言走向现实:2025年初最新推出的国产通用型AI智能体Manus能够根据人类指令自主执行复杂任务并交付结果,不仅能替代人类完成机械繁琐的工作,更展现出类似人类理性的学习、推理甚至创造能力,这可能会导致技术发展的方向偏离人类原本所设定的航道,甚至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但需要注意的是,鲍德里亚的“终结”预言并非宿命论的判决书,而是用激烈的言辞为人类敲响技术失控的警钟。在AIGC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人类必须警惕人机关系对人际关系的遮蔽,智能机器判断对人类价值判断的替代,机器数据和算法共识对人类理解和交往共识的消解。若任由主体贪婪地使用一切技术来行使所谓引导自己走向美好生活的权限[35],放任客体蚕食主体的判断与思考能力,主体将在技术灾难的预言中逐步走向终结的悲观宿命。正如《黑客帝国》中所描绘的人类真正的生活状态:主体的躯体被放置于充满黏稠液体的钢筋豆荚,头部连接着金属导管,其思维生活在虚拟的电脑程序中,沦为信息的奴隶。据此,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在异化状态下,可能会丢弃原本为人类服务的本质,成为统治、压迫人类的异己力量。
一. 诱惑:客体瓦解主体之“始”
二. 迷狂:客体加速主体趋近死亡之“点”
三. 灾难:客体宣判主体走向“终结”
-
鲍德里亚以“反叛者”的姿态提出“客体策略”,实现对传统主体性哲学的全然颠覆,考察人类在数字化世界中的生存危机。这不仅是对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反思,更是对人类自身的深刻反思。但“客体策略”并非鲍德里亚思考未来主客体关系的终极方案,其最终目的在于使主客二分的旧世界彻底消失,以期抵达“象征交换”①新世界。由于这一终极方案使鲍德里亚放弃了唯物史观,脱离了政治经济学基础,导致“客体策略”附带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变成一种末日预言式的“哲学呓语”[36]。
① “象征交换”是鲍德里亚建构的一种克服经济逻辑,超越消费社会的一种理想形式,它作为一种本真而原初的交换形式,抛弃传统的使用价值尺度和等价交换原则,纯粹由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驱动。
-
“客体策略”是鲍德里亚基于对主客体社会秩序变化的感知与考察,进而提出的一种涵盖哲学、符号学、人类学等层面的批判性策略。它颠覆了常规化的批判路径,立于客体视角反思现代社会中的主体困境及重构主客体关系的可能,既能拓宽“主客体关系”的理论视野,亦能敲响“技术决定论”的思想警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从理论意义看,“客体策略”拓展了思考主客体关系的理论视野。“客体策略”并非鲍德里亚的最终建构方案,而是在“象征交换”的地基上建构新的主客体关系,这很好地回答了“客体策略”后怎么办的问题。鲍德里亚认为,只有主体设定、规定、奴役客体的历史结束,客体复仇主体的历史终结,新的关系模式才有重构的可能。“客体策略”的核心工作就在构筑这一“消失之点”的到来。鲍德里亚抛弃“平庸策略”的传统模式,从“物”出发揭示主体不断被“客体”所消解,批判人的异化与社会的物化,并借助拟真模型的编码使客体达到自身性质的极点,以期待消失曙光的到来,探寻“物役人”后的出路问题。当旧的主客体关系模式完全消失之后,他意图建构“象征交换”的境域,以实现主客体之间和谐统一、愉悦恬静的“田园牧歌”①式的关系。在“象征交换”之域,人与物将不再被命名为“主体”和“客体”,二者通过可逆且互惠的交往方式维持交融状态,是鲍德里亚关于主客体关系未来命运的理想诉求。
① “田园牧歌”起源于古希腊,是用来描写农村生活的文学形式,主要以农村生活和自然景观为主题,通常呈现出一种安静、优美、柔和的氛围,此处用来形容鲍德里亚所设想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和谐统一,愉悦恬静的象征交换境遇。
从现实意义看,“客体策略”不仅为人类思考未来生存境遇给予警醒,更为规避人工智能技术演进可能造成的主体性异化风险提供理论启思。鲍德里亚以犀利的挑战性姿态,颠覆主客体之间的地位,张扬“物”的主体性,顺从“物”的计谋和轨迹,将对主体的关注转移到对技术物复仇的思考上,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在他所描绘的“客体策略”中,技术物借助拟像与仿真的方式实现自我复制和编码重复,在多次反复中掩饰自身功能潜藏的主体特性,使主体的思想行为逐渐被控制而顺从客体的计谋,沦为“官能性的人”。这提醒人类主客体关系可能会陷入危局:主体由于自身欲望的无限膨胀将会创造出与自己对立的“客体”,引发被创造者要消灭创造者的技术灾难,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例如,木马病毒入侵导致隐私泄露、基因工程滥用引发生命伦理困境、虚拟世界沉溺造成情感疏离等负面效应不断凸显,使技术客体的世界日益壮大,逐渐演变为操纵主体的异己力量。但以ChatGPT、Sora、DeepSeek与Manus等为代表的AI大模型的终极愿景是构建一个AI与人类和谐共生的社会。在这一愿景中,AI不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人类的智能伙伴,帮助人类释放创造力,专注于更有价值的工作。
-
鲍德里亚曾哀叹于自身成为一个“虚无主义者”,并以绝望、倒退式的姿态将客体逻辑推演至超级状态,来构筑主体消失的独特逻辑。主体性消解的末日宣判既是他最有煽动力的预言,但也充满悖论,使主体走向消解的悲观宿命。
一方面,“客体策略”具有悲观的“命定论”色彩。在鲍德里亚看来,主体消解并非缘于近代哲学主体神话的破灭,而是由于人类过度实施启蒙的伟大计划——“掌控宇宙和穷尽一切知识的普罗米修斯式计划”[37]。他秉持与主体完全相异的秩序原则,赋予“客体”人类主体的思维,使它能够按照自身意愿和策略发展,并在自我延展中消解主体的思考与批判能力。但鲍德里亚选择瓦解主体的同时也意味着放弃建构新的革命性主体的可能,悲观地放任主体在客体的俘虏下自行消解,无视技术的正向作用,对主体进行肆意戏弄,使主体消亡成为命定结局。事实上,主体面对狂轰滥炸的信息诱惑并非不能做出自主选择,消费社会的诱惑策略也恰恰坐实消费者的主观能动性。在后现代社会的虚无主义逻辑面前,主体更应慎思明辨、锤炼心性,树立对主体能动性力量的自信自觉,避免陷入“命定论”的陷阱。
另一方面,“客体策略”投身于“虚无主义”的怀抱。“让我们相信这么一个假说,哪怕只相信短短一刹,即,在事物的秩序中存在着一种致命的和谜样的偏好。”[13]275“客体策略”中的“真实消失”“主体剔除”等激进批判毫无掩饰地表达出鲍德里亚对“虚无主义”的痴迷,使“客体策略”最终沦为一种乌托邦构想。为彻底摆脱符号与技术逻辑的束缚,真正实现主体性自由,鲍德里亚后期尝试以“象征交换”的逻辑实现主客体关系的重构,这实际上是一种“回到原始”式的规划,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回归原始”并非重新回归到之前的原始社会,而是回到以“象征交换”为核心的一种自由、平等的生存状态。进入象征交换秩序后,主客二分对立的传统范式将不复存在,人与物之间处于平等地位,并通过一种可逆且互惠的全新交往模式实现彼此交融,进行象征交换。但鲍德里亚仅勾勒出交换框架,并未提出具有实操性的解决方案,且脱离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基础。摒弃商品经济原则的“理想化社会”只能是一种飘荡无根的理论想象,弥漫着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
一. 警钟的“轰鸣”:鲍德里亚“客体策略”的现实启思
二. 飘荡的“幽灵”:鲍德里亚“客体策略”的内在局限
-
人工智能物作为人的机体延伸与实践手段的外化,既助推了人机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协作,亦造成人机之间的主客体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以Sora为代表的AIGC智能技术借助反应扩散模型架构“超真实”世界,生成以假乱真的视频,重塑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活动条件,加速“人工智能换人”时代的到来。例如,一些美国公众接到“深度伪造”的美国前总统拜登的电话,知名歌手泰勒·斯威夫特的AI虚假“不雅照”在网上疯传……智能机器开始替代人类从事技术性工作,借助资本对人进行宰制,颠倒主客体地位,并伴随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愈演愈烈。即便如此,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产品,并非会造成人的主体性丧失。因为人工智能既非社会关系的“建构者”,亦非“‘感性思维’的拥有者”[38],本质上是解放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劳动工具,旨在助力人类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迈进。
鲍德里亚作为“后现代精神解剖的执刀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对当时最先进的技术现象做出悲观预测,将“技术物”以—种极端面貌呈现出来,提出颇具颠覆性的理论预想。他抛弃“平庸策略”的传统模式,立于“客体”视角批判人的异化与社会的物化,并借助拟真模型的编码使客体达到自身性质的极点,期待早日抵达“象征交换”的境域,探寻“物役人”后的出路问题。然而,在“符码统驭一切”的时代,象征交换存在的根基早已被拔除,人们亦不可能退回到原始社会践行象征交换原则,象征交换的世界只是一种“苍白呐喊”。是否能够真正地探寻出一条本真主体的复归之路,还亟待进一步挖掘深究。不可否认,鲍德里亚的这一理论虽然只是一种分析与诊断而非实质性且带有荒诞色彩的解决方案,其中蕴涵的真知灼见却具有深刻的镜鉴意义。一方面,在理论维度上,拓展了思考“主客体关系”的理论视野;另一方面,在实践维度上,对重新考量人与自然、技术之间的关系提供有益启思,为人类思考未来生存境遇予以警醒。为此,人类主体既需热情拥抱新技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立场,使人工智能回归工具本位,实现技术能够真正普惠于民,亦需警惕技术带来的新风险,避免沦为技术附庸、剥离人的本质,而应当更加关注自身,思考如何在技术日益发展的同时保持自身的本质属性和独特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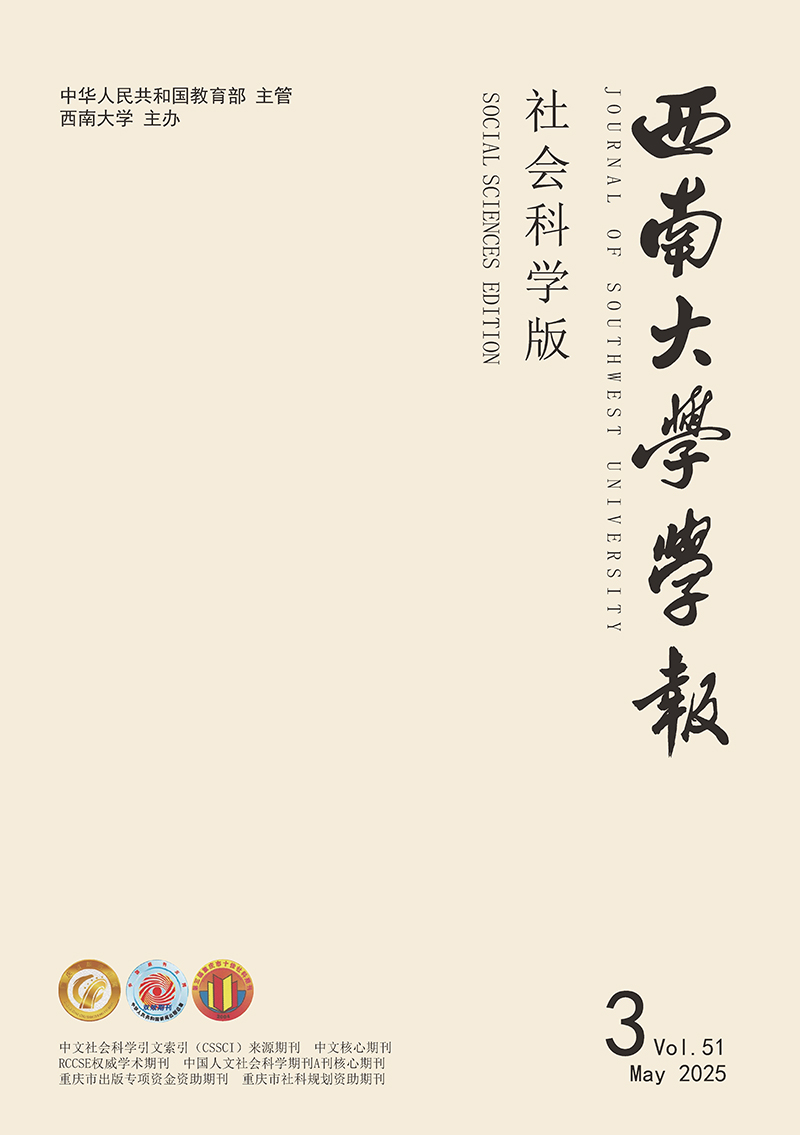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