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先后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1]。2020年2月10日,教育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有针对性地做好教师工作若干事项的通知》,指出要做好学生的心理疏导和教育引导工作。为进一步了解实际情况,更有效地促进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同时为高校和社区教育单位提升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提供有效参考,笔者于2020年2月上中旬对西南地区四川、云南、重庆等三省(直辖市)的3 178名大学生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焦虑状况进行了在线问卷测试。
HTML
-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笔者向四川省、云南省、重庆市的10所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就其焦虑状况发放了在线问卷。其中,普通高校6所、职业院校4所。问卷填写和收集过程严格遵照学术伦理,提前在填写导语中告知被调查对象问卷的基本情况、用途及信息保密承诺等事宜,被调查对象确认并同意后,方能进入答题界面。在线测试通过所在学校的专任教师、就业干事、辅导员、心理咨询教师在学校、二级学院(系)、班级的微信群和QQ群发布问卷链接,邀请学生通过手机或电脑直接在线作答的方式进行。在线测试结束后,共收回问卷3 182份,其中有效问卷3 178份,有效率99.87%。3 178份有效问卷中,显示在性别方面,男生878人、女生2 300人;就读学历层次上,研究生8人、本科生2 271人、专科生899人;就读学科专业方面,自然科学类专业531人、社会科学类专业697人、人文艺术类专业713人、不清楚就读学科1 237人;就读年级方面,一年级797人、二年级750人、三年级662人、四年级216人、五年级3人、其他年级750人;每日上网时长方面:1小时及以内165人、2~3小时632人、4~5小时789人、5小时以上1 592人。
-
研究使用1959年汉密顿(Hamilton)编制并临床使用的焦虑量表。2001年,中华医学精神科分会组织编著的《CCMD-3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一书将其列入焦虑症的重要诊断量表工具之一,临床中亦常将其用于焦虑症的诊断和程度划分[2]。汉密顿焦虑量表共14项测试题目,并依据其分类标准又将焦虑影响因子具体划分为躯体性与精神性两类。在具体题目中,第7至第13题属躯体性焦虑测试范畴,第1至第6题和第14题属精神性焦虑测试范畴。按照中国量表协作组提供的标准,我国诊断焦虑的临界分数值分别为7、14、21、29,依次代表“可能有”“肯定有”“肯定有明显的”和“可能为严重的”4种焦虑程度。
-
一方面,使用SPSS23.0量化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卡方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性、标准差和单因素分析等,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的焦虑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使用Excel软件的统计功能对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分析。
一. 研究对象
二. 研究工具
三. 统计方法
-
不同性别大学生在焦虑总水平(t=-1.743,F=10.265,P=0.081)和躯体性焦虑水平(t=0.811,F=11.473,P=0.417)上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但在精神性焦虑水平(t=-3.616,F=2.768,P=0.000 < 0.01)上存在显著相关性。具体来看,不同性别大学生在精神性焦虑的焦虑心境、害怕、失眠、认知能力、抑郁心境、人际交流行为焦虑表现等6个方面均存在显著相关性(详见表 1)。女性大学生在“时常担心和担忧最坏事情发生,易被激惹”(焦虑心境)、“害怕黑暗、陌生人、独处、动物和人多的场合”(焦虑心理)、“难以入睡、易醒、睡眠浅、多梦、睡醒后感到疲倦”(睡眠问题)、“注意力和记忆力较差”(认知能力问题)及“对一般事物或曾经喜爱事物丧失兴趣、忧郁”(抑郁心境)等5个诊断指标上,焦虑水平均高于男性大学生。但是,女性大学生群体内部对以上焦虑症状的认识存在分歧,不同于男性大学生认识相对一致。另外,男性大学生在“与人谈话时紧张、咬手指、握拳、面肌抽动”(人际交流行为焦虑表现)方面,显示其焦虑水平要高于女性大学生,但女性大学生群体内部对这一焦虑症状的认识却更为一致。
-
不同培养层次的大学生在焦虑诊断的总体项目和子项目的得分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和差异性。在总体焦虑水平上,本科生与专科生的焦虑总水平(t=-3.198,F=13.621,P=0.001 < 0.01)和精神性焦虑水平(t=-3.289,F=9.783,P=0.001 < 0.01)均存在显著差异性。由于研究生样本量(n=8)较少等客观因素,致使该方面的统计学意义较小,且与本科生和专科生在焦虑总水平、精神性焦虑水平、躯体性焦虑水平3个方面都不存在显著差异性。具体到焦虑诊断的子项目方面,不同培养层次的大学生在焦虑心境、紧张、害怕、失眠、肌肉系统焦虑症状、感觉系统焦虑症状、心血管系统焦虑症状、呼吸系统焦虑症状、胃肠消化系统焦虑症状、生殖泌尿系统焦虑症状和人际交流行为焦虑表现等11个诊断指标上所表现出来的焦虑水平,均存在显著相关性(详见表 2)。这11项指标包含5项精神性焦虑指标和6项躯体性焦虑指标。一方面,在“时常担心和担忧最坏事情发生,易被激惹”(焦虑心境)、“有情绪反应、不能放松、感到不安”(紧张心理)、“害怕黑暗、陌生人、独处、动物、人多的场合”(焦虑心理)、“与人谈话时紧张、咬手指、握拳、面肌抽动”(人际交往行为焦虑表现)等4项指标上,显示研究生的焦虑水平要高于本科生和专科生,且群体内部对以上4个指标的认识均存在分歧;但在“难以入睡、易醒、睡眠浅、多梦、睡醒后感到疲倦”(睡眠问题)这一指标上,专科生的焦虑水平却高于研究生和本科生,同时,专科生群体内部对这一指标的认识也不一致。另一方面,不同培养层次的大学生在“肌肉酸痛、活动不灵活、经常抽动、牙齿和声音发抖”(肌肉系统焦虑症状)、“视物模糊、忽冷忽热、浑身刺痛”(感觉系统焦虑症状)、“心动过快、心悸、心博脱漏、胸痛、血管跳动感”(心血管系统焦虑症状)、“呼吸困难、胸闷、窒息感”(呼吸系统焦虑症状)和“食欲不佳、消化不良、腹泻、便秘、体重减轻”(胃肠消化系统焦虑症状)等躯体性焦虑指标上,研究生的焦虑水平均高于本科生和专科生,且研究生群体内对以上5个指标的认识存在分歧;但在“尿意频繁、尿急、停经”(生殖泌尿系统焦虑症状)这一指标上,专科生的焦虑水平却高于本科生和研究生,其群体内对生殖泌尿系统焦虑症状的认识也并不一致。
-
每日不同上网时长的大学生在焦虑诊断的总体项目和子项目的得分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和差异性。在总体焦虑水平上,每日上网时长为2~3小时者与4~5小时者相比较,仅在精神性焦虑水平(t=-2.890,F=2.971,P=0.004 < 0.01)上存在显著差异性。每日上网时长1小时及以内者和5小时以上者相比较,焦虑总水平(t=-2.139,F=1.622,P=0.03 < 0.05)和精神性焦虑水平(t=-2.478,F=1.036,P=0.01 < 0.05)均存在显著差异性。每日上网时长2~3小时者与5小时以上者相比较,焦虑总水平(t=-4.263,F=13.586,P=0.000 < 0.01)、躯体性焦虑水平(t=-3.389,F=21.069,P=0.001 < 0.01)和精神性焦虑水平(t=-4.646,F=14.027,P=0.000 < 0.01)均存在显著差异性。值得注意的是,每日上网时长在1小时及以内者与上网时长为2~3小时者、每日上网时长1小时及以内者与上网时长为4~5小时者、每日上网时长为4~5小时者与上网时长在5小时以上者,在焦虑总水平、精神性焦虑水平和躯体性焦虑水平上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进一步对焦虑诊断的子项目进行分析发现,每日上网时长不同的大学生在焦虑心境、紧张、失眠、认知能力、抑郁心境、人际交流行为焦虑表现、肌肉系统焦虑症状、感觉系统焦虑症状、心血管系统焦虑症状、呼吸系统焦虑症状、胃肠消化系统焦虑症状、生殖泌尿系统焦虑症状、植物神经系统焦虑症状等13项指标上,焦虑水平均存在显著差异性(详见表 3)。表格中前5项和最后1项指标属精神性焦虑范畴,测试结果显示,每日上网5小时以上的大学生,该6项指标的焦虑水平均高于5小时以内的大学生;剩余7项指标属躯体性焦虑范畴,也呈现出与精神性焦虑指标类似的情况,即每日上网时长5小时以上的大学生,该7项指标的焦虑水平均高于上网时长少于5小时的大学生。
-
就读不同学科专业的大学生在焦虑诊断的总体项目和子项目的得分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和差异性。在总体焦虑水平上,就读自然科学类专业的大学生与不清楚就读学科的大学生在精神性焦虑水平(t=-2.011,F=0.014,P=0.044 < 0.05)上存在显著差异性。但是,就读自然科学类专业与就读社会科学类专业的大学生、就读自然科学类专业与就读人文艺术类专业的大学生、就读社会科学类专业与就读人文艺术类专业的大学生、就读自然科学类专业与不清楚就读学科的大学生、就读人文艺术类专业与不清楚就读学科的大学生,在焦虑总水平、精神性焦虑水平、躯体性焦虑水平上不存在明显差异。另外,在焦虑诊断的子项目上,主要表现出在焦虑心境和认知能力问题两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性(详见表 4)。同时,在“害怕黑暗、陌生人、独处、动物、人多的场合”和“注意力和记忆力较差”两项精神性焦虑指标上,均显示出不清楚就读学科的大学生,其焦虑水平要高于就读社会科学类专业、人文艺术类专业及自然科学类专业的大学生。但是,从群体内部对以上两项精神性焦虑症状的认识来看,不清楚就读学科的大学生其认识更为不一致。
一. 不同性别大学生的焦虑水平存在差异
二. 不同培养层次大学生的焦虑水平存在差异
三. 每日不同上网时长的大学生焦虑水平存在差异
四. 就读不同学科专业的大学生焦虑水平存在差异
-
基于我国量表协作组提供的诊断依据,本次在线测试发现,56.04%的大学生有焦虑表现(平均得分15.91±1.50);15.48%的大学生表现出明显焦虑(平均得分23.94±2.25);更有28.48%的大学生可能有严重焦虑(平均得分36.65±8.53),涉及905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地纷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具备了突发公共事件“造成公民心理阴影,危及心理平衡,造成心理恐慌”[3]的一般特征。本研究对大学生群体焦虑状况的调查,从一个角度较为直观地反映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公众心理造成的影响。按照汉密顿量表题目的因子分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被调查大学生的精神性焦虑水平平均得分(13.12±5.98)要高于躯体性焦虑水平平均得分(9.93±4.67)。其中,依据被调查大学生的量表得分高低排名,精神性焦虑水平7项诊断指标中,仅有“人际交流行为焦虑表现”1项排名靠后,其余6项排名依次为认知能力、焦虑心境、害怕、失眠、抑郁心境、紧张。躯体性焦虑水平的7项诊断指标得分排名则整体靠后,组内得分排名第一的是“肌肉系统焦虑症状”,排名最后的是“生殖泌尿系统焦虑症状”(详见表 5)。
-
通过对被调查大学生所填写量表得分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得知,女性、专科层次、尚不清楚就读学科的大学生群体焦虑水平更高。首先,女性大学生的焦虑总水平得分(23.25±9.88)高于男性大学生(22.55±11.00)。已有研究表明,女性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呈下降趋势[4]。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女性大学生也表现出比男性大学生更为明显的焦虑症状。其次,专科学生焦虑水平比本科学生更高。因研究生样本量较小,虽焦虑水平得分最高(26.25±19.20),但不具备统计学意义。除去研究生样本,专科学生焦虑总水平得分(23.97±10.95)高于本科学生(22.69±9.83),从侧面反映出专科学生群体因受高考失利、对自身学习能力不自信、对高职教育缺乏足够认识、社会传统负面认识等一系列消极因素影响,造成了有别于本科生和研究生群体的心理特质[5],也导致专科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并呈现多年持续下降趋势。最后,尚不清楚就读学科的大学生相较于其他大学生而言,其焦虑状况更为明显。他们的焦虑总水平得分(23.35±10.34)高于就读人文艺术类专业(23.06±10.19)、社会科学类专业(22.90±9.61)和自然科学类专业(22.59±10.66)的大学生群体。同时通过进一步了解得知,尚不清楚就读学科的大学生群体中,有55%的人为大一年级新生,反映出这一群体普遍存在的大学生活过程中的心理适应问题[6]。学习适应不良作为重要表现之一[7],可能导致其对就读学科认识模糊,并使该群体相较于其他大学生群体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更容易出现焦虑症状。综上,女性群体、专科生群体、尚不清楚就读学科的大学生群体,其焦虑水平更高,焦虑症状表现更为明显。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以上三类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应当引起社区、高校等相关机构的密切关注。
-
依据汉密顿对焦虑因子的分类,通过对性别、培养层次、就读学科等基本信息变量和焦虑影响因子变量的结果分析得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群体的焦虑主要表现为精神性焦虑。在基本信息方面,不同性别大学生的精神性焦虑水平明显高于其躯体性焦虑水平。具体而言,女性大学生的精神性焦虑水平平均得分为13.36±5.88,高于其躯体性焦虑水平平均得分(9.89±4.49);男性大学生的精神性焦虑水平平均得分为12.51±6.19,也高于其躯体性焦虑水平平均得分(10.04±5.11)。不同培养层次的大学生精神性焦虑水平也明显高于其躯体性焦虑水平。具体而言,专科学生的精神性焦虑水平平均得分为13.67±6.35,躯体性焦虑水平平均得分为10.29±5.06;本科学生的精神性焦虑水平平均得分为12.90±5.79,躯体性焦虑水平平均得分为9.79±4.48。就读不同学科的大学生精神性焦虑水平也明显高于其躯体性焦虑水平。其中,尚不清楚就读学科大学生的精神性焦虑水平平均得分为13.32±6.01,高于其躯体性焦虑水平平均得分(10.03±4.74);就读人文艺术类专业大学生的精神性焦虑水平平均得分为13.18±6.02,高于其躯体性焦虑水平平均得分(9.88±4.50);就读社会科学类专业大学生的精神性焦虑水平平均得分为13.06±5.76,高于其躯体性焦虑水平平均得分(9.84±4.30);就读自然科学类专业大学生的精神性焦虑水平平均得分为12.69±6.11,高于其躯体性焦虑水平平均得分(9.90±4.93)。在焦虑影响因子变量方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在“时常担心和担忧最坏事情发生,易被激惹”(焦虑心境)、“有情绪反应、不能放松、感到不安”(紧张心理)、“害怕黑暗、陌生人、独处、动物、人多的场合”(焦虑心理)、“难以入睡、易醒、睡眠浅、多梦、睡醒后感到疲倦”(睡眠问题)、“注意力和记忆力较差”(认知能力问题)、“对一般事物或曾经喜爱事物丧失兴趣、忧郁”(抑郁心境)和“与人谈话时紧张、咬手指、握拳、面肌抽动”(人际交往行为焦虑表现)等7项精神性焦虑水平指标上,平均得分高于其躯体性焦虑水平平均得分。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社区、高校等相关机构应当着重研究精神性焦虑的诱发原因、症状病理、临床表现、人群特点等因素,采取有针对性的心理咨询和援助措施。
-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每日上网时长与其焦虑水平呈显著正相关。本次在线测试结果显示,每日上网时长5小时以上的大学生焦虑总水平得分最高(23.72±10.44)。同时,他们的躯体性焦虑水平平均得分(10.17±4.88)和精神性焦虑水平平均得分(13.55±6.11)也最高。每日上网时长4~5小时的大学生焦虑总水平得分(23.10±9.78)次之,他们的躯体性焦虑水平(平均得分9.96±4.43)和精神性焦虑水平(平均得分13.13±5.82)也与其焦虑总水平密切相关。另外,每日上网时长1小时及以内和上网时长为2~3小时的大学生,其焦虑水平差异不显著,前者焦虑总水平得分(21.88±10.44)仅略高于后者(21.66±9.66)。同时,每日上网时长1小时及以内和上网时长为2~3小时的大学生,其精神性焦虑水平差异也不明显,前者得分(12.32±6.11)仅略高于后者(12.25±5.68)。进一步对每日不同上网时长的大学生焦虑水平进行比较,发现每日上网时长为2~3小时的大学生与上网时长为4~5小时的大学生(t=-2.890,F=2.971,P=0.004 < 0.01)和上网时长5小时以上的大学生(t=-4.646,F=14.027,P=0.000 < 0.01),在精神性焦虑水平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性。值得一提的是,梅茨格(Metzger)等人的研究证实,大学生群体普遍存在无意识地严重依赖网络信息的现象[8],且绝大多数学生上网缺乏明确目的[9]。本研究对被调查大学生“上网目的”进行调查的结果也证实,37.04%的大学生上网目的是“获取信息”,39.11%的大学生是“休闲娱乐”,说明75%以上的大学生,每日上网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漫无目的地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上。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一些人会散播虚假言论,引发网民的恐慌”[10]。有研究表明,我国信息焦虑人口占全国4%左右,青年人是主要群体,并已发展成为社会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11]。伍曼(Wurman)认为,信息焦虑既降低生活质量,又易引起焦虑、困惑等焦虑情绪;李维斯(Lewis)的研究也进一步提出,信息焦虑会诱发信息疲劳症,信息疲劳症候群表现出焦虑、记忆力不佳等系列症状。个体的上述症状持续失控后会出现无助、沮丧等情绪反应[12],同时,还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心理负担,诱发或加重焦虑情绪。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社区、高校等相关机构应当对大学生的上网时间和频率进行科学引导,帮助大学生形成科学的网络媒介素养。
一. 近一半大学生表现出明显焦虑
二. 女性、专科层次、尚不清楚就读学科的大学生群体焦虑水平更高
三. 主要表现为精神性焦虑
四. 每日上网时长与大学生精神性焦虑水平呈正相关
-
大卫·佰恩兹(David D.Burns)提出的由觉知令人不安的事件、描述情绪体验、暴露消极思想、搜寻认知歪曲、树立积极思维等一系列步骤组成的CBT焦虑循证疗法,可有效指导大学生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调适焦虑情绪和外部压力[13]。同时,依据本研究的结果和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的现实状况,笔者认为,高校和大学生所在社区教育单位应在积极强化和完善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通过线上咨询、干预等方式,主动积极地运用心理调适技术调节大学生的焦虑水平。
高校和大学生所在社区教育单位就此可以采取的一般性防御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建立健全依法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防机制,坚持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应收尽收,依法控制和积极应对;(2)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依法处置机制,在认真调研和科学研判的基础上,针对病原体的影响范围实施区别化、精准化的隔离、防控和诊治方案,将疫情危害波及范围控制到最小;(3)建立健全疫情信息及时发布和舆论监控机制;及时依法向社会公布疫情发展程度、影响范围和应对措施,并对疫情防控期间,不同层级信息源发布的信息进行及时跟踪和核实,加强疫情防控期间的舆论监控,防止不实言论、不良言论、恶意言论影响公众对事件的科学判断;(4)进一步加强和倡导文明卫生习惯及移风易俗、生物安全等专题宣传教育活动,有效监管公共卫生区域、社区(村落)、家庭卫生状况,落实群体和个体防护意识及行为监管主体责任;(5)高校和大学生所在社区教育单位应积极引导大学生树立积极健康的人生观,秉持对社会大众负责任的态度,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决策和部署。
高校和大学生所在社区教育单位可以采取的具体应对措施有:(1)依托官方媒体的科学报道,引导大学生树立新冠肺炎可以预防、可以控制、可以治疗的正确观念,对党和国家在此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战胜新冠肺炎的举措充满信心,坚信“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14],因为较高的自信心有助于降低个体的焦虑水平[15];(2)整合网络资源开展在线科普活动,帮助大学生科学认识新冠肺炎等传染性疾病的病理、传播方式、诊断原理、治疗手段,对疫情发展趋势形成科学判断,改善自身的卫生习惯,增强安全防护意识和遵纪守法观念,避免由于认识不全面造成不必要的焦虑等负面情绪,影响身心健康;(3)挖掘疫情防控期间大学生群体中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例,树立良好榜样,并在学校官网、院系和班级QQ群、微信群大力宣传和报道大学生中的先进典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主动抗击疫情的正能量,丰富立德树人内涵;(4)关心和爱护每一名学生,及时跟进疫情防控期间学生居家过程的学习、生活状况,深入了解不同学生的需求和困难,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学生缓解后顾之忧,增加大学生在疫情防控期间的抗压能力;(5)积极开展形式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服务活动,传授给大学生常用的心理保健知识与技术,让他们能主动应对和处理心理问题,缓解在此期间的焦虑等不良情绪,同时对存在心理障碍、有心理咨询需求的大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援助服务,帮助他们尽快从心理不适中走出来,恢复健康心态;(6)鼓励大学生开展多种适宜的居家体育健身活动,使他们增强体质,提升免疫力,进而增强抵抗新冠肺炎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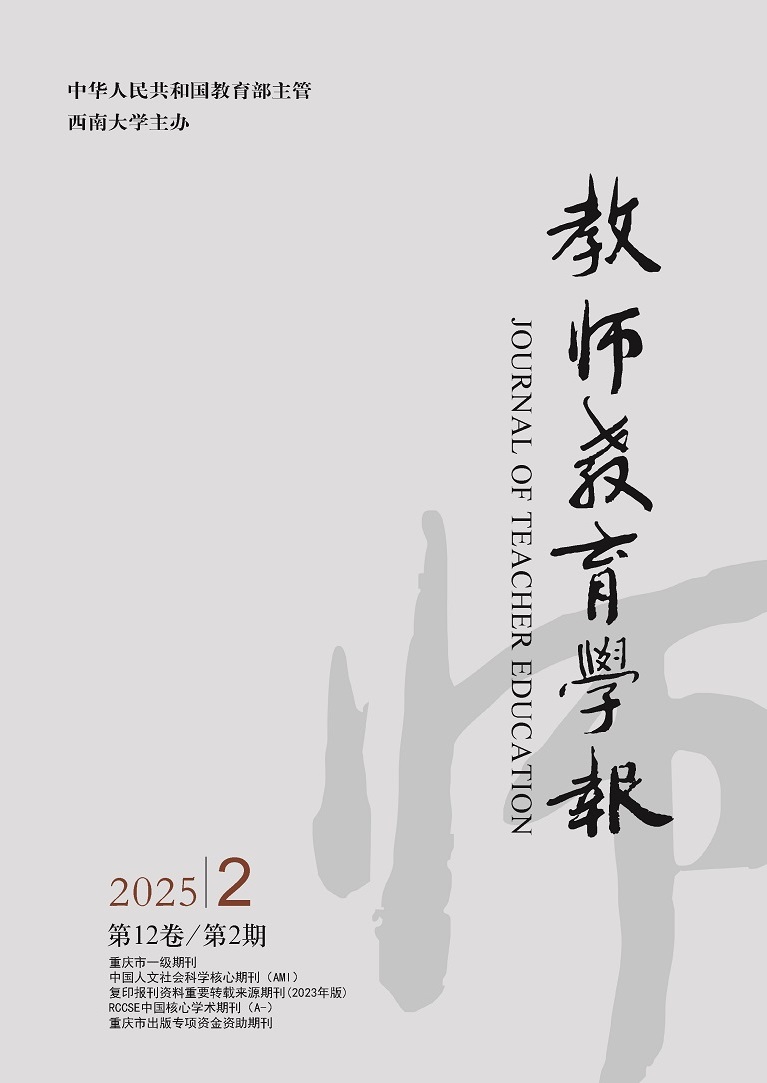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