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汉帝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之一大变,实现了政治大一统,也推动了族群整合。钱穆提出秦统一推动了“中国民族之抟成”[1]116; 范文澜从共同语言、地域、经济、心理特征四要素论证了“汉族在秦汉时已经开始形成为民族”[2]; 罗志田指出秦统一后,“复数的诸夏”成为“单数的统一之华夏”[3]32; 葛兆光认为自秦汉起,“语言文字、伦理风俗和政治制度就开始把民族在这个空间中逐渐固定下来”[4]28。
上述研究展示出秦汉帝国政治大一统对华夏整合或汉族形成的重要影响,但对“华夏”或“汉族”的界定,往往依据“华夷之辨”观念或近代“民族”“族群”概念,因而受到新近研究的挑战。较典型的是,胡鸿提出“走出族群看华夏”,倡导以政治体视角来考察“华夏”的性质及形成[5]2-19,并论述了秦汉帝国如何“凝聚复数诸夏成为单数华夏”[5]35-45。从政治体视角来审视“华夏”,抓住了古代中国“特有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一性传统”和“华夏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相互交叉、合一的特殊性”[6],但对中国古代以文化分辨“华夷”的传统不无忽视之嫌。对此,朱圣明在肯定胡鸿之说的基础上,提出政治与文化都是界定作为“族群”的“华夏”的重要因素[7]20-28,或为平允之论。
无论采用哪种视角,既往研究皆注意到秦汉帝国对族群认同的塑造作用,但也不乏有待讨论之处:其一,研究者提出秦汉统一促使“复数诸夏”走向“单数华夏”,或形成“汉人”认同,但此前“复数诸夏”在族群认同上是什么情形?其二,秦末汉初,政治统一出现“逆流”,对族群认同造成怎样的影响?笔者注意到,战国至西汉前期,存在着以“国”为名号的人群称谓,例如秦人、楚人、汉人、齐人等,可统称作“国人”。他们与西周春秋的“国人”不无渊源,但性质和范畴皆发生变化,其中蕴含着重要的政治认同和族群认同信息。对此考察,庶几能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新的线索。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考察战国秦汉的“国人”意识与族群认同,审视秦汉帝国如何塑造“华夏”。
HTML
-
战国时期,存在以列国为名号的人群称谓,包括秦人、齐人、楚人、赵人、魏人、韩人、燕人等。例如翟强谓魏襄王:“晋人见楚人之急,带剑而缓之; 楚人恶其缓而急之。”[8]卷25,940武安君说秦昭王曰:“长平之事,秦军大克,赵军大破; 秦人欢喜,赵人畏惧。”[8]卷33,1250其中“楚人”“晋人”“秦人”“赵人”,皆指某国之人。这种以“国”为号的人群称谓,可统称作“国人”。比如赵孝成王时,公孙龙论封赏不均,称“亲戚受封,而国人计功”[8]卷20,732,“国人”指赵国民众; 再如燕惠王遗乐毅书,提到“寡人之罪,百姓弗闻”,因乐毅言之于外,以致“寡人之罪,国人不知,而议寡人者遍天下”[9]卷3,347、356,“国人”与燕国“百姓”相当; 又楚考烈王时,李园欲杀春申君,“国人颇有知之者”[8]卷17,593,亦指楚国民众。晁福林指出战国时期的“国人”,不同于西周春秋的“国人”,“多指某国之人”[10]。
西周春秋“国人”的内涵和性质,虽存争议,但大体认为“国人”出自统治氏族,在列国政治中有参政议政、废立君主、组成军队等权利,而与“野人”有别。西周春秋列国“国人”,也可作“某(国)人”,如《春秋》《左传》中“晋人”“卫人”“郑人”“齐人”等,即多指该国“国人”[11]。由春秋入战国,“国人”内涵的变化,源自“国野之别”的消除。而这与郡县制、户籍制的施行和兵役制度的变化息息相关。
春秋晚期,郡县已出现; 至战国,郡县制在列国普遍推行。近年,研究者据楚简指出,楚国或因灭国置县,破坏了原有的政治与宗族体系; 或改贵族采邑、县邑设县,破坏了旧的基层政治结构[12]14-16、64-65。列国的郡县制虽存在差异,但在推行过程中,旧的基层组织无疑都遭到破坏和重组,打破了原本的国野体制。同时,列国施行户籍制度,对“国人”“野人”以及新征服地区的民众采用同样的管理方式。“编户齐民”成为一国民众共同的新身份,皆需承担赋税、徭役、兵役等义务。尤其“当兵特权由国及野”,“国人”与“野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差异走向泯除[13]139-148。
“国野之别”消弭,“国人”内涵转变为一国民众,“国人”意识也随之诞生。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呈现出“领土国家”面貌[14]89-94。国际政治学者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认为战国列国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类似,为“领土国家”和“主权国家”[15]5。在这种情形下,列国“国民也各有其认同与归属”[16]25-26。这种认同和归属感,即列国“国人”意识。它是一种国家意识和政治认同,在兼并过程中,“呈现为强烈的坚持其国家主权”[16]26。较典型的是,燕将乐毅下齐七十余城,而“齐人未附”[17]卷82,2974,成为田单复齐的基础。
当时,列国皆在国内统一法令、文字和度量衡,“凝聚控制疆域内诸种人群”,从而“形成新型的、以国家为基础的”“国族群体”[18]。这种“国族群体”,有各自的文化特点,所谓“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19]卷6,212。《孟子·滕文公下》载孟子讲的“楚人学齐语”假喻[20]卷6,151,表明“楚人”与“齐人”存在语言和习俗差异。《吕氏春秋·用众》曰“戎人生乎戎,长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 楚人生乎楚,长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21]卷4,101,亦显示出“楚人”的“地域文化人群”性质[18]。是故,列国“国人”,皆为一政治-族群共同体。“国人”意识既是以国家为依托的政治认同,又是基于一定制度与文化的族群认同。
列国“国人”意识,又因敌国、它邦等“他者”的存在而得到强化。“岳麓秦简”《尸等捕盗疑购案》提及“秦人”和“它邦人”,即呈现出“我者”与“他者”之别。在简文中,“秦男子治等”被称作“秦人”; “荆男子阆等”被称作“荆人”“荆邦人”,因不属于“秦人”,亦称“它邦人”,二者在法律权责上存在明显不同[22]113-117。沈刚指出“它邦人就是不在秦国户籍上的他国人”[22]145,显示出编户身份对“国人”身份的界定功能。“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也提到“秦人”与“臣邦人”之别[24]250。“臣邦人”为秦国臣邦、属邦之人,而不同于秦国本土民户——“秦人”。“它邦人”和“臣邦人”,构成了“秦人”自我认同的“他者”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提出春秋“诸夏”认同“着眼于共同的礼乐文化和政治立场,开始超越一族一姓的狭隘血缘关系”; 至战国,七国皆在“诸夏的政治体系”之内[5]42-43。此说对春秋“诸夏”的认识诚属卓见,但对战国列国的认识却不够充分。盖春秋“诸夏”上承西周封建体制,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彼此间尚存在一定的政治认同; 而至战国,列国兼并,统一的政治认同已彻底崩溃。正如许倬云所论,“若与春秋华夏诸侯还有相当共同意识相比”,战国列国隔阂极大,只是“还不曾强调种族主义而已”[16]26。而且,战国结盟并不限于“诸夏”之间,例如秦惠文王七年(公元前318)“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17]卷5,261。显然,战国时期,所谓“诸夏的政治体系”,并非是由列国的“政治立场”来维系的。
《荀子·正论》曰:“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 [25]239所谓“仪”,王念孙曰:“谓制度也。”[26]1831制度可分为政治制度与礼乐制度。列国政治制度虽不尽相同,但在将相制、郡县制和文书行政等重要方面颇为相近,兼之战国士人流通,列国制度不乏共通之处。礼乐制度,自西周、春秋以来,即为列国“诸夏”认同的重要表象,并成为文化视角下“华夷之辨”的基础。战国“诸夏政治体系”,正是基于政治制度和礼乐制度形成的。
从西周春秋至战国,列国“领土国家”的形成,一方面促成列国内部的人群整合,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列国之间的隔离和分裂。前者促使列国“国人”意识的形成,而后者却令昔日基于封建制度或“尊王攘夷”理念的统一的“诸夏”政治认同趋于瓦解和崩溃。但列国间政治制度和礼仪制度的共通性,维系了“诸夏”政治体系和文化认同。就此而言,春秋战国之际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令时人产生了“二重认同”,即“诸夏”认同和“国人”认同。“国人”认同,可谓是“诸夏”认同之下的亚族群认同。而“诸夏”认同的维系,促使战国由分裂走向政治“大一统”,也为后来秦汉帝国的族群整合奠定了基础。
-
秦并六国,统一“诸夏”,六国“国人”意识依托的政治体不复存在,促使“复数诸夏”走向“单数华夏”。其实,战国秦国已通过推行郡县制、编户制和秦法,有意识地将新兼并土地上的人群整合到“秦人”中。《商君书·徕民》提到秦国存在“故秦(民)”与“新民”之别[27]卷4,92; “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也提到“故秦人”[24]158。“故秦人/故秦民”为“秦国旧有的人民”; 而“新秦人/新民”则是新征服或归顺之人,通过“纳入秦国版籍”,整合进“秦人”[18]。秦统一后,延续并发展了上述做法,推动“故秦人”与六国故民的整合,以期将“秦人”身份在秦帝国疆域内普及,塑造新的“秦人”认同。
历史学家范文澜将秦朝“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和划定疆域比对为共同语言、经济生活、心理状态和地域等“民族”四要素[2]; 民族学家费孝通认为秦朝“车同轨,书同文,立郡县和确立度量衡的标准,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为统一体立下制度化的规范”,是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实体形成的重要一步[28]10-11。二说提示我们秦朝族群认同的塑造,是在帝国官方主导下进行的。“秦人”认同的普及,实质是令“故秦人”与六国故民(“新秦人”)“同质化”,亦即“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7]卷6,304。具体来讲,包括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两个方面。
在政治认同上,秦朝在帝国疆域内推行郡县制和编户制,对“故秦人”、六国故民和其他族裔人群采用相同的统治方式,使之具有同等身份。其他人群,是指秦帝国编户中戎人、越人、淮夷等原非“诸夏”人群,比如“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29]卷85,2809。各郡县编户(黔首)在法令上具有同等权责,皆需依法承担赋役,打破了不同人群以往的政治隔阂,实现政治身份的“同质化”,推动新“秦人”认同的形成。
在文化认同上,秦帝国在“法令由一统”的基础上,整齐各地的文化与风俗。战国列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30]卷15,315,正是列国“国人”意识存在的文化基础。秦法的推行,以法令整饬各地风俗。“睡虎地秦简”《语书》,为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南郡守腾发布的文告,即提到“乡俗”“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故设“法律令”“以教道民,去其淫避,除其恶俗”[24]29。这篇文告虽发布于秦统一前,但“以法化俗”政策为秦帝国延续。工藤元男即认为《语书》反映了秦朝“追求一元化统治的坚强意志”,为此否定社会旧俗,“督促秦法的彻底化”[31]361。这从始皇刻石可得到证明,比如琅琊刻石曰“匡饬异俗”,之罘刻石曰“黔首改化”,会稽刻石曰“禁止淫佚”[17]卷6,314、320、333。清人顾炎武即认为秦朝“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32]卷13,752。除整饬风俗外,秦朝“书同文字”,从文字和用语上消除各方言人群的隔阂,确保帝国内部交流和文书行政的畅通[33]; 统一学术,焚毁六国史书和百家语,“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17]卷87,3091; 整合各地信仰,确立国家祭祀[34]76。秦帝国从文字、学术和信仰三方面,塑造统一的“秦文化”,促使帝国编户实现文化“同质化”。此外,秦始皇采纳“五德终始说”,确立“黄帝—夏—商—周—秦”的华夏王朝正统序列,将帝国编户纳入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祖先记忆,也有助于强化帝国民众的认同。
正如葛兆光所论:“身处一个共同空间的人们,在统一帝国影响下,都对这一文化、信仰和历史给予‘认同’的时候,由‘语言与书写文字的媒介’联系起来的这个文化传统、神圣信仰和共同历史中的人,就会想象自己拥有一个传统,因而也应当是一个民族,理应成为一个国家。”[34]74秦帝国从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推动帝国内部人群的“同质化”; 兼之“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17]卷6,307-308,加强帝国内部人群的联系,试图令“秦人”认同得到帝国各地的普遍接受。
秦帝国自上而下的新“秦人”认同塑造,取得了一定成功。鲁西奇已指出鄢郢地区的“楚人”渐次“秦人化”,演变为“新秦人”[18]。再如秦汉时朝鲜半岛南部的辰韩,“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言语“有似秦人”,亦称“秦韩”[35]卷30,852。“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者,多来自燕齐地区,若秦韩确因“秦人”得名,则“秦人”身份已被部分燕齐之人接受。“秦人”还成为周边族群和外国对中原人的称呼,甚至延续至汉代[28]169-170。颜师古即谓《汉书》中汉代匈奴人“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36]卷96,3914。不过,研究者也注意到,在秦代,“各地区的名称如燕人、齐人、赵人、魏人、楚人等仍然存在”[37]76。可见,各地对“秦人”身份的接受并不彻底,旧的“国人”意识仍然存在。这种情况的出现,实源自秦国与山东六国在法令制度和文化风俗上存在较大差异。宫崎市定即注意到,秦国法制与六国旧俗多有差异[38]84-85; 陈苏镇认为“秦之‘法律令’与关东文化存在距离,特别是与楚‘俗’之间存在较大距离”[39]37; 李禹阶指出秦与关东,尤其是齐、鲁文化,存在价值观上的冲突[40]。因法制和文化上的差异,六国故民对秦法往往难以接受; 而秦帝国却以强硬甚至残暴的手段来推行秦法、秦制,无疑加剧了秦国法制与六国旧俗的冲突。这反而激起了六国故民的故国之思和残存的“国人”意识。比如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17]卷7,385,正是故楚之人怀有强烈“楚人”认同的表现。
六国故民“国人”意识尚存,无疑给秦帝国塑造的新“秦人”认同带来危机,也为秦帝国的覆灭埋下了伏笔。汉人徐乐称“秦之末世”可谓“土崩”,“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36]卷64,2804-2805,正是秦朝政治认同危机的写照。因此,秦末,陈胜起事,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17]卷6,355,六国得以复兴。随着秦帝国崩溃,新塑造的“秦人”认同也随之瓦解。“秦人”身份又缩回到“故秦”范围,比如刘邦入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史称“秦人大喜”[17]卷8,459,此“秦人”即指关中百姓。
新“秦人”认同的塑造与瓦解,表明在族群认同塑造上,来自帝国自上而下的权力,往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或者说,在统一政权下,政治认同是族群认同的先导和基础。而制度和文化的整合,则是塑造政治-族群认同的手段与工具。然《荀子·议兵》曰:“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25]206自上而下的权力,或能起到一时之效; 但新认同的维持,必有赖于制度和文化整合的完成。新“秦人”认同的瓦解,正源自秦国与山东六国间法制和文化的鸿沟较深,并非是短期内通过强制手段所能消弭的。
-
史家李开元将“秦末陈涉起义至汉景帝在位之间”的历史时期称作“后战国时代”,他写道:“秦王朝在此期间崩溃,战国七国在此期间复活,项羽在此期间称霸分割天下,汉王朝也在此期间诞生。”[41]74-75在“后战国时代”,“楚人”“齐人”“赵人”等以国为号的人群称谓再次出现。这些“某(国)人”称谓,被统称作“诸侯人”“诸侯国人”。例如《汉书·高祖纪》载刘邦立为汉王,“楚子、诸侯人之慕从者数万人”。[36]卷1,29文颖曰:“楚子,犹言楚人也。诸侯人,犹诸侯国人。”再如汉文帝时,淮南王“聚收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17]卷118,3741。“汉、诸侯人”,即“汉人”与“诸侯国人”[42]3527。
鲁西奇指出秦楚汉之际的“楚人”,是兼具政治体和族群性质的人群[18]。其实,齐人、赵人、燕人等“诸侯国人”,也同样如此。比如齐人,在秦末支持田儋、田横兄弟等故齐王族复齐,“以距诸侯”[17]卷94,3207-3210,展现出强烈的政治自立性和认同感。韩信谓刘邦曰“齐伪诈多变,反复之国也”[17]卷92,3178,实为“齐人”政治自立性的表象。刘邦立韩信为齐王,及招揽齐王田横,以“存恤楚众”,也是考虑到齐地的政治文化特点[39]75-76。后来,刘邦立刘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17]卷52,2427。语言是文化和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刘邦此举则是顾及齐人的文化认同。可见,秦末汉初的“齐人”,既是以复兴的齐国为依托的政治人群,又是基于齐地文化的族群。
秦楚汉之际的“诸侯国人”,彼此互为“他者”,还以周边族群为“他者”。《汉书·高帝纪》载汉四年(公元前203)八月“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36]卷1,46。“燕人”与“北貉”并列,当具族属或种族性质。再如《史记·朝鲜列传》称“(卫氏)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卫满亡命后,“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17]卷115,3617。“故燕、齐亡命者”与“真番、朝鲜蛮夷”并举,显示出“燕人”“齐人”的族属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秦末汉初的诸侯国与战国七国并非完全一致,“诸侯国人”与战国“国人”也不完全重合。比如项羽封诸侯,分秦地为汉、雍、塞、翟四国,分楚地为西楚、九江、衡山、临江四国,分齐地为齐、济北、胶东三国。不同国别的“诸侯国人”,政治身份无疑有别; 但在族群认同上,因与战国“国人”无法完全割裂,造成政治身份与族群认同的复杂关系。鲁西奇指出,项羽“分楚为四”后,楚地之人“以不同的政权为依托,成为不同意义上的‘楚国之人’”[18]。至汉初,张良还将淮南国人称作“楚人”[17]卷55,2485。与之类似,三齐之人皆以“齐人”自居,三秦之人皆以“秦人”自居。可见,诸侯国作为政治体,固然是划分人群身份的重要依据,却非判断族群认同的绝对标准。对秦楚汉之际“诸侯国人”的族群认同来讲,战国以来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可能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历史记忆和文化风俗,成为超越政治体的族群认同的基础。
在列国“国人”意识复生的同时,还出现一个重要现象,即“秦人”身份走向消弭,而“汉人”人群出现。上文指出,秦末,“秦人”认同缩回到“故秦人”的范畴。但他们仍保持较强的认同感。项羽分封“三秦”,而治下之民皆称“秦人”“秦民”[17]卷92,3168-3169。然随着汉定关中、灭“三秦”,“秦人”渐次融入“汉人”中。
“汉人”称谓出现,刘志平近年指出,是在楚汉相争之际,系“汉王刘邦一方人员之统称,是‘汉’这一新诸侯王政权名号统摄下的包含‘秦人’‘楚人’‘燕人’‘韩人’‘赵人’‘魏人’‘齐人’等在内的人群集合体”,但还不是“族群与文化意义上”的人群称谓[43]。其将汉初“汉人”界定为政治人群,堪称卓见。刘邦集团本多为“楚人”,立为汉王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17]卷8,465,加上巴、蜀、汉中的“秦人”,共同构成最初的汉国之人(“汉人”)。
“汉人”身份自始即以政治归属来界定,与作为政治-族群共同体的“楚人”“齐人”等存在较大差异,其人员构成呈现出多元化面貌。这令“汉人”身份具有较大的变动性和包容性。其范畴会因汉国扩张、诸侯国人归降等原因而扩大,也会因分封诸侯、吏民军士逃亡等情况而缩小。“汉人”构成的多元化及其身份的包容性,为日后“汉人”身份与认同的推广提供了便利。
随着楚汉战争的发展,“汉人”范畴逐步扩大,而关键点即关中秦人的“汉人化”。田余庆曾提出汉朝建立过程中“非承秦不能立汉”之说[44]28; 陈苏镇进一步解析为“据秦之地”“用秦之人”和“承秦之制”[39]43-66。秦人的“汉人化”,也是“汉人”政治体扩大的关键一步。我们注意到,汉国“郎中骑”左右校尉重泉人李必、骆甲曾自称“故秦民”[17]卷95,3234,正是秦人“汉人化”之遗痕。
随着汉国兼并诸侯,更多“诸侯人”加入“汉人”。但因诸侯国的存在,“汉人”与各诸侯国“国人”间始终有别,即便某诸侯国臣属或依附于汉。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刘邦即皇帝位,天下归汉后。陈苏镇指出汉初“东西异制”:西部为中央直辖郡县,由中央派遣郡守、县令“奉汉法以治”; 东部为诸侯国,在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皆有一定自主权,“从俗而治”[39]66-107。汉朝分封诸侯王,有着缓解地区文化冲突的考虑; 而诸侯国的存在,却强化了各国的“国人”意识。在这种形势下,“汉人”往往“只是与关东‘诸侯人’相对的汉朝直辖地区的人群称谓”[43]。而“诸侯国人”,在汉法中,被视作“它国人”[45]93。
汉朝与诸侯国并立的形势,自汉文帝朝逐渐发生改变。历经文景二朝的削藩和七国之乱的平定,“王国的独立性日益削弱,中央对王国的控制逐渐加强”,汉朝法令“越过关中和关东、郡县和王国的界线”,推广到原诸侯国地区[39]107。伴随着诸侯国“日益削弱”,“诸侯国人”意识也渐趋瓦解。至武帝朝中前期,“后战国时代”结束,诸侯国与汉郡相差无几,“诸侯国人”与郡县编户民身份趋于等齐。原本的“诸侯国人”意识也走向消弭,而代之以“汉人”认同。“涵括旧‘汉人’和‘诸侯人’的整体性的新‘汉人’认同”最终形成[43],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从“复数诸夏”到“统一华夏”的转变。
在一定程度上,“汉人”认同的塑造,是对秦朝塑造新“秦人”认同的重复,同样是在帝国主导下,以权力来塑造编户民的政治-族群认同。但汉朝经历“郡国并行”阶段的过渡,推行汉法、汉制的方式较秦朝要缓和得多,从而较稳妥地规避了不同地区文化的强烈冲突,最终将“汉人”认同推广到汉帝国的疆域内,实现了“统一华夏”的重塑。
同时,“汉武帝时代的版图扩张,也促使了汉文化共同体的内聚力的显示”[46]405,“汉人”国家意识和族群认同因之增强。在汉朝与周边族群的交往中,“汉人”的族属或种族性质得到凸显。贾敬颜注意到东汉“汉人”“汉民”之称,不乏出现在与周边族群互动的语境中[28]170; 刘志平进一步举证,指出“汉人”称谓在西汉已具有族属含义,至东汉更加明显[43]。在“汉人”认同普及的同时,“中国人”所指也由“中原人”转变为统一的汉帝国统治下的编户齐民[47]1-54。与之相对,“汉人”将周边政权人群则称作“某国国人”,如“大夏国人”[36]卷61,2689、“莎车国人”[36]卷96,3897等,又统称为“外国人”,如匈奴降人金日磾自称“臣外国人”[36]卷68,2962。“外国人”作为“他者”存在,增强了“汉人”“中国人”的自我认同。
-
“国人”本指西周春秋时期的列国统治氏族; 至战国,随着列国内部的人群凝聚,“国人”内涵转变为一国民众。兼具政治认同和族群认同的“国人”意识,也随之形成。秦并天下后,从政治和文化两方面整合“诸夏”,推动六国故民“秦人化”,力图塑造新“秦人”认同。这一举措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秦法与六国旧俗的冲突,以及秦帝国塑造认同方式的强硬,激起了六国故民的故国之思和反秦情绪,最终造成秦帝国的崩溃和新“秦人”认同的瓦解。秦楚汉之际,列国复兴,“国人”意识得以再现。在此期间,“汉人”作为政治人群出现,与“诸侯国人”并立。历经文景二朝削藩,至汉武帝朝,诸侯国渐与汉郡趋同,“诸侯国人”成为汉朝编户,接受“汉人”身份。同时,在汉帝国与周边族群的互动中,汉朝吏民的内聚力得到加强,“汉人”的族属性质得以凸显,确立了兼具政治体和族群性质的“汉人”认同。
纵观战国秦汉的“华夏”和“汉人”认同的塑造,族群认同的形成,往往以政治体为基础,受政治认同和国家意识的直接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历史上的族群,具有政治共同体性质,与现代“国族”(nation)含义相近。但现代“国族”是民众自主选择的结果; 而中国历史上的族群,比如本文所论列国“国人”和“秦人”“汉人”,则是自上而下塑造的产物。普通民众在政治和族群认同上的选择机会极少,即便出现机会,“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民众的“主动性”也非常虚弱,“且很快消失”[18]。不过,“国家权力”在族群认同塑造上,也不是为所欲为的,受到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制约。这从秦帝国塑造的新“秦人”认同的瓦解即可窥一斑。
历史上的“华夏”或“汉人”认同,主要可划分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两个层面。胡鸿指出:“政治体意义上的华夏化是指加入或建立华夏式帝国政治体,被制度承认为华夏国家的成员,略等于‘王化’; 文化认同意义上的华夏化则涉及语言、习俗、祖源重构、心理认同等方面。这两者并非同步进行的,但一般来说,政治体意义上华夏化的完成基本可以宣告文化认同意义上华夏化的启动,只要不出现大的变故,两者间的差距只是时间。”[5]164需补充的是,在政治与文化之间,尚存在制度认同这一层面。本文即指出战国“诸夏”认同,有赖于列国制度来维系。制度认同涉及政治制度和礼乐制度,兼具政治和文化色彩,但又有别于二者。正如制度史家所论,制度在塑造中国社会形态和维系中国历史“连续性”上起到重要作用[48]8-9。秦汉帝国建立后,典章制度成为华夏帝国的重要标志。在“华夏”塑造上,它是促成政治与文化认同的内在强化剂。
政治(权力)、文化与制度,三者共同塑造了历史上的“华夏”或“汉人”认同。但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情境下,三者的作用有所不同,尤其是在政治统一时期和分裂时期差异尤为明显。在政治统一时期,政治认同对“华夏”或“汉人”的塑造起到主导作用,文化与制度整合往往成为手段或工具; 但其最终完成与维系,则又有待文化与制度认同的形成。在政治分裂时期,由于政治认同的崩溃,文化认同与制度认同,上升为各割据政权、地方政权维系“华夏体系”的主要因素,甚至推动周边民族政权“华夏化”。尤其是制度认同,成为周边民族政权“华夏化”的首要条件。研究者即注意到北族政权对华夏制度的接受与适应,是将其“纳入中国的制度与文化体系的重大步骤”[49]3。正是有赖于文化认同与制度认同的存在,“华夏”或“汉人”认同在政治分裂时期仍可维系,历久长存。历史上的“华夏”或“汉人”,也正是历经统一与分裂,不断重塑和壮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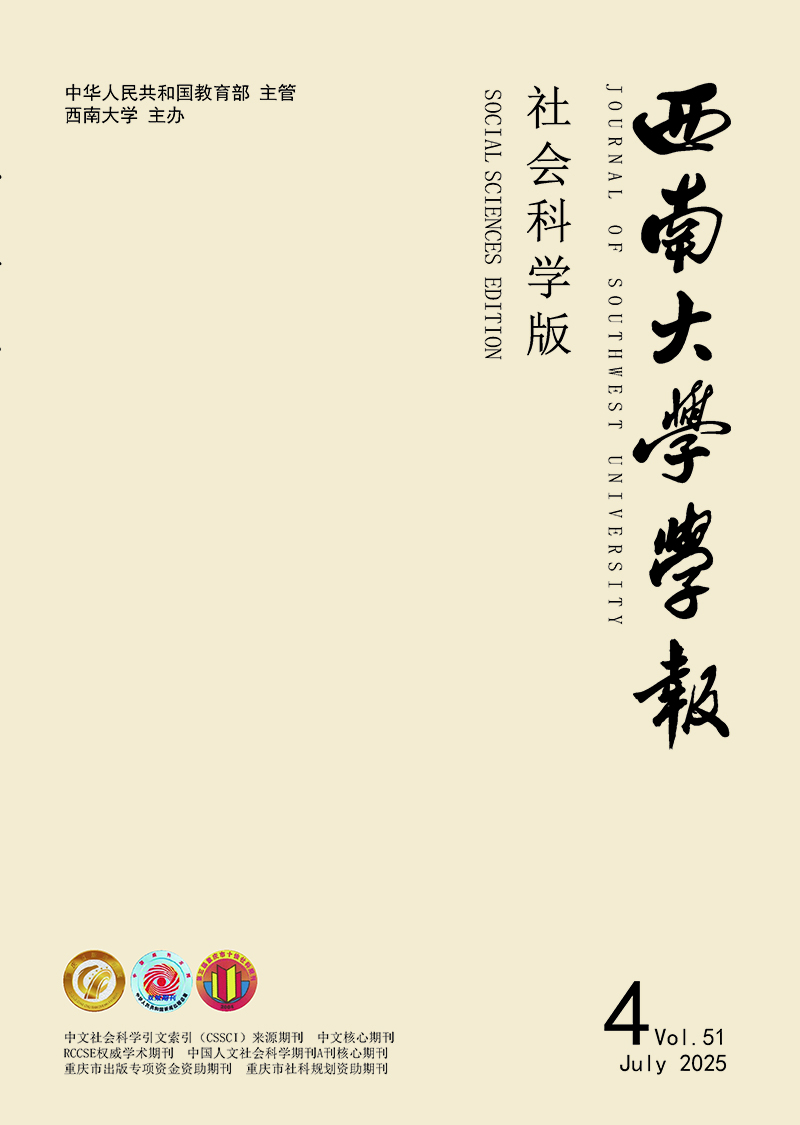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