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源于2019年年底,并在2020年初大规模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引发公共安全危机和全球性大恐慌,而关于病毒来源的假说也再度将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推上了风口浪尖。新型冠状病毒飘忽不定的发病时间和难以捉摸的发病规律,更是给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狂妄与自信敲响了警钟,并为我们重新思考自然的本质提供了反省之契机。在此背景下,对中西方文化中的自然观念进行考察,就成为一种必要与可能,并可为人类反思如何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提供启示与借鉴。本文拟对西方文化中最为常见的三种对自然的隐喻——“盖亚”“夏娃”与“伊西斯”,进行环境文化史回溯和哲学层面的阐释,并积极省思其对当代人类构建与自然良性互动关系的生态意义。纵观学界研究现状,目前尚无这方面的尝试。在现有为数不多的成果中,亦多囿于对三者分别展开研究,且大多流于宽泛。比如在对盖亚的关注上,学者们限于对盖亚的现代版本也即拉夫洛克提出的盖亚假说进行科普式介绍,或是满足于对中国的女娲和希腊的盖亚之母神给予粗略的对比分析;在对夏娃的研究上,学者多从女性视角出发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解析,且与生态话题相去甚远;在对伊西斯的研究上,学者们或挖掘伊西斯对古埃及文明的影响,或对伊西斯在希腊罗马时期在战争、医疗、航海和秘仪中所发挥的“拯救”功能进行历史爬梳,或试图厘清圣母玛利亚与伊西斯之间的历史性渊源,但都未从生态视角进行尝试性诠释。这也间接说明学界在本论题上尚存在可深挖的余地和空间,也由此使得本研究具有了一定的意义与价值。
HTML
-
盖亚(又名“盖娅”,Gaia,Ge),既是希腊神话中的地球(自然)女神,又是众神之母。传说正是由于她的出现,才将世界和人类从混乱的虚空中创造出来,并从此走向有序。“盖亚从永恒的虚空中向前跳着,把自己滚成一个旋转的球。她在自己的脊梁上塑造了群山,在肉体的凹陷处塑造了山谷。群山和绵延的平原有节奏地跟随着她的轮廓。从盖亚温暖的湿气中,带来了一股温柔的雨水,滋润着她的表面,带来了生命。蠕动的生物在潮汐池中繁殖,微小的绿芽从她的毛孔中向上生长。她填满了海洋和池塘,使河流穿过深深的垄。”[1]受该神话叙事影响,在荷西俄德和荷马谱写的希腊史诗中,盖亚都是以众神、人类、植物和动物的母亲的身份出现的。“万物都由她而生,死后又把所有的东西都归还于她。盖亚用她那富于创造力的子宫孕育了世界的一切,像看护自己的孩子一般养育和照顾着所有的生灵。”[2]古希腊人对盖亚也即地球女神充满虔敬,这不仅可从他们将自己称为“地球人”的这一喜好中看出来,还可从其对盖亚祭拜时所选择的地方窥见一斑。譬如,将祭品安放在泉眼之处,暗示着生命之水像母亲的乳汁一样从乳房中流出;摆放于洞穴,象征着万物都由之所生,从之所出;陈设于树林中,寓意着对地球旺盛生命力的崇拜。这些被祭拜的地方被看作圣地,任何人不得进行干扰和开发,比如砍伐树木、狩猎或捕捞等。在历史学家色诺芬笔下,盖亚甚至被描述成了一位充满正义感的女神。因为盖亚会将好的东西给予那些能更好地服务于她的人。“你服侍得她越好,她报偿你的好东西就越多。”[3]而对于人们的懒惰和胡乱行为,如使土地荒芜以及砍伐森林等,盖亚则会进行惩罚以示告诫。我们所熟知的正义之神忒弥斯,在希腊神话所提到的所有女神中,与盖亚的联系最为紧密也最为重要,因为据说忒弥斯是盖亚的女儿。之所以会被这样安排,是因为在古希腊人看来,地球有一套自己的法则,能保证她将正义传授给有能力向她学习的人。这些人会看护好土地上生长的植物,从而变得丰衣足食,也即会得到地球相应的回报。而那些给地球带来伤害的人,则会被施以报复。当然,希腊人之所以将地球比作一位伟大的女神,与他们的另一种想象——“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体”亦分不开。而在把地球看作是生命体的背后,实则蕴含了一种有机论的自然观。在古希腊思想家眼中,自然界是一个由其自身内部具有活力从而会不断运动变化的物体所组成的世界。如泰勒斯就把“自然界想象成为一个有机体:实际上就是一个动物”[4]34。亚里士多德也倾向于把地球也就是自然看作是有灵魂和充满活力的。在他看来,正是这种灵魂和活力,会使一粒种子如他在“四因说”中所描述的那样,有着努力实现自己的生命潜能,并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的冲动。“种子之所以生长,完全是因为它正在致力于变成一棵植物……尽管植物没有理智或心灵,不能想象我们所讨论的形式,但它有一个灵魂,因此它有要求或欲望。”[4]90或者如柏拉图所言,“宇宙是一个有生命的生物,一个可以感知的生物,在它的内部包含着所有与它在本质上相似的生物”[2],而这个生物被柏拉图赋予了灵魂和理性。斯多葛派紧随其后,将世界看成了一个理性的,充满和谐气息的有机体。恩培多克勒更是提出了“海洋是地球的汗水”的有趣论断。总之,对希腊人而言,地球是弥足珍贵的。而作为活生生的有机物和养育者母亲的形象,地球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约束,制约着人类的行动”[5]。
古希腊对自然的盖亚隐喻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了回响,只不过它更多是在人类面临全球性的环境破坏的背景下被提出的。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拉夫洛克提出的“盖亚假说”。拉夫洛克将“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看作一个自我调节的生命体”[6],认为地球自身能通过负反馈调节机制,抑制和减弱最初发生改变的那种成分的变化,从而尽可能地保持一种有利于生命活动的状态,使生态系统达到或保持平衡或稳态。“地球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它能够调节自身气候及其构成,以便始终适宜于那些居住其上的有机体。”[7]序13拉夫洛克的这一思想遭到了持“环境演化只由化学和物理力量决定”的正统观点的“硬科学家”们的质疑、反对甚至是声讨。比如《科学》和《自然》等顶级学术刊物的评审者在评议拉夫洛克有关盖亚假说的研究论文时,就给出“不予通过”的结论。理由是拉夫洛克的“观点是危险的”[8]。还有的科学家将“盖亚假说”视为异端学说,因为它似乎相信地球生命在主动、有意识地控制着环境。这种将科学与神秘和说故事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势必会把科学变成坏的科学。譬如生物学家理查德就反驳说,地球并非是生物体那样具有自主性的东西,因而不可能像生物个体那样进行新陈代谢活动。故此,将地球视为能通过自主调节以保持生活于其上的生命们活动的主张毫无根据,是必须被抛弃的。但拉夫洛克仍坚持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正是有赖于地球这个超级有机体也即“活着”的星球的持续运作,大气、海洋和土壤的状态才能始终适合生命,万物也才得以保持欣欣向荣的状态。而一个东西既然拥有如此让人惊叹和敬畏的力量,那就必须有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名称去加以指称。这个名称,则非古希腊人早已阐明的宇宙理论也即大地(地球)女神“盖亚”莫属。拉夫洛克还基于人类所面临的环境危机颇具深意地指出,如果盖亚是一个“活着”的、和谐的和有秩序的“有机体”,那么环境问题的突现毫无疑问反映了该有机体的不和谐或疾病。而盖亚总是坚强和严厉的,“她总是为那些遵守法则的人创造温暖而舒适的环境,但她对于那些越轨及破坏法则的人也会冷酷无情。她的无意识的目标就是一个适合生命的星球。如果人类妨碍这一目标,那么,我们将会被无情地消灭”[9]242。既然如此,盖亚就理应“成为我们审视地球、我们人类自身及我们同其他生灵相互联系的一种方式”[9]235,我们也应“强烈热爱和尊重地球”[7]序3,并积极进行纠错,以便更好地“在盖亚中生存”。
拉夫洛克的上述想法在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学者斯普瑞特奈克那里得到了声援。斯普瑞特奈克将拯救地球的良方寄托在恢复古老的自然女神崇拜上,也即盖亚女神身上。“穿裙子的耶和华并不能激发我们的好奇心。而女神的诸多外表和动植物图腾之间的神圣联系,神圣的小树林,如子宫般的洞穴,如月亮之节奏而周期般出现的月经,狂喜的舞蹈,感知盖亚的经验,她的丰满的轮廓和肥沃的平原,她的给予生命的流水……,这些才让我们为之着迷。”[10]在斯普瑞特奈克眼中,万物之所以呈现出一派繁荣和谐景象,从根本上说,与地球这个有着强大生育力的盖亚女神分不开。而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女权主义和生态象征,复兴对盖亚女神的崇拜不仅有助于打破和肃清充斥着父权制气息也即男性精神的犹太教和基督教观念,而且可恢复自然之神圣性,激发人们尊重自然之情感,这对于缓解当前的生态危机是非常有益的。美国环境史、环境伦理学和生态女性主义研究专家麦茜特则认为,当有机论的宇宙被进行了范式转换,也即转变成为机械论的宇宙时,盖亚的生命与活力便被抛弃,并沦为了一堆死的被动的质料。可以说,自牛顿以来的西方的机械科学与资本主义已经把地球变成了可从外部嵌入和操纵并被用来赢利的资源,伴随而来的工业污染则将大自然置于生态崩溃的边缘。“盖亚依然活着,但早已伤痕累累。她的肺被烟尘阻塞,她的头发被剪短,她那繁花似锦的长袍早已被撕碎,变得破烂不堪。”[11]人类也因此深陷困境。基于此,麦茜特推出了她的“伙伴关系伦理”[12]。在她看来,人类与大自然不应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应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人类应清醒地认识到并承认“自然是一个自主的行动者,且只能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被预测和控制”[13]。既如此,“自然为仆,人类为主”的“控制自然”观念就应被“视自然为伙伴”的“伙伴关系伦理”取代。
-
“夏娃”(Eve),作为西方文化中又一个被用于自然之隐喻的称谓,是众所周知的《圣经》中的角色。关于夏娃的诞生,也即“夏娃是什么时候被造的?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同时创造了夏娃与亚当,还是先造了亚当后再取其“肋骨”造了夏娃?”[14]这一问题,《创世纪》中有两个版本。在第一个版本中,据说上帝在创造了土地、海洋、青草、果实、太阳、星星,还有各种鸟兽之后,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也即亚当和夏娃,并告诫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天上飞行的鸟,地上爬行的野兽,海里游泳的鱼,都可作为他们的食物,供他们使用。而在第二个版本中,上帝则先是造出了植物和草药,接着从尘土中创造了亚当,然后创造了生命之树和河流。上帝还把亚当安排到伊甸园进行打理和看守。在用尘土造出鸟兽后,上帝把它们领到亚当面前让他一一命名。至此,夏娃才被上帝用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造了出来。不管是以何种方式出现,夏娃终是受了盘绕在象征知识和善恶之树上的蛇的诱惑,偷吃了禁果,并使亚当也一同吃了。他们因此获得了智慧,却也失去了继续停留在伊甸园的资格,并被上帝放逐到了尘世中。而按照神的旨意,亚当须终身经受劳苦,才能从他从之所出的土地上换取粮食与衣物。夏娃则不但会因怀孕和生产遭受身体上的苦痛,而且毕生要受丈夫管辖。
在西方有关重新返回伊甸园的叙事中,尽管堕落是由男人和女人也即亚当和夏娃共同造成的,但二者在其中却充当了不同的角色。由于男性亚当扮演的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所以在改造地球的过程中,男人便成为了技术和工具的发明和使用者。而被他们借助技术工具进行改造和征服的大自然,此时却被当成了夏娃。“如果说亚当是改变土地的英雄,夏娃就是被性别化为女性的大自然本身。”[15]110在关于美国殖民地的历史、文学和艺术等文化叙事中,夏娃被普遍地以三种形象进行了描述:等待开发的处女地;需被开垦的堕落的自然;有待收获的大花园。其一,作为处女的夏娃,她代表的大自然是原始、纯净和光明的。尽管它原始而贫瘠,但却充满了发展潜力,需要被探索和挖掘。其二,作为堕落的夏娃,她代表的大自然无序且混乱,是黑暗的和类女巫的,是需要被改良的荒野、荒地和沙漠。其三,作为母亲的夏娃,她代表的大自然是一个有待改善的花园;一个物产丰富的肥沃地球;一个成熟的卵巢和子宫[16]32。但不管是哪种形象,自然都被隐喻成了一个亟待被开发的对象:作为处女,它是有待开垦征服的处女地;作为堕落和无序之物,它必须“被驯服以使之屈服”[16]32;作为母亲,它是有待收获和享用的多产的大花园。
在美国文化中,夏娃作为自然的形象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而在恢复伊甸园的主流叙事中,自然则清一色地被描绘成了未被开发的“处女地”,其所蕴藏的丰富潜能可以通过人类智慧被大大释放。例如当时的探险家和地图师就乐见把美洲原始大陆描绘成一个半裸甚至全裸的女性,等待着男性去探索和引诱。而作为处女的自然在英国对美国的殖民叙事中也尽显无疑。英国的清教徒作为第一批来到新大陆的人,在面对空旷的荒野时内心除了恐惧,更多的是野心勃勃。扩大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则被其视为是所有野心中最健康和最高贵的。“要使荒野像玫瑰一样盛开,要建立法律,要努力使地球繁殖并对其加以征服,这是全能的上帝的第一命令。”[16]39清教徒们甚至将这片“无主之地”比作了一位“渴望在婚床上满足其爱人的处女”[16]42,认为通过技术和工业就可对其开垦征服。男性农学家则在“犁”这一农具技术的使用中,看到了如何唤醒大地的神秘力量并迫使其生产,就如同男性使女性生产一样。譬如农业改良人士亨利就热切地主张推广弗·培根通过发展农业以恢复失去的伊甸园的理想。“人类对自然行使统治权,命令他脚下的大地唤醒她神秘的能量……迫使死气沉沉的大地充满生机,并将营养、权力、健康和幸福传授给无数依靠她的人。”[15]117小说家诺里斯则使用了极具性意象的语言描写了大地渴望被人们开发的场景:“棕色的大地迎着晨光袒露出庞大的腹部,散发着朝露的湿气……大地像地毯般展开着……你在农庄里不消走上十来步路,就会猛然感觉到脚下的土地是生气勃勃的。它到底苏醒过来了,怀着生产的渴望,脉搏卜卜地跳着。在土壤深处,那颗巨大的心脏又跳动起来,激荡着热情,震颤着欲望,自动地献身,让犁来抚爱,一往情深,迫不及待。”[17]这种将大地视为丰腴的女性,等待着男性去耕种的想法在美国西部拓荒者和倡导者的想象中随处可寻。
在对自然形象进行贬抑,将其视为堕落的妓女、阴险的女巫,或是无序的混沌之物的过程中,培根可谓当之无愧的开路先锋。受《圣经》和《创世纪》启发,培根一心想要恢复人类曾在伊甸园中对万物的统治权。在他看来,亚当和夏娃在被上帝惩罚之前,并无对权力和统治的渴求。因为按照上帝的旨意,他们曾凌驾于所有造物之上,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由于一个女人的诱惑所引起的伊甸园中的堕落,人类失去了比之其他造物的优越性。因而,必须在被放逐到凡间后恢复自己的地位。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好途径,就是“越来越深地挖掘自然知识的矿藏”[18]187。也唯有借助这种方式,人类对宇宙统治的狭隘界限才能伸展到他们所意愿的任何疆域。就这样,通过对《圣经》的后续演绎,培根开启了开发自然的伦理许可和时代风尚。在他眼中,努力开启并扩展人类自身统治宇宙的力量是最有益和最崇高的目标。唯其如此,人类才可找回原本属于他的神所赐予的对自然的权力。而鉴于多年做法官的经验,培根不惜将自然比作邪恶的女巫或继母,主张只有用技术发明装置折磨它、审讯它、拷打它,才能使其吐露秘密,为改善人类福利服务。他还将物质贬低为一个低等妓女,认为必须对其隐蔽或从裂缝处进行窥探,方能破解它的秘密,以使之屈服。培根还对女性和自然进行了类比,认为正像女人的子宫只有服从手术用的镊子才能顺利生产一样,大自然的子宫也暗藏着极有用处但却不肯轻易吐露的秘密,故而必须借助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强取以迫使其“说出真相”[19]。而将自然比作母亲去尊敬,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殖民叙事中并不占主流,因为对攫取财富的狂热和征服未知疆域的野心,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进取精神的核心要义。在此精神引领下的人们,无一不因向大自然无休止地索取而变得狂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填满他们的钱袋和粮仓,才能使之获利。“资本主义的神秘之处在于,它把活的自然变成死的物质,把惰性的金属变成活的货币。对资本主义的木偶表演者来说,大自然就像一个由小麦交易控制的玩偶,它把钱变成有利息的资本。”[16]49
-
伊西斯(Isis),原是发端于古埃及的神话人物——“一位对古希腊罗马具有重大影响的埃及女神”[20]。在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记载的有关她的经典神话中,伊西斯嫁给了自己的哥哥奥西里斯。后奥西里斯被和他争夺王位的弟弟赛特杀害,装到一个大箱子中并投进了尼罗河。伊西斯顺流找到箱子,但不幸被赛特发现。赛特将奥西里斯的遗体分割成14块,抛到了埃及各地。伊西斯找到它们后,变成了一只鸢,并借助魔法成功怀下儿子荷鲁斯,荷鲁斯长大后击败了赛特并最终夺回了王位。据说尼罗河的洪水泛滥就是伊西斯为死去的丈夫悲伤哭泣而流下的泪水。作为“埃及众多神祇中最为闪耀的女神”[21],伊西斯“集忠贞、善良、勇敢、睿智、仁爱等多种美德于一身”[22],不仅被视为完美女性的典范,更影响到了埃及之外包括希腊、古罗马在内的西方世界的很多地区,在西方整个历史进程中也不断被关注和提起。
在西方文化中,伊西斯作为自然之化身,自古希腊时候起就已开始。在希腊人那里,伊西斯被塑造成了一位身披长袍头戴面纱的女性,并拒绝向凡人展露真容。“自然试图掩饰自己,并且精心守护它的秘密。”[23]37一如赫拉克利特的箴言:自然喜欢隐藏自己。而随着苏格拉底将德尔菲神庙所刻下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作为人生的座右铭,他成功地将世人的目光从自然转向了“人”自身。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类首要应关注的是如何让自己过一种道德的生活,而不是对自然进行研究。“苏格拉底第一次使哲学背离了曾被自然本身隐藏和包裹起来的、此前的哲学家所关注的东西,让它回到了人的生活层面。”[23]103柏拉图则认为,人因为没有技术手段,故而无法洞悉自然之奥秘。比如在谈到颜色时,他就声称:“但如果有人想把这些事实付诸实验检验,他将显示出对于人性与神性之区别的无知:神足够聪明和强大,能把多合为一,再把一分成多。现在不会有,以后也不会有人能够完成这些任务。”[23]36而我们知道,由于有数量众多的奴隶从事体力劳动,所以古希腊人对技术少有兴趣,他们更热衷于进行自然哲学的沉思性活动。而尽管被视为近代实验理性奠基人的阿基米德发明了很多东西,如引水用的水螺旋,能牵动大船的杠杆滑轮机械等,但他仍把这些机械视为只是满足消遣的几何学的副产品,并认为人们应当追求那些因其美妙和卓越而与生活需要脱离一切接触的东西。卢克莱修则断言,“戒备的自然将原子的奇观隐藏起来,不让我们看见”[23]37。德谟克利特认为,人类对真理一无所知,因为真理藏在深渊之中,就如同深井中的井眼或泉水的泉眼一样秘不可测。总之,在大多数希腊思想家眼中,自然不愿把自己赤裸裸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她更青睐于人们用神话叙事的方式倾听她的言说。
不过,在古希腊有一股力量也在潜滋暗长。这就是试图揭开自然的面纱,以发现她秘密的雄心。这似乎可从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火种的神话故事中窥见一二。火作为技术的象征符号,暗示着人类可以借助技术去强取自然的秘密。如我们熟知的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就宣称,必须迫使自然交出她所隐藏的东西,而当自然拒不交出其迹象也就是临床症状时,医生便可采用医术寻求制约手段,以便能够“使自然放手”。伊壁鸠鲁则因提出了原子论假说而遭到卢克莱修批评,因为后者认为他从自然那里夺走了遮盖她的面纱,并妄图用原子论打开自然紧闭的大门。
如果说古希腊对获取自然秘密的普罗米修斯式热情囿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还不足以形成气候。那么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对科学技术生发出的需求可说是为其培植了丰厚土壤,并为人类试图揭开其神秘面纱扫清了道路和障碍。培根及其追随者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引领者的作用。比如培根就采用了大胆的性意向,怂恿科学家去和自然建立起一种虐待式的婚姻关系,如用手和心解剖它,用各种巧设的实验折磨它,诱惑它,占有它,征服它,以使其离开悠闲状态,并认为唯有这样,人类才能“迅速、即刻、同时地预知和发掘这些秘密”[18]187。罗伯特则表达了对大自然未被开发状态的惋惜:“尽管在地球的内部孕育着、在她的表面滋养着自然所予的所有那些最丰富、最珍贵的产品,大地是这个世界上全部富饶和宝藏的源泉和母亲,然而在许多国家,凭日常的经验就可发见,在这些日子里真正的探索和研究被极大地忽略或遗忘了。”[18]205-206而成立于1662年的英国皇家学会,其初衷就是要实践培根的设想。当时的自然哲学家们几乎都遵从着培根的告诫,对自然采取了一种进攻的态度,以求掌控大地,谋取福利。如波义耳就认为人们在研究自然时,必须对其发号施令,并坚决拒绝将自然构想成一种人格性的东西或力量。笛卡尔也明确指出:“我所说的自然决不能理解成某位女神或任何其他类型的想象的力量……我用这个词来指物质自身。”[23]149-150格兰维尔则将化学推崇为最有用的技艺,因为化学能用人工之火的强暴迫使自然“招供”。“科学史之父”萨顿更是将其主编的科学史期刊用《伊西斯》来冠名,这可说是充满了吊诡意味。对他而言,科学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揭示“她”(自然)内心隐藏的秘密以揭示其深藏的奥秘。带着这种信念,萨顿不无自豪地感叹:“当我注视着我的同类与大自然角逐以揭示其奥秘,解码其信息时,我一次次地被深深打动。”[24]
在科学家开足马力向自然进发时,一些思想家却对此感到不安并试图进行纠偏。比如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就对知识之快速演进表达了疑虑。他虽然并不拒绝接受实验哲学所传输的理念,但也不确定科学家能从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在他看来,科学实验所能达到的也只不过是搞清楚了存在之链条上的几个支离破碎的片段,故而不可能真正洞悉自然的秘密。卢梭则明确指出,科学与艺术兴起的同时势必伴随着人类道德的堕落。而大自然“用来掩盖其一切活动的那张厚厚的面纱[即永恒的智慧]似乎足以告诫我们,她并不打算让我们从事徒劳的探索。……而她所要向你们隐藏起来的一切秘密,也正是她要保护你们不去做的那些坏事,因而你们求知时所体会到的艰难,也正是她最大的恩典。”[23]160席勒则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表达了对古代众神离去的哀叹。在他看来,古代被认为富有情感从而具有灵魂的高贵的自然,正逐渐被科学家粗暴地褪去“迷人外衣”,变成了屈从铁一般规律的机械时钟。歌德认为,大自然在人类的拷问之下依然会保持沉默,“不让人揭开她的面纱”[23]277,她不愿向人的心灵表露的东西,任凭“用杠杆用螺旋也撬不开”[23]277。而要想发现自然的秘密也即“自然之魅”,唯有借助感知和对感知的审美譬如诗歌才能加以描述。康德在将理性活动限制在经验范围内时,也吁请人们用心体察自然带给人的审美体验、情感体验和道德体验,并直言大自然在力学和数学上的崇高固然使人感到恐惧,但也会激发起人们对自然之美的热爱与敬重之情。荷尔德林也对科学处理自然的进路与方式不满,指认它会使我们身处的世界陷入黑暗。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亦不无忧虑地指出,支配现代技术来对大自然进行“解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促逼和挑衅,是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使其源源不断地提供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麦茜特则坦言,在自然为其“羞怯的长袍被撕碎而感到的悲哀中”[18]189,为了人类的善而“强奸”和剥夺自然变成了合法化的事业,由此使自然走向了“死亡”。
-
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希腊的盖亚传说,还是基督教的夏娃想象,抑或是埃及发源并在西方传统中扎根的伊西斯叙事,它们均是分属西方文化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下的产物。而作为三种对自然的不同隐喻,它们也都有着各自独特的意蕴和内涵。如果说对盖亚的想象表征了古希腊人在大自然母亲面前的一份尊崇和现代人在经历了严峻的生态困境后的一次大觉醒,那么中世纪关于夏娃的言说则突出体现了人类在人猿揖别之后看待大自然时所滋生出的自信和试图将其征服的决心,而伊西斯在古今的观念流变则揭示出人类在自然面前的矛盾心理——在“强取”和“倾听”自然秘密之间是否需要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与平衡。从对盖亚的崇拜到对夏娃的罢黜贬抑,从伊西斯的真容被刻意隐藏到堂而皇之地揭开其神秘面纱,甚至不惜撕碎代表其尊严的长袍进行窥探,其实质说到底,不过是人类在与自然相处时根据自身意愿和需求而对自然之意向所进行的“范式”更迭。随着这种更迭,人们看待自然的眼光和与之打交道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尽管面对的依然是那个熟悉的自然,但自然却变得不再亲切和需要敬畏,而是沦为了“被动的物质”“充满诱惑的处女”“可憎的妓女”“可怖的女巫”和“机械的世界图景”。这种转变不仅向我们提出了“女性和自然是如何被相互隐喻”为这样一个女性主义者和环境主义者都极为关心的问题,而且引导和指示着人类对待自然之路径的后续走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人类的历史演进尤其是近代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合中,盖亚、夏娃与伊西斯无一例外地统统成了必须向之进发征服的对象。而即使是在这当中出现了一些如卢梭那样可贵的异音,但终究还是无法阻挡人类大踏步前进的征程。在由科学技术助力从而获得强劲动力的现代化征程中,人类完成了从敬畏、尊重自然到轻视、贬低自然的格式塔转换,这种转换也把本该作为自身无机身体的自然推向了对立面,并由此遭到自然的无情报复而深陷生存困境。
其实,无论把自然想象成是充满活力和有着自主性的盖亚女神,还是比拟为堕入凡间必须为其原罪付出代价的夏娃,抑或是蒙着神秘面纱不愿示人的伊西斯,她们背后都隐含了人类对自然的好奇并希冀一探其究竟的心理。这原本无可厚非,因为作为区别于其他非人类物种之独特的一员,人类无法也不可能被动地听凭自然摆布,而必须主动地反作用于环境,必须“不听任‘世界之所是’”[25]。且唯有凭借科技之手,方能弥补先天缺憾不足,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求得生存席位。但是,随着人类活动空间的无止境扩张和人们欲望的无限度膨胀,已经导致一些非人类自然的自为性几近消失殆尽。更可怕的是,另一些非人类自然却超乎寻常地以其自主性嘲讽着人类的狂妄与自信。譬如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就正以其难以捉摸的发病规律彰显着大自然的混沌性、不可控性和高度复杂性,以至于有学者将其视为是“盖亚”派来惩戒人类的结果。其实,这毋宁说是大自然在变相警告人类:不要去触碰本该恪守的界限和底限,否则就只能是自食其果。而反观我国和欧美各国在应对此次疫情时的态度,不难看出:西方国家由于秉持个体权利自由不容侵犯剥夺的理念,故而更多地采取了放任自流和不加干预政策,甚至主张通过群体免疫来对抗病毒,但由此造成民众更多死亡的后果也将其置于恶性循环的可怖境地。而中国却凭借政府强有力的引导和干预,成功将病毒传播的链条阻断,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群众的健康与安全。中西方在新型冠状病毒上大相径庭的治理路径背后,实则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观念。具言之,中国在面对大自然的“报复”时,保有了一份恰当的敬畏之心——不和自然强行对抗,而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认知的有限性,并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事实上,也正是通过对病毒运行特征和规律的了解掌握,并选择将感染病毒者进行强制隔离和使人们的社交距离保持在合理的界限与范围之内,才有效地防范了病毒传播。而西方极为消极的“人毒共存”,人与病毒协同进化的疫情治理路径,尤其是为数甚多的民众拒绝在公众场合佩戴口罩和保持必要社交距离等任性举动,恰恰折射出其对自然还缺乏足够的敬畏。在其眼中,自然只是等待其征服的被动客体,新型冠状病毒亦不过是影响其自由而必须被踢开的绊脚石。“不要欺负我”“让我自由,或者让我死”等革命年代口号的提出,即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但事实证明,不尊重自然(病毒)的规律并选择强行与之对抗的思维路向根本行不通。这也正是欧美各国,尤其是当下的美国为何会遭遇民众大规模死亡困境的根本所在。而拒绝从大自然的报复中深刻反思并认真吸取教训,只能是将自己置于更加被动和尴尬之境地。这对全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也无疑是一种变相的伤害。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重构对自然的想象,重建对自然的观念,重塑对自然的理解。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要恢复古希腊的盖亚女神崇拜,抑或重构中世纪的夏娃形象,或是为伊西斯重新披上面纱,而是要充分认识到自身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的有限性,在大自然面前保持本不该缺乏的敬畏之心。只有这样,方可能与自然为伴,协同进化,共创生态文化, 共铸生态和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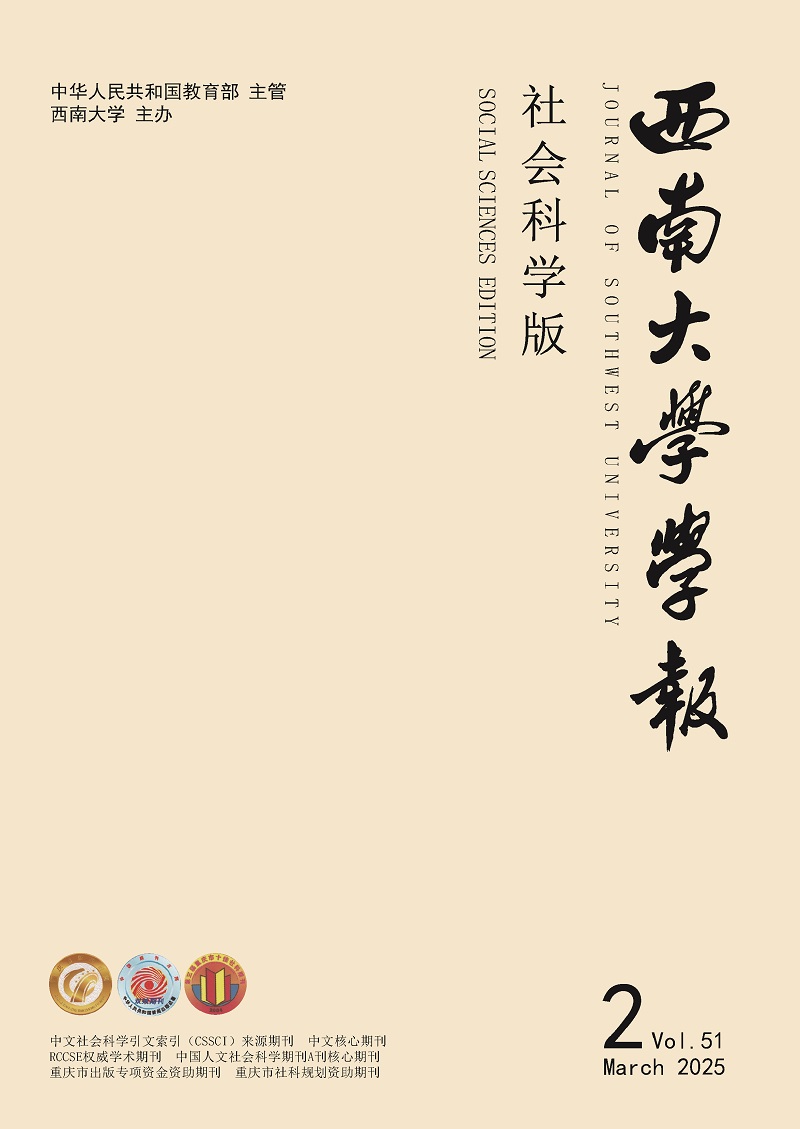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