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朱元璋的刻意塑造和崇道信佛的社会氛围烘托下,明朝初年涌现出包括张三丰、周颠、铁冠道人、冷谦、刘渊然等在内的一大批术士异人。这之中,由于朱元璋亲自为周颠撰碑而使之家喻户晓,明清文献中有关周颠的记载堪称汗牛充栋。以《古今图书集成》为例,涉及周颠的文字即达45处,然而考究文献,多是转相沿袭,少有新材料出现。因此本文以明代文献为依托,在勾勒周颠生平事迹的基础上,借助于梳理文献传承脉络,辨析明代官方文献与民间传说的互动关系①。
① 有关周颠的专论,仅有程宇昌:《文化认同与社会控制:明清鄱阳湖区周颠仙信仰》(《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及氏著:《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的部分章节。
HTML
-
周颠,江西永修人。“不知其名”[1]卷二二九,洪武二十六年七月辛未,3348,因周颠自幼患颠病,行为举止异乎常人,故时人以颠呼之。周颠一直生活于社会底层。从14岁开始,周颠离开家乡,前往南昌行乞。“年一十有四岁,因患颠疾,父母无暇常拘。于是颠入南昌,乞食于市,岁如常。”成年后,周颠为了生存开始在城市佣工自存,“有时施力于市户之家,日与侍人相亲,暮宿闾阎之下”[2]112。
周颠的命运在至正二十二年(1362)发生改变。这一年,周颠的生活轨迹与朱元璋发生了交合。至正二十一年十二月,陈友谅的江西行省官员投降朱元璋,“陈友谅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遣宣使郑仁杰诣九江纳款”[1]卷九,至正二十一年十二月己亥,123。朱元璋对胡廷瑞等人的投降极为重视,不逾月,即前往南昌视察,至正二十二年正月,“辛酉,上至龙兴(即南昌)” [1]卷十,至正二十二年正月辛酉,125。寄居于南昌的周颠开始尝试与朱元璋建立联系。朱元璋自述道:“朕抚民既定归建业,于南昌东华门道左,见男子一人拜于道旁。朕谓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颠人。’”[2]112由于周颠位卑言轻,此次二人的遥见并未引起朱元璋的重视,因此周颠离开南昌,前往南京,借助各种方式,希图引起朱元璋的注意。“朕亲出督工,逢颠者来谒,谓颠者曰:‘此来为何?’对曰:‘告太平。’如此者,朝出则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务以此言为先。”[2]113通过频繁创造见面机会,周颠最终引起了朱元璋的关注。
周颠主要凭借着三方面的特殊才能引起朱元璋的注意。第一个方面,周颠以政治隐语解读天下局势。如“颠者以手划成圈,指谓朕曰:‘你打破个桶,做个桶’”[2]114。这一浅白的政治隐语,明人陆深最早将解释行诸文字,“盖隐语代革之事。桶,统也”[3]卷十九《豫章漫抄》,108。周颠借谐音预示朱元璋的政治前途。此外,朱元璋问及周颠身上虱子有多少时,“复谓曰:‘几何?’对曰:‘二三斗。’此等异言,大概知朕之不宁”。周颠借虱子暗喻元末混乱的政治局势,将竞逐中原的群雄比喻为虱子,以“二三斗”暗喻朱元璋被强敌环绕的险峻形势。“当首见时即言婆娘歹。又乡谈中常歌云:‘世上什么动得人心,只有胭脂胚粉动得婆娘嫂。’”[2]113这里则借助谐音阐明朱元璋与陈友谅之间的关系。“婆娘歹”,吴国富将之释为“婆娘反”,认为“当是谐音‘鄱阳(湖)反’,意指陈友谅将于鄱阳湖与朱元璋决战”,“‘胭脂胚粉’应指南京,因南京有胭脂岗,洪武二十六年(1393)在这里动工开凿一条运河,即胭脂河,连接秦淮河,以打通南京与太湖的水上通道。以‘胭脂岗’或‘胭脂河’代指金陵,以‘婆娘’谐音鄱阳,又从胭脂可以打动婆娘心的‘动得’延伸出‘攻打、动摇、征服’等意义,隐喻只有占据金陵的朱元璋才能够吃掉占据鄱阳湖的陈友谅。这种隐喻手法,类似于灯谜”[4]276-277。
第二个方面,周颠凭借异术将自身形塑成异人奇士。一是不惧火烧。在《御制周颠仙人传》一文中,朱元璋不惜笔墨地描述了他三次煅烧周颠的情形。二是长期辟谷。《御制周颠仙人传》有周颠三次辟谷的详细说明,分别为辟谷“半月”“二十有三日”“半月”。尤其是第二次辟谷引发了轰动效应。不仅朱元璋亲自前往南京蒋山寺探望并赐食,而且普通军民也以之为奇人,“诸军将士闻是,争取酒肴以供之”。三是不惧水溺。鄱阳湖之战前夕,周颠预测兵不利,朱元璋大怒,“将颠者领去湖口小江边,意在溺,众去久而归,颠者同来。问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复生来?’对曰:‘难置之于死。’”[2]114-116
第三个方面,周颠擅长预言。“间为人言未然事,多验,人以为神异,称为颠仙。”[1]卷十三,至正二十三年八月壬戌,168至正二十三年,陈友谅倾巢而出,誓与朱元璋决战。《明太祖实录》极言陈友谅水军之盛,“舰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橹箱皆裹以铁。自为必胜之计,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1]卷十二,至正二十三年四月庚子,151。陈友谅的大举入侵,给予了朱元璋极大的压力。当朱元璋亲征陈友谅之前,周颠便预言朱元璋必胜,以“上面无他的”[2]115显示陈友谅并不具备正统性,坚定朱元璋的信心。行军之中,周颠的预言也是屡试屡中。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周颠的这三方面能力与我们的常识不符。合理的解释,或是周颠的障眼法,或是朱元璋的刻意营造,不过最终,周颠以迥异常人的异人奇士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然而也恰是至正二十三年,周颠离开了朱元璋,隐居庐山。
周颠的再次出现已经迟至洪武二十六年。此时朱元璋身患奇症,“朕患热症,几将去世”。赤脚僧借周颠之名前往南京献药。“药之名二,其一曰温良药,两片;其一曰温良石,一块。其用之方:金盆子盛着,背上磨着,金盏子内吃一盏便好。”[2]117朱元璋服之即愈。由于此事过于诡异,学界多加以否认。不过同时代的天师道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曾专以《钦承圣谕周神仙进药之异,于教有光,喜而赋以纪之》为题作诗一首[5]卷十一,267,诗题明确写明朱元璋在接见张宇初时曾谈及此事。此外,《永乐大典》亦保留一则材料,《茅山续志》引《神异记》云:
至是七月十七日召诣奉天门,赐观颠仙所进药,一曰温凉石,一曰辟瘟丹。其石如玉,微软,约崇四寸,广杀四之一,其面玲珑,其背质朴。其丹粉剂,色如辰砂,修如笔琯,异香仿佛菖阳。斯其应效之速,不逾宿而沉痾遂洒然之去体也。观毕,上谓:“何物乃此灵验?”臣恭谨对曰:“此必颠仙所炼而然。”上曰:“斯人草衣木食,何得此药而炼?”复谨对曰:“仙人真质已在仙洞,遗体应世而已,安知仙境无此药物?今皇天眷祐,真仙进丹,圣躬万安,实宗社之灵,苍生之福也。”语毕,叩头而退。[6]554
文中并未言及作者名字,不过文前有自我介绍,“上之洪武二十有六年春,臣恭由华阳洞灵宫知神乐观凡八载,蒙恩授今太常丞职,任黄冠如故”[6]553。可知其人在洪武二十六年时已经主持神乐观八年。张宇初《故神乐观仙官傅公墓志》:“(洪武)十八年(1385)乙丑,有旨于龙虎、三茅、閤皂三山选道行之士充神乐观提点,佥推公,应召赴京。上悦,授格神郎五音都提点、正一仙官,领神乐观事。敕礼部铸印如六品,命掌之。”[7]卷三,441据此,《神异记》的作者为龙虎山高道傅若霖(1322-1399),他曾亲眼得见赤脚僧所献丹药。二则材料证明赤脚僧献药一事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这剂药方仍是政治隐语。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太子朱标突然去世。为了扫清皇太孙朱允炆的继位压力,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悍然发动了蓝玉案。这剂药方即与蓝玉案有着密切关系,吴国富先生解释道:“朱元璋说两种药一名‘温凉药’,一名‘温凉石’,合起来就是‘温凉药石’,谐音‘温凉(代指蓝玉)要死’。又菖蒲如同剑,也称菖蒲剑,‘盏’谐音‘斩’,所谓的‘菖蒲香盏’,就是‘以剑斩之’的意思。”[4]279-280由于朱元璋病愈加之蓝玉案成功解决,朱元璋派人前往庐山寻找周颠,但周颠已经不知所终。
为了表彰周颠,朱元璋特命人前往庐山立碑刻石。洪武二十六年七月,“辛未,遣礼部员外郎潘善应、司务谭孟高往祭庐山,为周颠仙立碑”[1]卷二二九,洪武二十六年七月辛未,3348。《神异记》则言:“定选八月朔,遣使诣庐岳行谢礼,以九月朔致祭。”[6]554庐山石碑的署名亦可佐证,“洪武二十六年岁次癸酉九月日,从事郎中书舍人臣占希原奉敕书丹并篆额”[2]118。由此可以梳理出相应时间:七月,朱元璋下达立碑的命令。八月,使臣启程前往庐山。九月,石碑正式树立。石碑树立的仪式极为庄重,除官员外,佛道中人亦参与其中。“洪武十四年秋,高帝制碑于庐山,有手诏,命(呆庵普)庄主其事。”[8]卷十三,237尽管时间有误,但呆庵普庄禅师(1347-1403)确曾参与其中。“是年秋,函命至庐山祭祀立碑。感格圣灵,腾光现瑞,神灯映射,祥霭氤氲,碑坛下上,荡眩万目。陪祀官僚,僧道士庶,稽颡归依,同声赞叹。礼成复命,喜动尧眉,赐衣一袭,褒锡甚隆。”[9]卷八,1017这段文字描述了庐山立碑的盛况,“陪祀官僚,僧道士庶”更是指出参与人员之众多,来源之广泛。查慎行曾言:“丰碑一道,勒明太祖御制周颠仙诗文,附载官员、寺僧名凡六十三人。”[10]279这里所说的63人,应即直接参与立碑仪式的主要人员的数量。
-
以上有关周颠的生平事迹,主要本于朱元璋所撰的《御制周颠仙人传》。然而此文并未收录于《高皇帝御制文集》,缺乏权威性来源,明代文献在征引时只能依据不同的来源。这导致相关记载在内容、文辞、侧重等方面都有些许差异,从而产生出不同的文献传承系统。
第一个文献传承系统来源于朱元璋遣人所立的庐山石碑。此碑保存至今,碑高4米,宽1.27米,厚0.23米,汉白玉材质。碑阳刻《御制周颠仙人传》全文。第二个文献传承系统则是《明太祖实录》,卷十三记述了鄱阳湖之战前后周颠的预言,卷二二九则是《御制周颠仙人传》的缩编版。尽管《明太祖实录》的内容源于《御制周颠仙人传》,但由于篇幅所限,《明太祖实录》在文字上进行了精简,在某些细节上增添了部分内容。比较两个文献传承系统,大致可以胪列5处不同:(1)《明太祖实录》解释了周颠并非其本名。(2)《明太祖实录》描述了周颠的外貌特征,“身长,壮貌奇崛,举止不类常人”。(3)在解释朱元璋为何煅烧周颠时,《明太祖实录》解释为出自周颠自身的夸耀,“又自言入火不热”[1]卷二二九,洪武二十六年七月辛未,3348。(4)洪武十六年赤脚僧前往南京觐见朱元璋,未遂其愿。《明太祖实录》仅用一句话带过。(5)赤脚僧献药,《明太祖实录》极为简略。正是这5处明显的不同,使得我们完全可以追索明代文献的源流。
第一个文献传承系统本于《御制周颠仙人传》。除了单行本《御制周颠仙人传》一卷外,其他明代文献也是多有引用。然而《御制周颠仙人传》的文字繁多,明代文献在处理时也有两种不同方式。一是全文誊录。据笔者所见,最早见于文献者在嘉靖朝。嘉靖四十年(1561)刻桑乔(?-1564)《庐山纪事》,题名为《御制周颠仙人传》[11]卷二,401-404。嘉靖《九江府志》题为《御制碑文》[12]卷十四《外志》。他如万历刻本的《纪录汇编》[13]卷六《御制周颠仙人传》,45-48、焦竑(1540-1620)《熙朝名臣实录》[14]卷二,22-24及《国朝献征录》[15]卷一一八《道》,670-672、江盈科(1553-1605)《皇明十六种小传》[16]卷三《怪类》,985-987、天启刻本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17]卷六一《江西建昌府》,539-547、顺治三年刻本《说郛续》[18]卷四三《周颠仙人传》,263-265、傅维鳞《明书》[19]卷一六十《异教传》,363,皆全文引录。李贽《续藏书》所收《建昌周颠仙先生》一传,开篇即写明其文献来源是,“太祖高皇帝御制文”[20]卷二,40-42。虽然査继佐《罪惟录》中的《周颠传》已非完本,但就保存内容来看,也应抄录全文[21]卷列传二六《方外列传》,2512-2513。二是摘引文字。如正德《江宁县志》主记鄱阳湖之战前的周颠事迹,在文后写明“详《御制周颠仙碑》”[22]卷十《仙释》,804。相较于正德《江宁县志》,嘉靖《南畿志》的节录更为精炼,亦写明“详见《御制碑文》”[23]卷七《郡县志四·方外》,128。万历《上元县志》[24]卷十一《人物志》、万历《应天府志》[25]卷三二《杂传》,700皆抄录自嘉靖《南畿志》。嘉靖《九江府志》在叙述天池寺时,还有一段有关周颠的记载,“周颠,建昌人。元至正间居庐山竹林寺,与天眼尊者同修长生之术。太祖龙兴,颠入辇下,首以告太平为词而大著神异。详见《天池寺御制碑文》”[12]卷十四《外志》。《秘阁元龟政要》则只记赤脚僧献药一事[26]卷十五,810-811。
第二个文献传承系统源于《明太祖实录》,因《明一统志》而广为流传。永乐年间的《天潢玉牒》亦如《明太祖实录》,分两处记述周颠事迹[27]741-742,745。《明一统志》在“南昌府”“南康府”的条目下皆有周颠的记载,内容以《明太祖实录》为蓝本,只记鄱阳湖之战前的周颠事迹[28]卷四九,33;卷五二,79。此外“南康府”条目下,又多出赤脚僧献药一事。“住得,湖口县人,号赤脚僧。常居庐山。本朝洪武间,诣阙求见,不得。已而上不豫,复赍药自进,谓天眼尊者及周颠仙人所上奉。因服之,即愈。御制诗赐之。”[28]卷五二,90相对《明太祖实录》《天潢玉牒》而言,《明一统志》在明代的传播更为广泛,因此明代文献多以之为依据。正德《南康府志》[29]卷六《人物》抄录了《明一统志·南康府》的有关内容。万历《新修南昌府志》[30]卷二三《列仙传》,460、万历朝刊刻的《万姓统谱》[31]卷六一,925、张岱《夜航船》的“入火不热”条[32]卷十四《九流部》,534、陆应阳(1542-1624)《广舆记》[33]卷十二,291等明代文献则抄自《明一统志·南昌府》的相关内容。
第三个文献传承系统,则是综合《御制周颠仙人传》《明太祖实录》的相关内容,改写文字而成。如祝允明(1460-1526)《野记》(《九朝野记》)中所收《周颠传》,将《御制周颠仙人传》《明太祖实录》融为一文。如将周颠的外貌特征改写为“比长,举措谲诡,人莫能识”,强调朱元璋煅烧周颠是出于他自己的请求等[34]3-8。李默(1497-1558)《孤树裒谈》照录其文[35]卷一,185-186。陈建(1497-1567)所撰《皇明历朝资治通纪》(《皇明通纪》)亦参考了祝允明的文字,却将之列分为两处加以记载:一则系于至正二十三年条目下,主要记载鄱阳湖之战以前的周颠事迹;一则系于洪武二十五年,记赤脚僧献药之事[36]卷二,72-73;卷八,284。文字基本上与《野记》一致,只是在个别字句上不尽相同。由于《皇明历朝资治通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明代通史著作”[37]111,影响颇大,其后著述皆以之为本。如《皇明从信录》[38]卷二,154、《皇明通纪法传全录》[39]卷三,52;卷十,168-169等全文抄录。释大闻《释鉴稽古略续集》则删减了文字[40]卷一,14;卷二,29。此外,崇祯九年刻本的《昭代芳摹》[41]卷二,31、张岱《夜航船》的“周颠仙”条[32]卷十四《九流部》,537、张岱《石匮书》的《周颠传》[42]卷二百六《方术列传》,184-185则缩编了至正二十三年的文字。《明朝小史》“温凉药石”条,则抄录了洪武二十五年的文字[43]卷一《洪武纪》,462。
除祝允明外,其他人也进行改写,如郑晓(1499-1566)《今言》中所收《周颠传》[44]卷六,201-202,《国朝典汇》[45]卷一三六《礼部》,157-158、嘉靖年间的《高坡异纂》[46]卷上,4皆以之为本。屠隆(1543-1605)《列仙传补》[47]卷三一,877-878、何乔远《名山藏》[48]5902-5907、《明史》[49]卷二九九《方伎》,7639同样进行了内容和文字上的改编。
以上罗列明代文献40余种,文献的时间跨度从永乐年间直至清初。文献类型也是包罗万象,从官方文献至稗官野史。如此多的记载,充分表明周颠在明代是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尽管根据内容、文字等,可以粗略地将这些文献划分为三个文献传承系统;但是从内容上看,周颠事迹大致不出《御制周颠仙人传》所记的范围,这又体现出有关周颠资料的贫乏。
-
通过《御制周颠仙人传》和明代其他文献的传播,周颠成为明代异人奇士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在明代崇尚道教的氛围下,民间口头传说进一步神化周颠,随着这些民间口头传说进入到文字系统,明代文献衍生出一系列荒诞不经的故事。
第一则民间传说以鄱阳湖之战为背景。鄱阳湖之战前,《御制周颠仙人传》记载了一则周颠的预言。“当江中江豚戏水,颠者曰:‘水怪见前,损人多。’……至湖口,失记人数约有十七八人。将颠者领去湖口小江边,意在溺,众去久而归,颠者同来。问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复生来?’对曰:‘难置之于死。’”[2]115周颠预测到鄱阳湖之战并不顺利,朱元璋以其动乱军心,意将溺死周颠。然而这则材料进入到民间传说之中,周颠的神异能力被无限地夸大。都穆(1459-1525)《都公谈纂》:“(朱元璋)曰:‘我伐陈友谅何如?’曰:‘中涂覆舟。’上怒,令推堕水中。不溺,行水上,如履平地。遂与同载。至中途,舟果覆,上惊,得免。”[50]156《七修类稿》:“上问伐友谅何如?对曰:前途覆舟。……上怒,令推水中。见其不溺而行于水面,复召之同舟。无何,舟果覆。众皆惊骇。得周而免。”[51]卷九《国事类》,137在《都公谈纂》《七修类稿》中,周颠预言对象从明军变为朱元璋,正是依凭着周颠的预言,朱元璋才逃过一劫。这无疑夸大了周颠的预言能力,刻意彰显周颠之于朱元璋的重要性。而后半部分讲述周颠不惧水溺时,更是夸张为可以水上行走。这则民间传说后被误植于刘伯温,《宾退录》还曾进行过考辨。“太祖征陈友谅,大战于彭蠡湖。伯温时同在一舟。忽大呼曰:‘难星过,速更舟。’如其言而更之。未半刻,前舟已为炮所击矣。或曰:此周颠仙事,传者误伪为伯温耳。”[52]卷一,1
第二则民间传说则将赤脚僧献药的部分情节进行了修改。《都公谈纂》:“既而颠仙求归庐山,许之。临行,上问:‘世间何事最乐?’曰:‘吃饭去便最乐。’颠仙归,上一日忽大便不通,百方不效。颠仙已预知,密令庐山赤脚僧献药阙下,并侑一诗。适是日至,上见药,乃一小石。问其僧,曰:‘清凉石。’心颇疑之。见诗,乃颠仙手迹,用水磨之,异香袭人,久之不散。服已,大便随通。”[50]156《御制周颠仙人传》明言朱元璋所患为“热病”,这里却写为“大便不通”,文字粗俗,应该是都穆采自于民间传说。
第三则民间传说更为神奇。祝允明《野记》在赤脚僧献药之事后又增添了一段内容,《孤树裒谈》全文誊录[35]卷一,186:
上遣行人走江州,令三司索之。三司与行人偕入匡庐。至庐山观且漠然无为计。前道士忽至,语行人,周在竹林寺与天眼尊者校棋。就导之去,果见颠在门与一道流奕(弈)。行人致朝命,颠殊不顾。良久,行人屡诣之,颠令入寺姑游观。行人入,见殿堂庭庑甚弘丽,漫循廊行且观,廊左右对列室中,各有主者,或冠袍,或野服,侍从甚都,旌幢供设、珍具充牣。主者或踞座启门治事,通二十八室。独其一扃,中无人焉。一巨虺据席地,微有流血,出而问颠,颠曰:“若既见之矣。二十八室者,经天之宿也。递为人世主。汝主方御宇,故虚室。疾,故血然而行起矣。圣寿无疆。”行人曰:“固尔,然将以何语复皇命。苟无验,吾罪且死。”颠乃赋诗一章,升(畀)之曰:“上览此当信也。”又邀天眼同赋。行人持去,回顾,寺亡有也。[34]7-8
这段文字添加了三部分内容。一是明朝官员在竹林寺门前见到周颠和天眼尊者。二是经过周颠允许,明朝官员得以参观竹林寺。三是神化朱元璋,将朱元璋与二十八星宿扭结在一起。前两个部分内容皆与竹林寺有关。虽然竹林寺亦见于《御制周颠仙人传》,但实际上竹林寺并不存在,桑乔早已指出:“竹林者,废寺也,相传有影无形,僧隐焉。”[11]卷二,396一座并不存在的寺庙让周颠之事更显神奇。屠隆《列仙传补》亦抄录了这两部分的内容[47]卷三一,877-878。而第三部分将朱元璋比附为二十八星宿,则被屠隆摒弃,只有《龙兴慈记》记录其事:“一云:上有疾,差使访周颠仙于匡庐天池山颠。令遍阅二十八宿躔舍,皆有人,惟一舍空然无人,一蛟龙垂首流血。颠云:‘此世主也。’又角亢宿矣。”[13]卷十三《龙兴慈记》,129
此外,明人还将周颠与建文帝的下落联系在一起。卓发之(1587-1638)《红箧秘史序》:“因思红箧所藏,当是周颠、冷谦或刘青田所为。”[53]卷十《序》,443所谓“红箧”,即建文帝传说中朱元璋藏有度牒的箱子①。卓发之不假思索地认为其出于周颠之手,反映出明人对周颠事迹的确信。
① 有关红箧的具体考证,请参见吴德义:《政局变迁与历史叙事:明代建文史编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的相关内容。
考索明代文献,由于周颠的高知名度,民间口头传说进一步神化周颠,一方面创造了一些新神话,另一方面又将周颠与明初历史进行比附。随着此类事迹的繁多,有关周颠事迹的记载已非《御制周颠仙人传》《明太祖实录》等明代官方文献所能囊括。
-
尽管明代文献多有言及周颠之处,但其中所揭示的周颠事迹却是寥寥无几。大致可知:周颠生活于元明鼎革之际,是一位连名字都无从而知的下层民众。真正能确认的周颠事迹,只在1363年鄱阳湖之战以前。1393年赤脚僧献药之事,根本没有出现周颠,完全是依凭着赤脚僧的说辞而与周颠建立联系。
然而这些因素并未阻止周颠事迹在明代的传播,由于朱元璋的亲笔立传,加之明朝官方文献——《明太祖实录》《明一统志》等的宣扬,周颠事迹广为人知,明人坚信周颠的各种神异表现是真实的。在这一点上,南炳文所下结论无疑是妥当的:“除了利用谈话、发布文告直接宣称其君权乃得自上天授与之外,朱元璋还与和尚道士等以神仙迷信为职业的人串通一气,假造神迹,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如他曾撰写《周颠仙人传》,就是其中明显的一例。”[54]65朱元璋及官方的介入,使得周颠成为明代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也恰是因为朱元璋及明朝官方的介入,明代士大夫多抱持着与官方一致的态度,导致他们笔下的明代文献因循承袭,所记内容大致不脱于《御制周颠仙人传》的窠臼。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士大夫的有关记载也可被包容到明代官方文献系统之中。
在官方的刻意渲染下,民间也涌现出以周颠为创作对象的民间传说,经过文人的拣择和改造,被纳入文字系统。与明代文人主笔的文献有所区别,民间传说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所记内容偏离官方文献的内容,而是依凭道听途说进行再创作,内容多是荒诞不经;二是文字粗俗,尽管经过文人的润饰,但仍显浅白。17世纪法国的情况可为旁证。佩罗在改编民间童话时,达恩顿评价道:“他没有偏离原来的故事线索,也没有因美化细节而损毁口述版本的粗俗与纯朴。”[55]64依据这两点,大致可以甄别出三则民间传说,皆是从《御制周颠仙人传》的故事主干扩而论及周颠的神异。因为这些民间传说是明代官方说法的补充,才得以进入到明代士大夫的视野之中。因此,我们拥有了讨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互动的空间。明代士大夫并不排斥民间传说,反而出于个人喜好、价值判断等考量,积极地改造民间传说,将之纳入精英文化。而采择以上三则民间传说的文献共计7种,最早为成书于弘治、正德年间的《都公谈纂》和《野记》,此后,《龙兴慈记》《孤树裒谈》《七修类稿》成书于嘉靖年间,《宾退录》《列仙传补》成书于万历年间。从民间传说进入文献系统的时间看,要远远晚于《御制周颠仙人传》《明太祖实录》《明一统志》等官方文献书写的时间。这充分说明:从弘治年间开始,明代文化发生了重大转折。日益繁荣的大众文化已经开始影响到精英文化,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也采取开放性的态度,积极主动地将大众文化纳入精英文化之中。
在区分了明代官方文献和进入文字系统的明代民间传说之后,我们才可以解读为何周颠无法如张三丰等异人奇士那样在民间广为流传。因为明代官方文献已经明晰地呈现了周颠的事迹,这使得民间创作缺乏自由的空间,导致周颠无法被进一步神化。更因为明代官方文献的论述重点集中于周颠与朱元璋的关系上,使得周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皇权的附属品,是朱元璋确立政权正统性的注脚,这也导致民间缺乏持续神化周颠的动力。由于周颠与明朝政权的紧密联系,随着明朝的灭亡,周颠不再成为民众的关注焦点,民间传说也不见有关周颠的新故事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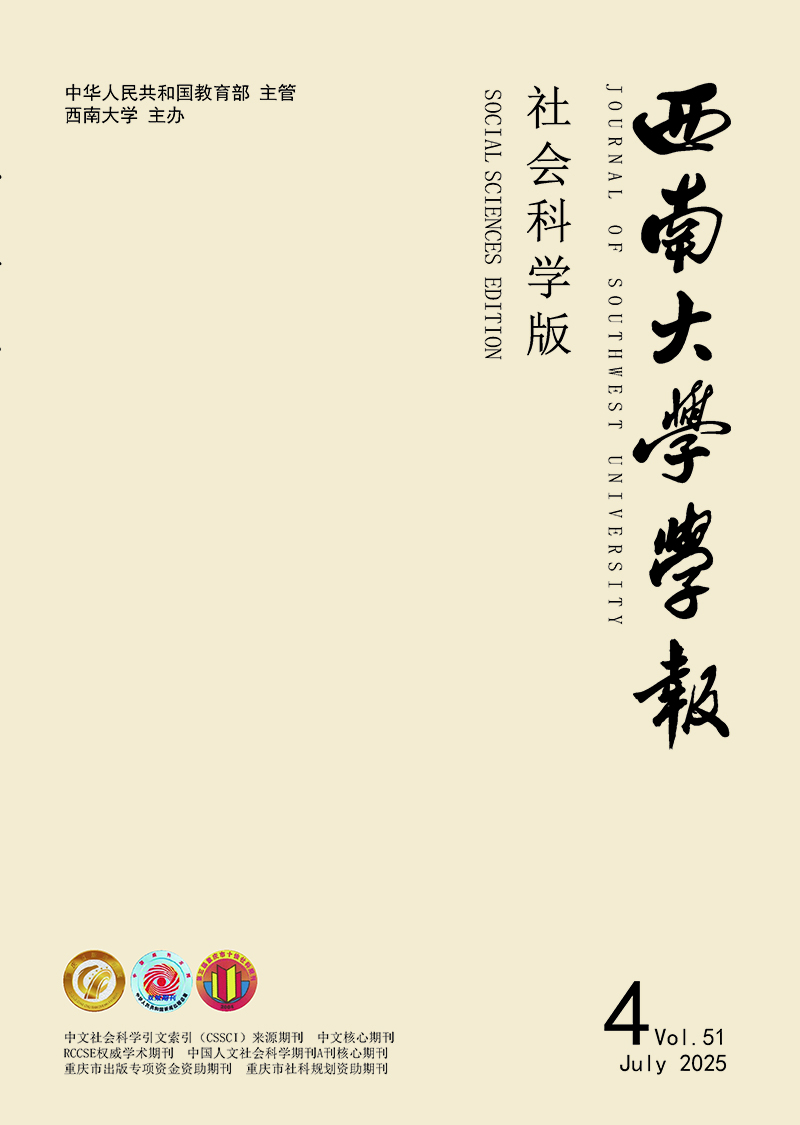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