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ML
-
早在20世纪,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便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指出家校合作的教育价值。他强调:“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影响的一致性。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性,那么学校的教学和教育过程就会像纸做的房子一样倒塌下来。”[1]数十年后,这一观点非但没有“褪色”,反而成为一股甚为壮观的教育潮流。近年来,“家长参与”和“家校合作”成为教育研究与改革的“关键词”。在教育研究领域,研究者们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聚焦家校合作的重要性和历史分析、家长参与的影响因素和阶层差异、家长参与的路径研究以及家校合作的目标定位等问题,使家校协同育人研究初具体系化雏形。与此同时,“家长参与”“家校协同育人”频频出现在党和国家颁布的教育政策文件之中,成为当下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议题。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家长学校”逐步推广,针对家长教育能力提升的讲座和培训活动被纳入学校教育工作。“家长参与从理念到实践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成为当下中国教育剧烈变迁的重要表征”[2],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推入“家长主义”的新情势之中。
当家长参与成为国家教育改革的实践议题,家庭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从“后台”走向“前台”,决定学生学业成就“看得见”的要素就不再仅仅是学生的能力和努力以及学校的教育质量。这样“优绩主义”教育信念将会受到挑战,教育公平也面临新的思考。基于教育公平关怀的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就不再只是“学校的事情”,而成为学校和家庭“共同的事情”。建立畅通的家校沟通渠道以促成高效的家校合作是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然而,农村家校沟通并未取得应有的效果,农村家长的教育主体意识未能激活,教育参与意愿低迷,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未能真正成为农村学校和家庭共同的事业。
针对农村家长教育参与低迷,已有研究从农村家长各类资本缺失导致的教育能力不足、农村学校相关支持缺失以及农村学校和教师的观念性排斥等维度进行了分析,形成了许多颇具说服力的洞见。然而,在中国文化情境中,将农村家长对教育的理解视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则更容易洞察农村教师向家长传递现代教育观念时所需跨越的文化鸿沟,揭示农村家校沟通困境的深层图景。本研究以对苏北M村的长期民族志调查为基础①,从家校文化“区隔”的角度对研究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揭示农村家长教育参与低迷的文化机制。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从“局内人”立场理解农村家长的教育意义体系,展现其作为“地方性知识”所内含的独特逻辑,并选择“文化转译”作为理论工具,尝试探索农村家校沟通的实践机制,以激发农村家长的教育主体性,使农村教育成为教师与家长对话和合作的公共领域。
① 在这项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深入至农村家庭的日常教育生活之中进行参与式观察,先后对30余名家长从教育期待、教育认知、教育情绪和教育价值观等维度进行深度访谈,以理解其日常教育生活中的“实践逻辑”。本研究的资料都来源于这项民族志调查,并在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基础上从家校文化“区隔”的角度对农村家长教育参与低迷的问题进行了解释。
-
自现代学校进入农村,学校教师便自然承担着现代教育观念在农村社会的“嵌入”与“再生产”。通过与家长沟通,实现对农村家长传统教育观念的现代化“改造”,促使其“分离于传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之外,与现代社会的‘抽象体系’实行整体结合”[3]成为农村教师的重要文化使命,也是农村学校隐性的文化功能。如今,在“家长主义”潮流的推动下,农村学校的这一文化功能由隐性转为显性。向家长传递现代教育观念、提升家长教育参与能力,成为农村学校家校沟通工作中有组织有规划的重要内容。但是,贯穿此历史进程的是一种以教师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传递,是现代教育观念在农村的“霸权式”再生产。这一忽视“地方性”的改造模式在现代教育观念进入农民日常教育生活的道路上竖起了一道“藩篱”,阻隔了农村家校之间的“融通”,造成了两者间的文化“区隔”。农村家长和学校间难以形成基于平等主体的交流与合作,农村教育成为教师的主控领域,无法彰显公共性。
-
在农村,家庭和学校间文化“区隔”的首要表征便是现代教育观念的融入困境。现代教育观念借助教育活动进入农村学校相对容易,但要进入以家庭为依托的日常教育生活,成为家长日常教育实践的指导观念,则要困难很多,甚至可以说是不太成功。当下,现代教育的语词虽已进入农村家长的话语体系中,但也只是停留于口头而无法成为指导其教育行动的实践逻辑。就观念层面而言,农村学校依然是悬浮于农村社会的一块“文化飞地”,无法实现与家长观念的“融通”,其教育观念改造与转化的文化功能受到限制。访谈中,当被问及家长是否应该参与子女教育时,他们都会借用政策话语,如“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来表达对家长参与的认同。农村家长似乎接受了来自于学校教师的教育观念。然而,这仅是一种“口号式”认同。在此表象下,农村家长与学校教师的教育参与概念是错位的。农村家长虽然在话语层面认同家长参与教育的重要性,但同时也从不同维度表达了对学校教师所要求的家长参与的“不认同”。这首先表现为一些家长对深度参与子女学习的反对。他们不认为家长应积极而深度地参与子女学习,而是将其视为教师职责。一名农村家长讲述了他的“理由”:“我就是没这个能力,我要能自己在家教孩子,我还需要把孩子送到学校吗?我自己在家里教就好了。如果每一个家长都能教好自己的孩子,那还用学校做什么?老师还有饭吃吗?” (XHY-JZZY-7·13)据此逻辑,农村家长便无法认同学校教师从家长参与维度去寻求学生学业困难或失败的原因。
对于学校教师所指出的“家长教育不到位”问题,一名农村家长用举例的方式予以反驳:“老师会教育孩子吧?老师家的孩子也不是都考上了大学吧?” (TYH-JZZY-5·5)在农村家长的思维中,教师子女并非都能获得高学业成就这一事实极具说服力地向他们证明家长作用是有限的,常常被他们用来反对学校教师对家长参与的强调。
除深度参与子女学习外,农村家长还表达了对“关心”和“陪伴”要求的“不认同”。面对教师的指责,他们抱怨道:“老师嫌家长关心孩子太少,我们也知道要关心孩子、多陪孩子,但你就天天陪孩子啊,不吃饭了啊?老师不了解我们家长的难。” (XMF-JZZY-6·12)
一句“老师不了解家长的难”道出了农村家长实践亲子陪伴的条件限制。在他们看来,这只是教师讲的“大道理”,不符合农村人的生活现实,它仅能被理解却无法实践。与此类似,被农村家长视为“可知而不可为”的,还有被建构为主流教育技能的“沟通协商”。当下,从“命令打骂”式教育转向更为友好而民主的“沟通协商”式教育,已然成为教育专家的共识性原则。然而,在农村家长眼中,这也只是“说起来好”却“用不了”的“理想”。对于“沟通协商”式教育的普适性,他们表示出了疑虑:“怎么说呢,可能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每个孩子的性格也不同,有的时候我觉得老师讲得挺对,但是最后也不见得是按照讲座老师讲的去做。就是照着人家那样试了一下,但是不可能。有时你跟他讲不通,怎么讲都讲不通。刚开始是喊他,喊着喊着就开始打了。毕竟她是她,人家是人家。这些都是理想,都用不了。” (QMZ-JYFS-6·18)
很多农村家长都否认“沟通协商”的普适性,他们认为“沟通协商”只适用于那些“会说教”的家长和“说得听”的孩子,对那些“说不听”的孩子,还是“打骂”更有效。这种实质性“不认同”将现代教育观念阻隔于农村家长的日常教育实践之外。面对学校的家长参与要求,他们常常以“形式化”策略进行应对。例如,当学校要求家长协助孩子保质保量完成家庭作业时,他们常常以“签完字就不管”的消极态度予以应对。这一“形式化”策略提示我们,来自于学校的现代教育观念在“自上而下”的传递过程中,未能获得农村家长的实质性认同并融入其教育生活,农村学校和家庭间存在着文化上的“鸿沟”。
-
家庭、学校和社会应是教育的重要主体。家长与学校作为平等主体联合而成的“共同体”构成家校协同育人的本质。“家校合作是家庭和学校围绕学生发展而结成的人与人关系的集合,其本质是共同体形态在教育领域中的一种存在形式。”[4]激发家长的教育主体责任意识,去除家校关系中的“‘中心’与‘附属’的位序观念”,既是家校合作的前提,也是家校沟通的实践追求。与此相差甚远,农村家长大多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缺乏主体责任意识,更无法以教育主体身份与学校进行教育协作,家校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距离。这一距离的产生首先缘于家长在子女教育中的“主动让位”,他们将教育主动权转让于教师。很多农村家长虽然关心子女教育,认同家长在子女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但认为这种作用仅体现于在家“督促”或者“指导”孩子学习,家长仅是教师的“协助者”,教师才是教育的“主导者”。访谈中,一名家长这样讲述家长需要“配合”老师的原因:“我一直很配合学校老师。我相信他们可以把我的孩子教好,孩子不跟着老师学,还能跟谁学呢?我就觉得,跟着老师肯定是没错的,老师也确实是为孩子好的。既然我们都为了孩子好,我为什么不配合呢?我当然要听老师的了,老师说什么,我就让孩子做什么。” (YMP-JZZY-2·3)
农村家长大多不加思考就将自己置于“听老师”的配合地位。访谈过程中,很多家长都表达了类似的“配合”态度。这一态度也主导着他们与教师的沟通实践。在谈及与教师沟通的必要性时,不少家长都表达出“等待”的想法。如:“没必要给老师打电话,孩子要是有问题,老师会打电话给我们;老师不打电话,就说明孩子在学校挺好的,没什么问题。” (LHY-JXGT-5·26)在家校沟通中,农村家长大多等待教师主动告知子女在学校中的“问题”,并将自己定位为“信息提供者”和“协助解决者”。因此,由农村家长发起的主动积极沟通并不多见。这不同于美国教育社会学者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中所描述的中产阶层家长“协作培养模式”:他们会以主体姿态“对孩子在组织机构中的经历进行密切监视”“代表孩子对教育机构提出批评并采取干预措施”并“训练孩子也承担起批评和干预的角色”[5]37。农村家长在子女教育问题上会更多依赖学校教师,全盘接受学校作为官方教育机构的意见。
除“主动让位”外,农村家长还常常陷入“被动失位”的困局。具体而言,农村教师常基于对自身专业身份的认同,认为家长是“能力缺失者”,从而将他们置于“被动配合”的位置。在农村家长“参与低迷”现象的分析中,有学者指出了类似的发现:“接受访谈的教师倾向于认为家长在学校教育中的角色是‘边缘性’的辅助角色,家长常被看作教师的追随者,而不是平等的合作伙伴,而教师则视自己为专业的工作者,其专业判断不容质疑。”[6]农村教师的专业身份及其认同建构了其对家长参与的理解,也形塑了家校沟通实践中家校间的“不平衡”。农村家长“被动失位”,沦为教师意见的“执行者”和子女教育的“配合者”。在农村家校沟通实践中,家长的“主动让位”和教师的“专业建构”上下联动、双向强化,共同建构并维系着教师与家长间“中心-边缘”的层级结构,导致农村家长在子女教育中的主体性缺位。农村学校和家庭无法以平等主体身份形成紧密合作的教育共同体。
一. 现代教育观念的融入性缺失
二. 农村家长的教育主体性缺位
-
家庭与学校间的文化“区隔”折射出现代教育观念“自上而下”的进入并未能获得农村家长作为地方教育行动者的共鸣,农村家长并未能以责任主体的姿态行动起来,学校成为现代教育观念下移至农村社会的“末梢”。这提示我们区别于现代教育观念的“另一种支撑体系”①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无论农村学校经历着何种制度和观念的转变,农村家长都拥有由乡土文化传统、现实社会情境以及日常生活逻辑共同构建的教育意义体系。这是一种不同于现代教育观念的“地方性知识”,也可称之为“民间教育文化”。因此,我们需转变现代话语主导下的线性历史观及宏大叙事模式,将焦点调至“地方”和“民间”,窥探其内在的复杂脉络与细节,这样才能获知现代教育观念被地方社会拒之于门外的症结,最终寻得两者间的通道和有效衔接方式。
① 在《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一文中,杨善华提出“另一种支撑体系”,指存在于乡村基层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区别于国家力量所支撑的现代话语的意义体系。他指出:“无论当年的社会背景及生活形势如何,在村落意义层面,还有另一种支撑体系。”在对农民教育心态的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杨善华所提出的“另一种支撑体系”也存在于农村家长的日常教育实践之中。
-
在《乡土中国》开篇,费孝通即论断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7]在乡土社会中,“直接向土里讨生活”是中国农民普遍的谋生方式。它不仅决定了乡村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特质,更形塑着农民的思维模式,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教育文化传统。在农村教育百余年的变革历程中,传统思维模式及教育文化不断调适、存继至今,构成农村社会的“地方性”教育知识。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是此知识体系的文化内核,其要义在于对“天命”的“无违”。钱穆曾分析道:“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8]“‘天命’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支点”[9],是对“人力所不能及”的自然与人事中的“不可知力量”的“敬畏”与“顺应”。基于“天命”观念而形成的教育认知体现为农村家长对“天分”的信仰。所谓“天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读书的料”。这既包括“天性”,即农村家长在访谈中所说的“老鼠养不到牛大”“大麦怎么种也变不成小麦”②,是“脑子”和“智商”问题,也包括“后天努力”,即很多家长所强调的“靠自己”。如:“家长的教育也离不开学生自己的内心,有奋发向上的精神,像这种人就可教。还有另外一种人,说多了就发火,出了校门他想做什么还做什么,那种人教育也没有用。……学习要自身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产生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要自己领悟。” (TYH-KZJ-5·25)
② 访谈中一名农民的比喻,以论证农村家长在子女教育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子女学习好不好取决于其天性。
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对农村家长而言,都是“力所不能及的”,是“命定”的,只能“听天由命”。“读书的料”反映的是“看老天爷吃饭”,是对“天命”的遵从。他们不企图介入和改造孩子的“内心”,更倾向于“顺其自然”。访谈中,很多家长都表达出这一态度,如:“我就是顺其自然。孩子他脑子好使,他愿意学,愿意接触这东西,那咱们就好好支持,他不愿意咱也不强求这些事。谁都是望子成龙,但是你也不能过度给他太大压力。” (LZM-KZJ-6·16)
“顺其自然”的心态体现了农村家长对孩子是不是“读书的料”由“天定”的认同,以及对“天命”的“顺应”与“接纳”。然而,“听天命”并不意味着个体完全的“无为”。与“听天命”辩证存在的是“尽人事”,两者微妙地平衡于中国农民的思维之中,是“天人合一”观的农民解读。“天命靡常”,农民用“尽人事”,即做好一切“可为”之事,应对“天命”无常。“成败利钝为天所决定,人能够做的就是专注于人事的努力,……‘尽人事’成为了一个儒家普遍性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准则”[10],并下移至广大农民的观念之中,成为中国社会的集体心理。
中国农民在“敬天”之下的“主体自觉”的典型表现之一是“忧患意识”。它“要求以自身的力量,掌握自己的命运。忧患的本身,即是‘人的自觉’的最初表现”[11],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动力。“忧患”思维也主导着农民对教育的价值考量。当被问及如果考不上大学,教育是否有用时,几乎所有人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一名家长更是用“学而不用不浪费,用而要学不可能”这一极富生存智慧的实践总结给予了回应。他还进一步分析道:“我觉得学习就像钱存在银行里一样,会贬值,也有一天又会升值的。如果你的钱存在银行,有一天升值了,你就运气好。学习也是一样,我当时学习了,现在找到好工作,有用了。这就是机遇问题。” (TYH-JYZY-4·25)在“忧患”思维中,农村家长被“未来导向”的理性逻辑所主导,将教育和知识物质化为一种需要储备的“财富”,用以应对命运的无常。基于“忧患”意识的储备观念一直贯通于中国传统社会,上至国家治理,下至民众日常生活,如今,它依然主导着农村家长对教育作用的考量,使其坚信“教育有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敬天”之下的“主体自觉”另一典型表现是“修德”,追求“配德于天”。“天与人之间可以相互呼应,相互沟通,‘德’是沟通天命与人事的纽结。”[12]在中国农民的观念中,“失德”是“天理难容”的,无法得到“天命”的眷顾与庇护。因此,“做人”是首要的,是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伦理关系及其维系作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基准和一切价值的根据”[13]。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指出,中国社会并非“家族本位”,而是“伦理本位”。晚年的费孝通也将“从‘心’出发的……符合‘天人合一’、‘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人际关系的基本伦理关系”[14]作为中国社会结构背后的“文化精神”。这样,道德教育便成为家庭教育的核心内容,被视为父母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访谈中,谈及家长的教育责任时,很多人的回答都是“学做人”,如:“咱们家庭教怎么做人,怎么成人,处世。比如说来人了,你得让人进屋吧,坐吧,沏茶吧。走的时候你得送出去吧,就是出于礼貌。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必须得结合在一起,她才能健康成长。” (YCY-JZZY-6·17)
在农村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中,知识成为一种强势力量侵入学校,道德教育的空间被不断挤压。但在此情势下,以“学做人”为中心的道德教育依然存在于农村家庭之中,为农村家长所坚守。
-
中国社会改革与发展内含“城乡二元”的逻辑,造成了城乡间的鸿沟与区隔,城乡二元对立依然是我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在此社会结构中,农民生活于边缘、弱势并相对封闭的社会情境中,建立了独特的生活机制,形成了特殊的“实践逻辑”。在布迪厄看来,这种“实践逻辑”便是社会场域中特定“位置”所形塑的“习性”,是“条件制约与特定的一类生存条件相结合”而成的“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15]80。它表现为“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16],影响着农民对教育的意义建构和行为倾向,构成了农民特有的教育“习性”。
在农村,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模式形塑了农民“想要富就要做”的生存哲学。艰苦的自然环境和土地劳作使他们处于生存边缘,生计和生存是其生活的中心。在此生活情境中,中国农民形成了“实用”的思维逻辑,他们不追求玄想空幻、抽象思辨的精神世界,而是以“务实”为标准衡量事物价值。农民如何判断某事物是否“实用”呢?其间蕴藏着更为独特的逻辑:“求验”。他们会以身边的人经历之后是否取得想要的效果来判断此事物的“实用性”。看得见的“现实经验”是他们确定“务实性”的方式,也是他们确定教育“有用”的逻辑。访谈中,被问及为什么不想让孩子上大学时,一些老年人会将其归因于“村里没有大学生”,如:“那个时候哪知道啊,也没有人想啊,没有,家家如此,根本就没有大学生,上了初中就足了啊。” (TYZ-JYQD-5·17)当周围有了大学生,看到他们“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了,农村家长才会意识到教育“有用”,读大学便成为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待。一名农村家长描述了“教育有用”信念的传递过程:“十个人中只要有一两个人上学有了用,那他的邻居、亲戚、朋友就会问,你家孩子怎么样,他们就会说我家的孩子我准着他上的啊,现在有用了。这一个有用,个个就跟。邻居访,亲戚听,就形成了这个团。这就像病菌传染一样,没钱的人家哪怕借也要给小孩上。” (YMZ-JYQD-4·25)
“病菌传染”极为形象地描绘了教育观念在农村社会的传播方式,也展现了农村家长教育价值认知中的“务实求验”思维。对此,程歗描述道:“小农平日不做玄想,轻视冒险。无应验的话不信,无先例的事不做。一步一个脚印,‘不见兔子不撒鹰’。”[17]这使农村家长对教育的价值认知表现出情境性和后生性。
农村生活的艰难深深烙印于中国农民的记忆之中,并成为他们的一种“集体记忆”。“苦难”成为农民讲述过去的基本框架,并建构了其“生存第一”的认知惯习。“生存第一”是农村生活烙于农民心智图式中难以抹除的印记,决定着他们对教育地位的考量。访谈中,很多农村家长会讲述生活的无奈,解释无法陪伴孩子的原因,如:“中国这种家庭不就这样嘛,肯定得有一个人出去拼命地挣钱,完了才能养活这个家嘛。陪孩子的时间就少了。” (ZXB-JZZY-6·13)
生存是农民生活的中心,“围着生活打转”“一切向钱看”是他们生活的底色,也是他们对自我的认知。对他们而言,教育虽然很重要却是次于生活的。进一步而言,教育实际是外在于农民日常生活的。现代学校作为专门教育机构,以接替家庭的教育功能为存在基础。它将教育从农民日常生活中抽离,辅之以“超地方”的现代知识体系以及掌握现代教育法的专业教师。这建构了教师的权威,使农村家长将教师视为教育的“专业人员”,自己则是“业余人员”。在子女教育中,农村家长依赖教师的领导,“找教师”是他们遇到教育问题时的首选。一名家长说:“孩子要有什么情绪啦……因为孩子有时候跟我不对付,孩子不听我的,我管不了她嘛,我就找她们老师来沟通,让老师来安慰她一下,或者是抚慰一下,然后我们俩配合一下。” (LAH-JXGT-8·21)
在《不平等的童年》中,安妮特·拉鲁发现:“与中产阶级家庭父母相比,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父母在教育孩子上则有赖专业人士的领导。”[5]14农村家长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他们眼中的“专业人士”是教师,自己只是起“辅助”作用的“业余人员”。
-
农村社会中,乡土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情境共同形塑着农村家长对教育的理解,使其在内容上表现出异于现代教育观念的独特性。然而,无论是传统抑或现实,都以日常生活为践行空间,并在其中延续。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具体与实在的领域,在人类历史上是宏观与抽象的对立面”[18],赋予农村家长的教育意义体系不同于现代教育观念的形式特征。研究者只有摒弃自身习以为常的抽象和思辨逻辑,承认并接纳农村家长教育逻辑的“日常”形式,才能更好地进入并理解其教育意义体系的完整样态。
何谓“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指的是“对社会行动者或行动者群体而言具有高度熟悉性和重复性的实践活动”[19]的时空。基于重复性实践而形成的“熟悉性”是日常生活的首要品质。不同于现代教育观念生产过程的问题化、对象化和反思化特征,农村家长的教育意义体系形成于日常生活的重复性教育实践之中,表现出日常生活的“熟悉性”特征。它可以用“‘得心应手’、‘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这三个日常的词语来加以诠释……人们不去反思自身和他人的日常行为,不去质疑人们为何如此行动,因为一切都在得心应手、司空见惯和熟视无睹中被赋予了最高的合法性,剩下的只有不成问题、习惯化和非反思”[19]。也即,农村家长的教育意义体系存在于日常教育实践的“前意识”层面,其运作无须借助“理性反思”。“生活世界是原初的自明性的领域”[20],无须通过“理论-逻辑”的对象化论证来确定如何行动。他们所依赖的是“不成问题的”、惯例的“自动化”运作。布迪厄称这种行动为“实践”,它“排除任何计算,它取决于直接铭刻于现时的可能性——要做或不要做某事、要说或不要说某事,取决于排除了慎重考虑而迫切要求变成现实的可能的将要到来”[15]81,可以说是一种即兴的行动。正是因为日常教育实践及意义体系的“自明性”和“惯性”,农村家长难以与其拉开距离并予以反思,一切都陷入“理所当然”之中。
当农村家长的教育意义体系展现出“自明性”和“惯性”特征,并以“自动化”方式运作,就意味着它是铭刻于农村家长身体之中的“默会知识”。不同于现代教育观念的论述性,作为“默会知识”的教育意义体系不是来源于对教育情境中各要素及其关系的理论辨析,而是来源于对于教育情境的整体把握。默会知识不同于“可言传的观念知识”,它不是对细节的认知,而是“对细节之间关系的整体把握”[21]。“只有我们的注意力从细节移开并且转向它们的联合目的时,我们才能恢复这些细节的动态特性,才能实现它们的联合目的。”[22]简单而言,默会知识是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知识形式。在日常教育实践中,农村家长通过对整体教育情境的综合性把握作出教育行动的选择,并依据行动效果得以在身体中固定,成为铭刻在身体里的默会知识。正因为此,农村家长在访谈中常常能够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却无法言说“为什么”。同样,他们在接受一种新观念时所依据的也是其在特定教育情境中的实践效果,而非内在的逻辑特质。
一. 乡土文化传统的教育延续
二. 社会情境的现实建构
三. 日常生活的默会形式
-
在日常教育生活中,农村家长拥有关于教育的“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构成其独特的教育意义体系。而忽视此“地方性知识”,则是农村家校文化产生“区隔”的根源。走入农村家长的教育逻辑,消解农村家校间的“文化距离”,实现两种文化间的相互吸纳与互动是农村教师作为现代教育观念“传播者”和家庭教育“支持者”的重要素养。“文化转译”,作为深度动员的发动机制,能够为探究农村教师如何完成这一任务提供理论启发。“转译”①这一概念最早由布鲁诺·拉图(Bruno Latour)提出,用以探求实验室里的科学知识有效介入大众社会的运作机制。拉图将此概念定义为“以自己的语言说出对方的兴趣”,并指出“谁能把别人的兴趣转译成自己的语言,谁就能取得胜利”[23]。不过,拉图的“转译”是单向的。他将大众群体置于弱势地位,试图借助“转译”将科学知识融入大众生活,而未能关注大众知识的价值。事实上,农民的“地方性”教育知识和现代教育知识是“平起平坐”的不同知识类型。因而,这两种知识之间的“文化转译”必须是“双向的转译”。学校教师需要“以农民的语言说出自己的教育观念”,还要反过来“以自己的语言说出农民的教育意义”,将农民于传统社会延续至今的教育智慧转化并提升为体系化的教育理论。经过这样相互的文化转译之后,双方得以成为平等的交流主体,两种知识形式能够更为深入地沟通。根据我国农村家长教育意义体系的“地方性”特征,“文化转译”可以具体化为三个相互联系的过程:识“农村理”、讲“农村理”和学“农村理”。
① 布鲁诺·拉图注意到科学社群和社会大众拥有不同的关注兴趣:“实验论述知识(以具体数据呈现的科学知识)”和“身体实作知识(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解决)”。为使科学知识进入社会民众的生活,拉图摒弃了“扩散模型(the model of diffusion)”,认为此模型的致命问题在于将“科学”和“社会”隔绝,“相信存在一个与技术科学分离的社会是扩散模型的结果”。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和大众社会是可沟通的,社会行动者可以创造出“联系点”以建构两个领域间的“联想链”,也即“文化转译”的过程。此后,这一概念出现于“跨文化传播”领域,被视为文化有效传播的必要机制。“在文化的传播中,为了达到最有效的传达和推广,需要对文化进行理解性的翻译,将异质或异构的文化符号翻译成文化主体能够接受的文化信息,也就是文化转译过程。”它同时也在语言学领域出现,用以反思和应对翻译中的文化之维。“文化转译”被理解为“跨文化阐释”的翻译,它“不只是拘泥于语言层面的忠实,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还要将其所蕴含的文化传达给另一个文化群体”。(参见:孙艳娜.论文明戏对莎士比亚的文化转译[J].国外文学,2019(1):19-25,156.)“文化转译”在这些领域虽有不同的意义侧重点,但它们都被理解为一种“单向”过程。
-
农村教师要对农民的“地方性”教育知识进行“文化转译”,就必须走入农民日常教育生活,理解农民的教育意义体系,对其文化逻辑进行标注。长期以来,大多数农村教师以“现代教育的理性逻辑”为标准,将农民视为教育的“不思者”和“无能者”,自身则成为教育的“主导者”。这种文化优越感形塑了农村教师的文化自我中心,使他们止步于家长的教育意义体系之外,无法进入并理解家长的教育逻辑。这也就意味着,农村教师走入农民日常教育生活不仅是指身体层面的,更是心理和文化层面的。他们需要放下教育“专业人士”的优越感,悬置“现代教育的理性逻辑”,以“尊重”和“开放”的心态走进农民,以多元文化包容的姿态理解农民的教育逻辑。
只有走出文化自我,将农民视为平等的教育主体,农村教师才可能进入农民的教育意义体系。当农村教师抱定“主体间对话者”身份,其首先要做的便是身体的进入,这是理解农民教育逻辑的直接路径。农村教师只有走出学校,主动接近农民,走入其日常生活,才能“触碰”到农民的教育逻辑及其生成机制。具体而言,农村教师需要“走近”农民,多与农民进行深度交谈。借助和农民“拉家常”,倾听他们讲述琐碎而繁复的“教育故事”,农村教师才能够理解农民对教育的认识及所面临的困境。然而,除了可言说的部分外,农民的教育知识还有一部分以“默会知识”形态而存在,表现为日常教育实践中的“无意识”,它们是“无法言说”的。要理解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知识,还“应该透过日常生活的实践、做事情的方法等,来揭示这些无名者的行动策略……必须进入日常生活的‘实践’”[24]。这就需要农村教师创造条件“走进”农民的日常生活,观察他们在具体生活情境中的教育行为,理解他们的教育困境及其应对策略。凭借交谈与观察的相互印证与补充,农村教师才能够更好地进入农民的日常教育生活。
与身体的进入相伴随的应是心理的进入。也即,农村教师要能够站在农民的立场对其教育意义体系进行“同情式”的理解,将其作为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另一种文化”来加以认识。农村教师不可以自己的教育理念和逻辑来标定农民的教育知识,将其硬塞进现代教育观念的解释框架和理论谱系之中,从而“制造”出农民教育知识的各种“问题”。“同情式理解”要求农村教师摒弃对农民的“先见”与“偏见”,理解他们在日常教育情境中的教育行为和教育困境中的应对策略,把握其中深藏的文化逻辑。这也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感同身受”。在此意义上,农村教师应成为业余的民族志研究者。民族志不仅是专业研究的工具,还可以是社会大众获取有关自己和他人生活世界中微妙而复杂知识体系的方式。它表征了社会大众实现多元平等理解与交流的潜力,也构成农村教师理解农民教育意义体系的必要素养。如此,农村教师才能真正认识“农村理”,掌握农村理“全景”,窥探农村理“深景”,成为农村理的通达者。
-
识“农村理”,理解农民的教育逻辑并非农村家校沟通的最终目的,而仅是农村教师实践“文化转译”的起点。农村教师需要在农民的教育意义体系中寻求与现代教育观念的“连接点”,将现代教育观念“转译”为农民能够理解和实践的观念体系,也即讲“农村理”。只有经过这一“转译”过程,作为“超地方性知识”的现代教育观念才能进入农民的日常教育生活,并在其中“生根”“生长”。最终,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农民教育意义体系才可能发生转变,走向基于本土的、创造性的现代化转型。
“逻辑差异”是现代教育观念与农民教育意义体系间文化区隔的根源性要素,基于逻辑的“文化转译”是现代教育观念实现话语转换并为农民所理解的深层要求。这也就意味着农村教师要“掌握农村居民的行为逻辑与话语体系,即‘用农村理说农村人’……对乡土文化有深度了解,并能够将其内化为某种与学生及其家长在同一意义体系内的思维能力,将普世的、积极的教育理念转化为家长和学生惯用的话语体系”[25]。具体而言,农村教师可以将现代教育观念中有关“人的发展”“家长参与”“亲子陪伴”以及“亲子沟通”等内容与农民的“务实求验”逻辑、“天人合一”逻辑以及“土地耕种与经营”逻辑相对接,用“农民的逻辑”转译现代教育观念,将现代教育观念再现为农民能够理解并认同的知识,打通现代教育观念和农民教育意义体系之间的逻辑障碍。
逻辑层面的“文化转译”将现代教育观念变得“可理解”和“可接受”,但与实际践行间还存在着距离。现实中,农村家长会从不同途径接触到现代教育观念,并且“认同”这些观念,但无法真正落实到日常教育实践中。很多家长都以“用不了”,或者“孩子不一样”,那些都是讲给文化人听的“大道理”予以回应。其间的问题在于农村教师和家长所拥有的教育知识“形式不同”。前者是“论述型知识”,而后者是“默会知识”。对于农村家长而言,容易被接纳并落实到教育实践中的是关于“怎么做”的操作型知识,并且判断知识有效性的标准不在于内在的“表述逻辑”,而是实际的效果。因此,农村教师需要把现代教育观念从“论述型”转译为“操作型”的具体知识,这是知识形式层面的“文化转译”。这样,现代教育观念的传递过程就不再是农村教师对家长的“说教”,而是针对学生的具体问题将“论述型”的教育观念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知识,并且与家长合作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如此,农民不仅接受了经“文化转译”后的操作型知识,还亲身经历了“文化转译”的过程,感受了教育理论知识的“运用”,自身的教育能力也得以提升。
除逻辑和形式层面的两种“文化转译”外,农村教师还需要根据农民的生活现实进行“文化转译”。决定农村家长对现代教育观念的运用除了教育知识的形式外,还有实际生活的限制,如自身受教育水平、职业特征和经济水平等。因此,农村教师在家校互动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农民的现实困难。这不仅指家校互动的时间和形式能够考虑到不同家长的需求,还在更深层面指称农村教师能够了解家长的具体生活现实,将现代教育观念创造性地“转译”为农民在现实生活中可行的具体教育策略。这样,现代教育观念才可能在教育实践中成为农民的重要参考。
-
农村教师和农民之间的“文化转译”应是双向的,两者之间理应形成互补性互动。在此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农村教师将现代教育观念“转译”为农民的语言以及农民对现代教育观念的吸纳,还存在着农村教师将农民的教育知识“转译”为现代教育观念并纳入自身的理念体系,成为自身专业化发展的文化根基。在乡土生活中,中国农民形成了丰富而精深的精神文化世界,用以解释周围的自然、社会和人,也主导着他们对教育的认识和理解。这些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也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源泉。在农村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以此为认知框架理解教育的新样态、新理念和新措施。中国传统教育文化在应对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悄无声息地延续至今,深藏于农民的教育意义体系之中,成为其“文化底蕴”,也是我国教育文化传统的“活化石”。也就是说,在农民的教育意义体系中存在着烙有文化传统和实践智慧印记的教育知识。通过家校沟通,农村教师需要主动发现它们,承认其作为独特教育实践逻辑的自主价值,并“转译”为现代教育观念,纳入自身的专业知识体系。
农村教师借助“文化转译”学习“农村理”有助于扭转教师与家长间的“中心-附属”结构。在“文化转译”过程中,当家长反思自己的教育实践和认识时,便会意识到自己的教育意义体系的存在。进一步,当他们的教育知识被农村教师承认和学习时,他们便会意识到自己也是懂教育的,其教育自信便会增强。因此,在“文化转译”中学习“农村理”是激发农民教育自觉和自信的有效途径。
在“文化转译”中学习“农村理”也是农村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独特路径。这不仅因为与农村家长的沟通能力是农村教师专业能力的一部分,更是因为农民教育意义体系中的文化传统和教育智慧构成了农村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文化之根”。在理解和学习农民的教育知识时,农村教师能够真切地触摸到“传统”,感受到传统中的“教育智慧”。这不仅能够给农村教师带来处理教育问题的启发,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他们基于传统教育文化的背景去思考现代教育及观念,最终在自我反思中实现自身专业能力的发展。当农村教师能够将农民的教育智慧“转译”为论述型的教育理论体系,或与现代教育观念对接,或反思其存在的问题时,他们便能够建构起独特的教育知识体系。这是中国教育“自主知识”的另一种生成与存在形式。相较于以教育研究者为主体的、来源于经典文献的中国教育“自主知识”,它更“接地气”,更具“生命力”,是农村教师的独特知识体系。在此过程中,农村教师既得以浸润于中国教育文化传统之中,又能够在更高层面认识现代教育观念。也即在“传统-现代”的多元交织中实现自身专业发展,形成“为了乡村、扎根乡村、忠诚于乡村教育事业”[25]的乡土教育情怀。
农民教育观念的现代转化必须基于“地方性”文化,并只有在日常教育生活中慢慢积累才可能实现。农村教师需要将目光转向农民的日常教育生活和教育意义体系,在长期的探索中用农民的逻辑和语言“转译”现代教育观念,这样才有可能使现代教育观念进入农民生活,并在日常教育实践中被加以运用。这是一种教育能力的提升,更是一种教育“生命”的塑造。这种提升和塑造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借助现代教育观念和农民教育知识之间双向的“文化转译”,不仅农民的教育能力得以提升、教育主体意识得以觉醒,农村教师也在“转译”和学习“农村理”的过程中重塑自身的专业认知和自我认同。农村教师的现代教育观念与农民的教育意义体系在“文化互译”中平等交流、相互提升,农村家校成为教育的“共同体”。如此,农村教育就成为家庭和学校的公共领域,农村家校沟通便能够走出“中心-附属”的层级结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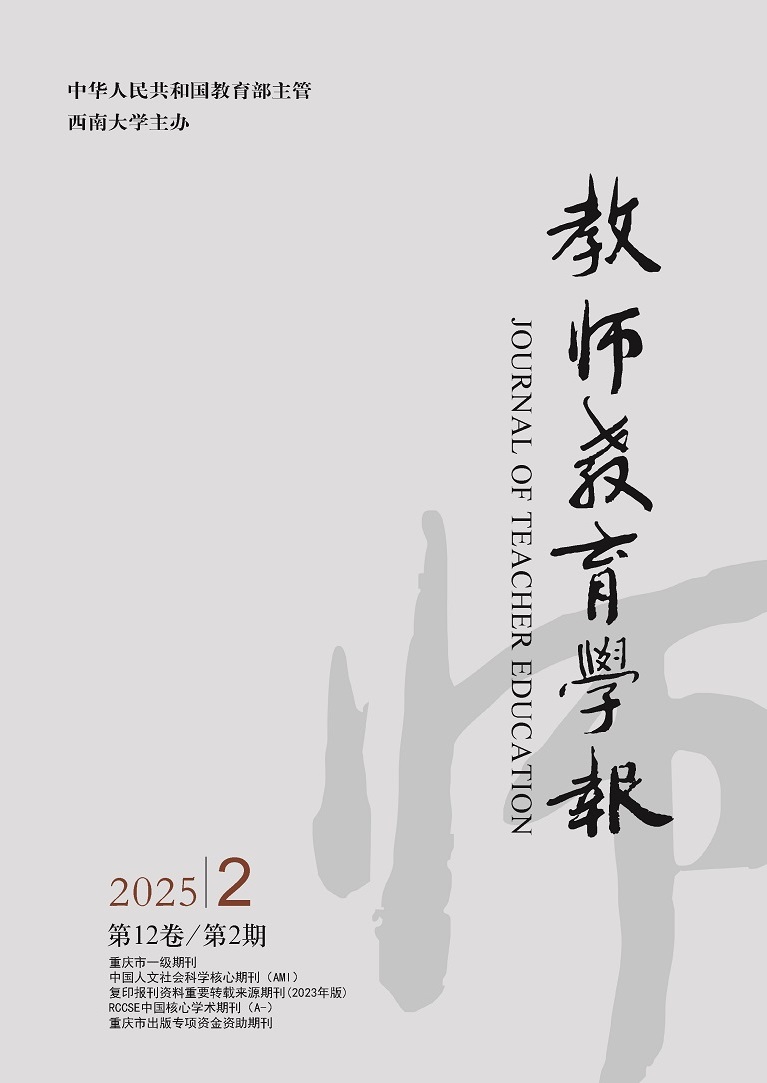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