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ML
-
2023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首次提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并深刻阐释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即“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1]。这是对教育家精神的系统阐释,彰显了教育家精神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教师高尚道德品质的充分肯定和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殷切期待,为广大教师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目标。对此,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回答了教育家精神的时代意涵[2]、生成逻辑[3]、理论基础[4]、价值意蕴[5]与培育路径[6]等方面的问题。也有学者从教育家精神引领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7]、促进教师教育发展[8]等方面展开论述,探索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理论逻辑、实践路径以及促进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路向。已有研究对我们深刻认识和理解教育家精神很有启发,但这些研究大多从宏观、中观层面进行理论分析,缺少从教师的主体性视角深入探讨作为个体的教师应如何践行教育家精神。在笔者看来,学习、研究和阐发教育家精神的根本目的在于践行,尤其是作为个体的教师如何具体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所阐释的教育家精神,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践行教育家精神的目的和要求在于不断提升教育境界,坚持立德树人。而教育境界的提升需要加强教师个体的自我修养。因此,笔者从教师个体修养层面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对切实践行教育家精神有所裨益。
-
践行教育家精神应是每个教师的自觉行为。这是教师身份角色的要求,有其理论根源。
教育家精神作为人之精神的一种,具有精神的一般特性。“精神”作为人之为人的一种属性,在不同人心里会有不同的认识,在不同人身上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因此,“精神”一词的含义颇多。《辞海》中“精神”一词的解释包括五个义项:一是指与“物质”相对的范畴,即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二是指人的神志、心神,如“精神恍惚”;三是指人的精力、活力,如“精神振奋”“振作精神”;四是指神采、神韵,如宋代卢钺《雪梅·其二》一诗中的“有梅无雪不精神”;五是指内容实质,如“传达会议的精神”“领会文件的精神”[9]。基于这五个义项,“精神”的含义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指向人(前三个义项),包括人的意识、思维、心理、心境、情绪状态等,是人在社会活动中主观层面所产生的某些状态特征,不仅反映了人在特定情境下的存在状态,更是对人的本质、人的内在气质的提炼和概括;另一类指向事物(后两个义项),包括事物的本质及其体现出来的韵味、意境,即内在的精神气质和外在的表现形式。总体而言,“精神”一词主要指向的是人,其含义涵盖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在宏观层面,“精神”是人所具有的一种本质属性,即精神属性,与人的物质属性相对,是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与客观事物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心理状态。在中观层面上,“精神”是对特定群体的主观存在状态的描述和定性,是对不同群体进行区分的标准。在微观层面上,“精神”指的是作为个体的人在成长与发展过程中对生命价值与人生境界的追求。简而言之,精神的三个层面分别对应的是整体的人、群体的人、个体的人。教育家精神是人的精神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化。因此,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来认识和理解教育家精神。
-
在宏观层面,“精神”作为人的一种本质属性,是相对于人的物质属性而言的。正是因为人具有精神属性,我们才能将其与外界的客观事物区分开来,才能根据主体与客体在本质属性上的不同去把握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人通过认识和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仅将自己的主观意识借由客观对象表现出来,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人化”,还在认识和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建构和提升自己的主观精神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文明得以进步,这种进步不是客观物质世界本身进步的结果,而是人之精神的提升所导致的。这是因为只有人的精神的不断提升才能促进其更好地认识和改造客观物质世界,也才能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诚如海德格尔所言,“肉体的所有真正力量和美,战争之稳当与冒险,还有理智之老实与机灵,都植基于精神之中,它们只有在当下精神的有力或无能中,获得提高或陷于崩溃”[10]。概言之,“精神”就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过程中所创造出的哲学、文化、思想、观念等精神力量,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属性,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不竭动力。
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实践活动,同样伴随着人之精神的建构与提升。这里所说的“精神”就是人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教育精神。所谓“教育精神”就是从事教育活动的共同体成员所具有的一种共同的气质,“是具有确定效用的价值和规范构成的复杂体系”,它通过共同体成员的“思想、实践推理及行为习惯表现出来……对教育工作者具有约束力”[11]。正是因为具有这种精神,教育工作者才能使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实践活动既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又符合教育本身的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如果说教育精神产生于教育实践,是一种抽象的客观存在,那么教育家精神则通过教育实践的主体——人,使自身具象化、人格化。因此,从“精神”的宏观层面来看,教育家精神是人类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教育精神的人格化,存在于人们的教育思想与教育行动之中,是对从事教育实践活动的人的一种外在的期望和要求。
-
在中观层面,“精神”作为对特定群体主观存在状态的描述和定性,其作用在于使我们能够辨识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区别。这些区别一般就是精神状态的不同,人们据此可以分辨出不同的群体。这里所说的群体,从比较大的方面来讲,其中有国家的区别、民族的区别、宗教信仰的区别;从比较小的方面来讲,其中有团队的区别、单位的区别、职业的区别。人们能够根据不同的精神状态,对身处其中的人加以区分。相较于宏观层面的“精神”,中观层面的“精神”指向的是作为群体的人,用以区分不同群体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面貌主要来自历史、文化的影响,能够使每个群体均表现出自己的独特之处,这种独特之处就是精神状态反映出的群体差异。“教育家精神”所指向的是教育家这一特殊群体,是他们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形成的精神状态,因而应将其理解为“教育家群体所独有的精神”。
在人类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教育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承的特征。从被誉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古代教育家孔子,到怀揣教育救国理想的近代教育家黄炎培、陶行知、梁漱溟,再到坚持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当代人民教育家于漪、卫兴华、高铭暄,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具有高尚的人格与卓越的教育能力,具有一种兼具思想性和实践性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就是教育家精神,是“一代又一代扎根中国教育事业的人民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积淀和展现出来的坚定信念、崇高人格和专业能力”[12],它不仅体现教育家的独特性,使人们能够将教育家与其他群体相区分,还能够对教师群体产生一种价值引领。
-
如果说中观层面的“精神”所反映的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差异,那么微观层面的“精神”所反映的就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往往就是指个体之间在精神境界上的差异,即个体精神境界追求的不同。据此,我们能够将人区分为不同的个体。个体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亦是人类精神的源头。没有个体的存在,就不会有群体的出现,更不会有所谓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说的“精神”就是对个体精神境界追求之价值和意义的确立。
个体的精神主要包括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心理。这是人之精神得以存在的基础,是生而为人所具备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需要个体在后天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进一步的规范和提升,从而使人的心理状态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和跃升。第二个维度是道德。这是由心理维度发展而来的,是个体在社会环境中通过与他人相互交往而逐渐形成的一种高级心理状态。它体现的是个体处理与他人关系的一种能力。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极端利己的人,不仅会让人避而远之,还会给自己制造无尽的烦恼;相反,一个始终能够站在他人角度来考虑问题、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人,其道德水平显然更高,精神空间也更为广阔。因此,一个人道德水平的高低就是其精神状态是否良好的标志。第三个维度是理想。这是个体精神的核心之所在,反映的是个体精神所志在达成之境界的高度。理想通常与信念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信念的支撑,理想就会失去内在的动力。正是因为理想有信念作为支撑、信念有理想作为目标,人们才会矢志不渝地去追求理想。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物质生活的需求而失去对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从微观层面来看,教育家精神指向的是作为个体的教师,是教师个体对自身教育境界的理想追求。它决定了“教师个体生命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和所从事的教育活动能够达到的境地和程度”[13]。
由上可见,无论是从宏观层面还是从中观层面来看待教育家精神,它都是一种外在于教师个体的规范和要求。教育家精神最终要落实到教师个体的践行上,转化为教师个体对自身教育境界的理想追求。换言之,教育家精神的三个层面为教师个体践行教育家精神提供了一个解释机制:只有教师个体不断追求与提升自身的教育境界,才能实现教育家精神由整体到群体、由群体再到个体的落实与转换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教师个体践行教育家精神的过程。
一. 宏观层面:教育家精神是教育精神的人格化
二. 中观层面:教育家精神是教育家群体所独有的精神
三. 微观层面:教育家精神是教师个体对自身教育境界的理想追求
-
教育家精神的践行要求教师不断提升自身的教育境界,加强自我修养。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修养是做人和做事的需要,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求得更好生存与发展的需要”[14],同时也是个体自觉追求和提升精神境界的根本途径,因而每个希望提升自己精神境界的人都需要加强自我修养。
在现代汉语中,“修养”一词主要有以下两个义项:一是指人们在理论、知识、艺术、思想等方面达到的一定的水平,如理论修养、文学修养;二是“指养成的正确的待人处事的态度”,如“这人有修养,从不和人争吵” [15]。通常而言,“修养”是作为名词来使用的,用以“描述人的品格高低、人格完善程度以及个人努力的目标”[16],例如“某人修养高”。从“修养”的内涵以及通常的理解来看,人的“修养”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个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持续努力,不断提升。修养还指人们为了在理论、知识、艺术、思想、道德品质等方面达到一定的水平而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学习等活动。因此,“修养”除了用作名词,还可用作动词。
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有云:“修,饰也。”又云:“饰,即今之拭字,拂拭之则发其光采,故引申为文饰……修之从彡者,洒刷之也,藻绘之也。修者,治也,引申为凡治之称。匡衡曰:‘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17]按照段玉裁的解释,“修”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修者,饰也”,即通过擦拭使物体变得光洁,由此又引申出装饰之意,意为在物体上加上繁复的彩色饰物;二是“修者,治也”,即通过“长善救失”来使个体变得完善。可见,“修”之于人,是一种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途径。《说文解字》有载:“养者,供养也。从食,羊声。”[18]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根据“养”的这一构字方式将其形象地解释为羊的食物。他认为,“羔羊是非常温顺的动物,没有什么智慧,如果没有引导者,最容易迷路,就像人的心灵那样很容易被善恶所影响……如果放任自流的话,最终是不可能向善的……修养的‘养’字就像每个人管理的羔羊,稍不细心,就会死去。相反,如果耐心饲养的话,它就会最顺从你。就像对待羔羊那样,你要给心灵食物,寒冷的时候给它温暖,火热的时候替它降温,走上迷途时,把它叫停,带它走回正道,采取各种方法,培养它走正道”[19]。新渡户稻造对“养”字的解释引用了《圣经》中“迷途的羔羊”这一典故,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修身养性”与基督教所倡导的人要悉心管理“心灵的羔羊”这一思想结合起来。据此,我们可以将“养”理解为培养、养成,是一种对心灵即“精神状态”的关注与把握,如孟子所说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20]212。
由“修”“养”二字所组成的动词“修养”,与我国古代儒家所强调的“修身养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关于“修身养性”,儒家经典《大学》对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可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方面[20]136,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修身”。这里的“身”所指的不仅仅是身体,而是身体与心灵的“统一”,且这种“统一”不是指业已完成,而是始终处于“修”的过程之中,具有长期性和未完成性。
从上述分析可知,“修养”不仅可以作为名词,还可以作为动词。当作为动词时,修养等同于古人所说的修身,指的是个体为实现自己对精神境界的理想追求而自觉进行的一种自我调控、自我教育的主体性活动;当作为名词时,修养指的是个体通过这种自我调控、自我教育的主体性活动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前者指向人的行动,后者指向人之行动的结果,二者具有内在的联系。就教师个体来说,作为动词的修养是教师个体对教育境界不断追求与提升的过程,即教育家精神的践行过程;作为名词的修养是教师个体在追求与提升自身教育境界的活动中所涵养的教育家精神。因此,加强教师自我修养是教师个体践行教育家精神的重要依托和根本途径。
-
教师践行教育家精神的过程是教育家精神由整体到群体、再由群体到个体的落实与转换过程。作为个体的教师,应通过自我修养提升教育境界,进而践行教育家精神。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
“正心”指的是端正自己的心态,其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心正”。“正心”中的“正”与“歪”“邪”相对,代表着人前进的方向。心正之人能够不受名利的裹挟、杂念的干扰,朝着正确的目标一路前行。心不正的人往往目光短浅、患得患失、见利忘义,通常会走入歧途,落个“满盘皆输”的结局。“立志”指的是确立自己的志向,与“正心”有着紧密的关联。如果说“正心”解决的是方向问题,那么“立志”解决的就是动力问题。志大则力大,志小则力小。
儒家倡导“志”要“立乎其大”,也就是一个人所立之志不可过于具体,要立就要立大志,立高远之志、鸿鹄之志。这是因为过于具体的志向能够提供的动力较小,难以支持主体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持续发展,而高远的志向则能够为主体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使其不被一时的得失荣辱所动摇,始终保持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勇气。“正心”与“立志”对教师的自我修养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均十分重要。教师所正之心不应是个人层面的私心,而应是国家层面的公心,即以教书育人来造福国家和人民的初心。教师所立之志不应是关乎个人得失荣辱的小志,而应是以天下为己任、以弘道为追求的大志。
-
陶行知曾说过,“我们生在此时,有一定的使命。这使命就是运用我们全副精神,来挽回国家厄运”[21]。这里所说的“使命”就是指教师应具有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其突出的是教师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责任担当,强调的是爱国主义与家国情怀。作为教师,不仅要有教育情怀,还要有家国情怀,即将个人的教育行动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教师要能够正确处理“小我”与“大我”之间的关系。所谓“小我”即作为个体的我,所谓“大我”即作为集体成员的我,“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即个人与集体、民族、国家的关系。教师在处理“小我”与“大我”的关系时应超越“小我”的狭隘与局限,追求“大我”的胸襟与格局,把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国家的富强、民族的进步、人民的幸福联系起来,以教育的方式担当起对国家、民族、人民的责任。
正如“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于漪所说:“教师的生命价值在于内心的深度觉醒。当一名教师把自己日常的平凡的工作和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和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千家万户老百姓的幸福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那就会胸襟宽广,有用不完的劲。这是我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22]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自打从教那天起,于漪就有明确的使命和追求,即“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祖国的未来……做一名合格的教师,不负祖国的期望、人民的嘱托”[23]。正是因为具有这种高度的生命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于漪才能在其长达68年的教育生涯中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人民教育家。
-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弘道”的思想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观点[20]100。孔子基于对人之主观能动性的肯定和赞扬,将“弘道”作为人的特殊使命。对教师来说,“授业”与“解惑”固然重要,“弘道”同样重要。身为师者,既要精于“授业”与“解惑”,更要将“传道”摆在第一位,自觉将促进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新时代教师不仅肩负着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培养人才的重任,更肩负着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崇高使命。因此,教师一方面要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要不断拓展自身的国际视野,培养世界眼光,深刻领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要义,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自身的教育实践。
我国高等教育学领域著名教育家潘懋元先生的从教经历很好地体现了“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方面,潘先生始终致力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体系,强调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体系相结合,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与人文精神,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人才;在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潘先生认为全球教育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互学互鉴的过程,因而他积极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与国际教育界同仁深入交流,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为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全球教育革新和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24]。
-
躬行践履是传统儒家极为重视的一种修养方法。“躬行”即亲身实践、身体力行;“践履”即行动、实行、实践。躬行践履实际上指的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关于实践,人们往往会从传统认识论的视角将其与理论对立起来,认为实践不过是理论的应用,其本身附属于理论,因而应将理论置于实践之上。这种观念忽视了实践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独特作用,使人的身体与心灵、知识与行动相分离,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实践并不只是理论的应用,还包括现实的生活。“生活是人生的根本,也是道德的根基与归宿。人要生存、要活着,这是无须论证的第一位的铁的道理。如果有人想脱离生活或不为生活去构建理论大厦,那只能是一厢情愿,无异于想把自己正坐着的凳子举到自己头上。”[25]
因此,人不能只满足于知识、理论的学习,停留在“知道”的层面上,更要投身于现实生活实践,以“行道”为旨归。这是因为只有“行”才能使人对“道”的领悟更为透彻,才能将“道”变为现实,进而产生新的“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教师不仅要注重自身的内在修养,还应注重外在修养,加强教育实践。实践是检验教师教育水平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教师教育境界的重要途径。教师教育境界的提升过程是“教师个体在立德树人教育实践中、在个人生命体悟中,不断认同、体验、反省、提升,不断形成教育家精神所涵盖的优良品质”[26]的过程。这一过程要求教师将“知”与“行”统一起来,在丰富、生动的教育教学生活中践行教育家精神,提升个人的教育境界。
-
践行教育家精神不仅强调“勤学”,即不断地读书学习,更重视“笃行”,即成为教育的实践者,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求是创新、启智润心、因材施教,不断提升自身教书育人的能力。换言之,践行教育家精神,是一种实践性的活动,致力于将教育理想变为现实。因此,践行教育家精神“不仅意味着思想的阐发和独到的见解,更意味着能够深入教育实践并造就大批优秀人才”[27]。教育实践与一般的生产性实践有着根本的不同。教育实践的对象是人,其目的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生产性实践的对象是物,其目的是生产出符合标准要求的物质产品,二者不可同日而语。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教师不能仅从个人的经验出发,而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遵循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不能视自己为教育活动的主宰和权威对学生进行单向的知识传递和灌输,而应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成长的促进者,善用启发诱导、润物无声的教育方法。
-
教育实践与生产性实践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其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使教育教学活动变得复杂,又对教师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应对教育教学活动的不确定性,教师就需要成为教学研究者,将教育实践与教育科研结合起来,以研究的态度来对待教育,关注教育教学活动中每一个变化,用心去研究每一节课、每一位学生以及每一个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教育教学事件。教师成为研究者的目的是“让教师更加有意识地进行教学反思,有意识地进行实践的行动改进,获得教学理性”[28]。这种基于教学反思的理性思考有助于超越个人经验与感性认识,促进教师育人能力的提升,强化主体性自觉,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以李吉林老师为例,她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情境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当代著名教育家。李吉林老师在系统总结自己的成长经历时说:“教育科研也开发了我潜在的智慧,教育科研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获得了充实而丰富的人生……中小学教师学习教育理论、参加教育科研,对于提高自身的各方面素质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十分有效的。”[29]
-
自我省思亦称自省、内省、反省,其中的“自”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表示省思的主体和对象都是自己而不是他人;二是表示主体的省思是一种自觉的行为,非外部强制的结果。其中的“省”就是察看、检视、审视;“思”就是思考、反思、思索。“自我省思”就是自己审视自己,自己反思自己,实质上是一种为促进自身完善而进行的自我教育。在中国传统的修养方法中,自我省思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20]2曾子强调,人只有通过不断地自省与反思,不断地发现自身的不足与欠缺,才能及时改进,实现自我的提升与超越。有学者指出,人的自我省思具有主体的自觉性、主客体的一致性、过程的反复性、内容的向善性等特点,具体包括三个既相互联系又层层递进的环节:一是自己对自己进行客观的评价,找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二是针对不足之处,找出其中的原因;三是对自己的不足之处进行修正与改进[30]。
对教师来说,经验固然重要,但不经过反思的经验往往是狭隘的经验,最多也只是浅层次的知识。如果教师仅仅局限于经验的获得,而不注重对经验进行深入的反思,那么这些经验就无法转化为教师的教育智慧。省思是教师自我修养的必由之路。省思的过程就是教师不断完善自我的修养过程。内省与反思能够使人始终自觉处于一种开放、包容的精神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教师践行教育家精神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就是自我省思。有很多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可以促成教师进行有效的内省与反思,其中就包括读书与写作。
-
“勤学”是教育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师践行教育家精神的重要方式。“教师要有学习的愿望,要有对知识的渴求和理解智力活动奥秘的志向,沿着这些小路攀登,才能使你达到教育技巧的顶峰——即师生之间心灵交往的和谐的境界。”[31]对于教师而言,读书是最为便捷、最为有效的学习方式之一。通过读书,教师能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最小的代价、最低的成本、最经济的方式来获取他人经过长期实践、反复思考所形成的知识经验、实践智慧、思想观念;通过读书,教师能够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使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能够充分体现人类知识生产的最新成果;通过读书,教师能够获得教育教学智慧,形成独到的专业眼光,用简洁明了、深入浅出的教学方式带动学生学习知识、技能,培育学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的核心素养。因此,教师“要读书,要如饥似渴地读书,把读书作为精神的第一需要。对书本要有浓厚的兴趣,要乐于博览群书,要善于钻研书本,养成思考的习惯”[32]。
在当前这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日益加快。如果教师不能及时而准确地获取人类最新且最为先进的知识成果,那么他们教给学生的知识就会脱离于时代的需要。如果教师不能用最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来指导自身的教育教学实践,那么他们就难以用适切的方式将人类最新的知识成果传授给学生。教师和大部分其他职业的成员从此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即他们的入门培训对他们的余生来说是不够用的,他们必须在整个生存期间更新和改进自己的知识和技术[33]。因此,“教师要常读书、读好书,以诗书育浩然之气,进而认识和相信道德之理”[34]。教师读书应注重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读什么书;二是如何读书。首先,教师所读之书既可以是与教师职业直接相关的学科专业书籍、教育理论书籍,也可以是与教师职业没有直接关系但有利于提升教师科学文化素养、道德认知水平的其他书籍,关键要看这些书籍是否具有真知灼见、是否能够使人的灵魂得到洗礼。其次,教师读书不是为了被动接受书中的知识信息,而是要通过对书中内容的批判性思考和个性化吸收来形成自己独特的认识,同时还应将读书作为自己教育生活与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窦桂梅就是这样一个将读书作为自己成长的土壤和阶梯的教师。她曾说:“我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生,深感自己缺少厚重文化积淀所带来的底气与灵气,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束缚着我专业成长的道路。但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书本这最好的老师,并将书本给予我的惊喜与力量呈现在课堂上,于是以教促读、以读促教,就有了一节又一节的精彩教学。”[35]
-
写作对教师提升自身的修养同样具有重要作用。窦桂梅老师曾说:“写作不仅是积累经验的一种方式,更是逼迫自己勤于阅读和思考的强劲动力。因懂得这些,虽工作辛劳,文笔稚嫩,但我仍坚持用文字记录自己的教育生活,让忙碌的我不断与宁静的我进行对话,让冲动的我不断接受理智的我的批判,让实践的我不断接受理论的我的提升。”[36]在窦桂梅看来,写作是教师表达自己的最佳方式,“只有真切体会到写作价值的教师才会对写作充满感激……写作不是创作,而是一种教育生活。具有写作兴趣的教师往往富有丰富的情感,拥有理性的头脑,总是保持一种敏锐的目光,悉心体察身边的冲突和矛盾,聚焦点滴的教育教学感悟,汇成思想的洪流”[37]。可见,教师写作是针对其所处教育生活而进行的体验式写作,其目的“是用语言符号对生活体验进行‘如其所显现般’的描述”[38]。“只有通过写作将处于现在进行时状态的体验描述出来,才能迫使人对其持一种反思的态度。”[39]这是因为写作的过程也是思考的过程,针对体验的写作使人们能够通过回忆再次回到事件发生的“彼时彼刻”进行思考,这种思考就是一种促使人进行省思的活动。
教师通过写作所进行的省思,是“对儿童生活的环境和根植于其中的价值意义的反思”[40]53,因而是一种教育学立场的学理省思。一般意义上的省思强调主客体的一致性,即省思的主体和对象都是自己,而教育学立场的省思强调教师向学生传授的知识信息、教师的教学风格和方式、教师在学生面前的一言一行等对学生的意义是什么,是否对他们的成长与发展有利。这种以教师写作为途径的教育学学理的省思,能够帮助教师养成教育的敏感性、抓住教育的时机,从而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的成长。范梅南对教师提出了以下两点建议:“(1)主动地体验教育生活;(2)反思性地谈论或记述这些体验。”[40]40因此,教师应有意识地通过写作将日常教育生活中的体验记录下来,尤其是那些解决问题和应对危机的体验,让教师在描述它们的过程中往往能够加深理解和思考,收获更有价值的感悟。
-
“择善而从”从字面上来看就是“择取好的来跟从”的意思,出自《论语·述而》中“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20]36。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将其注解为“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恶,则我从其善而改其恶焉,是二人者皆我师也”[41]。这就是说,在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中,要选取他人身上善的一面进行学习,如果发现他人身上存在恶的一面,就需要引以为戒并加以改正。如此这般,无论是善的人还是恶的人就都能够成为自己的老师了。“择善而从”的修养方法强调了人在社会交往中需要遵循的两条原则:一是要广泛地结交不同类型、不同水平、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人,以他们为师,虚心向他们学习;二是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要以他们为镜子、为参照,重新审视自己、观照自己、修正自己,不断完善自己。人生活在社会中,是社会的人,而生来就与社会交往相隔绝的人与动物无异[42]。这是因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3]。对于肩负传道、授业、解惑使命的教师来说,“择善而从”尤其重要。
教育家精神为广大教师带来了极大的精神鼓舞,从教师与国家的关系、教师与社会的关系、教师与教育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等方面为广大教师指明了发展方向。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应积极践行教育家精神。社会交往为教师个体践行教育家精神、提升教育境界提供了平台和资源。特别是教师与学生、同行的交往,能够使教师从不同维度、不同视角、不同立场的对话交流、思想碰撞、经验切磋中发现差距、启迪智慧,不断加深对教育的理解,进而获得境界的提升。
-
教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教学为主业。但教学并不是教师个人的“独角戏”,也不是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的单向性活动。真正的教学既包含着教师的“教”,也包含学生的“学”,是教与学的统一,其本质上是一种“多极主体间展开的有目的的社会交往活动”[44]。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与学生建立起合理的交往模式。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一个追求沟通的行为者必须和他的表达一起提出三种有效性要求”:第一,“所作陈述是真实的”,即真实性;第二,“与一个规范语境相关的言语行为是正确的”,即正确性;第三,“言语者所表现出来的意向必须言出心声”,即真诚性[45]。基于此,哈贝马斯提出了“认识式—相互作用式—表达式”交往模式以及“客观性—遵从性—表达性”交往态度[46]。这种层层递进式的交往模式与交往态度,对理性的教学交往关系的建立很有启发性,非常有助于实现教师与学生的相互认同、相互理解、相互信任乃至相互建构。因此,师生之间的交往理应是一种基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教师不能凭借自身的优势地位,以一种居高临下的主宰者的姿态来对待学生,使学生对自己的话唯命是从,而应保持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主动地去倾听学生的心声,通过倾听,洞悉学生一言一行背后的真实状态,理解学生的内在诉求与需要,进而使自己的教学能够以最为恰当的方式引导学生学习。
-
人的认知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只有通过与他人的沟通、交流、合作才能实现思想的互通、知识的共享、经验的互鉴,从而使自身获得更为全面、深入的发展。教师的专业成长与发展同样是在与他人的交往特别是在与同行的交往中实现的。这是因为在与同行的交往过程中,教师能够“对自己或他人的教学理念、教学方式、教学行为和教学效果加以考察、审视、反思、改进”[47],以优化自身的教学,提升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在日本学者佐藤学看来,学校改革的核心就在于构建学习共同体。这里所说的“学习共同体”,其主体不仅包括学生,还包括教师。他认为,不仅要把学校建成学生相互学习成长的地方,而且还要使学校成为教师相互学习成长的地方,“在教师之间建立相互开放教室、共同创造教学的合作性同事的关系……把学校建成一个能使每位教师既独立自主又协同合作的组织”[48]。因此,对教师个体而言,要善于与身边的人尤其是同行分享自己的经历与体会,主动学习借鉴他人的先进经验与思想精髓,寻觅和结交一批志趣相投、志同道合的同事,形成既相互协作又相对独立的同事关系,携手构建教师间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的学习共同体。
一. 正心立志,以家国情怀和弘道追求涵养自我
1. 厚植家国情怀
2. 担当弘道使命
二. 躬行践履,在创造性的教育实践与研究中提升境界
1. 扎根教育实践
2. 投身教育科研
三. 自我省思,在读书与写作中启智增慧
1. 勤于读书
2. 乐于写作
四. 择善而从,在多维交往中持续完善自我
1. 在与学生的交往中建立师生平等的对话关系
2. 在与同行的交往中构建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
-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全国广大教师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并深刻阐释了教育家精神的内涵,这是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价值导向和精神引领。我们学习它、研究它、阐发它,不仅仅是为了知其内涵、理其逻辑、明其价值,更是为了促进广大教师能够更好地践行教育家精神。教师践行教育家精神的过程就是教育家精神由整体到群体、由群体再到个体的落实与转换过程。这种落实与转换的实现需要教师个体在自我修养中提升自身的教育境界。也就是说,教师践行教育家精神要紧紧依托教师个体的自我修养,要不断促进教师自身教育境界的提升。为此,教师要始终坚持教育的初心,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认真履行促进文明传承与发展的弘道使命,坚持将教育实践与教育科研相结合,在读书与写作中不断省思自我,在与各教育主体的多元交往中持续完善自我,以饱满的精神、积极的态度、过硬的本领投入到教书育人的事业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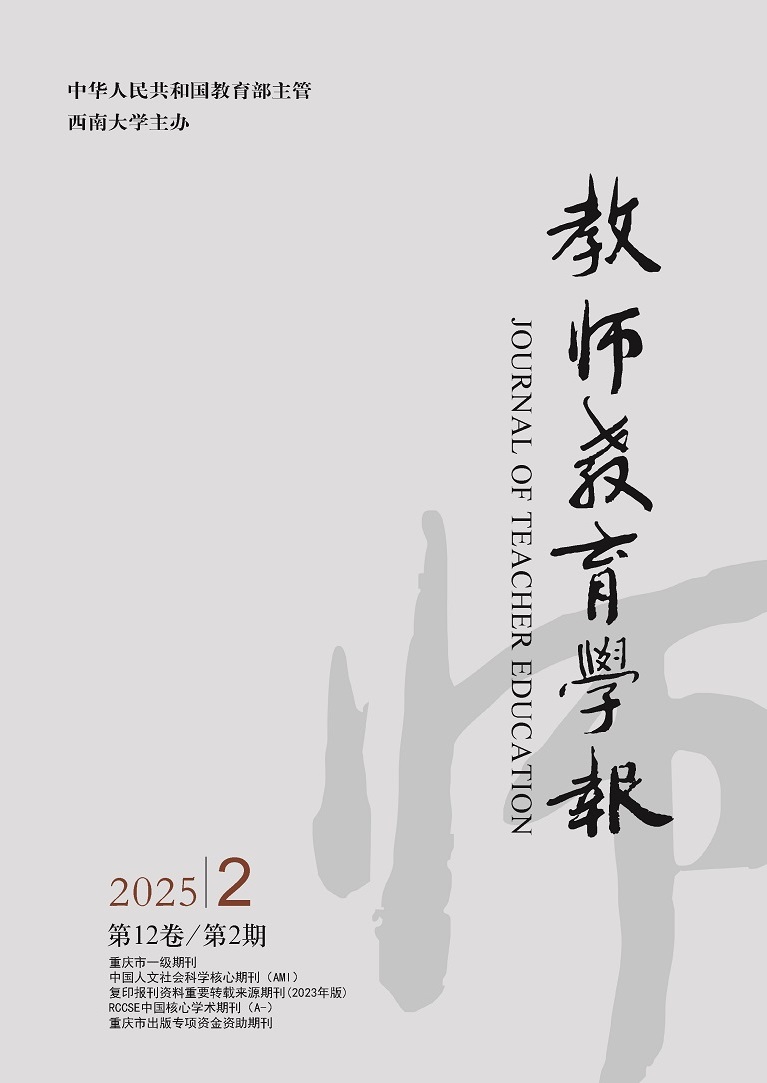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