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文学经典”问题,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研究堪称经典。他说:“我们拥有经典的原因是生命短促且姗姗来迟。人生有涯,生命终有竟时,要读的书却前所未有地多。从耶和华文献作者和荷马到弗洛伊德、卡夫卡及贝克特,经历了近三千年的旅程。但丁、乔叟、蒙田、莎士比亚及托尔斯泰是这一旅程所必须的深广港口,每一位作家都足够我们以一生的时间去反复阅读,实际的难题在于每次广泛的一读再读都要排除掉一些东西。”[1]24-25反复阅读的过程也是经典生成的过程,被排除掉的“一些东西”是“非经典”的,抑或是“非原著”的。“经典”和“原著”的关系很值得讨论,特别是在布鲁姆的理论构架中,作为“经典的中心”[1]37的莎士比亚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可以看到从“原著再造”到“经典生成”的典型过程。
HTML
-
何谓“原著再造”?“原著再造”和“经典生成”有什么关系?这一问题值得提出深入讨论。在很多情况下,当谈论“经典”时,“经典”并不等于“原著”。要弄清“原著再造”,先要理解“经典生成”。
-
关于文学经典生成的问题,国内学界已有不少研究,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经典生成的方法。经典生成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可以运用校勘方法对古典文学中的“异文”作比较,“择优”[2]有助于经典文本的生成。文本的不断修改也可以产生经典,“作者自我深刻化之后的回顾与修改,就是自我经典化的努力”[3],例如金庸对自己作品的多次修改,就使其小说从“流行经典”“迈向‘历史经典’”[4]。文本的不断积累也是经典生成的方式。例如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涉及周作人的“秋草园”记述、1906年《秋草闲吟序》、1953年《鲁迅的故家》、1960—1962年《知堂回想录》等[5]。这种累积过程,就是生成历史经典的重要途径。
第二,经典如何生成。“文学接受史本质上乃是文学经典的形成史。”[6]接受促成了经典的生成,对“接受”可有多层面理解。首先是文本阐释,例如冯雪峰对丁玲小说《水》的阐释,让文本在革命的历史情境下被接受和理解[7]。其次是文本的传播。例如现代报刊对作品的传播意义重大,其他传播媒介如电影、网络等促成了经典被更广泛地接受。再次,“文学选集潜在地参与了文学经典的遴选,有时甚至就是文学经典生成过程的一部分”[8]。阐释、传播、遴选作为不同接受方式在经典生成过程中均能起到重要作用,不过,经典的生成还必须有其他外界条件。
第三,促成经典生成的条件。“着力维护市场经济中‘文学场’的生成功能,对作家进行正向引导与及时推介,努力培植经典文学作品繁育的人文环境和社会土壤”[9],是文学经典得以生成的保障。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还应树立“新标尺”[10],“需要更大的文化价值系统的整体设置与之配套”[11]。经典的生成不仅在于作品本身,还需要外部的促生力量。
已有对文学经典生成问题的研究已较为充分,不过其中似乎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经典”和“原著”的关系问题。
-
“经典”就是“原著”吗?在经典生成和定型的过程中,原著会不会被改变?这个问题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其实很普遍,校勘过程中“异文”的出现就是对“原著”的质疑,无论选择哪种“异文”,都有可能构成对原创作品的再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的例子就十分突出,这些世代累积型作品最终所成就的经典定本和“原著”之间差距甚大,尽管金圣叹批本、李卓吾评本都是经典,但并不能就此称之为“原著”。即使《金瓶梅》《红楼梦》这类独立创作的经典作品,也存在词话本和崇祯本的区别,存在脂砚斋评抄和高鹗补缀的区别。这种现象在现代文学中也不少见。作品最初在报刊上发表,到后来成书出版,收入文集,也可能会有不同,《子夜》《骆驼祥子》《围城》以及金庸小说都是十分明显的例子。今天读到的“经典”,不一定就是作品最初的原貌,不一定就是所谓“原著”。把生成的经典认同为“原著”,这种“原著”就是被再创造出来的。
这一问题在经典的跨文化传播中更为突出。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传播首先会涉及到翻译问题,翻译文本不可能等同于原著。“从传播机制来讲,翻译文本属于从经典衍生的次文本,因为译文总在原文之后产生,是原作的生命在新的社会语境中的再生。”[12]这是翻译文本和原著的基本关系。译本要尽可能切近原著,严复译《天演论》时已有了明确认识:“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13]严复虽然指明了译事的信达雅原则,但他自己也不能完全做到。翻译要贴合原著,是难事。不过,严译《天演论》尽管存在诸多瑕疵,在中国依然是经典之作,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知识界,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
译本可以脱离原著限制,表现自身价值,读者甚至可能把译本当成原著来读。“如果翻译真的只能够扮演次要的角色,而且永远也不及原著的话,那也没有阅读的必要或意义——读者怎会愿意去阅读一本早已知道是有问题的、不准确的、次要的书?可是,假如所有人都只阅读原著,唾弃翻译,那么,作品的读者人数必会大为减少。”[14]18所以,“从一般读者的角度来看”,“原作和译文的分界线也是没有必要的”[14]21。好的译本可以代替原著,或者在译本所处的语境下它就能成为原著,译本因此成为原著的一种再造。
-
在经典生成包括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原著会被再创造。原著再造的结果产生经典,经典很可能就会遮蔽了原著的最初面貌。被布鲁姆奉为经典中心的莎士比亚戏剧就是这样的经典:“无论怎样,我们不能抛弃莎士比亚,或抛弃以他为中心的经典。我们常常忘记的是莎士比亚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我们,如果再加上经典的其他部分,那就是莎氏与经典一起塑造了我们。”[1]33
但凡谈论经典,自然绕不开莎士比亚戏剧。但一般读者很少知道,在全部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中,至少有一半“原典”存在着一个或多个“四开本”与“第一对开本”之间的版本问题。换言之,作为经典接受的莎士比亚戏剧就是莎翁“原典”吗?以一般中文读者所熟悉的朱生豪译本来说,朱生豪翻译的莎剧底本是1914年的“牛津版”。仅以《哈姆雷特》为例,在1623年被视为最早“权威本”的“第一对开本”中的《哈姆雷特》之前,已有两个“四开本”,即1603年的“第一四开本”和1604年的“第二四开本”。单从篇幅上说,“第二四开本”比“第一四开本”多出1 800诗行。而从舞台脚本来看,显然“第一四开本”更接近最早的剧团演出本,因为这个被后人诟病为“坏四开本”的“第一四开本”本身就是对演员记忆的台词的整理、编辑和出版。问题来了:朱生豪以1914年“牛津版”为底本翻译过来的中译莎士比亚戏剧到底算不算莎翁“原著”?
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行旅,就是一个“原著再造”和“经典生成”的过程。莎剧在中国如何成为经典,中译本如何再造莎翁原著,都值得讨论。莎剧出现于晚清中国的最初面貌,是被完全改造过的。1903年上海达文社出版《澥外奇谭》,署“英国索士比亚著”。此书是从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中“选译其最佳者十章”[15]译成文言,每章都用八字标题,不但与莎剧原著不同,与兰姆姐弟的书也面貌迥异,其中涉及迻译作品的具体时代情境、文学场域,也与接受者的态度、认知水平等相关。莎士比亚每部剧作的创作、上演、出版情况都不同,各剧被引入中国的情况也不可一概而论。创作于1595—1596年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的早期剧作,和《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李尔王》等拥有较多中译本的莎剧相比,《罗密欧与朱丽叶》在现代中国的翻译、改写等情况十分突出,这与该剧选择的是广受欢迎的爱情题材有很大关系。
“宁愿为情而死,也要捍卫爱情的自由与尊严。”[16]《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不仅是由家族仇恨造成的,也在于时机不凑巧。劳伦斯修士原本把一切安排妥当,可送信的约翰修士因瘟疫被隔离,罗密欧没有得到消息,误解发生,墓穴自杀,酿成悲剧。“中古时代,瘟疫带给人们极大的恐惧。防止瘟疫扩散传播的唯一办法,是一经发现,即将患者家门窗钉死封锁。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曾多次采取此法杜绝瘟疫流行。”[17]188瘟疫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并不罕见,约翰修士遭遇瘟疫能成为酿成悲剧的合理乃至寻常的理由。这也就可以理解莎剧为何没有渲染这场瘟疫,只是从约翰修士的口中简要述出。然而,瘟疫这一导致悲剧无可挽回的直接原因,在莎剧中国化的“再造”中,或多或少地被忽略了。
对莎剧的中国行旅问题,学界已有不少研究。但已有研究较少触及莎剧故事的改写问题,较多集中于文本翻译,如群体性误译问题[18]、不同版本手稿对比研究[19]等,关注的都主要是莎剧文本翻译的具体问题,并且大部分讨论的是朱生豪和梁实秋的译本,对其他重要译本的关注并不充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中文译本及故事改写等问题,尚有不少史料值得深入开掘和细致论析。本文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从故事的翻译和改写、现代诸家的中译本、傅光明译本的“原味儿”等方面来讨论莎士比亚在中国经典化的历程,可以呈现莎剧以不同形式被再创造的现象,也可以显现莎剧在中国的独立生命形态。那些不能等同于原著的故事和翻译,本身也能构成历史的经典。
一. “经典生成”的三个方面
二. “原著再造”的表现方式
三. 莎士比亚经典的原著问题
-
1936年,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出品的乔治·库克导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中国放映,中文片名改为《铸情》。1944年1月3日航空委员会政治部所属神鹰剧团在成都国民大戏院以“铸情”之名公演曹禺译本《柔密欧与幽丽叶》。《铸情》因此成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中国被接受的另一个文本。而推原其来由,则要从林纾的翻译开始。
-
《罗密欧与朱丽叶》译为《铸情》,源于林纾。19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说部丛书第一集第八编”“英国莎士比原著”《吟边燕语》,由林纾、魏易合译。此书未注明所据原本,只称“莎诗纪事”[20]2,实际上译自兰姆姐弟的书。《吟边燕语》是《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通过《吟边燕语》中的文言短篇小说《铸情》第一次引入中国。
《铸情》列为《吟边燕语》第四篇,还有《肉券》《驯悍》《神合》等20个故事,以林纾特色文言翻译。小说道:“夜中筵罢,罗密欧出。迨二友既去,遂越过短垣,入加氏园中,月光烂如白昼。红窗忽辟,周立叶盈盈已在月中。月光射面,皎白如玉,以手承腮,似有所念。此时罗密欧自念,能幻身为手套者,尚足以亲香泽。周立叶对月久之,忽生微喟。罗密欧隅伏听之。”[20]24无论是后来的电影还是话剧,“铸情”标题均源自《吟边燕语》。林纾的神妙译笔奠定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中国的呈现基础。故事的翻译与改写,成为此后《罗密欧与朱丽叶》进入中文语境的一种方式。
1929年狄珍珠译述《莎士比亚的故事》由上海广学会出版,收录了白话文译本《罗梅阿与周立叶》。其后《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还有多个中译本,常用译名是《莎氏乐府本事》,其中《罗密欧与朱丽叶》被译成《罗米华与裘丽特》(1936年张光复译本)或《露迷欲和主丽特》(1937年杨镇华译本)。最著名的是1956年萧乾译《莎士比亚故事集》,1957年重印时书名改为《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萧乾的学生傅光明译《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京华出版社2006年版),是继萧乾之后又一个值得称道的译本。
-
傅光明追溯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的来源。在5世纪的《以弗所传奇》中可以“找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源头”[21]。1476年意大利诗人马萨丘·萨勒尼塔诺(Masuccio Salernitano)的《故事集》、1530年路易奇·达·波尔托(Luigi da Porto)的小说《最新发现的两位高尚情人的故事》、1554年意大利马泰奥·班戴洛(Matteo Bandello)的小说《罗梅乌斯与茱丽塔》、1559年法国皮埃尔·鲍埃斯杜(Pierre Boaistuau)的《悲剧故事集》、1562年英格兰亚瑟·布鲁克(Arthur Brooked)的叙事长诗《罗梅乌斯与朱丽叶的悲剧史》、1567年威廉·佩因特(William Painter)的散文译作《罗密欧与朱丽叶》、1594年意大利科尔泰(Girolamo della Corte)的《维罗纳的故事》,以及奥维德《变形记》和阿普列乌斯《金驴记》等,都构成了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前文本。在莎士比亚写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前,已有相关故事流传。
这些莎剧之前的故事,有的也引入了现代中国。戴望舒翻译出版《意大利短篇小说集》的第一篇即《罗密欧与裘丽叶达》,译自“马德欧·彭德罗”(Matteo Bandello)的小说。商务印书馆有两版《意大利短篇小说集》:一版是1935年9月“万有文库”版;一版是1935年12月“世界文学名著”版。“世界文学名著”版封面上印有“彭德罗等著”及英文翻译。戴望舒既是诗人,也是翻译家,是莎剧的现代中译者之一,1930年上海金马书堂出版了他翻译的《麦克倍斯》。戴望舒译班戴洛《罗密欧与裘丽叶达》文笔优美,开篇道:“假如我对于自己的故乡所应有的感情并不是错误的话,那么我敢说,在我们这个美丽的意大利地方,再没有几个城能比委罗那所处的地点更为优美的了。”[22]可以看到班戴洛的故事与莎翁故事主体情节一致,但莎翁的故事演绎更为紧凑。班戴洛从“我的故乡”着笔,徐徐道来,主要采用裘丽叶达视角,思想矛盾刻画得十分生动,在戴望舒的译笔下,她成了故事里比罗密欧更加动人的人物形象。从《罗密欧与裘丽叶达》到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对朱丽叶描述偏重的痕迹依然存在。
有意思的是,班戴洛的这篇小说不只是有戴望舒译本。在戴望舒之前,1933年广州《东方文艺》杂志第1卷第1至3期刊出了“包三易译”“班德洛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译文之前有译者对“马特奥班德洛(Mattes Bandello 1480?—1560)”的简介:“生于伦巴底(Lombady),早年居于米兰(Milan),后才迁居到孟都亚(Mantnε),他是一位僧教徒,他最后是做法王亨利第二的主教。他曾经尝试过不少冒险的生活,他的小说多半是爱情的和惊险的传奇,文体美丽而有力。这篇小说为后来莎士比亚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悲剧的蓝本,不过他参用了法国的删改本,把那两个情人死别时缠绵的一节省略了。(莎翁此剧,有田汉的中译本,在中华出版。)本篇译自Great Short Novels of the World。”[23]包三易对这篇小说颇有研究,在班戴洛《短篇小说集》中,《罗梅乌斯与茱丽塔》是其中一篇。不过,说“他参用了法国的删改本”,却把事实颠倒了。包三易把小说标题译成“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无田汉中译本的影响。《东方文艺》创刊号选择刊登班戴洛的这篇小说,可以说与故事本身或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盛名相关。
-
莎剧故事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不仅是翻译之功,还在于故事改写。1933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陈少平编述《罗米欧与朱丽叶》,此书被列入“新生命大众文库”,以长篇“故事”形式面向“大众”读者。书分十章,每章冠以小标题,《序言》介绍了莎士比亚及其文学成就[24]。陈少平“编述”以莎剧为基础,含有创作成分,可以见出编者所倾注的情感。1948年上海永年书局出版萧叔夜编写的“电影小说”《罗密欧与朱丽叶》,作为“电影小说丛书第二辑”出版。这本书包括四篇故事:第一、二两篇分别是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仲夏夜之梦》,第三篇是特里斯《罗宾汉》,第四篇是罗斯《爱弥儿·左拉》,都改编自当时著名的电影。在正文中,《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标题还是“铸情”,是电影的名字[25]。故事改编自电影,具有通俗性,描述仍沿袭莎剧,传达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在电影、故事、戏剧之间的流转变换。
更有意思的改写是1948年陶君起“故事新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用章回小说笔法写莎剧,第十七章刊登于《游艺报》1948年第6卷第4期(复刊新64号)。《游艺报》1921年8月在上海创刊,10月即停刊,后来在上海复刊,主要刊载时事消息、通俗作品等,对戏曲和小说尤为偏好。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第十七章一起刊于《游艺报》同一期的还有梨园小说《金锁计》、滑稽小说《红楼新梦》、京剧总讲《生死恨》等。陶君起既是戏剧评论家,也是通俗作家,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连载时标题上注明“故事新编”。第十七章“生把鸳鸯分开两下里”叙道:“这时节疏星满天,露台上虫声唧唧,树枝头夜莺啁啾,奏着断续的乐曲,楼中却是静悄悄地。直到月已西斜,正东方天上已露出鱼肚颜色,只见卧室门一闪,走出一双少年男女。那少女披拂着黄金般秀发,偎依在那少年肩臂之间。正是才缔新婚,骤生魔划的罗密欧与朱丽叶。”[26]故事还是莎翁故事,叙事话语却不是翻译的中文,也不是新文学的白话,而是中国章回小说的故事语言。陶君起虽然把莎剧变成了言情小说,这种“新编”虽不无“游艺”味道,却也能够突出青年人婚姻不自由的主旨,令读者在“游艺”之外得到感动与教益。
莎士比亚剧作才华横溢,也是博人所好的通俗性创作。莎剧在中国的翻译和演出,既是经典流传,也是时尚西潮,和“通俗”有着距离。章回小说版《罗密欧与朱丽叶》及电影故事编写等,可看成莎剧文本在中国的另一种生成方式,是一种通俗化的表现,使莎剧故事在中国更加深入人心。不过,莎剧故事经过翻译、改写和新编,不可避免地会与原著故事有所不同。各种不同的中文版《罗密欧与朱丽叶》于是有了更多传奇性质与现代色彩,具备了独立形态。
一. 从林纾的翻译开始
二. 马泰奥·班戴洛的小说
三. 面向“大众”的故事改写
-
《罗密欧与朱丽叶》在20世纪中国的接受和传播是从翻译开始的。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中译本主要包括:田汉《罗蜜欧与朱丽叶》(1924)、徐志摩《罗米欧与朱丽叶》(1933)、曹未风《罗米欧与朱丽叶》(1943)、曹禺《柔密欧与幽丽叶》(1944)、朱生豪《罗密欧与朱丽叶》(1947)、梁实秋《罗密欧与朱丽叶》(1967)、孙大雨《萝密欧与琚丽晔》(1998)、方平《罗密欧与朱丽叶》(2000)、傅光明《罗密欧与朱丽叶》(2014,2018)、辜正坤《罗密欧与朱丽叶》(2016)。有人列出其中八个中译本,指出田汉译本“具有首译之功”,曹未风译本“不纠结于原文的韵律等诗歌形式”,曹禺译本“非常口语化,读起来朗朗上口”,朱生豪译本“融入了译者的情致、偏好”,梁实秋译本是“学术性翻译的典范”,孙大雨译本是“以诗译诗的最早实践者”,方平译本“注意译作的舞台效果”,傅光明译本是“原原本本、原汁原味”的,但在对比各种译本文字异同时略去了田汉与曹未风的译本[27]。本文以下对田译本、曹译本和一向被忽略的徐志摩译本作具体论析,考察这些译本如何带着译者个人的特色与时代氛围而再造莎士比亚。
-
田汉译本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之前田汉已翻译了《哈孟雷特》,作为“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的“莎翁杰作集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1922年出版。《罗蜜欧与朱丽叶》是“莎翁杰作集第六种”,1924年出版。“少年中国学会丛书”是由“少年中国学会”出版的一系列编译图书,学会专门组织了“丛书编译部”,制定了“编译部简章”[28],预告将要出版的书目。田汉是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成员,积极参与了丛书编译工作。1923年田汉致宗白华信中说:“归国后以舜生介绍即在中华书局编辑所工作,终日与舜生相对,服务之余,商榷时政得失,旁及文坛近事;有所感触则相与痛叹或相与砥砺。同部诸友复皆少年英俊可与有为,故任事以来颇为合意。今将以三四年之力独出二十种丛书,计为莎翁杰作集十种近代小说及戏曲诗歌十种,前者已出《哈孟雷特》(Hamlet)一种,第二种《罗蜜欧与朱丽叶》现连载于《少中》,下期即可告竣。”[29]1922年9月,田汉结束在日本的留学生活,经好友左舜生介绍到上海中华书局任职。《哈孟雷特》《罗蜜欧与朱丽叶》均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在出版单行本之前,两部译作均已曾在《少年中国》杂志连载。
《哈姆雷特》前三场1921年连载时译为《哈孟雷德》。在译文之前,田汉译叙说:“今日予将偕漱瑜往上野观落樱,谁则将吾等泪珠,一洒梅舅墓头草者。呜呼,夫复何言,夫复何言!闻变后哀愤填膺,稍稍平静,则取莎翁《哈孟雷特》Hamlet剧译之以寄其情。”“译此剧时,态度颇严肃而慎重。特原文晦涩处,虽有各大家之解释,恐仍有不达处,则当就正于诸先进者矣。”[30]译叙日期为1921年4月16日,此时田汉居于日本。《哈孟雷德》是田汉哀念舅父所译,是他翻译莎剧的开始。田汉舅父易梅园1920年12月被军阀杀害,他是田汉求学的引导者和资助者,他的女儿易漱瑜是田汉的爱人。《罗蜜欧与朱丽叶》连载于1923年《少年中国》第四卷第一至五期,注明“莎翁杰作集第二种”。第一次的连载译文末有译者附言,全文为:“此译成于1922年居东京时,归国后诸事鞅掌,无暇整理,本志四卷一号将出版,舜生嘱将此稿现行发表,因仓卒付印,译语未妥及错误者知必尚多,希望阅者不吝指正,将来印单行本时当细心校订也。”[31]《罗蜜欧与朱丽叶》始译于日本,1923年7月译完。也就是说,除第一幕的五场是在日本译就的,其他部分的翻译和《少年中国》连载几乎同步。如果说《哈孟雷德》的翻译和舅父的死相关,那么《罗蜜欧与朱丽叶》的翻译则同他和表妹易漱瑜在日本的爱恋相关。田汉虽然没有说明他为何选择《罗蜜欧与朱丽叶》作为他翻译莎剧的第二部,但青年剧作家与名剧故事的青春投契感已不言自明。
田汉译本《罗蜜欧与朱丽叶》并不完善,甚至他自己也不满意。比较《少年中国》连载本与中华书局单行本,田汉作了稍许修改,不过不能令人满意之处依然存在。以《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场“凯普莱特家的花园”这一经典段落为例,对几种译本进行说明。在田汉译本中,罗蜜欧上场说:“没有受过伤的人,总好嘲笑别人的伤痕。——[朱丽叶从楼上的窗口出现。]可是,静!那边窗户里放出什么光来了?那是东边,朱丽叶便是太阳!——出来美丽的太阳,杀掉那嫉妒的月亮!她看见您,是她的侍儿,比她还要艳丽的多,她的脸色早急得憔悴可怜了:她既然这样嫉妒您,您也莫做她的侍儿;她那种灰青色的贞女衣不是蠢人谁肯穿它;把它丢了罢。——这是小姐:哦,这是我的情人!哦她知道她是的!——她说话了,可是又没有说;这算什么。她的眼睛不明明说着什么吗;待我答她的话。——我太唐突了,她不是对我说的。天上有两颗明星,因为有些事情公出,请她的两个眼珠到他们的星座里去照耀几晚。可是假如她的眼睛在星座里,星座在她的眼眶里时那可如何呢?那么她的粉面的艳光会把星光羞死,像日光羞煞灯光一样:她的眼睛在天上却把碧霄照一个澄澈,使鹄鸟唱起歌来以为不是晚上。看她把手儿托着香腮哩!哦!恨我不是那手上的手套不然岂不能触着她的香腮吗!”[32]田汉用散文体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字里行间可见青年剧作家的认真与才华。不过有些译文稍嫌费解,如关于“星座”和“眼珠”的文字。1926年,焦尹孚对田汉译本提出批评意见,分两部分发表于《洪水》第9期和第10/11期合刊,前半部分指出田译本在文体、文字、所据原本等方面存在问题,后半部分列举田译本多处段落并指出其中的翻译错误。
焦尹孚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外文系,早期文章见于创造社刊物。他从事过翻译和创作,据说“他翻译过莎氏比亚的几本悲剧”[33],但尚待查考。不过,他评价田汉的翻译确实具有专业眼光。对于译本所据“牛津大学出版的莎氏全集”,焦尹孚评论道:“莎氏剧的版本还不要说有folio和quarts的不同,就是目前流行着的,也有许多种类。因此常常小有出入。据我的原文版本,有好几处田君都不曾把他们译出。这一点,我想有三种可能:或者是田君所据的版本上是删去了的。或者版本上原来是有的,而田君偶尔忽略了。再不然,就是田君在实行‘删译’了。”[34]对开本和四开本是莎剧翻译和研究不可避免的重要版本问题,因为时代限制,现代莎剧译者在原文版本选择上存在局限性。无论是连载版还是单行本,田汉都没有注出他翻译《罗密欧与朱丽叶》所据的原版本。在单行本扉页的莎士比亚图像下面注出是用了第一对开本封面上的图。如果田汉译本是根据1623年的第一对开本,也存在问题。“虽然第一对开本对第三四开本进行了有益的校改,并增加了一些舞台提示,却完全因为排版的粗疏,造成了许多新的错误。现代编本一般习惯性地以第二四开本为蓝本。”[35]268焦尹孚指出田汉译本的版本问题,的确说到了关键点上。他对田译本的总体评价同样尖锐:“译文不是失于太散,就是过于拖沓,而且有时因田君过重直译,弄得来晦暗甚而至于不可解。这不能不说是田君很大的一个失败。”[34]“直译”还是“意译”在翻译中总是纠缠难解,焦尹孚并非否定“直译”,但如果译文效果“晦暗甚而至于不可解”,那翻译本身就存在问题。焦尹孚对田译本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莎剧中译的反思和警醒。在文章最后,焦尹孚说道:“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不妨重译的。”“田君的莎译我们就让它做走这条路的一个先驱(pioneer)罢。”[36]田汉是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第一位中文译者,虽然他的译本存在不足,但“先驱”地位功不可没。田译本是二三十年代中文读者阅读《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要依凭。
-
诚如焦尹孚所言,作为世界文学经典,《罗密欧与朱丽叶》必然被不断“重译”。1940年代以后,曹未风、曹禺、朱生豪等翻译家和文学家再译了这部经典之作。以曹未风所译《罗米欧与朱丽叶》“第二出第二景”为例,罗米欧道:“他对着绝不觉得伤痛的疤痕取笑呢。/(朱丽叶自上面窗口出现)/可是,静啊!从那窗口中出现了什么光?/那里是东方,朱丽叶便是那朝阳,/升起啊,美丽的太阳,消灭那/已然因了忧郁而憔悴的忌妒的月亮,/你虽然是她的女使,你可比她美丽多了,/不要做她的女使吧,因为她是忌心深重的:/她所给与的衣裳的颜色也只是憔悴而瘦绿:/只有愚呆的人才愿意将它穿起;脱掉它。/她是我的小姐,啊!她是我的恋人!/啊,她自己知道她是的!/她说话了,可是她没有说什么;是什么?/她的两眼在传言呢。——我得答应它。——/我太大胆了,她也许不是向我说话吧。/全天空中的两颗最美丽的明星,/为了一些事离开了它的星座,/现在请她们闪映到它们的归时,/假如她的两眼真在天上,而将星镶进她的眼眶,又怎样呢?/她面颊上的光彩便会淹没了一切的星光,/如白昼淹没了灯光一般;她的眼在天上,/便会从那广漠中的天空中洒下了那样亮的光明,/令鸟雀们都立刻唱起,以为又到了清晨。/看哪,看她把手支着面庞,多么美!/啊,我但愿变成那只手上的一只手套,/以便亲近她的面颊!”[37]曹未风没有田汉的才气,一些文句“晦暗甚而至于不可解”的毛病依然存在。不过,和田汉散文体译本相比,曹未风用诗体翻译《罗密欧与朱丽叶》,确实注意到了莎士比亚“诗剧”的特点。曹未风是一位认真和专业的翻译家,他为莎剧中译做出了重要贡献。
曹未风应该是第一位致力于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中国译者,他留学英国,在翻译的同时也从事莎士比亚研究和教学,并发表相关文章,1935年翻译了莎剧《该撒大将》。据李伟民研究,抗战时期贵阳文通书局出版了11种曹译莎剧[38]。1946年上海文化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推出“曹译莎士比亚全集”,其中第“34”封面标题为“罗米欧及朱丽叶”,内页标题“罗米欧与朱丽叶”,版权页写明“全集普及本”。《微尼斯商人》在“曹译莎士比亚全集”中是“9”,《马克白斯》是“35”。1944年《西风》杂志第69期《编者的话》说:“曹先生近年来致力于莎士比亚全集的译述工作,已完成了十七种。”[39]1947年上海大夏大学《大夏周报》刊登消息:“中国语文学会第三次学术讲座为纪念莎士比亚诞辰”,“敦请曹未风教授‘谈莎士比亚’”,“曹氏翻译莎翁作品出版者已达廿余种,故对莎翁一生事迹了如指掌,听众深感兴趣”[40]。一般认为,曹未风翻译了12部莎剧,另译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部。而据上述史料,曹未风译莎剧不止12种。他的莎译工作一直持续到1949年以后,到底译过多少莎剧,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数目。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从事翻译工作异常艰难。抗战期间呕心沥血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朱生豪,译稿就曾在战火中一再被毁。曹未风的“十七种”或“廿余种”译稿或许也未能幸免。曹未风的译文虽不及朱生豪雅致和顺畅,但1943年曹未风32岁、朱生豪31岁,他们翻译《罗密欧与朱丽叶》,正是艰难岁月里青年文学翻译家坚持理想的体现。
-
在田汉译本和曹未风译本之间,还有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中译本往往被人疏忽,这就是30年代徐志摩节译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刊于《新月》1932年第4卷第1期和《诗刊》1932年第4期,并收入1932年出版的《云游》。徐志摩译《罗米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景”,罗米欧道:“啊,轻些!什么光在那边窗前透亮?/那是东方,朱丽叶是东方的太阳。/升起来呀,美丽的太阳,快来盖倒/那有忌心的月,她因为你,她的侍女,/远比她美,已然忧愁得满面苍白:/再别做她的侍女,既然她的心眼不大;/她的处女的衣裳都是绿阴阴的病态,/除了唱丑角的再没有人穿;快脱了去。/那是我的小姐,啊,那是我的恋爱!/啊,但愿她自己也承认她已是我的!/她开口了,可又没有话:那是怎么的?/她的眼在做文章;让我来答复她。/可不要太莽撞了,她不是向我说话:/全天上最明艳的一双星,为了有事,/请求她的媚眼去升登她们的星座,/替代她们在太空照耀,直到她们回来。/果然她们两下里交换了地位便怎样?/那双星先就敌不住她的颊上的明霞,/如同灯光在白天里羞缩,同时她的眼/在天上就会在虚空中放出异样清光,/亮得鸟雀们开始歌唱,只当不是黑夜。/看,她怎样把她的香腮托在她的手上!/啊,我只想做她那只手上的一只手套,/那我就得满揾她的香腮!”[41]这是诗体翻译,也是诗人的翻译,在尽可能贴合原文的基础上,显得与翻译家、剧作家的译本不同,更带有诗人浪漫的神采。胡适于1930年底“任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翻译委员会,曾拟定一个试译莎翁全集的计划:由闻一多任主任,徐志摩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译《威尼斯商人》,陈西滢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译《麦克白》”[42]。这个“莎翁全集的计划”可说是集结了与胡适交往密切的“新月派”诸子。梁实秋翻译的《马克白》《威尼斯商人》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署“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编辑”。徐志摩译《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场应该就是这个“计划”的产品,只是仅译出这一场。
陆小曼为《云游》写序,无以言说的哀痛溢于文字之间:“人生的变态真叫人难以捉摸,一霎眼,一皱眉,一切都可以大翻身。我再也想不到我生命道上还有这一幕悲惨的剧。人生太可怪了。”“我眼前只是一阵阵的模糊,伤心的血泪充满着我的眼眶再也分不清白纸与黑墨,志摩的幽魂不知到底有一些回忆的能力不?你若搁笔还不见持我笔的手!!”[43]《罗米欧与朱丽叶》收入《云游》,和徐志摩那些浪漫的诗歌《爱的灵感》《云游》放在一起,其本身也是诗的。从陆小曼的序再读《罗米欧与朱丽叶》,爱的相逢和“生命道上”“悲惨的剧”,黏合与模糊了现实人生与戏剧故事的分界。《新月》第4卷第1期是“志摩纪念号”,发表两篇徐志摩遗稿,即《罗米欧与朱丽叶》与《醒世姻缘序》,另有胡适《追悼志摩》、郁达夫《志摩在回忆里》等12篇纪念文章。《诗刊》1932年第4期刊登《罗米欧与朱丽叶》,还有徐志摩的诗《难忘(断篇二)》、朱湘的诗《悼徐志摩》、孙大雨的诗《招魂》、邵洵美的诗《天上掉下一颗星》等,都是追念徐志摩的。徐志摩遗稿《罗米欧与朱丽叶》被一再刊印,那些深情动人的悼念诗文映衬着《罗米欧与朱丽叶》,让这部青春的悲剧益发和诗人浪漫的才情与年轻的生命融合在一起,成为徐志摩翻译作品的代表。
《新月》刊登徐志摩遗稿之前,还刊登过梁实秋译《莎士比亚时代之英国与伦敦》《莎士比亚传略》《莎士比亚的观众》、邢鹏举《莎氏比亚恋爱的面面观》、余上沅《翻译莎士比亚》等文。显然,莎士比亚契合了《新月》的喜好。作为新月派的灵魂人物,徐志摩对莎士比亚同样热爱和推崇。他说:“历史戏在英国文学里自从莎士比亚以来,几于成为绝调。”[44]徐志摩在《看了〈黑将军〉以后》一文中强调:莎士比亚的戏剧“是文学里最颠扑不破的杰作,同时也是戏台上最颠扑不破的杰作”[45]。在《近代英文文学》这篇长文里他还特别例举了《哈孟雷特》并说:“研究西洋文学非研究莎士比亚不可”,“莎翁的戏剧,到处都可发见‘诗的美’。不仅美在表面,(如雕刻绘画等)而内在的情绪尤能引起人们无限的同情”[46]。这样的评论用于《罗米欧与朱丽叶》,同样再合适不过。徐志摩译《罗米欧与朱丽叶》,不仅是积极履行“计划”,也是他会心于莎剧的成绩。
一. 作为“先驱”的田汉译本
二. 艰难岁月里的曹未风译本
三. 徐志摩的遗稿
-
《罗密欧与朱丽叶》经由田汉、徐志摩、曹未风、曹禺、朱生豪的中文翻译,到梁实秋译本就有了较多注释。梁实秋对《罗密欧与朱丽叶》颇有研究,梁译本也更为专业。2014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傅光明新译中英对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201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傅光明“新译莎士比亚全集”之《罗密欧与朱丽叶》。傅光明译本较之前的梁实秋、孙大雨、方平及之后的辜正坤译本,优点更为突出。傅光明是继曹未风、朱生豪、梁实秋之后又一位坚持以一己之力翻译莎翁全集的译者。他的“新译”距梁译已半个世纪。
-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傅光明翻译出版的第一部莎剧。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第二辑由世界书局1947年出版,《罗密欧与朱丽叶》列为第二辑第一种。梁实秋译《罗密欧与朱丽叶》作为“莎士比亚全集之二十八”由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67年出版。孙大雨译《萝密欧与琚丽晔》,1998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此前孙大雨已翻译了6部莎剧。与这些现代译者的翻译相比,作为出版的第一部傅译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显然在傅光明“新译”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是傅译“原味儿”实践的开始,保持莎剧原著风貌与行文艺术,尽可能贴合莎剧的本来面目,是傅译莎剧的主要特点。
傅光明考证了莎剧版本源流,比较了“四开本”和“对开本”的优劣,他的翻译是在精当的版本择取基础上进行的。除了参考《阿登本莎士比亚全集(修订版)》(The Arden Shakespeare Complete Works, Revised Edition)等书外,傅译本主要以“‘牛津版’莎士比亚(The Oxford Shakespeare, edited by W.J.Craig. 1914)为底本,更以最新出版的三部《莎士比亚全集》为参照:一是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the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推出的、由世界著名莎学家Jonathan Bate与Eric Rasmussen合编的《莎士比亚全集》(William Shakespeare: Complete works),简称‘皇家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二是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新剑桥版莎士比亚全集》(The New Cambridge Shakespeare),简称‘新剑桥版’;三是美国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2013年1月最新推出的、由全美莎士比亚学会前任会长David Bevington编注的第七版《莎士比亚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简称‘贝七版’。如此,是为在注释上互为参照”[48]541-542。选用最新《莎士比亚全集》,参考世界莎学研究成果,比照多个英文本异同得失,对原本的审慎择取和用心校勘,使傅译超越了其他莎士比亚中译。傅译本的丰富注释也带有研磨推敲品质,比没有注释的译本更呈现出专业特征。他的“新译”因此更为精准,为普通中文读者接受理解莎士比亚提供了更多帮助。
傅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并没有无视前人翻译成绩,傅光明在翻译过程中经常参照对比的已有译本主要有朱生豪、梁实秋、孙大雨等人的翻译。第五幕第三场墓穴中的朱丽叶醒来,发现罗密欧已死。朱丽叶说道:“我要吻你的嘴唇,也许上面还沾着些毒液,相吻而死,我依旧属于你。”傅光明注:“原文为To make me die with a restorative。朱生豪译为‘可以让我当作复原剂服下而死去’。梁实秋译为‘让我于兴奋中中毒而亡。’Restorative虽有‘恢复药’‘滋补剂’‘提神药’‘兴奋剂’之意,但朱丽叶此处更要表达的‘复原’意思是:毒药将把她归还给罗密欧。”[17]199显然,Restorative是一个关键词,对它的理解决定了中译表达。傅光明的翻译比朱、梁更合理,且更富有莎剧的诗意。这类对以往译文的突破和提升,在傅光明的译本中比比皆是。就《罗密欧与朱丽叶》而言,在傅译本之前,已有诸多名家译本,傅译本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做出了修正和提升,是其重要价值之所在。
-
修正和提升的标准是什么?首先当然是译出语,即莎翁原著。这涉及莎剧复杂的版本问题,此外还有译出语所在的文化系统,包括莎士比亚的知识教养、剧本演出、16及17世纪英国的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世俗观念等。这些渗透在莎剧的字里行间,却很难通过单纯的文字翻译表现出来。如果译者不能把握译出语的文化系统,尽管在文字上做到“直译”,其翻译必定与原著产生隔膜。还是来看《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场傅光明的译文。罗密欧道:“受过伤的人从不讥笑别人身上的疮疤。(朱丽叶自上面窗口出现。)轻声些!从那边窗户透出来的是什么光?那是东方,朱丽叶就是东方的太阳!升起来吧,美丽的太阳,把那嫉妒的月亮杀死;狄安娜竟会为了你,她的侍女,比自己更美丽,已经忧伤得面色惨白了。她是如此善妒,不要做她的侍女;她给你穿的这身处女的衣裳,颜色绿得如此病态,只有蠢人才肯穿;脱掉吧!那是我的姑娘,啊,是我的爱!要是她知道她是我的爱,该多好啊!她想开口,却什么也没说;有什么关系呢?她的眼睛在说话,我要回答她。我太莽撞了,她又不是在对我说话。天空中两颗最明亮的星星,因为有事要离开绕行的轨道,回来之前,恳请她用双眼替它们闪耀。假如她的双眼就是那两个星座,那两颗星星就镶嵌在她脸上,又有何不可呢?如同朝阳会使灯光失色,她脸颊上的光辉已使耀眼的群星含羞;/她的眼睛把一片天空照得如此明亮,/安睡的鸟儿以为黑夜已过开始歌唱;/看哪,她倾斜着身子用手托着面颊!/啊,我只愿化作她的一只手套,/那样我便可以抚摸她的面颊!”“她说话了!啊,光明的天使,接着往下说;夜空里,你在我的头顶闪耀,就像世间的凡夫俗子看见一位舞动双翅的天使,只能把身子退后,出神地睁大眼睛,仰视着天使架着飘动的云朵从空中驶过。”[17]60-61
傅光明的译文是散体和诗体的结合。“她的眼睛把一片天空照得如此明亮”之后五句用了押韵的诗体。英文中这五句的结尾词是bright、night、hand、hand、cheek,可见,傅光明尽可能贴合了原文的韵律。相比于之前朱生豪译本基本采用散文体、孙大雨译本基本采用诗体,傅光明用散文体翻译莎剧素体诗的部分,用诗体翻译韵诗的部分,和梁实秋的译法相似。这一翻译方法可以解决中英文对译存在的文体困难,使莎剧的素体诗和韵诗在中文里得到明显区分。
这段译文傅光明用了四个注释,在注释较多的梁实秋译本中,这段文字没用注释。傅译本的四个注释,第一个说明罗密欧提到“疮疤”的意思。“受过伤的人从不讥笑别人身上的疮疤”,一句话就摆脱了罗密欧之前的恋爱挫折,十分干脆,之后他与朱丽叶的定情也同样干脆。傅译通过注释文本给第二幕第二场开篇这句话一个确定解释,不会再让读者产生困惑。第二个注释解释Diana是谁,可能由于所依据原本的原因,Diana在之前的译本中没有被译出,之后辜正坤的译本中也没有出现。方平的译本用了一个注释,但译文中没有音译出Diana,只译成“月亮女神”。傅译本把“狄安娜”嵌入译文中,一是遵从所据原本,二是能显示出莎剧文本的互文关联,显示出罗马神话是莎士比亚创作的重要背景。傅光明在考辨《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来源时,指出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对莎士比亚产生了巨大影响,“狄安娜”在译文中的出现,是这类影响的一个显在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莎剧文本的丰富性。
第三个注释是对两颗星“有事要离开绕行的轨道”的说明。傅光明指出,这是古希腊“地心说”的解释,星星要离开绕行地球的轨道,这是莎翁写剧的认知背景。关于“星星”和“双眼”之间关系的文句,是这段翻译的难点。之前如田汉、曹未风等人的翻译,把这部分处理得比较模糊。傅译本把意思处理得顺畅清楚,也呈现了莎士比亚时代的文化常识。第四个注释引用《圣经》。《罗密欧与朱丽叶》对《圣经》的多处化用,均由傅译本以注释的方式一一说明。傅光明说:“《圣经》的确是解读、诠释莎士比亚的一把钥匙,也是开启他心灵世界的一扇精致、灵动的小窗。”[47]28莎士比亚对《圣经》的熟稔,可以代表那个时代西方文化深入骨髓的特质。《罗密欧与朱丽叶》对《圣经》的化用既不露痕迹又处处可见。在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长篇解读中,傅光明说:在莎士比亚“所有剧作中《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唯一一部以浪漫的抒情笔调抒写至死不渝的爱情,并让它去融化怨恨、救赎心灵”[35]243。“说到救赎,自然离不开《圣经》”[35]243,《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叙事结构“更是一种从原罪到救赎的《圣经》式的O形结构,即每一次都从人的爱欲原罪开始,最后无一不以基督牺牲意味的救赎结束,简言之,就是善与恶的冲突,生与死的交替;恶达到极致便向善转化,死亡之后便是新生。《哈姆雷特》是这样,《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这样,《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也是这样,莎士比亚的剧作都是这样。整个人类历史的演变何尝不是如此!因此,读莎士比亚,就是在读我们自己”[35]247。
-
傅译本融学者之心与译者之才为一体,从文句的贴合、文体的斟酌,到文化背景的呈现、文本意涵的揭示,充分显示了“新译”的价值。译本、注释、剧情提要、长篇论文、研究专书等,都被纳入“新译”的整体构架之中,回答、解决了莎剧中译的诸多问题。可以说,傅译本充分把握了译出语系统,做到了“原味儿”的翻译。不过,如果把傅译所呈现出的莎剧“原味儿”仅仅理解为是对原著的忠诚或信达雅的统一,似乎还不完全准确。傅光明对“原味儿”有一个解释:“简单来说,无论阅读,还是研究莎翁,要想领略‘原味儿莎’,便应努力以今天的现代语言呈现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语境。倘若总让莎翁笔下的人物不由自主地随口说出一连串的自带中文语境的成语,无疑不够‘原味儿’吧?”[42]16要达到“原味儿”,应“呈现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语境”,但同时又不得不用“今天的现代语言”,也就是用现代汉语来翻译。“一连串的自带中文语境的成语”通常被认为是朱生豪译本的不足之处,应当尽量避免,到底如何用“中文”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涉及翻译的另一个方面,即对译入语系统的把握。译出语和译入语可以寻求对应却不能够重合,何况各自处于不同的文化系统,译文要达到和原文完全对等,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傅光明对此有明确认识。他说:“一代又一代的莎翁译者开始将不同的中文译本呈现给读者。其实,每一个中国的莎翁译者都是替他说中文的人。”[42]6“每一位译者替莎士比亚说的中文,都是各自性情、文调的不同体现。因此,莎翁戏剧自然呈现出不同的文风。”[42]10译者不同,莎士比亚说的中文也会不同。这是傅光明坚持以一己之力翻译莎翁全集的用意,多人合译很难成就“一个”莎翁。这也恰好说明译本不可能与原本达到完全一致,否则就会有一个绝对完美的中译本。何况,莎翁“原著”本身就存在重大的版本问题。究竟什么样的译本是好的?焦尹孚评田汉的翻译可作为参考:“大凡迻译一部文学名著最要紧的是要使得它经过了翻译之后,仍旧是一部好的文学——至少也要不失其为文学书,本来翻译文学,没有不失去原著之美的。”[34]翻译文学应该“仍旧是一部好的文学”,这是以译入语系统为衡量标准,而非单纯以“原著”为标准。由此,译本就获得了独立性与自身的存在价值。
作为翻译家,傅光明认为:“翻译其实就是一个‘化’的过程。恩师萧乾先生在世时,曾多次告诉我,翻译有两点最重要,一是理解,二是表达,若细划分一下,理解占四成,表达占六成。”[42]11译文“表达”的重要性是译文独立价值的所在。傅光明用“化”来形容从原著到译本的过程。这一表述还可见于钱锺书谈林纾的翻译。钱锺书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48]钱锺书深谙翻译之妙,他不认可译本对原著的亦步亦趋,因为会“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他只说“保存”“风味”,这与傅光明说的“原味儿”可以相互映照。“原味儿”是把莎剧所在的译出语系统“化”成中文的译入语系统,就像莎士比亚在说中文一样,《罗密欧与朱丽叶》既是莎士比亚的,其中译本本身也能成为经典。
一. 版本问题的解决
二. 译出语系统的复杂性
三. 译入语系统和“原味儿”的获得
-
译本或译作,是一个自足的存在。田汉翻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先驱”之功不可没,曹未风、曹禺、朱生豪、梁实秋、孙大雨等译者则在不同的时代成就了不同的莎翁。如果徐志摩用他的诗歌译出全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必然也会跻身于莎剧重要译者的行列。从田译本到傅译本,每部《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有其存在价值与自身特色。译本就是对原著生命的延续,或者用本雅明的观点来说,译者的工作是打破语言的限制对作品的再创造[49]。
就通行的朱生豪译本而言,再创造的痕迹十分明显。朱生豪1944年为《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写的《自序》说得很清楚:“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50]457这一译书宗旨充分显示出一位正直翻译家的责任感,是朱生豪译本能够通行的重要原因。不过,“不惜全部更易”的做法难免造成了和“原著”的不同,而“保持原作之神韵”中的“原作”仅指的是“牛津版”。“越年战事发生,历年来辛苦搜集之各种莎集版本,及诸家注释考证批评之书,不下一二百册,悉数毁于炮火,仓卒中惟携出牛津版全集一册,及译稿数本而已。”[50]456-457灾难年代让翻译和研究变得异常困难,朱生豪的翻译已经做到了尽可能优秀,但现今看来,是有缺陷的。焦尹孚在评论田汉译本时,已经强调了版本的问题。不仅是田汉、朱生豪如此,曹未风、曹禺、孙大雨乃至梁实秋所据原著版本都有局限。即使是后来的辜正坤译本,也只是译自“皇家版”。这些著名的牛津版、剑桥版、皇家版本身都可以说是对原著的再造,何况局限于某一版本的翻译,更无法真正还原莎翁原著。
与其纠缠于还原的不可能,不如再行创造,用生成经典的方法来再造原著。《罗密欧与朱丽叶》在现代中国的行旅,无论是故事改写还是剧本翻译,都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使之“显现出更为独特的中国特色的面貌”[51]。从林纾的《铸情》开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逐渐为中国读者熟悉。田汉第一个译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戏剧全本,后来译者的重译,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和观点弥合之前译本的不足,以使莎剧能在中国语境中被认可为经典。布鲁姆说:“宏大在莎士比亚作品中随处可见”[53]51,“莎士比亚为我们呈现了许多无法化解的悖论”[52]47。这是莎士比亚被不断翻译和研究的重要原因。莎士比亚被引入现代中文的话语系统,同时也被现代中文的话语系统所“化解”和塑造。直到21世纪,傅光明“新译”莎士比亚全集,打破了“原著”版本的局限,以“原味儿”的面貌呈现莎剧应有的姿态。傅译本已然独立于“原著”,自成经典,译本话语让莎翁在21世纪的中国再度复活重生。
莎士比亚的不朽,是由不同形式的流播、诠释、翻译汇聚而成的伟大力量。这一经典生成的过程需要艰辛的努力与历史的契机。“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可以很短暂,也可以很长久,它或许刊登在报纸的某个角落在一天之内就被遗忘,亦或许披着世人的重重目光从流行走向经典。”[53]在走向经典的过程中,原著的面貌会历经时空流徙,因接受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伟大的作品总会提供出不断生成的可能。这正是艾柯(Umberto Eco)所说的“开放的作品”:“各个时期的所有艺术是如何要作为这样一种挑衅行动而出现的:有意要成为不完整的经历,突然中断的经历,以便通过落空的期望形成我们现在的走向完整的自然倾向。”[54]经典的生成正是在再造原著的过程中让作品“走向完整”,而“走向完整的自然倾向”或许永远不会终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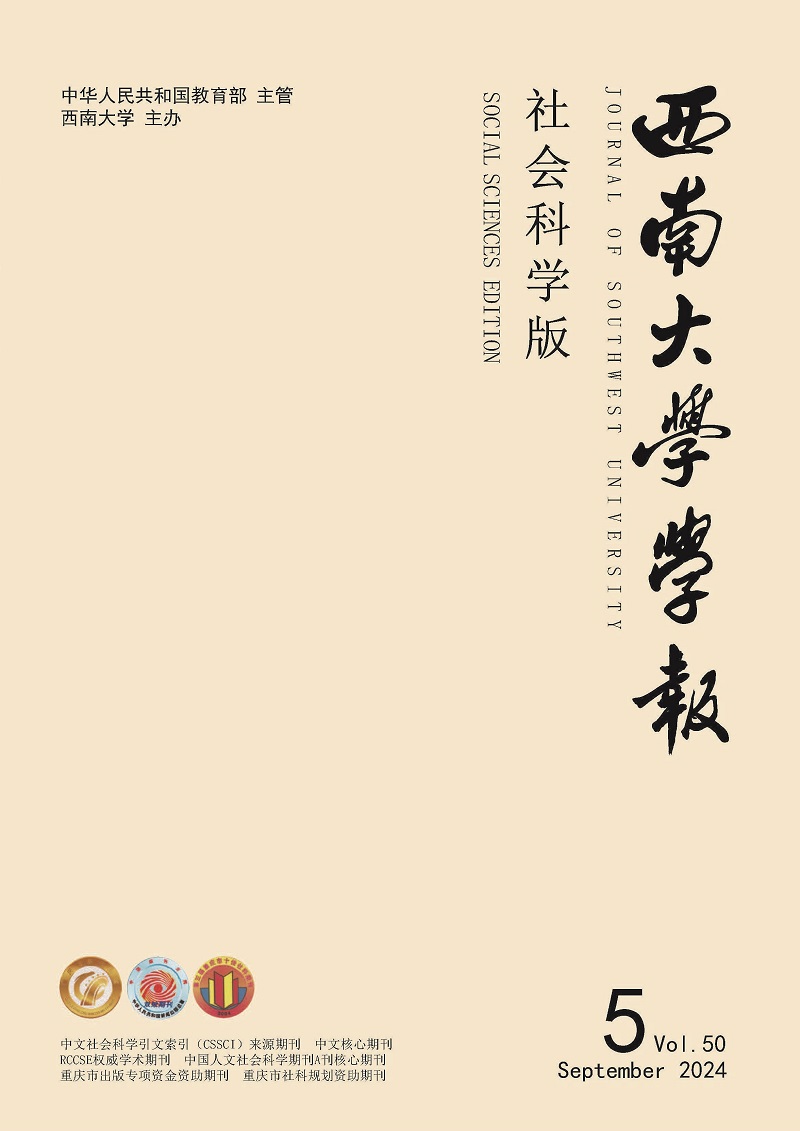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