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doi: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5e13eb92a7aad24f568616b58f811c3e
COPELAND W E, WOLKE D, ANGOLD A, et al. Adult psychiatric outcomes of bullying and being bullied by peers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J]. JAMA Psychiatry, 2013(4):419-426.
|
|
[2]
|
HAMBURGER M E, BASILE K C, VIVOLO A M. Measuring bullying victimization, perpetration, and bystander experiences:A compendium of assessment tools[M]. ATLANTA, G A: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2011.
|
|
[3]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9b4bf0ff9aa31801c853083c594f685c&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HEMPHILL S A, KOTEVSKI A, HERRENKOHL T I, et al. Longitudinal consequences of adolescent bullying perpetration and victimisation:A study of students in Victoria, Australia[J]. Criminal behaviour and mental health, 2011(2):107-116.
|
|
[4]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604f5acbc0593243c82139c36b897790&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TAKIZAWA R, MAUGHAN B, ARSENEAULT L. Adult health outcomes of childhood bullying victimization:Evidence from a five-decade longitudinal British birth cohort[J].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14(7):777-784.
|
|
[5]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b1f56db55de4671fe7809c9f261bcc7a&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VESSEY J, STROUT T D, DIFAZIO R L, et al. Measuring the youth bullying experience: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available instruments[J].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2014(12):819-843.
|
|
[6]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d4b1d8e41736d23bf7c6b25fd7eebcfe&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VIVOLO-KANTOR A M, MARTELL B N, HOLLAND K M,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content analysis of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measurement strategies[J].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14(4):423-434.
|
|
[7]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fb0893ec0d2cc7274f0f6026d5f33407&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RAINE A, DODGE K, LOEBER R, et al. The reactive-proactiv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Differential correlates of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in adolescent boys[J]. Aggressive behavior, 2006(2):159-171.
|
|
[8]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e95d95b7b3d881fe737cf2d3e970cf21&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BETTSL R, JAMES EH, STEER O L.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peer victimization scale-revised (MPVS-R)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peer bullying scale (MPVS-RB)[J].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2015(2):93-109.
|
|
[9]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0e06350af230c97401457acf213bfca6&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CHENG Y, CHEN L, LIU K, et al.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school bullying scales:A rasch measurement approach[J].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2011(1):200-216.
|
|
[10]
|
doi: http://d.old.wanfangdata.com.cn/NSTLQK/NSTL_QKJJ0229958441/
OLWEUS D. School bullying:Development and some important challenges[J]. Annual review clinic psychology, 2013(9):751-780.
|
|
[11]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d1e55e2e9c29408bc7f649f6e6d93bda&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CEREZO F, ATO M. Bullying in Spanish and English pupils:A sociometric perspective using the Bull-S questionnaire[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5(4):353-367.
|
|
[12]
|
doi: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89ae14ef2b9e427ac8574dd9627d0cee
AZAGBA S. School bullying and susceptibility to smoking among never-tried cigarette smoking students[J]. Preventive medicine, 2016(85):69-73.
|
|
[13]
|
OLWEUS D. The revised Olweus bully victim questionnaire[M]. Bergen, Norway:Research Center for Health Promotion, University of Bergen, 1996.
|
|
[14]
|
doi: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10.1177/016235321103400405
PETERS M P, BAIN S K.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rates among gifted and high-achieving students[J]. Journal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gifted, 2011(4):624-643.
|
|
[15]
|
doi: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10.1177/0886260511431436
CUADRADO-GORDILLO I. Repetition, power imbalance, and intentionality[J].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012(10):1889-1910.
|
|
[16]
|
doi: http://d.old.wanfangdata.com.cn/NSTLQK/10.1007-BF03173535/
GUERIN S, HENNESSY E. Pupils'definitions of bullying[J].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2002(3):249-261.
|
|
[17]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730c23f6d1a6121405d637b56b2e177d&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DOOLEY J J, ALSKI J P, CROSS D. Cyberbullying versus face-to-face bullying:A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review[J].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9(4):182-188.
|
|
[18]
|
doi: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10.1300/J135v02n02_06
GOTTHEIL N F, DUBOW E F. The interrelationships of behavioral indices of bully and victim behavior[J]. Journal of emotional abuse, 2001(2):75-93.
|
|
[19]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6c535730f465889268fdf6d34e77890b&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AUSTIN S, JOSEPH S. Assessment of bully/victim problems in 8 to 11 year-olds[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96(4):447-456.
|
|
[20]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9c51d944ef7c0e15172a44704ce6c919&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KONISHI C, HYMEL S. Bullying and stress in early adolescence:The role of coping and social support[J].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2009(3):333-356.
|
|
[21]
|
doi: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10.1177/0143034312454360
GOODMAN J, MEDARIS J, VERITY K, et al. A synthesis of international school-based bullying interventions[J].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apprenticeship, 2013(2):1-18.
|
|
[22]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84e19e15683b2cfbc96fb277af40bbd2&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FITZPATRICK S, BUSSEY K.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bullying involvement scales[J]. Aggressive behavior, 2011(2):177-192.
|
|
[23]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a2bf72409ce7873620322dc9f1a87207&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ANTONIADOU N, KOKKINOS C M, MARKOS A. Development, construct validation and measurement invariance of the greek cyber-bullying/victimization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 (CBVEQ-G)[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6(65):380-390.
|
|
[24]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d73525754aa18a6dd25d14dc9b1f6bb7&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ESPELAGE D L, HOLT M K.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Peer influences and psychosocial correlates[J]. Journal of emotional abuse, 2001(2):123-142.
|
|
[25]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2a4ec8a945c3e5982be0903f40b9bf8f&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HALL W J. Initi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bullyharm:The bullying, harassment, and aggression receipt measure[J]. Psychology school, 2016(9):984-1000.
|
|
[26]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359d4482ef79ad7accdfca384de75797&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KOWALSKI R M, GIUMETTI G W, SCHROEDER A N, et al. Bullying in the digital age:A critical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yberbullying research among youth[J]. Psychology bulletin, 2014(4):1073-1137.
|
|
[27]
|
OLWEUS D. Bullying at school: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M]. Oxford, UK:Blackwell, 1993.
|
|
[28]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8987be8c6bd584158a210bc795b024b6&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SALMIVALLI C, LAGERSPETZ K, BJ RKQVIST K, et al. Bullying as a group process:Participant role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social status within the group[J]. Aggressive behavior, 1996(1):1-15.
|
|
[29]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f8afc45720ff1b0c87c7b9e3f5ace4a3&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FELIX E D, SHARKEY J D, GREEN J G, et al. Getting precise and pragmatic about the assessment of bullying: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lifornia bullying victimization scale[J]. Aggressive behavior, 2011(3):234-247.
|
|
[30]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3b3da348831581d446012e0eb3bc2f03&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HARTUNG C M, LITTLE C S, ALLEN E K, et al. A psychometric comparison of two self-report measures of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Differences by sex and grade[J]. School mental health, 2011(1):44-57.
|
|
[31]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15d9e50afa72dd23847930fc8d6bd751&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HYMEL S, SWEARER S M. Four decades of research on school bullying:an introduction[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15(4):293-299.
|
|
[32]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2be4cf36887ac14c0f99dfdb564e74aa&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BOUMAN T, van der MEULEN M, GOOSSENS F A, et al. Peer and self-reports of victimization and bullying:Their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with internalizing problems and social adjustment[J]. Journal school psychology, 2012(6):759-774.
|
|
[33]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a48d6318fd3a59cb1d7a0947c4be1a1f&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VESSEY J A, DIFAZIO R L, STROUT T D. Increasing meaning in measurement:A rasch analysis of the child-adolescent teasing scale[J]. Nurse research, 2012(3):159-170.
|
|
[34]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94dcb46d5622d931748679b71adacf4d&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CHO J I, HENDRICKSON J, MOCK D R. Bullying status and behavior patterns of preadolescents and adolescents with behavioral disorders[J]. Education & treatment of children, 2009(4):655-671.
|
|
[35]
|
CORNELL D.Research summary for the Authoritative School Climate Survey[M].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Curry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2017.
|
|
[36]
|
LIPSON J. Hostile hallways:Bullying, teasing, and sexual harassment in school[M]. Washington, DC: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Educational Foundation, 2001.
|
|
[37]
|
REYNOLDS W. Reynolds bully victimization scales[M]. San Antonio, T X:The Psychological Corporation, Harcourt Assessment, 2003.
|
|
[38]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9013038531993ee03616ce30d9677cae&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SHAW T, DOOLEY J J, CROSS D, et al. The forms of bullying scale (FBS):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estimates for a measure of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perpetration in adolescence[J].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013(4):1045-1057.
|
|
[39]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21725955d20e932769c056a2beedbd86&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SWEARER S M, CARY P.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 bullying in middle school youth:A developmental examination across the bully/victimcontinuum[J]. Journal of applied school psychology, 2003(19):63-79.
|
|
[40]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d395814b0c1829b20939bb08fdc51c7e&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WILLIAMS K R, GUERRA N. Prevalence and predictors of internet bullying[J].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2007(41):s14-s21.
|
|
[41]
|
doi: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ee728115711ee6ebd1783ef9ce4f961d
RUSSELL S T, SINCLAIR K, POTEAT V P, et al. Adolescent health and harassment based on discriminatory bias[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2(3):493-495.
|
|
[42]
|
doi: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67864f45207cb0d7b9e4c4e65cdeaf7e
KERT A S, CODDING R S, TRYON G S, et al. Impact of the word "bully" on the reported rate of bullying behavior[J].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2010(2):193-204.
|
|
[43]
|
doi: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34f7dccb4b596a3370adb6639d554016
CORNELL D, KLEIN J, KONOLD T, et al. Effects of validity screening items on adolescent survey data[J].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012(1):21-35.
|
|
[44]
|
潘逸沁, 骆方.社会称许性反应的测量与控制[J].心理科学进展, 2017(10):1664-1674.
doi: http://d.ol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lxdt201710004
|
|
[45]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bf07b0cde795d02d66a7ced93a5316cd&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NAVARRO R, LARRANAGA E, YUBERO S. Gender identity, gender-typed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chool bullying:Victims, bullies and bully-victims[J].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2015(1):1-20.
|
|
[46]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39cfa995afa7bacd11df29c86ab666af&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COLE J, CORNELL D G, SHERAS P. Identification of school bullies by survey methods[J]. Professional school counseling, 2006(4):305-313.
|
|
[47]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a8a1041d972ec95e92ddfb31cf7aaca4&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SOLBERG M E, OLWEUS D. Prevalence estimation of school bullying with the Olweus bully/victim questionnaire[J]. Aggressive behavior, 2003(29):239-268.
|
|
[48]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bb6bf8cd64b7c9a3352f0d2c5c0910d5&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MORALES J F, YUBERO S, LARRANAGA E. Gender and bullying:Application of a three-factor model of gender stereotyping[J]. Sex roles, 2016(3/4):169-180.
|
|
[49]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0e1f4dbf6a6b2c37c4799862ad77f8ce&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KOH J, WONG J S.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nd the sexiest:evolutionary origins of adolescent bullying[J].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017(17):2668-2690.
|
|
[50]
|
CROTHERS L M, KOLBERT J B. Tackling a problematic behavior management issue[J]. Intervention in school & clinic, 2008(3):132-139.
|
|
[51]
|
doi: http://d.old.wanfangdata.com.cn/NSTLQK/NSTL_QKJJ028225635/
ESLEA M, MENESINI E, MORITA Y, et al. Friendship and loneliness among bullies and victims:Data from seven countries[J]. Aggressive behavior, 2003(1):71-83.
|
|
[52]
|
do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4d4337830f91d0e894e1c0d6efa21ab4&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SMITH P K, COWIE H, OLAFSSON R F, et al. Definitions of bullying:A comparison of terms used, and ag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a fourteen-country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 Child development, 2002(4):1119-1133.
|
|
[53]
|
doi: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10.1177/0829573509331614
KONISHI C, HYMEL S, ZUMBO B D, et al. Investigating the comparability of a self-report measure of childhood bullying across countries[J]. Canadian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2002(1):82-93.
|
|
[54]
|
苏春景, 徐淑慧, 杨虎民.家庭教育视角下中小学校园欺凌成因及对策分析[J].中国教育学刊, 2016(11):18-23.
doi: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zgjyxk201611005
|
|
[55]
|
doi: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10.1080/01443410.2011.633495
CHEN L M, LIU K S, CHENG Y Y. Validation of the perceived school bullying severity scale[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2(2):169-182.
|
|
[56]
|
张文新, 武建芬, Jones K. Olweus儿童欺负问卷中文版的修订[J].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9(2):8-12.
doi: http://d.old.wanfangdata.com.cn/Thesis/Y35272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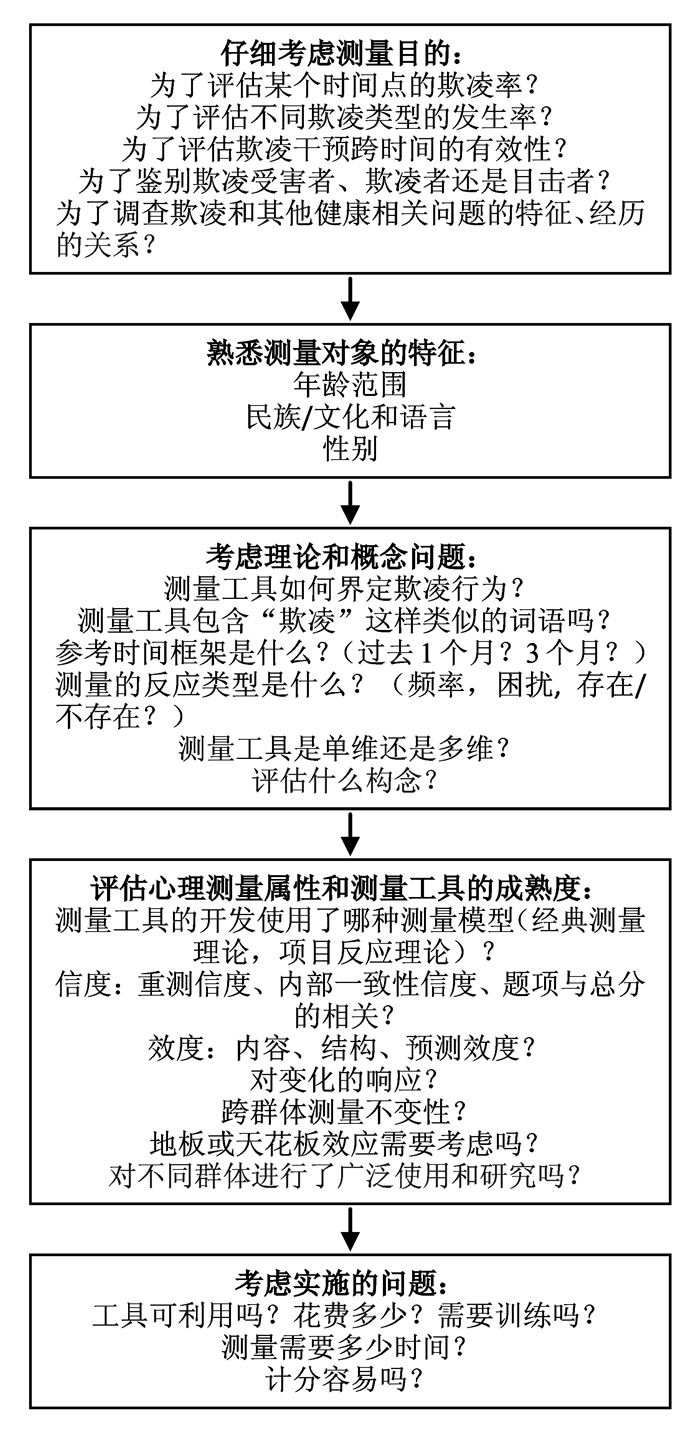
 下载: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