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疫情不仅让人类面临巨大的健康威胁,而且引发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国际秩序的深层危机,使人类经多年形成的发展模式、交流方式、全球化体系和文化间的互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逆全球化、新冷战、意识形态对立等话语不时出现。各种话语冲突引发的分裂与对抗、真相与谣言、协作与对抗、科学依据与政治栽赃、勇担责任与极尽推脱等,构成了新冠大流行中话语冲突的典型图景。在这场危机中,话语使用和话语权掌控彰显更加突出的重要性。一方面,部分政治势力恣意操控话语,掩盖事实,以谋求其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利益;另一方面,科学界、学术界和多数有识之士呼吁和倡导尊重事实,以团结协作对抗疫情带来的全球危机。新冠疫情下的话语冲突更充分地突显出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话语构建面临着困难和挑战。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以及国际话语冲突不断加剧,加快中国话语体系构建,已成为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使命和历史担当,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有关如何开展中国话语构建的战略性论述[1]。但是,中国话语在世界话语体系中缺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当前的对外话语体系构建有何历史基础?是否有可供借鉴和参考的历史经验?在西方话语处于垄断地位、全球话语权争夺日益激烈的事实前提下,中国话语如何真正有效地进入国际话语圈并逐渐获得认同?近代以来,在由旧转新的现代化过程中,以林纾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将西方现代话语引入中国,成功地构建了深入各个领域的中国现代话语。以史为鉴,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有价值的思考。当前的“走出去”话语构建可从林纾的话语构建模式中萃取精华。因此,本文拟在分析当前话语构建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基础上,总结林纾话语构建的成功要素和核心特征,以林纾“引进来”话语构建为参考和借鉴,探索当前“走出去”话语构建的有效路径。
HTML
-
21世纪以来,弘扬和传播中国文化、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成为学术界和文化界的重要使命,有关如何开展对外话语构建的相关论述愈加丰富。在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三种话语构建思维。一是自我怜悯思维,认为中国缺乏真正的话语体系,近代以前的中国话语体系“具有一定的虚幻性”,并非真正面对世界的话语体系,而自近代以来的话语体系则因遭受“全盘西化”倾向的毁灭性打击而不复存在[2];二是激进与自大思维,认为西方话语开始“跌落神坛”,出现了“后西方话语时代”[3],世界话语体系出现权力转移,东方乃至中国话语开始登场;三是挑战对抗思维,过于突出话语体系的差异性和话语立场的对立性,以西方霸权理论论述我们的话语构建,认定话语权的构建意味着以一种话语替代另外一种话语。这三种思维既割裂了中国话语的历史联系,对当前世界话语体系判断失准且盲目乐观,又并非在当前西方话语处于强势地位的语境下开展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明智之举。从根本上说,中国话语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失语”与西方话语的垄断强势,是目前的客观现实。中国的对外话语构建需要在这一事实前提之下,寻找一条切实可行的有效构建之路。
-
“话语”指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的语言形式。语言学家将话语定义为“大于句子的交际单位”“使用中的语言”“社会文化语境下的互动产物”,是包含语言和非语言元素的社会实践总和[4]。话语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表达意义或传递信息的具有交流功能的语言形式和单位。
哈里斯首次提出话语分析概念[5]。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话语被认为受制于社会现实,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构成社会进程中的意义产生,反映识解世界的方式[6]。批评话语分析强调语言、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主张以话语为媒介研究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建构。在福柯看来,话语是由思想、态度、行为、信仰等构成的思想体系,其话语定义包含以下内容:话语浸透着意识形态,话语依赖社会机构(如大学、出版社、报纸、图书馆)进行传播,话语的产生受某些社会规则或传统的制约,话语是在某种历史条件下被某种制度所支撑组织起来的陈述群[7]。福柯通过话语阐释了权力与知识的关系,认为权力产生知识,知识体系开辟权力运作的场所,而权力和知识的产生和构建都需要靠话语实践来实现。从社会学视角看话语,得以跳出传统话语思维模式,认识到语言是话语运作的工具,意识形态是载体,权力关系是最终结果。
本文所论述的中国对外话语构建包含三项基本内涵。第一,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构建是一种跨语言的话语实践。中国话语构建不仅是对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全球话语体系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立场和视角的中国话语,以汉语的表达为基础,但需要通过国际化的语言表达来实现。第二,话语构建依赖有效的叙事,跨语言的话语构建更需要搭建融通中外读者心理和认知的叙事模式,才能实现话语的有效阅读和接受。第三,话语构建是一种权力的博弈。一方面,话语实践是权力运作的工具;另一方面,话语的构建过程或多或少涉及权力的冲突,最核心的冲突来自思想和价值观的冲突。如何避免因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抗造成的话语构建受阻,是探讨对外话语构建时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
从时空坐标来看,晚清以来的现代性话语构建和当前的中国对外话语构建是中国话语构建的两个重要历史节点。前者以“引进来”的方式对中国传统话语进行现代性改造,使西方话语体系经由长达百年的“西—中”文化传播进入中国话语体系。一方面,“引进来”的现代性话语构建开启并快速地实现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在各个领域接近或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另一方面,“引进来”逐渐成为中国话语方式的“惯习”,出现“言必称西方”“一切学西方”的对中国话语不够自信的倾向,导致西方话语的垄断性和中国话语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失语”状态。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有识之士不断呼吁重建中国话语体系,使中国对外话语构建最终成为一种国民共识和民族责任。
“引进来”与“走出去”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两个不同方向的话语构建。但是仔细考察,会发现中国话语的“引进来”与“走出去”之间具有复杂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引进来”的话语构建形成了“走出去”话语构建的历史根源和实践基础,“引进来”既实现了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成功构建,使中国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现代化,但同时客观上又导致了中西话语失衡和中国话语缺失。另一方面,“引进来”与“走出去”这两种话语构建实为一个问题的两面,具有本质上的同构性,是中国话语构建这个大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两个不同方向上的实现。或者可以说,这两种话语构建同根、同源、同质,是为中国话语成功构建这一终极目标服务的两项任务。“引进来”的话语构建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任务,只有当中国话语成功“走出去”,才算中国话语的完整构建。
苏静、韩云波分析了金庸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遭受冷遇的原因,提出了中西方文化的“历史异代”概念,即中西方在相同的物理时间演绎的是不同的逻辑时间,导致物理时间与文化逻辑时间的不匹配,从而形成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化理解的歧异[8]。受此观点启发,本文认为,可以推演出中国话语构建在时空上的异向同构性,即近代的现代性话语构建与当前对外话语构建是在两个不同物理时间开展的不同方向(引进来与走出去)而本质属性相同的话语构建。从核心内涵看,不管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是以中国实践为基础、以中国话语为核心体系的话语构建;从终极目标看,引进来和走出去都应当是为包含中国人在内的全人类服务、通过解决中国问题而实现解决人类共同问题、以“世界关切”为最终关切的话语构建。因此可以说,这两种话语构建就是在不同“物理时间”但在同一个“逻辑时间”上开展的异向同质话语构建。更为重要的是,“引进来”作为一种历史事实,已经成功实现了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全方位构建,其话语构建方式为“走出去”的对外话语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考和有益借鉴。
一. “话语”问题与中国对外话语构建的内涵
二. “引进来”与“走出去”:中国话语构建的异向同构
-
19世纪末20世纪初,林纾通过180余种西方小说的译介打开了国人视野,开拓了中国文学的世界眼光[9],被称为“一个新文化的哥伦布”[10]199。林纾以西方小说为载体,成功开启了中国小说的现代话语,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话语构建的有效探索和成功案例。从话语构建的基本要素看,林译小说体现出以下话语构建特征:以弹性古文表达西方现代文化概念的话语形式、将史传叙事与西方小说叙事相结合的叙事模式、对西方价值观的选择性译介与中国传统价值观融合的思想意识承载,总体上反映出了“融合”话语的特征。
-
林纾以古文翻译西方小说,在学术界、文学界和文化界褒贬不一。但从话语构建角度看,他的弹性古文表达形式,巧妙化解了中西话语冲突,实为一种成功的选择。钱基博大赞林纾的古文造诣,称“纾之文工为叙事抒情,杂以恢诡,婉媚动人;实前古所未有”[11]。胡适也赞赏林纾的古文译法:“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实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么大的成绩。”[12]林纾作为晚清桐城派古文大家,其古文运用甚至起到了提升原文效果的作用,郭沫若评价称,《迦茵小传》“在世界文学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但经林琴南那种简洁的古文译出来,真是增添了不少光彩”[13]。
也有人对林纾的古文译法提出批评,指责林纾以古文译西方小说是翻译之弊。梁启超说:“纾治桐城古文,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于新思想无与焉。”[14]刘半农以“记者”之名说:“‘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乃‘林先生最大的病根’,理由是‘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绝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15]
林纾所处的时代,知识分子皆以中国文学传统和文言为傲,斥小说为小道,谓之难登大雅之堂。在此语境下,林纾的古文译法既源于发挥其深厚古文造诣之优势心理,也是出于迎合当时士大夫口味而为引进西方小说铺路。寒光说:“林氏译小说的时候,恰当中国人贱视小说习性还未铲除的时期,一班士大夫们方且以帖括和时文为经世的文章,至于小说这一物,不过视为茶余酒后一种排遣的谈助品。加以那时咬文嚼字的风气很盛,白话体的旧小说虽尽有描写风俗人情的妙文,流利忠实的文笔,无奈他们总认为下级社会的流品,而贱视为士腔白话的下流读物。林氏以古文名家而倾动公卿的资格,运用他的史、汉妙笔来做翻译文章,所以才大受欢迎,所以才引起上中级社会读外洋小说的兴趣,并且因此而抬高小说的价值和小说家的身价。很显明的,倘使那时不是林氏而是别人用白话文来译《茶花女》等书,无论如何绝不会收到如此的好结果。”[10]36
实际上,为实现引介西方小说的目的,林纾采用的古文并非纯粹的文言,而是一种弹性的古文。钱锺书指出,古文是中国文学史术语,并非文言就算得古文,古文也并非完全与白话文对立。古文是一种语体形式,也是一种叙述和描写的技巧。就语体而言,古文的使用本有诸多清规戒律的限制,“古文中忌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排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16]309。为了迎合士大夫旨趣,也为了适应表达小说内容和西方事物的需要,林纾采用了一种更为自由的古文,一种“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16]311。林译小说的选词范围广阔,古文禁忌词(如“梁上君子”“五朵云”“土馒头”等)、白话口语词(如“小宝贝”“天杀之伯林伯”等)、流行的外来新词(如“脑筋”“脑球”“社会”“个人”“团体”“反动之力”“苦力”等)乃至音译词(如“马丹”“密司脱”“安琪儿”“俱乐部”“列底”等)等,在《冰雪因缘》《块肉余生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巴黎茶花女遗事》等译文中频频出现。林译小说句法上也不受古文规矩之严密限制,甚至还有非常突出的“欧化”成分,如《迦茵小传》第五章里有一句“先生密而华德至”,将“先生”置于姓氏之前,即为欧化的突出体现。再如《孝女耐儿传》中的一段:“胖妇家向主妇之母曰:‘密昔司几尼温,胡不出其神通,为女公子吐气?’此密昔司圭而迫者,即密斯几尼温也。‘以夫人高年,胡以不知女公子之楚况?问心何以自聊!’……语后,于是争举刀叉,攻取面包,牛油,海虾,生菜之属,猛如攻城,且食且言曰:‘吾气填胸臆,几于不能下咽。’”[17]除有“密昔司”“密斯”等音译词之外,“刀叉”“面包”“牛油”“海虾”“生菜”皆西洋名词,而“胖妇”“主妇”则是白话词汇。整个句式体现出古文与白话混杂的特点。钱锺书说,“为翻译起见,他得借助于文言小说以及笔记的传统文体和当时流行的报刊文体”,但又游离于古文旧体与时文新体之间,前期译本如《巴黎茶花女遗事》等明显呈现更多古奥字法和句法,而“以后的林译里似乎不再碰见这个方式”[16]314。
总之,林译小说话语的语言形式,包含史传笔法、古文词法和句法,又对传统古文进行改进,采用更为灵活、通俗、富于弹性的古文,引入西方新名词,接纳部分新表达,容受部分西语句式和词序。这样的话语形式,既在一定程度上忠实地传达了西洋小说的原文内容,为读者构建了新的知识,也探索出了一种与西方现代小说更为切近的文学语言。林译小说的弹性古文话语继承了史传优势,又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古文的清规戒律,打破了“古文之体忌小说”的偏见,为中国近代小说话语形式由旧向新转变起到了开拓作用,正如林薇所言:“中国文学从文言过渡到白话这个演变过程,其实在林译小说中已经开始体现出来。”[18]44
-
林译小说的叙事模式是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史传小说)叙事与西方现代叙事的结合。陈平原将中国小说叙事的转变总结为两种位移的合力:外来小说形式的移植和传统文学形式的承袭转换,这种叙事模式的转变首先可追溯到1898年梁启超、林纾等一代“新小说”家的正式登台表演[19]4。
林纾对史传叙事传统的借用是一种创造性借用。一方面,他以中国传统小说叙事为对照来类比西方小说,认为西方小说与史传小说叙事结构存在近似之处。《黑奴吁天录》例言称:“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法,有不同而同者。”[20]228于是,林纾在翻译中常以史传叙事笔法对西方小说进行改写。多部小说的标题不按原文字面直译,而是参照中国传统传奇志怪方式套用改写,冠以“传、录、记、纪、遗事”等字,如《撒克逊劫后英雄略》(Ivanhoe,现译《艾凡赫》)、《孝女耐儿传》(Old Curiosity Shop,现译《老古玩店》)、《滑稽外史》(Nicholas Nickleby,现译《尼古拉斯·尼克尔贝》)等。特别是Gullier's Travels,通行译名是《格列佛游记》,林纾套用宋代吕居仁的笑话集《轩渠录》将这一西洋幽默小说译为《海外轩渠录》。林译小说以中国传统小说话语为参照进行的套译法,由此可见一斑。
林译小说叙事的史传模式还体现在对原文叙事视角、描写方式的改写上。在《海外轩渠录》里,林译多次将原文的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改为史传“代言”笔法的全知叙事,“根据原著设定的说话人的历史背景、实时场景和心情等,适度想象主人公的说话和动作,使读者获得更为真实的阅读体验和心理感受,进而达到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21]。陈平原认为,“新小说家”借鉴史传,既体现为史传的实录精神,也体现为传记体的叙事技巧,“林纾以史汉笔记法解读狄更斯、哈葛德小说,悟出了不少穿插导引的技巧”[19]202。
林译小说叙事模式的另一个方面是西方小说的立体交叉叙事,这是林译小说叙事模式的主要方面,也是为中国近代小说话语模式带来影响的主要方面。参照陈平原提出的小说叙事转变模式,可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方面考察林译小说的叙事模式。
就叙事时间来说,在接触西洋小说前,中国小说基本上采用连贯叙事。19世纪末,政治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的翻译为中国小说带来了倒叙、预叙、插叙、补叙等多种叙事时间安排[19]36。林纾对西方小说立体交叉、时空交错的叙事模式推崇备至,除了在译文中保留原文叙事顺序之外,还常在译序跋和译文中对原文叙事方式进行说明。《块肉余生述》第五章“前篇序”对原文“预叙”手法的说明:“外国文法往往抽后来之事预言,故令观者突兀惊怪,此其用笔之不同者也。余所译书,微将前后移易,以便观者。若此节则原书所有,万不能易,故仍其文。”[22]83-84此类提示在林译小说中不少,又如《巴黎茶花女遗事》文中加括号注明“以下均亚猛语”[23]15,表明是插叙。
就叙事角度说,20世纪以前,中国小说尽管有一些限制叙事(即叙述者与小说中人物知道的东西一样多,人物不知道的,叙述者也不会叙说),但并未突破“叙述者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全知叙事。西洋小说常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限制叙事为主[19]68。林纾在《巴黎茶花女遗事》里做了协调处理,并未完全保留原文的第一人称叙事,也没有将其改为中国读者熟悉的全知叙事,更没有用传统小说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有诗为证”等套语,而是将第一人称“我”改为第三人称“小仲马”,随之又改为第一人称“余”。如小说开头部分,王振孙译本为:
我认为只有在深入地研究了人以后,才能创造人物,就像要讲一种语言就得先认真学习这种语言一样。
既然我还没有到能够创造的年龄,那就只好满足于平铺直叙了。[24]
而林纾的译文为:
小仲马曰:凡成一书,必详审本人性情,描画始肖,犹之欲成一国之书,必先习其国语也。今余所记书中之事,为时未久,特先以笔墨渲染,使人人均悉事系纪实。[23]1
就叙事结构来说,林译小说实现了从情节叙事到性格叙事、从平铺直叙到立体交叉及注重过程、突出细节描写叙事手法的转变[18]242。在叙事主题上,中国旧小说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为主,林译小说转向以平民叙事、家常叙事为主,“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开启了从情节小说向性格小说的转变。中国传统旧小说以英雄美人的传奇故事和离奇曲折的情节结构为胜,而以狄更斯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则着力于人物性格的开掘,以性格魅力构建小说的艺术效果。林纾译书时特别突出小说对下层社会的描绘和平民意识的主张,避免英雄主义的审美观,所译《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滑稽外史》等都刻意描绘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林纾的相关论述也体现了“文学即人学”的审美意识,动摇了以情节为框架的小说话语模式。林纾《孝女耐儿传》序中说:“天下文章,莫易于叙悲,其次则叙战,又次则宣述男女之情。等而上之,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从未有刻划市井卑污龌龊之事。……则迭更司者,盖以至清之灵府,叙至浊之社会,令我增无数阅历,生无穷感喟矣。”[25]
在布局上,林译小说引入西洋小说时空跳跃手法,打破中国旧式小说以时间先后为序的格局。在《块肉余生述·后篇识》中,林纾表达了对迭更司叙事技巧的赞赏,称:“此书不难在叙事,难在叙家常之事;不难在叙家常之事,难在俗中有雅、拙而能韵,令人挹之不尽。且前后关锁,起伏照应,涓滴不漏。言哀则读者哀,言喜则读者喜,至令译者啼笑间作,竟为著者做傀儡之丝矣。近年译书四十余种,此为第一,幸海内嗜痂诸君子留意焉。”[22]85
在叙事手法上,林纾重视细节描写,特别是人物内心描写和动作神态的细致刻画,不太注重场景描写。陈平原指出,林纾在《巴黎茶花女遗事》中“基本保留了人物的内心独白,可又删去了开篇几章的不少场面描写”,“读者对有趣的故事的期待,再加上翻译家自身文学修养和语言能力的限制,决定了早期小说译作重过程的叙述而轻场景的描写”[19]102。也正因为林纾对这种叙事技巧的高超把握,使他所译的狄更斯小说备受推崇。
-
身处清末民初,林纾深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濡染,接触西方小说后又受西方思想和文化价值观影响,他因此既有保守传统价值观的一面,也有主张西方价值观的一面。这样的“中西结合、以中化西”意识形态立场明显地体现于他的小说翻译话语之中。从思想承载来讲,林译小说以传递西方文化为主,毕竟忠于原文(或者说尽力忠于原文)、引介西方思想还是林纾翻译的首要目的,只不过这种引介是以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能接受的话语形式来实现的。林译小说数量庞大,题材广泛,蕴含的西方思想有多方面的体现,较典型且产生了较深刻影响的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国家观和民族观。林纾对于国家落后的原因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富强的经验有过深思,在多篇序跋里有所阐述。《爱国二童子传·达旨》总结说,英法两国虽经历战火却“卒归于失业、始客自振”,很是钦羡小说中法国的孟叔“与同志嘉纳醰思制器之方,力图制胜于外,培植子弟为工程师,立实业学堂无数”,而其他国家如比利时、波兰、印度等则“赖实业足以支柱也”,甚至“以犹太煨烬之余灰,恃其实业,尚可幸存”,因此中国急需“讲解实业,潜心图存”。林纾认为,中国的“官本位”思想、贱视工商农学诸业,是造成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爱国二童子传》小说中的恩忒、舒利亚兄弟“卒能于国力衰败之余,间关自达于祖国……沿路见法国人人皆实业,遂亦不务宦达,一力归农”[26],林纾很是推崇,认为发展实业、兴办教育是强国富民之路。
二是平等、自由、尊重人性的现代思想。大部分林译小说都蕴含了与中国封建思想全然不同的现代思想,如解放个性、人人平等、尊重女性、婚姻自由等。林纾通过翻译小说塑造了很多忠于爱情、追求自由幸福的艺术形象,《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皆为突出例子。许多读者通过林译小说,知道了原来恋爱和婚姻可以如此自由,像迦茵这样身世畸零的女子也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像茶花女这样的妓女也能如此纯洁可爱。《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给中国近代文学带来深刻影响,有人甚至说,中国革命就是由这两部小说造成的[27]。
三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宗教信仰。对于西方小说蕴含的宗教信仰,林译采取了保留、删减和改写相结合的做法。《黑奴吁天录·例言》解释说:“是书为美人著,美人信教至笃,诸多以教为宗。顾译者非中人也,特不能不为转述,识者谅之。”而删减处理则是为了“删繁就简、以便读者”,“是书言教门事孔多,悉经魏君节去其原文稍繁琐者。本以取便观者,幸勿以割裂为责”[20]229。张佩瑶指出,林译小说保留宗教价值观有以下几种形式:(1)书中人物引用《圣经》或吟唱圣诗抒发情感的内容都保留译出;(2)书中人物以宗教为托词对社会不公现象(比如奴隶制)做出辩护的很多内容都保留译出;(3)对小说中人物涉及宗教内容的心理活动,很多都予以保留;(4)小说中提到上帝God、the Lord等时,大多以“天主”对译,虽然这一话语形式与“上帝”这个现已固定的表达相比并不能完全传达原文的所有内涵,但是其所蕴含的基督教思想已充分体现。[28]
林译小说话语价值观承载的另一面是将“礼、义、孝”等中国传统价值观植入西方小说进行文化改写。
以“礼”改写西方价值观的话语有多种体现,如在涉及长辈与晚辈、丈夫与妻子、朋友之间关系时,都有以“礼”这一概念来改写的例子[29]。在《黑奴吁天录》中,原文“I honored you so much, and hoped that you might one day honor me”,本意为妻子要求丈夫以同样的方式尊重自己,林译改为“然尚希冀顺谨恃君箕帚,附君得名,予愿已足”。另有一处将原文My mother went (我母亲过去了)译为“吾母即以礼延入”。
“义”主要体现为人的思想与行为遵循的道德标准和规范。林译小说以“义”改写西方价值观的情况同样大量存在,“义”字的出现频率非常高,如“义宜相卫”“在义亦当以往”等,有时甚至在标题里直接以“义”为小说主题,如雨果所著Quatrevingt-treize,原书标题本意是数字“93”,郑永慧译为《九三年》,林纾译为《双雄义死录》。在《块肉余生述》中,原文多以西方基督教的“博爱、仁爱”精神为价值观导向,林译以“义”的伦理思想进行改写。例如,原文斯提福兹与大卫对话中提到老渔辟果提先生,说他:“In short, his house is full of people who are objects of his generosity and kindness. You would be delighted to see that house-hold.”董秋斯译为:“简而言之,他的住宅中住满了接受他的恩惠和仁慈的人们。你一定喜欢见识见识那一家人。”[30]林译则为:“综言之,家有数口,均非己之妻子,悉以义育之。”[31]明显赋予老渔“重义崇德”的伦理色彩。
以“孝”伦理观改写西方价值观,则常以“孝”为小说命名。《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sity Shop)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小说,描写的是老古玩店主吐伦特和他美丽、善良的外孙女耐儿相依为命的故事,林纾将书名译为《孝女耐儿传》,强化“孝”的价值观。林纾将哈葛徳的Montezuma's Daughter(蒙提祖马的女儿)译为《英孝子火山报仇记》,而1982年林长路译为《托马斯复仇记》。林纾还将克力司蒂·穆雷的The Martyred Fool(殉难的傻瓜)译为《双孝子噬血酬恩记》,将Dr. Johnson and His Father(约翰逊博士与其父)译为《孝子悔过》。其他带有“孝”字的小说还有《孝友镜》《孝女履霜记》等。至于小说叙述中的“孝女”“孝儿”话语,则有多处体现。
总之,林译小说话语中的思想承载是西方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融合。林纾一方面借助翻译引介西方具有现代意识且在他看来是先进的价值观,如实业救国、尊重人性、倡导自由等,又基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或出于迎合当时中国封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需要,在翻译中表现出中西价值观并重的思想承载。
一. 话语形式的融合特征:以弹性古文译西方小说
二. 叙事方式的融合特征:史传叙事与西方小说叙事结合
三. 思想承载的融合特征:东西方价值观共载
-
从以上论述可知,从话语形式、叙事模式和思想承载来看,林译小说都体现出一种融合话语的特征。所谓“融合”,是指既包含源语言文化元素又顺应目标语言文化习惯,并兼具两种语言文化特质而将其有机融合的一种话语方式。在话语形式上,林纾采用的是当时知识分子普遍习用的古文。但他采用的并非是纯粹的古文,而是包含外来新术语、新概念、流行语、音译词、部分欧化句式的弹性古文,将史传笔法、古文词法和句法与西方新名词、新表达和欧化句法融合,构建了适合西方小说的话语形式。从实践效果来看,这种弹性古文受到了当时主流读者的普遍欢迎,甚至起到了提升原文质量的效果。在叙事方式上,林纾创造性地将中国史传叙事和西方立体交叉叙事融合起来。在思想承载方面,林译小说将西方的宗教、社会、政治、法律等思想与中国传统礼仪和儒家思想融合,在选择性地传达原文思想的基础上植入“礼、义、孝”等中国传统价值观。这种融合话语模式对当时以士大夫为主的林译小说读者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既符合他们的阅读习惯又为他们带来了众多新的知识、理念和文化价值观。
林纾所处的世纪之交,正是中国由旧转新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关节点,学习西方,以西方民主、科学等现代话语构建中国的现代化话语,是当时林纾面临的时代主题。而在21世纪的今天,当中西话语严重失衡、中国学术话语普遍失语、西方话语霸权盛行之时,我们的对外话语体系构建面临如何“走出去”的问题。以史为鉴,从林纾话语构建中,可以尝试探索当前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融合之道。
-
何为有效的话语形式?能准确表达话语者意图表达的思想内涵,易为话语接受者所接受,能实现有效传播的话语,便是有效的话语形式。在文言作为文学主流话语的时代,林纾选择了以“弹性古文”为核心的“融合”文言话语,将西方现代小说理念融入文言话语中,成功地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开启了现代小说话语模式。当前,要实现中国话语的有效构建,需要找到合适的、有效的话语形式。这个有效的话语形式应当具备以下特征:内容的充分性、表达的准确性和传播的有效性,能充分传达中国话语的内容和内涵,准确表达中国话语的价值取向和立场观点,从而在国际主流媒介和群体中得到有效传播。
进入全球化以来,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lingua franca),是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开展国际交流的主要媒介,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之一,甚至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国际组织的唯一官方语言。在学术研究领域,1996年全球91%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用英语发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用英语发表的成果在1995年也高达83%[32]。全球最顶尖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期刊都以英语出版,很多学者都努力寻求用英语发表论文以使其成果获得国际传播[33]。因此,英语理应是中国话语构建最重要的媒介语言。中国话语的英语构建,当然是以标准、规范的英语为基本前提,但并非一定要完全按照目标语言文化“标准”对中国话语进行“削足适履”的改造。话语构建的核心是增强话语权,以话语权为核心的话语建设,不能受“归化或异化”二元对立思维的限制,过于“异化”的跨语言话语表达,将使话语传播效率大大降低,而“归化”的译法则因过于依从目标语言规范而导致始发语话语权的丧失。正如苏静、韩云波在论述中国侠文化“走出去”问题时所作的论断一样:对中国侠文化的“归化”翻译,实质上是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操控下通过翻译对西方价值观与信仰的迎合,只能造成源语言文化信息传递的缺失[34]。
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英语也有很多国别、区域变体,被很多学者称为“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35],与不符合标准英语表达习惯、具有一定错误成分的“中式英语”(Chinglish)不同,很多学者主张以“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作为世界英语的中国变体[36],即“操汉语的人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反映中国文化、具有中国特点、能被英语本族语人理解并接受的英语”[37],包括反映中国价值观的文化概念、体现中国人文化心理的表达方式和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术语体系等。为了增强话语权、确保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得到准确表达,本文主张以中国英语作为中国话语国际表达的核心。话语构建背景下的中国英语,是在表达方式和解释权“以我为主”的前提下,选择既符合英语表达规范、又能完整和准确传达中国文化内涵、富有中国特色的“融合式英语”。王银泉认为,中国英语在世界通用英语的基础上融合了中国特有的表达,其存在的客观合理性已得到普遍肯定,可彰显我们的话语地位和话语主权,理应成为中国对外传播和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载体[38]。以中国英语为表达形式的话语实践,在近年来的中国党政文献翻译(如十九大报告[39]、政府工作报告[40]等)、多语种“中国关键词”项目、“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等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有效的探索,形成了一批中国治国理政新思想、中国关键词、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准确表达和阐释,已成为国际媒体表达的主要用语。
-
话语建构的有效性还取决于叙事模式,即采用何种恰当的言说方式来实现话语权的确立并能为话语对象所接受,这涉及话语习惯的解构与重建。任何时代的话语建构,都蕴含着推翻固有的、人们已经习惯的言说方式并重构新的话语方式的过程。在林纾所处的由旧转新的时代,他面临的是如何协调中国史传叙事与西方现代小说立体交叉叙事之间的矛盾冲突,实现中国小说叙事的现代转型。根据上文的分析,林纾巧妙地将两种叙事融合起来,如今看来,这无疑是一种成功的选择。
当前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面临的是对内话语和对外话语两个侧面[41],蕴含“中国问题”和“中国眼中的世界问题”[2]。近代以来,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抢得先机,依赖在现代科技、文化思想、学术研究方面的成果,形成了西方话语的优势地位,产生了“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惯性。这一过程从物理时间而言,恰好是中国走向衰弱的过程,在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科技界等各个领域形成了“西强我弱”的文化心理,产生了在解决中国问题时一切向西方学习、在看待世界问题时以西方观点为标准的惯性思维和盲从心理。这是中国话语在全球话语体系中整体缺失的根本原因,也是当前对外话语体系构建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要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思维以实现中国话语的重构,需要突破前述思维弊端,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一是确立中国话语的文化自信。中国话语自信既来自五千年传统积淀的文化自信,也源于中国道路作为“文化自信的现实展现,其丰富的实践为文化自信的生成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文化素材”,又为“中国道路的开辟、探索和继续前进提供了优质的文化基因、精神内核和思想动力”[42]。有了中国文化自信,中国话语建构就有了形成“中国化”标识性话语的坚实根基[43]。二是形成中国话语的世界关切。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话语的终极目标要么旨在消化吸收西方话语来解决中国问题,要么关注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以思考如何应对,形成中国本位的反应式学术态度。要实现中国话语的成功构建,就要改“中国本位”为“世界本位”,将“中国情怀”拓展为“人类情怀”,深入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仅解决中国问题,更要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关切和普遍问题,这样才能具有更高的格局和更坚实的立足点,与西方话语一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三是要树立中国话语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参与和共融。话语构建蕴含着话语权的争夺,必然会遇到障碍和阻挠。在此过程中,需要尽可能化解话语冲突和急功近利思想,以参与、对话、包容和竞争思维,建立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的沟通渠道,形成对话平台,形成共现与协同,才能在交流与竞争中让中国话语在全球话语体系中发声并成为其有效构成部分。
-
思想的承载和传播是话语构建的终极目标之一,也是话语权争夺的关键所在。在目前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西方中心主义语境下,中西方的价值观对抗和冲突是中国话语构建的最主要障碍。近年来,尽管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共存仍是世界主流,但在近期,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少部分国家和政治派别以“狭隘的政治立场”为出发点,夸大意识形态的对立,挑起“新冷战”思维,推动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导致国际话语体系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愈加突出,使中国的对外话语构建面临更大挑战。
从长远来看,全球化和多种价值观的交流与互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文明的发展本身就需要多种文化和价值观的共存。认为某种文化或价值观超越其他价值观的立场是一种为了某种利益而采取的话语“霸权”策略。因此,我们的对外话语构建需要采取三种思维。一是以包容的态度看待多元化的价值观存在。由于历史传统影响,西方形成了一整套相对稳定的价值观,中国在数千年文明积淀之下也形成了一套基于中国文化的价值观体系。中西方的价值观既有差异,也有类似、接近或交叉之处。以融合话语为指导的话语构建,就是要充分利用相似和相通的价值观搭建沟通的桥梁,“采取一种开放性、生成性、真正理性建构的”心态[44],实现中西方的对话。二是在价值观和话语冲突的语境下,保持自我定力,清醒地认识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总体趋势,构建立足长远、具有可持续性的话语体系规划,将中国文化优秀文明成果和价值观作为对外话语构建的核心竞争力以及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有效方案,通过实践让全球公民理解中国文化价值观所具有的包容性,以使中国话语有效融入世界话语体系。三是以互补的心态看待中西方价值观的共存。全球的话语,应该是蕴含包括中西方话语的复杂综合体,并非只允许一种话语体系的存在。我们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并非要以中国话语取代西方话语,而是要在全球话语体系中增加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提供解决全球问题的另一种方案。同时,这样一种融合话语价值观,还应该欢迎除西方话语、中国话语以外的其他话语及其价值观,如来自印度、中东、非洲等全球各地的话语及其承载的价值观。只有来源广泛、视角多样、文化基础广阔的话语体系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话语体系,也才能真正为解决全人类各种复杂问题提供全面、多样的解释和解决方案。
一. 构建以中国英语为核心的中国话语国际表达
二. 构建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中国话语言说方式
三. 构建中西方价值观互鉴的中国话语思想承载
-
在中国由旧转新的现代性转型之初,林纾以弹性古文表达西方概念,将史传叙事和西方现代小说立体交叉叙事结合,对西方价值观进行选择性构建并附载中国传统价值观,体现出话语形式、叙事模式和思想承载上的融合话语特征,是其“引进来”话语构建、开启中国现代性成功的关键所在。“引进来”与“走出去”是在同一个坐标体系里发生的两个异向同构、本质上具有相同内在属性的话语构建。以林纾的“引进来”话语构建为鉴,当前中国的“走出去”话语构建也应考虑融合话语的有效性。在话语形式上以既符合国际英语规范又具有中国特质的中国英语为主要表达手段,在叙事模式上吸取中国传统精髓与适应国际话语模式相结合,在思想承载上以中西方价值观的交流对话和互鉴互补为核心,实现语言形式、言说方式和思想承载的融合话语构建,方能避开话语构建中的直接障碍,化解冲突,在全球话语体系中逐渐确立中国话语的有效地位。
在如今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各种带有不同目的的话语纷繁呈现,话语权的争夺和由此引发的民族、国家、机构和群体之间的分裂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逆全球化和新冷战思维频频出现,多年以来形成的全球体系和文明间的交流沟通渠道遭遇前所有未有的挑战。在人类面临如此史无前例的灾难而尚未找到完全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之际,全球团结协作并从不同角度寻找解决方案本应是战胜疫情和解决疫后负面影响的最有效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融合”而非“分裂”、“多元互补”而非“彼此争斗”的话语模式,将对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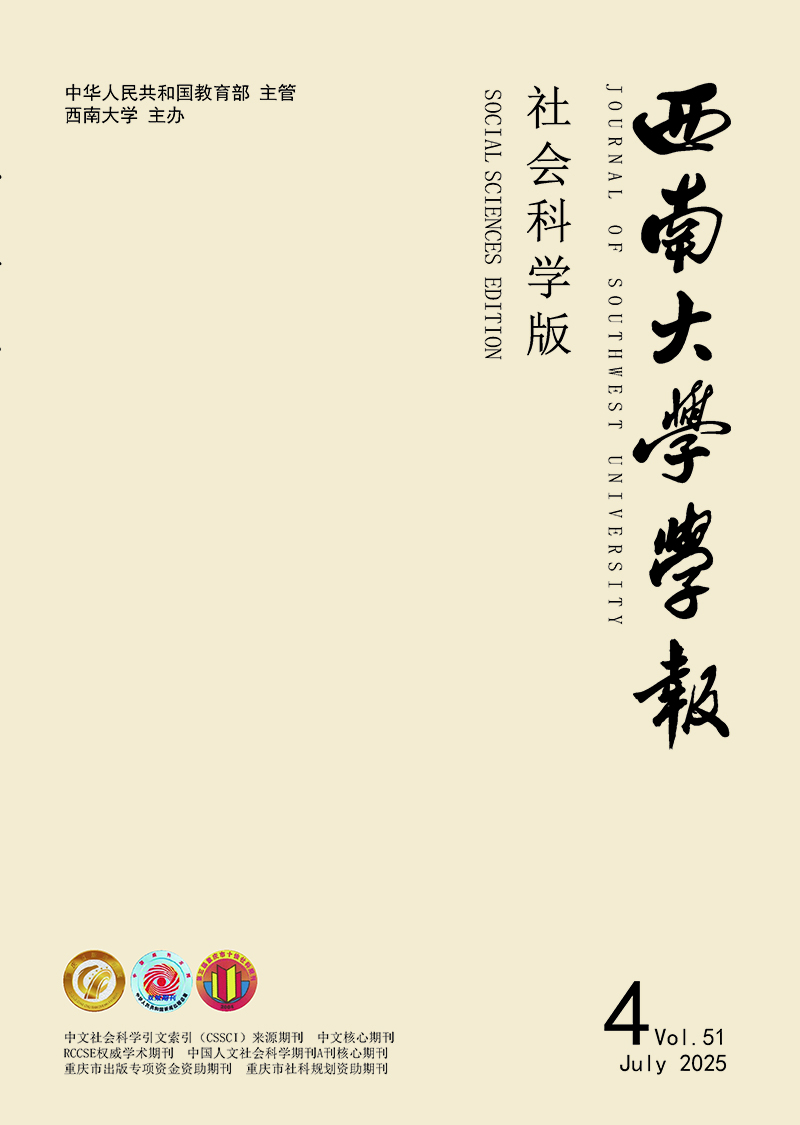




 DownLoad:
DownLoad: